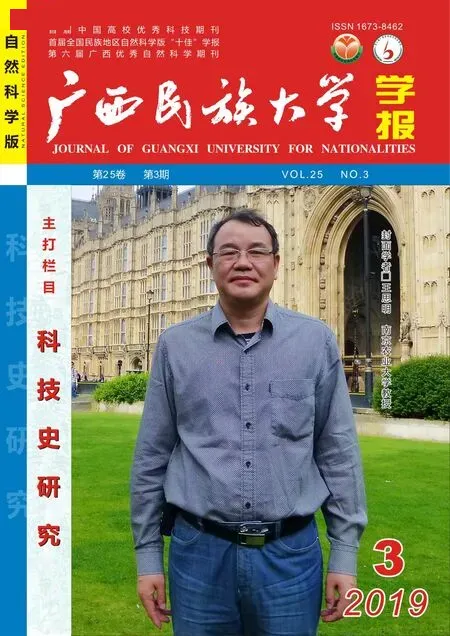挥毫奋笔书农史整铧修犁拓稼田*
——王思明教授访谈录
石慧王皓问王思明答
石慧(以下简称“石”):王老师,您好!广西民族大学万辅彬教授长期致力于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刊载科技史家访谈录,以搜集、整理、保存科技史研究者的访谈资料.此次我们也是受万老师的嘱咐对您进行访谈.
王思明(以下简称“王”):你们好!几年前,万辅彬先生曾提及希望给我做个科技史专家的访谈,当时我婉言谢绝,建议万先生采访一些科技史界的前辈,他们有开创之功,学术积累丰厚.我自认在科技史领域建树不多,达不到树碑立传的程度.但是万先生解释,专家访谈不单纯是介绍个人,更多的是希望通过个人的学术经历或学术见解,审视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方向.我觉得万先生所言有理,通过访谈让相关学者或读者了解科技史和农业史发展的历史脉络,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万先生说你们曾是他的研究生,后来又在南京继续读书和工作,所以就请你们来做这次访谈.
1 学承古今三师启术通中西两洲连
石: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作为万老师和您的学生,很荣幸能有这样一次跟您学习和交流的机会,那么请先谈谈您的学术成长经历吧.
王:我之所以会走上从事科技史和农业史研究的道路,与三位前辈学者的引导和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位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周尧教授,我曾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追随周先生学习和工作八年.周先生早年留学意大利那波里大学,在世界昆虫学权威西尔维斯特利(F.Silvestri)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周先生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在两个领域贡献卓著,享有国际声誉.一是昆虫分类学研究,他不仅发现和记述了众多昆虫新种,还提出了自己的昆虫分类系统,成为影响广泛的三大昆虫分类系统之一,在国内高校普遍被采用;二是开拓了中国昆虫学史研究,他是国内最早系统从事昆虫学史研究的学者,1957年即撰写了《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昆虫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80年修订后以《中国昆虫学史》之名再版,受到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昆虫学家朱弘复、赵修复,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等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亦被日本昆虫学家译成英文,在国际昆虫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第二位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郭文韬教授,郭先生是著名的农业科技史专家,也是南京农业大学科技史学科点学术带头人.郭先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农业科技史的研究,尤其是在土地制度史和大豆栽培史研究方面.另外,郭先生也非常注重农业技术哲学的研究,他写过一本专著《中国农学思想史》,认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应从技术、生产角度去梳理传统农耕技术背后的一些思想观念和哲理,探讨传统农学中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他将农史研究与现代农业发展结合起来,分析现代石油农业、工业农业的一些弊端,撰写了《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一书,获国家图书出版奖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除上述两位中国学者前辈外,还有一位外国学者对我学术生涯影响深远,他就是美国的皮特·丹尼尔(Pete Daniel)博士.丹尼尔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担任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农业部主任,也担任过美国农史学会主席、美国南方史学会主席、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丹尼尔也是美国农村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环境史研究的奠基者之一,闻名遐迩.作为第一个中美联合培养的农业史博士,1994年我获得美国史密森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奖学金,在丹尼尔教授的指导下从事中美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他为了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研究条件,让我住在他离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不远的家中,给我一辆自行车,并亲自陪同我骑行,以熟悉到博物馆和国会图书馆的线路,他的情谊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以后,我曾邀请丹尼尔先生来南京访问,并陪他前往北京参加学术研讨会,时任中国农史学会会长、原农业部副部长郑重曾专门与他在农研中心座谈并请他吃饭.
石:这三位前辈都分别是中国和美国学术界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您能详细说说他们都分别对您的学术成长和之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吗?
王:这三位前辈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在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反映在方方面面,最重要的不是知识和见解,而是学术视野、研究思路和治学风范.周尧先生让我认识到人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不能脱离自然而生存,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农业活动,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要跟动物、植物等各种各样的生物打交道.就比如说昆虫,有益虫和害虫之分,农业生产中怎样使害虫被控制在不大规模发生的程度,保持生态合理的水平,减少了农业灾害,就增加了农业的产量.另外像家蚕、蜜蜂、白蜡虫之类的益虫,可以直接给人们带来财富和生存资源.所以,害虫的防治和益虫的利用,反映出的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人类应该培养天人合一、用养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郭文韬先生专注于中国传统农业,他让我认识到中国传统农业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常常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发展远远不止五千年,众多考古发掘证明,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和小米.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无论是北方旱作农业,还是南方水田农业;中华传统文明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农业文明,农耕是中国一切文化现象、一切文明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就离不开对中国传统农业的考察.
丹尼尔先生虽然主要研究美国史,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他让我知道文明既有区别,也有相通性.文明的特色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显现.研究者不能画地为牢,而应将研究对象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视野.这一点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的观点颇为相似,民族国家的兴起,让人们习惯以国家为历史研究的单元,但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地完整讲述“自己的故事”.丹尼尔让我关注到东西方农业历史文化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尤其是为什么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会出现分野,这种分野背后其深刻的经济、技术和环境的原因是什么.
石: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美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在当时外文资料获取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您是如何克服困难进行研究的?
王: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农业生产大国,中国是农业古国,历史悠久,传统农学曾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到了19世纪以后逐渐衰落.相比而言,美国农业在短短两三百年间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重大转变.美国农业有三个历史传统:第一个是印第安农业传统,据美国农史学家拉斯姆森(Wayne D.Rasmussen)统计,包括玉米、马铃薯在内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农业发明大约占了美国农业产值的50%;第二个农业传统就是早期西欧移民带来的欧洲农业传统;第三个传统是建立在近代科技基础上的近现代农业传统.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美国农业丰富多彩,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强国.当时我想了解为什么美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巨大的历史转变,而中国为什么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美国的农业发展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所以我就选定了《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题目很大,需要的资料浩如烟海,好在有很多学界前辈和同仁的热情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研究任务.除丹尼尔博士外,在资料搜集和研究中给予我多方面帮助的还有美国农业部农史研究室前主任拉斯姆森先生,加州大学农史研究中心主任林彼德(Peter Lindert)教授、Mortten Rostein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马若孟(Ramon Myers)教授,等等.《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2000年由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出版.
石:您的研究不同于一般区域或国别农业史研究,而是非常注重不同农业系统之间的交流与比较,这种视角有什么独特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王:是的,文化发展是一个过程,文明并不是孤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一直都在相互影响.例如美国农业、美国的文明本身就是混合体,美洲本土文明最初是印第安文化,后来通过五月花号第一批移民的来到,给美洲带来了西欧的文明.但是当时的欧洲文明并不是真正的工业文明,最初去的很多都是一些罪犯和生存不下去的人,并没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和很强的资源背景,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欧的传统农业.美国农业真正的发展是在19世纪中期南北战争以后,那时候美国开始向近代农业就是马拉农业的半机械化方向发展.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农业转变,真正完成的节点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所以,在短短的150-200年的时间内,美国农业就完成了从原来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历史过程.回过头看中国也是一样.首先,中国的南北东西都存在很多并列文化的集群,我们说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主要是指北方旱作农业的小米文化,实际上与之相并行存在的还有长江流域的特色稻作文化,在更北方的红山文化也是一样的并行关系.另外,中国历史上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我们很多作物都有胡字,比方说胡椒、胡麻、胡桃等,这都说明它们是外来的.到了隋唐宋元和明清时期就更多了.现在我们的四大粮食作物中有三个是外来的,小麦四五千年前就由西亚传过来,玉米和马铃薯也都是美洲传来的作物,包括五大油料作物也有三种是从外面传来的.此外我们还有很多作物是来自于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费孝通先生曾说中华文明就是多元一体,李根蟠先生把这一命题进一步发挥,认为中华农业文明是多元交汇的体系.我是赞同这个说法的,中华农业文明并不是单纯汉民族创造的文化体系,既包括了南方、北方文化的融合,又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括了中国和外国农耕文化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华农业文明多元交汇的文化体系.所以我从他们的研究中体会到,应该用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农业发展的历史,不能太局限于自己的一块小小的自留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把研究重心放在世界农业史和中外农业交流史这些方面,如果不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去解读,很容易造成狭隘的理解和偏见.如果不放在大的文化系统中,所有中国的东西都是独特的;而放在更大的视野中看,往往会发现很多共同性.
2 金陵风雨延一脉农史沧桑跨百年
王皓:您进行农业史研究多年,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农业史学科的发展历程吗?
王:传统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平民琐事、经济生活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农业历史虽然重要,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并不久.农史研究学科化的建设开始于20世纪初期的德国,后来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展.美国后来居上,1919年成立“农业历史学会”,又在1927年创办了《农业历史》(Agricultural History)杂志,美国边疆学派的创始人弗雷得里克·特纳(Frederick.J.Turner)担任学会的首任会长,之后农史研究在美国迅速发展.此后,英国、荷兰、丹麦、日本、韩国等国也相继建立了农业历史学会并开展了相关的农史研究.中国的农业史研究也是受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慢慢开展起来的,最早有些零零星星的研究工作,真正开始建制化研究应该是从金陵大学农学院开始的.1914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科建立,1920年金陵大学跟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合作,启动了中国古代农业资料的搜集工作,在金陵大学建立农业图书研究部,开启了中国农业史建制化的过程.
王皓:请问是什么样的原因和契机在金陵大学建立了农业图书研究部?这期间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王:这实际上跟20世纪初期美国来华的农学家有关系,当时美国植物学家史文格(W.T.Swingle)在中国采集了很多农作物和植物标本寄回美国,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古国,有很丰富的农业遗存.因此积极地向美国国会图书馆和美国农业部推荐,应该把中国的这些古农书系统地收集起来,一起送到美国或者翻译出来让美国学习借鉴.在史文格和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思娄(Reisner.J.H)的积极推动下,金陵大学与美国农业部和国会图书馆决定合作建立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金陵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大学,在当时的十多所教会大学中属于A类,是唯一一个可以跟美国康奈尔大学学分互认、互换学生的大学.1920年建立农业图书研究部开启了中国农业史建制化进程,1921年的春天美国国会图书馆派王德女士来到金陵大学主持农业图书研究部工作.1924年万国鼎先生接任王德女士成为农业图书研究部的主任.
石:您曾说万国鼎先生对于中国农史学科有开创之功,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万国鼎先生吗?
王:万国鼎(1897-1963)先生,江苏武进人,是中国农史学科的主要开创者.曾任金陵大学农林学会会长、《金陵光》编辑、五四运动议事部副主席、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1920年毕业后留校,协助钱天鹤先生从事蚕业推广工作.他的第一篇农史论文就是关于中国蚕业史的,1924年万先生任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1932年任农业经济系教授、农史研究组主任,他给金陵大学学生专门开设农业经济史课程,甚至专门翻译了诺曼·格拉斯(Norman Grass)的《欧美农业史》作为教材,他的研究不单单局限于农业史,他在历史方面的成就也很高,在民国初期曾编过《中国历史纪年表》,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万国鼎先生在农业历史研究的诸多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曾经撰写了一部《中国田制史》,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万国鼎先生曾担任“国立政治大学”地政系主任,创办《地政月刊》并担任主编,因为万先生是中国地政研究的开创者,所以我们去台湾访问时,台湾政治大学把万国鼎先生看作是他们的鼻祖.也正是因为这样,李约瑟先生了解到万国鼎先生在农业历史方面的建树,所以专门请求到金陵大学与万国鼎先生进行交流,李约瑟先生一共来过南京农业大学(或前身)三次.有人说李约瑟先生最早提出“李约瑟难题”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出版之时,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
石:请问您认为更为准确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呢?
王:事实上李约瑟先生最早提出“李约瑟难题”应该是在20世纪40年代.李约瑟先生在剑桥大学工作时,受鲁桂珍、王玲等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对中国的科技史产生浓厚兴趣,后来他作为英国驻华的科技参赞和中英科技合作馆馆长,拜访了很多中国科技史家,包括竺可桢、万国鼎和石声汉教授.1944年他应邀在重庆的中华农学会会堂做大会报告,题目是“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农业”(Science and Agr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West),就是在那个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李约瑟难题”,15世纪之前中国在诸多科技领域领先于世界,但在近代以后就落后了,中国为什么没能保持这种优势,走上近代科技创新之路?他也尝试从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王皓:那么中国的农史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由一批前辈开创之后,又是如何逐渐发展壮大的呢?
王:新中国建立以后,因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成对立之态,西方封锁中国,中国要想发展就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多渠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另一方面要挖掘中国的传统知识宝库.1955年4月,农业部在北京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全面部署开展研究、整理、出版工作.万国鼎同与会专家一起,呼吁尽快建立整理祖国农业遗产的专门研究机构,以便有组织、有领导地开展农史研究工作.同年7月,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和农业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支持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农业历史文化专门研究机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南京农学院宣告成立,万国鼎先生被任命为第一任主任.
“文革”期间,南京农业大学迁入扬州与苏北农学院合办.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因为与中国农科院双重领导,没有搬迁扬州,而是并入江苏省农科院,成为江苏省农科院农业技术史研究室.1981年南农复校卫岗后又重新进入南农.2000年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下,农业遗产研究室人、财、物划入南京农业大学,在整合相关研究力量和学术资源的基础上组建了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继续保留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牌子.
王皓:所以以此来看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历史是否可以一直追溯到1920年?
王:是的,所以2020年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建立100周年,为什么把1920年作为起点呢?学术机构的历史发展界定应该看是否具备几个延续性:组织机构的延续性、研究队伍的延续性、目标宗旨和主要工作的延续性.早在1920年,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即开始系统搜集、整理古农书和研究农业历史,与其后的农业历史研究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有直接传承关系;从1920年起万国鼎先生即开始农史研究,不久又主持农业图书研究部和后来的农史研究组、农业遗产研究室工作,主要研究人员薪火相传,延续至今;从农业图书研究部开始,古农书整理与农业历史研究就一直是研究院主要工作,这一目标任务传承至今,所有学术资源留存在今天的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可见,今天的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与1920年筹建的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为了更好地配合院庆活动,2020年5月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学术年会将在南京农业大学举行,由我主编的《中国农史研究一百年——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史》也将在会前由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
王皓:您认为关于中国农业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应对整个农业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王:中国农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40年代,其特点是研究工作刚刚起步,研究机构零星分布,人员稀少,主要是靠个人兴趣和资料整理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金陵大学《先农集成》编辑工作.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其特点是国家大力支持,农史建制化取得重大进展,农史专业研究机构陆续建立.这一时期突出成就是学术资料建设和古农书的整理研究.农遗室建立以后,曾经派了40多个专、兼职人员,到全国各个公私图书馆把地方志中有关农业史的资料全部手抄下来,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方志农业资料库,被誉为中国农史资料的“万里长城工程”.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各农史研究机构对重要古农书进行了系统梳理校释,为之后的农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其特点是在古农书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开展农业科技史和农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成果丰硕,例如由遗产室主编的《中国农学史》获得了农业部的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获中国科技进步三等奖,缪启愉先生的《齐民要术校注》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的二等奖.此期出版的稻作、园艺、植保、畜牧、水利等各个方面的技术史研究专著不下于1000种.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农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由专题史研究转向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农史研究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生态学密切结合,农业起源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外农业交流研究、世界农业史研究成果丰富.我们研究院也陆续出版了《中美农业发展比较研究》《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等专著,并开展“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系列研究;二是从单纯静态的文献研究向活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转变.专题农业历史博物馆研究陆续建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文化部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利部开展水利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农业部也建立了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并启动了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遴选工作.我们研究院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农业文化遗产学》教材,《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名录》(上、下)、《江苏农业文化遗产调查研究》《江苏茶文化遗产调查研究》《中国传统村落记忆丛书》等著作,其中6本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三是农史研究与当今农村发展结合.我们研究院编撰出版了《中国传统村落与乡村振兴丛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希望为乡村振兴和农村文化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王皓:我们关注到,现在的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不仅在中国农业史研究中独树一帜,而且在国际农业史领域也有一定的影响力,请您谈谈研究院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工作和成果.
王:思想在碰撞中升华,学术在交流中发展.我们非常重视学术交流工作,尤其是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对标国际前沿,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我们很早就与美国普渡大学建立了学术联系,2014年我应邀去普渡大学讲学和访问,且专门签署了合作协议,共同建设“南京农业大学—普渡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我们互派学者、教师、学生展开学术合作研究,每年在南农和普渡主办轮值会议,迄今已召开了四届.我们与英国雷丁大学合作,建立了“南京农业大学—雷丁大学农业起源与传播联合中心”,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课题开展合作研究,分别在南京和雷丁联合举办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十多年前,我们就与东京农业大学合作,建立了“中日农业史比较研究中心”,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不少教师和研究生得以到日本东京大学和东京农业大学访学和进修.2017年,因为前些年国际合作方面的基础,我们积极申报并获批教育部区域国别研究基地“美洲研究中心”,目前在中国与美洲地区农业交流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3 传承文化护遗产关注社会谱新篇
石:您刚刚回顾了中国农史学科发展的历程,对于学科的未来发展,您又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首先,就像你们刚刚了解到的一样,中国农业历史研究已经有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一般资料工作的梳理、专题和专门史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和完善.最近这些年我们把精力放在综合史的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中外农业交流的研究方面.在综合史的研究方面,我们更侧重于把政治的、技术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多方面因素融为一体,单独地从某一方面看历史,往往只能看到一个局部,很难获得一个整体的发展概念,所以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其次,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现在国家越来越关注这个方面,前面已经讲到,住建部、文化部、农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等不同的系统都在做.所以可以看出,文化遗产是人类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很多部门都在关注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部门可以包打天下,而我们学者跟行政管理部门不同,我们的研究不受条条框框局限,我们从学理上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是以人类农事活动为对象,集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综合体系,所以我把农业文化遗产分为十个大类,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应该说这是我们理论上的创新,在国内是首次提出农业文化遗产新的概念.第三,农史研究要想获得社会的高度认可或者更大的关注,关起门来做学问是不行的,做的东西孤芳自赏、自说自话是没有前途的,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在于让社会大众知晓,并与他们自身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关系,这样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石:我们非常赞同您刚才提到的农史研究要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我们也了解到您和同仁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请您说说这方面的工作内容.
王:这些年我们比较关注农业历史研究如何在当代的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在农业和农村,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第一个就是产业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础,如何实现产业振兴呢?靠发展高投资的高技术的是不太现实的,农村本身缺乏技术、缺乏资本.所以要转换思路,尽可能依托历史文化资源,而地理标志产品就是很好的资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动员并利用好经过千百年积累传承的地理标志文化和产品,来让农民发家致富、助推农村发展.例如我们跟北京电视台合作专门做了54集的大型电视栏目《解码中华地标》,推出中国第一部《中国地理标志品牌发展》蓝皮书,今年还将推出第二本.今年12月我们还计划与农业部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和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合作举办“中华地标品牌国际推荐会”,为中华地标走向世界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
除此之外,2018年我们与江苏新华日报集团和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合作,建立了“特色田园乡村协同创新中心”,也是想致力于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服务乡村社会,联合举办过三次相关学术研讨会.
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目前运河沿线8个省市都在积极推进运河文化带建设.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由省委书记娄勤俭牵头,组建了领导小组,成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在南京农业大学建立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农业文明分院”,希望通过对运河农耕文明调查研究,助推运河文化带建设.
最后一个,也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一直在推动的一个学术基础工程,即农史学术资源的数字化.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不断纵深发展,原来那种完全的依托历史文献,靠个人奋斗的研究方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以前我们是资料短缺的时代,而现在是知识爆炸的年代,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资料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怎么得到你想要的资料,进而高效地去利用这些资料.信息科技的手段就可以弥补个人这方面的不足.近些年,我们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部、农业部的专项经费,从事农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包括明清方志农业数据库和民国农业数据库的建设,希望通过信息技术把所有相关农史资料数字化,提供给农史研究者更多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数字挖掘和数量化的分析,可以看到原来我们所忽略或者说不容易看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比如通过对比作物出现的频率、分布的地区,以研究作物传播的路径、分布的区域、作物的相对重要性、作物生产的结构和历史变迁等,这些课题都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石:可以看出,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之外,对于未来农业史学科的发展、南农农业史学科的建设方面,您都有深入的思考.
王:如前所述,我的三位导师对我的学术成长有相当深刻的影响.不是说他们给我到底灌输了多少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教会了我怎样去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例如周先生曾经提出“三位一体”的发展理念,他说科研上如果要有所突破和建树,首先要有一个团队和机构长期在这方面耕耘,所以他在民国时期就自己出资建立天则昆虫研究所.其次,有了团队做出的东西发表不了,形成不了影响也是不行的,因此还要有学术交流和发布的平台,这也是他陆续创办《趣味的昆虫》《昆虫学研究集刊》《昆虫分类学报》的重要原因.最后,科研成果欲获得社会支持不能脱离大众的理解,还应该做一些科学传播和推广的工作,这也是他创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和浙江宁波周尧昆虫博物馆的主要考虑.
受周先生启发,我对研究院的发展提出“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即:
一是农史科学研究中心.希望将研究院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农业历史文化科学研究中心,及创新成果的产出地,依托单位就是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包括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南京农业大学美洲研究中心”、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业历史研究中心”、与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合作共建的“中国地标文化研究中心”及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新华日报集团合作共建的“特色田园乡村协同创新中心”.
二是农史人才培养中心.团队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依靠科学研究,团队的稳定和新鲜血液的输送还需要有人才支撑.人才培养中心不光为自己团队,也是为全国事业的发展输送专业人才.人才培养中心分三个层次:一层是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博士后;第二层是培养科技史博士、硕士研究生;第三层是科技史或农业史的通识教育.科技史文理交叉的学科性质使得它成为沟通自然学科和人文学科的理想桥梁,可望在通识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我们的积极努力,目前南京农业大学已经将《世界农业文明史》列入全校6至8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之一,必将对学科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是农史信息资源的中心.做科学研究必须要依托一定的资源,包括了古籍、图书等,现在除了文献资料外内容扩大了,还包括有文物、音像、数据库等.近年来我们在原农业古籍书库和方志农业资料库的基础上,又陆续建立了民国农业资料库、农业文化遗产数据库,在日本北海道前农业研究会会长牛山敬二先生无偿捐赠4000册日本农业图书的基础上建立了“牛山敬二文库”,成为中国研究日本农史的资料中心.
四是农史学术交流中心.我们应该把国内外相关学术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学术事业共同体.目前挂靠农业文明研究院的学术组织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畜牧兽医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江苏农业文化遗产学会、江苏茶叶历史文化学会.除学术组织外,研究院还主办有国家核心期刊《中国农史》杂志,该刊创办于1981年,长期入列CSSCI等国内三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方阵.这些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是研究院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对学科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是农业历史文化传播展示中心.农业历史文化的价值在于它的社会影响,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靠社会大众的共同努力.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关注农业文化遗产,需要在传播展示方面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我们陆续建设了农业历史文化专题网站“中华农业文明网”和中国高校第一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对大学生和社会大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知农爱农的教育,博物馆先后被评为国家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荣获教育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2019年下学期开学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巡回展,首站就放在了博物馆,对社会开放.
总之,长期以来,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主要是围绕这五大中心建设来开展工作.为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十多年前我们就启动了《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下设四个系列,即:《中国近现代农业史丛书》《中国作物史丛书》《农业文化遗产丛书》《中外农业交流丛书》,目前已出版相关著作50余种,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石: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让我们有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再次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