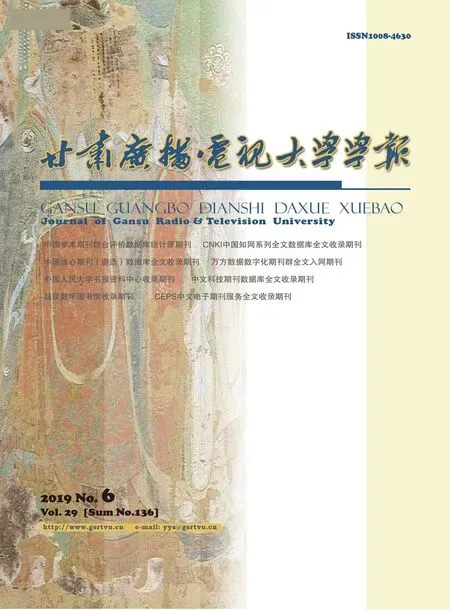从《语法答问》看汉语名词化
李 慧
(辽宁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 110136)
朱德熙在《语法答问》中将兼有名词性质的动词称为“名动词”,将兼有名词性质的形容词称为“名形词”,并认为不改变形式的主语、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和形容词就不是已经转化的名词。“在谓语和谓词性词组后头加上‘的’转化为名词性成分才是真正的名词化”[1]22。即没有“的”标志的动词和形容词,就是在主宾语位置上经常出现,也不能认为它们是已经转化为名词的动词和形容词,不可称它们为名词和动词或名词和形容词的兼类词,最好直接称为“名动词、名形词”。笔者对此观点尚存疑问,故考察了有关名词化的研究成果,企图为汉语名词化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一、对汉语名词化的研究现状
对名词化的不同看法实质就是对词类划分界限的不同看法。近十年来关于名词化及词类划分问题的探讨,基本上传承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看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流派。
(一)名词派
这一派认为句子中转变词性的动词和形容词已经完全变成了名词。比如“进行调查”中的“调查”一词。此时的词类或者说词的性质完全依据此时词的句法功能来判定。此派代表人物是黎锦熙,他的“依句辨品”说掀起了名词化讨论的波澜。彭道生也曾说:“我们应该根据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性质来确定它所充当的成分是名词性的还是谓词性的。”[2]73韩礼德也曾说:“名词化是生成语法隐喻的唯一最强有力的资源。通过这种方式,过程(一致式为动词)和特性(一致式为形容词)被重新措辞为名词,它们在名词词组中担当事物的角色而不再是小句中的过程或者属性。”[3]352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语法对名词化的认识和“依句辨品”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观点都是将“进行嫌犯排查”这里面的“排查”一词看成名词。这里的“排查”受具体语境或上下文的影响已不能受“不、没、未”的否定,不能重叠,不能带结构助词“着、过”,不能带宾语,但可以受数量词修饰,可以受名词修饰。典型的动词特征已经隐去,拥有了名词的区别特征,完全可以判定为名词。近十年的学者如宋荣超(2018)、邓云华(2018)、周韧(2012)、高航(2010)全都可以归类到这一派中。
(二)动词派(或形容词派)
这一流派认为句子中的动词或形容词只是暂时发生了“词类转化”和“语义变化”。动词或形容词原本的意义和语法功能依然大量保留,所以仍然是动词或形容词。这时的词类如果出现在相对来说不经常分布的主宾语句法位置上,就是临时的“名词化”。比如“玩是令人高兴的事”,这里的“玩”就是临时在主语位置上出现作主语,但仍保留动词的诸多典型的区别特征,能受否定副词“不”修饰,能带宾语,能带补语等。这时的动词在实现名词化这一过程时没有上一派彻底。代表人物就是完全反对名物化说法的朱德熙,在老一辈学者中还有王维贤(1987)、姚振武(1996)、裘荣棠(1994),在新生代学者中还有唐昱(2006)、郭锐(2011)等。
(三)中间派
这一派认为当动词(或形容词)在主宾语位置上出现时,自身的词类属性保留,名词属性显现,此时的动词并不是完全转变为名词,名词性质只是属于动词功能的分化,应判定此时的动词是动名兼类词。比如“老师应当批评做错事的同学”,这里面的“批评”就是一个典型的兼类词。需要根据语境来判断词性。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主张设立“动名词”的宋玉柱(2000),有提出非典型类名词的牛然明和高德文(2012),有提出零形式名词化的刘顺(2003),还有刘叔新(2002)、江悦宁(2017)等。
语法学界还有用广义的形态说、鉴定格式和词义·语法范畴来判定“名动词”“名形词”的方法。但在判定例句“这本书的迟迟出版”的“出版”词性时,广义形态说的中心性质不确定。矛盾地将中心划分成两个词性。鉴定格式和词义·语法范畴在界定词性时分歧很大,难以界定“出版”的词性到底是变还是不变。综上来看无论是哪一派都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说法完全正确的系统性力证,所以关于汉语名词化的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一件事。
二、《语法答问》有关名词化的观点
《语法答问》中有关名词化的观点大概有三条。
(一)跳出印欧语系的藩篱,进行汉语自身的思考
朱德熙在《语法答问》中指出:“早先的汉语语法用印欧语的眼光看待汉语……看不见汉语自己的特点,不知道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都是‘多功能’的,不象印欧语那样,一种词类只跟一种句法成分对应。”[1]7朱先生指出了用印欧语看待汉语的不合时宜,区分出了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和印欧语系语言的不同,并且抨击了“名物化”生搬硬套的有关观点,启发后世学者关注汉语自身的特点,找出适合汉语的的语法特征。由于汉语是不依赖于形态变化的表意文字,所以动词和形容词自然具有可以作主语、宾语的“多功能”特性,那么“名物化”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二)坚持用语法功能判定词类
在《语法答问》中朱先生指出:“划分词类的依据只能是词的语法功能。”[1]11“要是根据形态分出来的类并不能反映句法功能,这种分类就没有意义。”[1]12可见,划分词类,语法功能才是标准。比如“他带来一束花”,这里的“花”就不同于“花钱”中“花”的词性。“一束花”的“花”是数量词组修饰的名词,“花钱”的“花”是述宾结构中的述语动词,它们词类的不同归根到底还是依据语法功能的不同而判定出来的。所以在进行语法分析时要依托于具体语境下的语法功能,而不是只从词的意义出发。朱先生还指出:“属于同一个词类的词,语法功能不一定完全相同。”[1]14比如虚化动词“给予、进行、作、加以”它们是可以接名动词的一种形式动词,具有和其他的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不一样的语法功能。
(三)明确区分语法性质和语法特征
《语法答问》指出了语法性质和语法特征的不同,这就为区分“名物化”和“名词化”打下了基础。“名物化”所谓的动词和形容词名词化实际上是动词和形容词呈现出的名词的语法性质,而不是名词的语法特征。而且朱先生在《语法分析讲稿》中也指出:“根据‘什么’的替代作用划出来的‘事物范畴’跟作为名词这个词类的语法意义的‘事物范畴’不一致。”[4]102朱先生认为“名物化”所谓的动词和形容词具有名词特征是因为他们混淆了动词替代后的“事物范畴”和名词词类的“事物范畴”之间的关系,作主语或宾语的动词所呈现的名词特征和名词这个词类的语法特征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这种观点值得吾辈学者借鉴分析。
三、《语法答问》待改进之处
(一)以“的”作为绝对化的形式标记
朱先生在《语法答问》中以“的”作为真正名词化的标志,这和他自己所说的以语法功能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相矛盾。因为汉语的特点是不依赖于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朱先生在《语法答问》中也说:“汉语词类没有这种形式标记,不管放在什么语法位置上,形式都一样,这就造成了词类多功能的现象”[1]9可见朱先生自己先承认了词类的多功能现象,然后才提出了“名动词”“名形词”的概念。那么既然存在具有名词性质的动词、形容词,还以“的”作为真正名词化的标志未免太过绝对了。虚词虽然可以帮助汉语来确定语法关系,但虚词“的”本身存在多重意义。朱先生在《说“的”》中曾说“的”具有三种语素,具有多重性质。如果仅仅是以“的”这样一个汉字作为名词化的标志,那又将语法功能、数量特征的标准放在何种位置上?而且他在《语法答问》中还说:“所以‘的3’可以说是名词性语法单位的后附成分。”[5]这里的“的3”其实还应该细分,要考量“的”的分布位置,前后成分,还要分析动词、形容词加上“的”后的结构关系。所以,只凭一个不加任何说明的“的”就判定“动词/形容词+的”具有名词语法功能是不够有说服力的。比如“团结、博爱与互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里的“团结、博爱与互助”本身是一个动词,但在这里变成了抽象名词而且作句子的主语,“团结、博爱、互助”符合朱先生所讲的“名动词”的分布特点,但它们并没有带“的”,却依然成为了“名词”,可见以“的”作为真正名词化的标志恐怕不妥。再如“诸葛亮的果敢无人能及”这里的“果敢”本身是形容词,但在这里作“诸葛亮”后面的被领名词,就成了朱先生所讲的“名形词”,这句话里的“的”只是名词性单位“诸葛亮”的后附成分,与“果敢”无关,而且也分布在“名形词”的前面,这也证明了以“的”作为真正名词化的标志的不妥之处。
(二)借助“名形词、名动词”的名称来模糊类属问题
《语法答问》第二章在分析“调查很重要”和“我不怕困难”中的“调查、困难”的类属问题时,朱先生先对兼类这种处理方式提出了不满,然后说:“要是采取名动词和名形词的说法,就无需回答这样的问题”[1]25。但最终对于如何判定“调查、困难”的词性类属,朱先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不免让人遐想朱先生是否在逃避对于“名词化”类属问题的判定。在《语法答问》中的“名动词和名形词是具有名词性质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具有动词和形容词性质的名词”[1]25,这种观点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单独出现的名动词和名形词到底如何判定类属,朱先生在这里没有一个明晰的解释。而且朱先生在本书反复强调动词和形容词大多都可以作主语、宾语,此时的动词和形容词不算名词,那么为何又提出区别于正常动词的“名动词”抑或是“动名词”的概念?可见朱先生的心里也是有疑问的。在第二章末尾,朱先生简单指出作宾语的“名动词”的一些特点,但并没有非常清晰地解释“名动词”与“名形词”的结构类型、功能类型、性质类型。可见他还是无法清晰地判定类属问题,故朱先生本章的观点恐有漏洞,有待改进。
(三)混淆语义语用平面的“名物化”和句法平面的“名词化”
朱德熙从1961年开始反对“名物化”的说法,“汉语的语言事实完全不支持名物化的说法,”他说,“在我们看来,名物化的说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在实际的语法教学上也是没有意义的。”[6]52其实,“名物化”从语义上看是将名动词或名形词看成一种“事物”,从语用上看是将它们看成一种“指称”,即处于主宾语位置上的名动词、名形词行动意义减弱,事物意义增强,指称意义增强。而“名词化”是从句法层面上来看动词、形容词向名词性质的转化。比如在“老师不应对学生这般训斥”中“训斥”一词是语义上的打骂类“事物”,是语用上的对打骂这类行为的“指称”,是句法上的名词性质的动词即“名动词”。“名物化”没有形态标记,“名词化”的形态标记也不是绝对要有的。就比如“训斥”这类“名动词”并没有“的”来标志,所以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也是要承认“名词化”“名物化”现象的存在。总之,“名物化”和“名词化”是两个层面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不应混淆,而且应该承认它们存在的合理性。
四、《语法答问》之我思
“名词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麻烦,关键是因为汉语缺少形态变化或者说汉语不需要形态变化即可完成词性转变。朱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的”字这个名词性的标记,只不过有些绝对崇拜这个标记了。“的”字是在继承了古代“底、之、者、所”的语法意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现代汉语中“的”的语素义很多,需要对其进行清晰的约束与界定。下面对“的”字进行一个清晰的阐述,并提出一些有关汉语名词化的原则。
(一)古汉语中的“底、之、者、所”
1.底
在古代汉语中,“底”的语法功能和意义与“的”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元代“底”字已经可以写成“的”。可以说现代汉语中的“的”就是从“底”发展演化来的。《说文解字》:“底,山居也。一曰下也。从广,氐声。”[7]330“底”和“的”经常出现在动词后充当结构助词,而且可以对等。如“不堪问底子规声”和“正在游泳的教练”。“底”和“的”也经常出现在动宾结构后,如“师曰:‘乞眼精底是眼不?’”[8]116“买花的姑娘”。古代汉语中的“底”在充当结构助词时的语法分布位置和“的”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且在语义功能的自指和转指上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师云:‘卧底是,不卧底是?’”这里的谓词加上“底”后语义发生转指。同样,“吃”加上“的”后组成“吃的”语义也由谓词性转为了名词性。此外,古代汉语中的“底”还可以和“的”一样,加在名词、形容词、人称代词、方位词、介词结构、主谓结构及动补结构后作结构助词,虽然这些用例比较少,但也能证明“底”和“的”的相似性以及一脉相承性。
2.之
“之”《广韵》:“止而切,平之章。”“之”在古代汉语中有许多用法,其中有关名词化的用法是作助词,用在主谓结构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使主谓结构名词化,并使主谓结构作整个句子的一个成分。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之”使“大道行”变成了短语,从而充当整句话的主语。这里的“之”不能换成“底”,即“之”和“底”的语法功能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二者具有互补性。但在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却可以换成现代汉语的“的”,即现代汉语的“的”和“之”的关系也非常近,都可以作为名词化的标志。其实,现代汉语中的“的”是融合吸收了“之”和与“之”用法不同的“底”“者”“所”等多个助词的语法功能才发展演变而来的。
3.者
《字源》:“者,章纽,鱼部”。《说文解字》:“者,别事词也。”[7]97作结构助词的“者”最早见于《尚书》,如“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者”不但具有使动词、形容词、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或句子加“者”变成名词性质的功能,还具有为体词性成分作结构助词的功能,如“是释迦佛者”[8]3。这里的“者”就分布在体词性成分后。“者”也是名词化的标志,“者”字也具有转指和自指的语义功能。如“知者乐山,仁者乐水”和“仁者,人也”。但应注意“者”的大部分功能后来被“底”承担了,所以清末的口语中已基本没有“者”的踪影。
4.所
“所”心纽,鱼部。《说文解字》:“所,伐木声也。”[7]420在古代汉语中,“所”常加在及物动词之前,构成一个名词性结构,这个结构可以直接做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如“鱼,我所欲也”中的“所欲”是受事宾语,所以古代汉语中的“所”也是名词化的标志。陆俭明曾说“他所写的文章”中“他所写”应该看作主谓结构“他写”的体词化形式[9],也就是说“所”和“之”同样用在了主谓结构之间,使整个结构变成了名词性质。
总之,古代汉语中的“底、之、者、所”虽然都是名词化的标志,但是它们的语法分布不一样。“之、所”分布在“名形词、名动词”的前面,呈现为“N+所/之+名形词/名动词”的结构。“底、者”分布在“名形词、名动词”之后,呈现为“N+名形词/名动词+者/底”的结构。而现代汉语中的“的”则继承了它们的名词化标记功能,在主谓中间或动词、形容词之后都有分布。
在古代汉语中,动词和形容词也可以不加名词化标志而直接作为名词来使用,这就是所谓的“词类活用”。比如《战国策》:“虽强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强大乎?”这里的“强大”就是临时转变了“力量坚强雄厚”的形容词意思,而临时指“强国与大国”的名词意思。“小弱”也是形容词临时指代“小国与弱国”的名词意思。可见,古代汉语的这种“名词化”也就是词类活用,不是真正的一词多义,不是固定的词类用法,而是为了表达的需要而改变语法性质和语法功能的临时用法。
(二)现代汉语中的结构助词“的”
现代汉语中的结构助词“的”继承了古代汉语“底、之、者、所”的名词化形式标志这一语法功能,既可以在动词、形容词、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及主谓短语的后边,也可以在主谓短语、动宾短语的中间,“的”的语法分布是多种多样的,无论如何分布,都需承认结构助词“的”有使整个结构变成名词性质的功能。
1.从语音层面看
动词分为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单音节动词后面加“的”,由原来的动词转为名词,如“吃的、抢的”。双音节动词后面可以加“的”,也可以不加“的,如“跌倒的是一个女人”“进行检查”等,“跌倒”加“的”后变成了名词,但不加“的”的“检查”也是名动词。
2.从语义层面看
加“的”名词化后的整个词是一起表现出一个意义,不再是单独语素的字面意义,整个词需要意会是表示人称还是表示事物。最明显的是形容词,本来就表示一种性状,但加上“的”后就可以指称名词性质的事物或人物。如“红的”有时指称“钞票”,有时指称“红花”,有时也指“中国人”。“小的”有时指“儿童”,有时指“小东西”。所以变化后的词的意义要从整个词的层面,从上下文语境来理解。
3.从语法层面看
加“的”名词化后的成分可以承担主语、宾语、定语等名词所拥有的语法功能。比如名动词“离开”加上“的”后可以作主语“离开的是我们最亲的人”,作定语“离开的外婆”。中间插入“的”的动宾短语“结的瓜”可以作宾语如“我们是一根藤上结的瓜”。
(三)界定名动词、名形词的类属原则
界定名动词和名形词的类属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范围广大,标准模糊,体系不完备,所以至今都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文的“的”虽然可以看成是名词化的标志,但这个标志也不是万能的。比如“今天也需要的”这里给动词“需要”加上名词化标志“的”变成“需要的”,但此时的“需要的”完全可以不理解成名词,理解成“宴请、检查”等动作类行为也是可以的。类似的例外还有很多,比如“尝、染、晒、踢、抱、演、禁止”等,如“它还有一种功能,即由之人们可以知道自己的感觉正在发生作用,它是‘看的看’‘听的听’‘尝的尝’”;“禁止一切禁止的”“啊呀,相公你听,演的《喜逢春》呢!”。无论是感官动词还是动作动词,无论是单音节动词还是双音节动词,他们加上“的”后都存在没有变成名词的情况,或者说都存在可以不理解成名词的情况,此时的“的”当然不再是名词化的标志。而且许多不带“的”的动词、形容词也可以变化成名词性质,比如双音节动词“分享、宴请”等。它们既可以是“分享经验、宴请宾客”的动词,也可以是“分享资格、宴请权利”的形容词,还可以是“一种快乐的分享,一次开心的宴请”的名词。所以,界定名词化之后的动词、形容词、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是一个不仅涉及词类本身性质,还涉及词类划界、语义分布、语法功能、兼类及歧义等多方面工程的困难问题。所以对于类属划分,我们只能确定一些宏观框架,提出一些划分原则,具体的分类还要根据上下文语境去检验。
1.首先承认名词化现象的存在
“汉语的实词,不管是表示事物还是表示动作,天然地具有名词性。”[10]“名词化”这种现象是必然存在的。尤其是“教育、斗争、招聘、领导”这类不加标记的双音词的真实存在。20世纪50年代,曹伯韩的“变位”概念,马庆株的功能异化概念,陆俭明关于“研究”类词的划定观点,朱德熙的“名动词、名形词”概念,还有陆丙甫、邢公畹等,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承认有“名词化”这种现象的存在。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依据词类在具体句子中所作成分来固定此句中该词类的性质,即“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讨论也侧面证明了“名词化”的切实存在。
2.作过渡词处理
可以将名动词和名形词在语用过程中的具体性质看成是动词或形容词的非核心性质,但应注意动词和形容词的核心性质和非核心性质是平等作用于该词类的两个部分。如果动词或形容词经常用作名词,那么这种词性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固定化为动词或形容词的增补核心性质。所以从非核心性质向核心性质的这种过渡需要名形词或名动词在语用层面的大量分布。趋于固定的典型性质和正在慢慢过渡的非典型性质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且两个性质可以相互作用,因具体语境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侧重,这个渐进的过程并不严格,所以最好将朱德熙所谓的“名形词、名动词”作为过渡词处理。
对于《语法答问》中的名词化的研究还要继续下去,“广义的形态”“零成分”等说法都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名词化观点。故吾辈学者应继续加强自身学术素养,使名词化的研究成果渐渐丰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