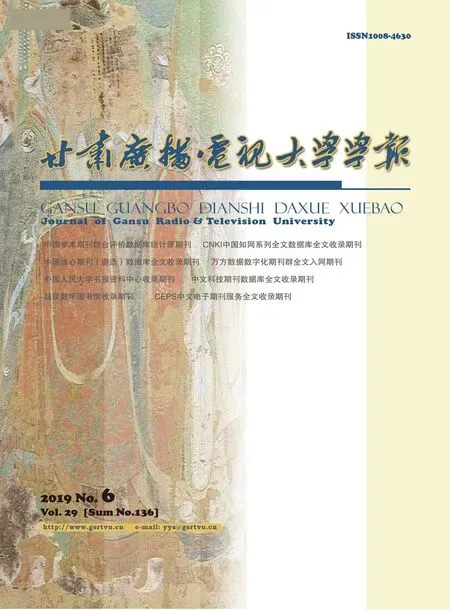市场经济中知识分子的人生境遇与价值取向
——评刘建东小说集《丹麦奶糖》
秦 悦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作为知识的拥有者,知识分子同时承担了社会的道德期待。从知识分子群体的处境和命运来窥探时代和社会的精神脉动,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本文所探讨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是指小说中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并且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物。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流落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他们原有的神圣使命和终极理想骤然之间失去了意义。因此,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
面对启蒙与市场、文化与政治、知识与道德等多重冲突,知识分子到底该如何抉择以安放自己的灵魂?河北作家刘建东立足现实,通过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描绘,表达了他对新世纪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刻思考。在小说集《丹麦奶糖》中,有的知识分子自觉追寻着“君子之道”,虽然没能完全实现个人目标,但同样抚慰了读者的心灵;有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被物质世界同化,尽管有时会在外部因素的触动下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却极难重新坚守文化精英的价值原则与道德操守;有的知识分子深感理想幻灭的苦闷,虽不甘成为一个庸人,却无力实现新的目标,只能运用心理防御机制获得片刻的安宁。
一、追寻:理想坚守者的生活姿态
1978年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社会转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体而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体制由高度集中向民主开放转变;文化体制由单一向多样、融合转变,由此带来了价值观由一元到多元的变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社会上出现了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的现象,知识与知识分子相对贬值,尤其是大学毕业生流入人才市场,逐步丧失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受时代诸多因素的影响,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呈现出世俗化、日常化、去精英化的趋势。然而,仍有部分小说中的人物秉承精英立场,自觉追寻知识分子理想,保持知识分子的德行操守,努力抵抗流俗,刘建东的小说集《丹麦奶糖》正是如此。
《阅读与欣赏》的主人公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他本来是被分配到工厂的子弟中学做语文教师的,但是天不遂人愿,学校撤销了,不得已,他被分到检修车间,学习焊接技术。车间的环境非常糟糕,处处弥漫着汽油、机油、铁锈的味道,“角落里那些废弃的铆钉、螺丝、法兰、阀门、换热器更助长了味道的扩散”[1]1。在这个不时令人作呕的地方,一心想写小说的他受到了工友们的嗤笑,但他仍然不改初心,坚持写作。在同样爱好文学的女师傅冯茎衣的帮助下,主人公逐渐弥补了缺乏生活经验的短板,一步步实现了他想写小说的人生理想。
新世纪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同样是《阅读与欣赏》的主人公自觉追寻的目标。人格理论认为:“理想人格是时代精神的凝聚”[2]23,它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特殊功能提升着实有人格和贫乏的现实”[2]23。小说中的主人公所追寻的理想人格集中地体现了“人生哲学或伦理学对于最健康的人格,或最值得追求和向往的人格的看法”[3]。《阅读与欣赏》中的主人公以传统的道德理想人格为准绳,要求自己和他人有高度的责任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所以,他不赞成冯茎衣放荡的生活方式,并且多次用自己的方式劝冯茎衣要庄重节制,听到别人讲冯茎衣的风流韵事还和那人打了一架。然而在道德与利益或道德与情感发生冲突时,主人公又会选择后者。他自私地默许甚至帮助冯茎衣用身体和唐副厂长做交换,从而实现自己调入机关工作的愿望;明知违背了职业道德,依然私下去见被纪委部门调查的冯茎衣。这些做法既体现了他的实有人格并未达到理想人格的高度,也暗示着践行理想人格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重重阻碍。虽然主人公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寻以失败告终,但是他曾付出的努力依旧为读者带来了心灵的慰藉,他的挣扎和悔恨本身就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说:“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间充满张力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正是现代性需要的和谐。”[4]从某种程度上说,《阅读与欣赏》中的主人公正是通过自己的坚守与追寻制造并维护着这种和谐。他的身上寄寓着作家的价值理想,也残存着超越活着之上的希望。
二、迷失:理想丧失者的精神危机
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5]。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城市的扩张、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从整体上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改变了人们评判事物价值的标准和为人处世的原则。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传统伦理道德“正人”“正己”“正心”“正气”的作用弱化甚至消失,人们想方设法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常常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作为现代社会的代表性群体,知识分子被经济社会的功利主义特质同化,基本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理想追求。然而,总有一些异质因素令他们怀疑自己所作所为的正当性,进而爆发不同程度的精神危机。
在中篇小说《丹麦奶糖》中,刘建东细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人际关系的紧张,从而表现了失谐关系中知识分子的“异化”和他们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小说的男主人公董仙生是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著名评论家,兼任社科院的所长。从名字上看,“董仙生”正好与“董先生”的音相同。由此可见,作家试图描绘的并不是某位知识分子,而是21世纪知识分子的社会群像。经过二十年的奋斗,董仙生拥有了较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亦在文化资本体制中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价值,俨然是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然而生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置身在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里,董仙生常有腹背受敌之感。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他成为了一个多疑的人。所以,在莫名其妙地收到丹麦奶糖之后,他怀疑上了自己的竞争对手——科研处处长老焦。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董仙生要求自己的好友曲辰利用送快递的机会为他拿一本老焦的笔记本。当曲辰问他是否太多疑时,董仙生回答道:“我知道自己多疑,但它让我感觉到安全”[1]69。这番回答,并不代表他内心多么安稳幸福,反而表现了他的焦虑和脆弱。问题在于:“是什么导致了人们的这种普遍焦虑?我们还能去哪里寻找安全感?”[6]董仙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现在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你不能简单地把一件事定性为好还是不好。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在怀疑、鉴别、揣测、辩解、确定之间来来回回”[1]72。社会大环境如此,为了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获得更多的利益,董仙生逐渐忘掉羞耻、激情、幻想……然而,这种变化是好是坏,他自己都不知道。在精神上,董仙生成了一个焦灼惶惑的人。不过,只有在董仙受到外界刺激并反思现实生活时,他才会感受到自己的软弱无力。惶惑感虽然令他苦恼,但并没有妨碍他的正常生活。换言之,董仙生仍旧可以在平静中度过绝大多数时光。因而绿皮的《安徒生童话》、放弃一切去支教的孙尔雅,以及北戴河的“鸽子窝”,都没能打动董仙生很大程度上“花岗岩化”的心灵,被董仙生想起并立志前往的云南勐海也只在极短的时间内唤醒了他沉睡的灵魂。在故事结尾,董仙生感慨道:“也许,生活就是这样,当多达六盒的甜蜜堆积如小山时,谁还想去思考那些干扰我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呢!”[1]116这标志着董仙生向平庸的堕落已经无可阻挡。
相对而言,在《声音的集市》中的董仙生遭受了更痛苦的精神折磨。在遇到盲人女孩莫慧兰之前,他和《丹麦奶糖》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在个人现实生存的基础上,构筑了自己的意义世界,并且同样迷失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忘记了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然而,在某次演讲结束时,他遇到了前来听讲座的莫慧兰。从莫慧兰的讲述中,他看到了一年到头四处演讲的自己,甚至还有从事着历史学家、生物学家、育种学家等不同职业的自己,而这与董仙生对自己的认识截然不同。于是,他开始反省自己:“我是如何成为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的,一个喜欢被别人捧在天上的人的,一个喜欢到处去兜售自己廉价思想的人的?”[1]234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董仙生不再频繁地四处讲学,直到推掉所有的讲座。一次偶然的机会,董仙生听到了莫慧兰具有感染力的发言,竟不自觉被吸引。正当他忘乎所以的时候,莫慧兰握住了他的手,并拉着他走到大街上。她对董仙生说:“刚才那个人不是我”[1]236。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但是它对董仙生、对读者灵魂的拷问并没有结束:到底哪个人才是我?自我认同危机的爆发完全打乱了董仙生的正常生活,使他长期处于彷徨痛苦之中,但他也因此有机会脱离知识分子平庸化的现实潮流,超越活着之上。
“董仙生”乃是作家对市场大潮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称呼。在市场经济的狂潮面前,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被世俗同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永久地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那些日常生活中宿命性的异质因素,以疾风骤雨般的强制性,逼使每一个人重新认识自己的工作、生活和精神状态,使他们有可能重获知识分子的身份。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刘建东保留了一些理想主义情怀,所以他在塑造了一位基本世俗化的“董仙生”之后,又塑造了一位极有可能冲破世俗牢笼的“董仙生”。尽管如此,刘建东仍在质疑后者能否真正突破精神困境,所以小说才会以“刚才那个人不是我”这句话收束全篇。从作家对“董仙生们”自信的缺乏可以看出,在当下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虽然承担着大众对他们的期待,但在现实中极难重新成为“社会的良心”。
三、逃避:理想幻灭者的消极斗争
理想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想象、向往与追求,然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人的理想往往不能完全实现。在小说《丹麦奶糖》中,曲辰因追求孟夏过失杀人,锒铛入狱。“犯罪—被判刑—监狱服刑等一系列负性生活事件”[7]完全打破了他想在新闻业有所成就的理想。出狱后的曲辰因生活没有意义而倍感沮丧。与曲辰不同,肖燕按自己的规划成为了一名桃李满天下的教师。但是,她辛苦培育出来的学生却将汲汲于名利的“成功者”视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意识到这一点的肖燕感觉自己所做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也陷入了理想幻灭的苦闷之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个体在面临障碍或经历挫折时,在其内部心理活动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某种方式,以摆脱烦恼,恢复心理的稳定。这一适应性倾向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防御机制”。这一理论在其女安娜·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发展。她不仅归纳了散见于他父亲著作中的10种心理防御机制,还添加了另外5种防御机制。在理想破灭之后,曲辰和肖燕不约而同地感到了自己的弱小无力。无法在现实中获得成功的他们只能使用心理防御机制,减弱消极情绪对自己生活的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曲辰主要使用了抵消、内向投射、升华和利他主义这4种心理防御机制。首先,“抵消是指一旦发生了一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人们常常以某种姿态或仪式来抵消由此造成的心理不安。”[8]115带着“释放犯”的负面标签重新回到社会之后,曲辰感到非常自卑和迷茫。所以他在社科院当门卫时,虽然董仙生多次劝他不用敬礼,但他都恭敬地向董仙生行军礼。通过行礼这一仪式,曲辰消除了自己内心的焦虑感。但是,当曲辰发现董仙生和他的前女友孟夏在一起之后,愤怒再次冲昏了他的头脑,他不仅当时打了董仙生,事后也不再向董仙生行礼。这一举动实际上意味着曲辰是作为一个被朋友背叛的男人在和董仙生交往,而此时他已经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所以他不再需要使用抵消这一心理机制来调节内心的不安。然而,母亲弥留之际所说的一番话使曲辰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疼爱,由此曲辰重构自我认同。他放下了对孟夏的执念,决心在兑现帮狱友小张找印彩霞的承诺后回老家种果树。此刻,作为回头的浪子,曲辰又开始向董仙生敬礼。其次,“内向投射”是把外部的东西吸收到自己的人格中去。由于之前的犯罪经历,曲辰迫切需要别人的认同。只要能从听众眼中看到一丝期待,他都可以绘声绘色地讲述不符合自己审美的监狱生活阴暗丑陋的一面;为了得到董仙生的认可,他本来不知道如何评价自己过失杀人的行为,却可以按照董仙生的想法说:“我白活了这一生。我为自己的冲动与不理智付出了一生”[1]66。通过使用“内向投射”这一防御机制,曲辰暂时获得了别人的认可,却放弃了自尊自爱,强行抑制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显然,这一做法并不是长久之道。再次,“升华是把某些冲动和欲望通过某种高尚的行为转变为社会所接受的东西”[8]114。在董仙生为学生们上课时,曲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在监狱中给狱友们讲童话;在北戴河度假时,曲辰和肖燕、董仙生一起追忆他们大学时去刘家峡游玩的往事,在肖燕的提议下,他还深情地唱了一曲临夏花儿。这是积极的升华,也使他在这些时间里摆脱了焦虑不安的情绪,得以享受内心的平静。最后,“利他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太明显的投射形式。人们通过采取利他主义的行动,既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又帮助了别人。“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人们可能会不惜放弃自己的需要来满足别人的愿望”[8]113。曲辰出狱后因过失杀人的经历而丧失了生活的动力。于是他把为小张“平反”视为“救命稻草”,希望能通过证实小张的清白,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同时也找到自己生存的价值。所以他即使没有别的收入来源,也请假为狱友小张找印彩霞,帮助小张洗脱冤屈。正如曲辰所希望的那样,他在找人的日子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他的生活也变得有意义起来。
肖燕常用的心理防御机制,有曲辰一样的利他主义和升华。在教书育人的理想“破灭”之后,肖燕感觉人生失去了方向,但是又被现有的物质基础和教学业绩牢牢地束缚着,不敢像支教老师孙尔雅一样抛弃现有的一切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因此,她将证明小张的清白视为生活的目标,在小张出狱之前帮助曲辰找印彩霞。肖燕从孙尔雅的朋友圈、《安徒生童话》以及北戴河的鸽子窝中获得了生活的乐趣。通过升华这一防御机制,她对梦想的追逐得到了变相的满足。除此之外,隔离是把引起自己负面情绪的事情通过某种方式,使它与自己的意识隔离,令自己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从而心情趋于平和。正是使用了隔离这一心理防御机制,所以肖燕早就知道了丈夫董仙生和竞争对手老焦的龌龊行为,早就知道了丈夫和其他女人的苟且之事,却什么也没说。不过,这种防御机制只是一种“自我欺骗”,它的作用只是让肖燕逃避现实,从长远来看,弊大于利。
总之,通过使用心理防御机制,曲辰和肖燕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内心的平静。但这只是逃避现实的无奈之举,个人心理的调适常常是滞后的,它只能非常有限地应对现实的打击。小说中小张强奸印彩霞一事突然打破了二人趋于正常的生活便是明证。曲辰作为小张的同谋再次入狱,而肖燕因为鼓励曲辰帮小张找印彩霞倍感愧疚。这表明,心理防御机制只能使人获得短暂甚至虚假的安宁。令人可惜的是,既无法实现新的目标,又不甘成为庸人的理想幻灭者,只能运用心理防御机制与不如意的现实进行消极的斗争。
四、结语
在小说集《丹麦奶糖》中刘建东通过对知识分子多元化人生境遇的描绘,表现了知识分子在世俗社会中的精神挣扎,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他们超越活着之上的可能性。然而,小说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真正回归精神家园的悲剧性结局则暗示着:在商品化、消费化、大众化的潮流中,知识分子越来越难以坚守个人理想和保持德行操守。当然,这并不能作为知识分子沉沦的借口。在重复和琐屑的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仍应坚守理想,并为实现理想而不断努力,如此才能尽量克服自身惰性和外界诱惑,保持自我的完整性,进而成为社会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