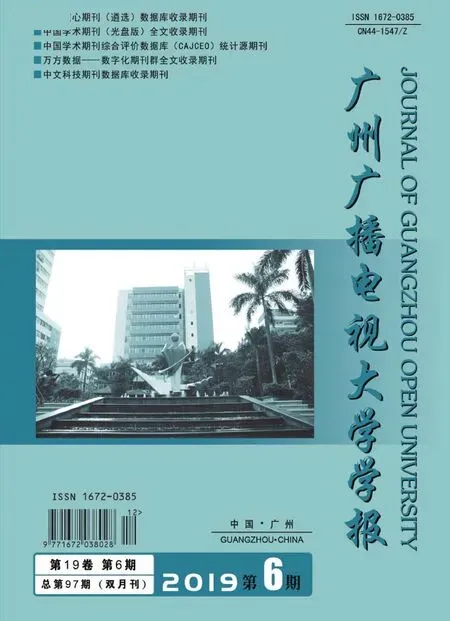“发篇温丽,无违其情”的缘情之作
——张华《情诗》研究*
彭 姣
(北方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身处政局动荡的魏晋之际,文人自觉转向文人化,两汉以来儒家思想逐渐衰微,儒家的正统地位相应受到严峻挑战。建安诗歌经历了曹操的慷慨质朴、曹丕的便娟婉约以及曹植的辞采华茂后,至西晋,玄学开始兴盛。文人受这一时代风尚之影响也被反映到相应作品中,最明显的便是作品中原来慷慨昂扬的描写逐渐向儿女情长的转变。作为“缘情”诗歌的领军人物,张华自然有其独特之处。张华,字茂先,他出身寒微,少时以牧羊为生,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止他汲取知识的强烈信念。因此,在诗作、历史、技艺等方面多有建树,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成为西晋诗坛甚至政坛的佼佼者。
《情诗》作为茂先代表作之一,离别之痛、相思之情、哀悼之伤被其演绎得多姿多彩,深情绵邈的同时亦给人哀婉动人之感。诗人对于“情”的体验是周到而又独到的,他有一颗女子般的柔软内心,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刻画出人世的离思之情,因此,《情诗》多情而非滥情。钟嵘《诗品》曰:“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1]可见“儿女情多”便是茂先情诗风格的重要一笔。在茂先重“情”创作观念的影响下,扶持并培养了一大批作家文人,因此,历史上还诞生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团体。[2]在此基础上,研究茂先《情诗》具有重要意义。
一、张华《情诗》产生之原因
(一)动荡政局的影响
魏晋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它从那个产生了慷慨悲凉不朽诗歌的建安开始。这开始就弥漫在战火、饥荒和疫疠之中。”[3]其时政局动荡、战乱不断、国家分裂,如走马灯般更迭的政权给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统治者的高压政权,人民生活的朝不保夕以及个人生命的何去何从令其苦闷不已,他们感伤、彷徨、愤懑,却又无法改变现世。在此境况下,许多士人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感知比常人更为敏感,心思更为细腻。“对于诗文的创作,他们不像其时多数士人那样,从娱乐的角度考虑问题,求华美,而是更多地从发抒情怀的角度,求适情。”[4]此时,他们便选择拿起手中的笔,为自己的情感寻求一份寄托,描摹出心中所向往的那个精神世界,以此换得短暂的人格自由。
(二)享乐、玄学思潮的影响
“玄学的文艺观是诗缘情说。情就是自然,缘情就是任自然。”[5]魏晋时期经学衰微,玄学思潮盛行,玄思成为这一时期士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加之当时人们的欲望以及个性逐渐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也使得文人都大胆追求情欲爱欲,重德轻色这一天平发生了倾斜,尚美之风逐渐流行于士族文人之间。”[6]其中以曹植的《美女篇》《浮萍篇》为代表,其中均有对佳人形象的深情刻画。古代思想史著作《列子·杨朱篇》对当生之乐主义进行了充分渲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那一时代人们有着追求享乐的思想,女色享乐主义自然也包含其中。也因此,女子这一群像逐渐活跃于文人笔下,同时获得不少文人情真意切的描摹、赞扬。这也是魏晋情诗发展不可或缺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各诗风之综合影响
1.汉末文以及诗表现内容丰富,诗歌以感伤为主要色彩。文人的情诗受此影响,大多以抒情为主,即使是写到诸如《昔思君》一类弃妇诗,也常常有自寓感伤的成分在里面,茂先亦不例外。
2.汉乐府诗具有叙事性的特点,汉乐府大多来源于民歌人乐,形式上以杂言为主。《汉书·艺文志》载有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7]的特点,也因此茂先的“儿女情长”变得有迹可循。
3.借鉴了古诗的写法与情感分类。古诗中多抒发“怀思”、“离愁别绪”、“人间失意”一类情感,这对茂先有所启发。谈及写法的借鉴,两相对比:《情诗·其三》“清风动帷帘,晨月照幽房”[8]源自《古诗·明月何皎皎》中“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9];《情诗·其四》的“君居北海阳,妾在江南阴”[10]与《古诗·行行重行行》中“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11]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情诗·其五》与《涉江采芙蓉》的联系则在“游目四野外,逍遥独延伫。”[12]与“还顾望旧乡”[13]这几句。在茂先情诗中大多可以找到古诗的影子,可见古诗深刻影响着他的情诗。
茂先诗歌体制众多,囊括三言、四言、五言以及杂言。“他的文学思想既有‘宗经’守旧的一面,又有‘通变’趋新的一面。”[14]除却以上种种影响,他的创作中还继承了汉末建安以来的传统,即反映社会现实、抒写个人情志,当然他并非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在诗歌的表现形式方面更是作出了大胆尝试,如其《杂言诗》写得较为成功,同时又有三言、四言、五言,呈现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为他的诗作添加了不少新意,是为传统与新变的融会贯通,这些都为后世文人创作提供了不错的范本。
二、张华《情诗》之归类探析
魏晋文坛,经历了建安风骨的慷慨激昂、正始之音的清幽遥深,至于太康,文人们把对政治的热情转至一己情感的抒发。在这溢情的时代,“情”的表现方式更是多样,哀婉感伤、离愁别绪、相思之苦等均成为一时代之强音。张华以其温丽清省的诗风于诗坛独树一帜,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教授评张华时“用了‘博物的记录’、‘鹪鹩之赋’、‘情诗的系谱’、‘游侠乐府的世界’,称茂先是‘魏晋南朝文学、思想上的坐标’。”[15]如此高的评价,说明茂先之诗确有特定价值。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总录茂先《情诗》5首,《诗品》评茂先诗歌的“儿女情”虽存在一定程度的贬斥,但站在文学作品的立场上来看,多有“儿女情”并非什么坏事,在此笔者试将《情诗》大致分为以下两类并作简要分析。
(一)闺中离妇思夫
茂先的《情诗·其一》以一端坐着鼓琴的“佳人”为伊始,极具画面感。以袅袅琴音晕染开来,营造一种脱俗的意境,抓人眼球,在此不得不感叹张华的确善发诗端。是什么原因致使其终日抚琴却始终不成调?原是思念远方行役之人。在这梦一般的幻想之中,“佳人”孤独的与高雅木琴为伴,内心是何等寂寞!手上做着抚琴的动作,内心却思之如狂。“初为三载别,于今久滞淫。”[16]似是“佳人”对“役人”的诘问:“初时分手说好三年为期,如今为何逾期不归?”直至新柳长成,庭院绿柳成荫,“鸟鸣偶”、“虫和吟”,皆是成双成对,如此描写,将“佳人”的形单影只刻画得入木三分。诗末,“佳人”突发奇想,幻想着长出鹯鸟的双翼,飞至“役人”身边,为他料理衣食。这类痴而又痴的行为再次赢得读者青睐,将这“同情”之情拔高至新的维度。发展至南朝衍生出《西洲曲》中“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17]的迷人韵味,将“佳人”的痴恋情态锻造得惟妙惟肖。值得注意的是,“束带侍衣衾”的细节描写,说明“佳人”在伺候“役人”之前特意整饰衣物,这不仅是一位多情、多艺的“佳人”,还是一位端庄、持重的“佳人”。对比曹植《杂诗·西北有织妇》中思妇“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18],茂先这首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则多了一种温丽之情在里面。
《情诗·其三》则以一幅月夜之景打开画面。月夜是中国古诗中惯用的意象之一,在月夜下,思乡、思人之情均无处遁形。“清风”与“晨月”两词犹佳,从侧面表现出少妇因思念丈夫而彻夜难眠之态。所思之人远在千里之外,闺阁中已不见他的音容笑貌。天上明月郎朗,流光溢影,此时女子举头生发离思,俯首环视而光泻入怀,那满身满襟满床满室的光和影,抹又抹不得,甩又甩不去。然明月依旧,床空无人!长久的分离使得思妇观注着周围的一切,由此,少妇对夫君的执着痴情,以及她那只有通过回忆来聊以自慰的痛苦,均在不言之中了。这里,诗人准确地把握了女子内心的复杂心理变化,将痴情的幻想和冷酷的现实进行赤裸裸的解剖,据实构虚,从而把诗意从正面归结于怀人思远,实为一大妙境。接下来转向今昔对映——“居欢惜夜促,在蹙怨宵长。”[19]往日夫妇二人共处一室,欢欣无比,故嫌夜时过短,常于夜分之时促膝长谈;今日一比,兰闺一人,寂寞难耐,转而怨夜过长,愿其速速逝去。“拊枕独啸叹”[20]中的“啸”字更为传神,撮口呼出清亮激越之音,是魏晋人常用的表达情志的方法之一。女子内心感慨、哀寂,轻叹恨不足,禁不住长啸。单单一个“啸”字将思妇的深深思念之情刻画得深入骨髓,令人动容。
茂先著诗不仅重时间的安排,也重空间的相互比对。再看《情诗·其四》,以空间为开端,交代两人的地理位置,男子居于北海阳处,女子住在江南阴面,也许这只是诗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写法,总归是天各一方,与《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21]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山高水长,路途遥远,两人想见却不得见。诗人通过这样的空间安排,为诗中两位主人公创造出一个绝对相思的环境。女子想到男子昔日对她的厚爱,便说出“衔恩笃守义,万里托微心”[22]的誓言来,对爱情的忠贞可见一斑。
(二)远游旷夫恋妇
茂先所写情诗语浅情深,质朴纯实,除却表现女性对男性的牵念外,也有刻画男子对女子的深深眷恋之情。试看《情诗·其二》中的男主人公思念佳人至入梦相见,可歌可泣。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言:“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23]对茂先有所启发,他以“明月”“昽光”这样清虚寥廓的良辰美景反衬幽人的“非赏心乐事”,衬托出主人公的“独悲”情态。思之如狂,在梦中终于与心心念念的佳人相约,梦中美人依旧,梦中情景是清晰、欢快的,只是美好的梦总是那么短暂,当主人公醒来,恰有一种“梦见在我旁”[24]的喜悦陡转至“忽觉在他乡”[25]的无尽凄凉。这才有了下面的“寤言增长叹,凄然心独悲。”[26]梦醒之后形单影只,倍添思念之苦。
《情诗·其五》诗人站立于四郊野外观览周围景色,自由自在地久久伫立。他看见兰草和蕙草沿着水道生长,水中的小洲遍布鲜花。男子独处于广阔的天地,猛然回神,要是她在该有多好!定当把鲜花采摘赠予她。读者也会不禁想到女子将花儿别在耳后的娇羞之态,男主人公深情对望的样子定是十分美好。只是心上人没在,采摘过后还能送谁呢?接下来的两句更是达到“物外传心、空中造色之妙”[27],诗句大意:巢居的鸟儿更容易知道天气何时会刮风、严寒;居于洞穴的虫蚁们更能预感何时会有阴雨。没有经过远别分离的人,哪里能知道夫妻之间思慕之情究竟有多深呢?这两句以比起兴,比喻他人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感知其中滋味,主人公的思念之痛也仅能靠自我消解,相思之苦应运而生。
茂先的五首情诗实属“秾丽之作”[28],沁入人心、从容且辞彩倩丽。这五首诗歌各自成诗却又暗成一体,《情诗·其一》告知人物、地点、交代相思缘由;其二云男子思念过度,以致于与心上人梦中相会;其三言女子夜夜拥虚影,寂寞难耐;其四解释山高水长,实难相聚;最后一首再次将镜头转向痴情男子,摘花却无处可赠。无论是从时间、空间、情节的连贯性以及人物的角色塑造,这五首诗都可看成一个整体,这也是张华著写情诗功力的体现。“扎实的分析有时比印象式的批评更富于认识的价值”。[29]因此将茂先所写《情诗》作出以上分析,固有一定价值。
三、张华《情诗》之相关诗学品评
了解一时代诗人及其作品,仅有今时人评论似有不妥,需将眼界开阔至整个历史上的诗学品评,尚存一定可靠性。王夫之评茂先诗歌历史地位:“茂先……欲开宋、齐之先,作唐人之祖。”[30]我们以此作前提研究茂先及其作品犹为重要。
(一)矛盾品评
一方面,历史品评中是对茂先的肯定。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观古今胜语……。”[31]对于此诗句,在一些学者之间存在一定争议,有的认为此句并非出自茂先,对此笔者特意进行了相关资料的查找。曹旭老师在《张华情诗的意义》一文中指出王叔岷《说文月刊》中第5卷1-2期有过相关考证——诗见《北堂书钞》卷一百五十七,在其《锺嵘诗品疏证》有云:“则仲伟所举,固茂先句矣。”[32]说明这一句实属茂先诗,钟嵘夸其为“胜语”。再有周振甫先生在《文心雕龙今译·时序篇》中评“茂先摇笔而散珠[33]都是对茂先作品的高度评价。
然而,另一方面又有对茂先诗的贬责。茂先主张“宗经守旧”之余又有“通变趋新”的一面,他的诗歌大多表现出一系列的形式美,诸如华丽辞藻、巧于修饰、追求对偶工整等,也因此呈现出绮靡妍丽的风格。然观钟嵘的诗歌美学:主张刚健之气。两者美学思想截然不同,故钟嵘曰“……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34]带有贬责之意。可见历史品评对茂先有褒有贬,具有矛盾性。
(二)品评“情多”之特点
茂先诗风源自王璨,王璨诗最大特点便是“自伤情多”[35]。茂先也有所继承,提出“发篇温丽,无违其情”[36]的诗学观点,这才有了钟嵘对其诗“情多”的品评。茂先用“私我化”的儿女情,将建安诗歌的主题基调进行改变。在和平统一的年代,建功立业不再是主旋律,风云气已无处施展,诗歌自然会朝着小我、闲情逸致和儿女情多的方向转变。[37]
(三)品评清虚、空灵之意境
国人一向注重意境,貌似对写字、绘画以及创作的最高评价都在“意境”层面。《文心雕龙·明诗》:“茂先凝其清。”[38]虽说清虚意境始于唐,但其实在茂先时就有了清虚、澄明意境的创作。他的《情诗》有不少体现这一意境的用词:“清景”“清风”“清渠”,除此之外的“晨风”“晨月”“明月”“静夜”“虚景”等词也有“清虚”之意。“清”字,由其本义“水清”引申。《说文》有解:“清,朖也,徵水之皃。从水,青声。段玉裁注:朖者,明也。”[39]“清”一是针对诗歌语言,二是因为其清虚、绝俗的趣味,《诗品》评陶潜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40],胡应麟:“清者,超凡绝俗之谓”[41]等都是“清”的体现。茂先以澄澈、淡远的格调注入诗中,展现出诗歌的清虚、空灵之美,从一定层面体现出西晋文人已萌发出诗歌意境的创作趋势。
四、结语
“魏晋时期战祸不断,男性劳动力大量消耗于战场,这无疑使女子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得到提升。”[42]这一时期的士人也逐渐由重实用与重功利走向重情感与自我,加之其时一些文人,如王弼、何晏、向秀等对于“情”的热烈探讨,故生发出许多“缘情”诗作。作为新晋时期重要的“缘情”诗人,茂先或与二陆、太冲、安仁等人相提并论,或风评高于这些文人,总观各论,茂先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着后世诸如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和宋征虏将军王僧达等人的诗文。若寻刘宋时代诗歌风格的源流,茂先也必当之。因此,世人研究茂先,研究《情诗》实属必要,笔者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