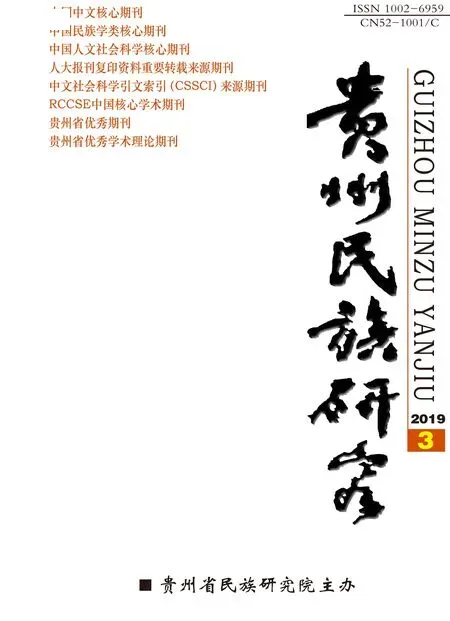唐朝胡乐入华源流及其对华夏音乐影响研究
刘 芳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唐代胡乐入华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之一,外来音乐的传入在唐代达到了顶峰。从全面接受到融为一体,外来音乐对我国后世音乐的成形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胡乐入华这一事件的形成,是以当时地理交通以及地区文化交流为前提开展的。其中,丝绸之路堪称打开胡乐东传的钥匙,也为中原地区和西域文化的互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胡乐胡舞的艺术风格
在传入中原后,胡乐受到了宫廷和民间的广泛重视。由于胡乐的音色、旋律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通过歌姬的轻歌曼舞,给人带来很高的艺术享受。因此,早在初唐时期,便对这些艺术精华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吸收,形成了风格十分独特的汉地流行胡乐,并配合了相应的胡舞。
(一)节奏鲜明,风格热烈
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这样记载:“族君递奏,金鼓迭起,洞心骇耳。”可知打击乐器对听者内心感受有着很深的影响。鼓乐队的敲击,声音坎坎、节奏鲜明,烘托出更加热烈的气氛。胡乐的感染力之强,从打击乐器的广泛使用中可窥一斑。不同于华夏音乐的轻缓、节奏散漫,任何一种胡乐器都使用打击乐,具有打击乐器的强烈节奏感。这也赋予了胡乐节奏更加鲜明、畅快的特点。在中原流传很广的龟兹乐是胡乐之中打击乐器最多的乐种。“龟兹乐,其声震厉。”可以想象的是,龟兹乐运用各种各样的鼓板,随着音乐的进行推动听众的情绪,呈现出的是一种热烈、奔放的感觉。很多西域胡乐的乐种都会对打击乐器中的翘楚“羯鼓”进行应用,此鼓本属于戎羯之乐,声音焦杀,声调急促,音色、音质上呈现出极强的个性特色。另外,在天竺等很多国家,打击乐器中出现了铜钹,此乐器为金属所造,声音十分高亢,穿透力强。由上述西域打击乐器、节奏乐器的使用情形可知,胡乐是一种节奏鲜明快捷、风格热烈奔放、感染力极强的乐种。
(二)朱紫玄黄,色彩纷呈
《梦溪笔谈》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皆胡服也。”胡服的传入自然对中原胡乐的表演服饰有所影响。下面以高丽乐和扶南乐为例,在《高丽乐》中,演奏人员会佩戴装有鸟羽的紫罗帽,着装以金黄色大袖为主,腰系紫色罗带,衣服上也会点缀一些五色斑斓的丝带。表演者会利用大红色的颜料布满额头,还需穿着黄色的长裙和红黄色的裤子,其衣袖较长,可以甩动开来。《扶南乐》之中的舞者会利用朝霞颜色的布进行绑腿,统一穿上大红鞋,显得十分整洁与利落。由此可知,胡乐乐舞表演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色彩有大红色、紫色、金黄色等。这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色彩,可想而知对汉地的歌舞表演有很大影响。可以说胡乐之所以能够在中原流行起来,起舞者的妆容以及服饰色彩起到了重要作用,鲜艳的色彩加强了舞台效果、长袖挥洒也提升了舞者体态动作的艺术性。
(三)回雪转蓬,急转如风
唐《康国乐》载道:“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胡旋舞的来源地即为康国,艺人经长途跋涉,将这种著名的舞蹈带入中原。初唐时期,胡旋舞的“急速旋转”的特色便被舞者展示出来了,这一点也可以从舞者的衣着上得到证实。《康国乐》表演者穿着红色上衣,腰系红色皮带,衣袖挥舞间色彩缤纷、炫人耳目。据服饰学家考证,康国乐舞者穿着的衣服主要由麻布制作而成,麻布透气轻便、利于舞者跳跃腾挪,同时麻布所制的舞服会利用起伏的线条呈现出一种变幻迷离、神秘莫测的感觉。唐朝诗人岑参在观看胡姬跳舞时,发出了“世人学舞只是舞,姿态岂能得如此”的感叹,此诗所描述的舞蹈便是胡旋舞。另外,白居易在其诗《胡旋女》中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此诗将胡姬舞蹈的韵味通过画面感描述了出来。所谓“心应弦,手应鼓”,随着音乐的旋律以及打击乐节奏,舞者将舞蹈内容一一展示出来。而他将舞女的动作比作“回雪转蓬”,可见胡旋舞在表演时,歌姬的衣裙可以像雪花一般在空中飘摇,旋转起来如飞蓬一样,可见其旋转速度之快[1],在传入中原之后,胡旋舞立刻以它独特的服装、动作和艺术效果,得到了大批观众的热爱。
二、唐朝胡乐的入华源流
(一)唐代的礼乐制
唐代礼乐的重新制定是胡乐入华的主要因素之一。唐代建国初,高祖就下令恢复传统的礼乐制度,唐初的礼乐事实上仿照了隋代乐制。隋代以前,礼失乐佚,制定乐制者必然会向民间寻求帮助。由于唐代前经历过南北朝、隋代各族争战对原有汉地文化的破坏,唐代礼乐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包容、灵活的趋势,在整体上保持与古代礼乐制度对应、继承的同时,也引入了大量新鲜的艺术血液。礼乐制度,除了用于祭祀之外,也用于宫廷的宴会歌舞,故礼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影响极深。因此,礼乐虽顺应朝廷制度,但却对社会生活、民间艺术产生了辐射作用。唐代官方订立的“九部伎”“十部伎”几乎全用胡乐,这也促使了胡乐参与到民间音乐和宫廷音乐的交流之中。另外,胡乐的传入,也源于隋唐时期人们对鼓吹乐使用范围的扩大,除了吉礼之外,军礼、宾礼和凶礼等均会有鼓吹乐参与其中。鼓吹乐来源于民间,具备汉胡相杂特性,这也成为胡乐进入到礼乐的重要途径。
(二)礼乐中的胡律
随着朝代的更替,礼乐之中的乐律出现了极大程度的改变。胡乐和雅乐的融合起源于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连年,汉民族的宫廷乐工大量流失,在建国后雅乐的整理工作上,各个朝代均出现了很大困难,其时传统的礼乐律吕尚且存在,但胡乐的影响力已经慢慢在扩大,导致在隋末唐初间传统音乐近乎灭绝。《全唐文》之中这样记载:“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证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从该段记述之中可以看出,唐代雅乐也是以前世为基础创新得到的。其根源在于:隋唐时期,官方乐律的制定,不得不借助于民间音乐,而民间音乐大多受到外来音乐的影响,这也促使很多雅乐已经脱离了传统雅乐的范畴。唐代礼乐在律调的把握上很容易受到胡乐的影响,这也加深了人们对胡乐的认可。这些举措印证着:唐代雅乐艺术性的提升,是通过对外来音乐律吕的全面吸收,并继承了隋代雅乐制定的“引入胡乐”传统,最终才得以完成的。[2]
(三)雅俗乐的交融
礼乐创作于周代,但经过朝代变换,真正的周代礼乐早已消失殆尽。南北朝时期,各个朝代模仿周朝对礼乐制度进行重建,但一时间无法找到合适的音乐对其进行替代,这也为胡乐的注入增添了很多机会。站在音乐史角度来说,乐在唐朝体现出三种形式,即雅、俗、胡,而胡乐入雅、入俗的时间开始于开元年间,唐乐由三乐并立的结构转变成胡俗融合。雅乐与礼乐存在很大区别,俗乐和燕乐也不同,相比之下,俗乐的范围较大,而雅乐的范围较小。胡乐入雅主要原因是雅乐的缺失,在各个朝代开国时期,雅乐自然不能被原封不动地继承使用(因为不能用前朝雅乐来歌颂前朝功业),还需进行重新创作。因此,新朝雅乐制定者需要对前代音乐进行改名和填词,并引入新鲜流行的音乐。而胡乐往往成为朝廷重建雅乐系统时的曲调来源。例如,在汉武帝时期,雅乐的创作者李延年最为擅长胡乐和俗乐;而以胡族为统治者的北朝,其郊庙祭祀音乐也以北方民族音乐作为主要来源。至唐朝,雅乐继承了隋朝音乐的“以胡为主”传统,并在太宗时期融入一些新的胡乐因素。由此可见,包括唐代在内的历代雅乐在制定时都十分灵活、包容,吸收了大量的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曲调。
(四)乐随胡舞传入
在唐朝,主要的舞蹈类型包括“健舞”和“软舞”,二者之间的风格存在很多不同点。其中,健舞风格十分硬朗和豪爽,软舞则十分柔婉和平和。胡旋和胡腾在唐代十分常见,属于典型的外来舞蹈。无论是大曲之中的《康国乐》,还是酒肆之中的日常宴会,这两种外来舞蹈经常会出现,具有明显的胡风因素,这也为唐代人带来了新的审美体验。胡旋和胡腾舞蹈的发源地处于中亚文化圈之中,在北印度和波斯文化的影响下,通过西域文化走廊传入我国。胡舞之中有很多富于观赏性的经典动作,如扭腰抬腿的“三屈式”,这也是胡人最擅长的动作,而这一特点可以在印度和波斯舞蹈之中找到共鸣。胡人将很多艺术类别融入到胡舞的舞蹈动作之中。而在唐人眼中,无论是胡旋舞还是胡腾舞,皆充满了力量感和速度感,不同的舞蹈动作各自传达出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感觉,促使人们感知到作为人类的旺盛的生命力。[3]胡舞的广泛流行也为胡乐对华夏音乐的渗透提供了有力渠道。
三、唐代对胡乐器的改良
很多胡乐器在进入中原之后得到了改良,人们在其中加入了多种“中华元素”,使它们逐渐演变成受到中原地区民众喜爱的乐器,与我国音乐文化相融合。
(一)材料和工艺的改良
乐器音质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其制作材料和制作工艺。以琵琶为例,在琴头、背板等选择上,材质类型不同,琵琶的音色也会呈现出一定的不同。在曲项琵琶来到中原之后,人们对其制作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琴头和背板制作上以坚硬的紫檀木、红木等材料为主,而在音梁和音柱的制作上,以桐木等轻质材料为宜。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着的一件保存完好的花瓷细腰鼓,便来源于唐代。这种鼓本是胡鼓,大多数用瓦制成,只有少数用木材制作,但唐代细腰鼓的制作材料主要为陶瓷,这也是唐时乐工对其进行改良的重要体现。另外,这种瓷是烧制的,外观十分唯美雅致。这种制作工艺只在唐代出现过,唐以后便失传了。除了上述改造之外,乐器制作中漆料的选用同样十分重要。而在唐代,由于油漆制作工艺十分先进,远超同时代的西域诸国,因此,乐器入华后自然会更换音乐性能更加优越的漆料。可以说,胡乐器进入中原之后,人们便对其材质和工艺进行了深入研究,但这些改良的来源多建立在先进工艺的使用上。
(二)形制和纹饰的改良
胡乐器传入中原之后,在形制上出现了极大改变。例如,曲项琵琶未传入到中原之前,属于四音位,再后来出现了四项十二品的十六音位,其音色、共鸣等音效得到了全面丰富。另外,曲项琵琶的颈部也得到了加大,音响下部则出现了由宽变窄的变化,为换弦和换把提供了方便,便于对音色进行控制。另外,铜鼓周身还绘制了不同的纹饰,如花草虫鱼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乐器,名为大忽雷,属于弹拨弦鸣乐器,制作工艺十分精美。该大忽雷上的琴颈雕刻着一个龙头,生态极为形象生动。龙纹和凤纹交相辉映,将“龙凤呈祥”的图腾含义深刻地展示出来,代表着祥瑞、和谐、希望和美。由此可见,唐代在器物图案和纹饰设计上十分讲究,由写实、生动的具体形象演化出一些抽象的符号以及各种纹案,对比西域乐器的原初形态,在理念和技巧上出现了较大飞跃。
(三)演奏方式的改良
唐太宗让罗黑黑演奏胡琵琶的故事闻名于世,胡琵琶和改良后的汉琵琶有很大区别。原始胡琵琶的弦拨比汉琵琶粗大,形制也较大。从形制的变化可知,唐朝使用的琵琶已经经过了改良,弦变得更细。一直以来,琵琶盛行于北方,弹奏时以木拨弹奏为主。但如果用手弹拨,呈现出的音色会更加柔和,听来更加舒适悦耳。由此可知,唐朝开始对胡琵琶的改良,在音色、弹拨方式上都有所涉及。可以说,胡乐器进入到中原之后,流传速度很快,渐渐被中原吸收和利用,并且和自身音乐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在宫廷和民间,都很受广大民众的喜欢,最终演变成华夏乐器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4]
四、唐朝胡乐对华夏音乐的影响
(一)胡乐对宫廷乐的影响
所谓“胡乐”,主要指的是西域地区的音乐,这其中包括乐曲和歌舞等等。胡乐在很早之前便已经在我国出现,南北朝时期达到了顶峰。到了唐朝,胡乐得到了当时各个阶级人群的喜爱,并逐渐演化成一种时尚潮流。唐代官方规定的三种音乐——雅乐、清乐和燕乐,其地位并不平等。其中,雅乐和清乐虽然名号十分尊贵,却已经趋于“阳春白雪”,十分式微。《新唐书》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由此看出,雅乐和清乐虽然居于庙堂之上,却并不受当时民众的欢迎,而与胡乐相融合的燕乐才是当时真正的“流行音乐”。在宣宗时期,宴请群臣之前必须准备好充足的音乐节目。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人,衣珠翠缇绣,联袂而歌。将中原之曲目和胡舞放在一起进行同台演绎,体现了唐朝对各种音乐文化的兼容并包,体现了西域音乐和原本华夏固有音乐整体融合的强大趋势。
(二)胡乐对中原调式的影响
宫调理论在我国古代很早便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建立起很多不同的调式体系。从周代开始,我国音乐中的音阶主要分为两大类,即雅乐音阶和清乐音阶。一般认为,传统的汉式音阶即“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到了隋唐时期,很多少数民族和异国音乐开始在宫廷之中出现,进而演化成了燕乐音阶。尤其是在“五音七调”传入到中原之后,新音乐乐律的统治形势已经基本形成,该种音乐律吕由龟兹人传入。在公元五六世纪左右,龟兹人寄居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带,成为了西域文化交流的中心所在,这也为当地音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条件。《隋书·音乐志》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先是周武帝,有龟兹人曰苏袛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弹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其后,郑译用宫调相旋,提出上午“八十四调”理论,也是以“五声七调”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他将龟兹音乐和传统汉族音乐在律吕理论方面融合起来,对当时隋唐音乐的发展,甚至是唐宋词乐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5]
(三)西域乐器的广泛应用
唐代的器乐种类很多,形制、音色、表现力都各不相同。擅长乐器的乐工之中也隐藏着很多民间的高手。他们将汉族固有的传统乐器和西域乐器汇集在一起,使得唐代乐器丰富到四五十种之多,如琵琶、五弦、箜篌、古琴、古筝等。优秀的演奏人员也是数不胜数。琵琶是唐代最为流行的乐器之一,出名的演奏者在唐诗中俯拾即是,如曹妙达、雷海青、米和等等。他们的演奏动人心魄,将琵琶乐器的特点展示得淋漓尽致。诗人刘禹锡在听了曹纲演奏的《薄媚》之后,写下了“人生不合出京城”的感慨,白居易等也对琵琶乐的感染力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以至今日人们还津津乐道于“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另外,敦煌壁画中也可见一些琵琶乐器,而很多的传世名画也为人们提供了唐代演奏者右手握拨琵琶这一弹奏方式的记载。“琵琶”在各类艺术中的广泛出现,可知这种来源于南北朝的乐器在唐朝盛行的程度,也可见胡乐对华夏音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四)唐人音乐倾向的矛盾
唐代音乐,雅俗互渗、胡汉交融。而唐人在对音乐的好恶倾向上,呈现出一种矛盾分裂的态度。这里的矛盾是指唐人由于对自己汉人身份的骄傲,导致了对西域音乐一定的排斥抵触心理。而从音乐艺术的欣赏、享受层面来看,胡乐的风格、艺术特征显然对于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听众和观众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很多胡乐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都会进行表层的“汉化”,在保持原有音乐特色的同时披上一层“汉文化”的皮,例如胡乐改汉乐名。唐代极其有名的大曲《霓裳羽衣曲》,正曲部分来源于《婆罗门曲》,曲风呈现出源自西域的宗教性内涵,蕴含了佛家思想[6]。本质上,这支曲调还是保留了典型的胡乐风格,但名称已经汉化。这种情况导致胡乐在维持自身特色、风格、音乐性的内容外包上汉文化的外壳,经过这样的“伪装”,它们更深入地融入了汉民族的传统音乐中,使汉乐内容发生了近乎彻底的变化。
五、结语
大唐是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是西域各族文化频繁交流、融合的土地。唐时人们对音乐艺术十分热爱,他们以包容的态度和敏锐的艺术审美对外来文化进行汲取和消化,让音乐成为了传播民族文化、推动民族融合的重要工具。胡乐的广泛传播,使华夏音乐在文明的碰撞中迸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为后世唐宋词乐、南北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胡乐入华”在我国整个音乐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