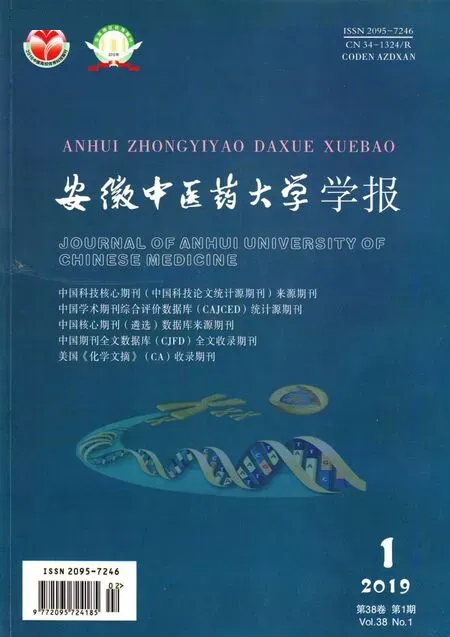《本草纲目》体质医学思想解析
钱会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北京 100029)
《黄帝内经》贯穿因人制宜的治疗思想,关注先后天诸多因素对体质的影响,认为由于体质的不同,个体对于药物的耐受性与治疗的反应性亦有不同。《本草纲目》遵循《黄帝内经》之旨,认为因脏腑禀赋有偏颇,药食气味有不同,治疗反应有差异,临证用药应中病则止,以防过度用药而造成危害。
1 脏腑禀赋有偏颇,服药宜有益无害
《黄帝内经》凸显先天禀赋在体质形成中的作用,如《灵枢·寿夭刚柔》曰:“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说明体质差异与生俱来,如刚柔以品性、气血强弱,形体短长等不同差异,可总归于阴阳之不同,强调先天禀赋对体质形成有重要的决定作用,亦关注后天因素对体质的影响。李时珍承袭《黄帝内经》之旨,用药出奇制胜,方简药纯,屡起沉疴,探索医家用药要旨[1-2],注意辨体质用药[3]。因人之禀赋有不同,故而体质有差异,《本草纲目》亦提出用药宜考虑药物之性味,又须关注药物使用者的体质状况,从而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避免药物偏性对人体造成危害。
例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七卷》关于附子作用特点的记载:“附子禀雄壮之质,有斩关夺将之气,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复其散失之元阳,并能引发散药开腠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达下焦,以祛除在里之冷湿。”并引朱震亨之言“气虚热甚者,宜少用附子,以行参。肥人多湿,亦宜少加乌、附行经”。李时珍提出气虚热甚治宜少用附子,而肥人多湿治宜稍加附子、乌头,说明因体质状况有异而用药不同。李时珍解析“乌附毒药,非危病不用,而补药中少加引导,其功甚捷”。但“有人才服钱匕,即发燥不堪”,对比提出“昔人补剂用为常药,岂古今运气不同?”说明同样使用乌头、附子类药,然其反应有异。举例蕲州卫张百户,平生服鹿茸、附子药,已至80余岁,仍是“康健倍常”。又引《医说》记载,赵知府耽酒色,每日煎干姜熟附汤,吞服硫黄金液丹百粒,乃能强健,否则倦弱不支,其亦长寿至90岁。而他人则服一粒即为害。李时珍明示其原理在于“皆其脏腑禀赋之偏,服之有益无害”,因患者禀赋有偏颇,药物使用宜因人而异,注重发挥其有益的作用,而力求减少和避免危害,故而告诫用药“不可以常理概论”。
又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二卷》关于仙茅的记载,李时珍解说仙茅性热,为补三焦命门之药,故而“惟阳弱精寒,禀赋素怯者宜之”,指出“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动火”。李时珍并引《医说》记载,一人服仙茅中毒,舌胀出口,煮大黄、芒硝与服用,再以药掺之,应时其舌得以消缩。究其机制,“此皆火盛性淫之人过服之害”。此以“火盛性淫之人”使用仙茅的危害为例,从临床角度说明体质禀赋与药物性质的密切关系。
再如《本草纲目·石部·第九卷》关于石钟乳的记载,李时珍阐释石钟乳乃阳明经气分药,其气慓疾,可以令阳气充盛,而饮食倍进,形体壮盛。不懂得其作用机制之人,大肆服用,导致“精气暗损,石气独存,孤阳愈炽”,久而发为淋证、消渴等病患,概言“五谷五肉久嗜不已,犹有偏绝之弊,况石药乎”,提醒其机制在于使用的偏嗜过用,告诫恐嗜欲者未获其福,而先受其祸。李时珍指出“有禀赋异常之人”,若使用石钟乳之类药物,“不可执一而论”。《本草纲目》引《医说》记载,武帅雷世贤多侍妾,而且常服用煎炼过的石钟乳等,以济其所欲。其妾之父患寒泄而不嗜食,求丹十粒服之,随即感觉脐腹热如火,进而出现热狂,跳入井中,救出时已遍身发紫泡,数日而死;但是雷世贤曾服饵千计,而了无病恼,反应实在奇特。又如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夏英公性豪侈,而“禀赋异于人”,其方入睡即身冷而僵硬如死,常服仙茅、石钟乳等,其寿命之长,“莫知纪极”。因其每日晨起用石钟乳粉加入粥中食用,有小吏偷窃而食之,遂发疽而死。从多方举例说明禀赋异常,对于石钟乳的反应性截然不同,明示体质因素是临证用药需关注的重要环节。
2 药食气味有不同,辨体施用药食有宜忌
《素问·五常政大论》云:“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指出根据个体体质对药物的耐受性不同,其用药应有不同。再如《灵枢·逆顺肥瘦》列举人有白黑、肥瘦之不同,故而有年质壮大、壮士、婴儿、肥人、瘦人之不同。《灵枢·根结》认为,“逆顺五体”是指人的“骨节之大小,肉之坚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浊,气之滑濇,脉之长短,血之多少”不同。故而针刺治病,刺布衣与刺大人采用不同的针刺方法。《本草纲目》承袭经旨,阐释气虚体弱,寒热偏胜,以及年龄等因素的不同,用药有所不同。
例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三卷》关于升麻的记载,李时珍解说,升麻具有“引阳明清气上行”之功,故而“此乃禀赋素弱,元气虚馁,及劳役饥饱生冷内伤,脾胃引经最要药”。其举例升麻葛根汤,为发散阳明风寒药,临床“用治阳气郁遏,及元气下陷诸病”,适用于阳气郁遏、元气下陷等病证,疗效甚佳。但是该方使用不可拘泥。李时珍进而引一病案,患者素饮酒,因寒月哭其母而受冷,遂病寒中,无姜、蒜不能进食。至夏季酷暑,又因多饮水,兼怫郁之病发,并右腰胀痛,牵引右胁,上至胸口,必欲卧躺。发作则频频如厕,大便里急后重,小便长而数,得酒、得热则稍止。但受寒食寒,或劳役,或入房,或愤怒,或饥饿,即发病,甚则每日发作数次。发作停止则状若无病。曾服温脾胜湿、滋补消导诸药,皆稍微止而随发。李时珍分析认为,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所致”。故用升麻葛根汤合四君子汤,加用柴胡、苍术等,用水煎服,服汤药后,仍饮酒一二杯以助药力,其药入腹,患者则感觉清气上行,胸膈爽快,手足和暖,头目精明,神采迅发。此后每发一服即止。然而若是减升麻、葛根,或者不饮酒,则效果变迟缓。这说明临床用药切合患者体质状况,对于药物作用的发挥和疗效的提高,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又如《本草纲目·木部·第三十六卷》记载,“枳壳破气,胜湿化痰,泄肺走大肠”,多用损胸中至高之气,故而一般只可二三服而已。用于“禀受素壮而气刺痛者”,宜分辨其为何部经,且治以别经药导之。引李杲之言,枳壳“气血弱者不可服,以其损气”,亦云“若气禀弱者,即大非所宜”。在此列举禀赋素壮宜用枳壳,而禀赋气弱、气血虚弱不宜使用。这说明因体质强弱之差异,即使是同一种药物其使用也有宜忌之不同。
《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三卷》记载,李时珍提出苦参乃是取其“苦燥湿,寒除热”,又具有治风杀虫之功用,并明确指出“惟肾水弱而相火胜者,用之相宜。若火衰精冷,真元不足,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提示药物使用宜兼顾体质,同一药物使用因体质差异而有不同宜忌,对于临床用药及配伍具有参考意义。
再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六卷》认为麦门冬治肺热之功为多,“寒多人禁服”,李时珍引《儒医精要》记载,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惟火盛气壮之人服之相宜。”故而“若气弱胃寒者,必不可饵”。《本草纲目·草部·第十八卷》天门冬亦记载,援引寇宗奭之言,说明天门冬性冷而能补,“患人体虚而热者,宜加用之”。其治肺热之功效突出,因其味苦,“专泄而不专收”,故而提出“寒多人禁服之”。李时珍亦解说,“脾胃虚寒人,单饵既久,必病肠滑,反成痼疾”。究其机制,在于“此物性寒而润,能利大肠故也”。强调脾胃虚寒之人,久用天门冬,必致滑肠,反成痼疾。因天门冬性寒而润,能通利大肠。
此外,《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三卷》言及升麻的作用,李时珍直接引“《素问》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解说人年五十以后,其气消者多,而长者少,降者多,而升者少,“若禀受弱而有前诸证者”,提出随年龄增长,气消而降多升少,故而若是先天禀赋弱而清阳虚陷,宜用“此药活法而治之”。《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二卷》关于麻仁的记载,小儿痢下赤白,“体弱大困”,使用麻仁三合,炒香研细末。《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三卷》关于黄连的记载,小儿下痢赤白多时,“体弱不堪”。以黄连用水浓煎,和蜜服用。以上说明因体质不同而服药剂量有不同。《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卷》关于糕的记载,李时珍提出,粳米糕易于消导,而粢糕最难消化,易于损脾而成食积,“小儿尤宜禁之”。
3 治疗反应因体而异,用药治病应中病则止
体质不同则对药物和针刺的耐受性及治疗的反应性不同,如《灵枢·论痛》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胜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胜毒也。”说明人体对药物的耐受性因体质强弱而不同,体肥骨壮胃厚者,对药物有较强的耐受性;体瘦胃薄之人,则耐受性较差。《黄帝内经》还指出,“人之骨强筋弱肉缓皮肤厚者耐痛”,“坚肉薄皮者,不耐针石之痛”,认为人有筋骨强弱、肌肉坚脆、皮肤厚薄之不同,对针刺反应则有耐痛与不耐痛之别。因而临床针刺用药注重因其体质不同而有所区别。《黄帝内经》提出人体对药物的耐受性因体质强弱而不同的观点,强调体质的不同是临证治疗须考虑的因素。《本草纲目》明言药物不可过服,宜中病则止。汗吐下法亦明确使用之宜忌,进一步说明临证用药关注体质的必要性。
例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五卷》关于艾的运用,李时珍解说,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太苦,其生温熟热,属于纯阳之品,“服之则走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则透诸经,而治百种病邪”,并指出“夫药以治病,中病则止”,临床防过度长久使用,而“助以辛热,药性久偏,致使火躁”。又如《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七卷》言及甘遂之使用,李时珍阐释,“甘遂能泄肾经湿气,为治痰之本”。然而“不可过服,但中病则止可也”,意在防其过用伤正。
再如《本草纲目序例·第二卷·张子和汗吐下三法》介绍吐法,认为吐法宜分体质,强者可一吐而安,而弱者作三次吐之,吐之次日,有顿快者,有转甚者,引之未尽,待数日再予吐之。吐后不禁物,惟忌饱食、酸咸硬物、干物、油肥之物。李时珍指出吐后心火既降,“大禁房室悲忧”,否则病患既不自责,必归罪于吐法之使用。其明确提出“不可吐者有八”,如性刚暴好怒喜淫之人、病势已危年老气弱之人、患病粗知医书而不辨邪正之人、病患无正性而反复不定之人、左右多嘈杂之言,皆不可吐。“吐则转生他病,反起谤端”,虽其恳切求之,亦不可强从。该篇的汗法指出,凡此皆发散之属,善择使用者,当热而热,当寒而寒;不善择者则反此,其病有变。李时珍重申“发汗中病则止,不必尽剂”,告诫“巴豆性热,非寒积不可轻用”,妄下则使人津液涸竭,留毒不去,则胸热口燥,转生他病。其明确提出“不可下者凡四”,如洞泄寒中,表里俱虚,厥而唇青手足冷,小儿病后慢惊,“误下必致杀人”。其余病大积大聚、大痞大秘、大燥大坚,非下不可,但须寒热积气用之,提示“中病则止,不必尽剂”。可见体质之强弱、情志之影响、年龄因素等体质相关差异,乃是汗吐下法需关注之内容,尤其是该篇在汗法、吐法、下法用药宜忌中反复出现“中病则止”之告诫,凸显其力戒过用伤正之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