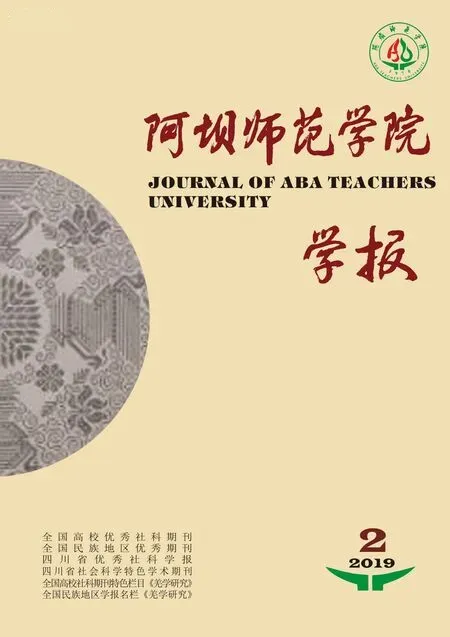行走在漂泊中的诗意——艾芜《南行记》系列小说的主题阐释
张高宇
艾芜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艾芜的创作从他的漂泊中得来,艾芜的漂泊和创作规定了艾芜,使艾芜成其自身,并由此与其他漂泊者和以漂泊为主题的创作区别开来。从艾芜的不同文本出发,把艾芜行走在漂泊中的诗意从下面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艾芜在漂泊的途中生存
在《人生哲学第一课》[1]18中,艾芜言道,他读书的条件已经失去,想去大城市谋生的计划也成了泡影,甚至连最低贱的出卖苦力的工作也找不到,他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挣扎在生死之间。当物质匮乏导致的窘迫来得最直接、最猛烈,即饥饿威胁着生命的时候,自然是痛苦不堪、忧心如焚,无暇顾及读书和大城市的漂泊生活,甚至忽略了大自然的美丽,只剩下能吃顿饱饭的最低层次的愿望。但艾芜自己却并没有被这种困境吓倒,生的希望依然涌动着,知道要有毅力,要去奋斗,才能摆脱困境,寻求生的机会。因此,艾芜的求生之路成为他的漂泊和流浪之途,它们主要有四川的怒江、云南某个偏远山区和缅甸的茅草地等。
在四川的怒江,艾芜写到:“江上横着铁链做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岩石,激起吓人的巨响。/……夏天的山中之夜,阴郁、寒冷、怕人”[1]121。咆哮怒吼的江水,震耳欲聋,惊心动魄之余,使艾芜感觉到就算两岸蛮野的山峰都要臣服于它的巨大威力之下。索桥是人力的象征,是人创造的作品,但即便是人工的痕迹,在自然的威力和伟力面前,也仍然显得薄弱和渺小。而夏天,本来应该是炎热难耐的季节,在这里却是阴郁和寒冷,这不仅体现了环境的恶劣和气候的高寒,更体现了这种恶劣和高寒对人的身心压迫带来的心灵的震撼和恐惧。在云南偏远山区,这种情况并不比前者好多少:“……在云南西部边疆流浪,饱尝了人世的辛酸。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天气常年炎热,疟疾流行……”[1]323云南本来就在中国的西南部,而云南西部,就是西部的西部,中国的最西边,与缅甸接壤。那里气候炎热,瘴气常年不散,有毒动植物造成的地方性疾病尤其是疟疾流行,严重威胁着人的生存,不利于人居住,大人都没法抵抗,很多小孩根本长不大甚至养不活。但正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艾芜开始寻求他的生存,把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而缅甸的茅草地,更是苦难的浓缩,他说:“……我在那边劳动过,病倒过,受过压迫、剥削和侮辱……”[1]326
四川的漂泊之途一样是艰难大道。“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云南的山道……”[2]132-133通过自己的双脚,艾芜把大地和世界聚集在一起。世界持立在大地上,大地穿过世界而伸延。因此,艾芜站立在大地之上,漂泊于世界之中。艾芜背弃熟悉的家园,来到陌生的荒芜之地做短暂的逗留,然后继续前行,周而复始没有终止。这些不仅给艾芜的身体造成痛苦,同时也给他的精神带来折磨。尽管如此,艾芜的身体虽在时间空间之中,他的精神却超越于时间空间之外。
二、艾芜在行走的路上创作
对于创作,在《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中,艾芜说到:“由四川到云南,由云南到缅甸,一路上是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油灯下,树荫覆着的山坡上,都为了要消除一个人的寂寞起见,便把小纸本放在膝头,抒写些见闻和断想。”[3]278可见,艾芜的创作,很多都是在路上开始和完成的,它包括直接的见闻以及对此见闻的感受和理解,主要包含着对人性中的丑恶的揭露和人性中的美好的赞美。
小人物对待女性的诸形态。在《流浪人》中,面对过路军官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不容拒绝的盘问,大脚女人都小心翼翼地搪塞着,生怕引火烧身,同路的一小伙子却忍不住接口告诉军官:“他们打花鼓的”[1]52。被小伙子泄露了身份,无权无钱无依靠的大脚女人不论如何推脱,最后还是被军官带走了。矮汉子一提到这事就“无名火高三丈……就是这狗东西一句话,把人家活活送给那几只饿老虎!”[1]60打花鼓母女俩被军官带走时,算命先生也跟着去了,似乎是因为不放心而去保护她们,“矮汉子这时已放下了酒杯,对那走在河床里面的算命先生,情不自禁地望着,脸上现出有些惆怅又有些羡慕的神色。”[1]54矮汉子惆怅什么呢?又羡慕什么?惆怅的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算命先生与军官抗衡,犹如螳臂挡车一般,是不自量力,军官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不费吹灰之力,跟去了也是白搭。但作为经常测算别人命运的人,算命先生对于生死博弈之道,自然是非常熟悉,他不会不知道自己此举的后果。但他还是毅然决定做无谓的护花使者,跟着去了,想必是存了必死之心。对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即便是悲剧,也凸显出它的悲壮,使人不能不心生敬畏感。矮汉子比算命先生勇谋有力得多,也同样经验老道,却不能自由抉择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因此,他羡慕算命先生,也敬佩算命先生的勇气。为了发泄这股“无名火高三丈”的愤怒情绪,矮汉子把无心说漏了嘴的小伙子追打得到处乱窜,满山都回荡着小伙子的哀嚎声。
死是到彼岸的祝福,生是在此岸的爱的表达。在《山峡中》,夜猫子及其团伙他们知道“原是在刀上过日子,迟早总有那么一天的”[1]132。虽然命中注定必有不得好报的死亡,但死亡都得等到来临之际,审判和惩罚才具有意义,这还不能等同于现世报。现世报既然尚未到来,那么能多活一天,都是上天的恩赐,是白赚得的。因此,他们虽然畏惧死亡但不对之恐惧,甚至还带有乐观式的侥幸心理,毕竟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的一切都成了多余的,况且也顾不了那许多。在这篇文章中,夜猫子的歌唱是高潮部分,具有统摄全篇的功能。夜猫子针对不同对象的两次歌唱,看似矛盾,实则在本源处是统一的。夜猫子第一次唱到:“那儿没有忧/那儿没有愁”[1]131,这是为小黑牛而歌唱;夜猫子第二次唱到:“这儿呀,也没有忧/这儿呀,也没有愁”[1]133,这是为艾芜而唱的。“那儿”是作为死的彼岸,暗示着对小黑牛生的苦痛的解脱,和对他到死的彼岸的期许和祝福。小黑牛得到了现世报,虽还没死,但跟死了没有多大差别,因此他痛苦的呻吟和死亡的控诉,已经显得多余。小黑牛还未断气就被扔进怒江激流,乃是送他早登西方极乐世界的神圣葬礼。而“这儿”,作为生的此岸,是痛苦的现实世界,夜猫子却说没有忧愁,并且她蛮横地不让艾芜离开她,她觉得她可以保护眼前这个处于生存困境中的男人,这乃是她对艾芜的朦胧的爱的向往和召唤。因为在爱的国度里是没有忧愁的,那里只有永恒的快乐和幸福。总体来看,夜猫子的第一次歌唱,带有原始的残忍的祝福的特点,而第二次歌唱却是纯净人性的爱的呼唤。由此得出,作为在土匪窝里长大的女孩,夜猫子自己的人性并未被扭曲,善良并未被泯灭,她的祝福和爱,都是美好人性的表达。
无所谓开始与结束的凄美爱情。在《红艳艳的罂粟花》中 “……叫作小玉的,一见她妈回去的时候,便挨到我旁边来工作,高兴地讲这讲那”,小玉说“我真失悔,人家叫我跟他走,我没有答应。我真失悔!……我以后呵,不论哪个,只要肯带我走!她没有说完,就朝前跑了。”[1]494小玉虽然识字不多,但凭着女性特有的直觉,她知道艾芜的心不属于这里,他铁定要离开这里,只是时间问题。她对于自己中意的男人,不想再次失去而让自己后悔,只要艾芜愿意带着她一起离开,她愿意跟着他走。这意味着,小玉在向艾芜传达爱的讯号。对于含蓄而矜持的她,如此直白表明心迹,她无疑有点害羞,因此“她没有说完,就朝前跑了”。此时,艾芜若追过去,必定有美好而浪漫的爱情发生,但遗憾的是,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了一段时间,艾芜决定要离开了,那时“小玉有着孤单的一个人留下的悲寂神情,凄然欲泪的样子……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不能泯灭。”[1]502-505正值青春的女孩,美丽又动人,作为正常男人,都不会无动于衷、视而不见的。有爱突然降临,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艾芜也不是不懂传递过来的爱情讯号,但他不接受此讯号,是因为他不敢爱也不能爱,他知道作为男人,理应对女人负责,而他给不了她幸福,他只有狠心装傻。小玉的悲寂和凄苦,艾芜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的,他“久久不能泯灭”的是心里的憋屈和苦闷无法释放。
坚守亲情和艺术,怀疑光明的到来。在《瞎子客店》[1]139-145中,艾芜让一个处于黑暗中的瞎子,来观感这个黑暗的世界,并让瞎子自己言说黑暗世界的黑暗。瞎子(年轻时并不瞎)在无二爷的戏台上演《蒋世隆抢伞》与明珠相识并结缘,也因艺术与其私奔和建立家庭,并靠搭戏台演戏谋生。但当地一个大军官不仅抢走明珠,还不准瞎子唱戏并拆了他的台,明珠也含恨自尽,幸福的家由此被拆散而破亡。瞎子哭瞎了双眼,憎恨并咒骂万恶的世界以致不愿意再看到这样的世界。他跟同样是瞎子的儿子住在岩洞里,靠开旅店为生。对于每一位路过的旅客,瞎子都希望旅客帮忙圆谎,说儿子不是瞎子,说他只是暂时看不见并能治好。这既是对儿子的爱护的表现,也是希望儿子能陪伴孤独的自己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说,爱儿子即是爱自己。瞎子一生与艺术结缘,艺术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中和生命里,他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艺术的存在。瞎子天天都练唱腔和拉胡琴,旅客和路人也都自发聚集过来听他的自娱自乐。这直接说明他对艺术的热爱,忠于艺术人生,同时这也间接表现出对老婆的精神的寄托和对爱的守护,因为艺术对于他而言,聚集和保藏着他的生命的全部。但瞎子的儿子银宝,面对艾芜的“老虎不可怕么”的询问,不认为虎叫可怕,认为“世间最可怕的,不是这叫声哪……那光明的日子为啥不快点到来了呢?”[1]139-145银宝希望光明的日子到来,这既是对自己的期许,也表达了对社会安定和谐的美好意愿。但银宝却质问光明的可能性,而且是带点不耐烦的质问,表现出他对光明世界到来的迫切,但更为确切地表达出他对此光明世界能否真正到来的质疑。质疑它,也就意味着不再相信它,也就不再需要它,它就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也许银宝觉得,自己本来就看不见,光明到来与否,都与自己无关,自己该怎么生活,还得怎么生活。况且,就算是光明有序的世界,也不是或不仅只是用肉眼去看的,而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感受,因为光明和美好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幸福度不在外在的世界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的黑暗给人带来的生理上的痛苦,远没有它给心理上造成的痛苦更让人绝望,而让大家都谈之色变的老虎,对他而言都不重要也没有意义了。
思念故乡和慈母,坚守独立的精神人格。在《墓上夜啼》中,艾芜写到:“回首岷沱的故乡/泪滴在异国的湖上/但愿将朽的皮囊/丢在慈母墓旁/冷静的幽夜呵/化作点点荧光/减我慈母的凄凉/方春来临呵/化作朵朵花香/让我慈母好徜徉/回首岷沱的故乡/泪滴在异国的湖上。”[4]295艾芜身在异乡,这个异乡不是一般的异乡,而是异国他乡,即缅甸。艾芜漂泊在异国他乡,他才会思念故乡,并从思念故乡到有归家的念头,因为他自己的全部精神动力和寄托都扎根于生他养他的故乡。作为儿子,另一头牵扯着他的心的是他的慈母,远离了故乡和慈母,没能回去祭拜,但根还深深埋在岷沱的那片土地上。在幽静的夜里,疲惫不堪的一个人,更显孤独和凄凉,也更会想念慈母,想跟慈母诉说自己的所有遭遇和苦痛。这看似孤独而略显脆弱的艾芜,却拥有他自己的精神人格。在《漂流曲》中,艾芜写到:“两天不曾吃饭/三天不曾睡眠/怕看人家嘴脸/怕向人家乞怜……”[4]296吃饭和睡觉,本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但本能的需求现在却变成了本能的反感和拒绝,因艾芜不想低三下四看别人脸色行事,也不愿装可怜求人怜悯施舍,这表明他有他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该文中提到万慧法师,他曾经在艾芜最为艰难的时刻,给予了艾芜物质帮助,并给他指了一条求生存的方法,还教给艾芜知识和学问[1]4。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慧法师是艾芜一生中最为感恩的人也并不为过,故艾芜不想因追寻并奋斗于光明的社会秩序而连累恩师,毅然搬离了恩师住所。
三、诗意的呈现
对于漂泊,艾芜在《南行记新篇》后记中写到:“滇缅相接的边界地区,我年轻的时候,在那里生活过的一段期间,有痛苦、有欢欣、有留恋、有憎恨。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可算是我的生活基地……”[5]505稍后,艾芜继续写到:“第一次南行记,饱尝了人间的辛酸,生活的痛苦;也对山川的美丽景色,感到欢欣,劳动人民的纯真善良,深为喜悦。”[5]387这是艾芜对他自己第一次南行漂泊的回忆及评价,时隔多年,提起它,艾芜都很兴奋而不是痛苦,这说明漂泊带给艾芜的是更多的精神上的快乐。这意味着漂泊之途同时就是精神之旅,漂泊的冒险同时也是精神的历险。这种生死相依共存的极限体验,会因极度紧张后的舒缓产生的巨大刺激和快感,这是任何其他快乐无法比拟的精神财富,它会化作积极的精神动力激起人去应对更多的不可知的命运的挑战。这些艾芜把它们都记录在了文字里:如《爱》在战争中的家破人毁凸显着亲情的不舍,《快乐的人》中的同行恶性生存竞争也映衬对生活的不屈和乐观,《山峡中》小黑牛对生的渴望与死的不屈和夜猫子对艾芜蛮横的爱,《瞎子客店》瞎子对爱情和亲情的守护、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光明的态度等。
因此,对艾芜而言,漂泊是大地的负重远行,创作是对负重和远行的显现和揭示,它显现和揭示了生死离别、祸福相依、失败与痛苦、委屈和耻辱等。诗意的呈现,就是聚集和敞开在这些漂泊和创作中,它是艾芜按照他经验世界和人生的方式承受并守护他自己的命运,艾芜把它称为他生命中的“纯金”①[6]。这“纯金”,改变着艾芜与他们的关系,他们使艾芜在自己的生命中和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处身和归宿。以克钦山的一个夜晚[1]174为例,随着光的地平线的消退并隐身而去,整个漆黑让艾芜感到异常狞猛。艾芜凭借听觉倾听到了大盈江震动心弦的水声,凭借视觉看到了树间轻轻款款飞动的萤火虫。对于此,艾芜惊异于它的造化神奇,却没有产生陌生感和恐惧心理,反而激起他的兴奋,使他喜欢上它。此刻处于生存困境中的艾芜,能够从困境中暂时摆脱,欣赏自然的美丽,除了源于他固有的文人情怀外,更在于这是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居住在大地上的本然状态,亦即与大地相亲熟,逗留于此,而不应为了生存疲于奔命,甚至残害生命。这些应该是文学承担的使命。文学表现大地的本性,滋养着人性和生命。在漂泊途中,艾芜的确用文学打发时间、驱散苦闷和缓解痛苦,也用文学提升精神并鼓舞自己前进,他也把他自己所遭遇的经历,都诉诸于文学,保藏于文学,借以发泄自己的苦闷和快乐。结合他自己的生命历险和创作经验,艾芜认为文学:一能够驱我们的逐利己之心,使我们对于陌生人发生亲密的关切,激起深刻的同情;二能够驱除因袭的观念,使我们对真实的人生,有着正确的见解;三能够武装我们,使我们不和恶势力妥协,并能鼓动我们为正义而战[7]11-13。文学具有召唤和指引作用,它召唤并激发人们身上固有的积极能量,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才是改变旧历史和创造新历史的真正动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力量就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应该是被动、消极观望,甚至忍辱偷生。
基于此,艾芜呼喊:“热爱生活,到生活中去!”[5]389艾芜认为在生存的艰难面前,我们不要丧失信心,不要被暂时的困境吓倒甚至压垮,而是要勇于面对困境,乐观积极地想尽办法克服它。人生就在于勇于面对挑战,挑战成功了,不仅战胜了困境,而且还能得到莫大的精神快感和享受。这种精神上的快感和享受是精神的无穷财富,它为人反观自身并突破、超越自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它不仅指引人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也给予其他人或后来者以人生的启示。
总体而论,艾芜漂泊中的创作语言比较平实,不华丽铺张,但平实中透露出深刻;艾芜的情感流露着平淡,几乎没有愤激之辞,但平淡中蕴含着深沉;艾芜笔下的众人物虽然卑微,卑微得犹如一颗颗不起眼的尘埃,但卑微中显现出伟大;艾芜的创作虽然是一时一地的人物与事件的聚集,但它穿透了历史,维系着人性的命脉,显得深邃而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讲,艾芜的漂泊和创作,具有不可多得的精神意义和研究价值。
注释:
① 谢辉认为:“老何、老朱,他们没钱没势,居无定所,拥有的只是一身的牛劲和善良的禀性。然而边境的生活尤为难熬,但两个人不论怎样腹忌难耐,却从未动过伤人性命、谋财害命的歹念,靠着出苦力、抬滑竿的普通活计养活自己。在贫苦的境遇中他们依然积极乐观,对待朋友真诚友善,尽管自己生活落魄不堪,依然能够雪中送炭,帮助仅有一面之缘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