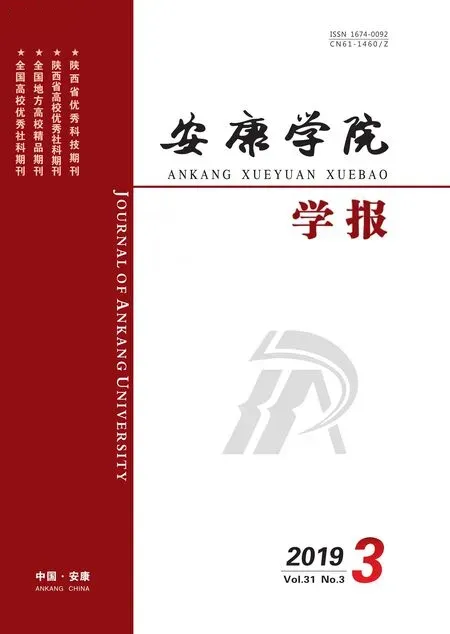《诗学》中古希腊悲剧的“严肃性”阐释
——以《安提戈涅》为例
吴月颖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戏剧艺术自古就是世界正统的艺术门类,其中古希腊悲剧则代表着世界艺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在亚里士多德《诗学》这部论“诗”的文艺理论专著中,悲剧以无可置疑的优越姿态胜于史诗,成为《诗学》中篇幅最大的戏剧门类。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作出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29可见,“严肃性”是统摄古希腊悲剧的一个重要概念,因为悲剧的首要标准就是对于一个严肃行动的摹仿。何为“严肃”?它的基本阐释是“庄重,令人敬畏”。德国古典主义美学家温克尔曼用“高贵的单纯,伟大的静穆”形容古希腊艺术,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的最高理想和对“严肃性”的一种阐发。这则美学理念概括了古希腊人民对艺术的崇高激情,但同时理性的回溯稀释了澎湃的热情,古希腊悲剧在一种“严肃”的状态下回归内心的静寂,以一种“克制”“适度”凝练的精神力量代替情感的勃发。“严肃性”在古希腊悲剧中是一个隐晦的概念,它可以体现在悲剧形式的严谨方面,同时还含有辩证统一的哲学意味。本文将结合剧本《安提戈涅》,从三个方面对“严肃性”进行阐释,即悲剧主题的“严肃性”、创作形式的“严肃性”和悲剧效果的“严肃性”。
一、悲剧主题的“严肃性”——崇高
悲剧的主题往往是和“崇高”相通的,这种“崇高”与令人敬畏、庄重的“严肃性”异途同归,都致力于追求一种更永恒的精神境界。古希腊悲剧的结局近乎相似,都是正义之士或本不该遭受如此厄运的人的自我毁灭,不论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还是《美狄亚》等著名剧作,英雄式人物毁灭的结局是古希腊悲剧难以变更的信条。但毁灭不是人生的终章,在突破人类精神局限中获得更高的正义才是生命的终点。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主人公在古希腊城邦法律与“神律”之间做出的主动抉择,更是直接导致了这位英雄人物生命的陨落。《安提戈涅》悲剧主题中充斥着宏大、高尚的人生选题,它是“礼”与“法”发生严重冲撞的结果,自然之礼与城邦之法从不应该存在于矛盾的两端,它的本质是理性纯粹主义的荒唐落幕。悲剧主题的严肃性反映在安提戈涅对高尚行动的摹仿,同时,这种严肃性也包含着一种更普遍的人伦。
《诗学》第四章中提道:“诗由于固有的性质不同而分为两种:比较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即高尚的人的行动;比较轻浮的人则摹仿下劣的行动。”[1]36所以按照戏剧的性质划分,悲剧的要求是严肃的人模仿高尚的行动。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是一个带有强烈反叛意识且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的女性形象,作为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她应该尊重宗教神权赋予的礼俗;作为王室贵族,她应当维护王权统治者和城邦法律的尊严,但是当自然之法与城邦法律发生不可逆转的冲突之时,安提戈涅选择的自我毁灭终于昭示正义的所在。她的两个哥哥厄忒俄克勒斯和波吕涅刻斯因抢夺王位互相残杀,两人皆战死。但波吕涅刻斯因在战争中请来外国援军,被执政者克瑞翁判为叛国罪,尸体必须曝于荒野;而厄忒俄克勒斯在克瑞翁看来则是保卫城邦为国牺牲,所以应当得以厚葬。克瑞翁作为希腊城邦的王权拥有者和法律制定者,其判定动因就包含着自己的整治规划。一般而言,叛国罪针对的是城邦外部的争斗而非本国之内的权力斗争,波吕涅刻斯虽然引来外国援兵,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希腊城邦带来实质性的威胁。克瑞翁严惩波吕涅刻斯其实就是他作为一个初登政治舞台笼络人心的政客的政治表演。在克瑞翁刚登场时他说:“长老们,我们城邦这只船经过多少波浪颠簸,又由众神使它平安的稳定下来。”后来又说:“一个人若是没有执过政,立过法,没有受过这种考验,我们就无法知道他的品德、魄力和智慧。任何一个掌握着全邦大权的人,倘若不坚持最好的政策,由于有所畏惧,把自己的嘴闭起来,我就认为他是最卑鄙不过的人。”[2]27可见,克瑞翁一直在神权与王权之间权衡,他不舍摆脱神权的庇护,又不想失去王权的绝对统治,因此他选择了用自己的政策僭越神权来达到他所追求的王者魄力,所以他下令将那个叛国者的尸体裸露在野外不得被亲属埋葬,违者立即处死。要知道在古希腊民众的信仰里,神律规定了埋葬死者是亲人最大的义务,如果亡魂找不到归途,就是对天界神祇的不敬,同时也是家门的耻辱。安提戈涅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冲击着克瑞翁的专制,揭开他隐藏在政客面具下的伪善,用人性的光辉还哥哥在世间最后的尊严。摆在安提戈涅面前的从来不是生与死的问题,而是善与恶、高尚的德行与下劣的伎俩的选择问题。所谓严肃的人摹仿高尚的行动,就是指严肃的主题会指导主人公如何对高尚的行动进行再现与创造。对高尚行动的再现表现为安提戈涅式人物良好的律己能力,他们在保持美德而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对传统文化中优良的精神文明和社会生活中因道德观念和民族习俗而形成的礼节进行传承;而对高尚行为的创造就体现为对礼法中不合乎普遍人伦之处进行反叛。悲剧主题的严肃性同样体现在昭示普遍的人伦上。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阿努图斯和莫勒图斯指控苏格拉底不敬神而败坏青年,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是第一位的,宗教是一种以政治服从为目的的哲学活动。在《安提戈涅》中,宗教的神法依然被推到了至高点,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安提戈涅推崇的是神法中彰显个体化情感和普遍人伦之处,而非浅薄地盲目崇拜宗教中的神性启示。“国家主义是一种客体化的道德,当它抽除了作为人性生存的基础时,当它毫无人道地践踏和扼杀人性与亲情时,以人性抗拒非人性的客体化的国家法律自然就是合理的了。”[3]安提戈涅的反抗是对人性和高贵德行的捍卫,她背负的不只是自己对亲人亡魂的责任,也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与个人欲望的表达,而是代表着所有尊重人性、恪守伦理的个体诉求,这就是令人敬畏的“严肃性”所展现的普遍人伦。所以,即使在国家强烈意志统治下的城邦法律也无法对个体的伦理义务视若无睹,普遍的伦理道德就是另一维度的神法,“悲剧人物性格和动作情节所遵循的目的是一种神性的伦理力量(理想)在人世现实中的体现”[3]。
二、创作形式的“严肃性”——秩序
《诗学》第六章至第二十二章是悲剧论部分,内容包括悲剧的定义、悲剧的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分析等,其中着重探讨情节的安排与“性格”,以及悲剧各部分体量的安排,最后还涉及悲剧的写作及言词、风格等行文规范。这一系列的创作形式要求,都旨在构建悲剧形式上的秩序和适度的美,即悲剧从创作之始就要有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的精密构思和巧妙布局,而不是自由涣散的灵感堆积和随意散漫的内容堆砌。正是这种严格的创作要求将悲剧限制在同一个美学标准之内,以达到庄重、审慎的“严肃性”氛围。
从悲剧的定义来看,《安提戈涅》主题严肃、情节完整、行动内容体量适度,是一部在创作实践和思想范畴上都达到标准化的古希腊悲剧。其主题关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健康生态,凸显英雄人物高贵的德行与对正义的执守;从情节整一性来看,事之有头、有身、有尾,从一而终贯穿着安提戈涅坚守人性光辉与自然之法,埋葬亲人而选择自我牺牲保全正义的行动;并且其行动体量适度,从安提戈涅请求伊斯墨涅的帮助到克瑞翁自食其果,行动集中在十三场之内,不像史诗情节过分冗长,可以较为突出地展现悲剧效果。而创作形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情节(布局)的安排,即是否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包含简单行动还是复杂行动;情节内部有没有“突转”“发现”与“苦难”;顺境逆境的编排;等等。在情节中起引领作用的是可然律与必然律,它们关乎整个行动的动因,是奠基性的条件。安提戈涅的行动在可然律的基础上进行构建,整个剧本取材于神话故事,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尽管在可然律指导下进行的行动不一定是现实的,却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它具有普遍性。安提戈涅身处王室,举手投足间都背负着君主统治下的政治谋划,这看似接近神坛的命运大大削弱了悲剧的普遍性。但安提戈涅也是在神祇庇佑下的普通人,她有着和普通民众相同的苦难经历与难以决断的人生选择,在人性泯灭与坚持正义之间她选择了最普遍的人伦,虽然情节存在虚构成分,但能呈现艺术之真。也就是在给可然律一个普遍性的条件之后,情节的发展走向了一种因果制约和自我毁灭的必然。《安提戈涅》与所有古希腊悲剧相似,严格践行悲剧的美学规范,在秩序规约的严肃框架中自成一派,但也正是因为创作形式的“严肃”,才使各式各样的悲剧形态得以被引向同一个归途,才能使古希腊悲剧有这样一把高质量的标尺,让艺术水准欠佳的剧作家自惭形秽。
三、悲剧效果的“严肃性”——平衡
悲剧的“卡塔西斯”的内涵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按照《诗学》第六章原文中给的定义“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36,悲剧效果经学者们解释大致分为“净化”和“宣泄”两种。但笔者认为,悲剧效果最终会回归到观者观看状态的“严肃性”,即悲剧的苦难意识从不会缺席,人生的真相就是痛苦与不幸、怜悯与恐惧,观者意欲的波涛会随着英雄人物的命运被宿命挟持而汹涌不止;但是古希腊悲剧又往往用一种高强度的精神力量与普照的人性光辉抚平意志的风浪,使得观者肯定现实人生并激起抵抗,悲剧效果在热烈的情感澎湃与冷峻的命运审视下被中和,灾难的外观世界终究会被摄入内心的平和,而达到心理状态趋向平衡的“严肃性”悲剧效果。
纵观《安提戈涅》的人物结局,每个人都难以挣脱悲剧宿命的桎梏。安提戈涅睿智、果敢、倔强,敢于挑战统治者的不合理权威,当克瑞翁质问她敢违抗法令的时候,她说:“我敢;因为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祇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因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的律条,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33。在安提戈涅心里,集合宇宙秩序与永恒正义的自然法要远高于专制的政客为了巩固统治而制定的人之法规,也许生而为人不管是长在帝王家还是落入寻常百姓家,总是会陷入两难的境地。安提戈涅自身的社会属性与人性的本能抉择的博弈,是悲剧苦难的开始。安提戈涅坚定的性格决定了她反抗的坚决,但这并不意味着生命中的灾难会因这场正义的选择而安稳度过,而选择的背后就是对生命的放弃。《安提戈涅》剧本的典型性就在于情节处理的极致性,首先是自然法与人法、生命与正义的无法调和的冲突,而作者极力把这种冲突勾画到情绪的顶点,让观众在对安提戈涅、伊斯墨涅的极度怜悯与对克瑞翁的极度憎恶中达到高潮。其次是反面人物终究悔悟,观众的精神得到略微缓和之后,又即刻感受到命运之手的残酷。克瑞翁终于在关键时刻迷而知返,但却仍然没有追赶上命运的脚步,安提戈涅、海蒙、克瑞翁之妻全部离开人世,命运没有那么仁慈,没有给克瑞翁任何挽回的余地,观众们立刻又被这种极致的悲恸笼罩。观众的每一个微妙的情绪都受剧作家情节设计的牵动,怜悯与恐惧如影随形贯穿于剧作始终。人生的苦难不会因为看客的怜悯而终止,因为看客本身也是被苦难命运拨弄的一枚棋子,人们可以靠人性的光辉互相告慰借以勇气,但泪水无法冲刷掉安提戈涅的毁灭结局。悲剧效果中的恐惧大多来自死亡与毁灭,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性中的本能,这种恐惧来源于未知。但以安提戈涅为首的一批英雄人物以死亡走向正义,以毁灭彰显人性的光辉,让死亡的结局不再是地狱式的空洞而变成已知的荣耀,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强加给观众恐惧又化解了恐惧,最终达到观众内心的平衡和释然,这才是悲剧的卡塔西斯要带给观众的真正效果。
四、结语
古希腊悲剧中的“严肃性”表达不只是一个单维度的概念,它涵盖了《诗学》中对悲剧创作至悲剧内涵的流动性过程。《安提戈涅》只是浩如烟海的古希腊悲剧中的典型作品,不论是主题的崇高、创作形式的秩序性,还是悲剧效果达到的平衡感都严格践行了悲剧的“严肃性”设定。而究其根本,“严肃性”折射出的是古希腊悲剧的“适度”美学,“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的中心思想是‘中庸之道’,他认为美德须求适中,情感须求适度”[1]29。纵观古希腊悲剧的“严肃性”体现,主题崇高以求悲剧体制的严格规约;采取有秩序的创作形式以达到适度的美学规范;悲剧效果给人的平衡更是激情与冷静互相制衡的结果。就像《悲剧的诞生》中日神所代表的“梦的外观”与酒神所代表的“醉的世界”在斗争中和解,古希腊悲剧在多重元素矛盾两极的撕拉牵扯中,最终因为洞悉世事的智慧,将饱含民族与时代精神的“希腊意志”与对宇宙天理运转之道的敬畏之心附着在悲剧艺术之上。悲剧主题的适当、创作形式安排适量、悲剧效果适度是古希腊悲剧“严肃性”的深度阐发,古希腊精神的高贵肃穆、理性自主也得以在适度的美学原则中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