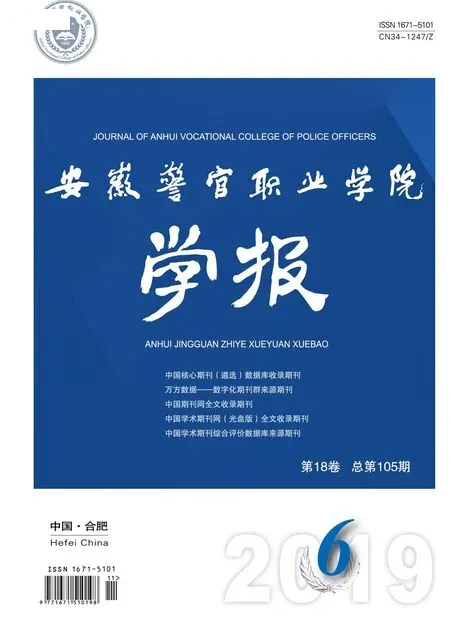从道德到法律:当代大学生犯罪预防教育路径新探
庄绪龙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600)
一、问题意识:频发的恶性刑事案件引起的教育反思
大学生,曾经被社会贴上“天之骄子”的标签,即便在当下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大学生仍然是社会中受教育层次较高的群体。 毫无疑问,“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 既是民族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1]俗话说,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与此同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知识水平、文化素质也就越高。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大学生等高素质群体的期望和要求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不仅在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准施加要求更高,而且在道德素养、社会责任承担等角度要求也会更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诉求。
然而,近些年来,在大学生群体中时常出现一些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比如陕西西安“药家鑫交通肇事后灭口杀人案”、“上海浦东机场儿子持刀杀害母亲(未遂)案”以及新近发生的“林森浩杀害舍友案”、“北大学子弑母案”、“中科院研究生被杀案”等,引发社会公众对大学生群体的普遍关注。
在法律程序上, 该类案件无疑会成为司法机关处理的对象, 涉案大学生也必将会伴随司法程序的推进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案结事了。 然而,这些大学生涉嫌犯罪的案件, 尤其是我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频频实施恶性刑事犯罪,留给法学界、教育界无限遗憾。 通常而言, 犯罪是单个的行为人以损害国家、社会、他人利益的反社会行为,存在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 并且犯罪的发生往往是矛盾累积的一种爆发。 但是,在大学生涉嫌犯罪的案件中,不少行为人根本不具备犯罪学上关于犯罪原因论的界定,被害人往往是其至亲至爱的亲人、朋友等,比如,在“浦东机场杀害母亲案”和“北大学子杀害母亲”的案件中, 被害人即为其亲生母亲; 在“马加爵杀害室友案”、“林森浩杀害室友案”以及“中科院研究生被杀案”中,被害人与行为人皆为朝夕相处的同学,关系不可谓不亲近。
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反思: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天之骄子不顾一切,走上不归路?有没有办法有效的阻止该类悲剧的发生?
二、当前我国大学生教育的主要现状及其分析
(一)大学生犯罪的原因归纳
对于我国当前频发的大学生恶性犯罪案件,存在一些理论分析。比如有论者归纳认为,大学生犯罪的主要原因有:性格和人格存在缺陷、学校教育不适应现实需要、 家庭教育失败以及社会犯罪亚文化渗透等。[1]19现阶段,学界主要从社会生态学角度、教育学角度和法学素质教育角度展开, 存在以下几个观点。 其一,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视角,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先进文化的要求存在一定脱节。具体而言,人们在努力实现经济自由、经济独立的过程中,可能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过于压抑,这也是当前不少人迷茫、感觉生活枯燥的内在原因。大学生虽然并未深入接触社会,但是社会中的文化缺失、精神匮乏问题也同样对其产生影响。 其二, 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模式、方法可能在实效性角度存在不足。 其三,从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层面,除非学习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其他专业的学生知法、守法的法治意识并不清晰, 高校对于学生的法治素养教育比较薄弱。
应该说,上述几种观点的归纳,对于当前我国大学生犯罪的原因作了较全面的解释, 尤其是教育学视角与法律素养视角的批评, 基本符合社会现实情形。 当然,上述观点,大多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方向性归纳,并未明确化和具体化。 事实上,导致大学生犯罪,存在着复杂的因素,主要包括文化生态、意识观念、价值取向、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多种交叉混合的因素。
当前, 国家教育部门十分重视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在小学、 中学和大学分别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强化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然而,反观社会现实,我国目前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取得很好的成效, 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完全没有问题。 在上文所提及的诸多大学生犯罪,应当引起我们反思。
(二)“德育观”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
认真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看出,我们更多的是侧重于大学生的“德育”,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 而忽视了大学生的法治教育。 当然,应当承认“德育”教育是基础性、关键性的教育内容,它决定了大学生群体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基阶段的思想模式, 德育教育的导向作用、 激励价值对于我们塑造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有不可置疑的作用。
然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 人们得以与世界交流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价值多元、文化多元色彩不断强化,对于广大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思想塑造产生了较大影响。换言之,在当前社会发展水平高、文化交流多元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德育”观价值理念不可避免地遭遇冲击。这无形中对青少年和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导致以“德育”观为主要载体或者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当前的背景下有些力不从心甚至“失语”的味道。 因此,德育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正成为教育界研究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三)“德育观”教育模式的逆向反思
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 从不懂事的婴幼儿到初谙世事的少年,再到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应当有所变化, 这是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基本规律。
比如,在孩提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必然是该或者不该的命令和要求。我们经常看到,小孩子在乘车时吵叫,此时作为教育者的父母一般都会制止,甚至严厉斥责。 当然,也有些父母会在制止、命令的同时,辅以解释,比如“吵闹会影响到别人,这样不尊重别人,不礼貌,要做个好孩子”之类。 其实,在控制不住自己吵闹的小孩子那里, 其在父母斥责命令时能够做到不吵不闹,但很难理解吵闹与尊重、礼貌之间的关系, 甚至根本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属于“吵闹”,属于影响到别人安宁的“不法”行为。因此,在此阶段,父母命令、说教甚至指责的方式虽然带有家长主义的痕迹,但至少能够收到良好效果,且不会引起被教育者的逆反, 因为小孩子在这个阶段可根本认识不到父母的教育对其行为作了否定性评价;再如,对于初谙世事的少年而言, 其做错事或者影响到别人的休息,此时作为父母就不应当以要求、命令甚至斥责的方式进行教育。这是因为,此阶段的被教育者已经有了一定的自尊意识,即便其行为方式、行为性质尚不成熟,但其心理已经在成熟的进程中。在此阶段,对其教育方式应该以引导和解释为主,命令甚至斥责的方式应当慎重。
对于已经年满16 周岁或者18 周岁的大学生而言,其对社会的认知水平几近成熟,自尊心等人格意识基本具备, 此阶段的教育如果还延续少年时段的说教、解释甚至孩提时代的命令、指责等方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这必然会引起心智成熟的被教育者的思想对抗。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逆反心理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社会心理, 尤其是在面对一些不能令人信服的人和物时,单纯的正面教导甚至要求,可能会遭遇心理抵触。 因此, 我们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再沿用说教、灌输等“简单粗暴”的方式,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因此,现阶段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在教育内容上做文章, 更要在教育方式和理念上下功夫。当然,本文绝非否定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及德育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正确性, 绝非否认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必要性。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在强调德育观的同时,也应该强化对大学生教育模式、内容、方向的系统反思,尤其是教育模式的反思。 笔者认为,在坚持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原则和方向的前提下, 对于教育的模式和内容需要进行系统反思, 不断优化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成效。
三、“德育观”教育应从灌输走向自我需求
道德,是较低限度的行为规范,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基础性要素。 如果每个人都无视道德要求我行我素, 那么很难想象我们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然,如果在某一领域道德不能有效治理的话,法律必然会出手制止。
比如日本, 在公共场合吐痰、 乱扔垃圾被视为“轻犯罪”,所以只有那些对被处罚、拘留、罚款不在乎的人才会随意而为。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道德的遵守绝非与生俱来的高素养, 而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要求。但是,遵守道德意味着对自己自由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是普遍认同的正当限制,但是在经济学视角, 这种对自由的限制毕竟是对自己权利的影响。
对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德育教育而言, 教育的最佳效果就是使得被教育者力争成为“慎独”者,即在原本有机会做不道德、违法事情的情况下,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 凡事通过法律甚至刑法规定这种生活琐事,显然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法律不理会琐碎之事”格言的要求。那么,道德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贯彻落实, 主要应当通过道德教育的方式完成。 然而,道德遵守是自我约束的结果,在理性经济人那里,自我约束意味着利益的损失甚至放弃,那么应该如何才能达成这种价值认同呢? 当前我国“德育”观的教育方式,大都采用灌输、说教的方式,正面诠释道德的价值、道德遵守的要求等,这种教育方式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中可能味同嚼蜡, 并无心灵震撼与启发效果。 因此,为了达到道德教化目的,我们必须转变教育理念,将灌输、说教的方式转变为自我管理和自我认同。
从两则真实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道德需求”会带有强烈的认知震撼。一名四岁的女孩被压在车底,看到这一幕的“路人”急忙上前施救。 该路人在施救时并未意识到伤者是何人,直到孩子喊“爸爸”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救助的是自己的女儿。 不幸的是,最终没能挽救小女孩的生命。姚某六岁的儿子玩耍时不慎落水。路过此地的姚某,明明知道有小孩落水,但是却冷漠地离开,事后才知道落水死亡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儿子,追悔莫及。
上述两起真实案例,一正一反,足以让我们感受到道德的巨大力量:助人者,可能就是助自己! 即便那名小女孩最终不治, 但其父亲不会因为自己不救助而悔恨。 所以,认真对待道德的人,最终也可能被道德温柔以待。 相反,那种与己无关、高高挂起的道德旁观者, 或许有一天会因为自己的冷漠和道德失范永远遗憾甚至遭受到惩罚。社会生活中,大量事实证明,人们在肆意放松道德要求的同时,在另一方面或许就是道德缺失的受害者。 这是因为,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试想一下,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不讲道德、无视规矩,那么每个人又都会成为道德缺失的受害者。再如,在南京彭宇案发生后,大家都会对老人摔倒的现象不闻不问抑或“有心无力”,因为害怕对方“碰瓷”。虽然碰瓷现象的确存在,但这仍然不是我们逃避道德要求的借口。 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想、都这样做,那么等到我们自己年老体衰摔倒在马路上时, 是否就没有理由要求别人来救助自己?
由此可见, 道德缺失的危险和实际损害并不针对任何特定、单独的个体而言,而是会在时空上持续性的延宕至整个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不特定个体。 事实上,道德信念及其实践往往与不特定的、具体的公民之存在样态及其生活呈现出不特定的相关性, 道德信念及其实践在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发展与优化不特定公民个体生活实践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和统一性。 因此, 在德育观教育的模式抑或方法选择上,要避免空洞的教化与灌输,改变单纯、生硬的教育方法, 已经成为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要求, 从灌输到自我认同、 从宣教到自我需要的转变, 将是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成功有效的基本方法和路径。
四、“法育”教育观理念及其展开
就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而言,道德教育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法治教育。 根据笔者多年的观察,在大学生群体中,即便其是成年人,即便其思想成熟稳定,即便其道德素养不差甚至高尚,但未经法治教育前,其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运用,几乎是缺失的。换言之,在我国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法盲”大有人在。 甚至有学者尖锐指出,当前大学生频繁发生恶性犯罪,暴露了其对“生命权意识”的缺失。[2]因此,在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过程中,强化对其法律素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令人欣慰的是,当前高校普遍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对于大学生法治素养教育而言无疑是有益举措。
但是,法律教育同样是枯燥乏味,不少大学生对该门课程并不重视, 课程结束后几乎仍然对法律一无所知。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教学时间少。作为两课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基础课,虽然是必修课程,但不可讳言教学时间难以保证,通常只有一个学期的课程。 然而,法律又是一门体系庞大、内容复杂的课程,因此在短时间内难以培养学生的积极性;其二,教学方式机械单一。对于法律的学习,首先需要培养兴趣,否则难以应对浩如烟海的资料、理论。即便作为通识教育的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不需要对法律知识拥有专业水平, 但至少应该明白权利、义务、程序等基本概念和价值,明白生命、自由、人格的珍贵及其在法律中的地位,最终培养学生在思想意识中的规矩意识、 底线意识和规则意识。 这种规矩意识、底线意识和规则意识,虽然与道德教育存在部分重合, 但是这与法治素养的教育并不冲突。客观而言,我们国家正在建设法治社会, 需要公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群体具有良好法治素养,法治社会建设任重道远。有学者指出, 大学生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是整个国家依法治国的重要部分。[3]
应该注意的是,在法治素养教育的教学过程中,与道德素养教育的道理一样, 应该尽量避免单纯的灌输与说教,多以经典案例阐释相关理念,引导学生对规则、规矩的尊重以及权利、义务的认识,并最终形成对法律精神、法律规范的自我认同和自我需要。
应该说, 对于大学生法治思想和法治素养的教育,能够让他们明白规则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法律产生兴趣和热情。值得警醒的是,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阶段, 但是我国目前的社会形态搭载的包括法律意识、 价值取向等在内的各种思想意识与现代社会所倡导的民主、 法治理念等为基本支撑点的现代社会的思想意识和思想储备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在有些方面还尚未做好准备。 因此,通过“法育”教育,强化大学生的法治素养, 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