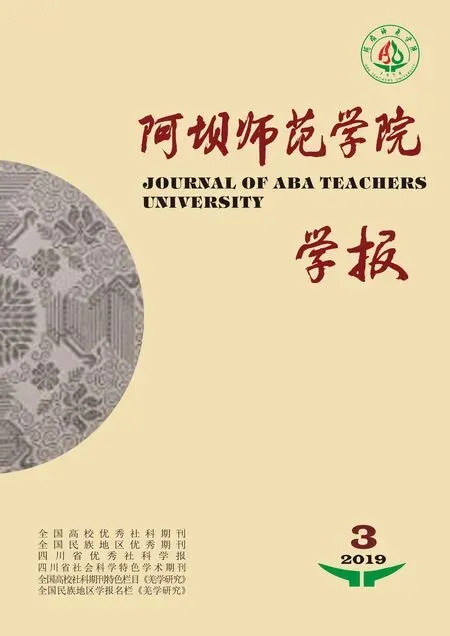浪漫主义与解构主义的碰撞
——杰弗里·哈特曼对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我意识理论研究
邓韵娜
作为美国解构主义批评阵营的代表人物之一,杰弗里·哈特曼的解构主义批评研究始于对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这一初始研究对象的选择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而他在第二阶段的解构主义批评研究乃至后期的犹太释经传统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批评方法和核心范畴,都肇始于他早期对于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我意识研究。可以说,对于文学、宗教作品乃至社会历史现象中的自我意识探索,几乎贯穿了杰弗里·哈特曼的整个学术生涯。值得注意的是,从具体的诗歌批评来看,哈特曼在解读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时常常提到自我意识范畴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概念之间有着显著区别,但他却从未试图对这一新生的自我意识范畴进行理论描述。
目前国内关于哈特曼对于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的研究并不太多,李增、王云《试论哈特曼美学批评思想》指出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的诗歌不具备统一风格,并重视其诗歌中的想象问题;李华燕《当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文学——从杰弗里·哈特曼的<批评的文化>出发》认为其文学批评研究重视想象和灵感,缺乏理论性;周霄《杰弗里·哈特曼:一个超越解构的解构者》提及哈特曼在解读华兹华斯诗歌时运用了心理分析;王凤《自然与想象的超越——杰弗里·哈特曼的华兹华斯诗歌理论研究》侧重于剖析哈特曼在浪漫主义诗歌批评中对胡塞尔现象学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继承和运用。但是哈特曼为何要选择浪漫主义诗歌作为自身解构主义批评的起点?他在浪漫主义和解构主义精神之间发现了何种共鸣?哈特曼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所发现的自我意识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概念之间有何区别?为何哈特曼拒绝对在自身批评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自我意识范畴进行理论描述?这一系列问题为本文留下了进一步探究的空间。
一、华兹华斯诗歌中的独特自我意识
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大部分浪漫主义诗歌里基本上都能挖掘出一个“被打断的旅人”形象,它既可以是在山水田园中跋涉的现实旅行者,也可以是在情感、回忆与思绪中脉脉流淌的如同天涯羁旅一般的心路历程,在大多数情况之下,现实的旅程与心灵的漫游是齐头并进,交织进行的。以华兹华斯的诗歌《孤独的割麦女》为例,这首诗描述了诗人在苏格兰高地漫游时偶遇了一位一边在田地里劳作一边白日放歌的陌生女子。一般文学批评都认为这首诗的重点在于这位形单影只的割麦女本身,哈特曼却将关注点放置于和割麦女一样形单影只的诗人身上。哈特曼认为,当诗人让自己驻足聆听时,已经将诗思指向了自身心灵。如果设身处地的进入一八零五年十一月五日,当诗人在旷荡开阔的苏格兰高地中漫无目的信步而行,游目四顾的那一刻,突然听到原本平静清幽的山谷里,在林风虫吟的自然天籁中骤然响起清越的人声,必然会在陡然的震惊之中停下脚步,成为被原野中的歌声打断行程的旅行者。在被阻止后仍然处于震惊状态的游移不定中,诗人问自己:是停下来偷偷听取一名女子劳作中的歌谣,还是默默离去,继续散漫无心的山林游荡?天地无言,万籁有声,可是发自肉声的人之高歌,在寂寞的山水田园之间别具深情。于是诗人在自然景致的环绕之中却为人类的歌声驻足流连,忘却山野美景,长久侧耳倾听。在倾听的过程中,眼前的景色仿佛被歌声驱散,诗人的心灵被牵引到了另外的时空:阿拉伯的沙漠、天边的海岛……最后更是超越了具体的时地与意象,开始抚今追昔,将思绪向着过去的悲欢离合与现实中的喜怒哀乐无尽绵延。歌声停止了,却在诗人心中余音绕梁,遗响回荡。当诗人继续自己的旅程,缓缓登上山坡,却仿佛看不到秋日山川的怡人景色,也没有描摹登高望远的视野开阔,因为此时此刻,他的心中只是回响着一个割麦女子曾经独自唱过的一首歌。
对于以描绘大自然湖光山色闻名的华兹华斯来说,《孤独的割麦女》是特别的,因为华兹华斯一向认为是自然给他带来源源不绝的创造灵感,可是在这首诗中,人类的歌喉胜过了自然的天籁与佳景,吸引了诗人心灵的全部注意。哈特曼强调,使得诗人心灵驻足的原因,并非割麦女单方面的形象与歌唱,而在于诗人心灵对于歌声的关注与回应。“他(华兹华斯)的主题是他自身的回应而非激发他回应的形象本身,尤其是在最后一诗节之中,因此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心灵与形象之间连续但不确定的关系,两者双方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1]3哈特曼指出,诗人并没有在诗中解释为何他的心灵会被割麦女的歌声所吸引。不管是诗人过去与歌声有关的经历、回忆或者诗人本身对于歌唱的喜好等主观原因,还是诸如割麦女歌声的悦耳动听或者饱含深情之类的客观原因,都不是这首诗所关注的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诗人心灵与山谷歌声之间的彼此碰撞,由此打断了诗人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漫游,流溢出充沛的诗情。
华兹华斯将心灵与对象彼此照面并相互敞开时对心灵旅程所产生的打断作用称为“惊奇”(surprise)。当诗人要求自己聆听时,包含诗人心灵与空谷之音双方互动的惊奇就在流水般散漫的思绪中脱颖而出,吸引了诗人所有的注意。“这一对内的沉浸或转向——自我反省的意识——是非常明显的。诗人自身被停留,开始反省和倾听,就像一个旅行者为无意间瞥见的景象而驻足。一个形象将他‘独立’了出来。”[1] 7惊奇本身包含着心灵与对象双方的结合碰撞,因此具有双方面的指向:外界对象和内在心灵。在外界的刺激之下,诗人的心灵触兴致情,如同从沉睡中觉醒,并且在外界对象的引领之下因变取会,沿着外界色声香味所启发的方向,接续瞬间惊奇所激发的力量在诗情流溢中尽情翱翔。在第二诗节中,诗人视通万里,由少女清甜的歌喉联想到了夜莺的婉转鸣唱,仿佛置身于遥远的阿拉伯沙漠,不管是少女的歌声还是夜莺的鸣啭,都化为了疲惫干涸之中的一捧润泽心肺的清凉泉水。接着又从夜莺转而联想到杜鹃的啼叫,在更加辽阔的海角天边,从一望无际的海面唤起明媚的春天。第三节诗中诗人从夜莺婉歌与杜鹃春啼回到了山地少女所唱的陌生歌谣,但又思接千载,对歌谣所倾诉的情思进行了无限的猜想,思绪从远古的兵荒马乱流向了现实的平常悲欢,以及未来的杳不可测。这两节诗歌的内容都既与割麦女的歌声不离不即、藕断丝连,又与心灵的徜徉一同纵横四海,在无尽的时空里往复回旋。可以说,整首诗都在心灵与作为对象的歌声之间来回跌宕,这种在心灵与外物两相契合交接之下所唤起的心灵对于自身的反省与解放,就是哈特曼文学批评中的自我意识。
哈特曼认为,在惊奇的阻断作用之下,自我意识被唤醒,开始在感知外物的同时反观自身,因此是惊奇使得心灵更新,从而产生了自我意识。“诗人……对于他那完全‘精神化’的状态如此忠实,以至于在他那里最不重要的心情也变得重要起来,因为这种心情的重要意义在于超越心情本身的某种的东西,在于与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的现实或隐藏的关系之中。”[1]6正因为如此,与一般人探求自己为何被歌声所吸引不同,华兹华斯在乎的只是被歌声所触动那一刻的细微心情,正是在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惊诧之中,自我意识浮出水面,心灵被更新了。在自我意识的产生之中,惊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惊奇一方面是对外界颜色与声音的直接震撼,一方面又指向了关于自我的哲学沉思。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将惊奇作为哲学的开始:“一个爱智慧的人也就是爱奥秘的人,奥秘由惊奇构成。”[2]5在哈特曼那里,惊奇使人开始关于自我的思考。那么在心灵被更新为自我意识之前又是何种面目呢?哈特曼认为,在被惊奇所唤醒之前,心灵完全融入了自然,不具备连续的、独立的自我意识,也无法对自我进行回顾与反思。如果进一步联系黑格尔对自我意识感性确定性阶段的论述,就能获得更为深入的认识。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意识从个别感性出发,经历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自我意识四个阶段,最终成为纯粹自足的理性概念。黑格尔将感性认识与感性对象之间的关系称为“意谓”。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向性的必然与确定,意谓是偶然性的,随机的,并且在产生之后立刻化为乌有。一切感性对象,比如具体的树木、房屋等,都是单个和零散的,不具备区别于其他树木或房屋的本质特征,无法形成确定的概念。相对的,在意识第一阶段的感性确定性中,作为个别自我的意识还不能反思和建立自身,只能通过依赖感性对象体察到自身的感官能力。如果外部世界都是碎裂分散的,那么感受外在世界的自我也是同样飘忽凌乱,各自倒映在感官印象的碎裂镜片之中,如同外界色相一般转瞬即逝,雁过而潭不留影。既然自我意识连自身的独立与统一都无法建立,那么对自身的反思与认识更是无从谈起。
从这种观点来看,《孤独的割麦女》一诗的开头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诗歌展现出的第一个场景,就是田野中独自收割的山地少女。而在山地少女之前所看到的其他任何苏格兰高地景致,诗人却只字未提。因为在听到山地少女悦耳的歌声之前,诗人的心灵还处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感性确定性阶段,飘忽不定,耳目所及,通通是无法把捉的梦幻泡影,无法在心灵中留下痕迹。当诗人的心灵蓦然被空谷清音激起强烈回应,在这歌声与心灵回应的强烈冲击之下醍醐灌顶,才在惊奇的一瞬间建立起了健全的自我主体。在瞬间的主体建立之后,诗人才能够独立而完整的把握眼前的整幅图景,并在主体力量的推动之下迸发出蜿蜒流转的诗情。从这个意义上讲,被“打断的旅人”在被打断之前,是毫无目的、无所用心的浪荡漫游,如同流水倾泻于平地,覆水难收,四面奔溢,无法建立一个统一体,可是在外物与心灵彼此触动所产生的惊奇的光芒普照之下,诗人的心灵瞬间得到更新,成为了独立于外界的连续主体。
二、哈特曼对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突破与创新
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诗人自我意识所建立起来的瞬间主体与理性主义哲学所追求的抽象主体截然不同。理性主义主体是抽象的,并且恒久持存,一旦建立就黄袍加身,构建出固若金汤的森严城池,宣告自身对于自然的永久霸占。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我主体,却只存在于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在建立自身以后随时将自身打散、冲毁,甚至力图打回原形。例如,在《孤独的割麦女》中,山地少女的歌声激起了诗人主体的建立,因此诗人的主体与原野歌声互为依托,可是接下来,已经觉醒的诗人自我意识却极力想要逃离山地少女的歌声,也就是要冲散被歌声唤醒的主体。诗人的思绪不断跳脱奔逸,从眼前耳畔的歌唱向着黄沙大漠、天涯海角来回激荡,仿佛想要冲破歌声与主体这一彼此维系的束缚,逃出固定主体的掌控。当自我意识在空间中极力突围之后,似乎不得不再度回到绑缚着主体的歌声,可是自我意识又立刻展开时间中二度突围,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流宕起伏来摧击屹立于当下这一刻的主体。最终,歌声停止了,余韵却留在诗人心里,开始了回归主体与逃离主体的最后一轮角力:诗人登上属于自然的山坡,象征自我意识朝着彻底冲散与自然隔离对立的主体并回到之前那样无意识融入自然的方向流动,歌声停止后留在心中的飞鸿远音绵绵若存,则是主体在大势已去的余音遗响中点起星星之火,极力对抗自然力量的淹没。整首诗就在主体隔绝于自然与自然浸没主体的持续对抗中余韵无穷的结束了。
总的来说,哈特曼文学批评中的自我意识具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无意识漫游阶段,这时自我意识未脱离自然的母体,尚处于毫不自知的混沌状态,跟随自然的节奏漫无目的的漂流;第二个阶段是主体建立的阶段,在惊奇的打断与呼唤之下,之前的混沌骤然开天辟地,无意识洪流中鼎立出了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主体与自然形成了相互映照的关系:主体因为自然中的惊奇回顾并认识了自身,同时也通过有意识的自我主体对自然展开了明晰的观照;第三个阶段是打破主体的阶段,自我意识在建立起独立于自然的连续主体之后,又极力冲散主体与自然之间所确立起来的界限,力图反抗主体对自然的僭越与掌控。在这个阶段中,自我意识在保持主体与击碎主体之间来回往复,无尽徘徊,营造出意味深长的诗情跌宕。
因此,哈特曼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所发掘和描述的自我意识虽然滥觞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却又开创新变,别立一宗,具有自身独特的生命轨迹与理论风景。哈特曼自我意识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具有四个发展阶段,从感性发展到知觉、知性和理性,最终实现理性对于感性的彻底否定与驱逐。哈特曼的自我意识却始终在感性的范围内流动,即使在建立起具有理性反思能力的主体时,自我意识仍然是通过感性的自然景象来确立主体的独立性的。同时,哈特曼自我意识的确立不需要循序渐进的按照四个固定步骤,一面扬弃感性、知觉、知性,一面向着理性亦步亦趋,只需要刹那惊奇的当头棒喝,就可以目击道存,令主体就地现身,不必经历环环相扣的严谨过程;第二,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在先后经历四个既定阶段之后进入了绝对精神,从此千载不移,永不更改。哈特曼的自我意识却随时处于自身的分裂与对抗之中,主体刚刚露出头角,就要经受自我意识中主体对立面力量的风吹雨打,随时可能冰消雪融,在这一点上,哈特曼的自我意识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保持主体的无限延续,一个却力图在主体诞生那一刹那将主体瓦解;第三,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将自然作为被自我意识吞并的对象,按照黑格尔的四个步骤,自然在自我意识的认识之中逐步抛弃外在的感性现象,当自然在自我意识的认知当中通过否定性运动的扬弃只剩下理性本质时,就已经成为理性自我意识自身的一部分,被自我意识所吞噬。可是在哈特曼那里,自我意识与自然却并非一方吞并、征服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互相确证与维持的肝胆相照。
三、浪漫主义与解构主义精神共振
哈特曼拒绝使用理论话语对自身所开创的自我意识范畴进行体系化描述,转而选择在对于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的具体批评解读中展开诗歌中自我意识的产生、流动和泯灭的具体过程,这一独特的批评理论创建与实践方式背后究竟有何理论洞见与哲思底蕴呢?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指出,兴起于十八世纪后期的浪漫主义精神内核,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启蒙主义运动所崇尚的普适性原则与理念之间,形成了对抗关系。“两种因素——其一是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试图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因素构成了这场价值非凡、意义重大的运动中最深刻也是最疯狂的一部分。”[3]118伯林所指出的浪漫主义运动两大核心因素与启蒙精神的基石恰好针锋相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现代性启蒙的内在目的是通过理性概念完成对世界的掌控。概念的建构是以主体对于客体的支配和占有为基础的。面对具体可感的现实事物,主体通过抽象化手段总结出前者的同一性本质,并将其凝固为纯粹理性的概念,原本鲜活的对象以固定概念的形式成了被主体所认知和把握的客体。在启蒙理性的统摄之下,多姿多彩的大千世界就这样以抽象概念的形式被分门别类的纳入了科学性的完整概念体系,失去了个别性与差异性。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之上,理性主体将整个客观世界纳入自身的理性范畴,并且建立起一整套理性概念体系。浪漫主义精神反对“事物的本性”即是反对归纳出对象本质的概念,反对“事物具有稳固结构”则是反对通过概念构建起稳定的理性知识体系。
无独有偶,哈特曼也曾反讽性的借用启蒙运动先驱笛卡尔的经典术语“我思”。“如果文学批评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的那样,是自传的唯一文明形式,那么我将延续这一脉络。而且我愿意为读者承诺更多。在与科学截然不同的自传式自我反省中,叙述主体渴望了解他自己,也就是传达一种依赖或安住于整个人生之中的自我意识;这预设了处于直接性的‘我是’与漫游的——持续建构中的——‘我思’之间的持续的自我认同。”[4]Ⅺ与启蒙运动所追崇的数学公式一般的普适性原则以及科学性思维相反,哈特曼认为文学批评是“自传”即自我的表达,而自我的表达是个别的而非普适性的,经验性的而非科学性的。在用个体经验表达自我这一点上,哈特曼的自我意识理论与浪漫主义精神产生了共振。“浪漫主义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3]23华兹华斯在听到苏格兰高地少女的歌声之后的驻足凝神倾听,就是作品中待批评者发掘的直接性“我是”;而哈特曼通过对华兹华斯的诗歌阅读所发掘的“被打断的旅人”形象,以及自我意识在诗歌中所经历的无意识、主体与打散主体的三阶段,则是漫游中的“我思”。但是,哈特曼文学批评中的“我思”完全不同于笛卡尔的“我思”,因此这里“我思”的挪用是一种反讽,而反讽这一概念正是浪漫主义美学奠基人施莱格尔所开创的,反讽代表着对于一切固定概念、公式和教条的冲击与反抗。
在笛卡尔那里,我思与感官、肉体彻底脱离,进入了纯粹又无垠的理性,普遍、确定、千载如一。笛卡尔理想中的我思是数学公式,能够以不变的原则代入所有问题,理性应当像几何的点与线一样,没有大小与面积,构造出不具备声音、色彩与气息的广延。在笛卡尔看来,真正的认识就是让我思在对象中通过对虚妄幻念的排除把握住永恒真实的理性知识。笛卡尔一块蜜蜡为例,刚从蜂房里取出时,可以用感官体验其甜味、香气、颜色、形状、硬度等,这一切感官体验都无法恒久持存,把蜜蜡拿到火边,它会渐至融化,失去原有的形状与色香味。排除了变化无常的感官体验之后,这块蜡在融化之前和融化之后唯一不变的就是其本身的广延:“把凡是不属于蜡的东西去掉,看一看还剩下什么。当然剩下的只有广延的、有伸缩性的、可变动的东西。”[5]31笛卡尔由此指出广延是我思中对于物质性对象能够清楚领会的首要观念,因此是物质的第一性质。不管什么样的物体、不管其在外观和性质上发生什么样的变动,它都必然占据一定空间因而具有形状,同时会在时间中进行运动。广延包括空间中的形状和时间中的运动,形状大小可以变化,形状本身却是始终存在的;运动方式各有不同,运动本身也确定不移。相对于感官特征的短暂,广延是理性的,因而能够永存。如果说笛卡尔的我思是理性主体的基石,那么广延就是理性概念的基质。
可是哈特曼的我思却始终追随感性印象与体验,在每一首诗歌之中都有不同的路径与风景,在《孤独的割麦女》中,唤起诗人主体的是一名女子的歌声,激荡主体的是关于歌声的自由联想;在华兹华斯另一首诗歌《有一个男孩》中,唤起男孩主体的是大自然的沉默,冲破主体的是男孩的死亡。诗歌中的作者自我意识独立于诗歌形象还是寓托于诗歌形象,唤起自我意识主体的是何种感官印象,打散主体的又是怎样的记忆与畅想,通通不确定,需要随着诗歌本身的波浪蜿蜒流转,文学批评中的我思始终倒映在诗歌文本的水面,与水中映照出的天光云影一同荡漾回旋,因此文学批评中的我思与文学作品中的感性印象体验彼此浸染,不可脱离。与笛卡尔排除一切感官印象的变化相反,正是感官体验的流动与变迁带了自我意识在主体与非主体之间的来回跌宕。文学批评中的我思不能像理性主义中的结构那样普遍套用于一切文学作品之中,而是要深入文学作品的血液肌理,与文学一同呼吸开阖,在每一次阅读之中寻找出不同的路径与风光,因此哈特曼指出他的我思是漫游的,而非固定的普遍体系。在我思的漫游之中,读者自我意识与作者自我意识观看同样的风景,体验同样的心情,也一同明澈本心,照见自我。如果说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之中诗人心灵与大自然互为明镜,那么在哈特曼的文学批评之中,读者自我意识与作者自我意识也互为明镜,读者自我意识发掘作者自我意识的流变轨迹,作者自我意识则带领读者自我意识进行漫游与反省。
综上所述,哈特曼选择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作为文学批评研究的起点,其背后的深层学理发端在于,哈特曼敏锐的发现浪漫主义运动对于启蒙主义运动所推崇理性体系与科学思维的激烈反抗与解构主义精神有着内在的呼应与共鸣,如果说启蒙理性开启了现代性历程,那么紧随其后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早已为后现代性孕育了萌芽。从这个观点来看,后现代性与现代性本身就相依相随,一体两面,后现代并不外在于现代性,而是处于现代性的内部。
四、结语
通过哈特曼自我意识理论与浪漫主义之间的精神共振可以看出,哈特曼拒绝对其自我意识理论进行体系化的理论性描述,正是对于浪漫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实践。他曾直言不讳的表示:“我必须从一开始就承认我不太能算是一个理论家。我的许多同事都会牢牢把握自身的观点,并使其在一套个人化的或者综合的观念体系中得到建立和完善……毫无疑问年岁也赋予了我一种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性的个人想法。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位诗人,我自身总是处于被辩论着的观念和缭绕着的印象所击碎的危险之中,我不得不在两股力量之中保持平衡,在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之中,我不确定会出现什么。”[4]Ⅺ事实上,哈特曼的自我意识始终处于浪漫主义诗人和解构主义理论家的对峙之间,一方面,对于自我的反思、对于自我意识的强烈兴趣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对自我意识的关注就是他“具有在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性的个人想法”,另一方面,他又极力反对以理性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思辨遏制文学情思的自由发挥与自然流淌,在理性主义那里,凝固的主体占据了绝对优势的霸权位置,文学中的情感、体验与词汇成为了不具必然性意义的偶然因素,被坚定不移的结构体系所排除和驱逐。
因此,在经过系统的理论训练之后,哈特曼转向了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并且采取了别具一格的研究方式:将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理性思辨融入对华兹华斯浪漫主义诗歌的文学性解读之中,用个体心灵中起伏变幻的联想与情感冲散理论的划一与普遍,用诗人对于自然风光的印象和体验稀释理论的固有结构与既定步骤,在他看来,文学中个人及其零散体验是永远无法被理论所建立的整体结构所代替的。如果说启蒙运动所推崇的理性主义追求的是掌控和把握整个世界的“有知”,那么文学的创作与体验追求的就是在情绪、回忆与想象的洪流中不知会浮现出何种思绪、也不知会选择何种表述语词的“未知”“我不确定会出现什么”。正因为如此,在确定了自我意识中第二阶段的主体建立以后,哈特曼同样重视接踵而来的第三阶段:主体的消解与分散。第三阶段对主体的拆解也为哈特曼日后奋勇投身于解构主义大军埋下了伏笔。哈特曼对理论的天然警惕与反击,使得他的文字总是力图避免建立完整划一和脉络清晰的理论线索,而是将相关理论术语点缀和隐藏在充满诗意的文学语言之中,让理论思考被诗情翻涌所卷挟、冲散和稀释,营造出独特的语言景观。这一特点造成了阅读上的困难,也常常让人认为哈特曼没有完整的理论内核。但是,如果对于哈特曼具体的文学批评进入深入的阐释与解读,就能发掘出其中若存若续的理论脉络,并追索出他企图继承、扬弃与改造的丰富理论史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