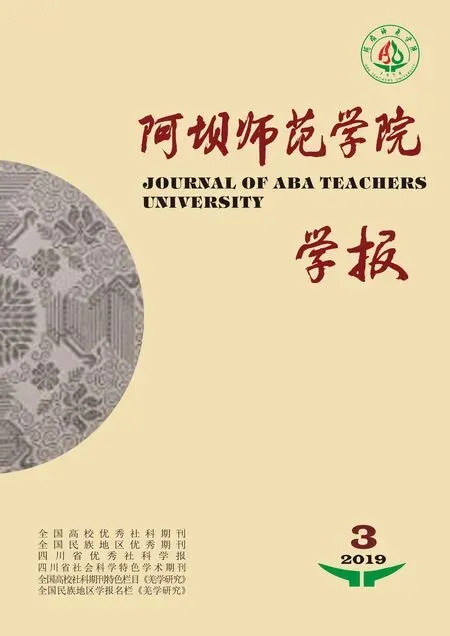党益民西藏军旅小说中的军人形象探析
马小燕
自从20世纪80年代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诞生以来,军旅题材一直备受西藏作家青睐,在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与西藏作家的来源密不可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从四川、西康、青海、新疆和云南等地进驻西藏,行使主权。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战士和四川籍的藏族战士中的“秀才兵”成长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第一批长篇小说家,代表人物有降边嘉措、益西单增、单超等人,这也使军旅题材成为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西藏的军旅小说创作群体中,绝大多数人都有军队背景,要么职业是军人,要么曾经有过当兵的经历,这一共同点决定了小说作品的中心集中在军人身上,但由于作家们所属兵种的不同,他们笔下的军人形象又各具特色,共同组成了军人的多元化群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党益民,他也是西藏最为多产的当代军旅作家之一。
一、作为军人的党益民
党益民,1962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9岁入伍,成为武警部队某部的一名打字员,1983年首次进入青藏线锻炼,先后参加了慕生忠将军开辟的青藏公路毛路改造、黑昌线、川藏线、中尼线、新藏线的筑路工作,在唐古拉山和雪拉山上战斗过,共进藏40多次,足迹遍布川藏线、青藏线和新藏线,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先后经历了冻死、累死、饿死、淹死、砸死、病死、摔死等七种死法,每次都大难不死,活了下来,逐渐成长为一名军官,并且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诉讼法学硕士学位,直到2014年才调离西藏,任武警辽宁总队副政委,是当初进藏的800多名陕西兵中仅有的两名留在部队工作的乡党之一。
党益民虽然是一名职业军人,但他却酷爱文学创作和艺术,小时候家境贫寒,买不起年画,他就自己画画来装饰房屋,也练就了一手绘画绝技。他自谦为业余作家,将西藏视为灵魂的栖息地,由于长期在藏工作、两地分居的原因,他与第一个妻子离婚,收养了一个父母在雪崩中死去的藏族孤儿,起名为雪拉,将其抚养长大,就业成家,为了这个孩子,他的第二个妻子甚至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战士也是人,战士也有家。”人到中年后,党益民在工作时也要考虑家人的感受,2004年6月1日,他独自一人由西向东穿越西藏时,就购买了5份人身意外保险,临行前交给妻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自己出意外的话,能够使妻儿后半生的生活得到保障,表现出自己要力争当一个好兵、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苦心。①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党益民40多次进藏,到基层部队调研采风,创作出《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雪祭》等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用胸膛行走西藏》,集中展示了西藏军人的光辉形象,特别关注到自己最为熟悉的武警交通部队官兵这一群体,弘扬了时代主旋律。
二、入藏公路的守护神形象
川藏、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车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和平年代,这两条公路在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铸就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对比这两条道路,川藏线更险,养护难度要大于青藏线。为了确保川藏线的畅通,1996年10月,江泽民签署命令,组建了一支武警交通川藏公路机械化养护支队,后改为武警交通第四支队,从此以后,这支部队就成为川藏线的守护神。
西班牙小说家M·德利维斯曾经指出: “一部小说的要素是人物。塑造活生生的人物是小说家的主要任务。”[1]872在《雪祭》中,党益民塑造了团长田牛、七连连长赵天成、代理指导员陆海涛、副指导员杜林、代理技术员方文这样的干部,机械排代理排长刘铁、炊事班班长兰洲、城市兵牛大伟等一批典型人物,组成了一个基层部队完整的官兵序列。这支部队为修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尽管团长一再强调安全第一,但为了按期完成施工任务,连队却接二连三出事,炊事班班长兰洲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给战士们加强营养,先是打了黄羊,又去捕捉雪鸡,结果被冻死在雪地里,眼睛都被秃鹫给啄掉了。潘明独自上山放炮,被炸伤,变成了瞎子。方文被落下的山石砸断了三根肋骨,被送到了西安四军大附属医院,刘铁得了肺水肿牺牲。在战友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后,部队终于完成了筑路任务。
普通士兵最辛苦,他们是“不拿枪杆拿锹杆”的战士,一年四季都在山里修路,夏天抗洪,冬天抗雪,任务非常艰巨。党益民详细描写了最惊险的打“飞线”工作:飞线是指山势坡度在80度以上,接近于垂直,测量员无法实地测量、在施工图纸上只能用虚线标注的地段,需要悬空打200多个炮眼儿,开挖200个导洞,然后进行定向爆破,在悬崖上炸开一条路来,即使是班长级别的老兵第一次悬空作业,也心虚冒汗、腿肚子打颤。打导洞时,因为导洞直径不足一米,最深可达十几米,士兵在里面工作,会缺氧,等在外面倒土渣的士兵,如果听不到里面的风钻声,喊话也没有回声,就知道里面的战士已经昏迷了,就赶紧爬进去,把里面的战士拉出来,给他吸氧,才能使他苏醒过来[2]110。
在修路时,遇到路面结冰,战士们只能把军大衣铺在地上,才能保证车辆安全通过危险路段。遇到大雪灾,战士们用手电筒给推土机照明,手和电筒冻在了一起,揣在怀里暖化了,继续照明。[3]31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施工时往往需要返工,花了三个多月修好的路被洪水冲毁,中队长和战士们都站在雨里哭。战士们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遇到暴风雪天气,帐篷经常会被大雪压垮,半夜都会被冻醒。战士们的伙食以各种罐头和土豆为主,新鲜蔬菜极度缺乏,由于海拔高,做的饭都是夹生饭,很难消化。有时甚至连这样的伙食条件也难以保障,一旦汽车兵上不来,给养供应不上,部队为了节约粮食,就要将干食改为稀食,战士们就要饿着肚子施工,很多战士的身体透支严重。
《一路格桑花》中,由于工作任务重,战士们根本没有时间回家探亲,唯一的希望的就是能收到家信,由于交通不便,往往是两三个月的信一起送到,好消息和坏消息一起看,战士们就哭一阵笑一阵,变得神经兮兮。最可怜的是年轻的战士们一年都见不到一个女性,最渴望有女兵或者大学生前去慰问他们,部队负责安排慰问工作的处长也向大学提出了“演出队不要男生,只要女生,而且必须漂亮。”[4]62的要求,来了放电影的女兵,战士们就向连长提出,要排队和女兵握手。可以说,这种在普通人眼中近似于不可理喻的要求却反映出战士们生活的寂苦,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和汗水维护着川藏线的畅通,是当之无愧的公路守护者。
在我国的军旅小说中,“高扬英雄主义的旗帜,聚焦当代英雄的献身精神,彰显中国军人高尚的家国情怀,是许多作品坚守的永恒主题。”[5]党益民延续了以往西藏军旅题材小说中的英雄主义情结,在小说中揭示了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上筑路官兵工作和生活的真实状况,突出了一个“苦”字,把武警交通部队的吃苦耐劳和献身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赋予了英雄主义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雪祭》中,无论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城市兵牛大伟,还是来自甘肃的农村兵兰洲,在军队里都是一名普通士兵,没有任何特殊性,而他们的连长赵天成的经济状况也很一般,并不能靠自己的军官身份获得经济效益。这些军人与世隔绝,就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样,宛如一颗颗螺丝钉钉在青藏线和川藏线上,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艰巨的筑路任务和单调的伙食,这些官兵却义无反顾地抛家舍业,坚守在青藏高原上,只有纯粹的革命理想和绝对服从命令的天职才能让他们生存下去,军队铁的纪律、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使他们拥有了强大的精神依托,担当起了公路守护神的重任。
三、藏族民众的守护者形象
在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平叛过程中,中国军人和藏族民众一起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这种情感在武警交通部队官兵身上得到延续。除了修路和维护道路畅通外,部队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遇险的民众。在《用胸膛行走西藏》中,党益民记录下了这些场景:在营救被大雪围困的10辆车25名群众时,支队给全线所有中队下达了“不能漏掉一个人,不能冻死一个人,不能饿死一个人”的命令。被营救的女人一下子扑进战士的怀里,哭着喊:“亲人哪,你们可来了。”15名奄奄一息的群众看见武警官兵突然到来,禁不住哭了起来。5名藏族群众已经瘫软在雪地里,司机丹增冻得四肢僵硬,神志不清,被战士们背了下来,司机们感动地痛哭流涕,说:“我们什么吃的都没有,要不是你们来我们就死定了。”[3] 35藏族老大妈一个劲地感谢共产党,感谢金珠玛米。为了节约粮食,每到吃饭的时间,战士们就以有任务为由走出营地,等受困的藏族群众吃完饭以后,他们才返回营地。
战士们的辛勤付出也得到了藏族民众的回报,在《雪祭》中,当赵天成被马摔下雪窝后,被藏族妇女救活,醒来时发现一个年轻的藏族女人正把他的双脚捂在温暖的皮袍里,当他慌忙抽脚时,女人说你们金珠玛米也救过我的命。《用胸膛行走西藏》中的黄新忠、张志宏、李炳岑三位战士牺牲后,藏族群众从四面八方拥来守灵,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劝也劝不走,开追悼会时,八宿县万人空巷。为了寻找落入江中的副营职助理员董杰,部队把下游几十里的河道找了个遍,八宿县的上百群众也自发加入了寻找董杰的队伍,把县城里所有商店里的电池都买光了。当战士们在营救被泥石流围困的车辆时,藏族民众用歌声来给战士们加油,“太阳出来的地方,晴空垂下白幛;不,那不是白幛,那是我可爱的家乡;太阳出来的地方,云里挂起的帐篷,不,那不是帐篷,那是金珠玛米驻扎的营房。”[3]261中国人民解放军拥有为人民服务的优良革命传统,党益民在小说中讲述了筑路官兵营救深陷自然灾害中的藏族民众的惊险故事,延续了解放军和藏族民众在革命战斗过程形成的军民鱼水情,而藏族民众的回报又使这种感情进一步得到升华。
四、重情重义的兄弟形象
在战争年代,军人是当之无愧的强者;而在和平年代,军人却成为社会上的弱者。“伴随着和平状态的不断持续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化,军队也实实在在的发生着巨大变化……曾经笼罩在军人头上的崇高光环渐渐褪去,价值解圣之后的军人职业日益退至社会的边缘。”[3]58在西藏服役的官兵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长期在同质化极强的军队里工作,无法与外界保持日常联系,思维也无法和社会人士同步,处于与社会“绝缘化”的后滞状态,回到内地后愈发不能适应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现实又反作用于军人,更加强化了军队内部的向心力,使战友情得到进一步升华。
党益民小说中的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在自然条件恶劣的青藏高原上保障畅通、营救受困群众,是天神一样的存在。但这些官兵离开军营,走入社会后却像孩童一样四处碰壁,又无处求助,只能寻找战友,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西藏武警战士之间无私帮助的战友情很好地体现了出来。《一路格桑花》中的邓刚给下岗的老婆郭红找工作,只认识一个曾经到西藏挂职的副处级干部刘知,在他的帮助下,求一个街道办主任帮忙,花了很多钱,又是请吃饭,又是请洗脚,结果才找到了一个月薪600元钱的临时工工作。《雪祭》中的刘铁因为收到了家里的电报,说父亲病重,老婆由于孩子夭折而精神错乱,他在请假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悄悄离开连队跑回陕西老家,但是没有钱给老婆看病,无奈之下去找连长赵天成的老婆毕秋帮忙,从她那里知道战友来建江创业成功的消息后,找到了雪域大酒店,来建江不但给他很大的经济援助,还找人专门照顾他的老婆,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让他安心归队。在刘铁牺牲后,来建江又出钱埋葬了战友,给刘铁的老婆提供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兰洲牺牲后,经济上并不宽裕的连长赵天成却坚持自己一个人出钱,给兰洲的父母买了彩色电视机和天线,完成了他的心愿。修建怒江大桥时,一个排的战士都牺牲了,只剩下排长,他悲痛欲绝,纵身跳下了滚滚的怒江,去追寻战友,后来的筑路兵在石崖上刻了一幅“排长跳江图”[3]69,将同生共死的战友情升华到全新的高度。
在以往军旅题材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中,军人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硬汉形象,代表着无所不能和勇往直前,例如单超《布达拉宫的枪声》中的主人公侦查科长赵惠渠,为了工作,让从北京赶到拉萨的未婚妻独守空房,义正词严地拒绝拉萨之花采力玉准的美色、金钱和高官的引诱,不顾自己在蝎子洞里受的伤,在敌人投掷手榴弹的紧要关头,用身体保护了副参谋长的人身安全。张庆桑的《博巴金珠玛》中的指导员洛桑面对敌人的拉拢和女特务的引诱,不为所动,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与这些小说作品不同,党益民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军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无奈和无助,给读者呈现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军人形象。在青藏高原上,武警交通部队的官兵能够守护一方平安,但回到内地,他们却没有任何社会资源,遇到困难只能向曾经的战友寻求帮助。这种现实情况又反过来促使军人更加依恋军队,倍加珍惜战友之情,也进一步激发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五、默默付出的军嫂形象
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藏当代汉语长篇小说不同的是,党益民的小说关照到军嫂这一群体,这是西藏军旅题材小说的一大突破,将战士们作为“社会的人”的一面很好地展现了出来。
青藏线和川藏线上的战士将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贡献给了国家的筑路事业,却没有精力和能力照顾自己的家人,体现出“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雪祭》中的连长赵天成在入伍时到西安去看望自己的叔叔,结果被婶婶拒之门外,他发誓要找一个城里女人,在西安安家,愿望实现了,但是由于他长期不能休假回家,妻子毕秋无依无靠后出轨,和自己的初恋情人李刚住在了一起,而赵天成还毫不知情。刘铁的妻子秀芸一个人在家既要种地,还要照顾双目失明的公公,身心俱疲,在收割庄稼时遇到大雨,无奈地大喊丈夫的名字,但也无济于事。于歆无法忍耐两地分居的生活,向方文提出分手,但是当她看到方文负伤后的模样后,又不忍心看着他伤心,两人又和好了。《一路格桑花》中的汽车兵王力牺牲后,妻子余秀兰一个人拉扯着女儿小雪,十年后才带着女儿来到西藏祭拜丈夫,她在进藏途中,一到军营里就搜罗战士们的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描写,党益民在小说作品中呈现出了真实的西藏军嫂的群像,她们与丈夫远隔千山万水,和普通女性一样渴望得到丈夫的关爱却无法实现,只能一个人默默承担起赡养父母、抚养孩子的重任,让人们对军嫂的不易和默默付出有了全新的认识。
党益民的小说中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使用了“藏光”这一具有西藏特色的名词。因为西藏的紫外线特别强烈,在高原上待得时间长了,脸上就会脱几层皮,结出紫黑发亮的疤痕,肤色也会变成紫黑色,这种特有的肤色被称为“藏光”。藏光的颜色与人在高原上待的时间成正比,时间越长,颜色越深,党益民的小说中多次强调藏光的重要性,“脸上有藏光,就算是高原兵。”藏光是高原军人资历的象征,深浅不一的颜色代表着服役时间的长短,但也给军人的生活带来很多烦恼,《雪祭》中的赵天成因为脸上有藏光,没法拍结婚照,技术员黄雪丽在高原上呆的时间太长了,脸上也有了藏光,皮肤变得非常粗糙,虽然注重保养,但也无济于事。在党益民的小说中,是否拥有藏光就成为检验合格军人的标准,是赋予资历和身份的象征物。
正如李佳俊所说:“部队作者无疑应当很好利用和发挥自己的生活优势,在军事题材领域里创作出既保持着我军优良传统又具有时代风貌的文学新篇。”[7] 291-292党益民的小说作品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数十年来,他用自己手中的笔写下了武警交通部队官兵的忠诚、勇敢和爱恨情仇,将这些战士的生活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他的长篇小说是建立在长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也融入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具有很强的纪实性,用悲壮的故事情节讲述着西藏军人的故事,代表了21世纪西藏军旅小说的最高水平。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题材的限制、写作对象的单一性,致使他的小说作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故事情节的重复问题。《用胸膛行走西藏》是党益民将自己调查采风积累起来的资料汇总而成的,属于报告文学的范畴,但这部报告文学却为他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经典的素材。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他忠实地记载了有两座坟墓的士兵王立波,一个苦等丈夫十年的女人王小宁,为爸爸叠千纸鹤的女儿王童,排长跳江图、被混凝土桥墩吞没的技术员,营救被易贡洪水围困的两名突击队战士、黑鹰直升机营救士兵徐明新和毛林宝、营救被大雪围困的藏族群众,女兵上厕所,藏光,狼吃了部队的羊,掉下悬崖的李名成,军官被石头伤了下体、无法进行性生活、交通部队一号首长石兆前将军的儿子石明在业拉山工作等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经过加工后,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他创作的长篇小说《一路格桑花》《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雪祭》中,《一路格桑花》中就用了排长跳江图、被混凝土桥墩吞没的技术员、将军的儿子和儿媳都在基层部队、女兵上厕所等故事,主人公邓刚大队长因为下身受伤,不能给妻子郭红正常的性生活,郭红去部队找他离婚;老兵王力牺牲后,战友们找到两个半具尸体,修了两座坟,十年后,妻子余秀兰带着女儿来看丈夫;黑鹰直升机营救被围困的战士。《雪祭》中则使用了狼吃了部队的羊、营救被大雪围困的藏族群众、牛大伟进洞打风钻窒息等故事。《雪祭》和《一路格桑花》中都是用了主人公当兵时请假去拜访城里的叔叔,却被婶婶拒之门外的故事。虽然小说在情节设计上有重复,但是因为故事背景的差异和人物姓名的不同,如果不仔细进行比较,很难发现这些问题。而在不同的小说中,这些典型事件又使小说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在这些小说情节中,主人公被婶婶拒之门外的故事备受党益民喜爱,通过在小说中反复讲述这个故事,来解释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给农村出身的军人造成的伤害,这又转化成行动和力量,促使战士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城里人。
“反思军人的主体规定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下的失衡与矛盾,乃至主观性的意味,是文学工作者未来的‘有意味’的历史使命。”[8]与以往的西藏军旅小说相比,党益民的小说作品表现出更多的真实性和人情味,将和平年代西藏军人不为人知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完整地记录和展现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实性应该是党益民小说作品的最大特点,完美地体现了“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的要义。
注释:
① 根据党益民小说作品中的自序、后记等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