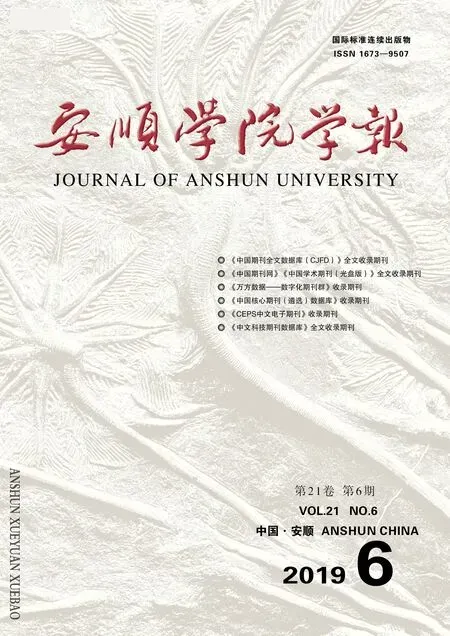原生态与本土性:安顺地域风情散文探析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贵州 安顺561000)
散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散文既包括诗歌以外的一切文学作品,也包括一般科学著作、论文、应用文章。狭义的散文即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是指与诗歌、小说、剧本等并列的一种文学样式,包括抒情散文、叙事散文、杂文、游记等等。”[1]174本文研究的是狭义散文,即文学意义上的散文。
一、地域风情与地域风情散文
关于地域文化,可谓古已有之。《诗经》中的“风”,是指某地之民歌,“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如《豳风》《卫风》《郑风》等,这些诗歌多具有显著的地域色彩。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蕴涵着鲜明地域风情特色的散文作品或摹写地理山川,或寄情自然秀色,或描写人文风物,有如群星丽天、繁花匝地。
所谓地域风情散文是指作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进行的散文创作。地域风情散文中“风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体,即描写对象。它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格、方言、行为,乃至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它们主要展示了独特的、气韵生动的人物画面与场景画面。另一方面来自写作主体,即作者自身。地域风情与人的生命存在着穿插交织的现象,体现在散文作品中的地域风情,就是作者通过自己的体验和感悟,运用各种文学手法对描写对象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因此,地域风情散文的创作过程,是作者主体意识作用于特定地域的山水地理、历史人文、民俗风物、文化结构、信仰习惯之上,通过创作手法将自身的体验、感受、领悟等恰切地展示出来的过程。
二、安顺地域风情散文
地域风情散文是作者通过散文创作表达对特定地域体悟的散文。对作家地域文化意识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往往是作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故乡的自然风物、乡俗民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一切,无疑是故土给予作家的伟大馈赠,作家本人从中得到熏陶、感染,最终形成他最基本的地域文化意识。当作家要表达这份浓郁的乡情乡思,描述他所生长的乡土时,他须先用极大的努力去认识他所要写的地方特点,即充分认识足下的土地。
安顺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在《安顺文化沉思录》指出,由于安顺地处“黔之腹,滇之喉”,又为“蜀粤之唇齿”,因此外来文化对它的影响和它对外来文化的吸纳改造,都比其他地方要更快更广。安顺因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之故,文化资源相当丰富。汉族文化与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共生,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共荣,屯堡文化与区域文化交融,多元共存造成了安顺地域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这也促进散文家们对区域文化的认知与强化,相应地拓展了散文作品的文化领域,增强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氛围,折射出作家对安顺本土文化的深度洞悉和对立身之地的思考与发现。这“不仅是对‘安顺地域风情’的重新发现,更是对安顺这块土地,这里深厚而独特的地理文化与历史文化的重新发现,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的精神传统,以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2]379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发现”看作是“地域风情”的自觉,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脚下土地的观察角度、认知手段和洞悉方式,同时也催生出“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何光渝先生语)”和“呼唤‘一个人的安顺’的‘大散文系列’(钱理群先生语)”的课题①。钱理群先生在《贵州读本·前言: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一文中认为:“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贵州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就会面对‘被描写’或者根本被忽视的问题。”[3]1安顺文化也是一种弱势文化,也在面临这样的问题,而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话来真诚与真实地描写自己。
安顺地域风情散文不仅贯注了作者生于斯长于斯,充分了解这一方土地并得之于心的特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取向;还通过揭示那些被人们忽略的种种地域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使作家获得各自独特的创作优势,极大地提高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档次和审美品位;同时活跃了散文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形成了各具形态、更具内涵的地域文化新格局。
三、安顺地域风情散文的原生态特征
刘纲纪先生在《黔中墨韵·序言》中认为安顺本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奇诡”“刚健”和“质朴”。确实如此,这三个词语精准而恰当地揭示了安顺地方文化的基本特征。安顺地域风情散文以安顺地域风情为描写对象,源于安顺独特的地理位置、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等因素,鲜明地展现了这样的原生态特征。所谓的原生态特征,即是指自然天成的,不需加工改造地描写、反映安顺地域风情、文化面貌的作品特征。
1.刚健勇猛的审美特征
安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境内山多壑深,一座座独立的山峰耸立于地表,构成一道独特的峰林景观。独特的自然风貌孕育了安顺人民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刚勇强健的人文精神。
安顺文化的刚健勇猛,突出地表现在安顺人的“尚武”精神上。在安顺的民间,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民间游戏叫打“石头龙”。春节前后,寨子里的村民就会分成两组,抛掷石块对击。当然,这种游戏由于极具伤害性现在已经被禁止,但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一扇洞察安顺人性格的窗口,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安顺民间的很多村寨都盛行“地戏”表演。地戏表演者穿着古戏装,头戴面具,手握武器,扮演各种角色。表演时舞台上身影勇猛矫健,厮杀穿梭,刀枪剑戟纷飞,极为精彩。中途还要撒黄烟,把整个舞台渲染得神秘而雄伟,这也是安顺人“尚武”精神的一种表现。安顺文化刚健勇猛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在这种群体性的文化追寻当中。
在地域散文中,这种刚健勇猛之风亦不少见。本土作家宋茨林的散文《美丽的“鬼魅世界”——安顺麻风村记事》里,描述了安顺人的野性:看看这些驮马队员:“十分剽悍,令人生畏。‘乐万’的驮队出现在新场和江龙的场坝上,总是威风八面、出尽风头。”[4]268在“乐万”担任驮运工作的队员中,21岁的王尚宝是一个布依族小伙,“方脸,浓眉,大眼”,身怀“马上打飞石”的绝技,“拳头大小的石头纷纷掷出去呼呼有声,而且准确度极高。”[4]269在这些神猛的勇士身上,体现的正是安顺文化中的“刚健”之气。
2.神奇诡秘的审美感受
安顺山水既雄壮大气,又神秘莫测,这样的奇山异水也激发了安顺人奇特的想象力,培创出安顺地域风情散文“神奇诡秘”的特质。
安顺地域风情散文的神奇诡秘首先体现在对民俗活动的描述上,譬如民间的“屯堡地戏”即充分地显示了安顺文化“奇诡”的特质。本土作家罗迎贤的《看地戏》就描写了地戏的演出情景:“那喊声似乎还有些耳熟,一声声带着苍凉,含着旷远。我感到心里有些颤抖,发酸:一群披坚执锐的军士,随着猎猎翻飞的棋幡,在阴寒的风中从遥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穿越历史,走在我的眼前。然后,一些熟悉的面孔不见了,又是一些;剩下的一身血迹,面容凄楚地被抛在一片荒远的山野中。”[5]142
作者描写的唱声带着历史留存的苍凉,给予人怪异之感,令人皮肉发麻,人们仿佛看到古代的军士穿越历史来到当下,恍若隔世,又惊奇此生,难免使人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穿越轮回,“奇诡”的感受相当突出。
丁杰的《火树银花里的图腾》叙述了普定冲龙的神奇与独特:由铁锅厂的师傅们烧炉熔化冲龙用的数以吨计的铁水,“拿铁勺舀出来,对准舞动的龙和热闹的人群,用木板使劲向天空打出去,无数双眼就顿时在夜晚里明亮起来——天上下起了红红的雪、空中绽开了红红的花,人群上飞舞着火红的蝶。”而且“三五个勇敢的舞龙勇士舞到酣畅时,索性把衣服脱了,光着膀子,引着龙在铁水花丛蝶海处舞动。在惊呼声中享受这种甜蜜的疼痛。”这样的场景真是极其诡异神奇,令人叹为观止,作者不禁叹到:“在普定看冲龙,你就会感受到什么是热血沸腾,什么是有惊无险。但就是这种过于烫的热,这种过于野的狂,这种过于艳的美,这种过于浓的情,才使普定冲龙千年来一直作为一种热的极致、狂的极致、美的极致、情的极致。”[5]1121-122普定冲龙给予作者神奇诡秘的非凡感受,并促使作者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
其次,安顺地域风情散文的神奇诡秘还体现在文学作品的描述中。宋茨林在散文《庙与学校》中写道:“树干上钉与铁钉,缠以令人心悸的红布条。有人说普定是个出精出怪的地方,想必这几棵巨树早已成精成怪了罢?乡人告诉我,这些白果树有‘公母’之分,‘公树’曾化为俊男上云南嫖过婆娘,‘母树’亦曾变成美女蛊惑过有钱人家的贵公子。”宋茨林在听到这样一些令人惊异的奇闻后,“不禁抬头仰望,只觉得这些巨大的怪树在冲我发笑。山风吹起,树叶沙沙作响,向我传递着神秘的暗语。”[4]295后来,作者就描述了自己对精怪的恐惧:有对白衣女人神出鬼没的惧怕,有半夜梦魇的惊魂缠绕,乃至于因害怕而产生的幻觉等等。他在《美丽的“鬼蜮世界”——安顺麻风村记事》叙述看到“夕阳映在河里,大红,软乎乎地浸在绿色的水里,显得异样的大,我第一次看见水里的太阳竟是这般的怪异。有山鸟在清脆地啼鸣,不紧不慢,忽高忽低,似有若无,安静极了。忽然听到河对岸的山崖上有人在唱歌,听不懂,声音不高,如吟如诉,同样显得怪异。”[4]362这最能体现安顺文化的神奇诡秘之美了。安顺的山川地形、人文景观赋予作者以神奇诡秘的题材来源,作家们把这种风貌诉诸于散文中,使散文成为具象反映“神奇诡秘”精魂的文本。
3.简洁质朴的表现方式
宋茨林将安顺散文作者丁杰、李天斌的新作称为“土地里长出的散文”,这一评价一方面说明了安顺散文有极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也恰当地概括了近年来安顺散文发展的主要特点——简洁质朴。简洁质朴的表现方式可以概括为两个鲜明特征:一是简洁质朴的体裁形式;二是简洁质朴的表现手法。 戴明贤先生在他的《一个人的安顺》的《后记》里,就谈到他因“找不到一个惬心的形式”而感到的苦恼,甚至因此而迟迟不能动笔,开始想写成一部小说,但感到这样一来,那些人和事都失去了鲜活的个性,掉进了类型化的模式里,于是最终决定去掉小说的虚构,写成“忆旧散文,一切按记忆实录,述而不作”,原汁原味地反映普通安顺人的普通生活。戴明贤先生这种“随笔风”文体的选择,也代表了安顺文化界、文学界同仁的共识。宋茨林亦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时代,这个‘生猛的时代’正为我们提供无数的传奇故事,无数的精彩细节,大量的生动事实。无数的读者渴望最直接最迅捷地了解这些,他们呼吁:不要以假乱真,要让事实说话!”[4]207实录安顺的小城故事正是让事实说话的明证,讲述了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也正是原生态生活的文学呈现。生于安顺长于安顺的作家们,作为这个边远小城文化嬗变的“目击证人”,将他们的所见所闻,用可视、可听、可触、可感的文字记录下来,留作永久的纪念。
与“随笔风”这一简洁质朴的文体相适应,安顺文人惯用的简洁质朴的表现手法即是“白描”。譬如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叙事记人,均只作白描勾勒,力求反映真实的内容。绝少夸张与铺陈,不作大肆渲染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描述,更不是洋洋洒洒的论说,而是一种内质深沉而表面平淡的叙述。例如作者入木三分地描写了无能而又无志的落魄人如何混饭吃,说这个人的本领就是到店铺混饭吃,老板员工都对他厌烦入骨,但又无可奈何,总想气气他。“一次,他又在恰当的时候施施然而来,天马行空聊了一会。大司务把饭桌摆开了,老板只好请他入座。店员们依照事先的策划,待他快吃完一碗时,各自专心扒饭,目不斜视,或径自端着碗去厨房舀汤,总之是不主动给他添饭,让他落个半饱,扫一回脸面。此公不动声色,对老板说:有个朋友想买一幢房子,托我帮他去看看划得来划不来。我今天去看了,抵得白捡!不说梁柱,连椽子都是饭碗粗。说着朝老板亮了亮空碗。老板听得大感兴趣,忙问下文,没有在意。他又亮亮空碗说:椽子都是碗口粗细。这下老板发觉了,忙叫:给先生添饭!小店员只好起身盛饭,双手奉上。”[6]]47
这一段叙述寥寥两百多字,用笔极其简洁,却将一个无才无能混饭吃的落魄者形象跃然于纸上,生动地刻画出其油滑世故、死皮赖脸混饭吃的嘴脸,但又让人忍俊不禁,这就是人间百态啊。
又如《一个人的安顺》对安顺人个性特征的描述:“数百年自足自乐的生活方式,涵养出大量的聪明人、超脱者、幽默家。百艺一学就会,浅尝辄止。世事洞察于胸,仅供谈助。月旦人物,绳尺从严,自我解嘲,言辞尖利……半天可办之事,无妨置之半月;一周可成之事,何不放它一年。终于不了了之,最为息事宁人;实在一旦提起,‘忙,搞忘了!’便是天大理由。谁若再较真,就是不会做人,大众嫌弃了。”[6]5-6戴先生以极其生动形象的文字传神地刻画了安顺人的性格特点:聪明机灵却又没有恒心、明白事理而又懒散度日。这引发读者的会心一笑,真是道尽安顺人个性之精髓。作者下笔很节简,给读者留出了想象与思索的空间,启人深思,给人以意犹未尽之感。此又为“质朴”的另一种表现。
4.恬淡闲适的审美内蕴
钱理群先生在为《一个人的安顺》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开篇《浮世绘》是让其最感动的篇章:“我从中看到了某种‘永恒’的东西。是小城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还是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我都说不清楚”[6][7]。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正是散淡的生活与闲散的风姿,而这正构成了安顺城及安顺人所特有的恬淡韵味。钱理群先生评价戴明贤其人其文,评价宋茨林其人其文,也冠以“恬淡”之美誉。何光渝先生亦认为,安顺近年来的散文大致皆有“安详沉静之美”。
恬淡闲适是一种心境,是一种韵味,正如一个看惯了人间宠辱哀荣的老人,带着安详沉静的神情坐在自家的菜园里细数落日。安顺人的恬淡闲适,来源于大模大样的黔中山水,更来源于安顺这座边陲小城海纳百川的气度。刘纲纪先生在《安顺文化沉思录》就指出:安顺文化是安顺地区历史悠远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撞击、交融的产物。刘纲纪先生的这段论述在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里也可得到佐证: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安顺来了“下江人”,带来了江浙地区的现代都市文明;来了“剧宣队”,即带来了五四新文化;二战结束后,美国大兵的到来则带来了另一种西洋的喧闹。这都说明,安顺这块土地并不封闭,它是和中国以至世界的更加广大的土地联结一起,息息相通的。所以,看惯了新鲜事物的安顺人保持着沉静内敛的秉性,凡事不张扬、不趋同,由此表现在散文中即是一种恬淡的风格。
本土作家李天斌读宋茨林的《我的月光我的太阳》,感觉像是“一个洗尽铅华的长者,很宁静的坐在太阳底下闲摆着曾经的经历,在冲淡平和的叙述中,我们根本看不出明显的惊涛骇浪和血与火。”[4]318这种风格不禁使我想起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二者在美学风格上是如此相似!确实如此,受到地域环境、文化精神的影响,安顺的散文作家自然共有一份“恬淡闲适”的气质。
四、安顺地域风情散文的本土性特征
安顺地域风情散文源于作者的本土意识,突显了本土性特征。安顺散文作家对安顺的感情深厚,故而作品多描写安顺,并在创作题材、表现手法、风格特色等方面不断发展变化,但是其本土性的立足点即是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其着力点即是安顺的地域特征。
1.极力再现安顺的历史风貌
安顺是散文作家生存、生长、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在描写文化意义上的安顺时,浓郁的乡土气息是作品的最大特色,正是“土地里长出的散文”,安顺地域风情散文真实地展示了安顺的历史文化风貌。如戴明贤的《一个人的安顺》以散文笔法叙写安顺的文化,他在《一个人的安顺·后记》称这是“一部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是文化志性质的散文”,正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大散文”,是“把文、史、哲都包容在一起”,“包含了社会科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等价值和功能的文体”[4]6。可见,这是一种历史文化含量极为深厚的散文。《一个人的安顺》以舒缓委婉的笔调,描绘了老安顺的城市面貌、地理位置、地域文化、安顺人的性格、生活等等,如开卷第一篇《浮世绘》写安顺的地理位置:“西门通云南,在政治军事上都很重要,所以安顺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称呼 。东门通省城贵阳,经贵阳而与全国相通。”安顺地域文化的特色:“明初中央政府的屯军移民,给小城带来一股强劲的江淮之风,形成今日备受注目的‘屯堡文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年代,大江南北不甘做亡国奴日占区同胞陆续流亡到这个大西南腹地小城,又一次带来一片惨烈的繁荣和多方位的外来文化。”[6]8
又如刘刚纪的《往事点滴》在对陈年往事的叙述中,一股文化气息在文字中流淌。其作《故乡的文艺》介绍了家乡普定的民间文艺:“如果说白天‘跳地戏显示了吾乡人民的阳刚之气和壮美的风姿,那么晚上‘玩花灯’。则刚好又表现了吾乡人民的阴柔之气和优美的一面。这一刚一柔,是互为补充的。”[5]236指出家乡的文艺有相当深厚的传统。此外,邓克贤的《上静乐下清泰》、孙兆霞的《沉淀在老照片中的文化》等散文都在述说安顺的历史文化。孙兆霞述说了对安顺文化的一种回望,指出安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展读这些照片,我仿佛看到了沉淀于其中的某种精神、文化信息。其中,有关城墙、城楼的几张照片,作为社会刚性秩序的物化形态,体现了被‘围’起来的家园之感。昂然挺立于坚硬岩石上的翘角飞檐,宛如铁骨凌霄,面对漠漠荒野,以其历史纪念碑式的沉稳和厚重,昭示着人类社会群体的组织、秩序与雄性。”[5]294
2.真实叙写安顺的现实生活
安顺地域散文真实而真诚地再现了安顺人的性格、生活等,极富个性地写出了自己身边的人或事,写出自己的“一个人的安顺”。 安顺小城故事可说是散文中的亮点。如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四十年代的安顺)、宋茨林《我的月光 我的太阳》(六、七十年代的安顺)。《一个人的安顺》展示了安顺人的文化生活圈,是名副其实的“小城故事”。有关文化教育、商业经济、战争、宗教、娱乐等各个方面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彪悍英武的马帮哥儿、霸道凶狠的练摊人、圣洁超凡的修女、慈祥稳重的账房先生,还有军人在戏院的提抢横扫、洋人餐馆的稀奇等等。
而《我的月光 我的太阳》中《邂逅放鸭人》《眼睛的故事》等描写的是下乡知青的经历遭遇,是作者避难乡下的岁月剪影。此外,如一尘的《记忆中的安顺》、陈明的《一个老人的古城记忆》、黄鹤生的《知青往事》、何平的《小城旧事》也在叙述往昔的安顺,一种怀旧的气息荡漾在字里行间。
这类散文中有一类是描写乡人的回忆性散文作品,如李培之口述,邵汇敏整理的《忆若飞》、朱文藻的《谈任可澄》、文龙生的《为西南联大校歌谱曲的安顺人》、姚晓英的《用生命歌唱——忆师兄蒙萌》、袁本良的《迟到的追挽》等作品多是对安顺的文化名人表示深切回忆与思念。
描写九十年代后安顺的散文作品,如邓克贤的《家有“仙妻》《杂话“冬至吃狗肉”》《店小名堂多》、李天斌的《我的小城生活》《夜晚三章》、卢仁强的《我和我的学生们》、周世杰的《昔日安顺市场》等散文展示充满世俗气息的城市风情画。
3.注重对山水风光的描摹
安顺地处黔之腹,滇之喉,境内喀斯特地貌极其显著,地域特征极为明显。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因地形地貌之利而形成的各种景观,这些景观进入作家的视野,赋予作家独特的审美感受,由此创作出描绘安顺山水风景、亭台楼阁的写景抒情散文。如王学书的《天台山记》、张麟的《三岔河》、杜应国的《古道精魂》、蒙卜的《回望穿洞》、梅培源的《高峰山 远年的虔诚》等。这类散文表现出景观与文学交融的奇采魅力。
安顺是一个旅游城市,拥有龙宫、黄果树、天星桥、格凸河等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其中既有自然景观,也有人文景观,皆是山水秀美,风光怡人。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赋予散文作品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有的优美动人,有的清新活泼,有的平淡悠远,有的深幽静谧……,都在展示各自的风格特色。这些优美动人的作品都是描绘自然山水的美文,如《至刚与至柔的不解缘》《山水灵性》《藏在大山深处的灵秀》《格凸三题》《犀牛潭传奇》等。在作家的笔下,千姿百态的瀑布、奇妙无穷的溶洞、闲静悠远的湖泊、秀美挺拔的石峰等等,都得到了富有情调而又纯美天然的描绘。戴明贤的《至刚与至柔的不解缘》对黄果树瀑布群进行了生动具体的描绘,“陡坡塘瀑布,是温厚的兄长,浩浩荡荡,浑然而下”;“星峡瀑布,是暴躁的小弟。那一段最窄最曲最嶙峋的峡谷,刺激得他气冲牛斗,咆哮如雷,跌跌撞撞地冲决而去”;“螺丝滩瀑布豁达爽朗,勤快地浣洗着一网又一网银色的丝束,一边絮絮地与割稻挞谷的农村妇女笑说家常”;“滴水潭瀑布便是最出众的妹妹,一位幽居在深谷的绝代佳人,洁癖使她甚至不许俗人偷窥一眼”;银练坠潭瀑布“有时笑靥如花,有时哀婉欲绝,喜怒哀乐,变幻莫测”;黄果树大瀑布“是家族的灵魂,群星的领衔。他尽显兄弟姊妹之长,涵养成一股雄浑、深邃、遒劲、厚重的阳刚之气。”[5]2-5作者采用拟人化手法,对不同瀑布的特征进行了极其生动的比喻说明,描绘出千姿百态的瀑布群。这些文字的脱俗清澈与调皮风趣,拉近了读者对景观的距离,扩展对于美的探寻视野和欣赏深度,极大地激发读者的好奇心。
4.注重文化内涵的丰富与深化
人文景观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精神追求以及人文创造,从而满足游者求知、求新、求美、求乐的需要。如郑正强的《千古之谜话红岩》、胡维汉的《人在谜中》、王学书的《天台山记》、邓克贤的《山城故事》等。
自然景观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着自然界蕴含的各种各样的美,深深地吸引人们去探求其中的美,令人身心愉快而又回味无穷。这“愉快”正是自然景观给予人的审美愉悦,而“回味”则体现在自然与人的心灵的深层次交合,即自然景观所具有的人生意蕴与生命价值。写景散文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游玩之中感悟人生、体味世态,所以散文作品展示的正是作者的生活秉性与地域特征。
如郑正强的《黄果树观水》把水与人进行了沟通,阐发了人与水的共同之处,并由此揭示睿智的人生哲理——人生如河:“人生不就是一条河!遇石就激溅,遇沟壑就奔流,能跑能跳能屈能伸不怕迭落敢闯阴河,磨秃岩的利齿打破山谷的苦寂,人生能如黄果树的水多好。不甘于平庸,做一名吼唱命运的摇滚歌手,当一回水流,用生命创造奇迹。到了哪一天不免要平静下来的时候,它已是博大得成为海的一部分。此时唯有它能说什么都经历过了。”[7]15
自然山水千百年来经历风吹雨打,一直屹立人间,多少沧海桑田,多少人事变迁,都能从中得到无尽感悟,这份深厚的文化内蕴从散文中阐发出来,拓展了散文的深度。
结 语
植根于黔中腹地的安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发掘安顺文化、培植安顺文化、推介安顺文化,正是安顺文人学者的历史责任。安顺文化是安顺地区历史悠远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所以,安顺文化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形态,并可以此来对抗全球化的单一和趋同法则。钱理群先生在《“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喜读<神秀黔中·安顺地域风情散文>》中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而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7]379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总体结构中,安顺文化无疑是一种弱势文化,面临着被边缘化、被忽略,甚至是被毁弃的危险;而汹汹袭来的城市化、现代化浪潮更是如洪水猛兽一般,企图吞没那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可见,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的某些历史在逐渐消逝,而文学理应还原历史的本原。当散文在叙说安顺的历史、文化、风物时,我们会感慨自己的城乡原来是如此美丽而迷人。散文把安顺地域的每一方面都纳入到作品的创作中来,使得很多也许被人们遗忘、不被人所重视的现象、人物、城市风貌、民俗文化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这种记录或者研究一方面拓展了地域文化的研究范围,扩大了文学的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地域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地域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怀旧情结、澎湃激情、感伤悲痛、欣喜惊叹等等都深深地感动我们,为那一份乡愁乡恋而感动。赞叹家乡风光、怀念故交旧识、为乡效力的情感暗涌于文中,热爱家乡之情溢于言表,使得我们为有这样的作家作品而自豪,也引发我们对历史、文化、人文精神进行深刻的思考。
注 释:
①关于这两种提法参见何光渝.构建地方文化的知识谱系——以五本关于安顺的书为例[C].安顺日报社编.黔中走笔——安顺报纸副刊文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钱理群.“土地里长出的散文”——宋茨林《我的月光,我的太阳》序,兼谈《黔中走笔》[M].宋茨林.我的月光,我的太阳.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