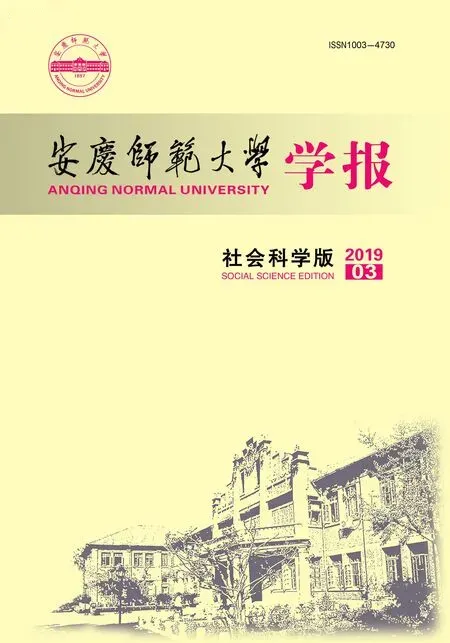评张乐天《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徐全民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048)
张乐天教授的代表作《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以下简称为《告别理想》)首版于1998年,2016年第三次印刷发行。从初版至今已整二十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二十年是较短的时间段。但就学术间隔而言,二十年会实现阶段性变化。《告别理想》再版说明该著作的理论观点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笔者认为,《告别理想》关于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发展与终结的论述剖析与资料发掘等方面至今仍属经典,值得研习。
一、宏观架构,立意深远
人民公社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时较长的农村社会制度,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同时期中国农民心目中,乃至此生命运都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而且,正如张乐天教授所言,今天的改革开放成效依然受其影响。“了解人民公社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解读当今改革开放中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的‘史前’。”[1]
《告别理想》不属于纯理论制度研究。张教授宏观着眼,建构了分析框架,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通过村庄里发生的人民公社活动实体展现了这一制度。全书结构框架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公社制度的嵌入”“‘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70年代中叶的公社制度模式”和“人民公社的终结”。张教授以村落世界—浙北联民村为故事舞台,用村落世界的活动书写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历史变迁,通过这四大问题完成了对人民公社制度的整体性论述。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是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人民公社制度建立意味着新制度与传统之间的相遇争斗。张教授在《告别理想》的第一部分“公社制度的嵌入”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在乡村社会的实行。他用“嵌入”这个词语形象表述了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的出现方式,这也留下了悬念。嵌入体与本地事物之间能否消除抵牾实现融合是这种活动将面对的挑战。处理结果即是“嵌入”活动的成功与否。为使“嵌入”活动得到准确理解,张教授将嵌入活动的整个舞台背景做了详细描绘交代,采用了完整的叙事写法。
第二、第三部分是对公社制度建立及其在乡村社会发展的论述。在第二部分“‘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中,作者从基层资料出发,详细描述展示了这些运动在基层的表现与实态,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建立、坚持和巩固。在笔者看来,这一部分的论述也是最出彩的论述。张乐天教授以旁观者的视角,小说式的书写展现了革命的袭来与当事人的种种际遇。它基本复原了那个时期里乡村社会的景象。
第二部分“‘四清’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村落政治”是四个部分中唯一题目里未出现“人民公社”或者“公社制度”词语的部分。这应是作者突出时代特色的处理。人民公社制度是中共于上世纪50年代后半段在乡村发展社会主义选择的基层制度。该制度的建立完善是在“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在公社制度的推行过程中,“阶级斗争”是伴行的工具或者手段。所以,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周围那些个早年认定的阶级敌人早已没了势力,但这一时期“革命”“阶级斗争”的色彩并未褪色。张乐天教授从乡村生产状况说起,先说明了公社制度推行后在乡村引发的动荡和随后的调整。随后第四章“新制度:秩序和冲突”直接点明了“继续革命”与“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无论“秩序”的稳定还是“冲突”的解决都引来了“革命”。而这里的“秩序”与“冲突”都是与“人民公社制度”直接相关的。“秩序”是“人民公社制度”引发的“秩序”问题。
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二十多年,在中国农村留下了较深的印记。我们也得以能细致地观察其表现与影响。第三部分展现了人民公社制度治理下的乡村社会实况。张乐天教授以70年代中叶为中心进行了说明。人民公社制度发展到70年代已成为农村社会里持续运转的社会体制。加之作者的经历,他选择了这个时间段来具体观察。张乐天教授从“公社制度的特征”“公社农业经营”和“公社的社会生活”三个方面说明人民公社制度治理下的浙北乡村社会景象。“公社制度的特征”表现为两点:“集权体制”和“村队模式”。这是张乐天教授关于人民公社制度运行模式的理论总结。制度特征说明了人民公社制度在乡村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关于“公社农业经营”,张乐天教授用了较多的笔墨。从“作物选择”“劳动投入”“生产技术”“产品出售”“工分制度”“收入分配”等方面详细具体地解析了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经济。而经济状况又反映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治理效率,更是影响决定着公社制度的存续。在各种语境里,人民公社时期的社会生活都不属于社会建设的重点。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活动依然是日常生活构成的主要内容。而且,恰恰是源于生活的动力支撑了社会的不断前行。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双方的互动表现为这样的结果,人民公社制度冲击了传统的村落生活,而传统的村落生活又对人民公社制度给以消解。
随着70年代的过去,人民公社制度也走向终结。第四部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从“公社的困顿”说起。首先张教授在“公社的困顿”一章里罗列说明了公社制度在发展中无法克服的问题。这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的概括:“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可能依靠强制长期维持,当与革命相关的强制随着革命的结束和时间的延展而日益弱化的时候,公社也就日益走向了它的终结。”[2]315新中国成立近三十年时间,农民生活没有富裕起来。人民公社制度的社会发展效率被怀疑就成了无法避免的反应。突破困境的办法最终选择了让公社解体。
《告别理想》一书是一种人类学的微观分析论述。单纯从知识性来说,张乐天教授的《告别理想》给我们展示了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的社会实景,贡献非常大,可微观分析容易陷入碎片化、无意义。张教授在书本的最后一章,把他的人民公社制度研究引向更加的宏大的主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张乐天教授在论述了公社制度被废止后没有就此收住。他进一步观察了公社解体后的乡村社会。时间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对改革后的乡村政治、经济、文化变迁进行了述论。从经济角度来看,人民公社解体后的联民村释放出了巨大的生产效率。人们不仅摆脱了贫困,并很快走向了富裕。乡村文化则在传统与新意中发展。这也使该著作的意义进一步深化。至此,张乐天教授对人民公社制度完成整体性分析。
二、微观剖析,结论清晰
关于人民公社的疑问不仅仅学界研究,也具有社会普遍性。张乐天教授在《告别理想》一书中论证了既是学术的,又属平常百姓关心的各种问题。如人民公社制度为什么会存在那么长时间,又是什么因素消解了这一制度。不同于抽象制度推理研究,《告别理想》对这些问题做了微观解析,结论清晰具体实在可触摸。
第一,“村队模式”是影响人民公社制度存在与结束的首要因素。“我们在村队模式中可以看到公社的秘密——公社制度存在的原因和公社制度失败的理由。”[2]189关于张乐天教授提出的“村队模式”概念,笔者认为最好用书本中的原话来理解,即“村落就是生产队,生产队就是村落”[2]7。最高层为在乡村发展社会主义所提出和建立的人民公社最初是一种完全突破自然与传统的单位。“一大二公”是它的初设特征。这种“一大二公”在“三年自然灾害”后做了调整,放弃了原来的“大”。大公社被调整成小公社,建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运行模式。生产队成为生产资料产权、生产组织管理、劳动收益分配等事项活动的基础,而生产队规模与传统村落范围基本吻合。由此“村队模式”出现。人民公社制度以“村队”吻合的规模继续运行。但传统村落的面貌在这种模式中又显现出来。一旦村落的形象出现了,村落的功能便也逐渐恢复。过去的生活传统终未能完全割断。在新制度与旧传统共存的局面下,我们需思考生产队或者村落是靠什么运转?是人民公社制度还是传统力量?人民公社制度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如何体现?就此探究下去,公社制度的失败就成了不难得出的结果。这是张乐天教授就上面那个问题给出的第一个答案。
生产效率水平是解开公社制度运行的第二把钥匙。“在泛政治化的时代,在大话、空话、废话泛滥成灾的气氛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些实事求是的东西,这或许也是公社制度可能得以生存的一个原因。”[2]218今天我们经常拿集体化时期有关劳动的荒唐场景进行调侃、戏谑:“‘下地一大片,回家一条线,做活互相看,争分轰轰乱’;‘出工鹭鸶探雪,收工流星赶月,干农活李逵说苦,挣工分武松打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后来演变成‘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和收工集体化’。”[3]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样的场景关乎其一日三餐,生命存亡接续的。照那样持续下去,人民公社无法延续二十多年。所以在公社巩固后的时间段里,生产情况肯定已是另一种情形了。无论劳动效率多么不理想,生产队的运转效率应是处于能维持自我生存的水平。这种维持与设想中的社会主义农村不相符,可这种状态却是现实可能的。张乐天教授对70年代中叶浙北农村生产经营的考察给了我们一种宣传报道中看不到的现实景象。勤劳务实的农民在一些时期里表现出愚昧无知、极易被煽动,可农民的务实性并未完全消失,还是社会自我救赎能力的构成。这种自救又背负了公社的生命。这种自救的另一面是农民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不认可。农民的劳动表现说明了公社制度对劳动积极性的调动能力。
“过密集型技术”构成了公社制度活力的维持因素。如果农民都实实在在的出力干活,具体在干什么农活呢?在户籍限制的前提下,他们在有限的村落或者生产队范围里,有那么多活可做吗?“过密集型技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过密集型技术的引进是公社制度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的原因之一。”[2]237这种过密集型技术具体的说明了当时农村农事劳作的情况。张乐天教授通过上述三点揭示了公社制度能存在那么多年的现实原因。
公社制度终结的原因除了前述“村队模式”的作用外,还有下面的问题。首先是收益分配促成的不稳定问题。“但是,外出农民与仍在本地务农农民之间的矛盾却加剧了,这种矛盾使得生产队的劳动力安排十分困难,并最终成为导致生产队解体的一个重要动因。”[2]231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对公社制度的消解,这种消解是一种平和间接的活动。人民公社制度在舆论引导与革命强制下建立起来,农民在支撑公社的同时又对其削弱,比如外出干活的农民带来的冲击。无论如何,计划总有顾及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在广袤的农村社会。一些有手艺的农民总是被自家生产队外的空间所雇用。而恰恰是这些无法杜绝的计划外活动凸显了公社制度的局限。外出农民比在村里只能靠年终结算的人能获得更直接、更及时并且更多的现金。这些钱对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是非常有力的。裂缝时时刻刻都在出现,万千农民在看似合法合规的自发活动中使公社制度逐渐崩塌。
第二,日常生活进一步凸显了公社制度的困境。“公社的这一制度安排有明显的二重性,公社在小农家庭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秩序,但小农家庭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瓦解公社的力量。”[2]282社会生活也与公社制度相排斥。公社制度最初的模式是“三化”模式,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在“三年困难”发生后,这种“三化”模式做了调整,生活集体化基本取消了。但追根溯源看,公社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生活领域。公社是高度集权的,高度计划的。这种集中的体现就是涉入百姓日常生活,甚至一日三餐。可公社、生产队等单位无法完全负责家庭所承担的功能。传统家庭恢复的同时,也意味着公社活动的收缩,最终公社被逐渐的“瓦解”。
由中央政府发起的举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社会被检验与淘选。无论其最初的设想多么美好,在现实面前成了落地却未能生根的理想。这些现实包括现实的劳动付出与收益,现实的衣食需要。正是这些平常琐碎的事情支撑与瓦解了影响整个国家的人民公社制度。张乐天教授通过考察集体化时期的联民村,把这个过程很具体详细地揭示出来。这样的研究要比那种纯理论或者宏大范围的研究更有说服力与具体性。
三、挖掘史料,贡献卓广
《告别理想》研究的是浙北村庄联民村。村庄研究在人类学、社会学中是较普遍的研究对象,属于微观研究。微观研究的成功离不开对区域地方情况的详尽掌握。体量虽小,却要实现小中见大,一滴水里看世界。研究者欲说明什么问题,需将村庄面相详细的描绘展示出来,所以研究者要尽可能地拥有丰富翔实的地方资料。张教授在写作《告别理想》时,拥有非常丰富充实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对学术发展具有卓著广远的贡献。
在写作《告别理想》时,张乐天教授掌握了联民村的丰富资料。其一,村庄集体化时期各种活动的完整原始档案。说明历史问题,最可靠的、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还是历史事件发生时自身留下来的文字或者实物资料。但由于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很多历史的原始资料或者遗失不存,或者记录时被人为修饰。而联民村集体化时期各种活动的文字资料都保存下来了,并为张乐天教授获得。其二,当事人的笔记资料。日记、笔记等资料的史料价值已被学者们认可并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利用历史人物的日记、笔记等资料做出了优秀的学术成果。这样的资料多出于文化人或者城市生活者之手。然而,联民村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周一堂却如同机关工作人员一样,保持着做工作笔记的习惯。在辛苦的农事劳作后,一个乡村农民趴在桌子上记下一天的经历。这一幅情景我们一般是不会想象到的。又因为与张乐天教授的早年关系,周一堂把六十多本工作笔记悉数送予张乐天教授。至此,张乐天教授拥有了非常详细的文字资料。“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家乡,我自己曾经所在的生产大队,我做过小队会计的那个生产大队,竟然保存着迄今为止全中国农村可能找到的最丰富、最完整、最多样化的原始文字和数据资料。”[2]16其三,访谈资料。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者通过田野调查向事件当事人了解信息或者感受,对地方文化习俗进行认识与体验。这些活动既丰富了研究资料,又使研究者能获得现场感,增加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在写作《告别理想》前,张乐天与曹锦清在浙北海宁做了长达一年半的实际调查,并合著《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4]。这些访谈资料也被利用在《告别理想》中。
四、余 论
张乐天教授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人类学研究成果,让我们更加直观具体地了解了该制度的表现与影响。这是《告别理想》一书的基本贡献。如若我们能结合实施该制度的来龙去脉加以认识,那我们会对人民公社制度形成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也将由此思考中国的“三农”特点,这也是该著作更具现实性的价值与意义。《告别理想》是一部极具引导性与启发性的著作。
在这里,我也想就《告别理想》一书中所谈到的内容作进一步的思考。张乐天教授以事件的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了人民公社制度。因其以村落世界为故事背景,所以书中也对村落生活做了一些描述。这也让我们在制度分析中看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农村面相,但村落生活的分析还是显得比较薄弱。
关于集体化时期的社会生活研究整体还是比较薄弱的。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一些主题研究中,如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知青上山下乡,等等,对这些历史的剖析也多习惯于从上而下地看问题。这与认为那个时代的发展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掌控有关。关于基层社会对国家政策的反应,与国家的互动的研究不够深入。
尽管在那段时间里政府表现出非常强的社会干预特征,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但社会的作用并未完全消失。看似整个国家的发展是基于追求政府目标实现的,可我们会于无声处发现事情的发展依然是由民众争取生活的动力完成的。人民公社制度的存在与消失实实在在地讲均未离开百姓的生活。这一点为张乐天教授所认识,可惜却未作深入的剖析。这在笔者看来是《告别理想》一书的缺失之处或者乡村研究的未来用力处。
——舒城舒茶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