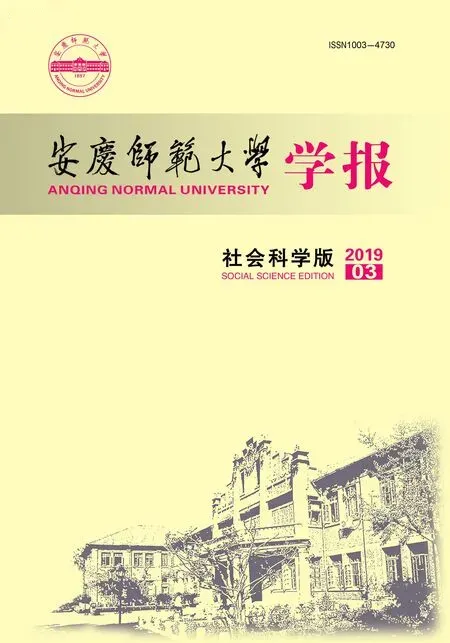韩愈“文以明道”思想对古文模仿的超越
王世红
(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中唐的士人积极入世,这源自他们对当时的现状和个人处境的诉求,更源自他们对当时民族、国家和社会状况深层次的忧虑[1]。当时的士人们怀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愿望,在忧患意识的支配下,他们对李唐王朝的社会秩序、统治思想、王朝中兴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探索,韩愈是这些士人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在对中唐文风改变的努力过程中,先提倡古文运动,倡导“文”与“道”合一,否定对古文形式与言辞简单模仿、因袭,并指出了这种否定的出路,提出注重创作者的个人修养,目的是“文以明道”,试图为李唐王朝建立统御的统治思想,完成王朝中兴。
但是,因为韩愈是从古文运动的角度来探讨创作主体的修养,这也成为后世尤其是宋儒对此颇有微词缘由之所在。理学大师朱熹虽然肯定韩愈“所以自任者不为不重”,但又指出他“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文字言语之工”,评韩愈《原道》是“无头学问”,评《读墨》也说韩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2]卷137,所以后世之人多以为韩愈“不知道”。另一位理学鼻祖程颐也对韩愈颇不以为然,《河南程氏遗书》第18记其语谓:“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3]第十八从程朱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程颐还是朱熹对韩愈从“文以明道”出发,最终达到修辞养性的心性之路颇不认同。笔者试图就此展开论述,就教于方家。
一、“性情论”与古文模仿
韩愈对唐代思想文化的贡献主要是基于对中唐文风的改变,亦即“文以明道”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演化自“去陈言”。韩愈思想中“去陈言”“文从字顺各识职”的创作理论,就是针对大历文坛的诗文形式与内容不相统一的现实提出来的。
历来不少论者虽皆注意到韩愈“务去陈言”之说。从大历以来整个唐代文坛的风貌看,气衰、文弱、辞弊,表现出一种“时艰方用武,儒者任浮沉”[4]的不景气现象。然而,由于大多数文人对当时文坛上内容与形式不统一的倾向危害认识不足,因此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到这一理论提出的现实意义。清代叶燮指出:“愈尝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俗儒即以此为晚唐诟厉,呜呼!亦可谓愚矣!”[5]卷一这一段话既深中时弊,又对韩愈“务去陈言”论做了中肯的评断。可以说“务去陈言”是对魏晋以来文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改变。
但是韩愈思想之主旨并不尽在“务去陈言”,而更在于由此推及的“文以明道”。
韩愈在《争臣论》一文中提出“文以明道”的思想:“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6]108可见他的意旨,简言之即是“修辞以明道”的主张:“‘修辞’就是写文章,‘修辞明道’的意思即‘文以明道’。”[7]柳宗元曾说:“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8]886又言:“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8]873可见韩柳主张在“明道”之处的不谋而合。
众所周知,“文”所载的本原应为“天地之道”,“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9]。这种“天地之道”应该如同宋儒所言的“理”,虽分殊,但理一也,这种“天地之道”韩愈称之为“性”:“性也者,与生俱生也。”[6]20“性”是人生而有之的,即人先天就存在的部分,不因贤愚及后天而改变其存在客观性,“性”即“天地之道”;“道”即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6]13韩愈确定了圣人所传之“道”的本质,即“仁义之道”,这样保证了道的正统性与正确性。
与“性”相对而存在的是“情”,情是由于人接触外界,受到外物刺激而产生反应的状态。“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6]20关于情,韩愈在《原性》中指出“情”的具体内容是指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其具体表现形态也依据性有三品而分为三种,即上品的性必发为上品的情,它基本上符合五德,“主于一而行于四”;中品的性必发为中品的情,它基本上是五德的不及,“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余四也混”;下品的性则必发为下品的情,它从本质上是与五德相违背的,“反于一而悖于四”。
个体生活在繁芜社会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各种外界干扰,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情”,因而不同人对不同事物产生不同认知,即便是同一人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也会因为时间、心境等而不同。而我们所作之文所记载的主体是具有唯一性的“道”,但是创作主体由于受个体“情”的影响,也就是个体对社会的不同认知与反应,导致古人的文章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形式,也即是“道”之载体——文章出现了多种形式。
在对“天地之道”以文记录时,由于记录者的“情”不一,记录者将自身对客体的感知也就是“情”付之于所作“文”之中,从而导致了“文”与现实的“天地之道”所载不一致。
韩愈认为是创作者个体因素和性格导致了文章形式的多样,简言之是创作者的“情”导致了文章的多样形式,诚如上所言,情为性之动,那么在不同人眼中,由于自我的个体感知不一,对同一事物肯定会有不同的认知,这样不同人所作之文,肯定会呈现不同形式。
“文”在韩愈看来是主体对客体感知的精华。“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6]233这种精华是作者的感知,但是作者为何要述著于“文”?在此,韩愈提出了“不平而鸣”,他认为创作主体对“情”的抒发就是“不平而鸣”。“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6]233
这种主体对客体的反应也即是心动,心动即是情,孟子尝言“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心之放亦即是本心不再,本心已受到外界干扰甚或污染,“情”在此处与孟子的“已放之心”内涵相同,情为性之动,“放心”则为“本心”之放。由此,韩愈思想深入到创作主体为何而“鸣”?
在《送孟东野序》中韩愈充分解释了“不平而鸣”,其一,韩愈提出了文学创作主体由“穷”的激发而到“鸣”,抒发其由“穷”产生的“不平”,而后达到文章“工”的整个过程。其二,韩愈讲“不平则鸣”,并不是只看到了在诗人身上存在的这种现象,而是从自然界的各种物体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平则鸣”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论述。其三,韩愈把个人的穷困愁思与国家兴衰结合,这就使郁积诗人胸中的“情结”有了实体,从个人的际遇到国家的兴衰,将个人与国家相结合,既愤己又忧国,不再是惨惨戚戚的悲己,思想得以升华。其四,就“穷而后工”这一个方面说,韩愈由诗到文,概括了整个文学现象,覆盖面较大。其五,韩愈不仅讲了“穷苦之言易好”,“穷愈极辞愈好”这一面,也比较辩证地论述了文学创作中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问题。即“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因此韩愈才有“恒发于羁旅草野”的体认。
“性”是唯一的,在“情”影响下,出现了记录“性”之文的形式多种,如此,带来的现实麻烦是如何认识“道”。“情”成为现实与“道”之间的横隔,一边是天地秩序、人之伦常的“道”,另一边是人因外物而激发的“情”,创作者如何保持“文”不因“情”而变样、走形。
韩愈提出了学习古文写作的主张,在他看来古文是对“天地之道”的完美记载。
他在《答李秀才书》中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6]176表明他对古文所载儒道的关注与重视。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他的表述更清晰:“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6]304-305表明他对古文所载之道和古文中所体现往圣道德价值的认同,古文是往圣对“天地之道”的完美记载,是往圣对社会的道德文章,是往圣的价值取向和意旨,做到了“天地之道”与创作者的完美结合,因此他主张学习古文,主张通过学习古文恢复儒道之传统,这就是“文以明道”。
至此,韩愈的思想需深入一步,他提出了文章复古的主张,复古人之所作,重新认识古文言辞中所载“天地之道”以及往圣的道德使命与责任,通过学习古文来了解古文之真正内涵,摒弃时下华而不实之文,传承开启新的载“天地之道”之文,这就是“古文运动”。
二、“辞意之辩”及对古文创作简单模仿的超越
现实中又当如何学习古文呢?可以说,学习的直接且有效的方式是模仿,问题是简单模仿的对象只能是形式和言辞,对创作者的社会道德和历史使命却无法承载,因此模仿必然需要被超越。众所周知,诗备众体者杜子美,文备众体者韩退之,就是说韩愈能集前代之大成,但是并不是说韩愈善于模仿,林纾在《春觉斋论文·忌剽袭》中曾论:“韩者集古人之大成,实不能定以一格。后人极力追古人而力求其肖,则万万不能不出于剽袭。剽袭即死法也,一落死法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何者?心醉古人之句法段法篇法,处处为之拘挛耳。……昌黎之‘迎而拒之,平心察之’此便是不存成心去就古文。”[10]
因为古人文章形式的多样使得后人在学习过程中并不能排斥为表达个体的不平而刻意模仿古人的文辞,结果是忽视了对古人文章中的“圣人之道”学习与继承,也有人基于此而质疑韩文之奇、怪。其实韩愈最根本的追求在于不落庸常,在于不苟流俗,并非单纯好奇尚怪。他在《答刘正夫书》中说,“无难易,惟其是耳”,认为作文当不拘难易,但要归本于其所当然,这个当然,就是“明道”,就是要表现一种足以发扬古道的卓荤不群的精神个性。他主张文辞统一,而又以传道为前提,“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6]176。
古文是对“天地之道”最完美的载体,所以在解决了别人对其文章形式的责难后,韩愈所要做到就是解决采取何种方式学习古文。但是从魏晋以来,华丽骈文盛行,模仿之风趋盛,导致文风式弱,从而对文章到底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也争议不断。
如果韩愈不解决纯粹对古人文章言辞与形式的模仿这一问题,势必导致对古人文辞形式的因袭与模仿之风大盛,因为学习古人文章最有效的且简单的方法是模仿因袭古人文章的文辞,如此则必然会使所作之文仅仅是对古文文辞形式的复制,不仅丧失其原有对社会的道德价值,更无法体现“天地之道”,不能全面反映天地秩序和人之伦常,如此必然无法体现出道之本原,势必回归到魏晋南朝以降注重文辞的做法,那么对韩愈而言何谈文以复古,怎能一振唐代文风?又何谈“文以明道”及“古文运动”?
有鉴于此,韩愈的思想又进了一步,他指出“师其意”的主张:“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6]206接着他进一步重阐释:“昔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有文字以来,谁不为文?然其存于今者,必其能者也。”[6]207
在这段文字中韩愈指出了学习古文的标准,即学习内容不是古文的形式或言辞,而重在于古文作者的意旨,同时也指出学习古人的方法,即“能自树立,不因循是也”,因为古人道德文章中所体现的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德性是无法“因循”的,因此简单的模仿是无法完成文章的道德使命。
韩愈所追求文字因气而发,摒弃对古圣人之作的模仿,并不是韩愈标榜个性,从而走进彻底排斥古圣人之作的狭隘境界之中。恰恰相反,他明确主张为文当闳中肆外,要博采众长,对于百家之作,非但不要排斥,而且要大加汲取精华,进而站在百家的坚实的精髓上成一家“明道”之言,文备众体者韩退之。《进学解》中太学生对国子先生的相关评论,可以看作是韩愈的“自我评论”:“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6]44
因为古文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言辞形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体现了先圣的社会与道德的规律与本质,承载了古圣人对“道”的体验与认知,可以为封建政治提供统治的蓝图与模式。所以作为出世文人,学习古文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同时对古文的学习又可以是一种修行的手段,学习古代圣人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社会道德责任感,比照自身而“日三省”以增加主体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心,而不是简单的学习古人文章形式与模仿言辞。
在这里韩愈指出古人文章的价值不在“文辞”,而是在于“文意”,而且正是因为“自树立”,才使得文章得以保存并传承下来。因为能够从典籍传统中提炼出“圣人之道”,所以他主张古文写作,但因为古文写作与思考古圣人的价值观是相始终的,所以简单的模仿又并不足以完成文章对古人价值观的追求。这样韩愈重新开启了一条学习古文之路,即在学习“圣人之道”时,无需对古人文辞的刻意模仿,而是注重于对“文意”的传承与遵循。
这种古人在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即古文中所含有“圣人之道”,这种“圣人之道”既可以指所有圣人的道,即从所有圣人的所有成绩中所了解的道;又可以指具体圣人的道,指作为圣人的孔子或者为其他圣人所拥有并用于指导任何人的价值观。后世文人通过学习与修养可以取得“圣人之道”。而这些并不是简单模仿或者因袭能得到的。
至此,韩愈需要解决的就是对模仿超越后的出路,即为文时如何做到“自树立”。
三、“自树立”与创作主体的修养
既然模仿古人文章的文辞是没有前途的,那么怎样才可以使“文”具有生命力呢?这就必然涉及作品“自树立”与创作主体修养的关系。因为“心动”导致文与道不一致,所以如何做到不“心动”成为关键,也就是创作主体如何保持本性,这沟通了为文与注重个体修养的联系。
韩愈认为要保持不“心动”,就需要创作者加强自身的修养,以保持本心的平静,唯有这样才可以领会古文中所体现的“圣人之道”,也即是文章体现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其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6]171因此韩愈认为这需要向古人学习,他认为古圣人“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因此“处心有道,行己有方”,他们善于修养,所以为文才能体现出“天地之道”。
那么如何修养,修养内容成为问题所在。对于修养内容韩愈提出了养“气”的要求。因为“情”的不一导致所产生“气”的多样。这种“气”是一种已发状态的,它由外物引起作者内心的不平感应而生,因此“气”的释放载体——“文”也必然体现了不同作者的创作目的与意旨。因为“文”由个体应“气”而产生,这种“气”是对“天地之文”的感应而生成的,正是这种感应联系了创作主体与自然本原“道”,而这种“气”又是以文字形式来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从而“文”具有了作者的主动性,加入了作者个人的情感,而非对“天地之文”的简单临摹或复制。这样因为个体所涵养的“气”的不同就导致了文章的形式多样。所以必须要通过养气来增加修养,以达到气养文顺的境界。
这里韩愈提出了修养“气”的具体要求。他认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兴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6]171“气”即作者的情感。韩愈认为为文者要养“气”,才可以使“气”保持在一种平静的状态,也即是宋儒所言的未发状态,如此所作之文方能体现“道”。在《答李翊书》中韩愈要求文以气为先,把气与蕴含气之语言形象比作水与浮物的关系,意在强调古文不同于矫揉造作、骈四俪六的时文,意在强调古文与道德的联系,从而提出道德修养的必要,这就为当时古文习作者指明方向,即为文者必须先养气,气平而心静,心静方可“参天地、赞化育”,为文者才可做到辞事一致,文亦能重现“天地之道”,可见辞事一致之重要。
从贞元至元和年间,韩愈多次论述辞事不称、陈言以造诟病等问题,其根本目的在于指出言气不一之祸。《答李翊书》云:“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6]170去陈言之难,当与时下俗文仍有广泛市场有关。《与冯宿论文书》云:“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小惭者亦蒙谓之小好,大惭者即必以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6]196正好证明陈言为祸之深,俗下文士之所好。
韩愈在创作新型散文时所提倡的“务去陈言”与“辞事相称”,即追求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一致性,也即是“文”应与自然之道一致。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点,仅仅“务去陈言”,简单解决辞事不称、陈言以造诟病等问题还不够,还要达到辞事相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立志养气,心醇而气和,立志养气方能做到“辞事相称”。他在《上襄阳于相公书》里讲辞、事、气的关系时,说:“劲气沮金石,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6]148又在《进撰平淮西碑文表》里提出“辞事相称,善并美俱”的问题。他很有见地的把辞、事、气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语言充满“沮金石”的劲气,才能言语与事相侔,使文章达到“辞事相称”的境界。他又进一层讲,要作到“辞事相称”,必须立志养气。志是养气之本,志立则气备,气备则言宜。他要求凡为文者必先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即“人文一致”。如此方能以文传道,道立则文成。
要立言必先养气,要养气必养根,只有根深才能实硕。韩愈言:“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哗。”[6]169无望其速成,是要有毅力;无诱于势利,是讲专心致志。此意,韩愈在《答尉迟生书》里作了进一步阐释:“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文。”[6]145“气”是人格修养的总和。气修则辞足,辞足为文则体现“道”。
他还向青年指出养气的方法:读圣人书,立圣人志。识真伪,练真功。一辈子都要坚持自身修养,读古书,辨真伪是一种境界,从芜杂到精醇是更高的境界。只有达到这一境界,才能使得所作的文章与道相一致。其实,韩愈一生就是以仁立志,以志养气,以气运辞,意随气转,气宏意肆,浩乎沛然。施于文章,法则天成,意趣横生,行则当行,止则当止,游刃有余。这样作出的文才可以承载“圣人之道”,才可以完成文章之“化成天下”功能。
古圣人中孟子重养“浩然之气”,所以韩愈树立孟子为榜样,“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已有方”,在韩愈看来,唯有养“浩然之气”,气、辞、文一致,即使文章形式不一,但是文章主旨和所载之道一致,“圣人之道”作为一种参照物,比照自身已经引发的情感,从而知道该采取何种方式使得“心”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即“性”的未发状态,以保持内心的平静。
因为古文的作者具有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因此他们的文章与“文”具有了一致性,反映了天地的宇宙秩序,这种“文”经历代传承成为“圣人之道”,唯有如此古人的文章和“圣人之道”才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古人的文章是演绎和阐释宇宙秩序的典范,这种文是古人对宇宙秩序规范的正确反应,因此体现了“圣人之道”。而现代文人的作品唯有如此才具有生命力,才可以看作为对“天地之道”的一种承载。
这样为了使文章具有和“圣人之道”相一致的价值,就需要注重自我的修养,这就回归到自我修养的“心性”之路。作者如果想表达不平,想使得文章具有生命力,那么就应该学习古圣人之道,“师其意”,但是在“师其意”时,我们要学会“自树立”,而能做到如此必然要求作者加强个人对“浩然之气”的修养。而对于“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6]48的现象是坚决要杜绝的。
韩愈认为虽然唐代“文”成为传承“圣人之道”的载体:“昔者圣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辞矣;然犹不敢公传道之,口授弟子,至于后世,然后其书出焉。”[6]135但是他同样不排除“文”所受挑战并开始下落这一事实,然而韩愈没有将“斯文”的衰落归结于片面地追求华丽的词藻和韵律,而是将文章的衰落与作者的道德相联系。因此他认为创作者为“文”当具有德,当加强自身修养,重在养“气”。
提倡文以载道的宋代周敦颐曾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11]卷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对文章本质内容的解释,即文章外在的文辞和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章中所体现的作者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如果作者没有对社会深刻了解,没有对社会深厚的责任感,其所作“文”的价值是不大的。而如果需要文章具有价值,则作者应该注重自身的修养,维护与文一致的道的行为是可以预见的。这与韩愈对古文的理解与要求如出一辙。
韩愈毕身致力于实现儒道对思想界的统御,着力于从开启主体道德自觉的角度来绍承儒道,他深刻地继承了先秦儒学注重主体修养的追求,也就是个体通过注重道德修养以达“道”,绍承了儒家心性之路。他倡导古文运动的目的是复兴道统,通过道统的复兴,恢复儒学的传统伦理观念,使得儒学的地位一尊。他以复古为号召,在思想上复儒学道统之古,文体绍承先秦、两汉时散文之古,目的是试图给当时混乱的思想界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建立维护唐王朝统治并统御天下的主流思想,在“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情势下,实现儒家一尊,从而达到思想界的一统,思想一统最终为实现唐王朝政治的统一。这也是他极力激励后学、推荐英才、敢为人师的原因所在。
韩愈为了避免创作者把古文写作简单当成一种形式的模仿和言辞的因袭,他提出创作者要注重对自身道德修养的要求,绍承了先秦注重个体修养心性的传统,是对先秦心性论的一种恢复,同时又开启了后世特别是理学中对心性问题的探讨。韩愈追溯并恢复了孔孟之道的心性论,试图以儒家一以贯之的心性说,重新开启修养“浩然之气”传统,目的是让中唐文人更多注重自身对道德的修养,实现“文以明道”的主张,重振中唐儒学的统御,最终完成中兴李唐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