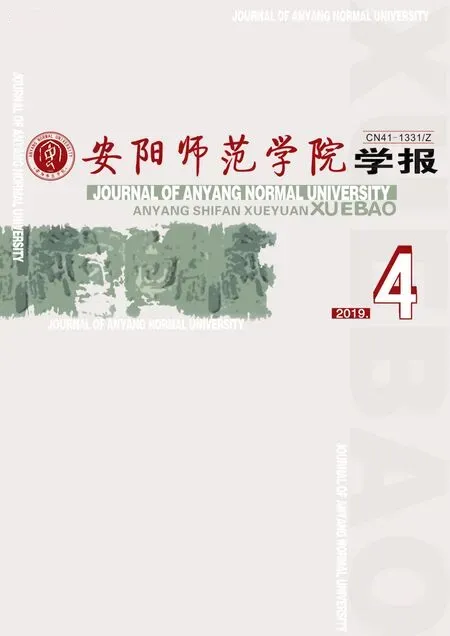论教师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行为
王守俊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北京 100048)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立法和主体范围
我国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只规定了适用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1979年我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基本不存在非公有制单位,因此实践中也不存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需要用刑法加以规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剧烈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过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组织形式、经营机制逐渐向公司制转变。同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大量涌现。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经济活动主体多元化,在经济活动和经营活动中,各种市场主体为促成交易而行贿受贿的现象开始滋生蔓延,对经济生活和经济秩序造成严重危害。为此,1993年9月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1994年7月施行的《公司法》都规定了追究商业贿赂行为刑事责任的条款。(1)1993年9月制定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 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7月施行的《公司法》第 214 条中又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由于这两部法律对商业贿赂行为都没有规定具体的罪刑条款,而当时我国无论刑法典还是单行刑法中都没有适用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具体罪名规定,受贿罪的主体又要求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这导致对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企业职工(包括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职工)在经营活动中的受贿行为进行刑事惩治于法无据。有鉴于此,1995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的《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4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本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这两个法条明确规定了公司、企业职工受贿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由于该决定第12条明确将国家工作人员排除在第9条规定的犯罪主体之外,(2)《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12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犯本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规定处罚。”因此第9、14条规定的犯罪是专门针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司、企业职工受贿行为而设的。这就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最初源头,当时被称为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受贿罪。
1997年刑法典修订时,《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内容被刑法典吸收,其中公司董事、监事、职工受贿罪的规定变成了刑法典的第163条,法条整合修改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5、386条(受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随后,两高司法解释将其命名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1997年刑法第163条的规定除丰富完善了该罪的犯罪构成外,对犯罪主体的规定与《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12、14条的规定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范围是一致的,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
1997年刑法出台后的几年里,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又发生很大变化,各类非公有非企业类社会组织,如各类协会、民营医院、私立学校等因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出现,这些单位也经常发生行贿受贿现象,危害严重,亟需规制。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批准了我国政府参与缔结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承诺履行的对于所有私营部门内贿赂予以刑事惩治的公约义务,需要通过修订国内立法加以落实。为此,2006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对1997年刑法第163条进行了修改,将原法条规定的犯罪主体“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修改扩大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3)修改后的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385五条、第38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以适应惩治私营、民营非企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行为和落实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两高随后将其罪名修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包括哪些?
从理论上说,一切雇佣职业甚至非职业行为都有职务廉洁性的要求,无论做什么工作,也不论身份如何,不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都是基本职业操守,否则就会破坏职务行为的廉洁秩序。国家工作人员从事的是公共管理工作,手中掌握的是公权力,其违背职务行为廉洁性要求的受贿行为危害更为严重,因而世界各国立法都对公务受贿犯罪单独规定,对非公务的职务受贿犯罪行为另行规定。
从逻辑上讲,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是一对矛盾概念,除了国家工作人员,其他一切职业甚至非职业雇佣劳动者都可以说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只要确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也就能确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我国1997年刑法有明确规定。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由于这一规定中“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意指不明,在司法审判中难以适用,2003年11月最高院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特征和范围做出了明确界定。该纪要中“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主体认定”之(三)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包括:(1)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4)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根据上述法条和纪要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或者由上述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协助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和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据此,我们认为,凡是不属于上述规定中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无论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还是在各类非国有企业、非国有非企业类单位工作,无论是从事管理岗位、技术岗位、生产岗位还是服务岗位的工作,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4)《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也规定:刑法第163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适格主体。
二、教师应当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教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这个问题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上没有明确规定。虽然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等物品销售方财物,为其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这似乎表明司法解释认可了教师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由于同条第二款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学校物品采购中收受销售方财物,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做了单独规定,(5)《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的采购等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385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第二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所以根据该意见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尚无法得出司法规范文件明确将教师认定为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结论。
在理论界,非公立学校教师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这一点大家意见一致,公立学校教师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则存在争议,有学者就认为,由于公立医院、公立学校依靠国家投资,获得了国家财政拨款,因而公立医院的医生、公立学校的教师当属国家工作人员。
教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判定涉及到的关键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和具体判定标准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理论界历来有身份标准说、公务标准说和身份公务结合标准说三种观点。[2]而从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看,1997年刑法第93条规定的,即刑事立法上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在在各类单位,基于各种依据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本质特征和判断标准就是是否从事公务。因此,界定清楚“从事公务”的概念和含义,也就能确定教师的工作是不是“从事公务”,教师是不是我国刑法中认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何为“从事公务”? 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给出了解释和界定。纪要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犯罪主体认定的解释之(四)对“从事公务”的表述是,从事公务是指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职务活动。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国有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会计、出纳人员等管理、监督国有财产等活动,均属于从事公务。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技术服务工作,如售货员、售票员等所从事的工作,不认为是公务。
由于从事公务是代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履行职责,非公立学校的教师肯定不是代表这些国有单位履行职责,所以他们肯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公立学校的教师是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呢?根据上述解释,公务是代表国有单位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的职务活动,主要表现为与职权相联系的公共事务活动以及监督、管理国有财产的活动,而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主要职务活动是教学以及辅助的教学管理,很显然,教师的工作既不涉及公共事务管理,也不涉及国有财产监督管理,其工作内容也不是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而是属于专业(技术)服务工作。因此,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非公立学校的教师,都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教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行为
虽然从逻辑上分析,教师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从来没有明确教师作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适格主体的身份,更没有明确教师职务中的哪些行为可能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008年11月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出台。该意见第五条第三款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这一规定第一次明确教师可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是该意见一出台,该条款的规定就招来了主要是来自教师行业的不同意见,有论者认为,制定意见者不了解当今学校的现状,现在学校要采购教学设施和桌椅、校服、电脑、多媒体设备等大宗货物,都要上报教育局,核准审批后再由教育局出面用集体团购等方式统一采购,普通教师包括校长根本没机会吃回扣。至于教材,也是教育局统一征订,教辅订什么,订多少都掌握在学校教务处或者学生处手中,教师连买一支粉笔的权力都没有。[3]
诚如所言,实际社会生活中,大到教学设施和桌椅、校服、电脑、多媒体设备,小到教材教辅等物品,教师参与采购的机会极少。笔者作为高校教师,知道目前高校大宗物品采购都是招投标,教材教辅学校已经不采购,都是教师开出参考目录由学生自己去买甚至复印。因此,《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在实践中适用的机会很小。不过该意见本来就是为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而出台的,其目的主要在于明确商业领域里的行贿受贿犯罪行为,教师职业行为中的行贿受贿并不是该意见关注的重点,其第五条第三款的规定目的只是在于明确如果教师参与学校的采购活动并且从中拿回扣、捞取好处的,也属于商业受贿行为,构成犯罪的也需要按商业受贿案件处理。(6)《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规定: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164条);(3)受贿罪(刑法第385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387条);(5)行贿罪(刑法第389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91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392条);(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393条)。
虽然教师因参与学校物品采购拿回扣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机会并不多,但在教师本职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中,却一直存在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礼物,这些行为可以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学和辅助的教学管理,虽然课堂教学不存在行贿受贿机会,但在辅助的教学管理方面,从学生学科成绩的考核评定,到学生干部的选拔任用,从各种推优评先,奖助学金的分配发放到学生入党参军,从推荐参加单招单考保送上大学到保送研究生,所有这些管理工作都涉及学生切身利益甚至影响学生前途,而教师的意见在这些活动中都起着主要作用甚至直接由教师决定结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这些事项、利益上,相关学生虽然也会努力争取,但行贿受贿、利益输送之事却极为罕见。但新世纪以来,学生、家长在上述诸多事项上为争取名额,争取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向老师送礼送钱的行为增多,一次少则几百上千,多则几千上万。在有些风气不正的中小学,学生当班干部甚至排座位都要给老师送礼,甚至老师明里暗里索要礼物的现象都不算稀奇。当前,教育主管部门为改变高等院校学生混日子、混文凭的严进宽出现状,要求大中专院校增加学生学习任务量,严格学习和考核管理,取消清考,坚决淘汰不合格学生。在这种背景下,少部分混日子的学生及其家长为考试过关顺利拿到毕业证,更有可能向相关老师送礼送钱。教师在教学管理中与学生、家长进行利益交换和输送的概率会更高。
教师在涉及学生利益的教学管理中收受学生和家长财物的行为一直被视为有损师德师风的违纪行为和不正之风,而较少受法律关注。实际上这是利用教学职务之便的受贿行为,不仅违反纪律,败坏师风师德,更严重的是破坏教师职务行为的廉洁秩序,在自己管理、决定的事项上制造不公平,污染、毒化青少年学子的成长环境,社会危害十分严重。鉴于教师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教师的这种受贿行为如果数额较大,完全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当然这不是商业受贿犯罪),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由于认识上的原因,对于教师的这种行为,即便数额较大,实践中也大多按违纪行为处理,很少诉诸司法。在2006年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修改扩大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之前,极少数公办教育机构教师实施的影响较大的此类行为,被按受贿罪认定处理,比如2003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教师收受300名学生财物放行考试案件。[4]这样的认定虽然不合法,但在当时也有一定合理性。在2006年之后,基于前文分析,这样的案件应该统一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笔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了2010至2019年全国教育机构工作人员被判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案件,在检索到的17个案件中,没有一起是教师利用教学管理的职务便利收受学生财物的案件。这显示近10年来,司法审判实践中极少甚至没有这类案件按照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案处理。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最高司法机关一直没有通过司法解释或其他司法文件明确这种行为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性质应当是主要原因。在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和环境下,如果没有法律或者司法文件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即使有这样的行为进入司法程序,法官一般也不会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青少年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地方,本来应该是一方净土,但近年来社会上的各种腐败风气逐渐传染给了学校,污染了学校的环境,严重危害了青少年学子的健康成长,亟需整顿治理。构建和维持良好的教学环境和秩序,不仅要靠高尚师风师德内在约束,还要靠校规校纪外在规制,更要靠法律来守住底线。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必然是教育治理方式的法治化,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是教育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重要甚至主要内容。因此,笔者建议最高司法机关适时出台司法解释,将教师在教学管理中收受学生或家长财物数额较大、为学生谋取利益的行为,明确纳入刑法第163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范围。惟有如此,才能发挥刑法对教师教学管理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调整功能,构建起来良好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管理秩序,提升学校的治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