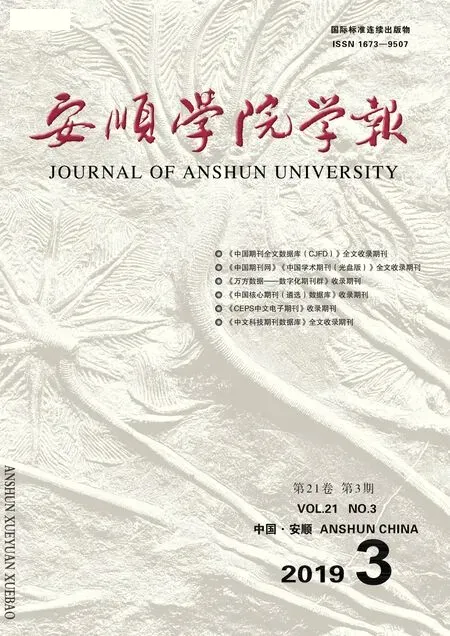张炎《词源》的词学价值及词学史意义
(河北大学文学院,河北 保定071000)
《词源》作为一部全面论述词学理论的专著,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蔡嵩云评价《词源》:“《漫志》追述调源,敷陈流派,亦未及作法。《词旨》广搜属对警句,而词说则甚简略,且不出《词源》范围。于词之各方面均有翔实记载者,莫如《词源》一书。”[1]39《词源》关于词体的论述十分全面,正如阮元在《四库未收书提要》所说:“下卷历论音谱、拍眼、制曲、句法、字面、虚字、清空、意趣、用事、咏物、节序、赋情、离情、令曲、杂论、五要十六篇,并足以见宋代乐府之制。”[2]《词源》下卷内容全面,逻辑严密,在书中张炎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理论建构意识,建构了自己以“雅正”为标准,以“清空”为最高审美理想的词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词学价值取向,对后世词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严守诗词之别
词本于燕乐,从源起就与音乐密切相关,乐体对于词章有着极为重要的规范作用。文人介入词曲创作,推动词体发展的同时,也给词体带来了词乐脱节、逐渐案头化的问题。首先,按谱填词给词乐结合带来困难。《宋史·乐志》:“国子丞王普言: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词。于是词律不相谐协,而与俗乐无异。”[3]3030又沈括《梦溪笔谈·音律》:“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4]31都指出了词律不相谐的事实,以及按谱填词带来的困难。沈义父坦言:“腔律岂必人人皆能。”[5]280张炎在《词源》序中云:“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词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6]255周邦彦以精通音律著称,而且提举大晟乐府多年,尚有未谐之句,可见词作协律之难。
其次,词乐失协,与文人作词的态度也有关系。自文人介入词体创作之后,就出现了“伶工之词与士大夫之词”的差别。词人伶工作词是为了应歌,因此重视词体的乐律特征,而文人士大夫是为了抒发情感,为了推尊词体,努力向诗歌靠拢,因此不甚重视,甚至忽视词体固有的音乐属性,在作词时尽量摆脱乐律的束缚,自由表达思想。
在词律失协,词作案头化的背景下,《词源》可谓“正本清源”之作。《词源》下卷开篇便说:“词以协音为先,音者何,谱是也。”[6]255表明张炎对于词之入乐的重视,也表明张炎严诗词之分的自觉意识。他追根溯源“古人按律制谱,以词定声,此正声依永律和声之遗意。”[6]255从源头为词作协律找根据,认为声律相协,自古而然,今日作词亦当如此。在分析各种乐曲特点之后,给出了协律的标准:“真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之语,斯为难矣。”[6]256
协律的具体要求是填词要注意拍眼,要做到“停声待拍”。“法曲大曲慢曲之次,引近辅之,皆定拍眼。盖一曲有一曲之谱,一均有一均之拍,若停声待拍,方合乐曲之节。”[6]257乐曲有法曲、大曲、慢曲以及引近的区别,乐曲样式的不同,谱子与均拍也各不相同,填词要注意曲式,灵活运用拍眼。然后总结道:“曲之大小,皆合均声,岂得无拍。歌者或敛袖,或掩扇,殊亦可硒。唱曲苟不按拍,取气决是不匀,必无节奏,是非习于音者,不知也。”[6]257指出按拍唱曲的重要性。在张炎看来协律是词有别于诗的首要特点,他重视词体的乐律特征,提倡“依谱填词”。
张炎强调作词协律,并不意味着他对词章结构与文本的忽视。张炎对于词作文本的要求也具体而微的,第四则到第七则,张炎详细论述了关于词章文本的创作方法以及具体要求。其意有五:一是词作结构的安排,词作结构尤其要注意换头处。二是词作完成后,要反复修改。三是对词作句法的讲求,要平妥精粹。四是要求字面,强调练字酌句,提倡“本色语”,反对“生硬字”,主张学习唐诗字面。五是要求词中虚字“用之得其所”。
其实,张炎对于词章的要求都是为配合词作协律可歌的,他强调反复修改词作是因为“倘急于脱稿,倦事修改,岂能无病,不惟不能全美,抑且未协音声。”[6]258求句法字面是因为“读之使人击节”“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6]258讲求虚字是因为:“若堆叠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乎。”[6]259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炎“词以协音为先”的词学思想,同时显示出张炎词学思想的融通,他吸收“士大夫之词”与“伶工之词”两派各自的长处,结合乐律谈词章,联系词章谈乐律,这是张炎对于词体的乐律与词章的双重要求,这也是张炎为区分诗、词二者做出的努力,更是为维护词体独立性作出的贡献。
此外,关于词体乐律与文本的矛盾冲突,终有宋一代从未停止,时而激烈,时而缓和,张炎《词源》中的论述也有调和二者矛盾的作用,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和导向作用。
二、标举“骚雅”
晚唐五代花间词与尊前词婉媚柔靡的风格对宋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词体香艳、柔媚、婉约的传统风格。这一风尚随着词体的发展与流行,最终导致词作流于软媚浮艳、意趣不高、词格尘下。文人对于此种词风多有不满,试图转变词坛不良风气。晁补之《词评》注意词作的意境,李清照《词论》强调词作的文雅,这些均可视为南宋“雅正”词派的先声。南宋时期,披风抹月的词风与国事日非、偏安一隅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南宋诸贤高举“雅正”的大纛,阐明“雅正”思想,用以指导创作,试图重振词坛。事实上,南宋词论中的雅正说, 正是建立在对香艳词风的批评上。
词之雅化是两宋词发展的趋向, 而词论中的“雅正说”则是南宋词论的中心命题。张炎在“古音之寥寥,雅词之落落”的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雅正说”。《词源》开篇便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6]255提出雅词的源头,《词源》一书就以此为基础,倡导词作的雅正。雅正的要求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雅词须先合律;二是雅词要音律词章双美。合律与词章是张炎“雅正”理论的两翼,“雅正”是张炎词论的核心。《词源》围绕这一核心,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的同时,还通过对当时几位词人作品的评述,重申“雅正”的作词标准,帮助人们理解“雅正”理论的内涵。张炎的雅正说, 毫无疑问地以白石词为皈依。张炎对于姜夔的推尊可谓不余遗力,无以复加。朱崇才在《词话史》中解释这个现象:“姜夔对于张炎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举为范例的词作家,而且还是一个标准,一个‘雅正’的标本。如果说,‘雅正’理论,是历代词话用于号召词坛,引导众词家的一面大旗,那么,在张炎看来,姜夔就是当之无愧的旗手。”[7]154
在“雅正”之外,张炎另外拈出“骚雅”二字,这是张炎本人的独创。“骚雅”二字分而观之,“骚”可解为比兴寄托的“诗骚传统”,这是对于词体的思想内容作出的规定,“雅”则指的是字面文雅,要求词作无侧艳软媚之病,亦无豪迈粗疏之习。在书中张炎高度评价姜夔词作“不惟清空,又且骚雅”[6]259。书中列举的姜夔词不仅语言优美,词律婉转,而且别有寄托,如《暗香》寄托身世之感,《疏影》抒发家国之悲,《扬州慢》效仿《黍离》感慨江淮之乱,所举其他词作亦无不渗透着家国之思,身世之感,称“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也”[6]261。称赞陆淞《瑞鹤仙》、辛弃疾《祝英台近》“皆景中带情,而有骚雅”[6]264陆辛二词也是有所寄托。由此观之,“骚雅”要求词作既要保持词体表意含蓄婉转的传统特色,又要表达深刻的内容和表现高远的志趣。
张炎承认为词的抒情功能强于诗歌,同时对于词中的情感也提出自己的要求:“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6]263又“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6]264强调词体抒情要节制,不可泛滥,要有乐府之遗意,不可近于郑卫,“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6]266词作“雅正”是与缠令等民间俗乐的分别,是张炎明雅俗之别的努力,显示出张炎对于词体的推尊。
张炎雅正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并非只重视艺术形式的雅致, 更重要的是针对淫艳词风而提倡词的情感内容的醇雅。抵制软媚浮艳的词风,力保词体的纯洁性与独立性,使得张炎的雅正说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起到了推尊词体的作用。这是以往雅正说所不具备的,也是张炎对于词学理论作出的独特贡献。
三、首倡“清空”
张炎于“婉约”“豪放”之外,另立“清空”一体,这是宋词雅化的必然产物。张炎在书中并没有反对“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只是对一些不符合其作词规范的词作进行了批评。他对于二派的“清空”之作,都不乏溢美之辞,由此可以看出,张炎所说的“清空”既是一种作词方法,又是一种风格境界,是词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的词体审美规范,于后世词学具有开创之功。
通过张炎的举例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清空”不仅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审美境界。张炎认为苏轼的《水调歌头》《洞仙歌》、王安石的《桂枝香》、姜夔的《暗香》《疏影》“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也”[6]261。三人的风格绝不相同,但却都达到了“清空”。
张炎在《词源》中指出:“词要清空,不要质实。”直接标举“清空”,反对“质实”,明确提出自己的词学审美理想。之后的论述包括对“清空”的阐释,也包括词作达到清空的途径。如下:
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意。[6]260
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6]261
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要须收纵联密,用事合题。一段意思,全在结句,斯为绝妙。[6]261
这些论述指出了“清空”词的创作方法:一是词的意趣要新,不落前人窠臼;二是使事用典自然,为我所用,不被事所累;三是咏物贴切妥当,别出心裁;四是情景交融,言有尽而意无穷,意有尽而情不止。
《词源》云:“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此清空质实之说”[6]259。显然,张炎指出清空与质实的两种表现。“清空”是潇洒飘逸,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审美境界,如天空中野逸的云彩,来去无踪。正与严羽在《沧浪诗话》所说“羚羊挂角,无迹可寻”[8]283的意境相同。“凝涩晦昧”是词作质实的表现,质实指过分拘泥现实,堆砌词语,导致词作意义不明,各个物象间没有联系。经过二者的比较,意义自明,优劣自现。
沈祥龙《论词随笔》云:“清者,不染尘埃之谓;空者,不著色相之谓。清则丽,空则灵,如月之曙,如气之秋。”[9]4054此说以“清丽空灵”解释“清空”,可谓精到。司空图论诗讲究“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严羽论诗强调“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相。”[8]23二者均与张炎所说“清空”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大杰说:“清空是张炎提出的词的最高境界……他所说的清空就是空灵神韵,同严羽讨论的意见相同。”[10]690夏承焘认为清空:“谓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11]16这些论述显示出诗词理论的合流同构,同时也说明张炎词论取径的广泛。
“清空”是“清丽空灵”的审美境界,要求词作意趣要新,用事妥帖精当,对于事物的描写要取其神理,不着色相,情景交融,表现一种疏朗含蓄的美感。朱崇才认为:“张炎提出了‘清空’这一概念,并加以简要界说,把词学从风格论拓展至境界论,是词学研究史上的一大飞跃。”[7]151张炎的“清空”不单单是风格,更是一种诗歌审美理想与审美境界,这是张炎在词论史上的又一大贡献。
四、《词源》的词学史意义
《词源》成书较晚,在前人词话、词论的基础上,书中内容涉及到了词体创作的方方面面,提倡音律与词章双美,尊雅正,尚清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词话丛编》辑录古今词话,其中后世词话对于《词源》的引用与发挥达346处之多,可见张炎及其《词源》在后世的影响之深广。《词源》的词学史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二是对后人的启示与影响。
《词源》对南宋另外两部词话《碧鸡漫志》与《乐府指迷》的继承与超越。首先,关于词体协律,《词源》明显具有进步性。三者无疑都受到了以李清照为代表的“本色论”“别是一家”的影响,但三者的继承却不相同。张炎是最好的继承者,坚持“别是一家”,严守诗词之别;王灼与之不同,更加重视词的文学性;沈义父对于协律问题则较为变通。张炎强调作词先须协律,然后才要求词章及内容。在当时词体衰落,渐趋案头化的背景下,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王灼则不然,他一方面尊重词体的音乐性,另一方面却高扬词体的文学性,把词当作单纯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他以风格论为核心,引入诗学批评之风骨、气格、品第流派等观念。这种批评方式混淆了诗词的界限,而在具体的词人词作批评中, 他也很少提及音乐方面的问题。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论及协律问题指出,“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细较之下,也能发现与《词源》之说的差别,沈义父的“律”指的是词的字声格律,这是针对词作案头化的现实作出的妥协。沈义父的协律只是出于强调音乐本位的词学观念,区分诗词的体性差异,这在《乐府指迷》中不是重点。这明显是受到诗法的影响,表明沈义父同样是将词体看成文学作品,从而迎合词体案头化、文学化的词学观念。
其次,“雅正说”。在这方面《词源》同样具有“后出转精”的优势。张炎的“雅正”不仅涉及词体的外在艺术形式,而且关注词体的内在思想内容,相比另外两部词话显得严谨全面。“雅正”是张炎词学理论的核心,讲求音律与词章是为了达到词体的“雅正”,在“雅正”的基础上,提出“清空”的审美标准。另外拈出的“骚雅”更是将“雅正”理论进行升华,将其推向更高的层次。在另外两部词论中,对于“雅正”则不够重视,“雅正说”在其中并不处于核心位置,仅仅是王灼与沈义父词学理论的一个方面。王灼提出“中正则雅”的概念,是将“雅”定位在音律方面的,认为词的音乐美是建构“雅”的条件之一。可惜王灼对于词体的音乐性关注不多,并未作深入论述。张炎于此则多有发挥,直接将协律看作是词体雅正的条件之一。《乐府指迷》论词围绕“四标准”展开,“雅正”只是其中之一,“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于缠令之体”。仅从词作字面出发,要求词作语言典雅,跟《词源》相比无疑落了下乘。《词源》的“雅正说”具有现实针对性,对于词坛软媚浮靡的词风是有救弊作用的。《碧鸡漫志》与《乐府指迷》的“雅正”说,多限于文辞的精美雅洁,对词的思想内容则没有应有的关注,他们所称道的雅词,情思旖旎,词风柔媚,不乏描写风花雪月与歌咏太平之作,黄庭坚所谓“狎邪之大雅”是也。
《词源》成书之时就广受关注,元代前期,钱良佑、陆文圭、邓牧、仇远等人为张炎的词集与《词源》写了一些序、跋、题记,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词学观点,皆以姜张为宗,以雅正清空为尚,这些论述实际是对张炎词学理论的发挥与鼓吹。对于张炎词学理论发挥最为得力的当属陆辅之的《词旨》,其说云:“凡观词须先识古今体制雅俗。脱出宿生陈腐气,然后知此语,咀嚼有味”。又:“《词源》云‘清空’二字,亦一生受用不尽,指迷之妙,尽在是矣。”[12]303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张炎词学理论在元代的延续。
张炎的词体意识十分鲜明,以“协乐”严诗词之别,以“雅正”明词曲之别,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作词协律,为后世词论家尊奉。宋词音谱虽已失传,但后世对词作协律的追求、对词的唱法的探寻却从未停止。明代,张綖《诗余图谱》、程明善《啸余谱》均标明平仄,以求协律可歌。清代对于词律的探究,远超以前,成果蔚为大观。清代三大词派,浙西、阳羡、常州,其理论主张不同,但对于协律的要求则十分一致。这些明清词家、词论家无疑都受到了张炎“词以协律为先”的影响。其次,《词源》提倡“雅正”,为后世推尊词体提供了理论支撑。清代三大词派,不约而同地提出自己推尊词体的主张,阳羡派陈维崧要求词作“存经存史”,常州派张惠言要求词作“比兴寄托”,这两派是从词作的思想内容方面推尊词体,从中不难看出张炎要求词体“骚雅”,具有“汉魏乐府之遗意”的影子。而浙西词派对于“雅正”的继承,则偏重形式,流于字面,注重“字琢句炼,归于醇雅”,不免有些偏狭。最后,张炎“清空”的审美理想成为浙西词派的最高追求。在朱彝尊的影响下,以姜、张为宗成为浙西词派的一面大旗,甚至形成了“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的大一统局面。
谢桃坊在《中国词学史》中评价《词源》的价值:“张炎是第一个以雅正清空作为艺术鉴赏的原型与评价作品的根据,以雅正清空的作品作为词的最高范本,而在讲词法和评论作家作品时将其观念具体化了,使其观念有一定的深度,这是在词学理论上的重大建树”[13]140。江顺诒在《词学集成》中,对《词源》做出总结概括之后说:“后之论词与作者皆不能出词源所论之范围。”[14]3280二位先生的论述分别道出了《词源》的词学价值以及词学史意义。
结 语
张炎《词源》作为宋代三大词话之一,自有其价值所在:一是他通过辨体,区分诗、词两体的区别,强调“词之本色”,维护词体独立性;二是提倡“骚雅”,对词的内容与风格提出明确的要求;三是标举“清空”,为词坛树立新的审美风尚。这些理论的提出有救当时词坛之弊的作用,而且在理论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对以前的词论有所超越。不仅如此,《词源》对于后世词坛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明、清三代词论无不受其灌溉。一方面,“词以协律为先”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对于词体音乐属性的认识逐渐加深。另一方面,张炎的“骚雅”理论,为后世的推尊词体提供了理论借鉴。“清空”的审美理想,风靡有清一代词坛,其影响直至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