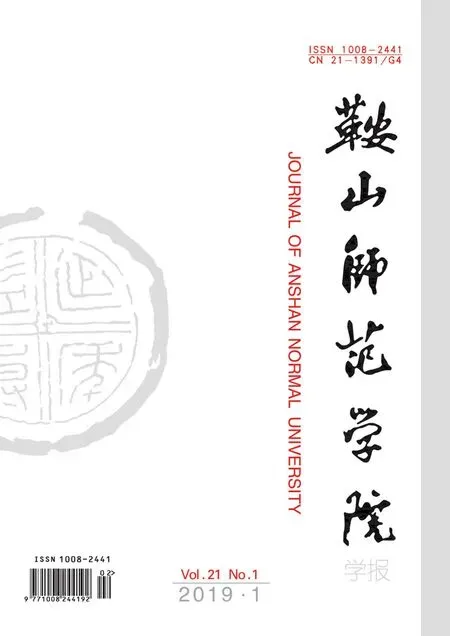自我与调和——志贺文学的创作轨迹
陈秀敏
(鞍山师范学院 文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一、志贺文学创作的背景
日本江户幕府(1603—1867)时期,为巩固幕府集权的封建统治,禁止基督教在岛国流传,1633—1639年,江户幕府共下达了五次《锁国令》,在外交、对外交通和国际贸易方面均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日本人出国,日本对外交通与贸易的门户,仅限于长崎一港,外国人的居住地也仅限定于长崎。实行锁国政策后,日本主要与中国、荷兰、朝鲜有往来,这导致日本人国际视野狭窄,养成了内涵狭窄的“岛国根性”,日本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
1852年11月24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培利(1794—1858)带着美国总统致日本幕府将军的亲笔信,率领舰队从美国弗吉尼亚州大西洋畔的诺福克港口出发,经南非的开普敦、新加坡、中国香港、上海、冲绳、小笠原诸岛,1853年7月8日,开进了三浦半岛东南部的浦贺港,武力强迫江户幕府采取开国政策。日本表态翌年做出答复。1854年2月13日,培利带领七艘军舰来到了江户湾(东京湾),3月31日逼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由此,日本的锁国政策开始解冻。
1868年,日本成功发动了一场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明治维新。国门开放,西潮涌入。明治维新的最高目标就是实现以西方民主为核心的近代化,鼓吹个人觉醒与个人确立。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无不积极追求精神的解放,随着合理个人主义的日趋成熟,他们看清了个人觉醒的价值。争个人自由,便是为群体争自由;争个人的人格,便是为群体争人格,日本明治维新后的一大批个人觉醒者认定了这个真理。
就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日本近代文坛大集团型的文学流派——白桦派于1910年4月赫然诞生。白桦派作家出生于特权阶层,但他们看淡物质,礼赞精神,崇尚“平等个人主义”,“白桦派在提出把富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活出自己’作为人生的第一要旨的同时,也主张他人要同样如此。也就是说,白桦派的个人主义苗根并非深扎在那种以‘于己有益,于人有殃’的损人利己为内涵的腐壤之中”。[1]个人觉醒了的白桦派作家倡扬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他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君临文坛的以“无理想,无解决”为宗旨的自然主义文学,向灰暗的文学世界射进了清亮的阳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白桦派作家中强烈贯彻自我、活出人生纯粹的志贺直哉(1883—1971)对日本近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非比寻常,这已是不争的史实。志贺出生在明治维新后的一个特权阶层家庭里,是家中的独苗。祖父祖母出于“传宗接代,保住门庭”这一家族观念,让孙子从幼年起就一直生活在自己身边,倍加溺爱,养成了志贺以异常任性为特色的自我意识。志贺少年失恃,父亲续弦,此事构成了志贺与父亲长年不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志贺就读特权阶级子弟的贵族学校“学习院”时,结识了文学青年武者小路实笃等同学,他生来的文学气质受到武者小路的良性刺激后,历经权衡,最后决定坚守个性解放理念,做自己愿做的事,一生笃志文学。志贺这位明治维新后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其人生观与崇尚实业实利的父亲完全相反,他甘于献身文学这一门“虚业虚利”,视精神为利益。再加之谴责日本公害史的原点——“足尾铜山矿毒事件”、贯彻自由恋爱婚姻自主等一系列个性化举动,导致父子间的意识冲突愈演愈烈,在很长时间内几乎失去了和解的希望。
正如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富兰克林所言:“留心你的决定性格,性格可以决定命运。”正因为如此,志贺固守自我至上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和文学创作特色。
二、志贺文学创作的轨迹
志贺是创作“调和型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大家,他的文学生涯分为四期。1904年5月,二十一周岁的志贺完成了甘美的童话《菜花与小姑娘》,象征志贺的文学生涯第一期开幕,1914年4月发表的《偷小孩的故事》,宣告他的文学生涯第一期闭幕。
这一时期的志贺,与父亲正处于“父子相克”阶段,为确立个性,精神苦闷的他告别了宗教家内村鉴三,放弃了基督教信仰。是故,志贺第一期作品中虚构内容较多,主旨在于抨击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如《混浊的头脑》);表现父子冲突(如《大津顺吉》《清兵卫与葫芦》);描写不良情绪导致的神经衰弱症在作品中的具体反应(如《鸟尾的疾病》《剃刀》《克罗迪斯日记》《范某的犯罪》《偷小孩的故事》等),这是第一期作品的几大主题。故此,从志贺的心旅历程看,这一时期的志贺精神明显处于“不调和的时代”,他的精神异常苦闷。“最苦闷的是那些脑子最发达的人”[2]。此间,志贺反父权斗争十分激烈,所以,这一时期的志贺被称作“战斗之人”。同时应客观看到,个人主义强调过度,也存在明显弊端。“夏目漱石认为,日本由西方引进的个人主义,使人赢得了个人自由与独立,但其副作用是使人心走向极端利己。”[3]《范某的犯罪》等作品就反映出个人主义的副作用问题。
志贺的创作活动带有“间歇泉”特色。自《偷小孩的故事》之后,志贺停笔三载,进入“沉默的时代”,也是“充电的时代”。1917年5月号《白桦》上刊载了志贺追求精神调和的心境小说《在城崎》,宣布志贺的第二期创作活动开幕。受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9)思想与“祖母情结”因素影响,志贺在心境上产生了与父亲和解的念头。《在城崎》的问世,就是深望和解的好兆头。1917年8月30日,三十四周岁的志贺与六十四周岁的父亲实现了彻底和解,父子间多年的精神死疙瘩终于解开了,志贺的心境也由此前的“不调和”进入了“调和”状态。1929年1月,《雪地远足》问世,宣布志贺的第二期创作活动落幕。志贺第二期创作活动成果丰硕,继《在城崎》之后,相继发表了代表作《佐佐木的故事》《小品五篇》《好人夫妇》《赤西蛎太》《和解》《鹄沼行》《十一月三日午后的事情》《学徒的神仙》《一个男人·姐姐的死》《雪日》《篝火》《赤城某日》《真鹤》《雨蛙》《护城河畔的住宅》《山科的记忆》等系列作品,并且完成了《邦子》《暗夜行路》的绝大部分。这些作品或者表现了志贺的“调和”心境;或者表现了志贺反对战争的一怀正气;或者表现了志贺对少年思春期审美心态的充分肯定;或者表现了志贺对合理的个人主义的赞同;或者表现了志贺艰难的精神炼狱景状;或者表现了志贺特色的“为了文学的恋爱”的价值;或者表现了志贺的自我主张与忏悔理念的关系。
志贺是一位全靠直感进行创作的作家,他没有发表过系统的文学理论文章。1928年7月号《改造》上发表的《创作余谈》是志贺的代表性文学创作随笔,凡是研究志贺文学的学者,都必须精读这篇重要的随笔。第二期是志贺文学生涯的高峰,“调和”意识纵贯了这一时期,鉴于此,志贺被界定为“和解之人”。
1929年至1945年8月是志贺文笔生涯的第三期。这一期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志贺为坚守人格,拒绝阿世,几乎等于“文士废业”了,只是1936年11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万历赤绘》。珍视文人风骨,不对非正义国家权势俯首帖耳,这正是志贺人格的可贵之处。
此间,志贺值得庆贺的大事,即荣膺“近代文学史上的金字塔”之称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终于完竣。1938年6月,改造社出齐了九卷本《志贺直哉全集》,而其另一篇文学创作随笔《续创作余谈》附于书后。这一时期,志贺与无产阶级文学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有过实质性的文学交流,出于人道主义正义精神,志贺对小林多喜二“不自然的死”表示由衷哀悼。文笔生涯第三期的志贺被称作“眺望之人”,他眺望的目标是战争阴霾尽早消散,和平的曙光尽快照临。
二战结束后,志贺的创作活动进入第四期。在这一期,志贺对日本文学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创作了“日本的伤痕文学”——《灰色的月亮》。日本发动一场残酷的非正义战争,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导致战败国的日本国民陷入空前虚脱状态。军国主义肆虐时代,在国家权力的高压下,志贺被迫罢笔。可喜的是,战争硝烟飘散,人民获得了思想自由,作家们开始摆脱精神禁锢,自主地向战后混乱的社会宣泄战争感想与愤怒,志贺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苦涩心情终于在《灰色的月亮》中流露出来。
志贺第四期创作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归纳表达他的山水情怀与“小动物情结”。志贺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虔诚的环保主义者。1901年,日本历史上第一个环境污染事件“足尾铜山矿毒事件”上升为社会问题后,志贺对因此受害的农民致以由衷的同情,并激烈抨击唯利是图、蹂躏庶民生命的资本家。
志贺酷爱小动物并反映在作品中,形成了志贺整体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志贺从小动物身上感受到人生启悟,柔化了他那显得偏激的自我至上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志贺文学与自然的亲密感。自我至上的志贺与自然开初是“人定胜天”的主客体对立关系,随着志贺阅历的深化与思维的成熟,渐次开始归顺自然,进而构筑起一个恬静调和的“天人合一”的精神世界。志贺对动物的关怀还表现在他对西班牙血腥的斗牛运动持强烈反对态度,从而彰显人类的道德观念与人道主义精神。毋庸置疑,志贺的这种观念与精神富有明显的超前性。
志贺第四期创作中,主流文章是对往事的缠绵回顾,带有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淡韵,这一时期的志贺被界定为“回想之人”。
还应指出,志贺在东京帝国大学专攻英文,其厚实的英文功底,为他接触诸多岛国之外的新文学与新思想打下坚实的基础。托尔斯泰、梅特林克、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纪德等都对志贺的文学创作产生过明显的积极影响。“一流作家有别人无法企及的独自领域。志贺直哉的这一领域是他的短篇小说。他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本领,已成定论了[4]。”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志贺受契诃夫、莫泊桑的启发是有据可查的。
三、志贺文学精神的实质
丹麦文学史家、评论家勃兰兑斯(1842—1927)云:“席勒在一封致歌德信中说过,对诗人和艺术家不能不要求两件事,一是他应超乎现实事物之上,其次他应该停留在感性事物之中[5]”。这两件事志贺都做到了。志贺得益于殷实的家道,没有物质生活的压力,他可以不劳瘁于衣食住行,经济基础与文学才气二者良性汇合,造就了日本的“小说之神”。情绪型性格的志贺视“愉快”为善,视“不快”为恶。为求“善”避“恶”,志贺的生活往往“超乎现实事物之上”,他跟随自己的感觉走,时常离别稠人广众,俨如闲云野鹤,放浪形骸,漂泊列岛,亲近自然,一生徙居二十余次。调整出良好的情绪,便为他酝酿文思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之上,志贺活用自己的艺术禀赋,可以“停留在感性事物之中”,离开功利打算,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待对象物,因而写出的作品富于艺术性。这就像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表述的那样,人摆脱了物质需要的束缚,进入自由的精神世界,才能享受“自由的欣赏”,即享受“物质以上的盈余”(过剩)美感。席勒认为,“狮子到了不为饥饿所迫,无须和其他野兽搏斗时,它的闲着不用的精力就替自己开辟了一个对象,它使雄壮的吼声响彻沙漠,它的旺盛的精力就在这无目的的显示中得到了享受”[6]。这就是席勒的“过剩精力”的艺术“自由游戏”说。在这种生命绰有余裕前提下诞生的作品,尤其富于美感与艺术性。通俗说来,即所谓“科学是忙出来的,文学是闲出来的”。深得鲁迅先生赞许的日本近代文艺思想家、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在其力作《苦闷的象征》中写道:
我说“人唯有在游玩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的意思,就是将人们专由自己内心的要求而动,不受着外底强制的自由的创造生活,指为游戏而言……想一想罢,在人间,能有比自己表现的创造生活还要高贵的生活吗?没有创造的地方就没有进化……
文艺是纯然的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7]。
不言而喻,精神贵族志贺的文学生涯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席勒与厨川白村的上述理论。志贺不必靠赚稿费养家糊口,从文不为沽名钓誉,他不受外界的强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己的自由意志。是故,志贺被芥川龙之介羡慕为“幸福的作家”。白桦派其他作家亦然。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志贺“专由自己内心的要求而动”的创作活动却意外地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物质收入。举其一例,譬如,“1928年7月,《现代日本文学全集》第二十五卷《志贺直哉集》刊行。他用这笔稿费,买下奈良上高畑的土地,新居建筑费用的大半也出自稿酬”。[8]
志贺以自我为中心,他的文学创作规模较窄,对社会的关心显得不足,这确实是志贺文学的一大特点。对此,芥川龙之介却持有如下观点:
志贺直哉的作品首先是活出精彩人生的作家之作品。精彩?所谓活出人生的精彩,首先该是像神那样活着吧?也许志贺直哉不像地上的神那样活着。但至少他确实活得清洁。(这是第二个美德)当然,我说的“清洁”,并非意指一个劲儿用肥皂洗,而是指“道德上的清洁”。这样一来,志贺的作品或许显得内容狭窄,实则非也,反倒很广阔。为何说很广阔?因为我们的精神生活被附加道德属性之后,必然要比未被附加之时广阔得多。(不言自明,所谓“附加道德属性”,并非意指教训。除了物质性痛苦之后,痛苦大多源于道德属性)。[9]
芥川龙之介独具慧眼,他认为,志贺直哉的作品因为具备“道德上的清洁”,作品规模反倒显得广阔,然而,我们再看看那些在创作道路上改弦更张舍弃自我、以国家为中心的日本作家又是如何?譬如,佐藤春夫(1892—1964)被郁达夫界定为“日本的娼妇”[10],在日中交战的紧要关头,著有劣作《亚细亚之子》(载《日本评论》1938年3月号),肆意丑化旧友郭沫若和郁达夫的形象,大肆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作家林房雄(1903—1975)沦为名副其实的军国主义者,而且死不悔改,否定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抛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1964)、《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1965)等臭名远扬的论著。
事实证明,古往今来,凡随波逐流违心高唱赞歌为政治权势涂脂抹粉的文学,从来就没有好文学。作家的真价在忠于人格,在于独立思考和不合时宜的发言,唯此才能创作出优秀文学作品。文学的价值在于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发掘,鲁迅先生是一个独立精神极强的一代文学大师,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发表过这样的精辟见解:
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唯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非吃麻醉药。[11]
按照白桦派的文学观,文学是个性自然流露的产物,无个性的文学是无特色的文学,无特色的文学绝非好文学。既然是个性,就不肯“遵命”。这正如反对“遵命文学”的鲁迅先生所云: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感人了。[12]
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与白桦派不谋而合。譬如,有岛武郎就提出:艺术是“本能生活”的流露,这里的所谓的“本能生活”,是指积极主动的个性活动。志贺与武者小路等,也都自觉地遵循这一创作法则。
志贺直哉是一个活出清洁人生的作家。这一点从他的作品的道德性语气里,即可窥见一斑[13]。志贺分外讲究精神卫生,精神卫生代表一种习惯,一种追求。他的精神与眼睛不能容忍物心两面的肮脏。一个文人若能容忍自己的精神肮脏,他就能容忍自己为文的不地道。志贺认为,自己要么“我笔写我真心”;要么干脆罢笔废业,宁肯保持沉默,也不曲笔阿世。志贺为文态度之恳真,足以令那些工于作假的“两重人格”者感到十分难堪。“与别的艺术形式一样,文学也是心灵与心灵互相交流的一种媒介”[14]。是故,志贺的代表作历经漫长时光风浪的吹打,最终没有变成一堆废纸,没有化作“文学泡沫”与“明日黄花”,至今依然能够放出光彩来。
志贺的作品中,闪耀着精神解放的光彩,流淌着真诚的爱情、亲情与友情,强调人格尊严,是志贺的终生课题。披阅志贺作品,不必怀疑字里行间会隐藏着言不由衷的欺瞒。志贺的文学精神与惠特曼名诗《再见》的精髓可谓一致:
同志,这不是书本,(Comrade,this is no book,)
谁接触它,就是接触一个人。(Who touches this touches a man.)
志贺文学活动的最高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不断调动智慧,调节思维,追求个人的精神和谐(调和)。不言而喻,唯有个人达到真正的精神和谐,才能实现货真价实的社会和谐,显而易见,志贺文学精神的真价就存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