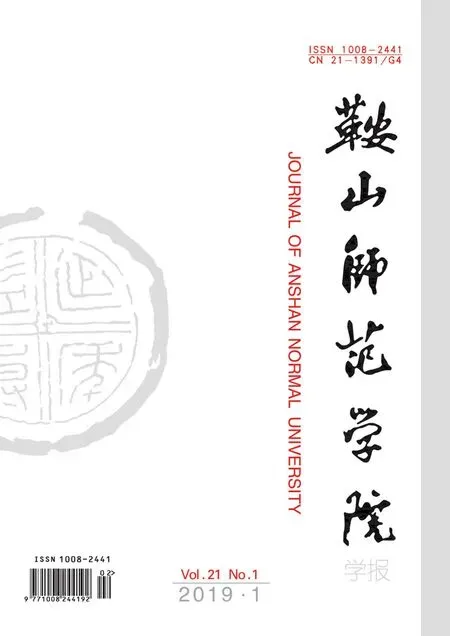《洗冤集录》的法律思想辨析
姜奎昊
(辽宁大学 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一、宋慈及《洗冤集录》
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年少时师从朱熹的弟子吴雉,深受朱熹理学的影响。后进入太学深造,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了仕途。宋慈先后任过福建长汀知、南剑州通判、提点广东刑狱、知常州军事、提点江西刑狱兼知赣州、广东经略安抚使等官职[1],居官清廉刚正,体恤民情,不畏权豪,决事果断,在其担任常州知州的时候,开始撰写《洗冤集录》。在洗冤集录序中宋慈写道:“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使得参验互考,如医师讨论古法,脉络表里先已洞澈,一旦按此以施针砭,发无不中。则其洗冤泽物,当与起死回生同一功用矣。”可见《洗冤集录》是宋慈根据自己一生的刑事司法检验经验和实践,参考前人的知识成果所著,用以指导刑事司法检验、官员检验行为,其问世后“官司检验奉为金科玉律”,备受推崇。《洗冤集录》历史地位极高,是中国现存第一部系统论述古代司法检验之专著,也是我国古代至今保存最完整的第一部法医学著作,后世法医著作大多以此为蓝本[2],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流传海外。
《洗冤集录》共五卷五十三目,约七万字。录前有序,卷一包括条令、检覆总说上下、疑难杂说上目;卷二至卷五分别记载了各种伤亡死因的检验方法[3]。条令目中所辑条文都是对检验官员规定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其余各目内容较为广杂,但大致可分三方面:一是检验官员应有的态度和原则,二是各种尸伤的检验和区分方法,三是保辜和各种救急处理。内容广泛又具有侧重点,基本上涉及当时司法检验的各方面。
二、“慎刑恤狱”的法律思想
“慎刑”主义法律思想来源于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强调统治阶级以“慎罚”为手段达到“明德”的统治效果,而“慎罚”的具体含义是在司法审判中主张用刑宽缓适中,而非一味使用酷刑强制其服从[4],这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体现。
在《洗冤集录》序中,宋慈便表明了自己的审理检验狱案的态度。他写道:“慈四叨臬寄,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若灼然知其为欺,则亟与驳下;或疑信未决,必反复深思,惟恐率然而行,死者虚被涝漉。”在宋慈的眼里,狱案需审之又审,不可怠慢,在审理案件、探查案情的过程中更要反复深思,勿率然而行。宋慈开篇这种态度奠定了《洗冤集录》的内涵基调——“慎刑恤狱”,而这里的“慎刑恤狱”不仅仅只是用刑宽缓的概念,其更多的是强调“决狱谨慎”的意思。
在全文中,“慎刑恤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规定官员检验行为的法律方面
在序中,宋慈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屈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法中所以通差今佐理掾者,谨之至也。”这表明大辟(死刑案件)重于狱事(刑事案件),初情(查清初始案情)是大辟中的关键,而检验是初情中最为重要的。序以此句为首,足可见检验对于掌管刑事的官员的重要性,要谨慎之至。在卷一第一目条令当中,第一句便列出官员现场检验存在的以失职论处的情形,如“诸尸应验而不验;初复同。或受差过两时不发;遇夜不计,下条准此;或不亲临视;或不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当,谓以非理死为病死,因头伤为胁伤之类。各以违制论。”同时按失职论处的还有如:“诸县承他处官司请官验尸,有官可那而称阙;若阙官而不具事因申牒;或探伺牒至而托故在假被免者,各以违制论。”对官员贪赃枉法的处罚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枉法二十匹,无禄者二十五匹,绞。若罪至流及不枉法赃五十匹,配本城。”对于鉴定错误的课罪标准:“其事状难明定 而失当者,杖一百。吏人、行人一等科罪。”以及过时不验、不接受验尸任务、泄露检验材料等行为的罪罚情形:“诸验尸,报到过两时不请官者;请官违法或受请违法而不言;或牒至应受而不受;或初复检官吏、行人相见及漏露所验事状者,各杖一百。若验讫,不当日内申所属者,准此。”另外,对于检验过程中程序上的法律规定在条令之中也有涉及,如:“诸初、复检尸格目,提点刑狱司依式印造。每副初、复各三纸,以《千字文》为号凿定,给下州县。遇检验,即以三纸先从州县填讫,付被差官。候检验讫,从实填写。一申州县,一付被害之家,无,即缴回本司。一具日时字号入急递,径申本司点检。遇有第三次后检验,准此。”这一段写道初验、复验验尸报告书的格式、内容等要求。无论是官员作出错误鉴定,推脱躲避检验任务,或是贪赃枉法规定将他们以失职、杖刑、绞刑、流配等定罪,都体现了对检验官员的法律要求。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条令中不仅规定了对官员检验行为的法律要求,还强调了官员以外的百姓在案件中诬告他人所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如“诸以毒物自服,或与人服而诬告人罪,不至死者,配千里。若服毒人已死,而知情诬告人者,并许人捕捉,赏钱五十贯。”“诸尸虽经验而系妄指他尸告论,致官司信凭推鞠,依诬告法。即亲属至死所妄认者,杖八十。被诬人在禁致死者,加三等。”以上“慎刑恤狱”的法律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对官员检验行为的严格要求上,通过以法律法令威慑控制官员行为,使其认识到刑狱之事切不可随意妄为,同时也侧面反映了宋代法律制度的发达,立法与司法不宥于旧律,法律思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宋史·刑法志一》中写道:“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恕,狱有小疑,复奏辄得减宥”,这便是“立法严、用法恕”[5]的价值体现。
(二)对(现场)检验的要求方面
检复总说上目首段即描写了官员检验的禁止行为,“凡验官,多是差厅子、虞候,或以亲随作公人、家人各目前去,追集邻人保伍,呼为先牌,打路排保、打草踏路、先驰看尸之类,皆是搔扰乡众,此害最深,切须戒忌。”强调了官员要重视检验,不能摆官架子,惊动乡里,乱闯尸场,预做手脚。另有一段:“凡到检所,未要自向前,且于上风处坐定,略唤死人骨属或地主、湖南有地主,他处无。竞主,审问事因了,点数干系人及邻保,应是合于检状着字人。齐足,先令扎下硬四至,始同人吏向前看验。”这段话描述了在案发现场,官员先不要急于直接验看尸体,应先了解案情,召集并审问案件相关人员后再行检验。还有“其余杀伤、病患诸般非理死人,扎四至了,但令扛明净处”等对现场检验要求方面的语句。从字里行间不难体会到宋慈对于官员检验要求的严格,同时也对“慎刑恤狱”法律思想进行了又一层面的表达,即检验绝非草草了事一环,这一环节贯穿案件侦查的始终,对现场的检验更是重中之重,对其要求越高,就越能接近案件真相,从而不会冤枉任何无罪之人,也不会使任何有罪之人逍遥法外。“慎刑恤狱”法律思想彰显无疑。
(三)对被告的保辜期限的规定
保辜制度是要求违法犯罪的行为人,在法定的期限内积极救助被害人,在保证被害人不出现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的同时,违法犯罪行为人也可以承担比较轻的犯罪责任的一种制度,它视期限届满时的伤情再定罪量刑,这是将因果关系理论融入其中。保辜制度始创于西周,经过发展,被完备地写入《唐律》之中,这也表明其已经趋于成熟[6]。在《洗冤集录》中也涉及了保辜的法律规定:“诸保辜者,手足限十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三十日折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三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诸啮人者,依他物法。限内堕胎者,堕后别保三十日,仍通本殴伤限,不得过五十日。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假殴人头伤,风从头疮而入、因风致死之类,仍依杀人论。若不因头疮得风而死,是为他故,各依本殴伤法。”通过对比《唐律疏议》中《斗讼律》第307条关于保辜制度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洗冤集录》中对保辜制度做了更细致更严格的规定,如“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三十日”在《斗讼律》中则为五十日;同时丰富了保辜情形,如“限内堕胎者,堕后别保三十日,仍通本殴伤限,不得过五十日。”这些变化在反映唐代到宋代法律进化严格全面的同时,也表明《洗冤集录》对狱案的谨慎规定,违法犯罪行为人在客观上虽已对被害人造成了伤害,但在主观上可能并不一定是故意,在考虑到过失的情况下保辜制度无疑会使行为人少受刑狱之苦,为违法犯罪人提供改正的机会,同时在受害人伤势稳定后再确定加害人的法律责任,也会大大减少案件发生错误的概率,因此《洗冤集录》中对保辜制度的规定对正确认定法律责任、准确适用法律条文具有重要意义,是体现“慎刑恤狱”法律思想的重要一点。
三、依法办案、礼法并用法律思想
在宋朝中央集权增强、司法权集中、刑事检验制度不断发展的大环境下,《洗冤集录》必然将法律作为刑事司法检验首要准则,依法办案、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贯穿其中,而《洗冤集录》中叙写的罪与行法定、回避制度与注重德礼则是依法办案、礼法并用法律思想的典型代表。
(一)罪与行法定
在条令中,无论是官员的失职情形还是各类处罚法律规定,包括保辜制度都是罪与行法定的表现。此处所论的罪与行是指罪罚与行为依法律而定,罪罚既包括被告所犯之罪,也包括检验人员行为违法所应承担之罪,而行为主要是指官员的检验和审理行为。其实在《洗冤集录》中有很多检验行为并非当时立法要求,例如“凡官守,戒访外事。惟检验一事,若有大段疑难,须更广布耳目以合之,庶几无误。”这句话的意思是官员应避免到社会上去做访问,但若遇到疑难案件亟须解决,就必须多方派人到百姓中调查,力求无误。这种检验行为非立法要求,但是宋慈深感责任在肩,便将自己的检验经验著于书中,以便更好地推动案件侦查审理,从另一方面思考,笔者认为这也是宋慈希望将有益的检验经验编撰立法的表达。
(二)回避制度
任官回避制度草创于西汉时期,而对官员审判回避制度作出具体规定是始于唐朝。为了防止审判官吏因亲属或仇嫌关系而擅权定罪,《唐六典》第一次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审判官吏的回避制度,称作“换推”制[7]。宋承唐制,规定了审判官吏的回避制度,且有所发展,并趋于完备。
《洗冤集录》中出现的规避的回避情形并不是直接关于任官回避和审判回避的规定,其涉及的是检验人员(鉴定人)的回避。在检复总说上目中有检验人员检验前对特殊人群的回避,“凡检验,承牒之后不可接见在近官员、秀才、术人、僧道,以防奸欺及招词诉。”“凡检官,遇夜宿处,须问其家是与不是凶身血属亲戚,方可安歇,以别嫌疑”这一句规定的更为详细,考虑到鉴定人员在外夜宿的回避情形,不可以在与凶犯有关系的人家借宿。回避原则在司法检验过程的运用反映了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司法公正正是依法办案的重要部分。
(三)注重德礼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法律思想记载于《唐律疏义》,即重视官吏职业道德,把法律强制与德礼教化结合起来[8]。宋慈在他的《洗冤集录》中也十分注重官员的德与礼。在上文所述的检复总说上中第一段不仅仅是对检验官现场检验的要求,也体现了身为检验官的职业道德,要做到不扰民,不接触官员和当事人,拒绝不良作风,礼的体现尤为突出。在检复总说下中最后一段:“……不可姑息诡随,全在检验官自立定见。”即检察官应对案件工作不迁就,有自己坚定的态度,可见检验官的德在案件检验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可见,《洗冤集录》的礼法并用法律思想主要体现为注重德礼。
四、尊重事实、证据至上的法律思想
刑事司法检验的目的是通过检验找寻证据,以证据决定审判结果。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制度是司法官吏听讼理刑,大多重口供,轻证据,忽视客观事实[9](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口供虽然在现代司法中也属于证据种类之一,但这里强调的是实物证据而非言词证据),而宋慈在《洗冤集录》序中便表达了客观证据的重要性,并在后文中始终围绕客观证据进行叙写。
首先,宋慈对事实证据问题做了很多指导性概括,同时强调从证据本身对全案进行思辨侦查。在卷二第六目初检第一段:“告状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开门见山地写出了不能轻信口供,要通过检验实现证据的搜集。在检复总说下目中:“虽广布耳目,不可任一人,仍在善使之;不然,适足自误。”这是表达证据的收集要广泛全面,不可以只通过一个方面,只轻信一人来寻找证据。还有,所有证据的使用要求必须“参会归一”,相互矛盾的证据不可使用。宋慈将自己对事实证据查证的经验性语句在《洗冤集录》中多次叙写,足以见其认为客观性的事实证据将是案件侦查的关键。
其次,《洗冤集录》中记录了许多重视证据的实际案例。比如,疑难杂说上目中记载一案:“有一乡民,令外甥并邻人子,将锄头同开山种粟,经再宿不归。及往观焉,乃二人俱死在山,遂闻官。随身衣服并在。牒官验尸,验官到地头,见一尸在小茅舍外,后项骨断,头、面各有刃伤痕;一尸在茅舍内,左项下、右脑后各有刃伤痕。在外者,众曰:“先被伤而死。”在内者,众曰:“后自刃而死。”官司但以各有伤,别无财物,定两相并杀。一验官独曰:“不然!若以情度情,作两相并杀而死可矣。其舍内者,右脑后刃痕可疑,岂有自用刃于脑后者?手不便也。”不数日间,乃缉得一人,挟仇并杀两人。”此案的亮点在一验官之词:“其舍内者,右脑后刃痕可疑,岂有自用刃于脑后者?手不便也。”这个结论是在检验尸体后通过客观分析得出的,正常人不会以砍自己后脑的方式自杀,所以众人认为其杀人后再自杀存在客观上的严重漏洞。通过这一案件可见,在有客观证据的情况下认真观察与分析问题是极为重要的。警惕先入为主的主观臆断是宋慈需要办案官员们切记的一点,宋慈将此案收录于《洗冤集录》中展现给人们事实证据永远是案件检验侦查的第一出发点。
《洗冤集录》中的案例大都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通过刑事司法检验的手段寻找案件的突破口,此突破口即证据之所在。
再次,《洗冤集录》作为一部法医学著作,录中法医检验经验均是事实证据的搜集过程,无论是验尸、验骨,还是火死、跌死等各种死因检验,都是对证据的探寻,如此丰富的法医检验方法在《洗冤集录》中展现并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是极为罕见与难得的。可以说,检验与证据制度的发展使宋朝司法检验发展到又一新的高度。
五、《洗冤集录》中法律思想在我国现代法治视域下的辨析
(一)“慎刑恤狱”思想对比当今刑事司法程序
无论是对官员检验行为、现场检验要求还是保辜期限的规定,“慎刑恤狱”思想在《洗冤集录》中都一以贯之,且主要以实体行为为基础在《洗冤集录》中展现。而现代体现“慎刑恤狱”的法律思想不仅在实体法中,更多的是在程序法方面,虽然法律思想内涵没有本质区别,但范围上却要远远大于《洗冤集录》,也就是说现代法治更为完善与全面,尤为体现在刑事司法程序方面。
以刑事法律程序为例,在司法程序上有一审、二审、再审、死刑复核程序等,这些程序间关系密切,法律的制定也十分全面详细,从本质上给予了每个案件最大的公平正义的基础,这实则是与《洗冤集录》中“慎刑恤狱”思想相通的,但若要辨析其中不同,不难发现现代刑事法律更多以实体法保障“用刑宽缓”,以程序法保障“决狱谨慎”,如果刑事司法没有程序上的环环相扣,人们便没有良好的法律途径去寻找公平与正义。所以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当今刑事司法程序所体现的法律内涵与思想都要在“慎刑恤狱”思想之上,外延更广泛,层次更丰富。
(二)“依法办案”“礼法并用”思想对比“依法治国”思想方针
十九大提出了依法治国总目标,是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通通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这意味着法律将处于国家的中心位置,这是我国法治新高度。“依法治国”思想方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治与法治同步同行。虽然这与《洗冤集录》中蕴含的“礼法并用”的法律思想一致,实则不尽相同。
首先,《洗冤集录》中“依法办案”的“法”是以宋刑统为法律基础,宋代法律严苛,条文的规定也十分详细,依法办案从两方面分析各有利弊。其一,关于“罪与行法定”思想、回避制度的具体规定,有利于官吏审判执法制度化、体系化;其二,严苛的法律条文成为百姓的负担,加剧了恶法的演化,造成了社会动荡。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新时代“依法治国”思想方针将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放在首位,全面地从实质上和形式上保障了人民的利益,国家威严,二者不同之处可见一斑。
其次,在《洗冤集录》中“礼法并用”强调了要注重德礼,进一步发掘这里所说的“德礼”会发现其主要是强调官员的德与礼,是从官员自身行为上做出规定。然而“依法治国”思想方针中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则是从案件本身入手,将我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国法、天理、人情融入案件审判当中,因而范围更大,最重要的是联系了实际,以当代国情为出发点,应时顺民。
总的来说,“依法治国”思想方针中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站在当代法治发展道路之上,充分融入古代德礼之理,以顺应民心,推动具有我国特色法治道路发展为目标,作用于我国目前法律体系的完善。无论从人权角度或是法治角度,都是古代“依法办案”“礼法并用”法律思想所无法比拟的,究其原因在于法律继承。法律继承不仅仅是不同历史时期法律条文与制度的继承,还包括法律思想的继承,《洗冤集录》中“依法办案”“礼法并用”思想是当代“依法治国”思想方针必不可少的前提铺垫。
(三)事实与证据的法律思维
通览《洗冤集录》全篇不难发现,《洗冤集录》中体现的事实与证据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关于事实与证据的思维本质上其实并无区别,但现代法治中事实与证据的法律思维方式更细化、更灵活、更先进。另外,与当代我国的证据制度相比,《洗冤集录》中无论是对证据种类的丰富程度,证据搜集方式的科学合理化,还是证据勘验的技术与方法,都显然远远不及现当代,但作为事实与证据的法律思想的萌芽,现在的参天大树绝不可否认其曾经的重要作用。如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思想深入人心,这是后人对前人宝贵经验的传承,是历史的趋势,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