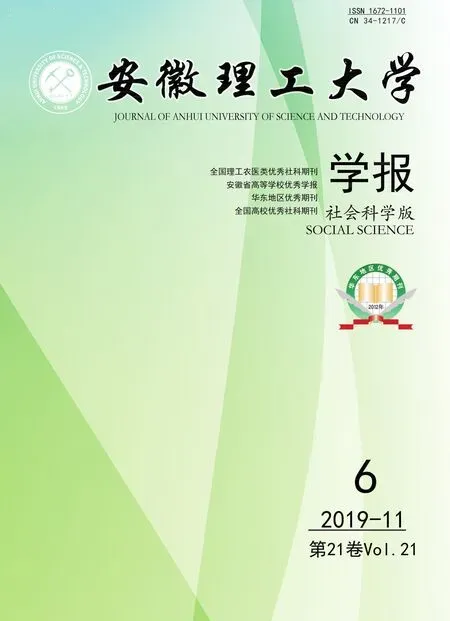惯习,场域?
——中国喜剧片集体困局的反思
陶荣婷,郑 雯
(安徽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随着《李茶的姑妈》《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富》等影片的热映,有关中国喜剧片的探讨又再次回到大众媒介的议事日程上,虽然此前上映的两部影片在豆瓣都获得不俗的口碑(《我不是药神》评分9.2、《西虹市首富》评分7.2),然而这仍然不能改善中国喜剧片目前的集体现状,相反关于其困局的反思却层见迭出,其中较常见观点认为“‘恶搞’的创作态度、‘后现代’的炒作标签以及看不清当前喜剧片艺术身份”[1]是制约我国喜剧片发展的三大瓶颈。诚然,上述总结了一些中国喜剧片存在的问题表征,但其实还是将喜剧片抽离当下社会历史语境的简单解读,有关喜剧片议题的探讨应该植根于整个国家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
一、惯习与场域
结构主义创始人维斯特劳斯关注结构对社会的形塑,认为“结构的因果力量在个体意识之外起作用并塑造个体的选择”[2],这种视角超越了简单的主客观对立的二元关系的局限性,更多的关注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性,由此他提出文化社会学理论。
布迪厄早年深受维斯特劳斯影响,其社会实践理论也有着结构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中的“惯习”与“场域”概念对于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喜剧片集体现状及其原因有着重要参考作用。“惯习”是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概念。但他强调,惯习(habitus)不是习惯(habit),习惯是反复性、机械性和被动性的,而惯习是“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3]惯习是一种结构形塑的系统,它以无意识的方式运作,将外在环境内化为潜在的、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特有的、持久性的思维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4],是人们从特定的文化氛围中获取的。
按照布迪厄的定义,场域是其实践理论中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5]场域界定社会的关系系统,塑造着惯习的结构,惯习就是在这个系统中运行。
因此,本文即从惯习与场域的视角,立足于文化社会学的层面,探讨中国喜剧片如何在艺术场域中得以制度化,并如何体现在审美“惯习”中。
二、传统惯习与中国喜剧片的文化冲突
当下,喜剧电影日益繁盛,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观众对喜剧的偏爱,形成了一定的观影偏向,而这种观影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电影诞生之初的场景。因此,探究喜剧这一纯粹审美活动的历史生成过程,考察喜剧艺术“关注方式”的“发明创造”过程,有助于厘清传统惯习与喜剧片内部的文化冲突。
(一)审美偏好惯习制约中国喜剧片的发展
1896年,在那个没有影院的时代,中国早期的电影观众诞生自传统娱乐场所,是从茶馆、戏园开始的,当时“并非独立成场地展现,而是作为茶馆、戏园消费中的配套设施,穿插舞蹈等诸多方式,作为杂耍、游戏,从而吸引眼球,达到让观众娱乐放松的目的;抑或在戏剧的前场、后场作为过渡阶段穿插放映,调节戏民心情”[6],在这种观影空间下,观众关注的是“热闹”“开心”“聊天”,这些目的与电影放映同时进行,阻碍了电影多元化的形成,模糊了作为审美意义上的喜剧与闹剧的区别,固化了人们对于喜剧的界定。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文化传承,文明戏——从传统戏曲改编而来的话剧形式——异常盛行,“它在演化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描写日常琐事充满噱头笑料的闹剧”[7],在当时的大都市上海很有市场,成为滑稽片的源头。
可见,中国喜剧片在孕育之初就延续了中国人的审美偏好惯习:偏向喜庆的、热闹的、滑稽的、大团圆的喜剧。
按照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将趣味还原到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审美惯习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产物,不仅不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消弭,反而会加剧这种日习不察的文化性情正当化甚至成为促使它不断蔓延的利器。
1.审美偏好惯习使得泛娱乐化现象凸显。作为“余兴”的消遣,这种长时间的审美偏好一直延续到上世纪末,集中体现为冯小刚式“贺岁片”和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冯氏喜剧已经成为中国喜剧片的一张名片,无论内容如何低劣,观众都心甘情愿的为其买单,《私人订制》累计票房7个亿,豆瓣评分5.6,一举拿下当年的“金扫帚奖”,成为当年“最令人失望影片”。而周星驰的黑色幽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喜剧片的标杆和方向,观众用票房撑起了“星爷”的名号,影评人更不吝溢美,将其奉为华人喜剧片的无冕之王。
自1997年之后,喜剧片内地市场异常活跃。陆陆续续出现“囧途”系列、盗匪类、开心麻花系列、探案系列、神经系列、魔幻类等等影片,这些影片也延续了观众一贯的喜好风格:轻松、幽默、有极强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2.审美偏好惯习导致现实主义题材被日益边缘化。传统延续下来的审美偏好惯习,一方面热衷于热闹的、喜庆的插科打诨,而另一方面排斥悲剧的、写实的、直面社会的、真实的影片,直接导致了现实主义题材日益边缘化。
从2010年“囧途”系列开始,中国的喜剧片就在矫揉造作与哗众取宠的路上渐行渐远。以《厨子·戏子·痞子》《分手大师》《恶棍天使》为代表的神经喜剧糅合了夸张、戏谑、噱头,制造了一系列滑稽、插科打诨的场面,试图讲述一个严肃认真的故事。然而,《厨子·戏子·痞子》的四个神经质一出场就带着满满的出戏的感觉——自带高级任务的燕京大学毕业生,几位实力派演员刘烨、张涵予和黄渤,在整部剧中夸张的台词、造作的表演加之封闭的环境都让观众频频出戏。到了《分手大师》《恶棍天使》,装傻充楞、自黑自贱、无逻辑的打闹、近乎谄媚的讨好,已经将所谓的主题消解的一片狼藉。而《煎饼侠》《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举着爱与梦想的旗帜,实际上低俗恶趣、难以寻梦,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无法切身的感受到普通人的真实欲望,影片展示的不过是鸡汤文似的温情,剧情陈旧、毫无深意。
如果说开心麻花系列的前两部《夏洛特烦恼》《驴得水》还有关于梦想的现实解读,那么到了《李茶的姑妈》,已经退化到只能用笑料去取悦观众,用媚俗去迎合影迷。至于2018年年初的探案系列,其笑点多集中于同性、女装和下俗的动作戏上,尤其是王宝强,影片中浮夸的肢体动作、喧闹的台词以及无意义的对白,名为推理,实为喜剧,用不断的庸俗来迎合大众。这些闹剧看起来像是摆脱了“生计之苦”的自由的审美倾向,实际上不过是“以求在动作的不谐中博得观众的笑声。这种做法无疑相似于游戏场中的杂耍活动,寓无理性的动作方式与逗乐观众的目的之中,令人轻松也令人无法驾驭的非理性纵情。”[8]
较之上述“无意义的形式”,《我不是药神》的热映,失落已久的喜剧精神开始被寻回。用喜剧的形式来讲述一个悲情的、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与当下社会、现实背景相结合,将生活揉进喜剧的元素。而之后的《邪不压正》则又一次回到了虚拟的梦境之中,架构在民国时期的复仇武侠片,剧情老套、人物空洞,既无法承载历史,也无法映射现实,就像片中不断出现的屋顶一样,高高在上,无法直视。
可见,在传统惯习的影响下,纵观整个喜剧片市场,闹剧称霸影坛,无出其右,现实主义题材被日益边缘化。将喜剧简单的等同于闹剧,将恶搞文化等同于喜剧文化,用低级趣味的快感来消解现实主义的困惑,回避真实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不断弱化社会的阴暗面。写实题材被不断排斥,奇幻剧、偶像剧大行其道;嘲讽类喜剧被束之高阁,严肃艺术和精英艺术被漠视,虚无主义占据主流。
3.审美偏好惯习导致多元题材的参与者身份认同危机。长期的审美偏好惯习造成的“剪刀叉现象”,将闹剧标榜为喜剧,一方面加剧了喜剧题材闹剧化的泛滥;另一方面边缘化现实主义题材,压缩了其他类型喜剧片的份额和占比,导致其余类型片参与者身份无法得到认同,多元题材的参与度降低。
因传统审美偏好惯习影响,喜剧片在中国人心中一直等同于娱乐、消遣的“下里巴人”,观影的目的也很明确为了纯粹的“找乐子”。同时,目前喜剧片的主流消费群体,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在人生的进阶初期,承担着来自职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在休闲的片刻时光中,大多会选择轻松愉悦的减压方式,刻意回避沉重无解的社会话题。于是在传统惯习和观众选择的导向下,被边缘化的喜剧类型参与者越来越难以得到市场的肯定,自我身份和社会身份均难以实现认同。
(二)喜剧精神缺失制约中国喜剧片的发展
相比欧美等国,中国的传统惯习侧重于笑闹喜剧、癫狂喜剧而缺少真正反映社会现实的喜剧精神。所谓喜剧精神就是在喜剧情境中融入嬉笑怒骂,使笑具有审美内涵和社会意蕴,创作者们用严肃的态度对社会进行解构,用幽默、温和、睿智的手段进行重构,反映真实的社会。喜剧精神缺失的惯习必然会影响中国喜剧片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确立以后,“唯市场论”“唯受众论”的观点更加促使影片的制作者们一味追求巴赫金式的狂欢,消解权威、抵制严肃、戏谑人生。
喜剧精神缺失直接导致中国喜剧片长期与社会脱离,关注乌托邦式、虚幻的社会矛盾和近乎癫狂的笑料,而对社会转型期真实的底色不闻不问,“题材、故事、人物、情感、价值观都远离这一切,仿佛天外来客,对这一切毫无所闻或不痛不痒”[9],纯粹为了搞笑而搞笑,把喜剧当成了逗乐的小丑,自黑、自贱讨好观众。而观众在长期隐匿的偏好惯习的熏染下,观看喜剧也只是为了放松、减压和乐一乐,不愿意直面真实的社会,刻意回避社会的多个层面。
长期与社会脱离必然会制约喜剧片行业的整体发展,高票房掩盖下的“海市蜃楼”终究只是幻影。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矛盾凸显、问题突出,如何有力的表现是中国喜剧片集体的缺陷,回避和假寐并非长远之计,正视问题、寻求途径,方是解决之道。
三、场域关系制约着中国喜剧片的未来
(一)场域内:中国喜剧片在虚无主义中挣扎
1.喜剧片创作者叙事水平低下。谈到中国的喜剧片,叙事是绕不开的话题。题材同质化、人设浅薄化、层次形式化已经成为喜剧片普遍存在的症状。
首先,影片的题材同质化严重,多为爱情片、公路片、动作片、历史片,单一且不接地气,缺少反映社会的现实片,《女儿国》之西游系列与《邪不压正》等抗战题材已经成为每年必拍的题材,乏善可陈。开心麻花系列除了《驴得水》隐喻了一部分讽刺和嘲弄,其余的都只是一连串小品式笑话的拼凑,毫无新意;其次,人物设置脸谱化、单一化、缺乏辨识度。《猛虫过江》即是典型的“二人转”移植,尴尬又粗俗,而王宝强参演的电影无一例外都带有明显的“傻根”痕迹,从《天下无贼》到《泰囧》、《唐人街探案》,呆痴蠢笨的人设深入人心。
而作为喜剧,最关键的叙事层次亦是流于形式,不得要领。有的相对简单,《煎饼侠》《分手大师》《恶棍天使》等遵循的是单线索的历时叙事,但影片节奏混乱、结构松散、情节平淡、单调乏味。《唐人街探案》《邪不压正》之类型片打着“后现代”“解构”的名义,拼盘式的多角度、多线索的一起讲述,前后矛盾、漏洞频出,其创作实践“却是以牺牲喜剧创作的主体性而在迎合市场的世俗性上作了较大妥协的”[10]。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内容层面看,有些作品市场反映良好,然而艺术价值不高,归根究底是创作者们叙事水平低下,无法创作出既能满足市场,又能满足审美的艺术作品。叙事技巧不得章法,创作态度敷衍随意,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却只是社会片段的编织与结构,在一种狂欢化的叙事中,我们无法看到创作者的看法或态度,或者只能看到创作者专注的游戏姿态”[11],当然如果仅仅是娱乐片,似乎不应提出过高的要求。然而如果创作者们一味沉醉在狂欢的幻影中,不思考影片叙事规范、任由这种游戏的态度泛滥于喜剧文化中,长久必将贻害喜剧市场。因此,破局的首要问题在于提高叙事水平,完整的情节、流畅的叙事、明确的逻辑、清晰的人设、张弛有度的叙事结构以及精雕细刻的创作态度方可改变喜剧影片浅层次聚合的现状。
2.喜剧片的关键即摆脱笑闹喜剧、聚焦价值取向。然而如果仅仅浅层次的谈论喜剧片创作者的叙事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近十年来,中国喜剧片讲述故事水平整体下滑,并非只是创作者能力局限,传统审美惯习促使。究其根本,价值取向失焦、虚无主义价值观才是深层次原因。“故事衰落的终极原因是深层次的。价值观,人生的是非区直,是艺术的灵魂。作家总是围绕一种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来建构自己的故事……可是我们的时代却变成了一个在道德和伦理上越来越玩世不恭、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时代——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12]
相较于中国喜剧片遭遇的瓶颈,多元化表达的美剧也一度经历了纯粹商业化的阶段。近十年来,美剧从早年的《绯闻少女》到《欲望都市》,从《实习医生格蕾》到《绝命毒师》,直到最近大热的《纸牌屋》,影片逐渐从情感、都市类的轻松愉悦的题材转移到小人物、特定人物的挣扎、无奈,进而深入到民众最为敏感的参众两院等严肃的政治话题。影片大多改编自非虚构故事,直指生活的无奈与国人的迷途,风格的转移、犀利的批判、严肃的题材并没有抹杀美剧的魅力,反而以其紧凑写实的剧情和现实主义的话题成功圈粉,拥趸无数。
反观中国目前的喜剧片,霸屏的仍然是魔幻、探案、历史、穿越、抑或是青春岁月,再不然就是网络段子与低俗恶搞,直接把喜剧等同于闹剧。美学范畴内的喜剧并不是简单的令人发笑,正如果戈里所言,这种“笑比想象的更有意义,更加深刻,这不是由于性格一时受了刺激和易于激动的、变态的心理所产生的那种笑,也不是供人们消闲解闷的那种笑,而是为了深刻地认识事物,使那些不引人注目的东西更加鲜明突出的笑。”[13]而中国目前喜剧片大都没有运用悲欢交融的笔法来描绘小人物的无奈、困惑与挣扎,也没有直面出底层人民生活中的不易,更不用说影片中的人文主义关怀。因此,尽可能的记录当下的价值观冲突,悲喜剧故事常态化,聚焦价值讨论才是当下提升喜剧片艺术质量的关键。
(二)场域间:中国喜剧片是社会形塑的产物
1.情感宣泄的喜剧。有人说,文字表达思想,艺术表达情感。当下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机械复制”时代的单调乏味、“消费社会”下的欲望张力,人们遭遇的困境与迷茫也是前所未有的,当现实社会遭遇的各种压力无法排遣时,艺术就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而喜剧则是首当其冲的宣泄出口。这种宣泄转化为需求更多的体现为理想主义状态下的狂欢,对现实主义的消解,对自由的渴望,对现状的戏谑。在喜剧描绘的漫画式图景中,艰辛的现实、苦难的人生、底层的无奈完全被稳定的社会、小康的生活所遮蔽,人们可以暂时忘却周遭的不愉快,寻求精神的慰藉。
不仅如此,青年亚文化表达了年轻群体的诉求,引导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就目前的电影市场而言,观众大多为青年,代表的是社会边缘的一群人,他们社会地位不高,渴望获得认同,然而无法通过现有体制获得理性的赞同。同时,他们在成人世界中缺少话语权与主导权,无法用相应的权力与其对抗,所以“他们更擅长在公共空间中运用无害的符号的颠覆性手段来隐蔽这种对抗性,从而用消解和躲避权力的方式来推翻社会和意识形态给他们建构的主体,并从这种反叛中获得挑衅的快感。”[14]
与此同时,作为情感的宣泄,喜剧的安全阀功能不仅体现在自身场域内,对其他场域而言,也是一种宣泄的出口。当人们的欲求在政治场域得不到响应时,艺术场域就成为最好的对象。当批评家们无法在社会场域中畅所欲言时,电影场域成为最佳的目标。于是,当一部喜剧热映之时,如《西虹市首富》,也是其饱受苛责的时候,并非它没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而是喜剧已经习惯性地成为影评人消费的焦点。
2.人生写照的喜剧。艺术不是社会的简单反映或“现象表征”,更不是社会的镜子或投影,是“人生的写照,风俗的明镜,真理的反映”[15]。中国目前处于经济迅猛发展、社会急剧变迁的转型期,如何用光影故事讲述人生百态,用悲欢离合承载社会变化,让观众在故事中触摸人性温度,在荒诞的讽刺中感受人生坎坷,而不是用低级的搞笑、幼稚的逗乐和庸俗的底线来取悦大众,这是艺术应该思考的问题,也是喜剧应该反思的地方。
回顾往昔,不难看出,无论是默片时代的卓别林,还是“喜剧之王”周星驰,他们的作品莫不如此。以演绎小人物见长,在一幕幕的转换中感受社会的写照,在一次次嘲讽中流露人生的无奈,戳中我们的不仅仅是滑稽和无厘头的笑点,更多的是对社会的批判、对爱情的渴望、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甚至是影片中那个平凡、普通,但却处处碰壁、认真生活却令人发笑的“自我”的投射。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丰富的内涵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而反观当下,各种思潮涌动,大部分的喜剧不过都是为了搞笑而搞笑的“段子”的集合罢了,粉饰后的“镜像”只是自欺欺人的手段,看不到讽刺,更没有思考,为娱乐而来,为娱乐而去,无法真正的反映当下的社会变迁。现实生活有很多素材值得制作者们去挖掘,比如城市变迁、观念差异、阶层图景以及人类社会共通的欲望、失落、挣扎、迷茫等情感。有的创作者或者为了经济利益,或者为了自我价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短期来看,或可名利双收,实则拉开了自己与当下观影人群的距离,长此以往必将被观众抛却。
四、总结
研究认为,中国喜剧电影市场如今乱象丛生,一方面观众需求剧增、饮鸩止渴,另一方面投资者谄媚迎合、毫无底线。其原因除社会因素,环境影响,观影人员的自身素质、市场化的考量标准之外,也是长期以来传统文化的“惯习”浸染、场域内不同力量的博弈、场域外社会形塑的产物。因此,中国喜剧市场的未来不仅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还依靠艺术创作者精准把握喜剧精神:不迎合、不媚俗,回归批判和嘲讽的初衷,还原社会潜藏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