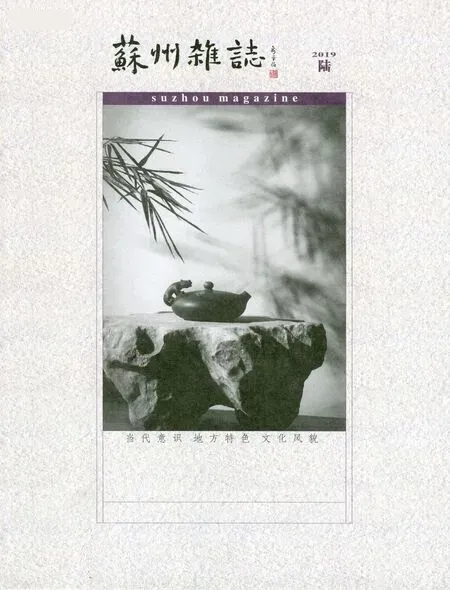诗歌与江南
小 海

陈如冬书画作品
首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于8 月24 日正式开幕了,在持续一个多月里,集中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丰盛的文旅融合大餐,呈现江南地区最新最优的艺术成果和旅游产品,并以此向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献礼!节日期间,有一场“诗意江南”经典诗词朗诵会。笔者受邀为这台朗诵会挑选了以颂咏江南和苏州为主题的古典诗词篇什。重温唐诗宋词中的这些经典篇目,让笔者再一次感受到江南的山水之秀美、人文之璀璨、诗意之丰澹。古往今来的诗人们,用他们不朽的创造,赋予了江南、苏州以词的意境和诗的灵魂,给梦里水乡、诗意江南铺陈了浓墨重彩的底色。
一、忆江南——江南可采莲
江南,是和中国、中原相对应的一个地理兼文化坐标,是依据中国、中原概念的定义而定义的。
1963 年,在陕西宝鸡出土了国宝青铜器“何尊”。“何尊”上的铭文中,首次出现了“宅兹中国”一语。《何尊铭》记载了西周初年,周成王营建洛邑王城的重要历史事件。以洛邑为天下之中,故称其“中国”。这里的“中国”,指涉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
随着不同历史时代更替,和“中国”这一概念的发展与变化一样,“中原”和“江南”的定义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之中。
根据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的观点,在空间上,“中原”是移动的,可由秦汉的黄河中游及关中,扩大为中古时代的华北,再转移到近古时代的东南,迟到近代的沿海。而且,“中原”作为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观念,也与讨论政治史的内涵不同。(参见许倬云:《万古江河》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11 月版)
自然,江南这一概念的产生、演进及变化,是依据中国、中原这些地理坐标概念而发展、位移的。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有着泛文化意义上的坐标式概念。
而在诗歌地理中,文人士大夫笔端“营造”的江南,和民间歌谣中“构建”的江南,常常呈现出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
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写有《楚辞·招魂》,其结尾有以下千古绝唱:“皋兰被径兮,斯路渐。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诗里的“江南”,毫无疑问,指涉的是楚国,当然也包括吴、越故地。
公元前306 年,楚国乘越国内乱的时候,联合齐国进攻越国,占领越国位于原吴国故地的国都,杀死越王无疆,把原先吴国一直延伸至浙江的土地全部收为己有,并设江东为郡。
公元前299 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秦昭襄王约楚怀王在武关会面。怀王不听昭睢、屈原等近臣劝阻,决意前往武关,被秦国扣留。秦王威逼他割地保命,被楚怀王严词拒绝。秦无奈下只能一直囚禁楚怀王。楚怀王在被拘期间,逃跑不成,于公元前296 年,怨愤成疾,命殒咸阳。后秦欲与楚修好,归怀王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屈原在《楚辞·招魂》中,以楚国的民间风俗,反复召唤楚怀王的灵魂,返回故国。
从先秦至两汉,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江南概念,常常也被称作“江东”或是“江左”,讲的多为包括吴、越等战国时期诸侯国在内的原楚国属地,也泛指长江中下游以南广大地区。
南北朝时的庾信,写过一篇著名的《哀江南赋》,题名应源于《楚辞·招魂》的“哀江南”句。南北朝时,侯景叛乱,庾信时为建康令,亲自率兵御敌。兵败后惜别江南,从此辗转流寓北朝。“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
《哀江南赋》,是庾信的“黍离之思”,抒写了“亡国大夫之血泪”。
与屈原、庾信等士大夫笔下哀怨凄婉的江南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却是从先秦民间歌谣到汉乐府《江南》等诗,它们留下的,是生动、热烈的一幅幅民间江南意象。
古老的吴中大地,曾经口口相传过一首歌谣。今天,你走进张家港河阳山歌馆,依然可以听到这首古老的山歌——《斫竹歌》:“斫竹,削竹,弹石,飞土,逐肉。”
这几句诗行,节奏感分明而强烈,又是可以循环和重复的,充满了原始语言艺术中那种感性而稚拙的无穷意味。
在汉赵晔所撰的《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记载了一首无名氏所作江南民歌《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和张家港河阳山歌非常接近。反映了当时江南大地上先民砍伐、制削竹子,做成弓箭后,追逐狩猎的民间风俗。短促有力的诗行,跳跃、闪回,如电影画面般浮现在人们眼前,呈现力与美的生动交响,充满力量感和场景感。
江南可采莲,
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汉乐府民歌《江南》)
乐府诗,都是配曲入乐的。读这首诗,可以想象一幅生动的江南采莲图。这是明着写鱼戏,实则写的是江南采莲时节的少男少女们。这里面,有此起彼伏、回旋循环的和声,有载歌载舞的欢娱和甜蜜,有民歌独特的清新、恣肆、放逸。鱼戏,也是对生殖与繁衍力的一种隐喻,这种灵动、活泼、欢快的场面,完全是民间的、接地气的,充满了江南鱼米之乡生活气息。汉乐府民歌《江南》,无疑也是对“江南”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活泼、旺盛生命力的一种象征与礼赞。
士大夫与民间诗歌中的江南意象,反差是如此强烈。两种抒写范式,不一样的视域;两种叙述角度,不一般的情怀。士大夫们浓郁的家国情结、人文理想和民间生生不息的蓬勃生命力,它们在共同拓展江南这一全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同时,彰显了诗歌艺术的极大张力。也使我们对江南这一地理文化概念的认知,更加全面、立体和多元。
二、枕河人家——梦里水乡
说到江南,人们自然会想起苏州。只因为苏州,是古往今来有代表性的一座江南城市。
苏州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苏州是唐宋故城,水乡典范。他在《顾颉刚自传》中讲:我小时候说,看见了苏州城市街道,几乎全是唐、宋朝代的样子。苏州是一座周围三十六里的长方形的水城,水道同街道并列著,家家户户的前门都临街,后门都傍水。——小河则不停地哼出清新快活的调子,叫苏州城浮动起来。(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1 月)
为什么留在顾颉刚先生眼底里的苏州,会是唐宋旧时的模样?这是基于他对苏州历史的了然于心,更直观的,来自于宋《平江图》上,可以一一对应的河街旧时模样。
唐、北宋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虽然还留在北方中原,但经济重心,已经逐渐南移到长江下游。当年宏大规模的帝都中,集聚着庞大的人口,包括驻扎镇守于周边的军队,不得不仰仗江南的物资供应。隋炀帝开凿的运河,从黄河通到淮水长江以至钱塘江,于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一条帝国生命线。
在唐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中原元气大伤,对江南基本生活保障物资的依赖,几乎到了一日不可或缺的地步。贞元二年(786)唐德宗好不容易从运河盼来了江淮的三万石米,欣喜万分,兴颠颠跑去东宫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参见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商务印书馆,1944 年出版)
唐朝前期,全国的六个雄州,都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安史之乱后,苏州一跃而为雄州。人口规模达到了十多万户。苏州成为了重要的税源地和兵源地。白居易在他的《登阊门闲望》一诗中写道:“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
从苦寒的边塞,战乱的中原,到杏花春雨的江南和如诗如画的苏州,简直如另一番天上人间。诗人们对苏州、对江南经典形象的营造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
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
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
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
(杜荀鹤《送人游吴》)
诗歌一开头,这位诗人导游就直接点出了姑苏这座水上城市的风物特征。从此,枕河人家,几乎成了苏州的专属用词。接着,诗人又用古宫闲地,水港小桥,来勾勒水乡悠久的历史和现实的美景。夜市菱藕,春船绮罗,则描画了这座城市的富足和繁华。最后,诗人深情款款地说,我知道远方的你在不眠的月明之夜中,把对我的思念就寄托在这江南渔歌声中吧。其实,这话不止是送给友人的,更是讲给对苏州、对江南抱持美好情感和想象的所有后人们听的。也因了这首诗,“人家尽枕河”的江南,成了多少人的梦中福地。正如清代的诗人龚自珍所言:“三生花草梦苏州”(《己亥杂诗》)。后世,有许多被迫离开了苏州,开枝散叶的家族,世代相传,还都把做梦称作“去苏州”“回苏州”。殊不知,这粒经由唐诗埋下的乡愁的种子,相遇适宜的环境或情境,就会发芽开花结果。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枫桥夜泊》)
唐诗也是苏州最好的代言人。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让大运河畔的烟雨枫桥,成了江南乡愁千年的寄寓之地。枫桥因了张继而更加出名,所以明代高启有“诗里枫桥独有名”。枫桥、寒山寺,作为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早已成了苏州文化的一张名片。更多的异乡人,乃至海外游子,来到苏州,来到江南。苏州既是抵达地、驻足地,也是立足点和新的出发地。
“苏州刺史例能诗”。在唐代,有三位杰出的诗人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曾先后出任过苏州刺史。他们在主政苏州时,保境安民,整顿吏治,兴修水利,修筑山塘河街——更重要的,他们留下的光辉诗章,已经成为苏州乃至江南的文化符号。
三位刺史诗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白居易。他825 年从杭州转到苏州任刺史,隔年就离任了。可是,他的诗歌,却永远留在了人们关于苏州的记忆里。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
(《正月三日闲行》)
天平山上白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
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白云泉》)
在告别苏州时,他写下过依依不舍的“怅望武丘路,沉吟浒水亭”(《别苏州》)。而五年后,接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则记录下了白居易当年离任苏州时的动人场面:
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谿。
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太守驻行舟,阊门草萋萋。
挥袂谢啼者,依然两眉低。
朱户非不崇,我心如重狴。
华池非不清,意在寥廓栖。
(刘禹锡《白太守行》)
三位苏州刺史诗人中,白居易任职时间最短。可他却留下了不少怀念苏州的佳句。“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忆江南》)“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徊。”(《忆旧游》)“扬州驿里梦苏州,梦到花桥水阁头。觉后不知冯侍御,此中昨夜共谁游?”(《梦苏州水阁寄冯侍御》)
如果说,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那么宋代,在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看来则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太祖赵匡胤在太庙“誓碑”中,指示子孙“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否则“天必殛之”。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成为君臣共识。人才是文化创造的主体。重视人才,造就人才,善待人才,才能人尽其才。人才是成就盛世的根本要素。难怪明代徐有贞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物质决定论与精神能动论是统一的,构成相辅相成、彼此成就的关系。唐宋时期,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天地蕴秀,物阜民丰,但如果仅仅是物质的极大丰盛,生活的奢靡,而不能完成由物质生产向文化艺术等精神生产的转化,留下千古传诵的优秀文化艺术遗产,是不足以被称为伟大朝代的。必须是社会经济繁荣的同时,政治清明,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在国家、民族文化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上,开创过一个文化高峰的时代,并以此成为全体人民文化自信的压舱石。
顾颉刚先生认为苏州是一座浮在水上的城市。事实上,让苏州浮动起来,支撑起这座古城的,还有诗歌等伟大的文化艺术。这是在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这片神奇的山水之中,所完成的物质向精神的飞跃。这是一种神奇的能量转换。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白居易《忆江南》)
从屈原、庾信的“哀江南”到唐朝诗人们笔下的“忆江南”,国力的盛衰强弱,诗风的趋时转变,无不折射出文人士大夫们,因所处时代不同,而呈现出如此迥异的心路历程。
三,诗意江南——心灵故乡
在重温歌咏苏州、歌咏江南的这些经典诗篇的过程中,笔者忽有所悟。江南,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更可能是一个心理概念。
从为“诗意江南”经典诗词朗诵会所选的唐诗宋词中,笔者发现了开启这种“江南抒写”的一个心理密钥。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
(南北朝·陆凯《赠范晔》)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
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唐·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
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
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宋·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柳叶鸣蜩绿暗,
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
白头想见江南。
(宋·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
苏州(或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处北纬31 度左右,可以说是四季分明的,不可能四季如春。但是,在诗人们笔下,她已从泰伯奔吴时的蛮荒之地,变成了农耕文明的典范甚至人间天堂,变成了一处士子们优游于斯的温柔富贵之乡。吴地人格从断发文身、重义轻死的刚硬尚武之气,转化得如此之快。春秋战国时期四大侠士(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王、荆轲刺秦王)两个出在苏州啊。班固的《汉书·地理志》曾如此感慨古代吴越民风:“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这种转变是令人惊叹的,其中包蕴了强大的文化渗透力。
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讲到梁简文帝到唐太宗这百年的艳情诗时说:谁知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屈服了。(参见闻一多《唐诗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年)
《世说新语》中则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支道林入东(会稽),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
晋室南渡,作为洛阳人的名士支遁,还在嘲笑门阀士族豪门的王氏家族人,学吴语像乌鸦叫。可曾几何时,江南已成为时尚文人争相咏叹的对象。唐诗开始向吴歌学习了。《子夜吴歌》成为唐诗中著名的形式范例。
“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毫无疑义,江南寓意春天,这是诗人们通过文学想象力构建起的江南和春天的关系。江南幻化为了永远的春天,永恒的天堂。“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同样原因,江南也成了最佳的归隐终老之地和心灵之春的栖居所。
我们知道,所谓永恒的春天,在人间并不存在。无论是西方基督教《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伊甸园,还是东方佛教《阿弥陀经》中的西方极乐世界和伊斯兰教《古兰经》中的天堂,只有这些想象中的天堂,才能做到和风细雨,四季如春,香花常开,鸟鸣婉转,鲜果满枝,河湖中流淌着酒和蜜——
恰好是在南宋,一位致仕后隐居苏州石湖的诗人范成大,在其所著《吴郡志》中收录“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这是对人间世俗生活由衷的赞叹,也是至高的美誉。
诗人本人隐居石湖,度过了长达十年较为闲适而优裕的晚年生活。在其名作《四时田园杂兴》中,收录了大量传诵后世的田园牧歌。
柳暗阊门逗晓开,半塘塘下越溪回。
炊烟拥柁船船过,芳草缘堤步步来。
(范成大《半塘》)
晓雾朝暾绀碧烘,横塘西岸越城东。
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
信脚自能知旧路,惊心时复认邻翁。
当时手种斜桥柳,无数鸣蜩翠扫空。
(范成大《初归石湖》)
毫无疑问,范成大是继陶渊明之后的又一位田园诗的大家。诗中所涉及的阊门、半塘、横塘都在苏州城西、城西南,越城东当然也就是指诗人的居处石湖了。《半塘》写出了姑苏春日胜景图:柳暗花明,舟楫往来,半城烟水,芳草漫堤。《初归石湖》中的苏州横塘,因贺铸的一句“凌波不过横塘路”而名噪一时。诗歌中写出诗人在春夏之季回到石湖时的情景:初升的暖阳透过晓雾,洒落在满心欣悦的诗人身上。“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鹭孤明菱叶中。”真是一幅色调明快晓畅的江南写真像。“信脚自能知旧路,惊心时复认邻翁。”诗人出使金国,不辱使命后归隐石湖,苏州的田园风光无疑抚慰了他那颗因山河破碎而时时隐痛的心。同时,也暗示诗人平复一颗激荡的心,决意归隐时信步走回家,竟然奇怪地发现,原来自己本身就能认得旧路,好像才离开不久似的。更主要的是,对归隐者而言,“知旧路”和“认邻翁”,和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是一脉相承的。实则上是指隐者回归心灵故乡时的“识本心”“认归处”。从此,诗人不仅可以“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和“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更是将心安在了自己的“家里”,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得“自在”了。也正因此,无论是诗人当年亲手栽种的斜桥柳,还是无数的鸣蝉在上面已将原本翠绿的叶子扫食一尽,都无法影响到诗人收拾旧家园、一隐归空的心境了。
苏州园林,堪称缩微版的江南,也是世人心目中的天堂。中国人的诗意天堂,不同于中外宗教中彼岸性的所在,它是结合此岸世俗生活最高生活理想范式的,是诗情画意、诗意栖居的所在。诗人们也把江南视作了归隐意义上的桃花源和精神故乡。
“诗意江南”,已成为一处乌托邦式的存在,成为许多人心灵的故乡。“诗意江南”,是由文学艺术创造出来的理想境界,是一种文明的实现形式,是追求最高生活形态的一种理想规范形式。
今天,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无论是苏州,还是江南,都迎来了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历久弥新的江南,将再一次浴火重生。文化苏州、诗意江南,将会以崭新的面貌,走在改革开放、再创辉煌的前列,也必将为中华文化增添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