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国家而于身无所利”的顾宪成
樊树志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创建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禁毁于天启五年(1625),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却在当时社会激起巨大的反响。康熙《东林书院志》写道:“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它的创建者顾宪成因此名扬天下,诽谤之声也如影随形,东林书院也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当时人对它的看法大相径庭,毁誉交加。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的赵南星给顾宪成写神道碑,为之鸣不平,“其于名教是非、社稷安危之计,无不挺身力争”,招来的却是罢官;居家讲学,“非孔孟之道不谈也,善无巨细无不为也,行无隐显无不兢兢也”,招来的却是政治诬陷。赵南星感叹道:“讲学者皆欲忠国家于身无所利,倘亦可以无苛呰乎!”

顾宪成(1550-1612)
一、“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府无锡县人,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七生于无锡泾里。年轻时游学于唐荆川、薛方山两先生之门。万历四年应天乡试第一名中举,崭露头角。他的同乡兼志同道合者高攀龙为其所写的行状,是最有价值的顾宪成传记,谈及他的抱负:“当是时,先生名满天下,其为文章斟酌古今,独辟乾坤,学者宗之如山于岳,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谓:此非吾人安身立命处,心所冥契则五经四书、濂洛关闽,务于微析穷探,真知力践,自余皆所不屑矣。”清晰地表明,他的安身立命之处并非文章虚名,而是传统经学与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穷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他一出场,就为自己立下极高的标准。
万历八年二月,他会试中式第二十名;三月殿试,得中第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授户部主事。时年三十一岁。顾宪成与同科进士魏允中、刘廷兰,并称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许,以道义相琢磨,慷慨激昂议论朝政,对处于权力巅峰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有所讥刺。张居正颇为忌惮,对主持会试而成为“三解元”座师的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你知道吗?每日都在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
顾、魏、刘三人确实是在评骘时事,鉴于时事日非,三人相约上书内阁次辅申时行,请他出面匡救。在《上申相公书》中,初涉政坛的新科进士锋芒毕露。开篇就点明主题:“窃闻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无君子之领袖乎?”继而批评申时行无所作为:“老师(指申时行)之于首揆(指张居正),将一切听而顺之欤?吾惧其为随抑逆而挽之欤!”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于现状的不满情绪,希望申时行有所作为。三名新科进士虽有别具一格的眼光,却过于书生意气,忽视官场的政治规矩。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势必与张居正保持高度一致,根本不可能出面“匡救”。
申时行豁达大度,并未为难三名小人物。《上申相公书》的过激言词没有带来麻烦,他们的锋芒依然毕露。万历十年,张居正旧病复发,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达官贵人纷纷斋醮祈祷,高级官僚带头,中层官僚仿效,放弃本职工作,沉迷于撰写祈祷表章,奔忙于庙宇道观之间,忙得不亦乐乎。再三为之设醮祝厘,手捧香炉,拜读表章,长跪于烈日之下。顾宪成看不惯这种献媚谄谀行为,特立独行,冷眼旁观。高攀龙《泾阳顾先生行状》写道:“江陵(张居正)病,举朝若狂,为祷于神,先生独不可。同官危之,代为署名。先生驰骑,手抹去之。”同僚出于好意,代他在祈祷表章上署名,顾宪成以为奇耻大辱,快马加鞭赶去,亲手抹去自己的名字,不愿同流合污。
万历十一年,顾宪成请假回乡,研读《易》和《春秋》。万历十四年七月,假满北上,出任吏部主事,依然特立独行。他拜谒内阁辅臣王锡爵,两人有一段绝妙的对话。
王锡爵问:“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指北京)近来有一异事乎?”
顾宪成回答:“愿闻之。”
王锡爵说:“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
顾宪成不以为然:“又有一异事。”
王锡爵问:“何?”
顾宪成说:“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
两人相与大笑而起。
这段对话见于顾与沐《顾端文公年谱》。高攀龙《泾阳顾先生行状》也记载了这一对话,文字大同小异,“庙堂”写成“内阁”,“外人”写成“外论”。一个持“外论”立场,一个持“内阁”立场,政见的歧异显而易见。
官场犹如江湖,各有各的规矩。顾宪成自视清高,无视政治规矩,使得他很难在官场立足。万历十五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京官考察工作,把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名单,引起内阁辅臣不满,给事中陈与郊等人,仰承内阁风旨,攻击辛自修,导致辛自修与何起鸣同时罢官。对于这种不分是非,不辨君子小人的做法,顾宪成慷慨陈词,批评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许国与王锡爵,“以智角智,以力角力”。《毗陵人品记》一语道破,由于“语侵执政”,顾宪成因“肆言沽名”,降三级调外任—补湖广桂阳州判官添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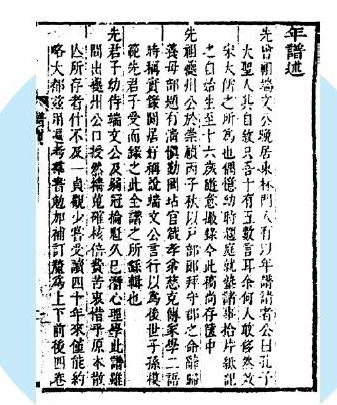
《顾端文公年谱》 〔明〕顾与沐记略
此后,他调任处州府推官、泉州府推官,政绩卓异,以“天下推官第一”,于万历二十年提拔为吏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再度回到权力中心。“三王并封”之议一出,顾宪成与首辅王锡爵的政见分歧发展为正面冲突。以后在考察京官、会推阁臣时,多次与王锡爵意见相左,遭到革职为民的惩处。万斯同《明史·顾宪成傳》写道:“(顾)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可见顾宪成既得罪了首辅,又违背了帝意,革职为民是不可避免的。
顾宪成的理想是构建清明澄澈的政治局面,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海瑞为楷模。万历十四年,海瑞出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本着一贯作风—洁人先洁己,要整肃百官必须先整肃负有监察权的御史,严厉约束自己管辖的御史,带动南京官场风气大变。陈建、沈国元《皇明从信录》说:“每下一令,不数语洞中情弊。而都人涂传巷诵,自大僚至丞郎,无不凛凛奉法。其市物必以价,无敢剧饮为大宴乐,雨花(台)、牛首(山)、燕(子)矶诸处,官舫游屐顿绝,往时城社豪猾皆屏息莫敢出。”大摆筵席,公款游览的风气顿时消失。
南京提学御史房寰,人品卑劣,凌虐士人,贪污贿赂,恣睢狼藉,人称“倭房公”。他深知海瑞惩贪不遗余力,害怕自己遭到严惩,恶人先告状,诋毁海瑞“大奸极诈,欺世盗名,诬圣自贤,损君辱国”。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顾宪成的弟弟)与同僚联名上疏,抨击房寰为代表的邪恶势力,义正词严地说:“臣等自十余岁时即闻海瑞之名,以为当朝伟人,万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天上,人不能及者。及稍知学,得海瑞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大有功于宗庙社稷,垂之千万年不磨,盖从万死一生中树节于我朝廷者。”至于房寰,早已臭不可闻,浙人每谈及者,无不掩鼻,视若臭秽。顾允成等大声疾呼:“一海瑞不足惜,正人有如海瑞者相继而指为邪,则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邪人有如房寰者相继而妨贤能,则小人之道日长矣!”明确无误地倡导以海瑞这样的正人君子为榜样,重建符合儒家伦理的政治局面。顾氏兄弟的理念是一致的。顾宪成主张像海瑞那样反对“乡愿”,慨乎言之:“乡愿之同流合污,从而不倡者也。大家如此,一滚随去,凡事都不做头,既以忠信廉洁媚君子,而其同流合污又不为倡而为从,则君子亦宽之而不责矣;既以同流合污媚小人,而忠信廉洁又不为真而为似,则小人亦安之而不忌矣。”
令人不解的是,皇帝在慰留海瑞,切责房寰的同时,以“出位言事”为借口,处分了顾允成等三名进士—“革去冠带,退回原籍”。如此有失公允的处分,激起正直官员的强烈反弹,对于“今日以建言防人之口,明日以出位加人之罪”,颇有微词,皇帝固执己见,寸步不让。
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姿态,与政治现状格格不入,显得不合时宜,革职为民是迟早的事。“君子之道日消”难以避免,“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的理想,渐行渐远。
二、“東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万历二十二年九月,革职为民的顾宪成回到无锡家乡,丢掉了乌纱帽,返归一介书生本色,沉浸于五经四书与濂洛关闽之学,倾心讲学著述。读书人仰慕他的道德学问,纷纷前来求学,于是有“同人堂”的设立。参与讲学的有宜兴吴达可,武进钱一本与薛敷教,金坛于孔兼等。学生中有的后来成为知名人士,如缪昌期、马世奇、张大可等。一时盛况空前,论者以为“程朱之门所未有”。简陋的“同人堂”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求学者,顾宪成有意复兴宋儒杨时的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在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支持下,以民间集资的形式,先后修建道南祠(祭祀杨时的祠堂)、精舍、依庸堂、丽泽堂,这就是日后声名远扬的东林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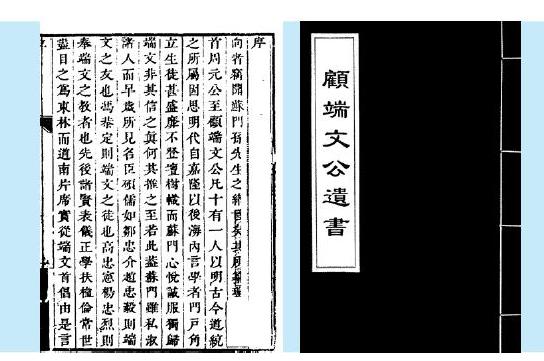
《顾端文公遗书》 〔明〕顾宪成撰
顾宪成在弟弟顾允成及挚友高攀龙、钱一本的辅佐下,把东林书院这个民间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赵南星写道:“其学唯就孔孟、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温故知新,不离乎区盖之间。高明者闻而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久之,白当道为东林书院,大会吴越之士,讲学其中,东林之名满天下矣。”
顾宪成引用曾子的话“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作为东林书院的宗旨。他解释道:“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群天下之士讲习,则天下之善受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东林书院的愿景,以继承孔孟程朱的学脉为己任。高攀龙把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概括为六个字:读书、静坐、会友,与“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一致的。每个人都下功夫读书、静坐,到了互相切磋时,才可以收到以友辅仁的效果。
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称为讲会,每月一次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大会(春季或秋季)。届时吴越及其他各地士人纷至沓来,蔚为壮观。东林书院的小会大会,究竟议论什么呢?某些学者以为是“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其实不然。顾宪成起草的《东林会约》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讲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东林书院诸君子聚在一起,并非议论政治,而是在交流研读四书的心得,由一人主讲,然后讨论,互相切磋,与今人的想象相去甚远。
《顾端文公遗书》收录了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课的讲义—《东林商语》,通篇都在探讨《论语》《孟子》的要义,向学生讲解自己的心得。试举一例如下:甲辰年(万历三十二年)共十则,全是关于《论语》某一章的阐释。第一则是:“《论语》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又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顾宪成阐释与一般经学家截然不同:“细玩此二条,圣人应是重有所感而发。盖当时人见孔子与群弟子讲于杏坛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却嚣然自以为伶俐。见孔子汲汲皇皇,忘寝忘食,略无休暇,多嗤其劳苦,至以戮民拟之。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却飘然自以为撇脱。曾不知迂拙者极是稳当,伶俐者反落险途;劳苦者到底安闲,撇脱者竟何归着。”为了说明这些高深的道理,他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向学生解释:“人生天地间,日子不是胡乱度的,屋不是胡乱住的,饭不是胡乱吃的,朋友不是胡乱搭的,话不是胡乱说的,事不是胡乱做的。这个心,极灵极妙,不是胡乱丢在一边的。”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的院规明确告诫书院同人,不得“评有司长短”“议乡井曲直”,意思是,不可以在书院中评价政府和官员的好坏,议论家乡市井的是非。他把社会上流行的作风蔑称为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要众人摒弃这九种卑劣习气。具体说来:“鄙”指的是比昵狎玩;“僻”指的是党同伐异;“贼”指的是假公济私;“浮”指的是评有司长短,议乡井曲直,诉自己不平;“妄”指的是谈论暧昧不明、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怙”指的是恶人之言巧为文饰;“悻”指的是对众人指责,致其难堪;“满”指的是问答之间意见偶殊,动辄沮抑,使之有怀而不展,有激而不平;“莽”指的是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听途说,略不反求。
天启初年主持东林书院工作的吴桂森,继承顾宪成的既定方针,把上述院规具体化,特别强调两点。其一是“绝议论以乐时”:“自今谈经论道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以期不负雍熙,是今日第一时宜也。”其二是“屏俗风以安分”:“夫布衣聚会,既无马腹之鞭,居肆讲求岂堪蝇营之听!故愿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凌垢淬之言,不以闻此席。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不以入此门。”
由此可见,以往风行一时的说法—东林书院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云云,便有点不着边际了。
三、“虚和闲止,不关世事”
钱谦益少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到东林书院拜访顾宪成,以后又和其子顾与亭、顾与沐交游。在他心目中,顾宪成的印象竟然如此:“端文(顾宪成)为人,虚和闲止,不关世事,凝尘委衣,危坐终日。”这种印象与人们的臆想截然不同,却是耳闻目睹所得的真相。吴亮为顾宪成立传,描述顾宪成在东林书院的生活就是如此:“杜门却轨,潜心理学”,“与同志阐绎濂洛正脉,其说以性善为本体,小心为工夫。岁有札记,沉潜粹密,与《读书录》相表里”。与顾宪成一起在东林书院讲学十几年的高攀龙,对他潜心理学给予高度评价:“自孟子以来得文公(朱熹),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来得先生(顾宪成),又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万历二十二年)以来,见理愈微,见事愈卓,充养愈粹,应物愈密,从善如流,徙义如鸷,殆几于无我矣。”高攀龙说顾宪成把全部精力用之于理学,达到无我的境界,是君子退居林下的真实写照。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写传记,突出的也是这一点:“每岁一大会,每日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明史》(全八册)〔清〕万斯同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
东林书院的另一位导师钱一本,罢官回乡后,回归学者本色,“杜门绝迹,不入公府”,“生平无他玩好,终日兀坐,手不停批”。纪晓岚为钱一本著作写提要,说:“东林方盛之时,(钱)一本遂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这是东林君子的共同心态。
言官一再弹劾前任内阁首辅王锡爵,将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薛敷教等正人君子斥逐一空,至今海内扼腕。主张起用废弃诸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当权大佬不能等闲视之。为了应付舆论,朝廷宣布起用顾宪成。
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任命:“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显然是执政者敷衍舆论的对策。顾宪成罢官之前先后担任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的郎中,握有人事权;而光禄寺是掌管宫廷膳食的机构,何况又是南京的光禄寺,连宫廷膳食的职掌也没有,基本是一个“投掷闲散”的虚职。顾宪成征求书院诸同志意见,有的以为“宜行”,有的以为“宜止”。他自己说:“仕宦宁退毋进,吾衰矣,当从其退者。”这一任命毕竟是以皇帝圣旨形式发出的,必须诚恳地向皇帝表明態度,他为此写了辞呈—《奏为衰病交侵恳恩休致事》:
臣以疏庸,重负任使,顷蒙皇上简录,谊当竭蹶而趋。唯是臣年六旬,两目昏花,两耳重听,起居尚须扶掖,何能勉效驰驱?反复思之,与其冒昧而进,孰若审量而退;与其出而颠沛,孰若处而苟全。伏乞敕下该部查臣别无违碍,容令休致,臣愚幸甚。
婉言推辞的理由是“衰病交侵”“两目昏花”“两耳重听”“起居尚须扶掖”,深层的原因则是,他不愿放弃蒸蒸日上的东林书院事业,不愿放弃潜心于理学的追求。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他吐露了内心的想法:“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不我弃,欣然其事,相与日切月磨其中,年来声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三盆,补缉桑榆,无虚此一生。”
吏部不接受他的推辞,再三催促,并且宽限赴任日期。顾宪成再次上疏,情词恳乞地写道:
独计臣少不自爱,逾壮便衰,行年六十,目昏耳聋,老态尽见,已不足效驰驱鞭策。况今病入膏肓,纠缠无已,奈何尚欲侥幸于万一也。且夫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图,臣之所大耻也。
这段话值得细细推敲,前半段是对朝廷的陈情,实在是身体有病,难以担当重任;后半段是为自己辩白,并非不顾国家安危理乱,而自便其身。其实流露的内心独白,恰恰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他给李三才的信吐露自己推辞的原因:“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指李三才)卓识如丈,方有旋转之望。如弟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所谓“水间林下藏拙”,就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极好的注脚,挑明了自己的真实心态。在《与孙柏潭殿元书》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不问门外是非的隐士:“弟向来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其意以诗书为仇,文字为赘,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把自己说成是桃花源人:“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几如桃花源人”,并非顾宪成的矫饰或夸张,而是真实写照。东林君子都有类似的况味。同在书院讲学的高攀龙,给老师赵南星写信,一再流露入山闭关、不问世事的心境:“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也矣”,“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入山闭关的闲人,几如桃花源人,含义并无二致,这与一般人对于顾宪成、高攀龙的印象,似乎相去甚远,恰恰是真实的另一面。
四、“不肖独何忍心而默默”
顾宪成自况为桃花源人,是对政治时局极度失望的回应—“门外黑白事寂置不问”。正如高攀龙所说:“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但是受儒家政治伦理熏陶的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难以割舍,要真正做个桃花源人谈何容易!他晚年卷入关于李三才的政治纷争,便是一个明证,既义不容辞,也迫不得已。
万历三十七年,李三才升任南京户部尚书,又被提名为都察院都御史。此时适逢内阁缺人,有些官员建议,内阁不当专用词臣,应该参用外僚,意在荐举李三才。此人既有才干又有声望,在漕运总督淮扬巡抚任上政绩卓著,抨击矿税太监贪赃枉法导致民怨沸腾,毫不留情。这样的舆情,显然触犯某些阁部大佬的权益,于是策划了一场诋毁李三才的运动。
工部郎中邵辅忠率先发难,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罗列贪、伪、险、横四大罪状,说什么“藉道学以为名,依豪贤以立脚,或无端而流涕,或无故而感慨,使天下士靡然从风,乘机躁进者愿依其幕下,感时忧世者误入其套中”。耸人听闻地扬言:“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上势孤,党与日甚。”字里行间影射李三才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结党”。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与之一唱一和,诽谤李三才“结党营私”,“年来是非日以混淆,攻讦莫之底止,主盟挑衅,三才乃其戎首”。
清者自清,是非自有公论,李三才连上四本奏疏,主动向皇帝请求辞去官职,杜门谢罪。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瑞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相继为李三才辩白。内阁大学士叶向高也向皇帝陈言:李三才已经杜门谢罪,为漕运大政考虑,宜速定去留。皇帝不表态,诽谤者愈发嚣张,一些别有用心的言官钱策、刘时俊、刘国缙、乔应甲、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等,接二连三弹劾李三才。正直的言官胡忻、曹于汴、段然、史学迁等,奋起反驳,为李三才辩护,双方激烈交锋。正如万斯同《明史》所说:“朝端聚讼,迄数月不已。”
身处东林书院的顾宪成目睹这场聚讼,难以抑制心中不平,一反桃花源人的常态,写了私人信件,寄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讲几句公道话,希望两位实权人物能够平息持续数月的“朝端聚讼”。信件的主旨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李)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醇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二是“李公在淮扬,能制税珰(矿税太监)不敢动,安民弭乱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舆情反映,也是人之常情,况且是私人信件,并非公文。孰料被别有用心的官员抓到口实,诬陷顾宪成以下野官员身份,插手朝廷政务,可见东林书院企图“遥执朝政”。
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为了搞臭顾宪成,搞臭东林书院,无中生有地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而结淮胁秦,并结诸得力权要,互相引重,略无忌惮。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
工部主事沈正宗十分仗义执言,顾宪成等僻处乡间书院,“一味讲学,反骂醉生梦死”,“今隐身不忘报国,却以为罪案矣”,“今一阁部书,便‘遥制国事,弹射不休矣”。
礼部主事丁元荐针对“遥执朝政”的诬陷,据理反驳:一个远在江南无锡的民办书院,何以能够遥控朝廷政治?“夫使东林果操天下权重之势,则长安诸缙绅何不舍要津而趋山林,而乃操戈秣马以向攻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僻处山林可以遥执朝政,那么京都衮衮诸公为何不退处山林呢?
顾宪成在写信之前,已经预料到可能带来负面影响,为了表达对于李三才人品才干的敬仰,在所不顾。他和友人谈及写信的缘由:李三才由于拨乱反正,“外犯权相,内犯权阉,死生祸福系之呼吸,并不稍顧”,“旁观者遂群起而求,多吹索抨弹,不遗余力”。对此,他忍无可忍:“漕抚(李三才)尝简不肖:‘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出于敬仰,决心打破沉默,仿效老朋友的作风—“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预料到有风险,“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尽此一念而已”。因此,他不计较寡不敌众,不顾虑可能带来大麻烦,一定要尽自己的心念。
他在《以俟录》中说,给叶向高、孙丕扬写信,并无“遥执朝政”之意,纯粹是好善、忧世的本性使然:“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他在《自反录》中再次提及此事,强调写信给叶、孙二人,一是不敢辜负李三才,二是不敢辜负海内诸君子。对于邵辅忠、徐兆魁之流毫无根据的肆意诬陷,他据理反驳:“百千罪过,胪列满纸,而实证一切茫如也。”至于宵小之徒攻讦他与李三才“结党”,他机智地反驳,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么他早就是“吕坤党”“王国用党”“吴中行、赵用贤党”“江东之、李植党”“沈思孝党”。于是乎感叹:“其又何所党哉!如此看来,有党乎,无党乎?一凭人谓耳,予何敢择焉!”真是痛快淋漓,把徐兆魁、邵辅忠之流的谰言驳得体无完肤。
这位谦谦君子显然低估了宵小之徒的险恶用心,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及至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时,他才意识到给阁部大臣写信之举大为不妥,管了不该管的事。为此他悔恨不已—“去岁救李淮抚之书,委是出位”,“忏过而亦悔且恨”。
当他看到李三才遭到四面围攻,处境岌岌可危,写信提醒,加意提防,收敛锋芒:“窃见足下任事太勇,忤时太深,疾恶太严,行法太果,分别太明,兼之辖及七省,酬应太烦,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过,口语太直,礼貌太简。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戒,亦恐嚬笑令居种种可为罪案,检点稍融,得不加意乎!”眼见形势急转直下,他又去信劝他立即引退:“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去也可以速矣,不可以缓矣。”
政治斗争不以善良愿望为转移,顾宪成不但救不了李三才,反而使得他自己和东林书院受到牵连。一些政客将李三才与顾宪成一并扣上“东林党”的帽子,严厉声讨。
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逝世,享年六十三岁。临死前,他握着儿子顾与沐的手说:“作人只伦理二字。”这句遗言的内涵,或许可以从十几天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揣测些许端倪。他说:“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于我无所致其毒,久之,或消渐释,故独是伸则众非自诎,同心盛则异类自衰。”君子坦荡荡,他以宽容的姿态回应无端的诽谤。
对于他的朋友门生而言,已经臻于无我境界的谦谦君子在诽谤声中死去,激起的是无限的悲愤和感慨。
东林书院为他举行公祭仪式,参加的知名人士四十余人,有于孔兼、钱一本、薛敷教、诸寿贤、王士骐、朱国祯、岳元声、汤兆京、吴亮、孙慎行、于玉立、高攀龙、刘元珍、文震孟、钱谦益、丁元荐、安希范等,都是晚明政界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众人先在东林书院“会哭”,再到他家中拜奠,相向失声,留连浃日始去。
五、“朋党之祸中于国”
有正义感的官员激于义愤,向朝廷建言,为顾宪成讨回公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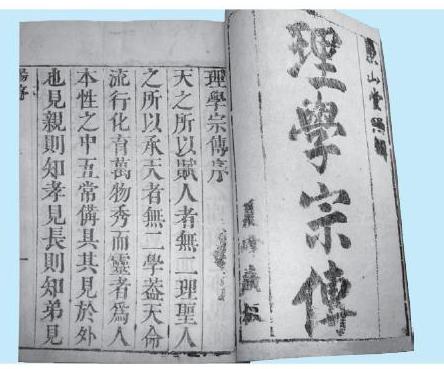
《理学宗传》 〔清〕孙奇逢撰 自刻本
江西道御史徐缙芳说:“故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忠本天植,学为人师,所著诸书有体有用,断断乎名儒君子也,或咎东林触犯时忌,臣窃以为不然。”
尚宝司丞章嘉桢说:“顾宪成豪杰圣贤者也,当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学脉之醇一,操守之精绝,神理之绵密,居处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唯思为国家进用贤才,其教泽几遍海内。”
行人司行人刘宗周说:“东林者先臣顾宪成倡道处也,从之游者不乏气节耿介之士……一时士大夫景从如云,以故东林最著。唯其清议太明,流湎之士苦于束湿,遂乘淮抚之救,谤议四起。宪成殁,而忌者因指东林为门户,合朝野而锢之,以为党人。夫东林果何罪哉?”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处境艰难的李三才还不忘为顾宪成与东林书院辩白:自从内阁首辅沈一贯以来,奸党排斥正人君子,合于己者则留,不合则逐,“今奸党仇正之言,不过两端,曰东林,曰淮抚。何以谓之?东林者,乃光禄寺少卿顾宪成讲学东南之所也。(顾)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岳元声、薛敷教等,皆研习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异哉,此东林也,何负于国家哉?”
尽管正直官员一再呼吁,对于顾宪成与东林书院的诽谤却日甚一日。到了天启年间,那些诽谤者纷纷投奔大太监魏忠贤门下,成为阉党的骨干分子,张四面之罗网,造无底之陷阱,对不同政见者扣上“东林党”的帽子,予以整肃。朝廷下令取缔并拆毁东林书院,关中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受到连累,一并拆毁。高攀龙目睹东林废墟,愤慨赋诗十首,其中之一曰:
蕞尔东林万古心,
道南祠畔白云深。
纵令伐尽林间木,
一片平芜也号林。
名列阉党“五虎”的倪文焕扬言:东林还未得到清算,东林巨魁尚未全部伏诛,流露腾腾的杀气。阉党干将王绍徽编造《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炮制黑名单,为首的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阉党的另一名干将卢承钦感到,仅仅镇压一百零八人显然不够,便仿照北宋末年的“元祐党籍碑”,炮制了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东林党人榜》。把已经逝世多年的顾宪成也列入黑名单,排在李三才、叶向高之后,位列第三。卢承钦的恶毒用心,比王绍徽犹有过之。
事已至此,“东林”已然成为莫须有的罪名,大开杀戒,先后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以“东林”的罪名,把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以及高攀龙、周起元、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黄尊素、周顺昌,迫害致死。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崇祯十一年,复社名士吴应箕与顾杲(顾宪成之孙)相会于无锡,凭吊东林书院废墟,感慨系之,赋诗一首:
同展道南祠,而伤东林址。
东林何负国,草色已及纪。
不见崔魏时,金碧连云起。
巍巍九千岁,蓬蔂安所倚。
万古此东林,子无忘所始。
鼎革之后,东林书院终于在废墟中重建,绵延后世。唐文治撰写的《重修东林书院碑记》说得好:“书院旧址为顾端文、高忠宪两公讲学之地。方是时名儒硕彦风起云从,研求正学,四方响应。而有明一代之气节,遂彪炳于寰区。厥后太仓之复社,复东林也;松江之几社,几东林也。然则东林之气节,岂非千古不朽哉!”
万斯同《明史》回顾这一段历史,一唱三叹:“(顾)宪成既没,攻者犹未止。诸凡救(李)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魏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于是朋党之祸中于国,历四十余年,迄明亡而后已。”对晚明党争的分析,鞭辟入里,“朋党之祸中于国”七个字,令人震慑不已。
孙奇逢《理学宗传》提到一种奇谈怪论:“万历年之党局始自泾阳,国运已终,而党祸犹未尽也。今日嚷东林,明日嚷东林,东林之骨已枯矣,而在朝在野仍嚷东林,岂非作始之人贻谋之不善乎?”孙奇逢反驳道:“乙丙死魏逆诸臣,甲申殉国诸臣,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乎?诸君子之所以为忠臣,而撑柱天地,名扬日月者,在五十年之后,而鼓盪摩厉者,在五十年之前。则泾阳之气魄精神度越诸子远矣,岂向俗儒曲学问毁誉定是非者耶!”企图把朋党之祸归罪于东林的谬论,不独当时流行,今日也有市场,有的人甚至鼓吹“明亡于东林”,这种戏说不是糊涂之极,就是别有用心!读者诸君只消细细体味万斯同和孙奇逢的分析,便可辨明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