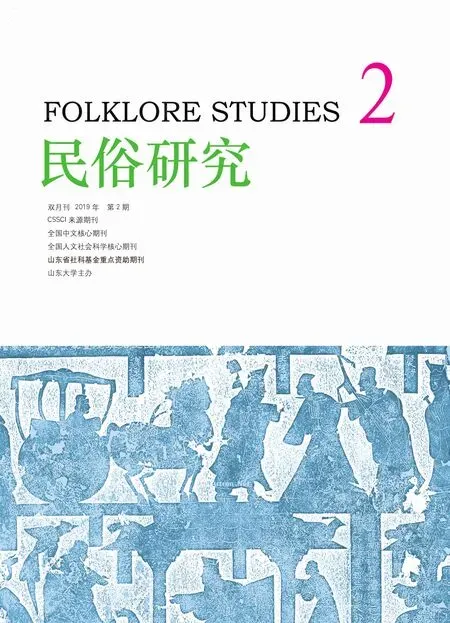阿兰·邓迪斯的“宏大理论”建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之实践理性
李 牧
1812年,格林兄弟(Jacob and Wilhelm Grimm)编著的《儿童与家庭故事集》(Kinder-undHausmärchen,英译Children’sandHouseholdTales)(即《格林童话》)问世,标志着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地位的确立。然而,长期以来,民俗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受到来自外部的质疑、挑战甚至否定。[注]①参见Regina Bendix, “On Names,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and Disciplinary Futur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1, no. 441 (Spring 1998), pp. 235-246; Dan Ben-Amos, “The Name is the Thing”,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1, no. 441 (Spring 1998), pp. 257-280;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Folklore’s Crisi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1, no. 441 (Spring 1998), pp. 281-327; Elliott Oring, “Anti Anti-‘Folklo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1, no. 441 (Spring 1998), pp. 328-338.以北美的大学体系为例,民俗学的系、学科点、师资以及课程多被压缩、合并甚至裁汰。[注]例如,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民俗学系与民间音乐学系合并,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民俗学由于师资未能补充而不再授予学位,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民俗与神话学(Folklore and Mythology Program)课程受到压缩,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和拉瓦尔大学(Université Laval)也在师资等各方面受到严重冲击。近年来,由于一系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民俗学在各国又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以期重新找寻自身的学科定位、重估自我价值以及反思学科历史及其当代使命。本文从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倡导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建构思想与非遗研究的联系出发,重新审视和理解这一学术思想的现实意义,为当代民俗学的发展和非遗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思考与方法论框架。
作为中国学界较为熟悉的著名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的多部论著或编著作品已被译为中文,对国内民俗学者多有启发。[注]关于阿兰·邓迪斯的作品,目前译成中文的主要有:[美]阿兰·邓迪斯主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陈海斌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美]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户晓辉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美]阿兰·邓迪斯主编:《西方神话学读本》,朝戈金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美]阿兰·邓迪斯编:《洪水神话》,陈建宪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美]阿兰·邓迪斯:《21世纪民俗学》,王曼利译,张举文校,《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然而,中国学界对于邓迪斯民俗思想的研究较少,除译者在译著中所做的简要述评外,主要有王珏纯、李扬[注]王珏纯、李扬:《略伦邓迪斯源于语言学的“母题素”说》,《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杨利慧(等)[注]杨利慧、安德明、高丙中、邹明华:《阿兰·邓迪斯:精神分析学说的执着追随者和民俗学领地的坚定捍卫者——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二》,《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王杰文[注]王杰文:《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以及丁晓辉[注]丁晓辉:《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等学者展开了这方面的讨论。[注]在丁晓辉《阿兰·邓迪斯民俗学研究》一书的“参考文献”部分,对与阿兰·邓迪斯有关的研究著论进行了归纳整理,可供参考。在笔者看来,阿兰·邓迪斯所一直倡导的“宏大理论”建构目标[注]此一思想在王杰文《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一文中已有论述。,是其民俗思想体系与解析民俗实践的基础纲领和理论倾向。关于这一点,国内学人的讨论较少。同时,邓迪斯的这一倾向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未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有关“宏大理论”的论争
面对民俗学长期以来所遭遇的学科困境,阿兰·邓迪斯、哈里斯·博杰(Harris M. Berger)和艾略特·沃林(Elliot Oring)等学者将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归于本学科未能向其他学科提供可资利用的理论与方法论资源。[注]Alan Dundes,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8, no. 470 (Fall 2005), pp. 385-408; Harris M. Berger, “Theory as Practice: Some Dialectics of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 in Folklore Scholarship”,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36, no. 1 (April 1999), pp. 31-49; Elliott Oring, “Missing Theory”, Western Folklore 65, no. 4 (Fall 2006), pp. 455-465.即是说,民俗学仅停留于自说自话式的经验描述,而缺乏具有普遍解释力和跨学科性质的“宏大理论”。
何谓“宏大理论”?阿兰·邓迪斯将之定义为“可以帮助我们解读民俗材料”的理论,例如穆勒(Max Müller)之太阳神话理论[注]Solar mythology,或称,比较神话学comparative mythology。、弗雷泽(Sir James Frazer)的交感巫术理论[注]Sympathetic magic,或称,神话-仪式学说myth-ritual theory。、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sis),以及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paradigmatic structuralism)[注]Alan Dundes,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8, no. 470 (Fall 2005), p. 389.。邓迪斯在肯定这些宏大理论解释效力的同时,也意识到这些理论大多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且均非美国学界的创造。而当代美国民俗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如口头程式理论(Parry-Lord oral formulaic theory)、女性主义(feminism)民俗思想,以及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等,在邓迪斯看来,它们仅能被视为具体的方法或视角,均不具备对于经验材料内涵及意义的解释力。[注]Alan Dundes,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8, no. 470 (Fall 2005), pp. 388-389.由于美国民俗学研究中宏大理论的缺失,邓迪斯等学者对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的未来充满焦虑。因此,在其2004年为美国民俗学年会所作的主题讲演《21世纪民俗学》(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邓迪斯发起了关于积极建构民俗学“宏大理论”的号召,并将之视为确保民俗学独立学科地位及其世界学术声誉的要务。
阿兰·邓迪斯有关“宏大理论”的号召,引起了民俗学界,特别是美国民俗学者的激烈讨论,其中不乏批评与反对之声。在2005年的美国民俗学年会上,李·哈林(Lee Haring)组织了题名为“民俗学为何没有宏大理论”(Why is there no “grand theory”in folkloristics)的专场讨论。在讨论中,哈林[注]Lee Haring, “America’s AntitheoreticalFolkloristic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1-9.、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L. Briggs)[注]Charles L. Briggs, “Disciplining Folkloristic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91-105.以及约翰·罗伯茨(John W. Roberts)[注]John W. Roberts, “Grand Theory,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Folklor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45-54.等学者从美国民俗学的历史出发,认为本学科的分析基础是经验实证(ethnography-of-speaking)和表演情境(performance-centered),因此,其理论贡献多为具体实践方法(method),而非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宏大理论。另外,哈林等并不认同邓迪斯有关宏大理论与民俗学学科地位关系的表述。相反,罗伯茨认为,宏大理论建构将动摇民俗学之根本。[注]John W. Roberts, “Grand Theory,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Folklor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52.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在场一位德国民俗研究者詹姆士·道(James R. Dow)的认同。后者的背书源于其自身关于德国民俗学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相互关系的研究。[注]James R. Dow, “There is No Grand Theory in Germany, and for Good Reason”,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55-62.然而,参与讨论的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赞同邓迪斯的观点,肯定建构宏大理论的重要性。例如,法恩(Gary Alan Fine)认为:“理论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方式,可以使我们突破实际经验的局限。如果没有核心概念——无论这些是被称为宏大理论或是组织化的观点,民俗学者将发现很难去建构模型以超越特殊性,并证明民俗学的认知能帮助我们理解广阔绵延的时空。”[注]Gary Alan Fine, “The Sweep of Knowledge: The Politics of Grand and Local Theory in Folkloristic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 17.
更多的研究者则依托宏大理论概念展开对话。其中,虽然理查德·鲍曼认为鼓励民俗学者致力于宏大理论建构是一种误导(a misguided enterprise),但他承认应将知识生产与单纯的经验个案分析相分离。他呼吁:在认知社会文化语境的基础上(a set of premises about society and culture),应建构普遍性(general, common)的概念框架(a conceptual frame of reference/an orienting framework for inquiry),形成具有延续性的知识传统。[注]Richard Bauman, “The Philology of the Vernacular”,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 30.与阿兰·邓迪斯有关民俗学,特别是美国民俗学缺乏宏大理论的持论相异,鲍曼认为美国民俗学具有并仍在延续建构宏大理论传统。鲍曼进一步指出,这一民俗学传统可与结构主义、表演研究(performance studies)[注]此处所谓表演研究是指当代欧美学术界出现的新潮流,与鲍曼的表演理论具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二者存在差异。表演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即探究表演如何呈现和反叛既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挖掘其中的象征关系以及背后的权利话语和运作机制。代表学者包括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和理查德·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等。、民族史诗学(ethnopoetics)、互文性和糅合理论(hybridity)等新理论动向分庭抗礼,是民俗学知识生产及捍卫自身学科身份的重要基础,同时,它也是民俗学与其它学科进行有效学术对话的保证。可见,虽然邓迪斯与鲍曼在某些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存在分歧[注]关于邓迪斯和鲍曼的学术分歧,可参见王杰文《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但两位学者立论的基点和目标均在试图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希冀能从中寻找到民俗学独立于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范式。在此共同目标的推动下,与会的其他学者,如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和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leen Stewart)等分别提出了所谓“刍论”(humble theory)[注]Dorothy Noyes, “Humble Theory”,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37-43.和“弱论”(weak theory)[注]Kathleen Stewart, “Weak Theory in an Unfinished World”,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71-82.等概念,以定义和描述经由实证经验所提升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民俗学解释模型。
可见,由邓迪斯2004年主题讲演所引发的美国民俗学界有关宏大理论的论争表明,民俗学科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声音——以构建理论为要务抑或以经验研究为中心,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倾向。美国民俗学界的这一分歧(亦为世界民俗学界所共有之现象),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政治文化渊源。
二、民俗学传统与宏大理论
邓迪斯关于宏大理论的表述及其对于美国民俗学的忧虑表明,进入现代学科体系之中的民俗学具有两个不同的学术传统。笔者在此将之分别标记为欧洲传统和美国传统。作为现代民俗学诞生地的德国,便是欧洲传统的代表之一。由于当时德国尚未统一、社会上层喜用法语,以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和格林兄弟为代表的,受狂飙突进运动、浪漫主义思潮和国家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阶层,只能从仍在使用德语、讲述德国民间故事和实践德国风俗传统的农民阶层中寻找德国文化之根,建立了民俗学与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联。这一依托民俗文化建构民族国家的范式,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和社会实践。例如,在当时尚未独立的芬兰,知识阶层也转向其社会中的农民阶层,以获得其民族独立特性的佐证。著名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即因此得以发现。与德国民俗学的国家主义背景不同,欧洲民俗学的另一重要传统——英国传统,则源于工业革命后英国向全世界的殖民扩张。伴随殖民活动所传入英国社会的有关异文化的大量文献、见闻及器物等,极大丰富了英国知识阶层的文化想象与社会生活。[注]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Destination Culture: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面对众多的异文化资源,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和体认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文化异同,探寻各文明之间的联系与区隔,构建认知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总体框架。[注]Richard M. Dorson, British Folklorists: A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麦克斯·穆勒的太阳神话学派所建基之印欧语言和印欧文化假说,爱德华·泰勒(Edward B. Tylor)之人类社会进化模型,以及弗雷泽的神话—仪式学说,均为民俗学英国传统之代表性成果。因此,在民俗学的欧洲传统中,无论德国传统或英国传统,都意在生产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以理解超越单一国家、民族、地区或个人的经验存在。
然而,美国学者却在追寻一条与欧洲学者不同的民俗学之路。在19世纪末期,特别是189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一后,包括民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体系的中心便开始逐渐移向北美。虽然许多欧裔学者仍然秉承母国的文化与学术传统,但北美特殊的多元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使得这些具有移民背景的学者(以及本土学者)开始关注在地经验和土生文化。在1888年《美国民俗学刊》(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的《发刊词》中,学者们提出要致力于研究至少四类正在急速消失的北美传统:(1)古老英国民俗的遗存(如歌谣、故事、迷信以及方言等);(2)美国南方的黑人民俗;(3)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民俗;(4)加拿大法语区以及墨西哥的民俗等。[注]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 “The Funeral Ceremonies of the Chinese in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 no. 3 (October-December 1888), pp. 239-240.由此可见,自美国民俗学会建立之初,北美学者的关注目光便聚焦于其正在经历的、不同于欧洲经验的社会文化空间。弗朗茨·博厄斯(Frans Boas)等学者对北美印第安人部落的研究,以及他们将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引入民俗学的实践,即代表了北美民俗学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倾向。[注]Rosemary L. Zumwalt, 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 A Dialogue of Dissent. Bloom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1959年,美国文明研究(American Civilization Studies)学者出身的理查德·多尔森(Richard M. Dorson),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民俗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由斯蒂·汤普森(StithThompson)所倡导的、以文化单一起源(monogenesis)论为基础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机械民俗传播伦。[注]主要是指芬兰历史地理学派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在多尔森看来,虽然美国的民俗以及美国民俗学研究与欧亚传统关系密切,但是美国经验的独特性使之脱离原有的文化窠臼而具有独立之精神与样态。因此,他提出,要用“美国的民俗”(American folklore)代替“在美国的民俗”(folklore in America)[注]Richard M. Dorson, American Folklo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A Theory for American Folklo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2, no. 285 (July-September 1959), pp. 197-215; “A Theory for American Folklore Reviewed”,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2, no. 325 (July-September 1969), pp. 226-244; “American Folklore vs. Folklore 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15, no. 2 (May-August 1978), pp. 97-112.。多尔森对于美国经验独特性的关注,促使罗杰·亚伯拉罕斯(Roger D. Abrahams)、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罗伯特·乔治斯(Robert Georges)和肯尼斯·戈尔茨坦(Kenneth Goldstein)等“青年才俊”(young Turks)开始寻求认识和理解美国日常生活的路径与方法。[注]Richard M. Dorson, “Introduction: Concepts of Folklore and Folklife Studies”, in Richard M. Dorson (ed.) Folklore and Folklife: An Introdu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5-47.多尔森将这些青年才俊的理论倾向归纳为“情境”(contextual)中心论,并认为这一理论倾向开启了民俗学的新篇章。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正是在这一实践转向背景下提出和深化的。[注]参见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84, no. 331 (January-March 1971)中的相关论文。
在2005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许多与阿兰·邓迪斯提倡宏大理论持论相异的学者如罗伯茨等认为,多尔森放弃建构宏大理论而转向关注美国独特历史文化的原因,在于其民俗思想中的去意识形态化(apolitical)。[注]John W. Roberts, “Grand Theory,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Folklore”,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45-54.笔者认同罗伯茨等学者的观点,以为多尔森极力撇清民俗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其对于所谓“伪民俗”(fakelore)的批判密切相关。“伪民俗”的概念是多尔森于1950年所提出的,意在区分以口头传统为依托的“真民俗”和建基于文学创作、政治需要和资本主义商业扩张而创造的“伪民俗”。[注]Richard M. Dorson, “Folklore and Fakelore”, American Mercury 70 (January-June 1950), pp. 335-343.其中,多尔森对于本杰明·波特金(Benjamin A. Botkin)的批评最为直接和深刻。波特金被誉为“美国公共民俗学和应用民俗学之父”,其早年的各项工作均与美国政府及其下属机构有关。例如,波特金被任命为美国联邦作家项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国家民俗的总编(national folklore editor)、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民间艺术委员会主席,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作家组项目(the Writers’ Unit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Project)总编等职务。[注]关于波特金的工作,可参见Jerrold Hirsch, “Folklore in the Making: B. A. Botkin”,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00, no. 395 (April-June 1987), pp. 3-38; Bruce Jackson, “Ben Botkin”, New York Folklore 12 , no. 3-4 (1986), pp. 23-32; Ronna Lee Widner, “Lore for the Folk, Benjamin A. Botki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lklore Scholarship in America”, New York Folklore 12, no. 3-4 (1986), pp. 1-22.在多尔森看来,波特金的各项工作包括其后的“创作”[注]如波特金著名的《美国民俗的宝藏:人民的故事、歌谣与传统》(A Treasure of American Folklore: Stories, Ballads, and Traditions of the People,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44)。,均为意识形态指导下对于民间口头传统的误读和滥用,是与宏大理论相类的外在观念[注]罗伯茨认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亦是一种宏大理论。对于经验材料本真性的歪曲和破坏,其背后所依附的权力关系会使民俗学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价值和存在意义,沦为国家机器的文化附庸。[注]Richard M. Dorson, “Folklore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5, no. 296 (April-June 1962), pp. 160-164; Folklore and Fakelore: Essays toward a Discipline of Folk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多尔森拒绝此类自上而下、意识形态导向或理论先行的民俗研究方法和呈现方式,而极力推动基于地方性知识的、以民族志经验为前提的、去政治化的知识生产模式。从根本上说,多尔森的观点反映了许多美国民俗学家的困惑,即“旧大陆”(old world,指欧洲)的理论与方法论能否认识、理解、阐释和解决“新世界”(new world,指北美)的新问题和新现实。作为多尔森的继承者[注]Charles L. Briggs, “Disciplining Folkloristics”,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5, no. 1 (April 2008), pp. 94-95.,阿兰·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即是在寻求外部理论与内部经验相契合的可能性。
三、阿兰·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
虽然邓迪斯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和鼓励民俗学者建构宏大理论,然而,其并未完成此项目标。在批评其他民俗学者缺乏理论关怀的同时,他也自觉自己对于非民俗学理论以及欧洲同业所提出的理论亦步亦趋:“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仅会运用他人的理论,我自己深受俄国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和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注]Alan Dundes,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8, no. 470 (Fall 2005), p. 388.从阿兰·邓迪斯的学术生涯看,其早期的民俗学实践主要是运用普罗普的形态学方法重新定义民俗体裁,如俗信[注]Alan Dundes, “Brown County Superstitions”, Midwest Folklore 11, no.1 (Summer 1961), pp. 25-56.、谚语[注]Alan Dundes,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Proverb”, in Alan Dundes and Wolfgang Mieder (eds)The Wisdom of Many: Essays on the Proverb.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er, 1981, pp. 43-64.和谜语[注]Alan Dundes and Robert A. Georges, “Toward a Structural Definition of the Riddl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76, no. 300 (April-June 1963), pp. 111-118.等。在后期,邓迪斯主要是通过精神分析学说理解和发掘民俗事象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体系。目前,许多学者将邓迪斯关于“民”(folk)的概念重新定义,看作其对于民俗学的重大贡献。[注]Stanley Brandes and Laura Nader, “Alan Dundes (1934-2005)”,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 no. 1 (March 2006), pp. 268-271.然而,在笔者看来,阿兰·邓迪斯作为一位优秀民俗学者的主要成就在于其所努力推动的民俗解析实践。而其最终的目的,是维护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独立地位和存在价值。[注]关于阿兰·邓迪斯职业生涯及其为民俗学,特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民俗学学科点所做的努力,可参见Rosemary Levy. Zumwalt, “‘Here is Our Man’: Dundes Discov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olklore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30, no. 515 (Winter 2017), pp. 3-33.在阿兰·邓迪斯看来,确认一门学问是否是现代学科的标准,在于这门学问对于其研究对象是否具有解释力。邓迪斯的民俗解析实践,正回应了民俗学的解释力问题。
阿兰·邓迪斯在其《解析民俗》(InterpretingFolklore)[注]Alan Dundes, Interpreting Folkl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特别注意,户晓辉译《民俗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并非此书的中文译本,而是一本编选自阿兰·邓迪斯从1960年代至2002年著作的文集。的前言中提到:“现在出版的大量民俗著作主要是单纯描述性的经验材料。你只需要到最近的图书馆里,看看标着民俗的馆藏,就可以发现很多的书籍都仅是传说、笑话、谚语或者类似体裁的资料集。”[注]Alan Dundes, Interpreting Folkl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vii.邓迪斯观察到,民俗学者多将工作的重心置于真实记录和准确呈现田野材料上,并满足和停步于民俗事象的认证(identification)。然而,依据邓迪斯的观点,由于材料搜集本身并非创造性活动,因此,对于经验民俗事象的确认并不能证明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存在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邓迪斯认为,民俗学者应超越目前的经验局限,寻求对于民俗事象的解释和分析(interpretation)。而民俗解析的关键在于运用恰当的理论框架。在阿兰·邓迪斯所确认的诸多宏大理论中,虽然其首先选用的是普罗普的形态学方法,但是,邓迪斯一直将自己视为精神分析学说的忠实追随者。[注]参见杨利慧、安德明、高丙中、邹明华《阿兰·邓迪斯:精神分析学说的执着追随者和民俗学领地的坚定捍卫者——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二》,《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
在邓迪斯看来,包括普罗普形态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学说在内的结构主义(或符号学分析),多关注文本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和总体结构,虽有助于认知事项(what an object is),但却不能使我们知晓其存在的目的和表达的意义(what the object is for or what it means)。[注]Alan Dundes, Interpreting Folkl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5.当然,邓迪斯承认,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分析已经涉及到有关潜意识的深层结构,但是,与弗洛伊德所谓的潜意识不同:前者所认知的是潜意识的结构方式[注]因此启发了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而后者所追寻的是潜意识所内蕴和不断释放的意义;前者是外在和非情感的,而后者则是内嵌和个人的。[注]Alan Dundes, Interpreting Folkl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6.邓迪斯所试图揭开的,乃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潜意识——即民俗事象迷幻光影中的灵动内涵(the meaning of folkloristic fantasy)。[注]Alan Dundes, Interpreting Folklor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6.可见,结构主义仍然为民俗解析留下了诸多认识论意义上的空白[注]Alan Dundes, “Structuralism and Folklore”, in Juha Pentikäinen and Tuula Juurikka (eds), Folk narrative research: som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VI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Folk Narrative Research. Helsinki: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Seura, 1976, pp. 75-93.,而精神分析则是“使不可理解的变得通俗易懂,在非理性中找到合理性,让潜意识浮出意识层面”[注]Alan Dundes, Bloody Mary in the Mirror. Essays in Psychoanalytic Eolkloristics. Jackson, Mississipp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2.的通途。
然而,阿兰·邓迪斯虽然依托精神分析学说去找寻民俗事象背后的意义和价值,但其并未完全依赖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而是通过其视角观照经验对象以建构自身的理论思想和解释框架。迈克尔·卡罗尔(Michael P. Carroll)认为,邓迪斯的写作中真正有关精神分析的理论其实很少,实际上,他所依托的多为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早期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是集中在《梦的解析》[注]Michael P. Carroll, “Alan Dundes, An Introduction.” In L. Bryce Boyer, Ruth M. Boyer, and Stephen M. Sonnenberg (eds.),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ociet: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Hillsdale, New Jersey: The Analytic Press, 1993, p.7.中。而且,邓迪斯的许多观点是与弗洛伊德及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相悖的。例如,邓迪斯认为,在民俗资料中经常出现的“阴茎嫉妒”(penis envy)模式所反映的,并非像弗洛伊德所谓女孩由于自身“缺失”而引发的对于男性“所有”的负面情绪,而是男性对于女性独有的生育功能的逆向妒忌心理(male birth-envy)。[注]Michael P. Carroll, “Alan Dundes, An Introduction.” In L. Bryce Boyer, Ruth M. Boyer, and Stephen M. Sonnenberg (eds.),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ociet: Essays in Honor of Alan Dundes. Hillsdale, New Jersey: The Analytic Press, 1993, p.10.再如,邓迪斯曾说,“在精神分析学派关于‘投射’(projection)的讨论中,投射与反向投射(projective inversion)的区别从来都模糊不清。”[注]Alan Dundes, Parsing Through Customs: Essays by a Freudian Folkloris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 37. 邓迪斯关于“投射”的讨论,还可参见“Projection in Folklore: A Plea for Psychoanalytic Semiotics”, Modern Language Notes 91, no.6 (December 1976): 1500-1533.在研究中,邓迪斯第一次清晰地将后者定义为“一种心理过程”,“在此过程中,某人控诉另一人所为之事,乃是其自己内心深处想做之事。”[注]Alan Dundes, “The Ritual Murder or Blood Libel Legend: A Study of Anti-Semitic Victimization through Projective Inversion”, in Alan Dundes (ed.) The Blood Libel legend: A Casebook in Anti-Semitic Folklor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1, pp. 352-353.阿兰·邓迪斯的重新定义,不仅澄清了精神分析学说中长期存在的概念不清与混淆状况,同时也使得民俗学获得了分析诸如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故事[注]Alan Dundes, “To Love My Father All’: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Folktale Source of King Lear”, Southern Folklore Quarterly 40, no. 3-4 (1976), pp. 353-366.及古埃及“两兄弟故事”[注]Alan Dundes “Projective Inversion in the Ancient Egyptian ‘Tale of Two Brother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5, no. 457/458 (Spring 2002), pp. 378-394的理论框架。可以说,邓迪斯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批判继承者,而非被动的盲从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认为精神分析学说能很好地阐释民俗,但是我同样坚信,民俗材料也能拓展精神分析理论的视域和疆界。”[注]Alan Dundes, Parsing Through Customs: Essays by a Freudian Folkloris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 p. 38.在这个意义上,民俗解析或者解释民俗的过程,实为将经验事实提升为理论思想,甚至宏大理论的过程。即使是在2005年有关宏大理论的讨论中站在邓迪斯对立面的查尔斯·布里格斯也不得不承认理论建构在民俗学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布里格斯本人与另外一位民俗学家艾米·舒曼(Amy Shuman)在1993年便开始推动经由经验而来的民俗思想的理论化进程。[注]Charles L. Briggs and Amy Shuman (eds), Theorizing Folklore. Western Folklore 52, no. 2/3 (January 1993).
在民俗解析的过程中,与早期摇椅上的民俗学家(armchair folklorists)一样,邓迪斯在应用民俗材料方面遭受了来自多方的质疑。[注]关于阿兰·邓迪斯对此的解释,可参见杨利慧、安德明、高丙中、邹明华:《阿兰·邓迪斯:精神分析学说的执着追随者和民俗学领地的坚定捍卫者——美国民俗学者系列访谈之二》,《民俗研究》2003年第3期。在许多学者看来,邓迪斯极少进行田野研究,经验素材主要为来自世界各地的间接材料。然而,从上文多尔森将邓迪斯归入“情境”理论的青年才俊,以及邓迪斯的著作[注]Alan Dundes, “Texture, Text and Context”, Southern Folklore Quarterly 28, no. 4 (1964), pp. 251-265.中可知,其并非忽略田野调查以及语境在民俗研究中的重要性。邓迪斯对于所谓世界性材料的运用来自其民俗解析的思想,即民俗学应推进至其研究的第二阶段——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和解释,而非单纯地实地调研和搜集。在这一阶段,阿兰·邓迪斯实际上刻意回避了语境对于经验材料的束缚,而希望从具有相似性的文本中寻找文化之间相通的人类普世价值和普遍意义(universal meaning)[注]Robert A. Georges and Michael Owen Jones, Folkloristics: An Introdu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以进行范式化的知识生产和文化创新,即进行宏大理论建构。需要指出的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俗学宏大理论不同,邓迪斯并非是在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经验事实的相互印证,而是在材料相似性的基础之上,从普遍性中提取差异性背后的理论和方法论范式。对此,邓迪斯的追随者之一沃尔夫冈·梅德(Wolfgang Mieder.)曾评论说,“在阿兰·邓迪斯成果丰硕的一生中,他所不断强调的是,民俗学是更好地理解人类日常生活的关键,而民俗学者在其研究中应具备一种比较意识和国际眼光”[注]Wolfgang Mieder, “‘The Proof Of The Proverb Is In The Probing’: Alan Dundes as Pioneering Paremiologist”, Western Folklore 65, no.3 (Summer 2006), pp. 217-62.。
可见,与多尔森不同,阿兰·邓迪斯并不畏惧宏大理论对于地方性知识的“侵害”,而是积极应对,将理论建设与实证经验结合。在民俗解析的框架下,邓迪斯通过对世界性民俗材料的解读,在挖掘民俗事象内在文化含义和价值体系的同时,尝试建构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实践与情感表达具有解释力的民俗理论。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邓迪斯实际上正在重建普世话语与地方性经验之间的关联,即地方性知识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被不同主体所共享,同时,他也在追问全球化的趋势是如何影响社区思考自我身份与文化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邓迪斯关于宏大理论的讨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便产生了语义互动的可能。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与宏大理论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颁行、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国所签署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年,第2页。http://www.ihchina.cn/cms/ueditor/jsp/upload/20161024/28751477290630671.pdf。。从该定义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与属于地方性范畴中的社区、群体和个人息息相关的文化资源以及承载这些文化资源的载体。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无论遭遇破坏或者面临保护,地方性知识已经无可逆转地与外部世界发生着难以割裂的互动与对话。具体说来,各缔约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编制,以及国际合作和援助机制的互助性与制度化,使得原属某一特定社区、群体或者个人的具体知识和价值系统,成为了超越地域与族群的具有共享性的人类遗产和公共文化资源。[注]刘魁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本真性与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正如高丙中在《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中指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我们这个社会接受地方的文化与人类的文化的新关系。”[注]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同时,高丙中进一步指出,在很大程度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过去的日常生活”,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活态传承与外在的介入性保护,非遗由此转变为公共文化,具有了面向未来的特质。[注]高丙中:《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在这个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具有了阿兰·邓迪斯所谓超越时空区隔的普世价值和普遍意义,如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潜水捞泥者”神话(中国息壤神话、《圣经》“诺亚方舟”故事及北美洪水神话等),成为了潜在的(或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共通性材料(human universals)[注]Alan Dundes, “Earth-Diver: Creation of the Mythopoeic Ma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4, no. 5 (October 1962), pp. 1032-1051.,即构建宏大理论和宏大叙事的经验基础。依据阿兰·邓迪斯的设想,普适性的材料即可催生解释此种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与分析框架。
然而,在当今世界各国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大量实践活动并未超出特定社区、群体或个人的疆界,其为全人类共享的特质尚未彰显。此类情况的出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先作为一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资源互动的实践过程有关。就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形而言,由于行政权力、商业活动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大量介入,权力关系与利益纠葛促使大多数非遗实践驻足于形成具有可操作性和实际效力的方针策略,其指向性仍为实践本身。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特性和非理论性,也与主导此项实践的民俗学长期以来的学科定位与属性有关。如户晓辉所言,在“非遗时代”之前,民俗学从本质上即是一门实践学科,而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进展更推动着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注]户晓辉:《非遗时代民俗学的实践回归》,《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在北美,多尔森先期关于民俗学之经验实证特性的影响犹存[注]当然,多尔森关于“伪民俗”的看法在最后也有转变,开始关注其建构过程与语境。参见Regina Bendix, “Folklorismus: The Challenge of a Concept”, International Folklore Review 6 (1988), pp. 5-15; William Fox, “Folklore and Fakelor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Institute 17, no. 2/3 (May-December 1980), pp. 244-261.,北美民俗学者,特别是身处文化工作第一线的公共民俗学者,所关注的仍为非遗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独特存在,在提供民族志经验和导向性服务外,极少对实践经验进行抽象化的知识生产。[注]Robert Baron and Nick Spitzer, Public Folklore. Jackson: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Press, 2007; Robert Baron, “Sins of Objectification? Agency, Mediation, and Community Cultural Self-Determinationin Public Folklore and Cultural Tourism Programming”,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3, no. 487 (Winter 2010), pp. 63-91; Robert Baron, “ ‘All Power to the Periphery’: The Public Folklore Thought of Alan Lomax”, 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 49, no. 3 (September-December 2012), pp. 275-317; Heather A. Diamond and Ricardo D. Trimillos (eds.), Constructing Folklife and Negotiating the Nation(Al): The Smithsonian Folklife Festival,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21, no. 479 (Winter 2008); Elaine Lawless, Working for and with the Folk: Public Folklo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9, no. 471 (2006); 黄龙光:《美国公众民俗学对中国非遗保护的启示》,《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当然,在公共民俗学的实践过程中,诸如本真性(authenticity)、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复语境化/语境重置(recontextualization)、民俗主义(folklorismus/folklorism)等概念多得到了民俗学者的重新审视与反思。遗憾的是,自“非遗运动”开始至今,无论民俗学或其它相关学科,均未能产生相应的理论与方法论去协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享性和地方利益的排他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忽视非遗自身发展规律、非遗传承人失语以及非遗知识的过度商品化等,实质上均指向同一症结,即理论层面对象自身的共享性特质与实际经验层面的实践策略之间呈现的认识论断裂与方法论缺失。即是说,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地方性知识和共享性资源之二重性的认识并未得到理论观照。
在笔者看来,对于非遗保护实践,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内具之二重性,进行理论化阐释和提升的可能切入点之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这是因为,唯有超脱源文化社区(或个人)的时空局限,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共享性才有可能得以浮现,而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即是提供了超越文化、基于文化主体之主体间性而构建的场域和可能。因由文化主体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方式或可呈现为文化适应、文化融合抑或文化冲突等。在跨文化传播的途中或终点,外来文化无可避免地与在地文化形成对话。在文化交流与信息互换的过程中,各方均因文化接触而形成共同的文化经历和情感体验(即使相互冲突,也是共享的文化过程)。需要明确的是,基于跨文化接触而建构的共同文化经历与情感体验并非归属于外来文化或当地文化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一种糅合主客位(esoteric-exoteric)知识的新文化形态。笔者自身关于北美华人移民民俗生活的研究表明,传播者与接受者双方均为极具创造性的能动主体,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对华人移民所带来的母国文化,进行了符合自身需求的文化重塑。与过分注重传播效果与商业价值的单纯政治外宣与商业经营不同,移民自发的、基于自身日常生活经验与身份认同需求而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如中餐、舞狮及传统舞蹈等文化表演和新年庆祝等节庆仪式),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二重性经验更为突出,文化共享性在此并非只是已然的属性,而更是过程性和未完成的。
目前,在国际民俗学界,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的讨论多与移民文化有关,主要关注移民群体自母国所带来的传统在新文化语境中的传承与嬗变。此类讨论虽然涉及传统文化的跨境传播问题,但仅注重该移民群体自身的变化,极少将群体间的文化互动作为研究的主要视角。在中国民俗学界及相关学科中,除孙旭培《华夏传播论》[注]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仲富兰《民俗传播学》[注]仲富兰:《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及郝怀宁《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注]郝怀宁:《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著述外,学界关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跨境传播的理论研究较少,且多将研究视域限于中华文化圈,缺乏关于跨文化传播中语境重置和日常生活转向等问题的论述。另外,由于传播内容所凝聚的深层民族记忆和族群表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与其它大众文化事项,特别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品推广有异,故应寻求更具针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和方法论资源。[注]目前,有关跨文化传播的主要论著有:[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居延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美]迈克尔·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但以上著作皆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
本文以加拿大纽芬兰地区的龙舟竞技作为案例,简要阐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北美地区的跨文化传播问题。2008年9月14日,一场龙舟点睛和下水仪式在纽芬兰东部、距离其省府圣约翰斯(St. John’s)不远的天堂镇(Town of Paradise)的八角湖(Octagon Lake)举行。这条龙舟的赞助人是当时纽芬兰当地最受中外食客喜爱的中餐馆“苏记食家”(Magic Wok Eatery)的所有者苏金堂先生(Rennies So)和谭杏媚女士(Hum Mei Tam)[注]2016年,苏先生将餐馆转让给了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李雪峰夫妇。。苏先生和谭女士来自中国香港,20世纪80年代开始定居纽芬兰,并在此创业。他们对于中华文化十分推崇,其中,苏先生本人还是一位出色的舞狮表演者,曾为纽芬兰华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Newfoundland and Labrador,成立于1976年)舞狮队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而龙舟的使用者则是当地一些乳腺癌幸存者(breast cancer survivors,全为当地白人女性)。在一次当地慈善募捐活动中,纽芬兰乳腺癌幸存者协会请求苏先生和谭女士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苏先生因此建议:“在圣约翰斯,每年都会有赛舟会(Regatta Day)[注]通常是每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三。,这与我们唐人[注]香港移民一般自称为“唐人”,意指“华人”。传统的端午节赛龙舟很相似。既然你们要表现康复之后的激情与活力,为何我们不组织一个龙舟队呢?”[注]笔者曾于2009年5月9日在圣约翰斯对苏金堂先生进行访谈。苏先生的建议得到了乳腺癌幸存者们的首肯,于是,在各方的协调与帮助下,阿瓦隆龙舟队(The Avalon Dragons)[注]圣约翰斯所处的半岛被称为阿瓦隆半岛(Avalon Peninsular),龙舟队因此而得名。迅速建立,并积极参与到纽芬兰的各类赛舟赛事和募捐活动中。例如,阿瓦隆龙舟队每年都会参加圣约翰斯的赛舟大会。再如,2011年10月2日,该队伍还参加了由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Imperial Commercial Bank of Canada)组织的赛舟比赛,为加拿大乳腺癌基金会筹集了$6,000加元的善款。[注]The Telegram, October 5, 2011.与其它竞技队伍使用的船只不同,阿瓦隆龙舟队所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式样的龙舟,样式简单古朴,色彩绚烂缤纷。然而,苏金堂先生并不满足于单纯地引入传统龙舟的外在形式,他所着意传递与呈现的更是龙舟所蕴藏的文化含义和精神实质。这便是9月14日龙舟点睛入水仪式的由来。在仪式上,苏先生亲自为龙舟点睛,并解释了仪式的历史基础和信仰内涵。同时,在仪式过程中还加入了中国文化的其它元素,如同样以祛病禳灾和强身健体为主题的舞狮和太极拳表演。这使得仪式过程成为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集中展演。
苏金堂先生关于龙舟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观念并非是本土主义的,而是世界性的。在经济活动内外,他一直努力促成中华传统文化与纽芬兰当地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如许多菜肴和餐馆内饰中融入中西方传统)。[注]参见Mu Li, “Negotiating Chinese Culinary Traditions in Newfoundland”, Digest: a Journal of Foodways and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s Foodways Section) 3, no. 1 (2014)和Mu Li, “Chinese Restaurants’ Interior Decors as Ethnographic Objects in Newfoundland”, Western Folklore 75, no.1 (Winter 2016), pp. 33-76.在苏先生看来,中国端午文化所标识的是人们在失去(屈原对于国破家亡的哀思,以及时人和后世对于屈原殉国的缅怀)之后所迸发而出的勇气和活力,而这一对生命的尊重和努力正与那些和病魔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乳腺癌幸存者所体现的积极精神相契合。在此,跨文化主体间性的连结便不仅仅在于外在形式的相似,更重要的是内在气质的相通。在这个意义上,中华端午文化便超越了传统民族文化的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制,与普遍性的人类经验和情感相对话,创造并实现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跨语际和跨文化的共享与整合。可以说,纽芬兰的龙舟竞渡,虽然在外部特征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当地文化和语境相糅合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但是,这一文化重塑过程提供了文化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和想象的可能。
无疑,如包括阿兰·邓迪斯在内的许多民俗学家所言,仅有民俗学可以解决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与情感表达中的经验问题,且仅有专业民俗学者可以构建和发展具有解释力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框架。[注]Alan Dundes, “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8, no. 470 (Fall 2005), pp. 385-408.笔者以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应建基于跨境民族志的经验研究,通过将非遗传播过程中的各要素,如非遗代表作本身[注]如在海外广泛传播的中华舞狮以及饮食文化等。、传播主体[注]如以文化外宣为己任的精英主体——如艺术家,和以日常生活为实践目的的移民或其他群体。及社交网络[注]如当地华人社交圈或多元文化群体等。、在地公共文化政策及资源[注]如多元文化政策等。纳入考量范围,建构非遗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模型和实践框架,实现民俗学自身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建构,以进一步确立其在非遗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在此理论框架的建构过程中,诸如“跨境”(transnationality)、“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本真性”“语境”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等将是常会涉及之关键概念。该理论的最终指向,将是探讨现当代社会文化交流空间中,作为特殊性产品的地方性传统如何参与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宏观或微观互动,成为实际上或象征意义上的共同遗产,逐步构建与全球化经验相映衬的新的文化形态和知识范式,从传播角度认识和理解意义的生成、传承和变化过程。
五、结 语
2005年美国民俗学会年会“民俗学为何没有宏大理论”分会场的11篇论文于2008年在《民俗研究杂志》(JournalofFolkloreResearch)以“宏大理论”的特辑名发表。2016年,经过部分修改,这些文章又以《民俗学中的宏大理论》(GrandTheoryinFolkloristics)为题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注]Lee Haring (ed), Grand Theory in Folkloris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6.这本文集中增加了阿兰·邓迪斯《21世纪民俗学》一文并将之置于首位,彰显了此文及作者思想在学术史中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Dylan Foster)和雷·卡诗曼(Ray Cashman)在该书序言中写道:“我们觉得是时候将这些文章重新出版,因为这些十年前提出的问题在我们今天仍然十分重要。……我们之前的话题还在继续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期待能有全新的思想和不落凡俗的理论创见。”[注]Michael Dylan Foster and Ray Cashman, “Preface: Theorizing Grand Theory in Folkloristics”, in Lee Haring (ed.), Grand Theory in Folkloris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6, vii-x.作为此书评论者之一的丹·本-阿莫斯在其评述文章中指出:“总的说来,各家对于邓迪斯《21世纪民俗学》讲演中表现出来的关于‘宏大理论’的向往意见不一,但是所有人都赞同他建构民俗学理论基础的呼吁和努力。”[注]Dan Ben-Amos, “Review: Grand Theory in Folkloristics”, Folklore 129, no. 2 (2018), p. 205.
从民俗学的历史看,关于理论建构和关注地方性经验的论争一直在延续。论争所立足的起点是民俗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独立地位和存在价值。在民俗学式微的岁月中,尽管理查德·多尔森和阿兰·邓迪斯的观点不甚相同,但他们均试图提出如何挽救和重振学科的策略与措施。阿兰·邓迪斯所提出的“宏大理论”构想,一直启迪并引领着当代民俗学家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在当今所谓的“非遗时代”,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实践的兴起和发展,民俗学亦积极重塑本学科的独立意识与主体地位。面对众声喧哗的非遗场域,民俗学者应积极参与和研究对象相关的知识生产,与其它学科进行有效对话,将民俗学研究、公共民俗学实践与非遗进程相结合,重构认识论基础和阐释框架,加快本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与其内具之共享性和地方性的二重性特质密切相关,无论是进行民俗学的理论提升或经验实证,都应将之视为可行且有益的破冰之处和开拓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