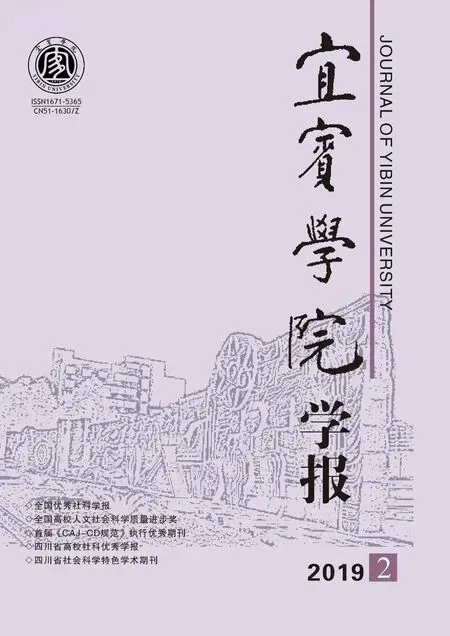穆时英《空闲少佐》出版时间及其意义
黄晶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在中国文学史上,穆时英一般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提起他,往往就会想到“白金女体的塑像”和“圣处女的风情”以及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象。苏雪林对穆时英的评价很高,认为“穆时英是我们最成功的新感觉派代表;并且是都市文学的先驱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可以与保罗·毛兰、路易士以及日本作家横光利一、屈口大学相比”[1]。但实际上,穆时英的作品大致两个阶段,早期他很关注那些闯荡江湖的下层人的生活疾苦,像《黑旋风》《咱们的世界》等,话语间充满民间气息的粗野和反叛,被左翼作家所欣赏;后面他的笔触转向了畸形的病态都市生活的描写,从《公墓》到《白金女体的塑像》和《圣处女的感情》,表现出一种颓唐和虚无。学界普遍认为在1933年左右,他的生活和艺术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蜕变,逐渐转向了新感觉派的艺术创作追求。但正如他所说“世界是充满工农大众,重利盘剥,天明,奋斗……之类的。可是,我却就是在我的小说里的社会中生活着的人”[2]231。实际上,早在1932年,穆时英20岁的时候,他创作的一篇小说《空闲少佐》就已经显示出穆时英创作思想开始转变。这个小说讲述了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淞沪会战)中被中国军队俘虏的空闲大队长被救治,后被释放但最终选择自杀的故事。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文史互证以及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了解穆时英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的加工与处理以及他在小说中的艺术手法运用等,分析这篇乍一看与他风格、题材格格不入的小说在当时的文坛、穆时英的创作生涯中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
一、 《空闲少佐》出版时间及背景考辨
根据李今在《穆时英年谱简编》中的考证,“3月3日(1932年),《空闲少佐》收入赵家璧主编‘一角丛书’第27种,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3]244。在申报1932年6月15日3版的分类广告的专栏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本收入“一角丛书”的《空闲少佐》的介绍是“俘获及后释放来沪在行镇自杀的日本少将作题材,表现人性之共鸣和对于战争的觉悟”①。同时书中附有赵家璧写的“篇前”:
在中日的上海战事,告一段落的今日,敬以穆时英先生的近著《空闲少佐》,贡献于读者之前。
空闲少佐之被俘及后自杀于庙行阵地等等事迹,谅读者已见诸报载。这里虽也按照事实写,然而作者的伟大成功, 不在忠实的记叙,而是当这一个人类兽性发展已达顶点的时代,作者的慧眼,能深入人类的心底,而抓住一点儿可爱的人生,发现他宝贵的价值,虽有一时被兽性所蒙蔽,然而一到被同样的人生呼叫时,就会产生共鸣的。[3]244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空闲少佐》不是作者凭空想象而来,而是依据真人真事、对已经见诸报纸的“空闲少佐之被俘及后自杀于庙行阵地等等事迹”加工而成。
那当时的新闻又是怎样报道的?空闲少佐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值得穆时英加以加工书写?在1932年3月31日的上海《申报》和4月2日《中华周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篇相似的关于空闲少佐的报道。《申报》的报道以《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自杀,被俘地点开枪自戕》为题:
大美晚报云,日本第九师团第七联队第二大队长空闲少佐,前在江湾战塲,被中国俘获,解至南京,拘留十日,约在两星期前释放后,顷据日人消息,业于星期一下午,在江湾西首严家宅囊日被俘地点,开枪自杀,查空闲系隶属植田少将部下,二月二十日,率部开往江湾前线作战,嗣被中国军队包围,日军苦战两日,未得进食,空闲为手溜弹炸伤胸臂等处,遂被俘获,解往南京,及三月十六日,空闲与其他俘虏数人,经中国当道释放后,即行解送来沪,空闲旋经日本军事法庭审问,而于星期一开释,讵是日下午,即赴被俘地点,出手枪对准口内开放,当受重伤,旋即身死,空闲于未死前,犹作遗书,声明所部兵士作战极勇,现闻日军当道伤悼空闲自杀,已请本埠日侨及本国人民,醵资恤其遗族云。[4]
另一篇《中华周报》的报道《中日举行正式停战会议:日军大队长空闲少佐自杀为题》与前者内容大致相同,但对空闲少佐的身份和自杀细节(时间、地点)的介绍更为明确②。
另外,在1932 年4月23日出版的第3卷第22期的《社会与教育》上,墨卿的《记日本空闲少佐的自杀:视中国的无抵抗主义者何如?》一文也多次提到了空闲少佐的经历,“二月二十日,空闲少佐所部与另一支队共同进攻江湾附近之敌……三月廿三日被带到中国的伤兵医院……三月二十八日……空闲少佐到曾经死了许多大小将士的阵地去。在其深自引咎并对其战死同伴致其最后的祝祷以后,他从容的自杀了”[5]。同时他援引了日本军事长官发表的官方消息,包括日本陆相荒木中将所言:“我非常难过,对于三月二十八日空闲少佐在江湾阵地的自杀。据上海日本司令部公布的消息,他在激战的时候,胸部受伤,而且在其昏迷的时候被俘。”墨卿的这篇文章于结尾处标注节译自字林西报,字林西报由英国人创办,曾经是上海地区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
根据这三篇相关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测,空闲少佐是1932年2月20日于江湾作战,因被炸晕昏迷被俘,解往南京,3月16日从南京释归,3月28日用枪自杀。
同时,在1932年(昭和7年)金蘭社出版的棉貫六助所著的《空閒大隊長:武人の鑑》中,也明确提到了:“三月十六日……同月廿八日(自殺の日)”[6]。棉貫六助同样参加了一二八事变,以大尉身份写了这本回忆录。
所以,基本可以断定,空闲少佐自杀的时间是1932年3月28日。在这篇小说中,穆时英虽然对故事主人公经历的具体时间进行了模糊的处理,但在细节上较之故事原型并没有作出多大修改。再加之赵家璧称这个故事有当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作参考的佐证,那必然创作时间要在事情的发生时间之后才可以。因而我们可以判断,穆时英以日本军官空闲少佐为蓝本创作出的这一故事,乃至后来被赵家璧收进《一角丛书》系列第二十七种、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事情,至少应该发生在1932年3月28日之后。而严家炎、李今等人在2008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穆时英全集》中提供的《空闲少佐》的出版时间显示这本书在1932年3月3日就已经交付出版,这之中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时间上的悖论。虽然对严家炎、李今等人的考证时间有所怀疑,但《空闲少佐》具体的出版时间因为资料占有有限仍然不能确定,这个问题还待进一步史料的打捞和清理。
二、 战争小说中的“逆子”
我们之所以这样关注《空闲少佐》的发表时间,不仅仅是因为这篇作品发表的时间节点在穆时英的创作生涯中显得格格不入,事实上这篇作品作为战争小说,在当时也实在是一篇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作品。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淞沪抗战爆发之后,上海文坛战争小说一时大热,除了以战地采访、新闻报道、摄影为主的《上海战影》 和《上海抗日血战史》的大型图书的出版,左翼阵营作家、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作家也拿起笔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书写对象不一,像“举凡此次战事发动之前因后果,十九路军及第五军抗战之悲壮惨烈,国际之调停干涉,列强之明争暗斗,政府之决心抵抗,国人之同仇敌忾,战区之灰烬瓦砾,灾民之死里逃生,无不详述颠末,一贯相承;他如迁都,罢市,炮轰南京,伪国铺张, 美国海操,苏俄动员,以及我国市民学校之义勇军大刀队等之组织与作战,各界之踊跃捐输热忱慰劳,妇女界之活跃,外交界之折冲”③。有从淞沪抗战的实景切入的,如民族主义派别的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张若谷的《战争·饮食·男女》等。以《大上海的毁灭》为例,这部小说通过对第十九军英勇抗战的事迹的描写, “抨击那些苟且偷安者,抒写爱国民众自发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以讽刺那些只说不做的可怜虫,同时也流露出对中日两国军力不对等致使中国政府被迫撤退的失望之情”[7]。虽然黄震遐作为民族主义派别的作家,这样的写法也不甚奇怪,因为这种类似的作品可看出当时普遍的创作手段和角度。同时期,左翼阵营的作家也积极行动起来,鲁迅、茅盾、叶圣陶、陈望道、胡愈之、冯雪峰、周扬、田汉、夏衍等 43 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8]。他们也以作家的身份创作出大量抗战作品,积极参与宣传抗日,揭露日军暴行。从这样的时代气氛来看,穆时英的这篇小说就显得很是格格不入了。他从一个被俘的日本军官的视角切入,虽然同样反对战争,但战争的残酷和血腥已经被转化成为人性的反思和选择,友情和爱情的符号的代入使得战争跳出了单方面的民族仇恨,而成为对人类的人性和生命普遍摧残的反思。这种思考在当时刚刚经历过战争腥风血雨的上海实际上是反主流的。逆潮流而行的穆时英未必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仍然这样创作,其原因就是他忠实于他的内心,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或抨击或赞美的政治言说,这一点我们通过穆时英在具体文本中对人物的描写塑造可以看出来。
在《空闲少佐》这篇小说里,穆时英除了主要以主人公空闲少佐的经历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外,还塑造了照顾空闲的护士黎小姐和与空闲有旧的×师长这两个重要人物。在小说里,黎小姐与空闲升虽然站在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不同立场上,但在医院这个特殊的空间里,同时又保持着病人与护士这样一种无国界的关系,一方悉心看护、一方感动感激,随之渐渐演变成罗曼蒂克的暧昧情感。
当空闲升甫一被俘虏到中国的医院,首先看到的是“友谊的笑劲,体贴的脸”,周围让人有“舒适安逸”的感觉,黎护士出于医者的善良让空闲升感到既亲切又感激,“要是伤好了的话,我要天天替她祝福,这支那的女儿是这么小心地看护着我啊!看护着她的敌人,是俘虏啊!俘虏哪……”[9]71渐渐地,空闲少佐沉浸于对黎护士的爱情,忘了战争,“创口慢慢儿的结了疤,乡思也和疤一同地掉了。妻的影子慢慢儿地淡了下去,简直不大想起啦。连自家儿是帝国军人的事也差不多忘了,能够老是这么的过下去,倒也愿意的”[9]79。
而另一边,作者也插入了想象中的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角——黎护士——矛盾的心理活动,尽管这个日本军人是侵略自己国家的敌人,但是她却没有恨他,甚至觉得他“很有礼貌,甚至有点温柔”,并且细心地照料他,并希望他回到国内去宣扬战争的残酷。穆时英在小说里提到,空闲少佐时常想起一本小说所写的美国军官和德国女间谍的一段孽缘,这实际上是源于当时上海通俗文化中的间谍叙事的潮流,暗示着作者在战争背景下试图淡化民族立场,而是从人性、情感的角度进行书写,空闲少佐与黎护士之间的温情隐喻着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之间的握手言和,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反战情绪之上。但这也并不是没有立场和原则的,因为这个故事最终指向的是更大意义上的和平和反战。空闲升被黎护士对他毫无芥蒂的关照所感动,开始怀疑战争的正义性,而他曾经也是一个杀过许多中国人、也瞧见过自家的部下奸死中国女子却并没责罚他们的日本军人,他内心逐渐动摇,腻烦和憎恶曾经的自己,“为什么要杀他们呢?对他们是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恶感的。可是,在步兵学校里,教员们不是告诉他征服支那是帝国军人的义务吗?”[9]76而这种怀疑最终变为憎恶,也最终导致他的自杀。
故事里的另外一个人物×师长,在穆时英的笔下,空闲少佐被俘后的优待和他的故交有很大关系,这个人在故事中的身份是中国军队的某师长,是他四年前的好友,两人在步兵学校时关系十分要好,现在却成为你死我活的敌人,空闲在受到×师长的关心和照顾后,越发羞愧,他叩问自己:“这就是战争,就是爱国吗?”“我们怎么会是敌人呢?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谁也不希望打的。谁要打呀?”[9]72并且开始反思战争或者说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否真的像他们根深蒂固被教育那样正确。他认识到,战争不仅带来了对中国这些善良的人们的痛苦和打击,同样对日本人也有很大的伤害,他的部下几乎全军覆没,年轻的生命在战场上灰飞烟灭,生命的可贵是不分民族的:
是的,全炸了,他就是毁了上海的人。他瞧见一大队望不尽的部队开拔到前线去,全像他那么的年轻,全是有妻子和孩子的,也许还有老年的母亲。这许多人在炮弹下毁灭了。他们哆嗦着,扯掉了军服,扔了步枪,想往后退,可是在督战部队的机关枪前倒了下去,没一个愿意死的。他看见过有三个十七八岁的兵士吓得哭,疯嚷嚷的,他们跪在他前面,可是他把他们拉出去枪毙了。为什么?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帝国。可是他们是什么也不懂的孩子,而枪毙了他们的就是他!
他又瞧见积着血的窟窿,各色各样的尸体,没了脑袋的,水没了胳膊,腿的,漏了肠子的,挂在树上的,压扁在坦克车的轮齿下的,烧焦在木屋里的……这里边有日本人,也有支那人,可是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谁也不想杀谁,可是大家都给杀了。这是躲在他们后面的人,那些坏蛋,那些骗子叫他们去打仗的。他们全死了,可是他们犯了什么罪?什么罪?[9]80-81
可以说,黎护士和×师长在空闲少佐的思想转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用爱情和友情共同感化了一个日本士兵,使他从一个侵略者变成了一个同样有着善良的情感,热爱和平、有血有肉,也会在生死面前懦弱想努力去活下来的普通人。根据当时的新闻,我们可以发现黎护士是穆时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而×师长则是确有其人。1937年潘书卿在《圣公会报》发表的《补拙续笔二则:甘介侯与空闲少佐之轶事》一文这样写到,“当甘昔年留学日本时,尝随空闲习军事,师生之谊素笃,今日不期而遇。亟命人运送往镇江某医院,为之医治。”[10]
在之前提到的墨卿的《记日本空闲少佐的自杀:视中国的无抵抗主义者何如?》一文也有这样的记载:“这个少年军官的名字叫作甘海澜(译音),曾肄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日本步兵学校……这少年军官不复是仇敌,他又重新做了空闲少佐的谦恭的学生。他为空闲少佐买了许多东西——自内衣以至袜子、手巾之类——并且小心的侍候昔日的先生。当时,江湾的战事,日趋激烈。少佐便从野战病院移至吴下医院,那里的四周,有优美的风景。经中国医生的治疗,少佐渐渐恢复健康而能够行动了。这少年军官则始终以非常的诚意与和气服侍着空闲少佐。”
除了这几条报道外,在1933年11月12日的台湾日日新报4版有这样一则消息:《甘氏归国在京有志饯宴菊池中将赠刀》④,其中介绍了去年上海事变救助空闲少佐的“中华民国”公使馆附武官甘海澜少佐于十日午后六时集于丸内中央亭开感谢送别宴的新闻。
根据类似的新闻,我们可以推测甘海澜应该就是穆时英笔下×师长的原型,他应该与空闲有师生之谊,但穆时英在小说中将他的身份改成了与空闲是同窗好友的关系,二人身份上是平等的,而非新闻中所说的出于学生对老师的恭敬。穆时英对甘海澜身份的再选择再加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故事的主题。在当时看到的报道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对这个事件的关注点都在于空闲少佐如何英勇地为武士道精神而献身,比如说“少佐是一个勇敢的人。当其做囚徒的时候,便已坚决的准备做一个武士,他的请求许他以手枪代刀的信,即可证明。一个人如其求死,到弹如雨下的战场上去,自然是比较容易,可是这种死法,则非有勇气而且真能懂得武士道的精神如空闲少佐者不辨”⑤。甚至在台湾和日本,空闲少佐成为大日本帝国武士精神的代表,还被排成舞台剧巡演,1932年8月25日的台湾日日新报的第10版就刊登有映画剧《呜呼空闲少佐》在台北的表演时间和剧院的消息。空闲少佐被这样被舆论塑造成为大日本帝国武士精神的代表、一种战争机器,仿佛空闲少佐的死是主动自愿的、没有犹豫和求生欲望的,这虽然符合政治言说的需要,但却与历史的真实和真相的复杂相去甚远。
穆时英就发现了这种舆论真实和政治宣讲背后所遮蔽的更真实的东西,那就是人性。他填补了这个人物性格中的空白,在作者的笔下,空闲少佐的军国思想是一点一点动摇的,他之所以在被俘虏的时候没有下定决心自杀,一方面是因为黎护士和×师长的善良爱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对“东京的年轻的妻和才六岁的孩子”的挂念,对生的渴望。而最终导致他的自杀的决定的也不是新闻里所大肆宣扬的武士道精神,而是他在回到司令部的时候遭遇的同胞军人的漠视和嘲笑,迎接他的“没有同情,没有友谊,没爱,有的只是冷笑。”他认识到即使他回了国内,收获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对一个没有按照武士道精神殉国的军人的严酷的惩罚。他最终意识到战争的可恶,在于将无辜的人卷入战争的同时表现出对生命最大的漠视。
空闲升为那些卷入战争而战死的年轻人而悲痛,他宁愿自己的死亡有一点价值,也不是背着懦夫的名义被送上自己国家的军事法庭:
我要告诉白川,告诉他们,这战争是不对的。我可以死。可以坐押,我是对的。他们可以把我押回国去,可是回到国里,我便要对大伙儿说,说那许多战死的年轻人,说那残酷的命令,说那没意义的武士道……可是我真的能活着回国里去吗?也许军部里会把我枪毙的。是的,一定要把我枪毙的。[9]89
……
我真的是懦夫吗?谁曾象我那么地苦战过两天呢?骂我懦夫!你们才是畜生呢!这许多人许多年轻人,是你们杀死的!我憎恶你们!憎恶你们!我憎恶战争!我犯了什么罪?要把我押回国去?要把我枪毙?[9]90
这些痛苦的呼号,在穆时英看来,才是历史的真相,才是人性复杂的地方。他独特的地方在于当同时代的人还大肆描写抗战,沉浸于民族主义、国家意识的单一历史情绪时,他已经跳出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立场的圈子,用“反战”的话语代替“抗日”的言说,从生命可贵和人性复杂的角度加以刻画战争的残酷。
空闲少佐的命运里所表现出的不安和焦躁、挣扎和绝望、虚无和无奈,这种“失败情绪”实际上恰恰是作者对生存现实的“忠实”的探求,这与穆时英1933年以后的创作理念形成了潜在的一致性,表现出了相似的矛盾和苦闷。正如他在《公墓·自序》(1933年6月版)中提到的,“我不愿意像现在许多人那么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装饰起来,过着虚伪的日子,喊着虚伪的口号,一方面却利用着群众心理,政治策略,自我宣传那类东西来维持过去的地位,或是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以为这是卑鄙龌龊的事,我不愿意做。说我落伍,说我骑墙,说我红萝卜剥了皮,说我什么都可以,至少我可以站在世界的顶上,大声地喊:‘我是忠实于自己,也是忠实于人家的人!’忠实是随便什么社会都需要的!”[2]233这里虽然可以看出穆时英对国共党争白热化之际对左翼文学和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抵抗和悖反姿态,但也可以看出他在创作过程中自始至终对“忠实”的追求。
三、 在穆时英创作生涯中的“启下”意义
事实上,这篇小说在穆时英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也有其独特意义。创作生涯之初,穆时英在1930年接连发表了几篇小说如《咱们的世界》《黑旋风》《南北极》,受到了左翼文坛的高度关注,如施蛰存在《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里写到的:“这种作品,在当时的左翼刊物,如《拓荒者》《奔流》等,也没有见过。”但到了1931年10月,他的新小说《被当作消遣者的男子》甫一出炉,这篇风格和描写对象与之前迥异、带有新感觉风的小说随即让他受到了左翼文坛的大量批评。1932年“一·二八”事件爆发之后,在文坛荒芜的情况下,穆时英出任了《现代》的主编,《现代》后来一度雄踞文坛的重要刊物。也大概是这个时间,《空闲少佐》一文被创作发表,这篇小说远不如他同年发表的《公墓》等出名,因为是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底本,它往往被认为是敷衍之作,被学界忽视。但是实际上重新审视文本,我们会发现,吊诡的是,相比于《被当作消遣者的男子》,《空闲少佐》中使用的艺术创作手法是创新的,像内心独白、时空错位等,这些创作手法在穆时英之后的创作中反复出现,特别是在那几篇被认为是新感觉派的经典作品里。
小说的一开篇,就是一段近乎意识流的场景变换,穆时英精妙地将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应用到了这里,描写了空闲少佐被炸弹炸飞后意识逐渐涣散时的精神流动,内心的思考在此时此景下是混乱无序的,一会在充满枪刺、钢盔、炮火的战场,一会是东京温暖的家人、美丽的樱花,而通过视角的转变,暗示了空闲少佐实际上是慢慢由站立到失血支撑不住而倒下,声音和画面的渐渐黯淡和飘远说明这个场景逐渐淡出。
东京的年轻的妻和才六岁的孩子浮到眼前来了,是的,他家是在东京郊外,门口有盏大纸灯笼,两盆精致的小盆景……挺着枪刺,咬紧了牙的自家儿的部下尽摇晃……家的四边是有樱花的……只听得各式各样的枪声,眼前的人,慢慢儿地模糊起来啦,便倒了下去。也不觉腰下那柄军刀垫的疼。人,人……枪刺,钢盔……子弹呼呼地掠过去……天,广大的天空,蔚蓝的天空。天小子下来,变成灰白的,这不是妻的脸吗?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远了,浮在空气里边,越浮越高,越来越远啦,接着便一下子,什么都没了。[9]70
像蒙太奇、淡出这些常常见诸电影的艺术手段,在之前的穆时英创作里鲜少可见,即使是之前具有新感觉特点的《被当作消遣者的男子》也不曾出现这样的艺术手法。但这种写法在后来穆时英的创作中可谓是“家常便饭”了,甚至这个相似的场景也仿佛作家的心理无意识,“改头换面”地多次出现。在他之后创作的《街景》里,在描写流落他乡的生活凄惨的老乞丐被车撞倒时,他写道:
猛的跳了出去。转着,转着,轰轰地,那永远地转着的轮子。轮子压上了他的身子。从轮子里转出来他的爸的脸,妈的脸,媳妇的脸,哥的脸……
(女子的叫声,巡捕,轮子,跑着的人,天,火车,媳妇的脸,家……)[11]68
同样是描写人受伤时意识涣散的内心无意识的流动,两段场景乃至手法都如此相似。不仅限于此,这样意识流的写法在穆时英后来很出名的《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也能够大量地看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将这一手法运用的很娴熟了: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地,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处的灯光。[12]334
此外,在《空闲少佐》里穆时英还使用了时空错位的艺术手法。明明空闲正在医院里养伤,还在痛苦和纠结于该不该自杀殉国的懦弱,而作者笔锋一转,场景就变成了他在日本出发前的场景:“大海的那边儿,在细巧的纸扎灯下,在樱花里边,在明秀的景色里边,有他的家,小小的矮屋子。出发的时候儿,妻在太阳旗,纸扎灯和欢呼的声音里边低低儿地哭泣着。儿子牵着他的武装带”。后来的《街景》同样使用了这一技巧,“也是那么个晴朗的,浮着轻快的秋意的下午……机关车嘟的一声儿,一道煤烟从月台上横了过去,站长手里的红旗,烂熟的苹果似的落到地上。月台往后缩脖子。眼泪从妈的脸上,媳妇的脸上,断了串的念佛珠似的掉下来,哥和爸跑起来啦”[11]65。场景从老乞丐的现在一下子跳回到他年轻时离家时和亲人告别的画面,但相似的是,这里的场景的变换实际上反映了主人公内心潜意识的归属和依恋,暗指时间跳转至他们最想返回的时间场。
更不用说《空闲少佐》这篇小说随处可见的大量的意识流的内容、内心独白,甚至可以这样说,整篇小说都是以空闲少佐的内心意识的活动为线索发展的,后来穆时英的《白金的女体塑像》中,在描写男医生在女病人裸体面前的心理活动和心理变化时,作者更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手法:
屋子里没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的过度亢进朦胧的语音淡淡的眼光诡秘地没有感觉似的放射着升发了的热情那么失去了一切障碍物一切抵抗能力地躺在那儿呢——[13]11
一大段混乱的没有逻辑的乃至没有标点的意识流动被完整地呈现出来,但本质上与这篇里空闲少佐内心的人性与国族印刻的纠缠痛苦的内心活动的描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可以看出,这篇《空闲少佐》与其称之为游戏之作,不如称之为实验之作,穆时英在思想之外同样关注创作的艺术手法,正如他自己说过很多次,他的文章、小说在实验、试验一种电影剧本式的小说,这也是他新感觉派小说独特的地方。在这篇小说里,他大胆实验了很多与之前创作完全不同的艺术手法,或许稚嫩生涩,但这些创作技巧的成功应用最终引导他走向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也成为他不可磨灭的创作记忆,在后来的作品中以不同方式不断显现。
结语
这篇一直不为学界所关注的短篇小说《空闲少佐》,如果被还原到真实的历史现场,无论是在当时战争小说大火的沪地文坛还是穆时英的作家生涯,都是反潮流、格格不入的,但是一观穆时英对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的文学加工与处理手段、运用的独特的艺术手法,我们就会发现这篇小说作为一个“实验品”,不仅反映了穆时英在创作理念上一以贯之的“忠实”原则,又对穆时英后来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启下”的作用。又或者说,只有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出发,才能了解穆时英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是怎样逐渐转向了新感觉派的艺术追求、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
注释:
①此为申报(上海版)1932年6月15日第3版分类广告。
②详见《本周国内大事记》,《中华周报(上海1931)》1932年4月2日,第22期第488-489页,确认其乃日军植田中将所领第九师第七营之营长,“本礼拜一”即二十八日在江湾严家宅地方自杀毙命。
③此为《上海抗日血战史》的广告,载《现代》1932年5月1卷1期。转引自吴晓东《“一·二八事变”与战争文学热》,《文艺争鸣》2018年第3期。
④详见《甘氏归国在京有志饯宴菊池中将赠刀》,《日日新报》,1933年11月12日第4版,部分重要原文如下:十一日东京电 去上海事变。救助空闲少佐者。为中华民国公使馆附武官甘海澜少佐。此次决定归国在京有志 十日午后六时集于丸内中央亭 开感谢送别宴 席上有菊池中将赠呈日本刀一口 极其盛会云。
⑤详见墨卿《记日本空闲少佐的自杀:视中国的无抵抗主义者何如?》载于《社会与教育》第3卷第22期,1932 年4月23日,类似报道对空闲少佐武士道精神的赞扬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