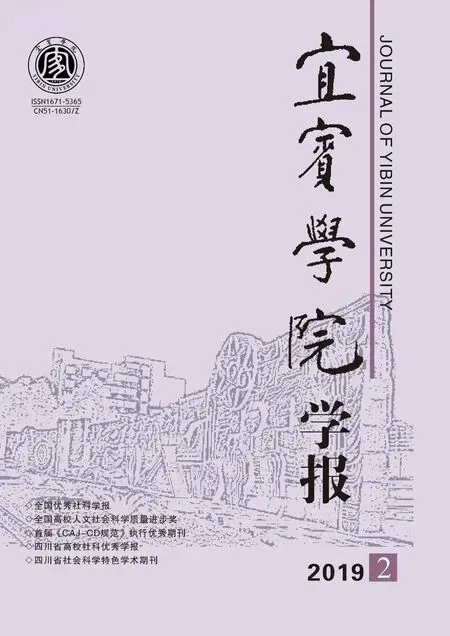人事与革命的真实描写
——论王林1949年以前的小说创作
刘若男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王林兼具作家与革命者身份,早期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他的个人风格,丰富了民国时期乡土小说的类型,抗战时期的小说更是解放区文学丰富性的证明,与民国文学框架下的其他作品有着鲜明的区别,新中国成立后《腹地》的遭遇标志着王林的创作发生了更大的改变,鲜明地体现了作家个人与时代的关联。王林被重新发掘,彰显了文学本身的生命力。本文主要对王林1949年前的小说创作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其艺术特征以及作家这样创作的深层原因,既能对他的小说创作本身有清晰的认识,又能启发我们理解他的作品之于文学史的重要意义。
一、 乡村人事的自然刻画
王林大学期间在沈从文的写作课上学习,沈从文要求听课的学生“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1]2-3,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王林是坚持听课的学生之一,“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1]2。沈从文言及王林的小说,认为是北方人写北方故事,文字粗率,篇章中具有泥土气息,即使组织不甚完美。
王林早期的创作拥有很大的视野,主要描写乡村间的人事,尤以表现乡村中日常人事的纠葛和小人物的悲哀为多,对人性的刻画亦寄于其中。《沥小盐的》刻画了胆小怕事的农人,自作聪明的旁观者,欺上瞒下的盐巡,八面玲珑的土皇上,写出了乡村中的人事复杂和人性软弱以及这背后的无奈。《龙王爷显圣》写出了乡村人的迷信与农人靠天吃饭,令人悲悯和同情的生活,我们一面会为农民的迷信感到好笑,一面又会为他们生活的不易叹息,体会到作家粗犷的描写下含有的细腻和深沉。他对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动有很敏锐的观察,原本以农耕为主的乡村有了商业的因素,使得人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机会,带来生活境况的好转,但也引发了人的堕落。《这年头》写老实巴交的农民黑丑在没有辨别力和自制力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了堕落,最终变成瘾君子。《二瘾士》同样讲述人被大烟毁灭的故事,也表现了人性的变异。小说中面对不如自己过得好的鸿业母亲,双福的母亲暗自庆幸自己的儿子双福争气,在姐姐面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欣喜。面对步鸿业后尘的双福,鸿业母亲幸灾乐祸地暗暗讥笑她妹妹,心想“在俺儿子胡糟的时候,你会说现成话。现在轮到你自己身上了”[2]40,人心的隐秘和复杂在这一刻冰冷地渗出。王林的笔触也延伸到了大的生活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关注个体的悲欢。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岁暮》讲述的是车夫胡三与妓女春芝之间的故事,刻画了原本应该热闹祥和的岁暮背后让人唏嘘的平常男女。《怀臣的胡琴》中性格孤僻、孤独一人住在空寂院落里的四黑在漫漫黑夜里拉着邻居怀臣传给他的胡琴,细微的清凉的调子在寂静的空中隐约地流淌着,四黑的孤寂和压抑与暗黑的夜融为了一体。《贾斯文》中贾斯文一家诠释了穷人没有出路的事实,贾斯文个人的不合时宜和保守腐朽的性格反而让人同情,带有悲剧色彩。这些小说都写出了时代变动下小人物的悲哀,呈现了个体在大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悲凉。
《幽僻的陈庄》是王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关注乡村广阔的日常生活场景,也关注小人物的心理和情感,在作品的架构中能看出作者的创作野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小说稍显杂乱,许是作者对乡村中各种力量的较量进行过于真实的描写而致,使得主要人物的复杂性和人物的生活本质不能更深刻地体现出来,而流于散乱①。比如主人公田成祥对自己家庭弃之不顾,任意打骂发妻,他和小白寡妇的周旋甚至让人生厌,成祥的性格并没有一个丰富的呈现。反而是对乡村的日常生活情景描写得鲜活生动,村庄里的洪水,街镇上的集会,衙门里的收捐,甚至夫妻间的打骂等都表现了北方农村广阔和粗犷的原生气息。总的来说,相比于短小精炼的短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在篇幅上显然有了更大的发挥,小说中对乡村人事的描写无不彰显着粗粝真实的气质,显示了广阔有力的生活质感。
这时期王林的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既以细致的观察写出了乡村中人事的复杂,又以充满生活气息的故事素材和语言呈现出了粗粝的气质,他的视角可以在广阔的乡村生活中自由转换,同时不妨碍他的作品反映出文学青年更加细腻和敏感的个人情怀。他善于“将乡村的人际关系、利益驱使下的人心悸动、乡村家庭生活中的无奈与苦痛等日常生活题材表现得淋漓尽致”[3]。这些小说标示了王林个人的创作风格。
二、 革命生活的真实呈现
在描写革命生活的小说作品里,王林主要关注革命背景下的日常生活情态,适时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风貌和革命工作的实施情况,同时能够对人物个体的心理活动加以细腻刻画。因此在这时期的作品里,我们不仅能够看到革命生活的紧张进行,又能看到个体的心理成长,这延续了他30年代早期对社会以及个体的细致考察。
王林有短篇小说描写了青年心理上的挣扎,述说了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有着深沉细腻而不失热烈的情感。如《一出自演自笑的悲喜剧》写主人公文容因为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看不到前途,怀疑人的作为产生的价值,决心自杀,跳下河的一瞬间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春雷》写已经成了太太的女主人公方玲见到了昔日的恋人洪渊,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充满斗志的革命青年,于是方玲就在是与丈夫依然过着锦衣玉食却死气沉沉的生活还是跟洪渊相奔到广大社会天地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之间纠结,最终,经过多次思想的挣扎和对自己内心的省视,方玲决定跟随洪渊去干革命,实现理想。作于1940年的《流星》写老友冯吉经历的革命与恋爱的矛盾,不稳定的战争生活中,他对恋爱的考虑和对自己思想的反省体现了自我成长中的痛苦。相比于《春雷》着眼于男女的情感纠葛以及对革命单纯的向往,《流星》对于革命的思考更加具有政治意味,心理的矛盾呈现为对自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省,恋爱在男女双方看来,也考虑得更加实际。这与王林在冀中地区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有关,小说的创作背景离不开他在革命生活中经历的阶级教育。整体上看,他作于40年代的小说对于革命生活的描写具有即时性,呈现了战争下的真实日常和革命工作的复杂性。
比如《一头牛四条腿》写了在双十纲领实行,坚持统一战线的情境下一个民事纠纷的案例。小说对于解放区乡村中难辨好坏的人际关系和革命工作实施的过程有着生动的呈现,以紧密的叙述表现了革命工作的复杂,如对双皂“里外人”身份的描述,真实地体现了统一战线环境下的工作面貌。另外,王林对革命生活的描写没有失去强烈的情感力量。如《十八匹战马》写出了战火中人与战马之间单纯善良的情感,在残酷忙乱的扫荡岁月里闪着人性的光点,村人想要保全马命的戚戚之心令人动容。《十八匹战马》没有《荷花淀》悠远淡然的美感,它的自然美体现在对生活现实的真挚描写,作品带有生活的质朴与原生的坚硬与柔软,它不是作家在艺术美、人性美的追求上进行的生活经验的有意转化,而是以最本真的情感灌入对生活的描写。这种对革命生活的即时描写在长篇小说《腹地》里得到了集中体现。《腹地》生动地还原了战时冀中地区的生活情景,如革命两面派的实施,选举活动的普及,剧场演剧的热闹,干部与群众的复杂心理、集体躲藏的紧张等。孙犁肯定“《腹地》是对冀中人民的一首庄严丰富的颂歌……作者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4]1-2。虽然结构粗糙,缺少细致的打磨,但我们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腹地》有着张弛有序的叙事节奏和强烈的情感力量。王林在严酷的环境中写下来的这部作品,正因带有生活元气的粗粝感和真实性,得以显出独特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腹地》遭受的批评更加体现了小说本身具有的区别意义。
总之,这些小说延续了早期的风格,王林对现实的生活素材进行真实的描写,赋予了小说粗犷的气质,结构没有达到完美,语言未加修饰,但能够从广阔的生活中发掘出精妙细腻的人生演绎,不乏强烈的情感力量和细腻的个人心绪。他既关照到了革命生活的宏大层面,饱含激情;又关照到了个人的革命心理,表现出了革命工作的复杂性。不似孙犁作品的优美,不似延安在地作家对战争的疏离,不似赵树理纯民间的叙述语调,它们代表了王林作为一个普通作家的价值和意义。
不可忽略的是,冀中的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林的小说创作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九四四年春,冀中的局面已经开始大的变化……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从电报上收到(以前只收到过新闻报道),并且油印成小册子组织学习。党委与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得到大大提高,对于文艺上的工农兵方向走上自觉。”[5]218虽然《讲话》在冀中地区没有立即产生反响,但冀中的文艺政策还是跟随解放区的文艺形势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王林身为冀中地区一个重要的文艺工作者,诸多政策文件②的号召不会不影响到他的创作。作品里粗犷中含有的细腻笔法不存,对于人的塑造有了对立性的痕迹。《红与黑》写工作团干部的反省,《夜明珠》用章回的形式写了复查工作团对地主的惩戒和对落后分子的教育。《火网下的一天》描写战争,通俗生动,但在这之余则有消解掉战争残酷性的嫌疑。《家庭会议》这篇小说里刻板果断的宋守业一心为党为革命事业,多年未回家,亲戚们想念他,见了他分外亲昵,但他“从心眼里嫌麻烦嫌啰嗦,总想跟表兄弟们谈谈组织生产,改造散漫的落后家庭,土改和自卫战争的事”[2]205,他挨排到各亲戚家走了一遭,亲戚们皆大欢喜,可是他挺懊丧,认为被这封建人情俗礼,把他的全盘计划打碎了。战争的残酷让家庭分离,革命事业的残酷则是亲情的浓厚被冲散,宋守业的不近人情之处远甚于他崇高的革命态度,这篇小说因为太显焦急的主题表达,反而失去了真挚与自然。1946年4月《十八匹战马》在《北方文化》第三期上登出,但删去最后一段,文章的结尾并没有写马被日寇掠去,大概是觉得战马被敌人掠去有损八路军的形象,这也许能够说明王林经历整风运动后的变化。
王林1949年以前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来的承续与变化,很分明地体现了他的小说创作轨迹。我们需要理解他的文学观念和革命心理,来解答他小说创作的深层原因,《抗战日记》无疑是最好的参考文献。
三、 日记与小说的互文
王林抗战期间的日记在他去世后被偶然发现,且未曾改动,经过整理结集成《抗战日记》后依然保持了原貌。吕正操称王林的日记记录下所见到的一切,本是为创作积累素材,如今却成为鲜活的冀中军民抗战图卷,并言其能留下来实属奇迹。整部日记内容丰富,“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6]1,不仅在于“将王林日记与剧作‘互文’,可以对当年冀中抗战宣传工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7],同时,将日记与王林的小说互文,可以对他的创作有更清晰的理解。
(一)独特的文学观念
王林在日记中所记种种,都为我们了解冀中平原抗日战争的细节提供了现实样本,也印证了王林描写革命生活的小说似风俗画,呈现了真实自然的生活面貌。这种追求真实性的写作一方面是因为彼时他的工作重心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无法细致打磨作品,更重要的是他秉持的文学观念决定了他对革命生活的这般描写,反映了他的创作实际并不仅仅只是在游击环境中作的调整。王林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均出于对文学价值的肯定和对写作的真诚追求。
王林肯定文学的伟大,作家的伟大,认为“文学是感觉感情的精神产物,潜意识中的活动是不自觉地起着决定的作用”[6]94“古典作品真乃人类性灵永恒不灭之光也”[6]81“艺术没有公式,为何先,为何后予人以此印象,全在作者之主观感觉”[6]81。他欣赏莎士比亚的文学创作,说其创作的主要大多数,“还是个性决定一切”[6]98。王林自信对于生活中小人物的熟悉程度,肯定贴近现实生活,接触广阔社会的做法,“关在房子里,是追索不出来的,我那不远离现实,深入现实的路线还是正确的”[6]193。对于作品的主题和思想以及人物如何塑造都有自己的见解,“凡以主题和思想为主的,都自然要走上宿命论的不自然的结局内,亦即专注于故事,把人物安在那个命运般的故事框子内,而人物只成了抽象思想的号筒。这虽然也可能是写实的,然而是宿命论的唯物论。以人物性格为主体的,是辩证唯物论的,是看重了主观认识的能动性的……”[6]98这些对文学创作观念的表述表现出了王林在文学上的苦心经营,他的小说创作也正是践行了这诸种原则。他肯定文学的精神力量和作家的主观意志,继承了沈从文在小说课堂上的教导,忘掉约束,用眼睛去观察,将一支笔运用自然,对人物的塑造和生活场景的描写都是以人为主体,发掘出了人性的弱点和闪光点,在粗粝中蕴含着细腻,写出了生活经验的鲜活。
王林对文学的思考还兼及他本人的革命者身份。他很早就参加革命,创作戏剧鼓舞观者的民族情感,在1939年就认为在这种犬牙交错的战争中,现今需要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剧作。“那种抽象的、一般的写法是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的……”[6]77问题是王林有政治意识却没有阶级自觉。对于革命者要坚持的阶级立场和在写作中体现阶级性,很早的时候他就有对自己的反省。“我十足地还保持着小布尔的心理和阶级感觉。这大概是我不能表现积极人物和行动自由主义的原因吧?”[6]94“我常暗暗自思,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在文体上还是企图学习莎士比亚、契诃夫、莫里哀、托尔斯泰等作家比较有可能,若是企图学习高尔基的文体,那是绝对不可能的。”[6]94他认为作家的成长中幼年的生活环境会一直影响人生,这是一种潜意识,即使后来思想发达,学习了高级的马列的思想方法,对于文学这种感觉感情的精神产物来说,潜意识中的活动是不自觉地起着决定的作用。这与他肯定文学的主观性和作家个人的伟大价值息息相通。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林在创作心理上进行的反思与适应不是整风期间才开始有的,他早些时候对革命要求的创作规范就有思考,只是无碍于自己的独立创作。但整风运动在冀中的到来,使得冀中地区的文学创作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产生了割不断的关联。
整风之后王林的小说创作有了变化,虽然还是来源于现实的素材,却失去了真实自然的气质,在“即时”之外亦有“应时”的追求。《抗战日记》呈现出了他的革命心理,可以对这样的变化有所解答。
(二)复杂的革命心理
王林对参与整风这个大潮其实心情复杂,原本是相机参与,“整风之后,就可以相机过路‘甘做孺子牛’了。否则两个月后才入校,再整个半月到一年,那就可把人整得‘心情不定、神经失常’了”[6]272,中间又肯定整风的作用,“应当将改造自己,改造现实的整风伟大运动,视为今天与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过去一贯地认为自己处在整风浪潮外,自己当作看整风的第三种人,太不对了”[6]297,后又消极看待,心理矛盾“整风迄今,情绪颇有更加麻痹之感”[6]302,“艺术至上主义与艺术自由论的观点,对我越来越起着作祟力量”[6]302。但在这样反复无常的心情之下,他还是决定按照原来计划,写一小说,名叫《万象回春》,象征毛泽东思想如春天的太阳,使得大地万象都成了春天,欣欣向荣。以党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为主线发展人物发展故事,“较比《腹地》要肯定容易投上时代之需要,在写的技术上也可能有个新的创造”[6]303。他在之后的小说创作就践行了投时代之需要,但是王林并没有在这样的适应中放弃掉自己的文学观念。
1947年的日记里,他记录了延安来的文艺领导对冀中文艺的指导及对他的作品进行的评价。比如3月20日记“昨日上午由丁玲主持讨论‘创造’问题如何在会上进行。大家好像有一肚子牢骚,却抑制着不肯说……中宣部的来电好似说座谈会以前的写作都是错误的。可是我只在座谈会前(我见到)写了两部长篇。这些大概在一笔勾销之内,所以不愿再提什么意见,只是找缝子说了几句怪话”[8]。说“难道就不写文学了吗?”[8]这样的怪话的王林此时对延安文艺政策持有自己的看法,其他人提出的文学创作规范只是听听而已,但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在政治范围的考量还是在意的。3月29日记周扬要王林以群众的感情兴趣描写事物以及风景。王林解释自己不是不能用群众的感觉描写事物,而是因为实写做了群众感情的尾巴。“周又说群众有落后的。我答村干部对英模的谈论也是批评多于歌颂。周说光是看见英模的缺点,可是群众怎么选举出来的呢,我说冀中的英模并没有经过群众民主选举,多半是区县村干部指定的。周无语。我又说村干部缺点,不是孤立的,有一定的社会原因。问题就是写干部缺点,写的少而给人的印象深。优点写了又写,仍然压不住缺点。另一方面即歌颂英雄而无血无肉,不生动。”[8]王林的写作是实写而非修饰,因此在周扬等人对他的作品提出建议和批评时,他的争辩显得极其有底气,足以证明王林在整风期间改造的“不彻底”,那么对于他那些投时代之需要的小说作品,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从日记的记录来看,王林很早就意识到自己在阶级觉悟方面的问题。他对生活和人生的关注远超于他对自身的内倾性描写,当文学创作以被规范的形式来要求时,他求真求实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规范要求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产生了冲突。对于王林来说,整风运动后的写作是将以往的纠结与思考最终转化为必须要践行的写作事业,整风后的小说创作实践是他在适应规范的文学话语过程中的转变之作。“知识分子常常被他的某种幻想、向往、冲动、对现社会罪恶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而走上革命。也可以说是自觉地走上光明斗争之路!”[6]153作为一个坚决纯粹的知识分子,王林的革命心理和创作心理产生的变动表现了他和众多作家一样,经受了文学规范带来的思维纠结,这其中包含了他对文学与政治语境的考量,对大的文学创作环境的接近。因此于王林个人而言,他的小说创作发生的改变并非始于《腹地》遭禁,整风运动对其的影响已有清晰的痕迹,只不过此时尚未有之后那么紧张的环境。原本追求即时记录时代的光和音的作家王林在整风后的创作依循《讲话》的文学规范,代表了整个解放区文学的日趋统一。
(三)文如其人的写作
除了对王林的文学观念有所呈现,《抗战日记》还呈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它很能表明王林的创作是文如其人,王林的小说作品体现出的隐含作者形象和他本人的气质极其相符。
王林的性格坦白直接,与作品里体现出的隐含作者形象很契合。日记中记有很多他对红军干部、商人等的认知和评价,他总能在紧张严肃的气氛里真实地表达自我的感受,率直豪放。有趣的亦有作者的恋爱心理与小说里恋爱观的一致。王林往往以单纯不做作的姿态描绘出男女在气性上的直接吸引,但又不流于本能。他对恋爱的描写都是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如胡三与春芝的爱情,成祥对小白寡妇展开的追求,辛大刚对白玉萼产生的冲动,男性向女性展开的追求简单粗蛮。因为王林作品整体都具有一种粗粝的美感,因此它在作品中并不显得很突兀,但这种由作品折射出来的人事男女,表现出了简单直接的爱情观。王林走入婚姻很晚,他对爱情的渴望显得非常强烈,又因考量过多,在对象的选择上便多有犹疑,作家本人直接甚至蛮横的爱情观正好与作品中对于男女恋爱的描写相对应。这样的比较仅作一个方面的参考,它能够说明王林作品里奇异的爱情观是如何从笔下发生的。王林坦白直率,同时有着细腻的感情。他对乡村生活中的人事非常熟悉,详查农民身上具有的思想缺陷,但抱有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比如“一提杀狗,农民在感情上很不高兴,受了一下打击似的:你看这不是性命吗?再一说也是人的耳朵啊,黑更半夜的有点事,它还有点用啊……你们杀你们的去,我们反正舍不得……公事?那还了得,那谁能反对……”[6]116-117他笔下的农民在小说作品里不完全是落后保守的代表,而是身上既有小农的短浅,又有发自内心的善良,表现出人性可爱的一面。吕正操著《冀中回忆录》中回忆了冀中部队的情况和参与斗争的大小细节,其中“打狗运动”一节从大的局面和最后宏观积极的结果出发,认为“打狗,也可以说是冀中一举三得的一个特种运动,不失为平原游击战的一个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9]155,叙述宏大热烈,与王林对群众犹豫细密的心思描写不同。这样粗中有细的描写源于王林作家的身份和他本身对生活抱有的热爱,他在宏大的注视里没有忽略微小的细节,在宣扬伟大之下没有忽略赞美发自内心的良善。这样的描写反而更能够体现出即使战争给人生活造成不幸,但人在低落的境遇中不放弃希望的动人之处。这些记录跟作家在小说里直率的评论语言,简单直接的两性描写和对战时环境下人性的温情描绘两相呼应,呈现了一个善良直爽,不善矫饰的写作者形象,充分说明了王林的小说创作是文如其人。因此,他的小说创作体现出的粗犷真挚的特征不仅有求真求实的文学观念做基础,亦是本人气质使然。
结语
对于王林的小说创作本身进行的分析清晰地说明了作家创作的文学审美意义及其与革命的紧密关联。这可以避免研究上的不合理之处,如长篇小说《腹地》,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王林的中心,大多研究都将其看成是王林对解放区文学规范的僭越之作,称其为解放区文学的另类。但是经过本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腹地》不仅是王林战时环境下的即时记录之作,也是他本人文学观念的自然生发之作。彼时王林尚未接触《讲话》,写作自成一体,《腹地》自然相融于当时整体上较为多样的解放区文学之中,它代表了解放区文学在受到规范和约束之前的丰富性,更与民国文学框架下的其他文学相异,称其僭越文学规范或是另类有预设之嫌。王林之后的创作也并非是受《腹地》遭禁影响,从而服从于文学语境那么简单。作家本人在后半生的创作固然陷于程式化,没有做出更大突破,但他的文学观念与文学语境产生的偏差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经历,其本人对文学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因此才会呈现出悲剧性的一面。任何对于王林的创作进行的主观预设的解读,都是因为忽略了王林的创作在变化中具有的承续性,忽略了整风时期的创作变化,忽略了以《腹地》为代表的诸多小说本身的意义。
总之,王林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现生动的情状,无论是30年代对乡村人事的描写还是40年代早期对革命生活的描写,都表现了他对日常生活的细致体察和宽厚的热爱,体现出粗犷真挚的特征。整风后的小说作品在阶级意识上逐渐走向自觉,影响了他对来源于生活的素材进行真实自然的描写。将王林日记与小说互文,可以看出他的小说之所以呈现出粗犷真挚的艺术风格,不仅是因为他秉持着求真求实的文学创作观念,亦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对王林1949年前的小说创作进行分析能更加具象地呈现出他在小说创作上的独特性,启发我们对他之后的创作经历和人生遭际有更深的探究。它们代表了王林作为作家个人的价值,代表了民国文学的丰富性,代表了文学的生命力。
注释:
①30年代也消、李影心、罗烽等人都提出了作品的疏漏。也消评价此书有些地方写得太平淡呆板了,穿插的地方,也不很灵敏。 李影心认为《幽僻的陈庄》所写是一种新的事实,用了新的技术,却沿袭旧的手法,而给与这书以最大的损害,即是缺乏一种表现的力,和处理事项和人物的不得法,也因此影响了作品完整的艺术价值。罗烽认为作者具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寻找出了代表各阶层各种类的人物,作者所缺乏的是对于这些人物更深刻的观察和体验,从这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上发掘出它们同“古旧的中国”和新事变的关联,指示出复杂多样的力量。见:也消《幽僻的陈庄》载于《清华周刊》,1935年43卷11期; 李影心《幽僻的陈庄》载于《国闻周报》,1935年12卷45期;彭勃(罗烽)《评〈幽僻的陈庄〉》载于《大公报》(小公园),1935年8月25日。
②如:1943年5月21日《晋察冀日报》载有《加强文艺工作整风运动,为克服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而斗争》一文,批评了艺术至上主义,指出党的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是主导地位。1944年5月4日,《晋察冀日报》发表《贯彻文化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的社论,其中之一就是强调进一步贯彻文艺整风运动。1947年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号召“封建地主的骄奢淫逸的滔天罪迹,农民受奴役剥夺的凄惨生活,觉悟后的农民的怒火,团结的力量、轰轰烈烈的斗争,在斗争中所涌现的群众领袖,农民自觉的成为主人后,更加积极勇敢献身于自卫战争……这一切可歌可泣的题材,可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创作,尤须多写适应目前斗争需要有现实效果的短小作品”。王林的《夜明珠》就描写了地主的负面形象。周扬在1947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央局关于开展文艺创作的决定,主题是确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而且只能写与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有关的主题,要大半是群众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和英雄模范事迹。重申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宗旨,要求文艺工作者关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生活。在群众文艺活动上坚持“群众的需要与自愿”的原则,而不应以文艺工作者的主观愿望、热情、兴趣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