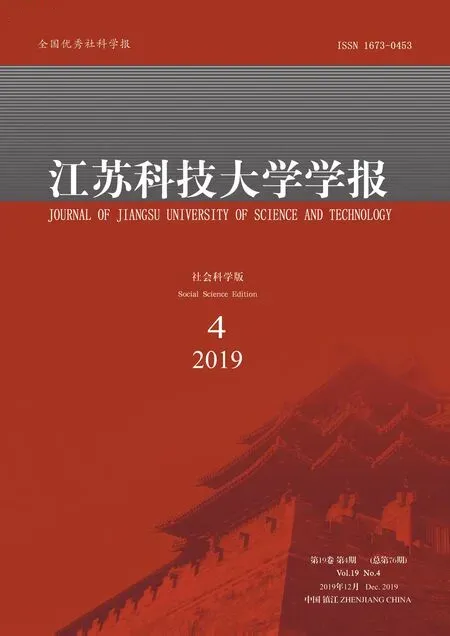略论西周到春秋聘礼赠贿风气之演变
王 睿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0)
《礼记》云:“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1]22这不仅是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家喻户晓的格言,也是人们交往的基本准则之一。在原始社会,“礼是商业性质的交往,有赠有报,有来有往,互通有无,施报平衡,故谓之‘礼尚往来’”[2]245。至商周时期,这种交往被政治化为“聘礼”,成为诸侯间、诸侯与天子间联络感情的方式。聘礼“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其详细过程载于《仪礼·聘礼》。郑玄的《仪礼目录》云:“大问曰聘。诸侯相于久无事,使卿相问之礼。”贾公彦《仪礼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聘义》:‘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问,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礼》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经云五介,又云入竟张旜,孤卿建旜,据侯伯之卿之聘者。”[1]573《礼记》中也有《聘义》专门论述聘礼之意义。郑玄《目录》云:“名聘义者,以其记诸侯之国交相聘问之礼,重礼轻财之义也。”[1]2334可见,聘礼之最初目的在于“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1]2340。
聘礼之往来在先秦古籍中表现为报礼、报币、报书、报使四方面[3]。其中,“报币”为物质方面之交流,聘问时,宾国须通过“聘”与“享”向主国赠送礼品;在聘礼结束时,主人家也须向来聘者赠“贿”,即是以礼物回赠。西周时期,诸侯之间、诸侯与王室的交聘往来是外交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礼书的记载体现着礼尚往来、对等性及重礼轻利等原则和精神。但平王东迁之后,王室衰微,五霸更迭,聘礼与其赠贿也有了不同的性质与意义,出现了如“厚来薄往”“厚来不往”等施报不平衡现象,其与霸主政治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
前辈学者对聘礼及赠贿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如,陈戍国的《先秦礼制研究》(1)参见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及《中国礼制史·先秦卷》(2)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书均对先秦聘礼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从有虞氏以前的宾礼源起开始引入,对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聘礼都有较详细介绍及论述;李无未的《周代朝聘制度研究》(3)参见李无未《周代朝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对周代朝聘的实际状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期研究,其中注意到了春秋朝聘政治功能的衰变,并讨论了朝聘的产生及夏代、商代的朝聘礼。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4)参见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中涉及到聘礼部分的论述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除上述研究著作外,还有许多论文也是专门讨论聘礼的。如,黎虎的《周代交聘礼中的“礼尚往来”原则》一文从报礼、报币、报书、报使四个方面研究了周代交聘关系中“礼尚往来”的原则[3],《周代交聘中的对等性原则》一文从交聘主体、接待人员、接待礼节等方面探讨了聘礼的对等性,并从文化、制度、思维等角度对产生对等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4];马卫东、张林《周代社会中礼物的功能及其流变》一文认为,从西周到春秋,礼物的形态与功能发生了改变,从西周的表达性功能转变为功利性功能[5];张亮《周代聘礼研究》一文中论述了聘礼在西周至战国时期的实施情况[6],其在《略论春秋列国聘问施报之不平衡与聘礼的衰亡》一文中归纳了春秋时期聘礼施报不平衡的特点及聘礼消亡的发展轨迹[7];韩静在《春秋时期的朝聘礼赠研究》一文中,从聘礼的形式、内容和天命观等层面分析了春秋时期朝聘礼赠变化的原因与过程,并论述了礼赠在邦交、战争等方面起到的作用[8];郑春生《朝聘礼制管窥》一文以《左传》所记聘礼事件为根本,深入探讨了称谓、目的和仪式等问题[9]。总之,成果众多,不一而足。但对于聘礼的研究大多只是涉及朝聘的称谓、类别、功能及各个时代特点,对于赠贿的专门论述很少见到,更多还是停留在以赠贿说明聘礼仪节变化的阶段。基于此,笔者尝试从聘礼赠贿之风气由礼尚往来变为厚来薄往这一视角进一步探讨春秋礼崩乐坏的时代特征,以期能为礼制研究增砖添瓦。
一、 礼尚往来:赠贿与还玉
“贿”字,《说文解字》将其释为“财”,又常与“财”“货”等字连用以表达器物、财货的含义。“器用财贿”在《左传》中是常用语。如,隐公十一年,秋七月,鲁、齐、郑三国灭许,“郑伯使许大夫奉许叔以居许东偏……又使公孙获居许西偏,曰:‘凡而器用财贿,无寘于许。我死,乃亟去之’”[10]75。文公六年十一月,赵盾使臾骈送贾季之妻归狄,臾骄“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亲帅扞之,送致诸竟”[10]553。同时,“贿”字也表达遗人以财物的行为,在聘礼中,它是临别时的馈赠,以答谢宾之来聘,是宾返回时的赠礼,是聘礼中体现“尚往来”的重要仪式。
礼在交往之时,双方一定以尊重对方的存在、对对方怀有敬意为前提,所以必然“尚往来”。“往来”即是交礼双方的互动与回报,故《礼记》云,“乐也者,施也。礼也者,报也”[1]1508。“故礼有报而乐有反。礼得其报而乐,乐得其反而安。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1]1843这些都是强调礼必有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交往时的礼就是报。
赠贿过程中体现的原则正是“礼之报”。《聘礼·记》云:“凡庭实随入,左先,皮马相间可也。宾之币唯马出,其余皆东。多货,则伤于德,币美,则没礼。贿,在聘于贿。”郑玄注:“贿,财也。于,读曰为,言主国礼宾,当视宾之聘礼,而为之财也。宾客者,主人所欲丰也。若苟丰之,是又伤财也。《周礼》曰:‘凡诸侯之交,各称其邦而为之币,以其币为之礼。’”[11]736-738胡培翚《正义》疏解:“云‘言主国礼宾’者,释经贿是主国礼宾也。云‘当视宾之聘礼’者,释经在聘,谓在宾聘财多少。云‘而为之财也’者,释经于贿也,谓主人视宾多少,为财贿报宾。云‘若苟丰之,是又伤财也’者,凡行礼为财者,取不丰不俭,取于折中。若苟且丰多,则伤于贪财。”[12]“多货,则伤于德,币美,则没礼。贿,在聘于贿。”[11]738这三句为理解赠贿的枢机:玉回赠多了,超过宾国之聘享,则伤败德行;束帛比宾国所送的华美,就会淹没礼意,显得重物轻礼;回赠宾国的财物数量当视宾国赠送的聘礼轻重而定。也就是说,无论国之大小、实力强弱,均要平等相待。
除上面的一般情况,《聘礼·记》又云,“无行,则重贿,反币”。郑注: “无行,谓独来,复无所之也。必重其贿与反币者,使者归,以得礼多为荣,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币,谓礼玉、束帛、乘皮,所以报聘君之享礼也。”[11]749此言之义为,若宾国只聘一国而不再去往别国,那主国国君要重礼回报,还要将宾国所献礼物全数返还。如襄公二十年,“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10]1054。此即是“无行则重贿”。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即人有礼义高于财物者也。
跟赠贿同时进行的还有还玉礼。在聘礼开始时,“宾袭执圭,摈者入告……公侧袭受玉”,“宾裼,奉束帛加璧享”[11]620-633。即,宾国使者对主国国君需以圭聘之、以璧享之,对国君夫人也需以璋聘之、以琮享之。此时,主国国君要派卿大夫把宾国的圭、璋、璧、琮归还使者。如此繁复严格,其义深也。《礼记·聘义》云:“以圭璋聘,重礼也。已聘而还圭璋,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1]2341“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1]2346-2347郑玄引之,注还玉曰:“玉,圭也。君子于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礼也。还之者,德不可取于人,相切厉之义也。”[11]689
聘享的四种玉器也不能拿普通的物件应付了事。《聘礼·记》云:“凡四器者,唯其所宝以聘可也。”[11]732即交往之时,无论国力强弱,都要拿出自己最宝贵的玉器以示其好。《礼记·聘义》曰:“古之用财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财如此其厚者,言尽之于礼也。”[1]2341可见除玉器外,赠予主国的其他财帛礼物也要贵重华美。《聘义》又曰:“尽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则民作让矣。”[1]2343此即聘礼本义,同时又体现出礼的教化作用。
由此可见,礼书记载的聘礼体现礼尚往来的原则,主国、宾国的赠物与回赠要按照有施有报、施报平衡的标准进行,且赠贿数量要与宾国礼品多寡、礼节隆重程度对等。
《左传》中只出现了“贿”“厚贿”等词,没有发现关于“还玉”的记载。如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一事。杨伯峻认为,“依聘礼有还玉及赠贿,此不言还玉,或视为当然而省略之”[10]589。《仪礼》是孔子后学教人行礼的教材,行礼仪节需概备无遗。《左传》因其史书体裁,对礼之记载多着眼于史实本身,礼仪的具体内容并不是其关注重点。因此,二书对聘礼仪节的记载出现差异是很正常的。《左传》虽未出现还玉礼,但从出土的金文材料(5)如西周颂鼎铭文载:“受命册佩,以出,反入堇章。”郭沫若谓:“反入堇章当读为返纳瑾璋……盖周世王臣受王册命之后,于天子之有司有纳瑾报璧之礼。”即类似还玉之礼。参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两周金文辞大系(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及《仪礼》成书年代(6)参见沈文倬《菿闇文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6—58页。来看,还玉礼应该是确实存在的,也确如礼书所载。
二、 厚来薄往:春秋之“礼”
平王东迁,天子与诸侯关系性质随之发生变化,西周及礼书所载之原则随时代变化渐渐成了空话,此后聘礼的实施与礼尚往来、重礼轻利的精神基本不再相符,聘问与赠贿的政治意图日益浓厚,聘礼的实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最终导致了春秋末期聘礼的衰亡。
王室衰微,对小国而言,霸主的重要性已远超周室,因此中小诸侯具币往聘霸主是春秋聘礼的主要内容,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聘问不占重要地位,双方聘问并不多见。但是,自天子本身开始,聘礼与赠贿就已经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如宣公九年,“春,王使来征聘。夏,孟献子聘于周。王以为有礼,厚贿之”[10]701。此即周王室为昭示“天命未改”,征召诸侯去聘问天子以显示其政治地位,故对鲁国厚加赠贿。此时,天子的贿已不再是“礼尚往来”的回礼,反而充满了政治意味。有了政治目的,礼的原则自然就随之破坏。从聘礼次数上也能窥知对“尚往来”原则的破坏。纵观《左传》,仅隐桓之世天子就聘鲁五次,整个春秋时代鲁却只返聘周四次。像上文所言天子征聘之事至鲁宣公十年后也再未见诸史料,以鲁知天下,礼之非礼,概可见矣。鲁不聘周之事也招致了经学家的批评。如,程子曰,“诸侯不修臣职,朝觐之礼废,不能正典刑,而返聘之,又不见答,失道甚矣”[13]346;赵与权曰,“五年之中,周三聘鲁,而鲁使未当一至,春秋伤周责鲁之意隐然矣”[13]346。
王权衰落的同时,五霸更迭,霸主政治深深影响了聘礼与赠贿的风气及内涵。诸侯聘问之礼虽仍可谓交邻国之道,却也不再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而是变成了政治目的性极强的外交手段,其赠贿情况也日益复杂。
齐桓称霸时,赠贿虽已开始掺杂政治目的,但大抵还是重其礼义——“薄来厚往”或者“厚来厚往”,且霸主对小国并无过多经济上的苛求。《国语·齐语》云:“(葵丘之会后)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个。诸侯之使,垂橐而入,稇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14]239由此可知,此时的贿与赂虽然有政治上的目的,但确实是轻币重礼的。
春秋中期晋楚争霸的局面逐渐形成后,诸侯间的聘礼与赠贿产生了新的变化,大国责贡,“府无虚月”;小国“聘而献物”,“职贡不乏”。小国聘大国,次数众多,施多而报寡,厚往而薄来。在诸侯国的聘礼之中,赠贿俨然成为了政治手段。有主国君主出于特定目的以赠贿收买宾国大夫的。如,僖公十年秋,晋惠公即位,其先使丕郑聘于秦,又杀丕郑同乡里克。丕郑不满,谓秦穆公曰,“君厚问以召吕甥、郤称、冀芮而止之,以师奉公子重耳,臣之属内作,晋君必出”[14]306-307。注云:“问,遗也,以厚礼问遗。此三人皆晋大夫,来因留止也。”[14]306-307欲以废惠公而立重耳为晋君。“穆公使冷至报问,且召三大夫。”[14]306冀芮曰:“郑之使薄而报厚,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诱我……”[14]306-307有小国频繁聘问大国,以向大国寻求帮助,求生存,求自保。如宣公十年,孟献子言于鲁公曰,“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见贿,贿则无及”[10]757。有小国向大国“加货”,即缴纳大量财物,以免己国之罪。还有霸主借小国来聘显示霸主地位的,如若小国不来便出兵讨伐,因而《左传》中出现诸如“晋人以公不朝来讨”[10]522“晋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晋人止公于会”[10]692等记载。
晋国称霸时,甚至规定了朝聘次数与贡赋数量。襄公八年,“五月甲辰,会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数,使诸侯之大夫听命”[11]335-336。襄公十二年夏,“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10]1232。又文公四年:“曹伯如晋会正。”杜注:“会受贡赋之政也传言襄公能继文公之业,而诸侯服从。”杨伯峻注云:“盖当时小国诸侯有向霸主纳贡赋之义务,因以定其额也。”[10]533由此可知,聘礼已成为小国对霸主不可豁免的定期贡赋,已背离“礼尚往来”与“外不相侵,内不相陵”的初衷。
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后,晋国公室卑而政在侈家,诸侯贡赋之轻重取决于执政卿大夫,晋国对诸侯的聘礼贡赋要求更为苛重,且政令无常。襄公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郑人公孙侨曰,“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10]1067。襄公二十九年,晋司马女叔侯云:“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10]1160与此对应,《左传》中常有“币重”之言,“币重”即是小国不堪重负矣。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虽经子产“寓书”,乃轻币。次年,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10]1089-1103,但各诸侯小国仍然不堪重负。因朝聘贡赋“列尊贡重”,故小国往往自贬降以省贡赋,如桓公十三年,“子产争承……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10]1358。以男爵自贬,可见贡赋之重,更可见聘礼与赠贿之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厚来薄往”风气的形成还表现在聘问次数上。通考《春秋》《左传》,鲁受聘41次,晋受聘37次,齐受聘22次,周、宋受聘各六次,楚、郑、卫受聘各五次,秦受聘三次,越、陈受聘各二次,莒、邾、牟、吴、邓受聘各一次。因《春秋》《左传》为鲁国史书,记载鲁国史事必然详细,而他国之事依“不告,亦不书”的原则,对于各诸侯国之间正常聘使往来的记载自然缺失有甚。分析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晋受聘独多。这是因为自城濮之战以后,晋国长期称霸中原,不但鲁、郑、宋、卫等实力较弱的国家入晋聘问,齐、秦等强国迫于晋国的军事压力也不得不遣使聘晋,而晋赠贿之事却不见诸史料。这正是“以弱事强”的表现,也是“厚来薄往”的表现。
大国聘小国却是另一番景象。以晋聘鲁为例,晋强鲁弱,两国聘问施报之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鲁聘晋有24次,而晋聘鲁仅11次,从聘享与赠贿亦可窥知。鲁襄公十二年,“夏,晋士鲂来聘,且拜师”;冬,“公如晋朝,且拜士鲂之辱,礼也”[10]996-997。昭公二十一年,“夏,晋士鞅来聘,叔孙为政。季孙欲恶言诸晋,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士鞅怒……鲁人恐,加四牢焉,为十一牢”;冬,十一月,“公如晋,及河。鼓叛晋,晋将伐鲜虞,故辞公”[10]1425-1431。晋卿聘鲁,鲁君必回聘晋,拜晋卿之辱。而强国来聘,弱国敢有礼薄之处,强宾稍有色作,则弱国朝野震恐,一介大夫强横犹如是,则强聘弱可想而知。大国与小国这种“厚来薄往”“厚来不往”的交往方式随着聘问变为贡赋成为必然。小国对大国的聘礼性质已变,礼之原则已不存,这意味着“尚往来”原则的赠贿仪节自然也不会继续存在。
至春秋后期,霸主愈加富强,小国愈加贫弱,以致难以承担聘礼重负。且诸侯纷争渐起,旧日霸主已无力或不愿承担责任帮助弱国,小国继续朝聘大国就变得无益且无必要了。小国犹有前往聘问者,大多成为大国内部卿族斗争的牺牲品。如定公六年,宋出于“诸侯唯我事晋,今使不往,晋其憾矣”之目的,遣使乐祁聘晋通好,但由于讨好赵氏而得罪范氏,乐祁被囚晋国三年[10]1558-1559。在这种情况下,春秋末期聘礼逐渐消亡。定公十五年,“吴之入楚,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为?多取费焉’”[10]1601。这表明了小国对聘礼的漠视心态。当然,结果导致“二月,楚灭胡”[14]1601。
进入战国,大争之世,列国伐交频频,均欲先灭他国而后快,变法图强成为主流,大国战争成为时代主题,礼之精神、原则彻底衰败。
三、 聘礼赠贿与春秋礼义精神的衰亡
“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1]2057报,即谓礼也。当初“制礼者”之初衷,是为了使各国通过聘礼与赠贿互通有无,以结友好,其内涵即是“礼尚往来”。如彭林所说:“礼的精神,是以谦虚恭敬的态度尊重对方,希冀对方能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15]
在春秋之前,国与国在聘问时,是按照礼的精神行聘礼的,以此交换宾国的赠礼与主国的赠贿。更为重要的是,贵族们重礼义而轻物质,譬如,当他国单独来本国聘问时,无论对方礼物轻重,本国不仅要全部归还,更要重重回赠,而且在赠贿的同时要将宾国所赠象征德行的圭、璋等玉器一一归还,以示轻财而重礼之义。此时遵行礼之贵族,可称君子。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尚往来”不仅是简单的一种来与报,它所产生的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人际和谐。至于春秋,天子式微,大国争霸,小国图存,礼制陵夷,聘问与其赠贿渐渐成了政治军事手段,成为一种服务自己利益的务实性外交。天子以重贿讨好诸侯,小国借聘问逢迎霸主,终竟演变成聘贿以致贡赋的局面,聘礼因此也被时代所抛弃。
“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19礼是人类文化自觉的开始,人之为人,即是不断地通过学习,遵循以礼为代表的后天人性,克服天性中诸如贪婪、残忍、恶斗等兽性。随着礼崩乐坏,“礼尚往来”不再被遵循,礼不再是报,而成了获利手段,“厚来薄往”成为大国显示实力之荣耀。至春秋末期,礼在贵族心中竟变成了“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10]1266之概念。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春秋乱世时也称其因在于“失其本”,即破坏了礼制,不再遵循礼义精神。
牟宗三曾经说过:“其实贵族有其所以为贵的地方。一般看相算命的人也知道贵和富是不同的。贵是属于精神的,富是属于物质的。由此可知,贵是就精神而言,我们必须由此才能了解并说明贵族社会之所以能创造出大的文化传统。”[20]
庶民受教程度不足,经常有意无意地消除礼之限制,而君子、贵族们应当深知并固守礼之本义。当贵族们也不再遵循礼、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转而追求钱财等物质层面的东西时,贵族就不能再称其为贵族了,礼之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但所幸“礼尚往来”等礼义精神没有随春秋贵族的消亡而一起消失,自汉唐以来,其始终为人与人、国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并为后世所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