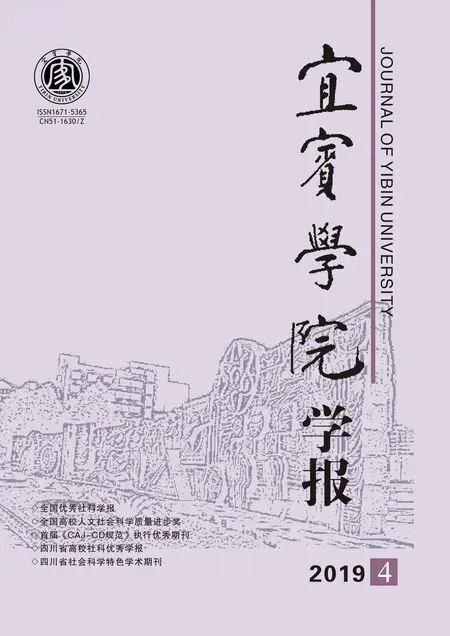家庭是形式
——唐君毅家庭哲学思想
陈张林
(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101)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君毅被牟宗三赞誉为“文化意识宇宙中的巨人”。他以其强烈的文化意识,建构起了庞大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其中,他首论家庭,并将家庭生活视为文化活动形成次序之首位,其重点则在“论孝友之意义及家庭关系之当求恒常之理由”。该内容实超出此前思想家之贡献,“可谓皆发前人所未发者”[1]自序二,18。
在唐君毅看来,家庭是中国人首要的生活单位。它既是个人走向社会的开端,又是人生的归宿。因此,家庭及其日常生活并不是追求其他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即具完整的价值,亦即其自身即为一目的,就值得追求。对于这个意思,唐君毅说道:“儒家之所以重视日常生活,乃源于儒家之自觉的肯定全幅人生活动之价值,而教人之贯注其精神于当下与我感通之一切自然人生事物。此即使一切人生活动皆可自身为一目的。夫然,而饮食、衣服、男女居室、劳动生产之活动本身亦皆可自具备一价值而非可鄙贱,亦不只视为一谋身体保存、种族保存之手段。”[2]180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中,人的所有活动,并非呈现一个手段与目的的序列,而是各自都有其独立的目的价值。但这并非否定超越的精神生活。形下的日常生活与超越的精神生活对于儒家而言,是相配合而和谐的。如果超越的精神生活不能充满、贯注于形下的日常生活,则精神生活易陷溺于空虚,甚且“精神之有所跨过而有所泄露。由此泄露,而有所鄙贱。则阻滞其情之生动活泼,而有一自虐虐物之念潜滋暗长”[2]181。而如果形下的日常生活不能跃升至超越的精神生活,则容易沾滞于表面之物事,使生命压缩、僵化,抹杀了生命的创造性。对于儒家而言,“人之道德修养,即赖在日常生活中礼乐之陶养”[2]179。在唐君毅看来,儒家在历史上之成功处,也正在于其“能融摄礼乐文化生活于人民日常生活”[2]179。换句话说,传统文化的生机恰在于其日常生活化,在柴米油盐、行住往来之日常生活中为百姓所重复遵守与践行。这种精神生活与日常生活之相和谐,一方面表现在“仁义礼智之德性”,一方面表现在“吾人之活动本身美化而艺术化”[2]181。此种日常生活之美化、艺术化,从“文”与“质”的关系说,则可说:“文必附乎质,质必显乎文。日常生活为质,精神文化生活为文。文质相丽而不相离,即中国文化之精神之一端。”[2]182日常生活由此德化、美化而富含文化意味,有了精神之意义。
日常生活之常态,乃为家庭生活,是为家庭日常生活。家庭日常生活亦因其上述文化意味而有精神性。中国文化擅长从家庭日常生活中“发现至高之精神文化上、社会人伦上之价值”。这是儒家尊重自然在家庭方面之生理关系之尊重的表现。而家庭日常生活,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生活。正是从此家庭日常生活的精神性、道德性上,唐君毅构建了其家庭哲学。
一、家庭成立之根据
尽管儒家尊重自然的生理关系,而且家庭成立的起源处也的确是依据自然生理上的关系(即性本能),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儒家所谓的尊重家庭即只是尊重性本能,尊重种族之繁衍呢?当然不是。唐君毅说:“家庭之成立,初固依于男女生理的本能。然中国儒家思想所发现、所建立之家庭之意义与价值,则纯为社会的、文化的,以至形上的、宗教的。”[2]148在唐君毅看来,性本能之说仅只能解释家庭之所以出现的生理原因,而并非家庭成立的根据。恰恰相反,家庭成立的根据正在于超越性本能上而得挺立。
那么,这种超越性本能的根据是什么呢?是道德理性。唐君毅说:“吾之所以说家庭成立之根据在性本能之超化以使其道德自我实现者,盖家庭之成立,乃处处根据于性本能之规范以实践一道德。”[1]63儒家并不否认人的自然属性,正所谓“食色,人之大欲存焉”。但就在规范“食色”上讲,即将此自然属性上提跃升至文化层面,而彰显人的社会性、精神性。由此而建立人的家庭意识。家庭意识的实质乃是道德意识。道德意识即是道德自觉、道德理性。道德意识、道德理性的指向在于建立、完成人的完满之人格,即道德自我。所谓道德意识,即是指自己自觉自己该做之事、支配自己以过道德生活之理性。唐君毅说:“什么是真正的道德生活?自觉地自己支配自己,是为道德生活。”[3]15这是自做主宰,自己规定自己的生活,是绝对自律的生活。简言之,自己支配自己即是道德意识、道德理性,此支配过程之显现即是道德生活,甚至可以说道德生活全幅即是道德理性,或反过来说,道德理性全幅即是道德生活。道德自我通过道德意识、道德理性所觉悟之善之延续、重复、充大而建立:“吾人有自觉的道德意识之见证,则此潜伏之善为我所自觉,遂得真对我为善而被保存。保存之,即延续之重复之,以充大此善之量。故吾人之自觉的道德意识多一分,则善之量充一分,大一分。……道德意识之发展无丝毫之间断,其中无不善之存。而吾人之道德自我之建立即成为一绝对之历程,而达至诚无息纯亦不已之至善境地。”[4]448-449如达至此境地,则可说道德理性、道德意识、道德自我而为一。
道德生活的开端在家庭生活。道德活动,从逻辑上说始于夫妇之爱情,并延续至父母对子女之爱,扩展至兄弟姐妹之爱,以使父母兄弟姐妹间的配偶(性本能)关系不相乱,从而构建起基本的人伦关系,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人伦之始亦家庭之始,家庭之始即同于禽兽之本能之节制与规范与超化之始也。”[1]68那么,为什么有家庭?没有家庭行不行?家庭于人而言为什么是必然的?
为了说清楚这种必然性,唐君毅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他认为,家庭之所以是家庭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是人的性本能之形式:“性本能至多为家庭成立之质料因。而家庭之所以为家庭,其开始一点即在节制规范此质料。家庭之所以为家庭,纯在其形式。此形式乃人之精神活动道德活动自己建立,以约束提防条理原始之性本能,并实现吾人精神活动道德活动之道路。”[1]68家庭是形式,这是唐君毅很深刻的思想。家庭并不仅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那样,认为它只是一个社会的细胞,是一个组织。在唐君毅看来,家庭是我们精神活动、道德活动条理规范原始性本能之格式。也就是说,家庭不仅是存在论上的组织,还是功能性上的形式。作为家庭成立根据的道德理性,当然并不是从性本能的现实意义中引申出来的,而是使性本能不再是原始性冲动,从而使其具有了形上学意义。
唐君毅尽管借用了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概念,但他认为在西方哲学语境中,形式是“悬空”的。在他理解,形式之所以能成为形式,在于其“持续”。——形式的要义在于其能不断保持。也就是说,家庭之形式是整体而言,分而言之,则有夫妇之形式、父子之形式、兄弟之形式。形式之能为形式,就在于“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之持续上”。而所谓“持续”,并不是自然血缘关系上的自动延伸,而是“自觉的保存与预期之精神的努力道德的努力之事”。家庭之形式正在此种自觉地维护、护持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的道德努力中得以表现,而得以支持与保证,由此而不虚悬。简言之,家庭既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的限制者、超越者,又是其自觉的道德活动所彰显者、实现者。家庭是个体性本能条理之形式,而个体以道德活动体验此形式、确证此形式,并因之而保持此形式。于此保持之努力而可见家庭意识:“故家庭之意识即一维持家庭之形式之意识。”[1]69于是家庭意识也正是家庭道德意识、道德自我,或者说道德意识、道德自我呈现于家庭。而个体依此家庭意识必超越个体而含摄家庭其他成员并条理化其关系。个体因此而自觉自己为家庭之一分子,为一受其他成员限制并共同维护家庭之形式之保持者。有此家庭意识之各个体彼此之间就须“节制、忍耐、牺牲,而相互之间则有同情互助相敬之事”。也正是在此“节制、忍耐、牺牲”使得自我不仅重视家庭之形式,而且在此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其道德意志、道德自我。[1]70换句话说,家庭中各家庭成员以家庭意识而相互自我节制、忍耐、牺牲,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没有作为形式之家庭、持续家庭之形式之家庭意识,道德理想主义也就落了空,而个人之成德当然也就无处着落。
那么,在家庭中,个体是如何进阶其道德意识、道德自我的呢?唐君毅认为要经过两重超越。他认为,道德活动其实是“吾人能以对方之心为心而实现超越自我之意志”。正是在以对方之心为心的实践过程中,自我完成了个体之超越而融摄了他人。这种融摄包含两个阶段、两种内容:“盖以对方之心为心,一方固包含对对方欲求之肯定,望对方之得所愿。一方亦包含对对方道德意志之肯定。”[1]70也就是说,在家庭生活中,既要肯定人的自然欲求,又要实现人的道德自我;既要现实化,也要理想化,——理想的超越性就蕴含在当下的实然性之中。在第一重超越中,个体以自己之道德理性出发而超越自己之欲求,以满足家人之欲求,由此而对自己之欲求予以节制、忍耐、牺牲。——否定自己之欲求。在第二重超越中,个体自觉到家人同样依据其道德理性而望自己亦能满足自己之欲求,家人同样对其欲求亦会加以节制、忍耐、牺牲,于是转而以家人之心为心而肯定自己之欲求,以满足家人之道德理性之伸展抒发。——肯定自己之欲求。经过肯定家人之道德理性而肯定自己之欲求,使自己的道德自我又得到跃升,实现了道德自我之绝对超越性。于是个体之道德理性、家人之道德理性都得到了全幅的实现,都各自肯定了家庭之形式,都自觉其为家庭之一分子,家庭成了实现道德理想的适宜场合。而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家庭物质生活,不复为满足自然之欲求,乃道德活动之展示。对于这样的过程,唐君毅说道:“故吾人真正通过对方之心以为心,又将顺吾人对对方之道德意志之肯定,转而再肯定吾人之欲求。”[1]70之所以要经过两重超越,是因为在第一重超越中,仍只是肯定己之道德理性而未肯认对方之道德理性,由是不免有自私之弊。此时之道德理性乃半截子的道德理性。只有经过第二重的超越,以己之道德理性融摄对方(家人)之道德理性,道德理性由是而得全幅伸展,是为道德理性之自我超越,是“超越自我之绝对超越性”。这样,各个体在家中既实现了自然之物质生活,又实现了精神之道德生活,使得个体在家庭中既能畅遂生机而成就自然生命,又能自我超越而成就道德理想生命。于是自然生命因道德生命而光辉充盈,道德生命因自然生命而立地挺立。家庭由是而成为人一生所不可或缺之形式。唐君毅由此也就论证了家庭的永恒性:“了解家庭成立之根据,即知家庭对人为一必须有之存在的组织,亦一对人永当有之存在的组织。盖家庭成立之根据,即在吾人之道德活动精神活动,乃所以实现吾人之道德理性者,则吾人之道德理性为永恒者,家庭即当为永恒者……吾人唯一可否定家庭当存在之根据,唯在吾人之可无性本能。若吾人无性本能,则家庭之形式无所规范,亦无所寄托而表现。然人若无性本能,则根本无人类之相续生……现在之人皆父母所生,即皆在家庭中存在,即皆对父母兄弟有责任,人对此家庭仍有维持存在之责任当实践家庭中之道德。故家庭之存在与家庭之道德,乃人所不可离。人存在则家庭存在,家庭之形式对人乃一永恒规范形式,故家庭之道乃人之无所逃于天地间之道。”[1]74-75
二、家庭道德及其形上根据
既然家庭乃人之所不能缺者,而我们习惯上往往又从己身之性本能的欲求和延续子孙的目的着想,使得家庭似为可有可无之组织。因此,从上述所言之家庭意识(道德理性)而论家庭之所必须、所不可或缺,乃是从改变视角带来的结果:“……须打断人向下看、向前看、以论家庭所以存在之论。吾人之论家庭所以存在之根据,唯归于人之不能亦不当无家庭意识。人之不能不当无家庭意识,乃依于吾人之皆当向上看向后看……”[1]37-38向上看、向后看,就会发现人皆由父母所生,并由此而意识到在己身之前即已有父母所建之家庭先存在。这个逻辑是理性不容不承认的。我们也就由此而建立起了确定不移的家庭意识、家庭道德。从这种向上看、向后看的视角出发,唐君毅主要阐释了家庭道德的三大内容及其形上根据:一为夫妇常道与变道,二为孝之形上学根据与其道德意义,三为友之形上学根据与其道德意义。
(一)夫妇常道与变道
这里所谓常道指的是夫妇关系之持续。而夫妇关系之断裂(离婚)是变道。唐君毅提出,夫妇关系是应当永续不断的。理由有三:一是从子女端说。夫妇因爱而结合,而生子,故爱其子。爱其子则当以子之心为心。而子之心当爱其自己,由此而知父母之爱本身亦可爱,以是期望父母能够继续如此这般的爱下去。父母以子之心为心,则应求婚姻关系持续不断。二是从父母端说。“人皆爱其父母,则子应以父母之心为心。”这就是说,父母因爱而生子,也会期望子之因爱而结婚、生子,因此体父母之心则亦应求婚姻关系持续不断。三是从夫妇自身之关系说。由于人有自觉能力,因此对于起初之“形色之慕悦、生理之冲动”而爱具体对方之男或女,转而“对相爱之关系之爱”,即对爱之爱。此是超越性本能之爱。此种爱首先表现为对婚姻之对方的照顾、体贴,由此而产生对己之节制,并引致对方对己之节制之感恩。由感恩意识的产生而使“夫妇间之情感之累积,与道义关系之加强”。夫妇双方都以此道义意识而建立起相互信任之坚贞。至此,夫妇即以此“坚贞互信之道德”规范彼此关系。对于上述历程,唐君毅有明确阐释。他说:“男女之间从本能欲出发之爱,通过爱之爱,至道义关系之形成,至道义之限制本能欲,整个是一道德生活之发展历程。在常态婚姻中,此种发展乃为无间隙而逐步上升者。至坚贞互信而道义关系乃居主位,本能生活即统于道德生活,而夫妇之道即完成。”[1]41在唐君毅看来,男女结婚后并非就是一直不变的直线型静止状态之关系,而是一个进阶的、由本能欲而最终达至道义关系的发展历程。此一历程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夫妇双方不间断地努力以实现之。因此,夫妇之道“以永续坚贞为常道”。
男女婚姻既以永续为常道,则不得已之离婚即为变道。需注意的是,唐君毅并不否定离婚。他认为常道固当遵循,而变道亦非不道。但是行变道的条件在于自己之良心,只要良心自觉理由无可疑则可为之。而如果一个人处在可行变道之条件下却自我牺牲以行常道,那么这个人简直就是世之模范,是为更高的道德。唐君毅由此不仅对那些守贞节者充满了崇敬,也对那些再婚之人充满了肯定。总之,他认为对待变道的态度,应该是“君子尊贤而容众”。这样才不至于抹杀各种层级的善良,不会像古代那样流于残刻而以理杀人。
(二)孝之形上学根据与其道德意义
孝是人向上看向后看而对最切近之父母所产生之爱敬情感及其相应行为。人们论孝往往是从对待的角度,或是人类学上的发现,而否定孝之必然性。唐君毅则认为孝之为孝自有其当然性、必然性。那么,孝的根据何在?何以谓其为必然?欲显此根据,唐君毅认为应从现实之我之“返本”入手。所谓返本,就是指理性地返回到我未出生之前之生我之父母那里,由此而实现超越自我并以此超越而观现实之自我之过程。这种以超越自我而观现实自我乃是道德活动的必由之路,是诸善之源。由此返本而意识到在我未出生之前,只有父母存在而我不存在。只有父母存在之时,所谓的“我”即是父母之我,也就是说我以父母之我为我;以父母之我为我,即意识到超越自我,无我、忘我,父母之我即我之我。——我与父母本为浑然一体。父母乃是超越之自己。孔子说仁乃“爱人”。那么爱从最初是如何显现的呢?唐君毅说:“在现实世界中人皆知爱我,然道德生活之开始,即以超越单纯之自爱而爱他人。人能爱他人之根据,在能忘我而以他为自。”[1]44在最初的能“以他为自”的地方,正在于以现实之我而返本于父母而知父母之我即我之我,由现实之自爱而返本地爱那无我之我,即父母之我。现实地看,父母是“他”;然返本地看,父母却正是“我”。现实道德生活要求之“以他为自”,由此而返本地以无我之我而化解了“自”与“他”的隔阂而还归于现实之“以他为自”之顺适。唐君毅对此说道:“……吾人……自动的将自己之现实存在性,还归之消纳之于父母之现实存在性,将对自己之现实存在之爱上推而成爱父母之孝。”[1]44现实存在之爱父母,返本地看却是爱自己。孝也就在这种返本意识中而得以确立。由此也就可以说孝“乃依必然之道德理性而说之必然命题,非自经验之归纳而得之命题”。更进一步看,所返之本可及于我之无我之我、以父母之我为我,又可设想父母又返本而推知其父母之我而为我……以至无穷,以达于天地宇宙。于是就现实之我而言,父母祖宗与天地宇宙之全体,皆可在我之返本意识中而成为无我之我、忘我之我、超越之我。于是现实之我也当将对父母之孝推扩至天地宇宙,而对天地宇宙致其爱敬。
返本之道德性,并不在于其所返之“本”,——此本乃指父母、父母之心;而在于“能返”之自身,——此“能返”乃指自己之道德意识之活动。此“能返”即人之自觉的道德理性,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良知”“良能”。由此“能返”至无我之我、以父母之我为我而对父母生出孝思。所以说孝的根据在于道德理性。
更进一步来看,孝乃必然之道德,其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自己对父母不仅有自然血缘关系之接受,而且通过返本而达至无我之我之境,于是觉悟无我之时,我以父母之我为我,即只有父母而无我,父母即我。如此,则父母于我不特是一自然血缘关系之存在者,还是在道德理性之照察下的道德之存在者。换句话说,父母之存在于我而言不仅是自然存在,而且还是道德存在。我由此而对父母予以双向肯定。此一点唐君毅并未明说,但是依其思路则是必然的结论。第二,现实之我由此返本之孝思,使得自己也得到双重肯定。现实之我显为一物质性存在者,有本能之欲望,然通过返本之孝思而达于无我之我,又通过此无我之我照察现实之我而知父母生我乃是他们道德自我之创造性超越。也就是说,我不仅是一物质性存在,而且还是一道德性存在。对于上述两方面之过程,唐君毅将其称之为“超越的我之两重超越”:“孝之为道德生活,乃由超越的我之两重超越。超越的我既超越其对父母宇宙之执以生我,而又超越对现实之我之执以孝父母宇宙。”[1]47第三,肯定人之欲望生活为应当。如上述所言,由返本而挺立之孝思,是首先到达于父母的,并由此转进以达于天地宇宙。由此路径所呈现之父母、天地宇宙皆为精神性之存在。即唐君毅所说的“由孝所培养之宇宙意识,正为最富生命性精神性之宇宙意识”[1]48。此一道德意识返本所肯认之父母,乃有本能欲望以具体生我者。此生为善,亦如天地宇宙生万物而为善一样。因此而可肯定欲望生活亦为善。唐君毅说:“肯定孝之作用有两方面,一方是求超越现实之我,而以父母为我,以超越本能生活,实现超越的我。一方是透过父母与超越的我,以印可本能生活,使本能生活含道德意义,升华成道德生活,而孝遂为统一超越的我与有本能欲望之现实之我之生活,以成为一整个自我之道德生活,并将形上之我与形下之我,沟通而一贯之者。由是而孝不特是返本,而是成末。”[1]50第四,孝能促进夫妇关系道义化。在子女对父母致其孝思时,父母亦能感受此道德性、精神性活动,由此而增进父母对子女之精神之爱。而父母对子女之慈爱,也就进一步升华为超越本能之道德性、精神性之慈爱。“由是而父慈子孝之关系,亦成为纯道义之关系。”[1]53夫妇双方各以其对子女之纯道义之慈爱为中介,更能增进夫妇间之道义关系。
(三)友之形上学根据与其道德意义
家庭中之关系有三种:一是夫妇关系,二是父子关系,三是兄弟关系。夫妇关系是交互关系,父子关系是因果关系,兄弟关系是并立关系。前两种关系之道德性及其根据,已如上文所言。为了解释兄弟关系之道德性之根据,并总结前两种关系之道德性之原因,唐君毅创造了两个词,即现实境和理想境。所谓现实境,是指自己和对方的现实存在状态;理想境是指自己从己之现实存在而追想己之未存在之时对方之现实存在状态。他认为,夫妇双方一时并在,是一现实境之关系;而父母对子女而言,子女未生之前,父母的存在乃为一理想境,而出生后其与父母为一现实境之关系,于是父母与子女关系实为现实境与理想境相交织之关系;而兄弟皆父母所生,其既为彼此独立之现实境之关系而又互为理想境之关系。正是因为夫妇为现实境之关系,故其常道之根据只能从其彼此间之现实关系之精神化处(“爱之爱”)着想。而父子为现实境与理想境交织之关系,故其道德之根据既要从子之现实境而返于父母以呈现理想境,而产生纯粹精神性之孝思;也要从父母之现实境出发而望子之未出生时之子之理想境,而产生“半精神性之慈爱”。——之所以说是“半精神性”,是因为子女初生,父母对其之爱还注目于其身体而有待于子女之孝思、孝行为中介,使其在子女之纯孝思孝行之感召下而转进跃升为纯粹精神性之慈爱。但兄弟关系与前两者都不同。尽管兄弟之道德可简言之为“友”,但仔细分别则可说因其彼此独立之现实境之关系而有“敬”,因其互为理想境之关系而有“爱”。
兄爱弟之根据在于父母自觉地对其爱情之爱之顺延、客观化。唐君毅说:“父母之爱情之客观化为子女,而父母‘爱’其爱中之‘爱’客观化即成子女间之爱,即兄弟之友爱。”[1]55而从兄弟角度说,则皆知彼此乃为父母所共生,由是自然产生共命意识。此共命意识乃是父母生命精神之客观化之一贯性使然。此兄弟友爱之道德意义,适在于能增进父母之爱,维持父母之婚姻关系之持续以使父母之夫妇关系增一持续进阶而道义化之外在力量。否则,兄弟纷争而使父母见其爱之客观化为无意义,由此即会削弱父母之夫妇爱情之持续、进阶。需注意的是,唐君毅认为兄弟之友爱,还有一重要道德意义,即与孝相配合,使得兄弟不因彼此独立而隔绝。他说:“孝者生命之返本而上溯也,友爱者使之念同为一父母所生而合源也。”[1]58返本上溯、合源之道德意识,使得父母、兄弟皆受一限制与规范,而维持家庭之形式。
弟敬兄则源于弟之自觉兄在己之未生前乃一理想境,而己乃为一“虚位”,弟由这种自觉的虚位感而在对兄之时自然生出“一承托之态度,同时对于我之现实活动加以收敛”,而“此种对对方之承托态度与对我之现实活动之收敛,即是敬之本质”[1]60。这样,兄在弟之理想境中而得到肯定。换句话说,也就是现实之兄因弟之自觉其为理想存在而为弟之精神所包围。于是可说敬乃弟对兄之虚位感而精神地生发出之纯粹道德。这种纯粹的精神性、道德性即为敬之根据。而敬的道德意义则在于承认个体之独立性,使得兄弟既拥有共命意识而合源,又能保持其个体独立而成就其私。如此,兄弟各自之私人生活亦因此而道德化、精神化。
综上,调节兄弟关系的道德,统一言之而为友,分而言之而为爱与敬。此爱与敬有明显的区别。唐君毅认为有如下四方面的不同:一是本质不同。爱的本质是发扬,由充实自己而润泽对方;敬的本质是收敛,由虚己以承托对方。二是来源不同。“敬源于觉己有所不足,爱源于觉对方有所不足。”三是精神活动方向不同。“敬为现实活动之纯粹超越”,向上;“爱为现实活动之扩展”,向下;并“于扩展中见最初现实活动之超越”,又向上。四是施与对象不同。爱“使未有而有”,故为长者向幼者施与;敬为承托与收敛,故为幼者向长者施与。[1]61
三、家庭道德之限制与社会道德之贯通
如上文所论,家庭成立的根据在于人的道德活动,在于人的超越自我之求实现。换句话说,家庭成立的根据不在血缘关系,而在家庭成员间的道义关系。在上述几种核心的家庭道德之坚贞、孝、慈、爱、敬中,孝是绝对的、最高的、纯粹的道德责任,因为人必有父母,却不必有夫妇、兄弟。因此如果要对它们做一个价值层级上的排序,则可说孝最高,夫妇之坚贞次之,兄弟之爱敬又次之,父子之慈最易故为最下。
那么,是否这就意味着人之道德囿于家庭呢?如何找到突破家庭范围而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呢?唐君毅的办法是从归谬来论证人之道德必突破家庭而进入社会。其思路如下:如果我们只限于家庭来讲道德,只对家人尽道德责任,那么将家人推至极致即可发现,个人可既无父母在世,也无兄弟姐妹并存,又无夫妇更无子女,那么他即不必尽家庭之道德责任,结论就是他没有家庭道德责任可尽。此一结论与人当尽其家庭道德责任相矛盾。唐君毅说:“凡主张人只能对家庭中人尽责任,即等于主张人可不对任何人尽道德责任。而人对家庭之责任,亦非必然者。”[1]77这样的结果,就与上述家庭哲学全部冲突,即使绝对性之孝亦由此而被抵消。
因此,由此归谬法而可得知,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原是贯通的,都是个人仁心仁性的表露,本不能由经验上有些人以家之私而害社会之公以得出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为两端之结论。经验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之只私爱其家庭者,皆为其所见之血统关系所蔽”。众人往往容易以为血缘关系是家庭成立的根据,有血缘关系即有家,无血缘关系则无家。但正如唐君毅所说:“血统关系只为家庭中之本能的爱之基础,而本能的爱并非家庭成立之真正之基础。”[1]78之所以先建立家庭道德,是因为由家庭道德生活所培养之道德意识,才是真实的、具体的、具有生机创造性的道德意识。家庭只是道德自我最初的表现场域,最初的实现场所,本没有只限于在家庭中流行之规定性。此道德自我自返本于父母而超越现实自我,进入无我之我、以父母之我为我,并进而返于天地宇宙万物,以天地宇宙万物为我,由此全幅的生命精神观照万物,则无物可逃于其间。故此自觉之道德理性本就遍照宇宙万物,当然也就包括不特定多数人之集合之社会。由此遍照一切之道德理性,在家而可尽家庭道德责任,在社会亦可尽社会道德责任,当然在国也就能尽爱国之责任。因此,从道德理性、道德自我上说,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本是一体之顺展,本无隔阂可言。
四、唐君毅家庭哲学之评价
唐君毅的家庭哲学思想已如上所论述。至于其思想之价值,唐君毅本人即已有清醒之自觉。他自认为其家庭哲学的价值在于从道德理性上论证家庭当存在之必然性,由此而论证人尽其家庭道德之必然。他说:“故吾人必须建立吾人之家庭哲学,以反对错误的家庭哲学,使吾人能在自觉的理性上肯定家庭之当存在,以防止一切违背家庭道德之思想之出现,此即吾人之家庭哲学之价值。”而如果“人根本无违背家庭之道德之罪恶,或人本直觉家庭之道德意义,根本不疑家庭之当存在,则吾人之家庭哲学亦为多余”。[1]74实则家庭哲学必不多余,因为立说皆为常人“日用而不知”,于是因没有自觉的道德意识而常常未尽到家庭道德责任。其结果必然是家道落而人道废。唐君毅以其强烈的文化意识,对此可能之后果必不能接受。故其建立此家庭哲学,乃其自觉的道德自我之不容已的结果。他之所谓“多余”,实则由现实而言乃为“必需”。
众所周知,家庭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所注目的领域。例如,孟子说:“国之本在家。”《中庸》有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而《周易·家人·彖》则说:“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序卦传》又说:“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此后历朝历代的儒学思想家无不在此思路上将家庭置于基础性地位而加以强调和论述,由此而建立起了庞大、精深的家庭思想系统。但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强势入侵,国人在反省传统思想文化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例如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就大力排斥家庭,认为国家、社会之一切罪恶之源皆可自家庭关系中找到,家庭不仅给个人带来无穷之痛苦,而且还祸国殃种。而傅斯年以西方文化之个性为据,认为应该将旧家庭一扫而光,重建新式家庭。[5]104-108顾颉刚也作《对于旧家庭的感想》一文表达对旧家庭的痛斥。当然,“五四”时期的人们并不是主张完全抛弃家庭这个组织,而是要抛弃中国传统的压制个性成长的旧式家庭,冀以建立一新式家庭。
在当代,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今天的家庭仍然很重要,由是而建构了“家哲学”。其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这是中国文化最擅长的领域,也恰恰是西方文化的盲点和弱点。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说,我们应该高扬传统文化中的家哲学思想,以贡献于西方,从而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6]而张祥龙出入西方之现象学与中国之儒学,也从中西对比中大力肯认传统家庭文化,并认为今天应当从家庭入手来复兴传统文化。[7-8]还有大批的儒家思想研究者也对儒家的家庭思想文化充满了同情的理解与弘扬。相比较而言,唐君毅的家庭哲学思想最突出的贡献是其致思路径和有关认识。他以超越的道德理性、道德自我为基线,纵贯地论证、肯认了家庭之当然性及家庭道德之必然性。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是他将家庭规定为形式的思想,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样经验的、社会学的认识。还有其他诸如夫妇之爱之爱、敬的根据、现实性与理想性之双重肯定等等具体思想都极具启发性。当然,在他的家庭哲学思想中,也有一些牵强附会的地方,比如其论“女嫁男之理由”,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发现家庭生活之种种现象不必有其当然之理由。这也提醒我们,在家庭哲学中不必去顾及摇摆之家庭现象。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唐君毅的家庭哲学思想还需认真加以重视。因为即使现在,家庭对于我们来讲仍然是重要的生活领域,可以说人一生也没有走出过家庭。而且,个人道德之培养,家庭的确是很重要的基础性场域,——只有经过了家庭良好的道德培养,个人才能具备真实的道德素质。时代在变化,经济意识横扫精神世界,今天的家庭面临诸多困难,以致有社会学者声称家庭已死,而普通人对家庭亦无维护之信心。当此之时,我们从唐君毅的家庭哲学中却看到了其对家庭所持之坚定信念,而其论证之严密、观点之鲜明,自有其不容辩驳之处,这对我们今天建构适合时代、提振家庭信心的家庭哲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