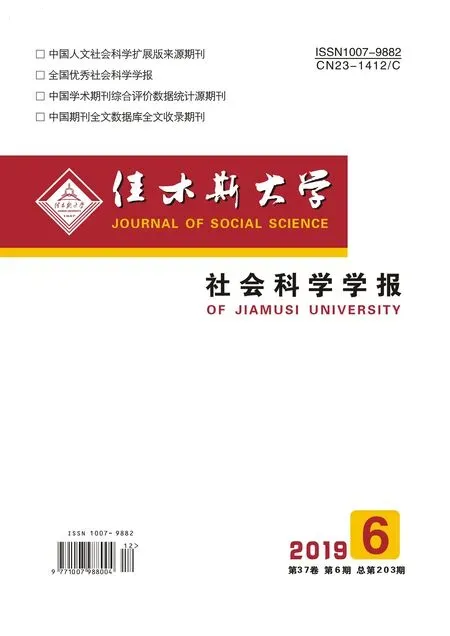明初词体观的诗性特色
郑 平
(韶关学院 文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明代初期,作家们对于词这种文学体式的认知独具特色。其时的词体观念具有浓烈的诗性色彩,即视词为诗,将二者的文体性质等同视之。这种观念在词体的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中都有体现,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词体功能观上,推重言志之用;一是在词体审美观上,崇尚高雅之格。
一、重言志之用
明代初期,词人对词的文体功能的认识比较通达,认为它具有与诗一样的表达功能,不严格区分彼此表达内容方面的区别,而是把二者等量齐观。他们没有把词体当做专门描写风月之情的艳科体裁,也不像明代后来词家那样大倡主情之说,而是像看待诗歌一样,关注词作的教化意义,重视词体的言志之用。
这种类同于诗的词体功能观,在当时的理论批评中有着明显表现,包括词集的序文、词作的评论等。这一时期的词论具有浓厚的诗教色彩,强调比兴寄托,寓意讽刺,重视修身行素,有补于世。
《写情集》是明初文坛领袖之一刘基的词集,叶蕃在其序文中这样评论作品的内容:“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 又说“先生当是之时,深知天命之有在,其盖世之姿,雄伟之志,用天下国家之心,得不发为千汇万象之奇而龙翔虎跃也。”[1]1456他指出杨氏所作其实都是或直接或间接地抒写其感时伤世的人文情怀。可见,他的评论中心在于寓于作品的意旨,作者表现的情志,强调的是寄托其中的“忧世拯民之心”与“用天下国家之心”。这显然是把词的功能与诗的功能等同视之,强调词的言志之用。《乐府遗音》是明初作家瞿佑的文集,其名“乐府”,是取广义,其中所收包括诗、词、曲三种文体。陈敏政在其序文中写道:“其间寓意讽刺。所以劝善而惩恶者,又往往得古诗人之遗意焉。”[2]268这则评论,注重其寓意讽刺,劝善惩恶的功能,明确提出作品“又往往得古诗人之遗意焉”,可见陈氏论词犹如论诗,是以诗的标准看待词的功能。《天籁集》是明初作家白朴的词集,孙大雅在其叙文中这样评论白朴的创作:“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韬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徙家金陵,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3]464他指出白朴之词是洁身自好之情志的寄托,是个人雅志的文学抒写。由上述这类词家的批评可见,明初对词体言志功能的认识,包括:济世之志、劝世之志、忘世之志。
以上所述文集序文属于对作家词作的总体评论,在对单篇词作的具体评论中,同样可以看到论者对词的功能的认识,是与诗等同的。先看一则刘崧在《刘尚宾东溪词稿·后序》中的评论:“惜稼轩《送春》一词,沉痛忠愤,悲动千古,至今读之使人毛发寒竖,泪落胸襟,真悲歌慷慨之雄士哉!”[4]文中所论之词为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是一篇典型的有所寄托的作品。作品运用比兴手法,讽喻小人作恶,感叹王朝颓危,抒发词人遭受猜忌而壮志难酬的忧愤。刘氏称之为雄士之悲歌,是激赏这种字里行间的忠君爱国情怀,而这种情志寄托正是传统诗歌的常见功能。在这一时期,黄溥的作品评论更具代表性,他的《诗学权舆》多有对词体言志功能的强调,论词角度与诗无异。在此列举几则以作例证,如他评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范文正公为宋名臣,忠在朝廷,功著边徼,读其《秋思》之词,隐然见其忧国忘家之意,位非区区诗人之可拟也。”评欧阳修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曰:“此词写出感物怀旧之情,惜老伤时之意,为真切。”评朱敦儒《西江月》(世事短如春梦)和秦观《蝶恋花》(钟送黄昏鸡报晓):“二词皆为警世而作也。辞虽少殊,而模写人情世故,与夫天道之变,君子乐天之常,则一而已。读之能不益敦其修身行素之志乎!”又评文天祥《沁园春》(为子死孝):“人臣之节,莫大于死国,文章之作,贵关乎世教。此词纪实张巡许远忠节,足以立纲常、厚风教,诚有补于世,非徒然作者也。盖亦宇宙间之不可无者,宜著之所传。”[5]1180由以上引文可见,黄氏论词,注重思想意义,强调教化功能,与诗等量齐观。他的评论着眼之处不在私情,而在高志,包括忠君爱国之意,人情世故之真。尤其是后面两则,更是提出警世之作读之能敦其修身行素之志,提出文章关乎世教、有补于世。于此可见,黄溥全是把词与诗相提并论,在他的理论中没有彼此之分,这反映出在他的思想观念里面,二者的功能是类同的。
总之,明代前期,词学家们在理论批评中特别注重词体的教化功能,象看待诗文一样,强调它的言志之用。
考察这一时期的词体创作实践,也能看到他们的这种注重寄托、强调言志的文体功能观念。在明初词坛上,刘基是成就最高的作家,在当时的词人里最具代表性,其词体创作最具时代特色,强烈关注社会现实,抒写壮志难酬的忧愤,是他词作题材的鲜明个性。他的很多作品是写身处乱世而心怀天下的特殊心理感受,如《沁园春·和郑德章暮春感怀,呈石末元帅》:“万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乡。奈狐狸夜啸,腥风满地,蛟螭昼舞,平陆成江。中泽号鸿,苞荆集鸨,软尽平生铁石肠。凭栏看,但云霓明灭,烟草苍茫。 不须踽踽凉凉,盖世功名百战场。笑杨雄寂寞,刘伶沉湎,嵇生纵诞,贺老轻狂。江左夷吾,关中宰相,济弱扶倾计甚长。桑榆外,有轻阴乍起,未是斜阳。”作者的拯世济物的用世之心,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表露的很是明显。其它著名词人如高启、张肯、刘炳等,所写也多是此类言志之作。把这些诗歌中常见的题材搬到词里面来写作,这也间接体现了在他们的意识里,对词的文体功能的认识具有一种诗性的色彩。
当时还有很多另外一种类型的言志之作,它们并非抒写忧时济世之心,而是谈理论性,表达人生哲学,劝勉涵养情性。如姚绶、周瑛、王达等作家,写有很多这类表现私人情致之作。如周瑛的这首《满江红·寓南都题西园池亭,用宋僧晦庵警世韵》:“宇内寓形,何须问、足与不足。天生物,五行均赋,有盈有缩。譬如车轮三十辐,迭为上下交翻复。履前途、孰谓皆夷,平无砾碌。 荒山下,一间屋,败壁底,一瓶粟。少有人于此,肯著双目。器小不能胜大受,命穷岂足膺多福。请从今、消释此生心,休多欲。”全篇意在说理,无涉言情,表达自己的人生思考和私人情志。
总之,明代初期,在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中,言志之作居于重要地位,无论是写天下之志,还是私人之志。这些都间接反映了当时词人重言志的词体意识。
二、尚高雅之格
明代初期,词学家们的词体审美观念比较统一。他们重视词的审美品格,崇尚高雅的格调。这与此后的词体俗化倾向迥然有别,体现出一种自觉的尊体意识。这种审美品格的取向,在理论批评中有明确表述,在实践创作中有侧面反映。
在明代初期的理论批评中,格调高古的作品,都得到了词人们的高度评价。先看一则王蒙在《忆秦娥·花如雪序》中的记述:“余观《邵氏见闻录》,宋南渡后,汴京故老呼妓于废圃中饮,歌太白《秦楼月》一阕,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视。良由此词乃北方怀古,故遗老易垂泣也。盖自太白创此曲之后,继踵者甚众,不过花间月下,男女悲欢之情,就中能道者唯有‘花溪侧。秦楼夜访金钗客……几时来得。’完颜莅中土,其歌曲皆淫哇蹀躞之音。能歌《忆秦娥》者甚少,有能歌者,求余作画,并填此词,以道南方怀古之意。”[6]142王叔明认为早期词作寓意高古,所以能够使人深为所动。而词到后来,只唱狭隘的个人感情,因而感人之力尽失。有感于此,王氏特意作词,寄托怀古遗意,可见他反对词为艳科的观念,主张词体应该具有高雅的品位。黄溥的《诗学权舆》评辛弃疾的《蝶恋花》(谁向椒盘簪彩胜)说“观此立春之作,抚景写情,感慨悲壮之意,超然高出物表,语倔奇自成一家。”[5]1181明初词人特重辛词的这种高雅艺术品位,因此在批评词作时,如果把它与辛词相比,也往往是从这一方面着眼。如陈敏政在《乐府遗音·序》中称赏瞿佑的词作“直与宋之苏、辛诸名公齐驱”,缘由之一即在于其“词调高古”,[2]对其词的高古格调给予高度重视。
强调命意超逸的思想,在明代初年词学家的理论批评中,是十分常见的。黄溥的《诗学权舆》评王安石的《桂枝香》(登临送目)曰:“荆公此词睹景兴怀,感今增喟,独写出人情世故之真,而造语命意,飘然脱尘出俗,有得诗人讽谕之意。”[5]1182这篇登临怀古之作,感叹王朝兴衰,忧虑国家命运,正是其命意超逸,所以才特为关注。这种重视超逸的思想,也是当时词人的尊体意识的一种间接体现。唐文凤写有一篇书法跋文,题为《跋杨彦华书虞文靖公苏武慢词后》。是看书法作品所写词作内容后有感而作,文章先论虞集之文是“高文大策,醇辞雅论”,为“一代大手笔”。接着由文及词,推而广之,认为其“歌词之丽,亦皆超诣而不凡”。[7]这种联系推论反映出,在论者的意识里面,并无文尊词卑的传统偏见,他认为词与文一样,格调超逸的审美品格是衡量其艺术成就高下的标准之一。
情致雅正也是在明代初年的词学批评里面受到特别重视的一个重要内容。叶蕃在《写情集·序》里说刘基:“风流文采英馀,阳春白雪雅调,则发泻于长短句也。”又说“其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性情之正焉。”[1]他评刘词为“英馀”“雅调”,进一步又说这是其“性情之正”使然,对其词雅正的品格给予了高度评价。又如孙大雅在《天籁集·叙》中评论白朴的创作时,把词品与人格联系起来,认为词作是词人志节的外化:“先生出处大节,微而婉,曲而肆,庸人孺子所不能识,非志和、龟蒙、林君复往而不返之俦可同日语。”他提出白朴之志非真雅之士不能真正理解,也是强调其志之雅,可见格调之雅是他评论白词的主要着眼点。又如刘崧在《刘尚宾东溪词稿后序》中对刘尚宾词的评论:“其闲丽清适如空山道者;其风流疏俊如金陵子弟;其闲情幽怨如放臣弃妇,色惨意庄;其述怀抚事如故京老人,感今道旧,语咽欲泣,亦何能言哉!”[4]由这段评语可以看出,刘氏对于词体艺术风格无所偏嗜,认为各种风格皆有其美。值得注意的是他称赏各种风格的形容,包括空山道者、金陵子弟,意庄、欲泣,这些都是重在清朗、庄重,反映出他对雅正之美的欣赏。
崇尚古雅的词品观念,不仅体现于当时的理论批评,在当时的词选里也有体现。吴讷的《文章辨体·近代词曲》的选词标准也体现了他的这种尚雅观念。他在其《序说》中说道:“庸特辑唐宋以下词意近于古雅者,附诸《外集》之后,《竹枝》、《柳枝》,亦不弃焉。好古之士,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之不一云。”[8]他明确说明自己所选尽是古雅之作,于此亦可以观世变。其中所选词作有三分之一不在《草堂诗余》之列,柳永词亦不在其选择范围之内,由此可见他的尚雅取向。
明代初期词体的创作实践,也间接反映出当时词人的尚雅倾向。那种情致超逸、语言清朗的作品位居主流,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是如此。如明初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刘基,他的词作数量众多,虽然风格有别,但品位高雅的总体原则很是显著。如其《水龙吟》:“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啼鹃迸泪,落花飘恨,断魂飞绕。月暗云霄,星沉烟水,角声清袅。问登楼王粲,镜中白发,今宵又添多少。 极目乡关何处,渺青山髻螺低小。几回好梦,随风归去,被渠遮了。宝瑟弦僵,玉笙指冷,冥鸿天杪。但侵阶莎草,满庭绿树,不知昏晓。” 词写面对时局的悲怆感慨,格调之高令人称赏。再如另外一类《渔夫词》:“采石矶头煮酒香,长干桥畔柳荫凉。歌欸乃,濯沧浪,来往烟波送夕阳。” 写隐逸之想,亦清疏超逸。
综上所论,明代初期的词学思想,有两个方面的时代特征。一是对于词体功能的认识,一是关于词体审美的意识。概而言之,重言志、尚高雅的倾向明显。这与明代后来的重言情、尚低俗的主流词学观念明显有别。而这种词体观念具有鲜明的诗性色彩,反映出当时词家的一种词诗等同的尊体意识。
明代初期,词体观念之所以出现这种类同诗歌的时代特色,是由于当时的词人处于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中。其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他们的文学思想观念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明易代的社会剧变,使得身处乱世的文人们的创作心态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他们不得不关注社会现实,文学创作的现实感增强,词体创作的社会内涵丰富,感情充沛。词体的言志功能于是得到充分发挥。明初词坛领袖刘基在《照玄上人诗集·序》中这样阐述其诗学思想:“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禆于世教。”[5]80坚决反对“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与其儒家诗教思想想通,他对于词体也强调寄托与教化,重视其言志之用也就不难理解了。
政权确立的王朝初期,统治者为统一思想,大力推行儒家学说。特重理学的文化政策,也对当时的文学领域产生影响,为文注重庄重高雅,必然成为一种共识。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在《清啸后稿·序》中有言:“诗之为学,自古难言。必有忠信尽道之质,蕴优柔不迫之思,行主文谲谏之言,将以洗濯其襟灵,发挥其文藻,扬厉其体裁,低昂其音节,使读者鼓舞而有得,闻者感发而知劝。”[5]53他的这种诗学思想,其实代表了他的基本文学观念,其中也包括词体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