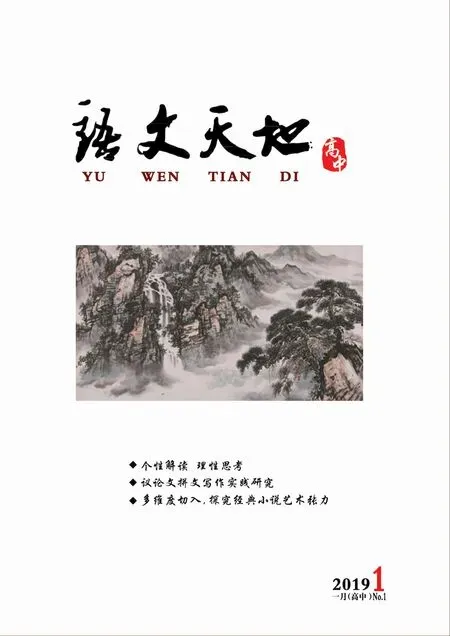“春夜”话“送”“别”
——《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新解
《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是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中唯一一篇送别诗必读篇目,它对学生理解送别诗内容、了解送别诗特点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唐诗鉴赏辞典》陶慕渊先生对该诗的尾联进行了如下诠释:“结尾两句写目送友人沿着这条悠悠无尽的洛阳古道踽踽而去,不由兴起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聚之感,末句着一‘何’字,强调后会难期,流露了离人之间的隐隐哀愁。”
明人唐汝询也曾在《唐诗解》中对此诗进行评点:“此伯玉将之洛阳,饮饯于友人而作也。言彼张灯设席,丰美如此,故我思其堂之所有,念别路之间关,未忍遽去也。于是月沉河没,天将旦矣。从此入洛,当以何年而续此会乎?”
究竟是何人行于“悠悠洛阳道”上,是友人,还是伯玉呢?
《新唐书·陈子昂传》(卷一百二十,列传三十二)中记载:“文明初,举进士。时高宗崩,将迁梓宫长安,于是,关中无岁,子昂盛言东都胜垲,可营山陵……武后奇其才,召见金华殿。”
可见,唐睿宗文明初年,陈子昂确实曾自蜀地入洛阳。而且在《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二)》中陈子昂写道:“怀君欲何赠,愿上大臣书。”这又与“举进士”相互印证。足见行于“悠悠洛阳道”上的正是陈子昂本人。
《春夜别友人二首(其一)》没有对至真至性的场景进行渲染,而是着力描画了筵席之盛:“银烛吐清烟,金樽对绮筵。”陶先生将其理解为:“这首律诗一开头便写别筵将尽,分手在即的撩人心绪和寂静状态。作者抓住这一时刻的心理状态作为诗意的起点,径直但却自然地进入感情的高潮,情怀颇为深挚。‘银烛吐青烟’,着一‘吐’字,使人想见离人相对无言,怅然无绪,目光只是凝视着银烛的青烟出神的神情。‘金樽对绮筵’,用一‘对’字,其意是面对华筵,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勉强相慰的话了。”
如此诠释有“无声胜有声”之妙,开篇定调,意趣深远。但如将这种定位还原到送别的彼时彼刻,却有不妥。将“银烛”“金樽”归入诗文,则不免有张扬炫富之谦,反显庸俗。况且频举金樽,兴起忘形,杯盘狼藉,与“对”不符。而若以一个将行者的视角分析一切,便合情合理。
本诗首联描述的是盛筵未开之时。诗人应邀赴宴,由室外进入室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徐徐青烟,金樽器皿摆放整齐,珍馐美味、玉液琼浆一应俱全。往来挚友,悉数到场,静候已久。此刻,诗人内心被友人的深情厚谊所打动,一时间无言以对,以成“无声”之境,情感进入高潮。
友人所以准备如此华筵,与诗人即将奔赴东都洛阳求取功名有直接关系。而席间友人所谈论的或许多是对诗人的祝愿和对诗人宏图大展的畅想。但此时的诗人却是“对此芳樽夜,离忧怅有馀”。因此诗人弃应酬之语不谈,直言“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琴瑟”指朋友宴会之乐,语出《诗经·小雅·鹿鸣》,“我有嘉宾,鼓琴鼓瑟”。陶先生释为:“借用丝弦乐器演奏时音韵谐调来比拟情谊深厚的意思……‘离堂’把臂,伤‘琴瑟’之分离;‘别路’迢遥,恨‘山川’之缭绕。”
笔者认为这一解释有些牵强。比拟要求本体与拟体之间有相似点。“琴瑟”确实可以用来拟情谊,但并非友谊。《诗经·东南·关雎》有句:“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后以“琴瑟”来比喻夫妻融洽的感情,与本诗的语境不符。此外,在陶先生的撰文中,“离堂思琴瑟”变成了“离堂伤琴瑟”。以“伤”易“思”,其意迥然。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陶先生以为是:“承上文写把臂送行,从室内转到户外的所见。这时候,高高的树荫遮掩了西向低沉的明月;耿耿的长河淹没在破晓的曙光中。这里一个‘隐’字,一个‘没’字,表明时光催人离别,不为离人暂停须臾,难舍难分时刻终于到来了。”
颈联所描写的景象,是否是诗人“从室内转到户外的所见”,无人考证。但此联除“表明时光催人离别,不为离人暂停须臾”之外,更暗写了诗人与友人彻夜把酒,难舍难分,以时间的推移写出友情的深厚。
尾联两句,虚实结合,意味无穷。“悠悠”两字既写出了由蜀入京路途遥远,又以“悠悠洛阳路”喻诗人仕宦之路前途难知。“此会在何年”,既道出后会难期的隐隐哀伤,抑或是诗人与过往生活的决绝。史载陈子昂十八岁还没有入学念书,因为是富家子弟,崇尚气派果敢,射猎赌博无拘无束。如今二十一岁的他即将进京求仕,“此会”便是以往自由放任生活的结点。
陶慕渊先生“春夜”言“送”,笔者“春夜”话“别”,其中蕴含着一个送别诗抒情主人公定位的问题——是以将行者来定位,还是以送行者来定位。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中有送别诗32首,其中除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外,其他送别诗均含“送”“别”字样。含“送”字的诗篇一般是以送行者来定位抒情主人公,含“别”字的诗篇一般是以将行者来定位抒情主人公。但“别”字类有特例,即“饯别”。“饯别”是设酒送行,诗题中含“饯别”二字的是以送行者来定位抒情主人公。当然诗海浩渺,各有珠玑,这种简单的定位方法自然不足以放之四海,但可以引为借鉴,在送别诗鉴赏过程中起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