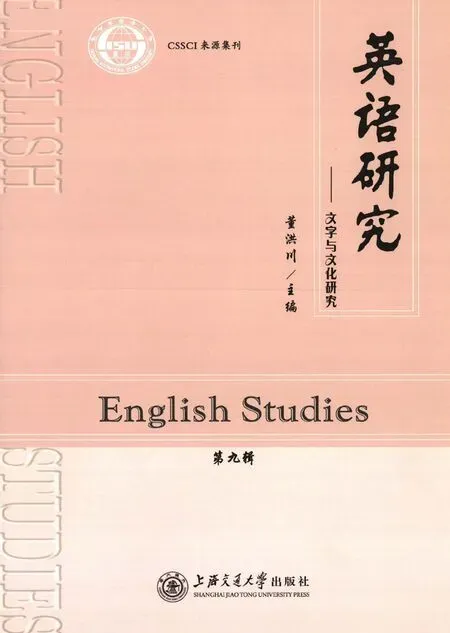非自然叙述学概要
布莱恩·理查森 著 王长才 译
(1.马里兰大学 英语系, 美国 20742; 2.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1756 )
非自然叙述由反模仿的事件、人物、环境或叙述行为组成。换言之,它们违反非虚构叙述、现实主义或效仿非虚构叙述的其他诗学实践的前提,不能被置于现有的、已确立文类的常规中。非自然元素主要处于虚构的故事世界中。马克·雷纳(Leyner,1995:59)有个好例子:“他遇到了汽车炸弹。他把钥匙插入点火开关并扭动——汽车爆炸了。他下车。他打开引擎盖,草草检查。他关上引擎盖,回到车上。他扭动点火开关上的钥匙。汽车爆炸了。他下车,厌恶地把车门重重关上。”这里描述了一个不可能的事件序列。
我也希望在一开始就明确和扬·阿尔贝(Alber,2016:25)不同。我区分了“反模仿的”(antimimetic)和仅仅“非模仿的”(nonmimetic),前者质疑非虚构和现实主义再现的常规,后者使用了一种不同的但完全是常规的范式讲故事(非模仿或非现实主义的文类,包括幻想和神话故事)。按我的定义,这些作品并不是非自然的。
大部分常规叙述理论基于模仿性叙述,因此用来理解反模仿叙述会遇到麻烦。非自然叙述学为那些拒绝遵守日常口头讲述常规,或者拒绝叙述再现的模仿形式常规的作品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在现实主义叙述中,有说话者,有可认出的人物,有具有一定“可讲性”(“tellability”)的相关事件,前后一致的本体性框架,以及或多或少可确定的听众。但反模仿叙述挑战而非遵守这些常规。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断言,叙述是某人向另一人讲述在一个可认出的故事世界里发生了重要的某事。相反,反模仿叙述会质疑这一论断的各个方面。它可以不采用单一、一致、像人的说话者,只使用不一致的、非人类的、或瓦解了的(collapsed)声音;它可能再现非物质的或不一致的虚构造物而非人物;它可能讲述那些似乎不值得讲或令人绝望地感到混乱或矛盾的事件;它可能将这些事件置于一个不可能的世界中;它可能投射出故事的接收者,这一接收者像其叙述者一样是非自然的。
在模仿或非模仿的世界中,叙述读者会相信拉斯蒂涅(Rastignac)生活在巴黎,有在“白雪公主”的世界中起作用的魔镜。但非自然叙述只需要部分地相信虚构世界,也破坏那种信念。当我们在故事世界中遇到相互矛盾的事件版本时(因此不能简化为人物的不同感知),我们被迫放弃叙述读者的通常信念。彼得·拉比诺维茨(Rabinowitz,1987:96)说,一种确定叙述读者特征的方式是问:“我必须假装成哪类读者——我必须知道和相信什么——如果我想把这个虚构作品当作真的?”然而,许多非自然的世界不允许它们被认为是完全真实的,作者的读者就变得与叙述读者相融合;我们想知道让故事世界混乱的(作者的)意图是什么。相似地,我们可以不再依赖玛丽-劳尔·瑞恩(Ryan,1991:48-60)所称的“最小偏离原理”(principle of minimal departure):这一规则以一个相对稳定的虚构世界为前提。对于非自然的小说,我们应该期待一种反复偏离的模式;有趣的是,这些小说通常会画出它们自己特定轨迹。随后沉浸于故事世界的体验也大打折扣。
非自然叙述学旨在识别和理解那些建构不寻常或不可能的虚构世界的叙述。比如,它邀请我们识别和辨别有着这些要素的作品:①像博尔赫斯(Borges)的《阿莱夫》(TheAleph)一样,有着搅乱稳定、模仿性空间的非自然空间;②完全自然化的描绘,一旦放在一起就创建了矛盾空间,如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的《嫉妒》(Lajalousie);③其本体论是(或暗示着)可疑的世界,如卡特(Carter)、卡尔维诺(Calvino);④成问题的空间,它在正被创造时崩塌,如贝克特的《每况愈下》(WorstwardHo);⑤一系列不同的、不相联的非自然空间,如《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inWonderland);⑥玛雅·索南伯格(Maya Sonenberg)的立体主义,如《静物》(NatureMorte)中反复出现的不可能空间,这空间与其他(非立体主义的)人物的经验相冲突。在这些情况下,通常是一个单独的不可能的空间或区域,要么嵌入以常规方式行动的普通世界中,要么被它们所环绕,要么被框住。因此,不可能的空间通过与我们经验的世界并置而凸现出来。
非自然叙述理论的范式坚持采用模仿和反模仿的双重、互动模式。后现代主义以其无休止的对反现实主义的和不可能的世界和事件的发明创建,已迫使概念/方法论问题走在前列:我们要么要一个很不完整的、主要是模仿的理论,要么发展新的概念来接纳后现代主义和其他实验性和前卫文本的非自然叙述实践。事实上,我们需要一种另外的、附加的诗学。非自然叙述学提供了这种另外的、补充的诗学。在大多数领域,我们不需要拒绝现有模式,而是用一个可涵盖模仿和反模仿叙述实践的、更为全面的模式加以补充。根据定义,模仿模式不能理解违反模仿再现规则的反模仿作品。一种完整的叙述理论需要双重视野和一种辩证诗学,它能处理虚构作品的虚构性方面。非自然叙述学是补足缺失的部分、缺失的理论、缺失的视野的更具包容性的范式。
叙述理论有一对基本概念:故事(histoire)和叙述话语(récit),即我们从文本推导出的故事和文本自身呈现之间的区分。俄国形式主义者确立的这个区分已存在了近一个世纪。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几乎总是可从每个非虚构的或口头的自然叙述以及模仿或现实主义的虚构作品中提取出来,这些作品力求与这些话语类型相像。如果不能,我们知道对于任何矛盾,会有明显的自然的解释,比如没有注意细节,记忆出错,或者露出马脚的谎言。然而,仍有很多种非自然的故事,完全避开了模仿模式。叙述可以绕一圈回到自身,因为最后一句成了第一句,因此永远继续,如乔伊斯(Joyce)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Wake,1939)、纳博科夫(Nabokov)的《循环》(TheCircle,1936)、贝克特(Beckett)的《戏剧》(Play,1963),这样的故事既是无限的,又是循环的。在另一些作品中,不同人群的时间以不同的速度流逝。因此,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AMidsummerNight’sDream)中,秩序井然的城市贵族们过了四天,而同时被施了魔法的森林只过了两天。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奥兰多》(Orlando,1928)中,主角经历了20年,而对于那些他(她)周围的人则过了三个半世纪。这些例子显示了双重或多重的故事。
另一些文本有相互矛盾的事件序列,像罗伯-格里耶的《嫉妒》(1957)、安娜·卡文的《冰》(Ice,1967)、罗伯特·库弗的《保姆》(TheBabysitter,1969)和卡莉·丘吉尔的《陷阱》(Traps,1977)。仔细研究丘吉尔这部戏剧非常有助益,因为它明确说明了在其非自然的故事世界什么正在发生、什么没有发生。其中,所有事件发生的房间在戏剧进展中改变了位置。房间的门对于一些人是锁着的,但对另一些人没有锁——没人碰过插销。第一幕雷吉为克里斯蒂和德尔带来了一盒巧克力,他说他希望他们从未从乡下搬到这座城市;第二幕人们正在吃巧克力,在乡下幸福地生活。我们看到希尔和她丈夫阿尔贝特在抱怨他们的宝宝引起的麻烦,几分钟后他们讨论最后要个孩子的可能性。接着人物杰克宣布他和希尔最近结婚了。一个人物两次经历了相同的相认场景;另一个人物改变了性格。阿尔贝特自杀,其余的人物反思他的死亡,然后阿尔贝特重新走进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其他人也没有惊讶。
就像罗伯-格里耶的《嫉妒》,丘吉尔采用了一系列完美的日常行为,在保持了人线性发展的同时,颠倒了进程中的部分序列,这就产生了一些不能协调的矛盾。各个序列的逼真性由于它们反模仿式并置而发生严重冲突。这种矛盾的效果在舞台上呈现时特别有力,引人入胜,因为所有观众观看了一系列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丘吉尔煞费苦心地说明这部戏的反模仿性;她不希望将其简单地缩减为一种常规化的解释策略。她在序言中断言,戏剧就像不可能的东西,或者像埃舍尔(Escher)的绘画,其中的东西能在纸上存在,但在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剧中时间、地点、人物的动机和关系都不能全部协调一致——它们可以在舞台上发生,但对它们来说没有其他真实性。可以认为人物是一次经历了很多可能性。没有闪回,没有幻想,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剧中其他部分一样真切而坚实。
对于解释更极端的非自然叙述,这可以是个很好的范本。
在库弗《保姆》中,多条故事线索的可能变体更为戏剧化。不同的、不相容的结局都出现在文本中,它们包括:保姆意外地淹死了婴儿;主人的丈夫早早回来与她发生性关系;邻居男孩拜访她,意外发现父亲和保姆在一起;父亲意外发现男孩们和保姆在一起;保姆追逐男孩;保姆被男孩们强奸;家人回来发现一切都好;母亲回家发现三个男人和保姆在浴缸里;母亲从电视上得知孩子们被杀,丈夫走了,浴缸里有一具尸体,她的房子已经毁了。不是一个事件排除了其他可能的选项,而是许多不兼容的可能性已然变成现实。
本节所举例子没有一个可以轻松地从固定的叙述话语中提取出单一、一致的故事。阿兰·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 1965:154)提及《嫉妒》中矛盾的故事时指出:“认为在小说中……存在一个清晰明确的事件秩序,而不是这本书句子的秩序,似乎我像洗牌一样打乱预先设好的日历给自己找乐子,这是荒唐的。”他继续说,对于他,除了在页面本身找到的秩序之外没有可能的秩序。再一次,这个文本并没有模仿那种其话语(syuzhets)会显露(divulge)单一故事的现实主义叙述;这里只有一个不确定的、矛盾的故事。
也有话语改变故事世界的案例。突出的例子包括文字文本生成器(verbal textual generators),独特的单词或按字母顺序等其他排序原则产生最终的文本。另一个是“消解叙述”( denarration),其中文本否定或“抹除”了它在虚构世界中已经描述了的事件。这些实验技巧使用话语来创建或摧毁故事。以上两种情况在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 1965:141)的《在迷宫里》(Danslelabyrinthe,1959)的开篇都显得突出。先是我们得知“外面正在下雨……风在光秃秃的黑色枝干之间吹动”;下一句话,这个环境被消解叙述了,我们被告知“外面阳光正灿烂:没有树,没有投下影子的灌木”。房间内每个表面都落满细细的灰尘;这种灰尘又会生成墙外特定的天气:“外面正下雪”。类似地,内部的其他表面图像生成了故事世界中的物:开信刀的印象变成了士兵的刺刀;长方形印象生成了士兵携带的神秘盒子;一盏台灯生成了外面雪中的路灯,接着又生成了倚靠着它,紧抓着盒子的士兵;而写实的绘画《赖兴费尔斯的溃败》(TheDefeatatReichenfels)确实让它描绘的战争场景活了起来。这里的描写让其表示的事件活起来,因为话语创造了故事;在消解叙述的情况中,话语既取消了环境,也改变了故事。
在另一些作品中,故事和叙述话语都是可变的。“选择你的探险” (choisissez votre propre aventure)图书提供了一系列选项,读者可从中选择。故事和叙述话语都是多线索和可变的,尽管一旦选定了某个特定事件,它会变得固定—— 这是一种组合规则,许多超小说(hyperfictions)以此方式建构。 安娜·卡斯特罗(Ana Castillo)的《米花拉书简》(TheMixquiahualaLetters,1986)采用了类似的原则。这本书是由一个人物寄送的一系列信件组成,但并不全要读者理解。相反,作者根据读者的敏感性提供了三种不同的阅读序列。因而,它告知保守者要从第二、三封开始,再转到第六封,而愤世嫉俗者从第三和第四封开始再读第六封。提供给空想类读者的是另一个顺序:二、三、四、五、六。重要的是要注意每个序列产生一个不同的故事。因此,我们有一个部分变化的叙述话语,一旦选择,会产生不同的故事。
非自然叙述学提供了扩展框架来解释反模仿故事,包括无限的故事;具有不一致时间顺序的双重或多重故事线索;内在的含糊和不可知的故事;内部矛盾的故事;消解叙述的故事;以及同一核心故事重复的多个版本。我们还形成了叙述话语的概念,也包括部分和完全可变的叙述话语模式。通过扩展我们的故事和叙述话语的概念,非自然叙述学能公平对待各类寻求改变和扩展传统实践的文本。
非自然叙述学也能帮我们保留和扩展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由罗兰·巴特等理论家对反模仿的人物所做的工作。再次,我们注意到,非自然的人物不仅仅是不可能的存在者,而是违反或戏仿现实主义规约的存在者。反模仿的人物,不同于非模仿的人物,即那些在标准的幻想和常见童话故事中的会说话的动物或飞马或其他常规类型。我们可以确认几种非自然人物违反模仿再现前提条件的方式。“不完美的人类角色”通过它们展示其非自然性:具有太少一致属性,以致不能让自己成为人的角色,或者有太多矛盾的特征以致不能合理地形成一个人物,或者它们可能是两个或更多人的融合。还有另外一些可能有很多正当的品性,但却错误地组合在一起。关于最后一类,最近有个很棒的例子,玛雅·索南伯格的《静物》,这是第一个立体主义孩子的故事,是来自阿维尼翁的未婚母亲1911年生的婴儿。他看上去很奇怪:“他是平的,不,只是当你从侧面或后面看他是平的。他看起来真的很瘦,但从前面看,呃,好像你几乎能看到他的全部”。其他男孩不想和他打棒球,因为如果他要击球,“好像甚至在他开跑之前,他就回到了本垒板”。他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是扭曲的。男孩的“世界是固体的。他呼吸的空间,随着它的接近而变成固体。他的身体形成了附着在墙壁、窗玻璃和地板上的空间和血肉的平面”。虽然他的身体看起来缺乏第三维度,他的意识超越了所有这三维:他甚至能观看自己的出生。(Sonenberg,1991:36-41)
剧场里有突出的例子,它们的人类特征很少,以致根本不被看作再现的人。特里斯坦·查拉1921年的达达主义戏剧《气动之心》(TheGasHeart)限于六个形象:眼睛、嘴、鼻子、耳朵、颈部和眉毛。他们交换无意义的评论,并展示出不可辨认的身份。也许最极端的是格特鲁德·斯坦因的戏剧。正如马克·罗宾逊谈到她第一部成熟的戏剧《发生了什么》时所说:“人物没有名字——如果有人物的话——除了括号中的一些数字意在表示出场。否则,这些声音完全没有确定身份的描述性要素。”这里的人物的确缩减成了代号。贝克特的《四个人》(Quad)完全解构了人物,只有尽可能相似的四位演员或“玩家”,他们的性别不重要,每一个都沿着固定的轨迹直线步行。没有言语,没有分别对待,没有性格塑造。也许彼得·汉德克(Handke,1975:9)1966年的《冒犯观众》是反人类主义表现的极端形式。他的演员们面对观众声明:“我们不给你们讲故事。我们不表演任何动作。我们不代表任何东西。我们不强给你们任何东西。我们只是说话。”
其他人物有数不清的矛盾属性。 在马丁·克里姆普大胆的戏剧《她生活中的尝试:为剧场演出的17个场景》(AttemptsonHerLife: 17ScenariosfortheTheatre, 1997)中可以发现一个极端例子,多个各自独立的个体呈现为一个角色。克里姆普不仅拒绝提供单一、一致的自我身份;他的戏剧通过呈现一系列关于叫安妮或安雅、安妮耶或其他化名的一个(或几个)女人的话语来挑战独特身份的观念。她们被呈现为在不同的境遇下有不同生活故事的不同的人:邻家女孩、表演艺术家、富有女人、恐怖分子、科学家、色情女演员、脚本人物,甚至一种新汽车品牌(自然是“安妮”)。 有人对其表演片断做了有见地的评论:“她说她不是真正的人物,如你在一本书或电视上看到的那样,而是人物的缺失,一种她所称的人物的缺席,不是吗?”(Crimp,1997:25)。
然而,这部作品不能仅仅被当作不相关片断的集合而被否定。这部戏剧从标题开始,采取了几种策略邀请观众将这些不同的故事带入情节,从而将其分散的主题部分地统一起来。这些策略包括,在戏剧第一场中安妮的应答机收到的大量看起来相冲突的消息,这些消息预示着许多后续场景中的故事片断。第14场中,一个音乐唱段同样地确认了一个单一的人物(“她”),它甚至颠覆了任何统一个性或形象的任何本质或基础:
她是皇室成员
她实践艺术
她是个难民
在一匹马和手推车上。
她是一个色情电影明星
一个杀手和一个汽车品牌
一个杀手和一个汽车品牌!
她是个恐怖主义威胁
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她是支廉价的香烟
她是迷幻药。
(Crimp, 1997:59)
在戏剧结尾,我们没有答案,叙述理论家(以及观众)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它是贯穿整部作品的一个人物的单一故事,还是只是不同女性的17个独立故事?作品本身同时既倾向又消除这两种立场。人们可以寓言式地或者元戏剧式地阅读它,作为一种对固定、稳定的人物的观念的批判,或者作为主体性由围绕它的自私话语所建构的方式的一种描述。尽管如此,人们可以把剧中安妮们和安妮耶们解释为一个女人在她生命历程中可能扮演的潜在角色;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观察过程中的单一、潜在的故事的变体。然而,这样的解释只是缓解了一些观众恢复模仿性的人文主义愿望,因为它对作品中多个安妮的不可缩减的异质性实施了暴力。
同样激进的是融合式人物(fused characters),在叙述进程中个人与他人相融合。许多新小说的人物受到其他人物侵扰的沾染或与其他人物合为一体。正如贝克特的莫兰对莫洛伊的反思,“也许我发明了他,我的意思是在我头脑中发现了现成的他”,又说:“因而在于我头脑中的莫洛伊和真正的莫洛伊之间………相似度不会很大。”(Crimp,1997:112-115)。
最有趣和最显著的虚构人物之一就是那些知道自己是虚构存在的人物,尽管在过去一个世纪较为盛行,这种情况仍没有被从理论上充分地讨论。布莱恩·麦克黑尔(McHale,1987:121-124)是讨论这种人物的少数人之一,他注意到它在小说中流行之前就在戏剧中盛行,重要的是,他区分了人物对他们虚构状态的认识程度。一个典型章节是皮兰德娄(Piradello,1952:217)1921年的戏剧《六个角色寻找作者》(SixCharactersinSearchofanAuthor),其中角色们出现在剧场,并要求作者完成他们的故事。他们说他们生来就是角色,正如角色“父亲”所说的:“一个人出生会以许多形式,许多形状,作为树或石头、作为水、作为蝴蝶或女人。所以一个人也可以一出生就是剧中角色。”另一个早期例子是《一个角色》,它出现在费利佩·阿尔福( Alfau,1990:17-38)的故事集《狂人》(Locos)中,其中一个角色不仅逃脱了他的作者,还与作者抢着叙述他的生活。叙述者开始说:“我打算写的是萦绕我脑海有一段时间的故事。然而,我的角色的叛逆特性不让我写。”写完为角色命名的第一个句子后,叙述者分心了。在此,角色接管了:“现在我的作者把我放在纸上,给了我身体和起点,我将继续讲故事,用自己的话讲。”
戏剧在舞台上演出时,演员的角色扮相可以大大影响其形象及接受;戏剧性再现就其本质而言倾向于使一个角色的统一性变得复杂,得到增强或消散。演员的出场为角色的再现增添了另一层次,演绎可以改变、反转或转换所呈现的故事。当表演者的性别、种族或年龄与故事所表明的不同时,这一点尤为明显。在喜剧《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中,阿里斯多芬通过让一个男性角色试图在舞台上将另一个男人伪装为女人,戏仿了在希腊戏剧中由男人扮演女性角色这一事实。一个男人所扮演的男性角色因此在舞台上被脱毛、易装,以便与故事世界的女性相似,这一女性角色也由男人扮演(尽管可断定伪装得更好)。
当莎士比亚剧中由男孩扮演的女性角色转而将自己伪装成男孩时,作者提供了元戏剧式的幽默。在《皆大欢喜》(AsYouLikeIt)中,穿男装的罗瑟琳说:“多谢上帝我不是个女人,不会犯他所归咎于一般女性的那许多心性轻浮的罪恶。”(Shake-speare,2004:340-342)。演员的性别似乎基本上抹去了角色的性别。同样,原先饰演克娄巴特拉的男孩演员非自然地实现了她的角色希望逃脱的命运:
俏皮的喜剧伶人们将要把我们编成即兴的戏剧,扮演我们亚历山大里亚的欢宴。……而我将要看见一个逼尖了喉咙的男童穿着克莉奥佩特拉的冠服卖弄着淫妇的风情。
(Shakespeare, 2004:216-221)
很多类似的转换可以写入脚本中,在卡洛斯·富恩特斯对他的戏剧《月光下的兰花》中关于玛丽亚和多洛雷斯(Maria and Dolores)角色扮演的引人入胜的笔记中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转换。他写道:“理想情况下,这两个角色由墨西哥女演员玛丽亚·菲利克斯和多洛雷斯·德尔·里奥扮演。更理想的是,在不同部分两个人交替扮演。”(Fuentles,1986:145)随后,富恩特斯接着说,他们可以由和原来演员相像的女演员扮演,或者是根本不像她们的女人,或者两个男人来扮演。这些可能性中的每一种都可能影响到最终的性格塑造、强化、疏远或否定角色的文学之外的身份,因为再现的可能性从认同到致敬到戏仿。在这里,性格塑造的表演维度是最为显著可见的。
我们观察到反模仿叙述自阿里斯托芬和佩特罗尼乌斯的时代以来就已经存在,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莎士比亚的更为大胆和具有自我意识的戏剧)很常见。反模仿策略影响了由《项狄传》(TristramShandy)启发的整个传统,在后现代小说和荒诞派戏剧中尤为突出。流行叙述媒体也充满了反模仿系列和文类,从开玩笑(tongue-in-cheek)的百老汇音乐剧、连环画册、儿童卡通到鲍勃·霍普-宾·克罗斯比的“某某之路”系列电影。
“非自然”这一术语常被人错误地过度使用。一些并没有读过多少相关文献的批评家经常将这一术语应用于各种轻微异常的现实主义文本、标准的现代主义的线性反转、特定意想不到的人物或场景,或传统的非现实主义作品。如前所述,我尝试仔细地将非自然或者反模仿叙述,与那些简单的非模仿叙述,比如传统神话故事、动物寓言和涉及魔法的故事区分开来。对我来说,非自然不包括超自然的叙述、幻想、托多罗夫所说的“奇妙”(marvelous)小说、传统科幻小说或寓言。我确认超自然与非自然非常不同:超自然的文本倾向于非常严肃地对待其故事世界,而非自然的作者们则公然地嬉戏。超自然事件通常可以放置在另一个自然主义的故事世界中,而非自然的作品解构模仿的或自然主义的世界。在超自然的世界中,一个角色可能试图骑着飞马升上奥林匹斯山;在非自然的故事世界中,一个角色可能像阿里斯托芬《和平》(ThePeace)的主角,骑在一只屎壳郎上,升到天堂直接与诸神说话。从阿里斯多芬和琉善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菲尔丁、歌德、乔伊斯、拉什迪,人们已经习惯于用非自然叙述来批评和讽刺超自然的主张。
大部分标准科幻小说与反模仿小说并无关联;许多作品的动力是敏锐的现实主义。最近的一个科幻故事集,芬尼和克莱默的《象形文字:为了一个更美好未来的故事和愿景》(Hieroglyph:StoriesandVisionsforaBetterFuture),强调了它现实的基础,特别是试图鼓励科幻小说作家“召唤宏伟的雄心勃勃的未来”,这未来激励他人“到达那里,让它们变成真实”(xxv)——不是那种可以问博尔赫斯或罗伯-格里耶的事情。同样,安迪·威尔的小说《火星人》(TheMartian)由科学家撰写并在网上发布,其他科学家可以对其场景的物理准确性进行质疑或确认。每当有错误,作者就检查计算,然后重写受质疑的段落,使其符合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法则。这是自从儒勒·凡尔纳和H.G.威尔斯的时代以来主宰大多数科幻小说的一般原则的极端例子:它是(或至少看起来是)可能的。自然会有作者违反这一原则,并另外创作出不可能的、反模仿的、后现代的科幻小说。
另一个常见的误解和非自然可能会变化或相对的性质有关。毕竟,许多人声称,在21世纪的工业化的西方,人们称之为不可能的曾会被认为是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谁来判断到底什么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争议总在继续。当我称一种行为或事件为“非自然”时,我一般意味着根据物理规律或逻辑公理是不可能的。物理学的基本规律在过去几千年没有变化,在伦敦、西藏、婆罗洲和南极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是物理学规律。逻辑的公理也同样是普遍的:排中律不会——也不能——随时间和文化而变化。
一些批评家试图将非自然叙述限制在如后现代主义或元小说等有限的类型以减缩或贬低它们。我们最近关于非自然叙述史的工作应该能轻松地消除这种错误。另一些人则采取相反的态度,比如认为它在维多利亚时期模仿小说中广泛流行。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注意到了在夏洛蒂·勃朗特、乔治·艾略特、简·奥斯汀、查尔斯·狄更斯和威廉·梅克佩斯·萨克雷作品中的非自然段落,并得出结论:“只要写现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就一直沉迷于反模仿的实践”(Herman et al.,2012:213-214)。我们的回应是:的确如此。我们可以在广泛的、表面上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发现非自然或反模仿的因素,尽管它们经常因为很快被归入作品的一般模仿框架之内而被忽略。除了如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Jacqueslefatalis)和贝克特的《无法称呼的人》(TheUnnamable)等明确地反模仿叙述之外,我们还可以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发现一条嬉戏的非自然的轨迹,至少从塞万提斯通过菲尔丁,继而发展到奥斯汀、萨克雷和特罗洛普。非自然是普遍存在的,它需要像这样被辨认,并得到更广泛的分析。
非自然的叙述继续进一步越过已有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和常规再现的既定界限,这些作品推动了我们将现有的叙述学模式拓展到仅仅是模仿作品的范围之外。传统叙述者死亡之后,一切都变得可能——除了按从前的、传统模式对叙述进行理论讨论。 J. M. 库切用接下来的术语说明了这种情况:
当你选择一个角色内心的单一视点,你可以选择心理现实主义,即描绘一个人的内心意识。而我这里强调的词是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而《内陆深处》(IntheHeartoftheCountry)正发生的是那种现实主义正被颠覆,因为你知道,她杀了她父亲,随后她父亲回来,她又杀了他,书进展了一段,他又到了那里。所以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游戏,一种反-现实的游戏。
(Penner,1989:57)
库切描述他与心理现实主义模式分歧所使用的特定语言,表明他的做法不是仅仅不同,而是有意识地反对这种诗学。的确,除了谈及它显然违反了的模仿的束缚之外,不能充分理解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补充现有模仿理论的另外的、反模仿的诗学。这一模式将使我们大大扩展叙述理论所涵盖的领域,并能更好地覆盖大量早期的非自然叙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在我们时代最令人钦佩的、富于想象力的叙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