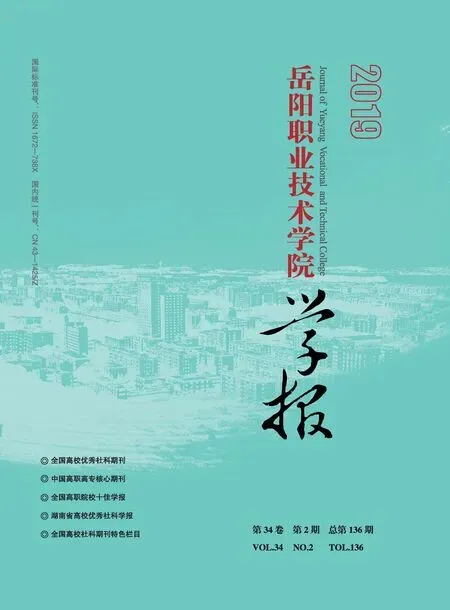论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上海意象
郑二虎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
上海是一座难以言说的城市,尤其是20 世纪以来,新旧文化的融合、碰撞,使其增添了不少传奇故事。虽然《长恨歌》的主人公是王琦瑶,小说亦围绕其传奇的一生进行叙述,但实际上,她起到了代言人的作用,代言的正是20 世纪上海这座城市。上海作为《长恨歌》的主角,承载了作家笔下大量的意象,肩负着文学想象与被想象的任务。作为王安忆的文学想象的存在,上海在《长恨歌》中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个地域符号,而被赋予了象征的内涵。本文从女性的上海、边缘化的上海、爱恨交错的上海三个方面对上海意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出《长恨歌》中上海的深邃象征意以及王安忆在小说中蕴含的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感。
1 女性的上海
《长恨歌》选定的人物王琦瑶是个双重身份,她既是个体的,亦是一个群体女性的代表,小说对王琦瑶女性气质描写的背后,是作家想要表现的女性化的上海意象。《子夜》作者站在社会与时代的高度,从大处着笔,描写了一个“大写的”男性化的上海。而王安忆的《长恨歌》,作者从个体经验出发,描绘个体生活中的小事,从细节落笔,描写了一个“小写的”女性化的上海。[1]琦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叙事中,《长恨歌》在不同时代的叙事中,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又一个女性形象,而最为形象的非王琦瑶莫属。通过对王琦瑶的几段爱恨情仇的感情经历的描写,《长恨歌》彰显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2]作家曾多次试图将苦难遭遇的女人安放在看似坚强的男人身后,但结果始终以男人的无法承担责任而失败,相比之下,王琦瑶对生活表现出来的韧性惊人,尽管这种韧性通常呈现出阴柔的状态,但却不是软弱可欺的,在艰难的时世中,男人的形象表现得比女人更软弱。
1.1 弄堂意象
情感描写中的女性形象,通过生活中的一些意象与上海产生了某种文化关联。而这些意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于弄堂、服饰和饮食方面。胡同之于北京,正如弄堂之于上海。老旧的弄堂里照常的传出家长里短,平安里的火炉上还坐着呼呼作响的、即将烧开的热水壶,像是一幅幅充满生活气息的上海图景,通过弄堂慢慢展现在人们眼前。王琦瑶从最开始弄堂里那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到之后阅尽富贵云烟的高官情人,再到最后又仿佛归于平静、回到自己熟悉的弄堂里,她就在这一走一回的反复中度过了人生近一半的路程,而上海这座城市正如在她身后操纵着一切的存在,总有办法将这里的一个个人生融入自己的变迁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百年沧桑的不是英雄般的史诗巨著,而是那生生不息、连绵不断的日常生活,这才是历史积淀中最真实、最本质的东西。[3]表明了上海这座充斥着人间烟火气的城市,其真正称得上“精髓”的地方不是随处可见的高楼广厦,而恰恰在于无时无刻不飘荡着生活气息的、拐角的弄堂里,上海作为人们容身之处,其最真实、最本质的东西体现在弄堂里人们的日常琐屑生 活中。
1.2 服饰意象
服饰意象,在《长恨歌》中意义非常。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各色服饰,其作用显然不仅仅是御寒这么简单,就文化意义而言,服饰才是上海意象中可以称其为意象的原因所在。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服饰描写,无一不是关于女性的,服饰之于女人,成就了相互的美,女人的服饰亦与城市在某种意义上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上海马路上的虚荣和浮华,在这里象找着了自己的家。王琦瑶身上的衣服,是橱窗里的时装的心;王琦瑶的简朴是阔绰的心”,王琦瑶甚至认为衣服是女人的文凭,可以“把内部的东西给个结论和证明,不致被埋没”,多年以后,女性的时髦表面上已经千变万化,但王琦瑶依然对那段充满服饰故事的过去念念不忘,时不时仍会讲评几句。或许在她的印象里,那些衣物早已不是简单的布料的组合,而更像是同自己一起经历了过去种种的老朋友,亲密无间,衣物一件件的被翻晒出来,记忆亦一点点出现在脑海中。女性对于服饰的喜爱,表现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体现,没有具体可感的形象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但其确实存在。在女性与服饰的无意识体现中,上海的某部分内涵逐渐丰富清晰起来,承载了人们精神上的、一个时代的需求。
与服饰意象所承载的作用类似的是,饮食也在《长恨歌》中,成为一种跨越具体存在的、具有文化意义的意象,是上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饮食的差异,体现了文化的差别。
1.3 饮食意象
上海的饮食文化,在小说中被“代表”王琦瑶说得甚为透彻,她在对比过去与现在的饮食中指出现在的饮食特点,“奶油是隔夜的,土豆色拉有了嗖气…西式糕点是泄了秘诀,一下子到处都是,全都是串了种的。中餐馆是靠猪油与味精当家,鲜得让你掉眉毛…中秋月饼花色品种多出多少倍,最基本的一个豆沙月饼里,豆沙是不去壳的”,[4]在两个时代的饮食中精致与粗糙的对比,显示了自己的喜好。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关于饮食文化的描写深入人心,从上海20 世纪40 年代的整体饮食文化,至每家每户平凡的一张餐桌或者桌布,表明了不论是身为女主人公的王琦瑶总是回忆起上海以前的姿态,还是作为读者们对旧上海会心向往之,这些表现均有道理并属情理之中。“每一个菜都像知道他们的心思,很熨贴、很细致,平淡中见真情,这样的菜,是在家常与待客之间,既不见外又有礼貌,特别适合他们这样天天见的常客”,小说通过萨沙和王琦瑶的对话,表明王琦瑶对于饮食的看法体现在“家常”,即在菜品中体现了一个人做人的体贴:不管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不要过分亦不怠慢,既要讲究自然简朴,亦要坚持品味问题,做到于自然之中有原则。简简单单的一桌子菜肴便让王琦瑶说出了这么多道理,可见饮食观念已不再仅是肠胃的事,而是一种处世的、文化层面的智慧。
弄堂意象、服饰意象和饮食意象三位一体,共同为表现上海意象而出现在《长恨歌》中。王安忆这样写的目的,回忆上海的旧时光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借此表达了对于变化着的现实的不认可,从而表明了她对现实生活之粗糙的否定以及对过去那种优雅和精致的生活态度的欣赏,将一个不一样的女性的上海活脱脱地呈现于读者眼中。
2 边缘化的上海
2.1 边缘化的叙事方式
边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小说主题而言,比较的对象自然是“中心”或是“主流”,主流存在于大时代下的政治和经济规律。《长恨歌》的人物并非全是处在那个时代和上海这座城市边缘的人物,有如李主任一样的权贵人物,但是通读文本,印象最深的却是一群“特立独行”生活在大时代之外的小人物,这些人各有各的生存方式,不可谓不丰富。例如,故事刚开始时,已经是上海革命走向全国的开端,但小说似乎并不想让此时的王琦瑶受到影响,而让她有了自己选美的梦想;此后,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的慌乱,王琦瑶均能安然自得地生活,与世界显得格格不入。王安忆多次刻意采取个人化叙事方式,使《长恨歌》自觉地过滤对于历史宏大主题的关注,恰恰显示了小说对塑造边缘化人物和边缘化上海的倾心。与茅盾所关注宏大的时代变迁不同,王安忆卷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而仅仅将时代作为小说发展的背景图,却不让它占据舞台中心。
2.2 边缘化的形象塑造
城市的边缘人多为生活在尘埃中的、平凡亦普通的人,衣食住行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每时每刻均围绕“材”“米”“油”“盐”这类事情烦恼,被生活之锁拷得严严实实,“十里洋场”的事,看似与他们发生在同一个城市,实则就是两个世界的事情。但大多数时间,虽是与他们无关的,“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回家,对政权”,从《长恨歌》中对流言、弄堂、服饰和饮食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王安忆在《长恨歌》中想要的上海就是这样边缘化的、生活的、普通的上海,王琦瑶从自己的弄堂闺阁,来到陌生的爱丽丝公寓,最后安定在了普通的弄堂“平安里”,在她不长的经历里面,人生几经起伏变化,既出入过上流社会的宴会,也曾穿行在平民街道间,但是只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她的生存方式。上海的弄堂让饱经苦难的王琦瑶,有了温暖安逸的生存之所。在这样边缘化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的描写下,是小说想要表现得上海的真正魅力。边缘化的上海形象让王琦瑶,这个代表着旧上海文化的女性,感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也表露出作家王安忆对上海爱与恨的态度。
3 爱恨交错的上海
《长恨歌》的叙述视角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将一个飞翔在天空中俯瞰上海的“鸽子”的动物视角确定为“上帝”的视角。鸽子全知全能叙事视角的选定和设置,包含了作者的叙事姿态和立场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冷静客观的,以动态的视角观察相对静止的城市与屋内缓慢流动的人生。[5]可以说,不管是刻意隐藏了男性身份的女性关系下的上海,还是被有意边缘化了的上海,作家在对《长恨歌》中的上海进行意象化的创作时,其中暗藏了自己对于爱与恨的态度。
3.1 日常美与文艺美对照
王安忆对上海的爱与恨的态度,融合在小说中随处可见的二元对照叙事中。《长恨歌》中的王琦瑶的确很美,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无意中被导演选中去试镜,当她踌躇满志的想要一展抱负时,却又落得失败而归的结果。相比之下,当她怀着平和的心态应邀来到程先生的照相馆,再出现时,俨然已是轰动一时的“沪上淑媛”。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成。小说有意的进行对比描写,以日常美战胜了文艺美的结果表明了作家对于日常之美的执着。
3.2 优雅与粗陋对照
美与丑的对照,应该是所有对比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堆关系了,《长恨歌》中自然也不乏这样的描写。吴佩珍、蒋丽莉二人,是王琦瑶少女时代的闺中密友,这二人的出现并不只对故事情节有用,对于王琦瑶的人物塑造也功不可没。吴佩珍的外形的丑陋与举止的粗鄙,刚好与王琦瑶的矜持、世故相衬;而蒋丽莉对待生活的懵懂与挣扎,王琦瑶的清醒与自然又再次形成对照。就在这样的对比展示书写中,一个活生生的王琦瑶的形象饱满而立体的出现在读者眼前。
3.3 聪慧与笨拙对照
人物之间的对照,不只在与自己的亲朋好友之间生效,和自己血浓于水的女儿之间也是一样。一生经历坎坷世事的王琦瑶生就了坚强和柔韧的品质,相形之下,自己的女儿薇薇却常显得笨拙、无力,在服饰潮流方面,二人的差距最为明显。不过,让人遗憾的是,看起来在各方面都要更胜一筹的王琦瑶,人生旅途却总是崎岖不平,最后更是以悲剧收场。母女二人截然不同的人生,造就了最后完全区别的命运,王琦瑶一生功利偷生,还是免不了无奈心酸的结局。这其中不得不说是有着作家精心的设计,对功利性的人生价值观的爱恨态度,随着王琦瑶人生的惨淡收场,已经不言自明了。
3.4 逃离与回归对照
邬桥的世外桃源生活,与上海繁华紧凑的生活构成对比,王琦瑶逃离上海不只是因为逃离战争,更是逃离伤心之地,李主任的离开让王琦瑶心生退意,爱情是她当时的全部人生打算,这个点的破灭对她打击太重。不过,在王琦瑶的心里,上海的繁华风情仍是她心所向往的,在短暂的心里斗争下,终于又回到了这个承载着爱与恨的地方。将邬桥与上海进行对照,先逃离继而回归,这是对上海的肯定,也是对上海象征的城市文化的肯定向往。
3.5 “战争与和平”对照
当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王琦瑶参选了“上海小姐”并成为了“三小姐”;当内战烽烟点起,王琦瑶独守在爱丽丝公寓中,安静的当她的贵妇人;当外面反右斗争进行得此起彼伏时,王琦瑶却又围着火炉和伙伴们有滋有味地说闲话。作家对时代大主题的可以回避,和对于日常书写的偏爱,固然是处于写作的整体考虑,但也进一步凸显了这种对比的强烈,更在这种对照中显露了爱与恨的态度。
《长恨歌》中作家王安忆将这些在二元对照碰撞中呈现出来的不同,放在上海这片文化地域上进行着筛选、淘洗,赋予了上海这样一个具体可感的城市,以远远超过其写实性的象征意味,这种隐喻的形象,处处可见,代表了作家对城市文化想象的爱与恨。
4 结束语
通过一系列对上海的描写,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呈现出一个女性化、边缘化、爱恨交织的上海形象。《长恨歌》构建出了属于她自己的上海艺术世界,深入挖掘除了上海城市文化的本质、精髓,想象出了一个“王安忆式的上海。[6]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