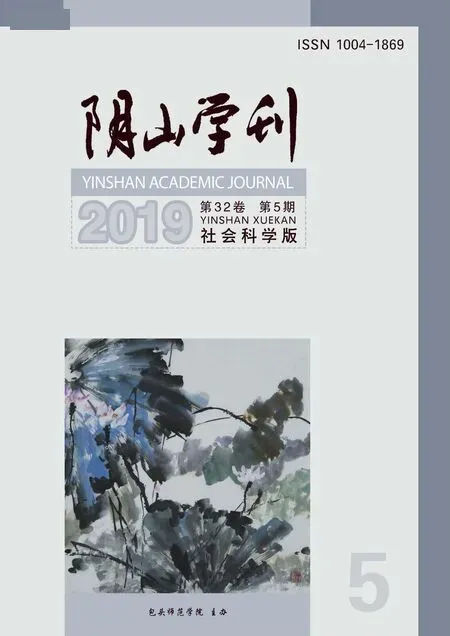逃离的姿态与空间经营
——论《奔月》对自由的书写 *
谷 雨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奔月》是鲁敏继《六人晚餐》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作品讲述了一个南京女子小六在一场旅游事故中,借用他人身份逃离到乌鹊县城的种种经历,同时,也展示了小六人为地“消失”后,被她抛在南京的众人的变化。
不论在情节还是叙事结构上,《奔月》都与福克纳的小说《野棕榈》有相似之处,小六更是无处可逃的威尔伯恩和回不去的高个子犯人这二人的结合体。对于逃离的主题和自由的思考,鲁敏一直没有跳脱出福克纳的思想层面。福克纳为自由的选择寻找出路,让个体对生存处境的超越转向共同自由,最终到达宗教性质上最高权威的建立,但鲁敏并没有试图探索出一条自由之路的指向,她的关注点在于逃脱这一反抗的姿态,意图在无解的困境中以积极的对抗带来一丝曙光。
一、逃离、反抗、自由与存在
(一)逃离即反抗,无处可逃的自由
小六为什么要逃离?她要逃到哪里去?她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当老警官例行公事地向小六发问,小六狼藉无解,最终她到底是琢磨出自己与别人的区别了:她是一只最普通的白蝴蝶,没有花纹,她不一样,她所求的就是消失本身。有关于逃离这一主题,不少学者将小六的行为定义为对庸俗日常的反叛。从现代性的层面考虑,这样定义是正确的,但不免有给逃离强行寻找动机的意味。实际上,小六的逃离是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动机的,如果非要强行给逃离的旅途设置一个终点,只能说小六逃离的全部意义是为了逃离本身。
社会、环境、集体、共同生活、境遇等是人类生存活动被划分出的一定范围,在这样的范围里,人类的一切活动就有了所谓的自由性,但同时也代表着,这样的自由只是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跳脱出自在的主体领域,进入更大的客观领域时,人类行动本身就会有诸多局限和约束。这种大意义上的环境约束,决定人类活动只能在社会这个整体大环境中得到被限制的最大自由;同样的,因为环境会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整个主体领域就会呈现出一个维稳的状态,即细小的变化不断产生,总体上一成不变的状态。庸俗的日常可以归为这样状态的一种主体领域。那么,逃离庸俗日常在现实中就成为了一种不成立的命题,除非将小六所去的世界描写成乌托邦式的世外桃源,一个虚构的世界。而在鲁敏最初的设计里,小六消失后的确是“去往了一个类似‘失踪者乌托邦’的所在地,那里聚集着落马官员、失败艺术家、假破产的商人、厌世的单相思者、过失杀人犯等等”[1],十足戏剧化,但后来被她全部推倒,她“觉得让小六逸奔在热乎乎的、同样平俗的生活里去,才具有普遍意义,以及由之而来的某种现代性。”
就像鲁敏在谈到《坠落美学》时说的,她“所倾心的不是坠落,是坠落之前的飞翔,或者说,是摆成飞翔姿势的坠落。”[2]略去现代性不谈,鲁敏所说的普遍意义,并不是小六逃离、追寻后想要得到的答案,而是逃离这个行为本身所隐含的意义。小六不是娜拉和思特里克兰德,本身没有觉醒的倾向和更高层次的追求,她固然对周围的一切有了厌倦的心理,她的出走却不是计划性的或者说建立在认识层面的追求。小六的行为仅仅出于一次偶然的巧合,某一瞬间迸发的冲动想法,更偏向冥冥之中人类共同命运的安排。就逃离的结果而言,若说逃离是对自由的追寻,这本身就更不成立。小六在乌鹊的发展和她逃离之前没有区别,乌鹊像是一个翻版的南京,舒姨代替了母亲的角色,给她带来了更多的纠缠;县城小超市争名夺利的工作环境更是原来写字楼里工作环境的直接写照;林子代替了情人和丈夫的位置,让她陷入了新的男女关系中。逃离过程中费劲得到的结果,不过是从一个环境投入了另一个相同的环境,最终不过是逃离无果;可以说,只要小六仍旧处在被框定的环境中,就不存在绝对的自由。
奔逃是为了脱离人间,最终目的地是月宫。既然月宫不存在,面对无处可逃的现实,鲁敏为什么还要坚持逃离的主题呢?阿伦特就法国存在主义言说“无家可归”这一特征上,提出了积极面对“荒诞”和“绝望”的解释:“人必须在荒诞中生活,以骄傲的对抗来生活,……永远拒绝在荒诞的生活中安逸求生”[3]27。这便解释了逃离的普遍意义,即反抗的生命价值。从小六逃离的行为开始,甚至更早地,从她产生逃离想法的那一刻起,对生活的反抗和抛弃就开始了。这里的生活不光指包括小六旧我在内的南京旧生活,还指包括小六新我的乌鹊新生活。就是说,逃脱即反抗固定的生活,同时也是试图将自我从被框定的范围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是对自我的追寻和本我的奔逸。结局小六又回到南京,这一次的回归实际上是又一次对新生活的逃离,一次一次地重复着“小六快跑”,是对“奔”“逃离”即反抗的再三强调。
(二)置换的存在,个人特殊性的隐去——主体的消失和他人的假想
探究小六逃离的最初契机——一场事故,可以发现,鲁敏用“死亡”“消失”来完成对“小六”存在的定位,也正是因为这些存在不同而导致的荒诞,赋予了逃离——反抗之上更大的价值意义。
雅思贝尔斯指出,存在必须由特定的途径去把握,最重要的是在与他者共同的群体交往中感知存在和从“极限境遇”去解读存在。小六“死亡”以后,在旧有的世界中,他人对小六的存在进行了个体所需的置换。贺西南将自己当作一个拯救者,他眼中合格单纯的妻子是一个等待他拯救的弱者,直到妻子的消失引出情人张灯的出现,贺西南才认识到小六的另一面,导致后来他推翻了心目中纯良的妻子形象,用活的“绿茵”取代了已经死去的“小六”。小六的消失,同样让张灯受到冲击,之前他眼中一个干脆利落的最佳床伴,摇身一变,成了和他最契合的心灵伴侣。真正意义上的小六死了,他内心隐秘的最佳小六出炉了。对于母亲来说,小六似乎一直存在,但实际上,现实中存在的小六已经变成用来安抚母亲内心创伤的虚幻的小六。在乌鹊,舒姨夫妻把小六当成他们儿子的替代品,林子一直把小六当成了依仗他的神秘恋人,聚香将小六当成一个开放洒脱的女导师。而小六则把自己变成了“吴梅”,让舒姨取代了母亲,钱助理取代了过去的竞争伙伴,林子取代了情人和丈夫,聚香取代以前的闺蜜。
死亡和消失作为一个契机,让他人重新建立对小六存在的认知,也让小六在他人取代身边人存在的同时,感知到了自己的存在。这一系列置换的条件之一,是作为存在主体的消失,也就是存在人物本身在交往中的不在场。存在毕竟是一个富含可能性的词,是“人以行动实现植根于自发性中的自由,并通过交际与他人的自由相联系”[3]8。当存在主体消失以后,主体与其他个体的联系已经中断,作为主体的行动已经不存在,对于主体的存在只能依靠其他个体进行联想推断,已经失去了存在最基本的现实性。被置换的存在只能说是存在于过去的既定印象,而置换来的存在,显然又是其他个体单方面的假想,这时存在的主体已经不是先前存在的主体本身,而是按照个体所需而被设计的另一个主体,是现实中用来替代或根本是虚构的主体(网络世界中的小六)。当然,置换的存在只是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的,并不是主体现实境况下最真实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对于其他个体而言,某一主体的存在可以被替换的原因。
贺西南自己都有感觉,绿茵只是一个妻子的代表,跟小六没什么区别,是生活给他的搭配,是现实中他要接受甚至维护的一个存在。对于张灯和林子来说,他们想象中的小六就应该是最契合他们本人的伴侣,而一旦真实的小六出现,这样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专属于他们的小六也即将不存在了。每个人都将他人的存在框定于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中,只要这个存在的主体的行动不超过他人的潜在设想,不超出他们所预定的关系,这样的存在就是成立的;而存在的主体,可以是小六,也可以是绿茵,甚至小五、绿叶皆有可能。这一存在可以随时被置换的事实,使得整个现实变得荒诞,当人从既有的关系中脱离出来,个人的独特性被完全隐去,留下的只有被他人划分和定义的共识部分,更可悲的是这一被套用在接替者的共识部分,也不是接替者个体存在的独特性。因切实生存需要而产生的存在置换,更体现出逃离这一行为背后,对荒诞生活所作反抗的价值意义。
(三)疾病的隐喻——逃离是每个人的“暗疾”
母亲认定小六的失踪是“发病了”,是遗传,家族就有的老毛病,DNA里就带着的。除去母亲自己情感上的规避,所谓的“失踪病”其实是病相投射与自我回避。不做文学上的过多阐释,疾病在普通人的印象中是不好的,应该被去除治愈的。对于母亲来说,丈夫和女儿的逃离为什么是一种病呢?恰恰说明在母亲的心中,她是渴望丈夫和女儿的病能够被治愈,认定他们的失位是不合理、不应该的。贺西南对小六还有留恋的时候,他一直坚信小六是失踪了,但他却从没有为小六的离开寻找理由,只是盲目地确信小六一定会回来的。似乎平安喜乐、生活安稳,并没有什么值得一个好好的人突然失踪,即便是消失了,那个人最终也一定会回来,毕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既定的安稳和现有的一切情感纠缠。除了母亲,没有一个人真心觉得小六得了“失踪症”,因为常理惯来如此,人不可能脱去夹杂在身上的责任和负累,就算是逃脱了,也一定有后悔和归来的一天。
世俗裹挟着情感的纠缠将人禁锢在既定的天地中,只有小六一个人以逃离的方式反抗,但这一行为最终被冠以病名,被母亲投以恶感,在母亲宣扬时,又被贺西南和张灯恐惧。疾病有向生和向死两种近况,包括母亲在内的人都将小六的逃离归于向死的行列,其本身就有对自身认识上的回避。对于他们来说,人本身想要超越固有的生存处境是困难的,对自由的追寻比不过世俗的安稳,这样的一种心境与其说是对逃离的回避,不如说是一种已知结果因而不愿尝试的无奈。但恰恰这样的无奈背后隐藏着每个人内心深处消失的念头,只不过他们没有像小六一样,通过逃离的模式外在地显现出来。
当贺西南发现小六已经不是他需要的妻子时,他从与小六的夫妻关系中逃离了出来,作为小六的丈夫,他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张灯疲于男女间肉体上的两性关系,伪造了一个虚幻的小六,最终逃到了网络空间去找寻心灵伴侣,从前耽于露水姻缘的张灯消失了。绿茵也是从现有的夫妻关系中逃出来,将自己对婚姻和家庭的全部幻想寄托于贺西南身上,因失败夫妻生活而幻灭的绿茵也自发地消失了。纵使这些人没有像小六一样,用逃离这样颇具仪式感的行为来宣告自己的“失踪病”,可他们意图将自己从之前固有的关系内抽离出来的行为,已经是自发地从一定的交往环境逃离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交往环境中的展示,虽然这样的抽离过程隐秘而含蓄,本质上与小六的逃离行为却没有什么差别。
鲁敏以往的暗疾叙事专注写人的伤疤、人的灵魂,指向人性的深刻。暗疾也不是指向自身,而是指向对意义的追问,在对意义的追问中就脱离不了个体与外界的关系。纵观小说中的“病人”,暗疾者实际上是孤独者,鲁敏以往总是让这些被暗疾缠身的孤独者走出来,让他们不溺于暗疾,有一定文学批判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鲁敏对于《奔月》中的“失踪症”并没有显露出宣判的锋芒,她不过是借母亲之口,探出每个人最隐蔽的病灶。《奔月》中的暗疾和以往的“暗疾”系列不同,并不仅是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文化病症,或是人性的困境和精神世界的痼疾揭露,这一次显然是鲁敏在价值世界上的深挖,人人皆有的暗疾使得逃离这一行为更具普遍意义。
二、空间转换
(一)空间维度的经营——点、面的叠合、回环与跨越
从一开始的“东坝”系列小说,再到后来的“城市”题材小说,鲁敏并没有局限于小说的特定空间,一直试图对空间做拓展性的转移和经营。《奔月》中所涉及的空间,就是鲁敏在城乡空间之外的空间展开。
从《奔月》的题目可以看出,鲁敏并不避讳将作品拿来与鲁迅的小说以及古典神话进行比照,其实本质上,三者都隐含着从人间到月宫的空间转换。但相比后两者单纯的人间、月宫两重空间,鲁敏在现代性的包裹下,有意利用时间的两相比照,将空间的维度拓宽、细化。总体上看,南京和乌鹊是同一时间线上的两个不同空间,大致可分为小六不在场的空间和“吴梅”在场的空间。再由这两重空间向内挖,又可以分化成由交际关系构成的数个小空间,具体可通过不同的交际关系进行分类。
首先是南京,有以贺西南丈夫身份构成的夫妻关系空间,也可以称为婚姻家庭空间;其次是张灯主导的男女两性空间到他之后沉溺的网络关系空间;有以回忆的方式向前展开的母女亲情空间;更次一层的有南京写字楼里的工作空间,闺蜜间的友人空间等。而乌鹊,几乎就是南京的小翻版,林子、舒姨、钱助理、聚香等人与小六的关系构成了与之前一模一样的小空间。这可以说是在同一时间线上,空间“面”层次的重叠和复制。
而在这些空间里,除了用人际交往的社会关系分类,还可以分为现实和虚构的两重空间。张灯虚构出一个假想的小六并与之谈情说爱的空间就是虚拟的网络空间,而母亲在丈夫和小六消失以后所杜撰的父女、夫妻和母女关系也都是虚构的空间。如此,就要涉及空间向内转的问题,由身体空间到精神空间的范畴,即由脚踏实地的人世间转向苍穹之上缥缈的月宫。以小六内心书写为主,她在不断地抽离过程中,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同样建立起了孤独者独属于个人的心理私密空间。在南京的整个现实大空间里,小六早前就已经将自己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她在网络上释放出自己被现实压抑的隐秘想法,因为网络世界不受拘束的特点,她得以释放了一部分真我。在之后与林子的交往过程中,小六受困于跟林子的男女关系,为摆脱不变的两性纠缠,她将肉身视为这段关系纠缠的牢笼,力图将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隔断开而产生了一种“决裂感”。实际上,由现实空间转而向不存在的精神空间的过渡,是对空间维度纵深层面的超越。
结局处小六归来,假设了以下四五种不同的回归顺序。
“贺西南公司—自己家—登陆QQ……
约闺蜜出来—绿茵茶餐厅—联系贺西南……
自己公司—登陆QQ—快捷酒店……
派出所—母亲家—自己公司……
登陆QQ—快捷酒店—派出所……”[4]
其实,这些都是小六回归路线上的不同“点”。最早的起点从她离开乌鹊开始,几条不同的回归顺序会引发小六接下来归家的不同支路,那么这些点就成了她回归路上的“拐点”:如果一个时机和次序改变了,在小六的预想里就有可能及时阻止某些替换她曾经存在的事实。但不论这些“点”如何替换顺序,“终点”都是小六又回到南京(已经抛下她的城市)这一既成事实。故事的起点从南京逃离,结尾止于小六回到南京,这一具有回环性质的发展,形成了“点对点”的精确对位。不论空间上如何置换,最终循环收拢性质的格局,都使人认知到一个事实:“我要疼,我要飞,我要我是我”的最后,通向的是无处可逃,而我失去了我的那一刻,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二)虚构的空间——追寻向月宫的逃逸
自古典神话起,想要从世俗红尘中脱离出来,创造者往往给嫦娥的逃离设计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缥缈月宫。奔逃的最终目的地是月亮,恰巧说明了逃离的不可能,奔月升天求得永生,是人们面对避无可避的死亡时的一种慰藉,一种归于理想世界的道家追求。至《奔月》,鲁敏将天空上的月宫换成无名之地,就给了无处可逃的孤独者一个暂时可以感受自由的安慰之地。
因个体需要而置换的存在,自假想开始,虚构的空间也就因为这个存在的出现而存在了。张灯和小六一度藏身的网络空间,小哥为舒姨和籍工虚构的密苏里世界,还有母亲幻想出的父亲与小六共处的无名空间,这一系列空间是他们在面对现实世界感到失望或是约束时内转而来的一个虚构空间。同样,虚构的空间反过来会赋予存在对象一定的空间意义。空间意义在一定层面上则出于个体需求,本质上说,就是个体对现处空间、对现实的规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虚构空间的迷恋和依靠,是每个人内心的暗疾寻找治愈之法,向最终的自由之所——月宫的无限趋近。
当然,像张灯、舒姨、母亲等人藏身在自己所幻想的空间里,其本质只是面对绝望的一种回避行为,是不需要任何勇气和努力就可以做到的稳妥举措,不具积极的反抗意味。这样的虚构空间并不是逃离的目的地,只能说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不是鲁敏所要追寻的月宫。网络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人们更多放逐自我的私密空间,像张灯这一类沉溺在网络世界的人数不胜数。但这样由现实空间向虚构空间逃逸的行为,已经不能看作为自由而抗争的全面逃离,更多的是偏向于趋利避害的规避行为。
不论是空间上的组合还是虚拟空间的设置,鲁敏在空间的经营上,大体都显示出一种大多数现代人对自由的无力感,而小六苦苦追寻的月宫,这个鲁敏以一种主动的态度来设计的虚拟空间,可以说是跳脱了整本小说弥漫着的无力感,不陷于自由出路的思考,从另一个层面以逃离者的身份敲响了希望之钟。鲁敏说,“我要做的只是跟小六一起走,即便走的是一条晦暗不明、悖论回环的小道——毕竟,可以时常抬头望月,有月亮照着,就不会有全然的黑,就不会慌与茫”[1]。从这段话里就可以看出,鲁敏要走的就是明知无路的路,月宫已经成了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正因为它的难以抵达却又高悬头上,便时时刻刻给人以追寻的价值,月宫这一虚构的空间也就有了引导的作用。那么,探寻她为笔下孤独者设置虚构空间的用意,应该是在飘逸的永恒哲学矛盾中,让追寻者在陷入无处可逃的绝望时因头顶的光亮而再次点燃希望,从而使逃离这一具有反抗意味的姿态立得更正,更具有积极意义。
三、结 语
与同类题材小说相比,《奔月》的情节设置和思想内涵都有着明显的不足,这既与作家的性别视角有关,也受到小说文本背景所隐含的现代性的影响。就其现代性而言,鲁敏的这次尝试是对当下庸俗日常的反叛,但《奔月》中小六的逃离行为并没有停留在浅显的现代性层面,鲁敏所探寻的并不是逃离之后的出路和结果。因此,《奔月》对于自由的书写,并不限于主体性觉醒和超越精神自由的层面,而是另一种“鲁敏式”的表达:一方面,鲁敏巧妙地经营着多重空间,在主人公逃离的过程中,逐步展示了一个关于永恒自由的无力现实;另一方面,她没有过分解读,更没有试图探索一条暧昧不清的理想主义出路。不论从空间还是个体与他人、环境等关系上看,殊途同归的命运和荒诞不经的现实都是鲁敏想要让人直面的问题,而小六以主动的姿态进行反抗,作为一个无意识的逃离者就有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反抗者意味。这样,《奔月》这部小说通过一个普通女人无目的无结果的逃离行为,就赋予了逃离这一姿态更深价值上的积极意义,给无处可逃的追寻者带去了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