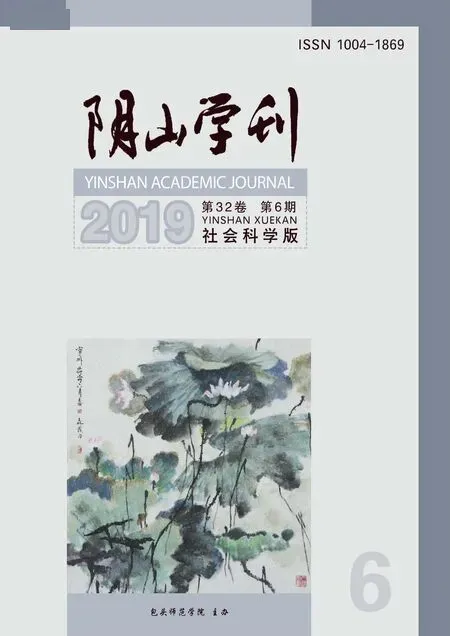《魏书》中“代人”的身份考辨*
高 俐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代人”是有关北朝至隋唐的史料及论著中频繁被提到的一个概念,其来源当与拓跋鲜卑政权早期的国号“代国”有关。学界主流认为,“代人”指的是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国及北魏政权中具有北方游牧族群文化或族源背景的人群。与此类似的称呼还有“代北人”“代北子孙”等。胡三省注《通鉴》言:“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以表达对当时门第阀阅观念的质疑,但对“代人”身份,特别是其划分标准的考辨,对中古史中族群关系和社会文化演变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于北朝史料中“代人”身份的政治意义,及其对隋唐时代观念的影响等问题,日本学者松下宪一在《北朝隋唐史料中的“代人”》一文中已有论述,但“代人”标准的判断仍存疑问。松下氏指出,“代人”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北人,然于“代人”中出身“汉人(晋人)”或其他族裔者,则未做详论。[1]需要指出的是,北魏太和改制以来,由于迎合朝廷主导的汉化政策和中原社会盛行的攀附炎黄的风气,北族成员在墓志和家谱撰写中常伪造出身,模仿或攀附汉人大族。相对而言,官修史书更具权威性,其中所称之“代人”自然符合北朝政权及社会对于“代人”的一般认定标准。故本文以《魏书》为依据,对不同族裔成员被划为“代人”之条件作一浅探。
一、汉人、晋人与“代人”
史料记载,北魏出身汉人的“代人”寥寥无几。据笔者统计,魏书中族源为汉人(晋人)且单独立传者为274人。其中为“代人”者仅区区四人:卫操、燕凤、许谦和来大千。举其首者,当属卫操,此人于《魏书·列传》中为首,甚至先于最早追随拓跋鲜卑部落联盟的一众北族酋长。可见在代魏统治者眼中,或至少在作者魏收眼中,其功勋地位不下于北人,也当被代魏国主视为可寄心膂之人。卫操出身于北边牙将,按照汉魏地方首长自署官僚的习惯,应为出身于并州北部的汉人。他自代国始祖拓跋力微时期便“数使于国,颇自结附”[2]卷二十三·卫操传,应该是奠定后来在代国权贵阶层地位的重要条件。其正式加入代国的时间为“始祖崩后”的穆、桓二帝之时。然而,莫含与其生活时代以及在代国政权中的地位相似,在《魏书》列传中则为“雁门繁畤人也。家世货殖,资累巨万。”[2]卷二十三·莫含传雁门繁畤为并州刺史刘琨最初割于代国的陉北五县之一,考其地望亦当为古代地,然其传中以汉人传统笔法写其出身,当是考虑其“家世货殖,资累巨万”的一方豪强地位。同样于代国早期之昭成帝拓跋什翼犍时期加入其政权的汉人勋臣燕凤、许谦则皆简书为“代人”,并以擅长天文图谶之学见任于代国。而同传中的张兖则似因其“祖翼,辽东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而被书为“上谷沮阳人”[2]卷二十四·张兖传。
然此类汉人中,似乎也有例外:李栗、刘洁皆为太祖从龙元勋,尤其李栗为二十一元勋之一,地位可谓汉人中最高者,后被诛,乃为太祖立威仪之始。刘洁亦内参帷幄,外掌大军,非一般汉人文臣可比。二者似乎并非出于汉人高门望族,但传中各具其籍贯而非“代人”,考其缘由,前者似因态度倨傲、目无主君,被剥夺“代人”这一与拓跋统治者类似“同胞”的亲密身份;而后者或因地位极显贵,不群于一般汉人出身的“代人”旧臣。此疑有待方家解惑。
稍晚加入代国的汉人中,出身清河崔氏名门的崔宏(玄伯)家世显赫,晋末以来历仕石赵、慕容燕、苻秦。但崔宏本人仍于道武帝拓跋珪时期便加入代国。同传与其同出一门的崔氏官员皆书为清河崔氏,无一人为“代人”。同样曾仕于苻秦和慕容燕的邓渊家族似非魏晋高门,然于苻秦、慕容燕已为名门。虽其人甚至其父加入代魏政权也不晚于道武帝时期,其传仍书为“安定人”。
事实上,以崔氏为代表的魏晋以来的大小士族高门,才是北魏政权中汉人的典型。考诸《魏书·列传》中的汉人列传,确乎可为魏晋以来汉人士族高门的家谱,基本囊括了北方所有的豪门大族,后期更是收纳了南朝不少高门乃至帝族降者,如渤海高氏高湖及其子弟、渤海封氏封懿及其子弟、辽东公孙氏公孙表及其子弟、河东薛氏薛提及其子弟、赵郡李氏李顺及其子弟、晋朝皇族司马氏司马休之及其他宗室、陇西李氏李宝及其子弟、范阳卢氏卢玄及其子弟、博陵崔氏崔鉴及其子弟、南齐皇族萧氏萧宝夤及其子弟,等等。
笔者认为,在出身汉人(晋人)的众多人物中,之所以“代人”寥寥无几,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地域和时间上说,拓跋代崛起于并州以北苦寒之地,在北族中汉化亦属较晚,其早期历史中必然只有少数如卫操等延边汉人得以与之接触并以自己的才能为其重用,从而被接纳为“代人”这一核心集团的一员,而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太武帝拓跋焘时代以后,北魏统一北方的大势已成,内部各集团成员之身份、职能亦已相对固定,新加入之汉人不可能再有佐命元勋之功,加之颇多其他政权之降将降臣,代魏统治者必将有所顾忌,故而这些汉人从文化心理上与代北之人融合的机会更少,自然难以成为“代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北魏最高统治集团本身的文化心理也日渐汉化,这就不可能不带动整个朝廷文化风向的汉化,最高统治者尚且欲脱离“代人”文化,皈依华夏,那汉人便更没有动力或理由“代人”化了。其次,从家世地位上说,拓跋代政权进取中原的过程中,不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出于控制汉地广大民众的功利性目的,都必然受到魏晋以来以门第阀阅品评人物之风气的强烈影响,因此他们所收取任用的汉人,特别是曾供职于其他十六国政权的汉人,也以这些高门望族出身的士人为主。而后者承袭累世族望,必然更愿意以传统家世籍贯自标,服务于五胡朝廷只为保持家门不坠和乡里晏安,内心实不愿与“虏”为伍而为“代人”,父子并显的崔浩之诛及其姻亲高门的一时诛灭,也反映了效力魏廷的汉人高门事实上与“虏廷”的离心离德。这一观念贯穿整个鲜卑当朝的北朝时期,直到隋朝仍旧。这从隋尚书杨素对南朝萧氏萧琮嫁女于钳耳氏羌人之不解便可见一斑[2]卷三十五·崔浩传。再次,从才能类型上讲,寥寥几个“代人”汉人无一人为纯粹经学儒士,而皆为懂得图谶天文等有关开基立国和行军用兵等学问的汉人,可以理解的是,在代魏万基草创的初期,其统治者不太可能过多重用异族的汉人来参谋军机大事,故而仅有少数几个如卫操等知根知底的汉人得以参谋帷幄。而多数被收取的汉人经学儒士只能作为其收取汉人民众信任的装点门面之人,这也客观上导致了多传承高门家学的儒士与代魏上层的距离,不被后者接纳为核心集团的“代人”。事实上,即便如清河崔氏这般高门,其真正最受重用的崔宏、崔浩父子最初也并非以经学受任,而是受任“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同时,以骑射征伐崛起的“代人”们恐怕也难以接受风雅儒士进入自己的生活交往圈,这也导致了“代人”集团中汉人寡少的现象。
综合以上分析,出身汉人者若被称为“代人”,大致要符合四个条件:一是早期家世未经过慕容燕等其他胡人政权宦途而直接加入拓跋代政权;二是出身寒族,无前朝世家大族背景;三是乡里处于代国初期版图内;四是其个人并非纯粹的经学儒士,而有占卜图谶或军事等“实用”才能。
二、“北人”并非皆“代人”
《魏书》列传中,人数最多的是汉人,其次则为北人。笔者此处所谓北人,即北方包括五胡十六国建立者在内的诸多少数部族——拓跋部落联盟的各部族当然也在其列。据笔者统计,除十六国王室成员列传外,北人中为家族之主列传者共75人,其中标为“代人”者62人,占到近83%。可见“代人”多出身于“北人”,但“北人”并非必然被认为是“代人”,兹将其中的差别及原因试分析如下。
姚薇元先生在《北朝胡姓考》中所列的宗族十姓,乃出于拓跋氏同门,从未分立政权,自不待言。出于其他氏族而始终围绕在拓跋部落联盟核心者如“勋臣八姓”和道武帝解散部落中被重新编制的“内入诸姓”后裔,如尉古真、穆崇、和跋、奚牧、莫提、庾业延、叔孙建、奚斤等,也自然皆为“代人”。而在拓跋鲜卑政权形成之前已经世代为北族显贵,特别是匈奴、蠕蠕集团中的上层贵族,虽加入拓跋集团甚早,贡献甚巨,似也多不被称为“代人”。举其要者,为“刘虎之宗”[2]卷二十三·刘库仁传、“南单于之苗裔”[2]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的铁弗刘库仁虽贵为外戚,也只书“为南部大人”[2]卷二十三·刘库仁传,不称为代人。与之类似者,宇文氏宇文福虽于南迁后融入“河南洛阳人”[2]卷四十四·宇文福传,然“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且其祖曾“仕慕容垂”,终不得传为“代人”。闾毗出于蠕蠕王族郁久闾氏,“本蠕蠕人”[2]卷八十三上·闾毗传。
事实上,这些北人王族后裔与“代人”的语言和习尚,应是最为相近的。之所以不列为“代人”,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存亡继绝”或对诸太后所出之族的格外尊重和荣宠;二是这些王族所代表的政权都曾是北魏统一北方的劲敌,后虽国破归附,北魏统治者对其之警惕也难以尽除,其亲近感毕竟难比共患难同起兵且离散部落后长期融合的“代人”集团成员。“代人”中的勋臣贵戚也恐不愿与这些亡国贵族同列,因此形成了这样不同的文化认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曾经敌国属下的其他北人,则很容易接纳为“代人”。费于,按姚先生所考为“西方费连氏”所改[3],其祖费峻于泰常年间太武帝平赫连夏才归国,仍被书为“代人”[2]卷四十四·费于传。似可为佐证。
另外,虽然也从早期便加入代国创建的军事政治活动,但由于族属稍远,在道武帝离散部落后仍然独立领有部落者,则仍以其出身部落及籍贯列传,而不称为代人。这方面的典例为契胡酋长尔朱荣。其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2]卷七十四·尔朱荣传其归国亦早矣。然而作为领民酋长,长期别处一部,北魏迁洛之后仍令其父“冬朝京师,夏归部落”。可见与其他登国初解散部落的北人明显不同,带有“属国”性质。因而只书“北秀容人也”。与之相类而可作比证的是,《北史》中斛律金家族也因“高车以类粗犷,不听役使,得别为部”,“世为第一领民酋长”。而同样曾世代为领民酋长,统领拓跋氏外戚独孤部的贺讷“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甚见尊重,然无统领”,因此被书为“代人”。[2]卷八十三上(补)·贺讷传可见,登国年间的部落离散政策,既是拓跋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代国过渡的标志性事件,也正是“代人”身份产生的源头。“代人”基本上成为了代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融合不同出身之人而形成的“国族”。
综上对比分析,可知“北人”被划为“代人”之条件大致有三:第一,太武帝时期前已加入拓跋代部落联盟,且未仕宦于慕容燕等其他北族政权;第二,无高车、蠕蠕、慕容燕、宇文鲜卑等其他北族敌对集团之王族背景;第三,登国年间道武帝离散部落后已无独立部落可领,纳入代国统一军事政治之中。
三、北魏迁洛后“代人”之演化
从时间上看,《魏书》中“代人”称呼多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而在魏廷迁洛之后,南迁的北人中祖考为“代人”者大多着籍洛阳,称“河南洛阳人”,或加上“其先为代人”。如基儁、山伟、刘仁之等。而留居代北并未南迁者,竟也不再简单以“代人”称之,而是仿效汉人籍贯,具体到某地。如并未南迁的斛斯椿为“广牧富昌人”,贺拔胜为“神武尖山人”。“代人”的称呼逐步退出了《魏书》的记载。这一简单的称谓变化事实上反映了北魏政治、族群、社会文化等方面重大的历史变迁。
自拓跋鲜卑南迁阴山地区,特别是道武帝登极于牛川,重建代国政权以来,代——北魏政权一直实行对南、北两个方向进行经略的政策。向北,自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年间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多次大举出击柔然及其所统高车诸部,每次虏获人众畜产少则数万,多则“弥漫山泽,蓋数百万”[2]卷三十五·崔浩传。北魏使柔然、高车等政权或部族势力难以长期休养生息,成功遏制了其势力的崛起和对北魏北方疆域的威胁。同时,大量虏获的畜产和强迫劳动的俘虏为北魏增强了经济实力,如北魏神麚二年(429年)大破柔然后虏获畜产数百万计,“自是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价贱”[4]卷一百二十一·宋纪三。被征服部落兵卒被迫从征,不断补充和增强北魏的军事实力。以至于南征刘宋,兵围盱眙之时,致言守将:“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鲜卑)人……卿若杀之,无所不利”[4]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而柔然、高车等漠北酋长贵戚的归附也壮大了北魏政权以北人为主的统治集团的力量。总体来讲,北魏向北方的经略为其政权补充大量的将领、兵卒、战马等资源,极大地充实了国力。
向南,北魏逐步击灭后燕、赫连夏、北燕和北凉政权,并且出击西域,基本完成对中国北方的统一,发展成为与南朝分庭抗礼并占据军事优势的华夏正统的有力争夺者。在这一过程中,北魏政权不断吸收和整合上述政权中各个族群的人才、政治制度和经济资源,一方面为进一步入主中原争夺华夏正统积累经验和实力,同时也利用其制度和人才优势为其北向经略服务。慕容白曜、源贺等属此类。
这种交替向南北经略的策略成为北魏政权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在这种向南北两个方向发生了经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包括旧都盛乐、平城以及六镇等地的整个“代北”地区,都是北魏王朝的腹心重地。居于其中的“代人”则是最受北魏政权宠信,被寄以心膂、“本充爪牙”[2]卷九·肃宗孝明帝纪。
然而,随着太和改制和迁都洛阳,北魏整个国家的政策发展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向。北魏改变了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经略的发展模式,转而效仿魏晋等传统汉人王朝“守在四夷”的国策,对北方柔然、高车等游牧族群及其生活的广袤塞北地区采取维持现状、羁縻防卫的“规遏北疆”姿态[2]卷九·肃宗孝明帝纪。六镇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本北向经略的前沿、整合北方族群融入“代人”的基地和邻近都城的腹心重地,逐步沦为远离国都、不异于魏晋边塞的穷荒边疆。原本作为京畿至重之地的平城左近地区地位也逐步被边缘化。“代北”地区由国家的腹心重地逐步沦为北部边疆。就在北魏政权频繁征伐南朝以图统一天下的过程中,代北子弟却因在整个国家战略中地位的下降而仕进受阻、待遇下降,“兹恩仍寝,用迄于今”[2]卷九·肃宗孝明帝纪。
在文化方面,最高统治者孝文帝及其后继诸帝不遗余力地推进汉化政策,称汉语为“正音”,代北语言为“北语”,要求南迁者落籍洛阳,且逝后不得归葬代北[2]卷七下·高祖孝文帝纪。这说明北魏朝廷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代人”集团和代北文化继续存在的意义,力图消解这种观念和现实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代人”称谓从不被提倡逐步成了一种“政治不正确”,越来越少地出现于其官方记载中。
此外,北魏后期,“代人”称谓或已成为代表早期开国集团的特定称谓,即这一概念可能被赋予了某种时效性。而后期这些人物虽为北人,抑或就是“代人”后裔,但并未参与早期创制代国之功,故“代人”这一代表南迁之前的代国统治集团的具有一定特殊政治内涵或待遇的身份便不再加诸其上了。
当然,记载的减少和缺失并不意味着“代人”群体的消失。随着北魏不断经略南北,掳掠和迁徙大批人口进入包括六镇和平城周边的代北地区,一个包括部分“代人”在内的不断扩大的代北人群体也在逐渐形成。他们在相似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中相互接触、同化,特别是共享着有别于中原汉人或汉化北人的文化认同,因而逐步形成了共同的“代北人”或“北人”意识。这与本文前述“代人”的形成过程非常相似,是一个不同族源的人群在共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逐渐凝聚成的具有共同的身份认同。与“代人”不同的是,这一扩大化的北人群体内部仍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各自的族群身份,如东魏权臣高欢对其世子高澄临终嘱托所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必无异心”[5]卷二·神武纪,又如羯胡侯景轻视高澄言:“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5]卷二·神武纪。说明这一群体还没有完全丢失其各自族源的文化印记,没有凝聚成一个如“代人”一般的新的族群。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代人”群体的扩大和延伸。
“六镇之乱”、改镇为州、北魏分裂等重大变局中,“代人”群体也逐步分化、演变。“六镇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太和改制与北魏迁都后六镇军民在官制迁转、赋税制度、族群身份等方面逊于内地州郡之民。因此,为稳定边镇局势,北魏朝廷在平定叛乱后推行改镇为州的政策,如此一来,原本可以互相视为同为“代人”的代北之人便分成了桑梓各异的不同个体,似也利于消解原本可能造成与汉化朝廷对抗的“代人”认同。
然而,着籍于新设州郡的“代人”并没有如其所愿地消解于北魏社会中。如前所述,代北地区的北人本已经逐步形成一个更为广泛和松散的,包括“代人”在内的北人群体。其主体集结在出身怀朔镇的高欢麾下,成为东魏、北齐政权的统治基础,如库狄迴洛[5]卷十九·库狄迴洛传、侯莫陈相[5]卷十九·侯莫陈相传、薛孤延[5]卷十九·薛孤延传皆此类。较少的一部分集结在宇文泰麾下,形成西魏、北周政权的统治集团,达奚武[6]卷十九·达奚武(附子震)传、尉迟迥[6]卷二十一·尉迟迥传、梁椿[6]卷二十七·梁椿传为其中代表。可以看到,随着六镇之乱后代北人群政治军事地位的上升,“代人”身份也得以在《北齐书》《周书》等历史书写中重现。可见,“代人”身份在官方记载中的隐浮,似乎主要取决于其所处政权的文化立场。
集结于东魏的北人恃其人众多于西魏,军事实力足以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在其统治中颇多族群偏见甚至压迫。如高隆之、高德政言:“汉妇人(李祖娥)不可为天下母”[5]卷九·文宣李后传,又如韩凤嫉汉臣如仇曰:“汉狗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等[5]卷五十·韩凤传。这也导致了北齐朝野代北人与汉人或汉化的其他族群的紧张关系和社会分裂,未能发挥出其军事和经济优势,在与西魏、北周政权的不断争夺中日趋削弱,最终亡国。与此相反,西魏、北周政权自感其代北兵力不足,不得已从立国之初便信用关中汉人及其他族群的地主豪强,以复周古制之名行胡汉杂糅之实,有效地将六镇代北勋贵与关中豪强大族笼络、结合为日后北周直至唐前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关陇集团[7],进入西魏政权的“代人”也最终演变为关陇集团中的“代北子孙”。
在开放包容程度突破前代的隋唐王朝治下,这些代北子孙们也最终逐步淡去了其代北人群的身份界限。成为中古中国族群融合与互动的大潮后扩大了的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 论
综上所述,《魏书》中的“代人”是一个代表北魏早期开国创业之功的特殊群体,可谓北魏最高统治者最为信任的统治集团。被称为“代人”者,基本都是代国创始时期居于境内或邻近地区的北族和汉人。他们具有和政治军事斗争直接相关的图谶、天文、骑射作战等技能,可以直接服务于代魏政权的创立和发展。他们基本没有其他敌对政权的世家大族背景,更易被拓跋氏最高统治者信任,也容易被整编调遣,从而形成了“代人”集团这一国家支柱力量。
随着北魏太武帝基本统一北方,北魏国家开基创业之功基本完成,“代人”集团也基本不再扩大,而是随着朝廷的汉化政策而逐步被淡化、转化。其中一部分南迁洛阳并依据朝廷政策成为“洛阳人”,留居代北者则基本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六镇之乱”和东西魏的分立。随着“北人”本位主义的回潮,“胡化”对“汉化”的反击,“代人”的历史书写得以在《北齐书》《周书》等历史书写中重现。其后裔则成为北朝史乃至隋唐史中的扩大化和模糊化的“北人”或“代北之人”。
北魏之“代人”的来源范围之广要超过完全按照族裔划分后赵、前秦等政权的“国人”,体现了拓跋魏政权经略、涵养天下的心胸与格局超过其他五胡,无怪乎其成就与历史评价也非五胡其他政权可比。隋唐以来“代人”概念的逐步淡化与消失,也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族群之间由界限分明到逐步模糊、混同的历史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