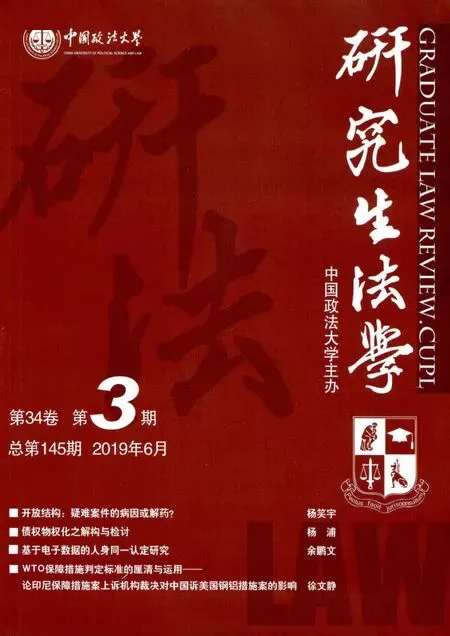法外施仁的背后:以清代“存留养亲”论传统法特质之原理
杨 晔
一、问题的引出
(一)研究与问题
具有悠久历史的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制度之一。该制度是我国传统社会法律伦理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为悯恤尊亲与老人而对犯人实行的一种变通的刑罚执行制度。(1)参见钟莉:“论‘孝’与北魏存留养亲制度”,载《法律史评论》2011年期,第153页。其展现出古代刑法人性化的一面,与中国古代传统法过时、落后与不近人情等倍受批判的印象有所不同。(2)参见岳纯之:“死刑复奏 存留养亲 优恤女性 古代刑法的人性化一面”,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9期,第78页。而学界关注存留养亲制度,主要着重于其展现传统法的“孝”的特点与以人为本的精神,以及传统刑法的人性化与人道悯恤等诸多方面。具体而言,相关研究可分为四个层面:第一,在横向层面,存留养亲制度被认为具有伦理性、人本性与人道性。其一,伦理性,存留养亲体现着孝道入法,核心是为了维护传统的伦常秩序,是法律儒家化与伦理化的重要表现之一;(3)参见张纪寒:“存留养亲制探源”,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476页。作者认为“存留养亲的核心是国家部分放弃对犯罪的惩罚权利,帮助犯罪人完成其孝养长辈的责任,以巩固亲伦关系,强化人们的忠孝价值观念”。龙大轩:“孝道: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价值”,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76页。作者认为“法律运行以维护孝道为宗旨,出现存留养亲、宽容复仇等各种屈法以伸伦理的制度和惯例”。其二,人本性,“存留养亲”等制度被认为体现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4)参见高绍先:“传统刑法与以人为本”,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4期,第68页:“存留养亲即含有缓刑性质,在当时战乱不休,社会动荡,家庭破碎的现实下,到了一定的安抚人心、稳定统治,减少社会问题的作用”。其三,人道性,“存留养亲”制度表现出人道主义精神。(5)参见张兆凯:“论我国古代刑律中的人性化成份”,载《求索》2006年第11期,第212页。作者认为存留养亲将儒家的孝道观念注入刑律之中,因之刑律更合乎人性与人情之理。第二,在现实层面,将存留养亲制度与当下热点案件相结合,论述该制度对现代法律体系与刑罚执行的借鉴,或者分析其当下适用可能与改进建议。(6)参见杨淼鑫:“‘存留养亲’制度的反思与借鉴”,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张智全:“‘存留养亲’传统司法制度刍议”,载《人民法治》2015年第12期。第三,在纵向层面,就“存留养亲”制度设计的纵向演变来看,梳理了该制度在各朝各代的基本情况,以及整体的发展趋势。(7)参见洪佳期:“《唐律疏议》中的留养制度”,载《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徐慧娟:“《唐律疏议》中的孝伦理思想”,载《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四,历史层面,分析存留养亲制度在传统帝制时期得以存在与运行的合理性与正当性。(8)参见刘希烈:“论存留养亲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133页;盖煜聪:“论存留养亲制度的合理性及现代适用”,载《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11期;张纪寒:“存留养亲制探源”,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王碧萍:“古代存留养亲制度研究”,湖南工业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杨翼:“论中国历史上的存留养亲制度”,复旦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夏静:“我国古代存留养亲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可见,对于“存留养亲”制度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但也相应地存在着问题:即对该制度的认知,更多地停留于伦理性与人文精神之上,强调其反映传统法的悯恤与人道,而未看到其在具体实践中的认定标准与限制;也没有更进一步探析该制度所具有伦理性特质的背后蕴含的价值逻辑。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问题,其一,在看到“存留养亲”制度所代表的传统法伦理性的特点,而忽视其在实践中的情况。包括“存留养亲”在实践中是如何认定的?其认定的标准是什么?对不予准许的存留养亲,其“限制”又涵盖哪些情况与标准?解决该问题,从实践的角度将更为充分地理解该制度的制度设计与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在认识“存留养亲”制度的伦理性特质与实践中标准之后,蕴含在此二者的背后,该制度产生原因、价值逻辑与基本原理又有哪些?对该问题的探析,将以“存留养亲”这一独特的制度出发,抽象分析其伦理性特质的来源与架构,从而为进一步分析传统法的特质与原理提供另一种思路与路径。
(二)路径与对象
“存留养亲”制度承续着传统法伦理性特点,在清代的《刑案汇览》中被称之为“法外施仁”。(9)参见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法外施仁”原文出自“本部查留养一项,原系圣朝矜恤孤独,法外施仁之至意,所以留养者存留养其亲也。”此外还有于第58页:“特宽本犯之罪,予以枷责,存留养亲,系属法外施仁”;第39页:“查犯罪存留养亲,原系法外之仁,非为凶犯开幸免之门,实以慰犯亲衰暮之景”;第44页:“龚奴才着施恩准其留养。此系法外施仁,嗣后不得援以为例”等等。而探索此“法外施仁”背后,传统法更为广阔与抽象的样态特质与来源原理,存在着两个逻辑路径。一方面,从制度到实践再到理论抽象的逻辑理路。学界对“存留养亲”的制度在各朝各代的制度与立法有了较为丰富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探究其背后具体的司法实践情况,最后再进一步考察二者背后的价值逻辑。另一方面,纵向与横向两种角度对该制度分别分析,再将此二者结合起来考察,并加之以理论概括。此两种路径实质上是一致的,本文以“存留养亲”制度为研究对象之时,首先对该制度的纵向发展进行考察,也是分析制度层面的演变过程;其次,对司法实践与制度适用的部分进行分析,也是以某一时期为研究对象的横向分析,具体而言还以该制度的内容与形式等维度展开;最后,两条路径都将在前者分析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概括与抽象,分析其特质背后的来源与原理。
而对“存留养亲”制度加以分析,本文则选用清代为研究时期。主要包括三个原因:其一,存留养亲制度在清代承继前代的制度设计与经验,并具备了新的变化。清朝是存留养亲制度适用较为成熟与完善,并且是最有成效与效率的时期;(10)参见贾康:“论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载《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7页:“纵观中国皇权专制时期各朝法律中的存留养亲制度,清朝是运用存留养亲制度较为成熟、完善的”。周祖文:“清代存留养亲与农村家庭养老”,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第129页:“有清一代,犯罪存留养亲的适用最为完善和广泛”。吴建璠:“清代的犯罪存留养亲”,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6页:“清代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运用犯罪存留养亲制度最有成效”。其适用宽严与价值取向同前期相比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达到了最高峰。(11)参见张纪寒:“存留养亲制探源”,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476页:“所以清朝存留养亲的实际条件比明朝大为放宽,不仅在实体处理上有一系列的成案与例文,程序上也有一套从声请留养到枷责发落的规范,该制度可以说在清代达到其发展的历史顶峰”;李俊颖:“孝与法的冲突——浅析清朝存留养亲制度的新发展”,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第72页:“自北魏创制,经唐宋时期的发展,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得到进一步完善,成为我国古代一项卓有成效且极具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其二,清代作为帝制末期,各类制度的发展形态具有一定代表性。明清时期被认为是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时期,传统帝制体制下的各项制度更进一步发展完备与成熟,有利于了解“存留养亲”制度发展至极致之时的基本样态。(12)参见何捷:“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载《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第178页。其三,清代对“存留养亲”制度的具体适用有较为丰富经验与研究材料。清代对存留养亲制度的适用,开始出现常态化、规范化与严格化等特点,《刑案汇览》中有关“犯罪存留养亲”的诸多案例可以展现出其研究材料的丰富。(13)参见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299页。文中作者认为清代的存留养亲,具备类型的多样化和规制的严格化,以及均衡的法律措施和合理性两个特点。总言之,以清代的“犯罪存留养亲”为研究对象,从纵向的制度演变与横向实践适用两个维度进行展开考察,有助于探究“存留养亲”制度“法外施仁”的背后,其所具有的伦理性特质的实践逻辑与来源原理,也能进一步探索传统法的基本精神与法律原理提供相应理论支撑。
二、纵向分析:“存留养亲”的制度与嬗变
作为伦理性特质的代表与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表现之一的“存留养亲”制度,其在中国传统帝制时期存在一种发展与演变的历程。自明代始设“犯罪存留养亲”,而清代沿袭此项规定。虽然明清的“存留养亲”制度在适用实践上相差较多,但其二者在律条立法规定上具有一贯性,并且实践中成效也与前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因而对该制度历史嬗变,可分为明清之前与明清时期两个阶段加以分析。
(一)明清以前
“存留养亲”制度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个案的形式实行后,大体在明清之前经过初创实行、定型确立与继承变化三个时期。第一,“存留养亲”制度最早初创实行于魏晋南北朝。具体溯源于勾容令孔恢一案,孔恢本应“弃市”与“大辟”,但“以其父老而有一子,以为恻然,可特原之”(1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74页。。此处置作为一时举措,缺乏普遍适用性。而后“存留养亲”的制度设计则表现于北魏孝文帝时的诏令:“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15)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著:《中国历代刑法志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而将存留养亲制度从令格的形式更进一步规范化与普遍化的是北魏律中的规定:“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16)(北齐)魏收:《魏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3页。。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赡养尊亲年老亲属的“存留养亲”制度开始逐步确立与适用,作为以“孝”入法、引礼入律的典型表现。(17)参见郑彦君:“历史上的孝道入法”,载《宁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143页。
第二,“存留养亲”制度定型与确立于唐代。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有关“存留养亲”制度,则较为完整地保留于“死流罪应侍家无期亲成丁之处置”一条中。(18)参见李文玲、杜玉奎:《儒家孝伦理与汉唐法律》,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谓非会赦犹流者”“不在赦例,仍准同季流人未上道,限内会赦者,从赦原”“课调依旧”“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计程会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应侍,合居作者,亦听亲终期年,然后居作”。(19)钱大群:《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113页。唐代的律文已经对“存留养亲”制度有了更为全面的规定,以侍亲为中心,对犯人的死罪、流罪时适用的条件与程序加以规范。可看出唐代法律条文设计的用意,依旧以“侍亲”为主要立法目的;(20)参见洪佳期:“《唐律疏议》中的留养制度”,载《枣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第77页。其实质是通过法律对孝行与“养亲”的维护,一方面使得礼与法更为紧密结合,体现了礼法结合的整体精神;另一方面,使孝道进入传统社会的行为规范之中,维护传统社会的伦理秩序。(21)参见徐慧娟:“《唐律疏议》中的孝伦理思想”,载《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45页。
第三,唐以后的时期,则是“存留养亲”制度继承与变化的时期,并主要集中于宋、金与元代三个时期。其一,宋代基本沿袭了唐律的相关“存留养亲”的规定。《宋刑统》中规定:“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周亲成丁者上请。犯流者,权留养亲。注云:谓非会赦犹流者。又云:不在赦例。注云:仍准同季流人未上道,限内会赦者,从赦原。又云:课调依旧。又云:若家有进丁及亲终周年者,则从流。计程会赦者,依常例。又云:即至配所应侍合居作者,亦听亲终周年,然后居作。”(22)(宋)窦仪等详定,岳纯之校证:《宋刑统校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8页。可以看出基本上宋刑统与唐律之间,仅存在字词的差异,没有较多的变化,照搬与复制了唐代的规定。(23)参见马洪伟:“存留养亲:传统司法的情理表达及其当代价值——从《刑案汇览》一则案例说起”,陈煜编:《第六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集 新路集 第6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283页。其二,金代出现了明显不同于其他时期的制度构造,即推行“官与养济”来对“存留养亲”实行加以限制。(24)参见钟莉:“论‘孝’与北魏存留养亲制度”,载《法律史评论》2011年期,第153页。其理由则为“在丑不争谓之孝,然后能养。斯人以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与养济”。(25)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76页。除此之外,还有相关例证。(26)相关记载包括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76页:《金史·海陵纪》记载,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沂州男子吴真犯法,当死,有司以其母老疾无侍为请,命官与养济,著为令。”被认为是最早适用“官与养济”的例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编著:《中国历代刑法志注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页: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尚书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为刘祐殴杀。祐法当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余,家无侍丁,上请。上曰:范德与祐父母年相若,自当如父母相待,至殴杀之,难议末减,其论如法。”但不可否认的是,金代原已有“权留养亲”的法律规定,并看到“存留养亲”在实践中的弊病,以“官与养济”的形式在个案中替代原有的“存留养亲”,维护该制度应有的立法原意与执行权威。(27)参见吴昊:“金元时期的存留养亲制度初探”,载《华章》2011年第22期,2011年第22期,第2页。其三,元代对“存留养亲”制度的变化主要在于进一步放宽其条件。元代法律规定:“诸犯死罪,有亲年七十以上,无兼丁侍养者,许陈请奏裁”;(28)(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90页。“诸窃盗应徒,若有祖父母、父母年老,无兼丁侍养者,则刺断免徒;再犯而亲尚存者,候亲终日,发遣居役”。(29)(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60页。可见主要的变化在于年龄、罪名与血缘亲疏的放宽,以及没有流罪的存留养亲的规定,并在一些案例中显示出灵活适用的特点。(30)参见王可心:“存留养亲制度的演进及其意义”,载《商情》2015年第24期;金元明:“存留养亲制度历史沿革”,载《祖国》2017年第8期,第295页;沙金:“存留养亲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页;谢渝:“存留养亲制度的历史沿革及价值分析”,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页;吴昊:“存留养亲制度流变探析”,西南政法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16页。但实际上,不管是年龄认定的数字变化还是血缘亲疏的放宽,都具备了元代时期的独特性,没有改变整体上促进“存留养亲”制度逐渐放宽的发展大方向。(31)参见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页。
从魏晋南北朝至元代的“存留养亲”制度的发展来看,可看出:早期初创与定型时期的“存留养亲”,其制度贡献更多于将“侍亲”“养亲”等孝道伦理的实践,逐步固定化为规范化的法律制度。其整体趋势基本符合法律儒家化的特征发展,促进儒家伦理的法律化以及法律制度中体现孝道秩序;并且主要规定了“存留养亲”的准予条件,更侧重于从正面角度对留养条件加以不断细化与严密,如在流罪上适用的细化与血缘关系上的放宽。其实质更为注重该制度的内容意义,强调在法律中体现孝道伦理与礼法结合的实质内涵。
(二)明清时期
从明代开始,“存留养亲”制度就首次以单独的条文出现,具体在《大明律》中被设置专条进行规定。(32)参见陈煜:《第六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集 新路集 第6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3页。并且,律文的内容相较唐代有所改动,并被清代基本承袭并添入注释,于乾隆年间改定,律文的具体内容为“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废)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从清代律文可以看到明清两代有关“犯罪存留养亲”规定的变化与特征。(33)吉同钧纂辑、闫晓君整理:《大清律例讲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而明清律文虽然相同,却同时展现出“从宽”与“从严”两个相反的趋势特征。一方面,明清的“存留养亲”制度都相较之前唐律的规定而限缩了适用条件,主要展现于相较唐律的“犯死罪非十恶”被改为“非常赦所不原”,较唐为严。(34)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75页。尤其于明代的司法实践中,符合“犯罪存留养亲”的犯人极少,成为了一种摆设,被认为是宋以后出现了对存留养亲制度不断趋向严格的发展方向,并在明代达到了最高峰。(35)参见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页。而在清代也延续对“存留养亲”制度的限制,导致在清初相关案件较少,具体如在明律文规定的基础上增加注释,对其符合的条件进行细化;在司法实践与适用中逐渐规范化与严格化,对该制度的准予有了严格的限制。(36)参见陈煜:《第六届张晋藩法律史学基金会征文大赛获奖作品集 新路集 第6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页;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294页。另一方面,明清关于“存留养亲”的规定也具有放宽的趋势。其一,在明代的律文规范中,相对于唐律中有期亲成丁,不在上请之列;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仍从流的规定,明代删去此部分,也是相较而放宽的设计;(37)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775页。在英宗与神宗时期,也对“存留养亲”进行定制化与从宽化的努力,但实际上并不具有实用性,成为了恩赦程序中附带提及而适用的非日常制度。(38)参见张中秋:《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其二,清代律文虽然与明代律条相同,但自康熙年间开始,在司法实践中就“存留养亲”的问题先后形成了一系列的事例和条例;(39)参见张亮:“清代犯罪存留养亲制度之结构与理念新探”,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7页。还形成了因承祀而留养的案例与规定,作为秋审结果处理之一;(40)参见李艳君:“论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3页;孙家红:“视野放宽:对清代秋审和朝审结果的新考察”,载《清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33页;谢全发:“留养承祀制度初探”,载《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2~56页。具体而言,针对包括了杀人、强盗、窃盗、“十恶”、诬告、孀妇独子和监候待质犯等情形,开始解除了有关留养的条件束缚,使该制度于清代得以有效而广泛地推行。(41)参见吴建璠:“清代的犯罪存留养亲”,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26~130页。
明清关于“存留养亲”制度所具备的“从严”与“从宽”两个特点,与其外部环境中明清帝制末期加强集权的趋势密不可分。一方面,集权的趋势,向上要求国家层面中,各项制度的适用与运行不断严密化与规范化,促进了“存留养亲”的“从严”特点。集权特性的需求,要求减少法外操作的空间与可能,传统制度在决断中的“权留养亲”具有极大不确定性,须加强制度的限制;并且,从“十恶”至“常赦所不原”的变化,也反映出强化传统帝制统治基础的维护。另一方面,集权的趋势,向下则要求社会层面中,强化宗法伦理与孝道伦常的维护,体现“从宽”的趋向。集权要求针对社会各方面的掌握与控制,以维护传统宗法社会的基础单位,即家庭的稳固。“存留养亲”制度就需要在规范与严格的制度的基础上灵活与多样进行适用,从而催生出清代存留养亲制度对明代严格限制的修正与补充,使该制度展现出“从严”又“从宽”的特点。
总言之,相较明清以前存留养亲制度的注重适用条件与实质内涵,明清时期则是更为强调程序限制与形式意义。其整体趋势反映出明清时期集权化的发展,主要从“存留养亲”的程序与限制入手,以反面的角度对该制度不断进行限制与规范。该制度的后期发展实际上更注重其形式意义,反映制度程序的严格化与社会控制的家庭化的形式特点。
三、横向分析:“存留养亲”的实践与适用
对“存留养亲”制度的发展历程梳理后,需要看到制度背后的实践情况,而《刑案汇览》中有关“犯罪存留养亲”的案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案例分析的路径存在两条路径,其一,对“存留养亲”中准与不准的案例进行分类探析,探求二者之间准与不准的案件类型、认定标准与考量情形;其二,以内容与形式两个维度分析各种案例,探究适用法条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案例适用的过程、程序与价值关联。实际上此二种路径是一致的,“准予留养”的案件考量的更是制度条文的规定,探求其背后制度设计的价值内涵,即内容分析;“不准留养”的案件除了法条规定的限制情形,也考虑到“限制”背后的不同价值追求之间关系,即形式上分析。
(一)内容分析:“准予留养”与情理适用
《刑案汇览》中所有“犯罪存留养亲”认定的最终结果“准予留养”的案件类型繁多,但有三个方法对其进行分类。第一种方法,即以案件性质加以区分。(42)采用此种方法对案例进行划分的主要参见李艳君:“论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陈文成:“清代存留养亲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杨翼:“论中国历史上的存留养亲制度”,复旦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周飞:“存留养亲制度及其现实意义”,曲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贾康:“论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载《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夏静:“我国古代存留养亲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沙金:“存留养亲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存留养亲”案件基本被大多数学者分为服制犯罪、杀人案、盗犯、诬告罪,以及监候待质犯的存留养亲等五个类型。具体而言,其一是,服制犯罪。多个案例涉及亲属之间的犯罪事例,主要包括服制命案的留养与误伤父母两种类型。(43)参见李艳君:“论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2~3页。如“放铳误毙功尊改缓后请留养”,“误伤父母拟斩改缓后请留养”和“殴妻致死随本行查亲老准留”等;(44)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51页。其二是,杀人案。主要包括三个类型:即存留承嗣而获得留养的杀人案、斗殴杀人案、孀妇独子杀人案。(45)参见贾康:“论清代的‘存留养亲’制度”,载《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37页。具体如“嫁母侍养无人准存留养亲”“斗殴误杀旁人拟绞随本留养”等;(46)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9页。其三,盗犯。在案例中单纯涉及该罪较少,多考量犯人家庭因素与案件严重程度等其他因素。具体案件如“蒙古偷马弟兄犯遣酌留一人”“弟兄共犯强盗不准存留养亲”等。(47)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67、68页。其四,诬告罪在案件中涉及的也较少,如“诬告抢夺复又拒捕应准留养”“诬告应视所诬情罪分别留养”,以及“被诬不准留养诬者亦不准留”等。(48)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2~74页。其五,监候待质犯也较为特殊,具体如“监候待质逸犯准留者准查办”和“监候待质首从未定限满再办”。(49)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6~78页。此种方法虽然可以充分展现案例的各种类型,但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而言,一些有关程序性事项的案件判决与说明,重点不在于具体的案件性质,如“留养亲属应视远近分别提讯”“业已枷责留养亲故毋庸置议”,以及“救父情切减流留养枷号日期”等;(50)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56、58页。部分案件因犯人的亲属情况而留养的案件,简单以案件性质分类即失去案例所欲表达的本意,如“守节已届二十年独子留养”“先经继子后又生子分别留养”,以及“弟兄死罪虽不同案情轻准留”等案例。(51)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64~65页。
第二种方法,即从存留养亲制度的具体程序中不同的阶段,以对准予留养的案件不同程序加以分类。根据清代的“存留养亲”的程序,要经过声请留养、查办留养、皇帝钦定,以及枷责发落等四个流程。(52)参见吴建璠:“清代的犯罪存留养亲”,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0~132页。因此,对于“准予留养”的案件,可以分为随案声请准予留养的案件、秋审情实二次改缓后声请准予留养的案件、以及“通行”等三个情形。(53)采用此种方法的主要参见郭伟.:“清代犯罪存留养亲制度研究”,河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由于本文此部分仅仅针对“准予留养”的案例整理分类,因此对该文中六种分类进行筛选后得出的三种情形。随案声请准予留养的案件,包括“嫁母侍养无人准存留养亲”“殴妻致死随本行查亲老准留”等案件;(54)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51页。而秋审情实二次改缓后声请准予留养的案件较多,如“放铳误毙功尊改缓后请留养”“误杀胞伯孀妇独子补请留养”,以及“服制改缓斩犯亲老有兄残废”等;(55)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41页。而“通行”发挥着类似司法解释的的作用,有较强的法律效力。(56)参见郭伟:“清代犯罪存留养亲制度研究”,河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28页。如“守节已届二十年独子留养”“捏结留养官吏亲族分别严惩”,以及“留养亲属应视远近分别提讯”等。(57)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54~55页。第三种方法,即根据“存留养亲”案件得以判处考虑的宏观条件进行分类,具体包括案件犯人的家庭情况与犯人本身行为与案情的具体解释两个部分。其一,主要考量犯人的家庭情况的案例,如“父母老疾有一于此均准留养”“守节已届二十年独子留养”,以及“先经继子后又生子分别留养”等案例;(58)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6~47、64页。其二,考量犯人行为、心理与具体案情的案例,如“误杀胞伯孀妇独子补请留养”“误伤父母拟斩改缓后请留养”,以及“亲属捉奸杀非有心随本留养”等案例。(59)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2、53~54页。
简言之,此三种分类方法都存在一定弊端,难以对“准予留养”的案件进行全面归类。但将此三种分类方法比较探析,基本可判断出“存留养亲”案件审理之时,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即平衡法律规定与“法外施恩”之间的关系。第一种方法不仅注重各类案件的性质,实际上是以伦理性的“存留养亲”案件中各种条件为解析工具,来分析国家法律中可能出现的不同性质与类型案件;而第二种方法,则一方面注重“存留养亲”案件审理之时的程序过程,另一方面,着重关注了“存留养亲”案件本身,将国家法律规定的各类普通型性质案件,放入至特殊性的“存留养亲”程序中各个流程加以解读;而最后一种方法中,犯人的家庭情况突显了伦理性的特殊需求,而犯人本身行为与案情的具体解释需要国家法律加以规定,即平衡了伦理性与法律规定的需求。可以说对“存留养亲”案件的整理与适用,实质上就是平衡法律规定的“国法”与法外施恩的“情理”之间的关系。
将其中同时包含了三种方法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如“误杀胞伯孀妇独子补请留养”一案,可进一步判断“犯罪存留养亲”案件,在整体上所表达的平衡“国法”与“情理”价值取向。(60)该案例出自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9~40页。后文对该案例的引用都来自此出处。首先,从案件类型上看,该案不仅是卑幼殴死期功尊的情形,但也是杀人案中的误杀案件,并且地方官认为“核其所犯情节实可矜悯”,反映出国法规定中的加重处罚与“情有可原”的情节之间的矛盾;其次,从案件程序看,不仅符合“未经声明亲老丁单者,亦得随时补请留养”的规定,参照了“四川省斩犯敬廷贵”一案,“拟斩,秋审情实,两次改入缓决”,从程序上具备了留养的可能;最后,再考量犯人本身的家庭情况,即“以该犯之母徐陈氏守节已逾二十年”,并且“家无次丁,死者并无应侍之亲”等具体“情理”上应予变通的情形,进而准予留养。可见,各类案件虽然都可以按照此三种方法进行分类,而其作出准予留养的决定,实质上在裁决之时都考量“国法”中的法律规定与程序,以及“情理”中是否“可矜悯”的具体家庭情况等,进而维护“国法”与“情理”的平衡。除此之外,还有繁多的“存留养亲”案件基本上都此种关系的体现,如“误伤父母拟斩改缓后请留养”“误伤父母拟斩随众声请承祧”“殴死外姻尊长情轻者准留养”等等。(61)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4、58页。对“存留养亲”案件审理与适用实质性分析,即需要在案件中将“情理”与“国法”相结合,在“国法”的规定下实现“情理”的适用与融合。
(二)形式分析:“不准留养”与以情相通
对《刑案汇览》中“不准留养”的案件分析,须先看到清代除了律文之外,还有数例对“留养”与否加以“限制”:“凡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亲,请旨定夺;斗殴杀人之犯应准留养者,查明被杀之家有无父母,如被杀之人亦系独子,其亲尚在,俱不准留养;凡触犯父母并素习匪类为父母所摈逐及游荡他乡远离父母,俱属忘亲不孝之人,概不准留养;死罪及军流遣返留养之案,如该犯本有兄弟与姪出继可以归总及本犯身为人后、所后之家可以另继者,概不得请留;各衙门差役倚势滋扰犯罪者,不准声请留养”。(62)吉同钧纂辑、闫晓君整理:《大清律例讲义》,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37页。此规定不仅有助于理解“存留养亲”案件中“不准”的原因,此些规范同样以实践的形式反映在案例之中。
对《刑案汇览》中“犯罪存留养亲”的案例整理,“不准留养”的情形可以分为五种:其一,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准予留养的案件,包括明文规定和案情性质恶劣与影响重大的案件。具体包括:“竹铳伤人情重之案不准留养”“偷窃红椿以内树木不准留养”,以及“谋故杀人情实无疑不准留养”等案件。(63)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5~76页。其二,不适宜随案声请留养而等待秋审报批的案件,如“殴死缌尊不准随本声请留养”“殴死胞兄未便随本声请留养”,以及“因斗失跌淹毙不准随本留养”等案。(64)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5、49页。其三,捏造符合留养条件的舞弊案件,如“服制改缓斩犯亲老有兄残废”“捏结留养官吏亲族分别严惩”,以及“尚未秋审旋即查明捏报留养”等案。(65)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1、54、56页。其四,犯人亲属情况对是否“留养”的影响,具体如“孀妇独子妇已再醮不准留养”“乞养异姓之子亲老不准留养”,以及“有弟兄为僧道不得以独子论”等案。(66)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7、62、85页。其五,被害人家庭情况对犯人是否“留养”产生影响的案件,具体如“死虽有弟尚未成丁不准留养”“被杀之家次丁出继不能归宗”,以及“死系独子不论其亲是否老疾”等案件。(67)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8~81页。
将两种不予留养的“限制”相结合分析,可反映出三个核心要素:即“通情”、“孝道”与“法律程序”。其一,“通情”。在律例规定中主要则是查明被杀之家有无父母,是否是独子。正如《刑案汇览》所言:“如死者之父母因其子被杀,以致侍养无人,则犯亲自不得独享晨昏之奉”。(68)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此种将“感情”通感与互受的做法,在案例中表现为“死系独子不论其亲是否老疾”、“被诬不准留养诬者亦不准留”等案之中。(69)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0、73页。其二,“孝道”。一方面,不管于例文还是案例之中,主要考察犯人平时是否行孝道,若为“忘亲不孝”之人,则“概不准留养”;另一方面,也是考察犯人之家是否符合“留养”的伦理性要件。其三,“法律程序”要素,体现于法律明确规定不得准予留养与等待秋审报批的案件之中,甚至在例文中“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亲”,也需要符合法律程序而“请旨定夺”。
而此三个核心要素也可以从具体案例中加以分析而出,最为典型的案例则是“死虽独子平日不孝凶犯准留”。(70)该案例出自祝庆祺:《刑案汇览三编(一)》,北京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后文对该案例的引用皆来自此出处。“存留养亲”做法的形成本来就以“通情”作为基础要件,也成为了限制其成立的条件之一。对于“鲍怀友扎死王胔成”的案情,回复称州县官员“必查明被杀之家是否独子者”此体现“通情”的要素;同时要求地方官府查清其平时是否有孝行,即“是死者生前已不能孝养其亲”,并且“并非被杀之后其父母始无人奉侍,似不必仍拘死者亦系独子”,此体现出“孝道”的要素;最后,该案最后也准予留养后准其留养后,即“行令俟秋审时归入留养册内办理”,并且不管是“通情”还是“孝道”,都转化为定例中固定法律程序,最后该案例在嘉庆年间通行为纂例。可见,三个要素确实反映在“犯罪存留养亲”的实践与案例之中。
更进一步分析此三个核心要素,实际上“通情”所代表“人情”、“孝道”所表现的“天道”与“天理”,以及“法律程序”所表达的“国法”,三者在“存留养亲”案件的审理中相统一。不仅法律规定富含“人情”的“存留养亲”,并自身出发需要践行“孝道”,还需要将此种“孝”进行“通情”传达,最后“情”与“理”结合之后,再进一步又回到了“法律程序”,在适用中需要符合法定程序的“国法”。因此,而对“存留养亲”案件审理与适用背后价值的形式分析而言,“人情”“天理”与“国法”的相贯通即为该案件适用中各价值的形式关系。
四、原理分析:“存留养亲”中传统法特质之原理
从纵向角度分析“存留养亲”制度的发展与嬗变,又以横向的角度分析该制度背后实践中的内涵要件与形式关系,都展现出孝道伦理与法律制度、“情理”与“国法”之间的结合与联系,即伦理性特点。然而此种特质背后的原因与原理来源何处,就需要从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两个维度加以解析。而外部与内部角度,实际上也对应着该制度原理的实质内涵与形式关系,两者统一构成伦理性特质之原理。
(一)外部维度:人的制度化
传统法的伦理性特质与传统的宗法社会密切相关,而传统宗法社会与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有关。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展现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其一,国家的起源阶段。古代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与西方血缘关系的解体而形成国家有所不同,而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原始部族在转变为国家组织之时,氏族血缘纽带没有断裂,固有的血缘关系没有解体,而是直接转化为新的宗法血缘关系。(71)参见张中秋:《原理及其意义:探索中国法律文化之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国家的初始形成不以氏族组织的瓦解为前提,而是在战争中强化的权力,以及族长传统的保留。(72)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因而,血缘关系、家族和氏族等“束缚”依旧存在,并把氏族内部的亲族关系直接转化为国家的组织形式。(73)参见梁治平:《“法”辩——法律文化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其二,中华文明定型阶段。国家起源的特殊性也逐渐影响到后期文明的发展与样态,西周时期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其实行的宗法制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形态。宗法制即建立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宗法与政治高度融合,更进一步完整地保留宗法血缘关系。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成为了君臣,此时君臣系统与宗法系统基本相一致,天下的政治秩序与宗法的家族秩序同构。(74)参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页。因此,宗法制既强化宗法血缘的特性,也在另一方面,建立传统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国家组织,政治运作中政治因素与亲缘关系互相影响。(75)参见晁福林:“试论宗法制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4期,第129~130页。其三,传统帝制阶段。传统帝制也基本建立于此特殊性的社会结构之上,从西周始,国家组织构成是被包含于扩大版的“家”之下的,于是整个国成为一个政治型的大“家”,这类政治文化模式是一种宗法制的后遗——家庭模式。(76)从家庭为对象来理解中国早期青铜时期甚至更早的政治文化传统,两个上文提及的最主要原因,其一是国家演进途径中家族血缘关系的保留;其二是从宗法制展现的家国一体的结构进行理解推断。除此之外,如马克斯韦伯所认为传统中国帝制为家产制官僚制;黑格尔认为“家”的精神和原则对中国人特别重要,实际上两者都从“家”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阶级分化的扩大,家庭在战争与动荡中破裂,也在破裂中家的范畴又进一步扩大。帝制时期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成为了在一个“大家”包裹之下的“国”与“小家”即地方宗族之间的二元关系。(77)参见刘毅:“家国传统与治理转型”,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1期,第61页。作者认为:传统中国帝制时代的社会结构,不同于现代西方意义下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元结构,而国与家是传统国家最为基本的政治主体与单位,形成国与家二元结构。因此,传统独特“家”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精髓被遗留了下来,形成同一化的社会结构。
因此,家庭化的社会结构之下,同样作为宗法制的遗留,血缘关系与政治架构相混合之后,人与人的宗法血缘关系成为了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此时“人”作为国家与社会制度得以运行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导致了“人”本身实际上也有制度化的特征。此种“人”的制度化,具体展现于三个具体特点:其一,主观化。“人”成为制度之后,人的主观思考与判断也成为制度运行的要素之一,传统宗法社会的制度与法律即展现出主观化的特征,并且其主观判断的内容则是血缘伦理道德与宗法伦常秩序。其二,教育化。人的主观判断作为制度运行的要素之一,具备易变性与随意性而存在着风险。因此,强调教育与学习,不仅成为对人的教育,也是一种“制度建设”,即教育“人”与治理国家有同等的意义。(78)如《荀子·君道》:“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对人的修养教育的追求作为国家制度建设的重心。并且,教育化就成为矫正主观化可能出现谬误的“制度后盾”。其三,同一化。人与制度结合之后,人与制度,制度与观念则相同一,而不是相对立、区分的二元对抗。同一化也促进形成了世俗化,人、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之间关系都相同一。
人的制度化特点在内容与实质上决定了传统社会与传统法伦理性的特征,即维护制度的协调稳定,关键在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所以,强调孝行孝道的“情”与伦常秩序的“理”,从而促进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固。总言之,从外部视角考察,“存留养亲”制度伦理性特质的背后原理,即实质上“人”的制度化,因而强调“情理”在立法与司法中的体现与适用。
(二)内部维度:情的贯通化
传统社会结构家庭模式形成了“同一化”的特殊性,也决定了传统社会与传统法在实质上“人”的制度化特征。而血缘宗法关系与国家制度构造的混同,家国一体的宗法制的遗留,导致了人与人的宗法血缘关系也就成为了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传统社会与传统法不仅在内容上关注了“人”的本身,在形式上人与人在“社会生活”中相处的重要关系成为国家制度重要要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通连方式也成为制度之间、价值追求之间关系的样板。
而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通连方式,则展现出“同情”“通情”为形式的贯通化特征。此种特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就客观层面而言,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衔接与拓展即以“贯通”的方式进行。《大学》中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79)陈蒲青:《四书注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80)《孟子·离娄上》。此二句话都表明了传统社会的家国天下秩序的运行方向,即以自我为核心的社会连续体。(81)参见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首先,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或者中心是自己,即“身”;向外拓展则是家庭、家族以及区域性的“乡里”,乃至“国家”;最后则是有普遍意义的客观范畴“天下”。此种从“身”“家”至“国”,甚至达“天下”的论述,则直接说明了此种从“己”推至“天下”的逻辑思路。另一方面,则是主观层面,贯通化的基本要素,以及传统法的特质出发点都为“情”。“身”相对应的则是自我的“人情”作为出发点,由“人情”向外拓延,则是与“家”与家法、“国”与国法。而家法、国法体现出“人情”即顺人情而为,而又制约人情。(82)参见俞荣根:“天理、国法、人情的冲突与整合──儒家之法的内在精神及现代法治的传统资源”,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第14页。国法的进一步外延,则为“天理”与天下。而“天理”反映“国法”的价值追求,其同时也根源于“人情”。因此,从“人情”的自我出发,向外延展又回到了“情”本身,反映出以“情”为要素的贯通化特征。
除此之外,以“情”为主要要素的贯通化,平衡了传统法特质中不同价值追求的关系。首先,人的制度化决定了人的感情、人情本身成为制度的要素之一,而“存留养亲”制度的立法原意最为直接体现出“人情”等人性化的价值追求;其次,“人情”普遍与抽象之后即为“天理”,“存留养亲”制度不仅体现人情,需要强调具有普遍意义的孝道孝行,成为一般性的伦理性道德,方得反复适用以规范人的行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普遍性的价值追求;最后,从“人情”抽象化后的“天理”,为“国法”将之吸收形成条件。而在经过“人情”与“天理”的改造之后,国法本身对犯罪打击的强制威慑性的价值追求,也与人性化与普遍性的价值相平衡。因此,情的贯通化在形式与程序上决定了传统法伦理性特质中,“人情”“天理”与“国法”的统一与协调。
总言之,从内部视角关注“存留养亲”制度,其伦理性特质的背后原理,即在形式上将传统法的不同价值之间关系以“情”为要素的贯通化。具体而言,以人性化的“人情”为基本要素与出发点,将普遍性的“天理”与强制威慑性的“国法”相贯通,存留养亲制度的法律适用上不仅将“情理”适用,更是以“情”相通。
结 语
“存留养亲”制度在历史发展的梳理中,礼法结合与孝道入法的特征明显。而该制度演变的背后,案件的适用上也体现出“情理”适用与以“情”相通的特点,二者结合可得知“存留养亲”制度作为“法外施仁”的特点。更进一步而言,探求立法与司法背后的特质原理,离不开传统社会与传统法的特殊性。此种特殊性形成了在内容上“人”的制度化,以及在形式上“情”的贯通化描述。因此,“法外施仁”的背后蕴含着传统社会外部环境,与内在价值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的原理,为进一步理解“存留养亲”与传统法有益经验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