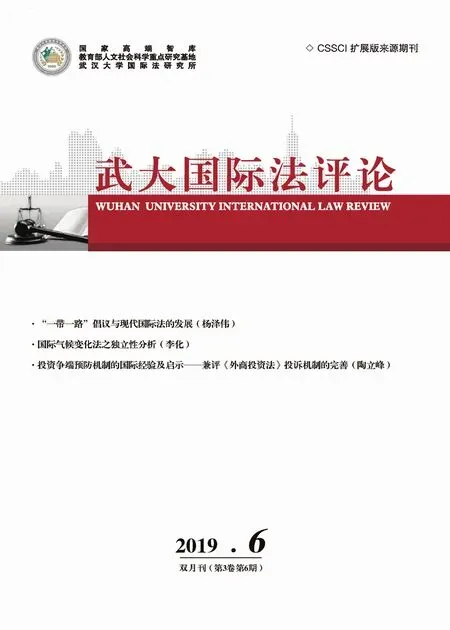国际气候变化法之独立性分析
李 化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人权法、国际环境法、国际刑法等法律日益成熟,现在这些法律部门之间相互影响,国家和国际司法机构视其为国际法体系的组成部门。①参见[意]安东尼奥·卡塞斯:《国际法》,蔡从燕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众多相互独立的国际法律部门的出现及其相互影响,构成当代国际法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基于共同利益观念的传播,地球气候的自然资源属性为公众所熟知,其法律属性也日渐明朗。②参见李化:《论地球气候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属性》,《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56-66页。在治理跨界大气污染、臭氧层损耗等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国际法领域产生了致力于维持地球气候系统整体安全为目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其议定书,国际气候变化法初现端倪。③See Cinnamon P.Carlarne et 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4-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伴随不断拓展的国际气候合作实践,《马拉喀什协定》《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巴黎协定》等一批国际法律文件的出现,国际气候变化法逐渐走进法学界的视野。可以说,国际气候变化法之所以渐趋生成,是气候变化科学认知、国际气候政治共识、国际气候合作、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等内部因素和国际组织推动、国内相关立法影响等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①参见李化:《论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82-92页。
历经二三十年的发展,国际气候变化法初具规模,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促进国际气候合作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其中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这一问题鲜有讨论,因而它在国际法体系中的地位也未能明确,这与国际气候变化法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极不相适应。具体而言,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是指国际气候变化法因具有某种特性要素的客观存在而在国际法体系中形成的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分析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需要回答三个问题:其一,国际气候变化法为什么能够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其二,独立的国际气候变化法表现在哪些方面?其三,在既存或者新增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如何展开?上述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定义为逻辑起点,这也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结构体系扩展与层次递进的基础。
一、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定义
“……凡科学,有正确之定义。即有精当之专名,研究之者,顾名思义,便得其性质之大略。”②宁协万:《现行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序第7页。学科定义是一个难以精当无遗和难获共识的领域,为了叙述的便利,简要界定国际气候变化法实有必要。国际气候变化法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形成的,用以调整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实现地球气候系统整体安全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简言之,国际气候变化法主要是规制国家间气候合作的法律,这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本质属性。
(一)国际气候变化法以维持地球气候系统整体安全为任务
作为国际气候变化法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均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公约》是基于谨慎原则缔结的一个“框架性”条约,其第2条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目标。③See Daniel Bodanksy,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 Commentary, 18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51-459 (1993).但是,《公约》第2条尽显抽象之能,既没有具体规定量化的减排限制,更没有指出“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温室气体浓度阈值。①See UNFCCC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Handbook 21 (Technographic Design and Print Ltd.2006).这些问题最终由后续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予以明确。作为《公约》的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第3条弥补了《公约》第2条的缺陷,施加《公约》附件Ⅰ所列缔约方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基于气候科学的发展,被视做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历史性一步”的《巴黎协定》,针对危险气候变化临界值2°C达成共识,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1.5°C全球温控目标,“……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C 之内,并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之内……”②《巴黎协定》第2条。概言之,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基本任务,是通过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两大路径,即减轻潜在的损失、利用机会或者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能力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或者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而干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最终维持地球气候系统整体安全以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气候变化法主要是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法律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标志着主权国家间国际体系的确立,这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的重大进步,其确立的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现代国际体系赖以建立和发展的国际法基础。③参见曾令良:《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潮流——推进国际法理念和原则创新》,《人民日报》2016年3月28日,第16版。自此以后,国家一直是最重要的国际法主体,具有其他国际法主体无法比拟的根本属性。在国际社会结构变迁、法律观念发展、客体范围扩展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与实践不断丰富,“国家间法律可以,并且已经给予其他实体及个人以国际人格的地位”④[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但是,国际社会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林立的分散国际体制,国家始终是国际法的基本主体,非国家实体和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的情形仅占国际法所有领域的少数,国际法的主要部分依然是由约束国家的规则组成。⑤See I.A.Shearer,Strake’s International Law 62(Butterworths 1994).根据国际法主体的基本理论,凡是能够独立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承受国际气候变化法上的权利义务,享有在国际法庭上提出诉讼请求的权利,具有缔结条约能力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均可被赋予国际气候变化法主体资格。但是,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仅仅在应对气候变化范围内享有国际气候变化法主体地位,个人缺乏解决应对气候变化这类重大国际政治事务的能力而不宜被赋予国际气候变化法主体资格。综上,基于国家具有最完整的国际人格,国际气候变化法原则上只规定国家间权利义务关系,国家间合作规则构成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的主体部分。
(三)国际气候变化法是规制国际气候合作的法律
国际气候变化法并没有伴随17世纪中期近代国际法的形成而产生,它是国际气候合作高度发展后的产物。进入20世纪中期后,环境公害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在臭氧层损耗为科学家所证实之后,国际气候合作萌芽渐生,产生了《欧洲控制大气污染原则宣言》《长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等防治跨界大气污染和保护臭氧层的零星国际法规范,这些可以被视为规制国际气候合作的早期国际法规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凸显,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与政治共识逐渐凝聚,国际气候合作以不可阻挡之势扑面而来,呈现出合作主体多元、合作内容丰富、合作形式多样等特征。任何法律都是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国际法存在的客观环境是不断变迁、变革的国际社会和国际秩序,法律规则的出现、修改、发展、消亡都以实践为基础”①贾兵兵:《国际公法: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伴随国际气候合作实践日益发达,国际气候变化法应运而生。换言之,国际气候变化法是在气候变化国际法规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这些法律规范基本上都源于国际气候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气候合作与国际气候变化法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一方面,国际气候合作促成了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并伴随国际气候合作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国际气候变化法通过规制国际气候合作,确认、巩固和发展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并伴随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发展而不断强化国际气候合作。
二、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法理基础
按照法理学的基本理论,一个法律领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应有基于其本质属性的内在要素,这些内在要素主要包括法律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当然,历经时间的积淀而形成相当规模的法律规范也是支撑独立性的要件。②国内学界主流观点是以法律调整对象和法律调整方法的“双重标准说”划分法律部门。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按照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划分法律部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离开了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等根本要素的存在,即使有再多其他要素的支撑,亦不会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正是因为存在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相当规模的法律规范,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才具有其合理性,否则也不过是国际环境法众多调整领域中的一个。
(一)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调整对象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的本质,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性内容,因为生产过程发生的占有、交换、分配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根本的社会关系,其他一切关系包括法律关系在内都是由此派生而来。①张文显、信春鹰主编:《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2页。进而言之,法律调整对象是体现意志关系的具体社会关系,“法律的生命力就植根于社会关系,这是法学发展史上最基本和最为成功的理论抽象之一,不可(目前也没有理由)轻易抛弃”②顾功耘、刘哲昕:《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法学》2001年第2期,第59页。。
传统国际法以国家间政治关系为调整对象,围绕国家间权利义务构建法律体系。进入20世纪后,国际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拓展,与之相适应,新的国际法律部门相继形成,结果是纯属各国国内法管辖的部门、领域和事项逐渐减少,国际法的触角逐渐深入到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③参见曾令良:《现代国际法的人本化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 期,第103页。气候变化进入国际法领域之后,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形成了以国际气候合作为中心的特定国际关系——国际气候合作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应对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法治最重要的领域,适应国际社会实践需要而形成的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的社会关系和调整这一类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出现,必然形成崭新的法律部门。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是顺应国际社会现实、自成一类的特定国际关系,传统国际法律部门不能或者不适合调整,必须由国际气候变化法予以调整。当然,需要区分国际气候合作关系与国际气候合作法律关系。国际气候变化法对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调整,通过规定其主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或者说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经由国际气候变化法调整而形成国际气候合作法律关系。因此,国际气候合作法律关系是国际气候合作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构成国际气候合作法律关系的实体内容。
(二)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调整方法
法律调整方法是法律对其调整对象施加影响的手段。或者说,法律是通过规范社会关系主体的行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因此规范社会关系主体的行为是法律调整方法。然而,规范社会关系主体的行为是一个复杂过程,需要一系列具体方法,一般认为保障法律实施的制裁方式是主要的法律调整方法。④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2页。
国际法的制裁机制一直是国际法为人所诟病的方面,但是依然存在由特定机制保障国际法的实施,国家自愿遵守和自助手段——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决定的——是国际法实施的主要方式。随着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被赋予实施国际法的职能,从而促进了国际法制裁机制的发展。①参见饶戈平:《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页。当前,国际法存在自助手段、国际组织制裁、法律权利或特权的丧失、司法执行等制裁方法,大体上呈现出对等性和对抗性的特点。②参见姜皇池:《国际公法导论》,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6-12页。然而,基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共进是国际气候变化法实施的主要方法。因此,国际法的制裁机制并不总是适合国际气候变化法,对违反国际气候变化法行为的制裁必须另辟蹊径,寻求非对等性和非对抗性的路径。“在多边环境条约领域,建立在合作与伙伴关系基础上的遵约机制已经发展起来”③Ulrich Beyerlin et al.,Ensuring Compliance with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 Dialogue between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a vii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或者说对违反国际气候变化法行为的制裁“已经从双边国家责任转化为确立与加强国际合作”④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 77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事实上,《公约》及其议定书通过缔约方会议的非强制性内部化程序来实施制裁。⑤非强制性内部化程序包括报告制度、申诉制度、援助制度、环境信息交流制度、处罚和补救措施等。《公约》第7、10、13、14条等规定的多样化的非诉讼方法强化了国际气候合作,保障了《公约》的实施。与之相类似,为了促进履行和遵守,《巴黎协定》第15条决定建立一个由专家为主组成的委员会机制,以透明、非对抗、非惩罚性方式行使职能。毫无疑问,《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主要国际气候条约确立的是一种合作而非对抗、平等者式而非执法者式的制裁机制。⑥参见宋英:《〈巴黎协定〉与全球环境治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66-67页。
(三)气候变化法律规范
除了应考虑法律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外,法律部门独立性的证成还必须考虑相应法律规范的数量。法律规范是构成法律体系的最基本细胞,是理论法学和实践法学的基础。在法学论著和日常语言中,广义的法律规范常常被作为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统称。⑦参见张文显等编:《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正是通过法律规范的执行、适用、遵守等途径实现法律对社会活动或者社会行为的具体要求。可以想象,法律规范数量不足,纵有自成一类的社会关系和调整方法,法律部门犹如“空中楼阁”,依然难以实现法律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
考察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必须顾及跨界大气污染、臭氧层损耗和气候变化三个问题之间的关联性。①参见[英]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国际法与环境》,那力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页。围绕跨界大气污染、臭氧层损耗、气候变化等主题,产生了《控制大气污染原则宣言》《禁止为军事目的或者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长距离跨界大气污染公约》《关于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诺得怀克宣言》《公约》《京都议定书》《能源宪章条约》《蒙特利尔议定书哥本哈根修正案》《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中国和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哥本哈根协定》《坎昆协议》《巴黎协定》等国际法律文件,这些国际法律文件间接或者直接地涉及全球气候治理。作为对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回应,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从无到有,从分散到集中,从零星到系统,逐渐成长起来。综观当前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其渊源不仅存在于综合性和专门性国际法律文件中,还广泛存在于其他涉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文件中;其内容涵盖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方面,不仅包括基本原则、目标、科学合作、公共信息、教育培训、财政资源、技术转让等实体性内容,还包括条约遵守、争端解决等程序性内容。
三、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表现
法律调整对象、法律调整方法和法律规范是证成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的内在依据。作为国际气候变化法这一部门法“安身立命”的基础,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必然以某种形式表现或形态存在,这既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重要依托。独特的价值理念、性格特质、基本原则、法律制度以及与相近法律部门显著的差异性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重要表现形式。
(一)价值理念
理念这一概念源自哲学,经中世纪经院哲学集大成者阿奎纳引入国际法,国际法学者菲德罗斯则阐述了国际法理念的内涵及其具体内容。②参见[奥]阿·菲德罗斯:《国际法》(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25页。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和平与发展为理念,国际法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与日俱增,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国际合作不畅、国家间对抗与霸权主义等问题。③参见何志鹏:《国际法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作为认知国际法的最高形式,“国际法的理念既是国际法过去的反思结果,又是国际法未来的价值目标”④古祖雪等:《国际法学专论》,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如果说和平与发展是现代国际法的追求,那么全人类共同利益必然构成当代国际法的重要归宿,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表达。
伴随全人类共同利益观念的传播,国际法从国际社会本位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本位变迁,所有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必然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并为之服务,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成与发展揭示了国际法理念正从和平与发展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拓展的发展趋势。从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到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逐渐形成了“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承“天下一家”思想的人类整体观,强调人类利益的整体性和共同性,从更高层面上回答和解决了人类发展的终极问题。①参见张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法社会基础理论的当代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56-57页。其中,“清洁美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根本形态,要求自然地理环境足以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可以想象,没有“清洁美丽”价值理念的追求,“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犹如“无本之木”。总之,维持地球气候系统整体安全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物质基础,需要国际法作出制度性安排,国际气候变化法正是回应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的现实需求,其“清洁美丽”的价值理念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落地生根而更加凸显。显然,“清洁美丽”价值理念的重要意义在于批判性地反思当下的全球气候治理,以前瞻性理念引领国际气候变化法律秩序建立的进程,其所呈现出的独特性彰显了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
(二)性格特质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紧密相连,“国际法是国际政治的规范表述……任何法律体系无不反映政治体系中的政治主张;国际法则反映了国家间体系的政治主张”②[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事实上,自近代国际法产生以来,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国际政治影响甚至决定国际法,同时也深受国际法的影响与制约。未来国际法的发展依然如此,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会促进国际法的发展,而强权政治将会扼杀国际法的生机,“国际法对国际政治有一种畸形的从属性”③杨泽伟:《国际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本质属性是规制国际气候合作的法律。在其本质属性之外,国际气候变化法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现实中的发展无不印证了这一基本点,具体反映在其创制和实施两个方面。在法律创制方面,围绕减排目标、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减排机制等方面,联合国体制中传统区域性集团或重组或分化,形成了“77 国集团”、欧盟、“伞形集团”、小岛国家联盟、环境完整性集团等利益集团组成的国际气候政治格局,深深影响着国际气候变化法律秩序的进程。譬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欧盟先后出台了“欧洲气候变化计划”“气候变化与能源一揽子计划”“2050年迈入有竞争力的低碳经济路线图”等系列气候政策,由此主导并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引领着全球气候治理。在法律实施方面,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的压力,都是制约国际气候变化法实施的一股现实力量,这些政治压力来自个人、企业、政府、非政府国际组织等。例如,受来自国际政坛和国内产业的压力,美国政府在《京都议定书》签署问题上摇摆不定,或拒绝签署或签署后又退出,致使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中的实效大打折扣。澳大利亚的情形与美国类似,2007年,澳大利亚霍华德总理下台的部分原因可能与其消极的气候变化政策有关,包括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其后陆克文总理上台后旋即批准《京都议定书》,并积极推动相关国内立法。
(三)法律原则
作为法律规则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集中体现法律的基本精神,决定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保障法律体系的统一。①参见张文显等编:《法理学》,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5页。国际气候变化法基本原则是各国公认、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效力范围、构成国际气候变化法基础的法律原则。伴随国际关系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际气候变化法基本原则,必然要反映国际社会发展的主题,体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价值理念,由此可以确定,可持续发展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公平原则等构成国际气候变化法基本原则体系的主要部分。
可持续发展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来自《我们共同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②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作为一项国际气候变化法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充分体现在众多国际法律文件中,并有新发展。譬如,《公约》第2条所载“终极目标”体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核心内容,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第3条规定“各缔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各缔约方应当合作促进有利的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这种体系将促成所有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等内容,体现了发展权以及改变不可持续生产、消费的义务。①参见[荷]尼科·斯赫雷弗:《可持续发展在国际法中的演进:起源、涵义及地位》,汪习根、黄海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80-82页。又如,《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共同规定缔约方履行义务应当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附件Ⅰ所列每一缔约方,在实现第三条所述关于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时,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应……”②《京都议定书》第2条。“本协定在加强《公约》,包括其目标的履行方面,旨在联系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③《巴黎协定》第2条。根据上述国际法律文件的规定,可持续发展原则暗含着对作为可持续发展三重底线的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部分予以同等重视,可持续性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体系中的核心原则之一,为《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所确认。本质上,国际气候变化法是一部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合作”国际法,《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法律文件处处闪耀着合作精神。《公约》序言强调“……尽可能开展最广泛合作,并参与有效和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其后关于原则、承诺、研究和系统观测、教育培训和公众意识、资金机制、争端解决等条款载明了合作义务;《京都议定书》要求缔约方在开发、应用、传播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和维持、发展观测系统的科学技术研究两方面开展合作,同时规定了以合作为基础的联合履行、清洁发展和排放交易三大减排机制;《巴黎协定》中关于国家自主贡献制度、可持续发展非市场方法框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气候变化不利影响所涉损失与损害、资金机制、技术开发和转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力建设行动等条款要求缔约方间密切合作。④参见《公约》第3-6、11、14条;《京都议定书》第6、10、12、17条;《巴黎协定》第6-11条。需要强调的是,国际合作原则意味着国家承担为实现全球减排目标而参与协调行动的义务,如果某一个国家不履行合作义务,由此产生国家责任。
公平原则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要求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应顾及国际社会近200 个国情各异的主权国家的不同利益诉求,也即公平地分担义务。《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国际法律文件明确规定了公平原则,为了贯彻该原则,将缔约方义务区分为“共同性义务”和“区别性义务”。其中,《公约》第3条规定:“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并在其第4条规定附件Ⅰ所列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缔约方应通过限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保护、增强温室气体库和汇以减缓气候变化,附件Ⅱ所列发达国家缔约方和其他发达缔约方应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履行义务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京都议定书》第3条明确附件Ⅰ所列缔约方的量化限制和减排的具体承诺;《巴黎协定》第3条规定“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以实现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目的。所有缔约方的努力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同时认识到需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以有效履行本协定”。然而,《巴黎协定》生效后,全球减排行动从“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模式发展为“自下而上”国家自主贡献模式,缔约方义务相应地由强调“区别性义务”转向“共同性义务”,这些是否意味着公平原则正从注重实质公平逐渐过渡到侧重形式公平,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作为《公约》基石的地位进一步弱化?
(四)法律制度
国际气候变化法是基于调和经济利益与生态价值间矛盾而建立的普遍性法律秩序,为达成此目标,国际气候变化法关注四大问题:一是适应气候变化以减轻其不利影响;二是减缓气候变化以限制或者预防气候变化的发生;三是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保障措施;四是履行、遵守和实施的国际监督。①See Daniel Bodansky et al.,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围绕上述主题,国际气候变化法构建了富有特色的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制度。其中,适应气候变化制度是指通过程序、实践或者结构的改变以增强生态、社会和经济的适应能力,进而减轻潜在的损失或受益于与气候变化相关机会的各种政策和法律安排,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工作机制、内罗毕工作机制、坎昆适应框架等内容;减缓气候变化制度是指促进削减温室气体各种源的人为排放或者增强各种汇的人为清除而干预气候系统的各种政策和法律安排,包括联合履行、清洁发展机制、排放交易、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所致排放、国家自主贡献等内容。
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制度具有鲜明特征。首先,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大基本路径。以全球变暖为基本特征的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正在发生,触及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一方面,对于已经实际发生或者可预期的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唯有通过制度介入以提高生态、社会和经济的适应能力,预防乃至减轻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人为因素是诱发气候变化的主因,而人类有意识地干预气候系统的活动是减缓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其次,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制度以合作、共进的方式协调全球行动。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为了避免“囚徒困境”“搭便车”等现象发生,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制度要求各国共同参与全球行动。为此,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制度辅之以激励机制和减排义务,譬如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资金援助以及缔约方的减排义务,以此协调彼此行动。最后,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制度的“硬性”因素持续增强。法律规范有“硬法”与“软法”之分,国际法中的部分规范往往被贴上“软法”的标签。然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区别性义务”和“共同性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制度的强制性,这是其他环境问题治理所欠缺的方面,反映了世界各国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关于共同体关系与合作意识的增强。
(五)与相近法律部门的差异性
国际气候变化法有其自身的内涵与外延,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是独立于国内气候变化法、国际能源法、国际环境法的法律存在。厘清国际气候变化法与相近法律部门之间的区别,才能进一步明确国际气候变化法在国际法体系中的地位。
其一,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内气候变化法。气候系统的整体性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决定了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内气候变化法在一些重要方面紧密相连,具有相同的基本任务、基本概念、术语、制度等,两种法律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共同作用下一起发展与完善。但是,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内气候变化法分属不同法律体系,在法律创制、法律渊源、法律实施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譬如,国际气候变化法是国家在合作过程中以反映各国协调意志的“合意”方式创制,国内气候变化法是由各个主权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渊源主要有国际条约、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国内气候变化法的渊源主要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实施依据不同国家实践有直接实施(采纳)和间接实施(转化)两种方式,国内气候变化法的实施采取体现国家主权行使的直接实施方式。
其二,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能源法。国际能源法是一个涵盖跨界能源活动的法律体系,由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比较能源法的一些规则组成。①See Thomas W.Walde,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and Policy, in Cutler J.Cleveland (ed.),3 Encyclopedia of Energy 557-582 (2004).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结论显示,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能源法密不可分,更不用说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进程已经与能源安全、经济转型等竞争性国际领导权的争夺交织在一起。②See Stuart Eizenstat, The U.S.Role in Solving Climate Change: Green Growth Politics Can Enable Leadership despite the Economic Downturn, 30 Energy Law Journal 1-9 (2009).结果是,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能源法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日渐加强,但是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能源法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法律渊源等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气候变化法关注人类开发利用传统能源过程中引起的气候变化问题,法律规范多为禁止性规范;国际能源法侧重于促进能源勘探、开发、生产、运输、贸易、储备和利用中的国际合作,法律规范多为鼓励性规范。
其三,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环境法。“虽然国际气候变化法以《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基础,但是其最初规范源于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理。”①Cinnamon P.Carlarne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应对气候变化本是国际环境法所调整的防治大气污染、管制有害废弃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防治沙漠化等众多领域中的一个。事实上,在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前,国际环境法领域出现了零星的气候变化法律规范。因此,基于法律调整方法、法律关系主体、法律渊源、法律创制等因素考虑,国际气候变化法本当作为国际环境法次级部门而存在。但是,分析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环境法的关系,不能忽视国际现实,现实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当前,没有人能够否认气候变化不是一个影响国际关系全局的国际政治问题,而国际气候合作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政治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国际气候公约更是国际政治博弈的结果。前文在“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表现”部分曾论及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且作为国际气候变化法生成现实基础的国际气候合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国际环境法,这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于国际环境法的根本原因。因此,国际气候变化法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法领域,需要综合分析和思考。尽管气候变化法可以被视做国际环境法的次级部门法,但是基于确定的主题和跨学科的考虑(例如能源、贸易、森林经济、农业),以及当代的重要意义和不断变动的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理应突出强调国际气候变化法作为一个独特国际法部门的需求②See Cinnamon P.Carlarne et al.,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四、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实现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际法体系正在遭受气候变化问题的冲击,突出表现在环境、人权、贸易、安全、移民等诸多领域,结果是国际法体系结构的冲突和分裂。众所周知,法律部门是基于学术研究而人为主观划分的结果,如果过度强调法律部门之间的差异容易造成学术壁垒、知识断裂和创新停滞,最终阻碍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③参见何志鹏:《国际法哲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因此,面对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问题,需要国际法学者运用新理念、新思维来看待国际法体系的革新,协调和整合国际法规范以创新发展国际气候变化法。
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独立性与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范围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范围有对象范围和规范范围之分,上文关于国际气候变化法对象范围及其独特性的论述是证成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最为重要的法理基础,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着重分析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范围问题,这一问题关涉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实现,包括如何认识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构成以及这些法律规范如何实现体系化两个问题。
一方面,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机制外,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散见于多个国际法律部门,且与国内气候变化法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其规范构成之复杂在法学领域较为少见。就其理论与实践而言,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的主体部分当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机制构成,此外还应当包括普遍国际法中涉及气候变化的原则与规则,其他条约机制和国际组织创制的规范,地区、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规章、政策和制度以及国家、地区和国际法庭的司法判决;①See Daniel Bodansky et al.,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10-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也有学者认为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应当由一般法律原则以及规制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国际关系行为体(国家、超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规范等组成;②See Cinnamon P.Carlarne et al.,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14-2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还有学者认为,气候变化法应当扩展至旨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立法(如法定减排目标、创造碳产权新形式的规范),还包括既存环境法中禁止、允许或者要求在环境评估、开发许可程序中考虑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内容和限制排放的预防、代际公平等一般原则的适用以及规制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③See Tim Bonyhady & Peter Christoff,Climate Law in Australia 2 (The Federation Press 2007).上述关于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构成的认识不一、仁智互见,更为重要的是,国际气候变化法依然处于发展中,伴随国际气候合作深入开展,新的概念、原则和规则必定不断涌现,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必定不断丰富与完善。总体而言,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远未定型,预先限定的做法无异于画地为牢,理当坚持发展观点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审视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构成。需要强调的是,科学认知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规范构成,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国际气候变化法学科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方向。
另一方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面向国际气候合作的实践需求,整合所有调整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法律规范,使之成为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规范体系,这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必然要求。体系化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生命,缺乏体系化的“国际气候变化法”只能称为“气候变化国际法”。正如上文国际气候变化法规范构成所论及的,调整错综复杂的国际气候合作关系,涵盖了不同功能、不同层次和不同部门法律规范。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基本价值,消除国际气候变化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理当打破传统法律部门划分和法学分科,将调整国际气候合作关系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私法规范与公法规范归为一类,构建起内在统一和谐的国际气候变化法律规范体系。这并不是新鲜出炉的观点,犹如学界曾经发生的关于国际经济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属性的激烈争辩一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法律趋同化”“私法的公法化”“公法的私法化”等现象的存在,应该说这一现象在国际气候变化法领域尤为明显。总之,伴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基于气候系统的整体性和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摒弃割裂事物客观规律的传统法律规范划分标准,是符合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内在要求。
五、结语
国际气候变化法已是国际关系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无论怎样,国际气候变化法在某些方面是国际环境法发展的典范,在另外一些方面又预示国际法其他领域未来面临的挑战;不论上述哪一种情形,从更广泛意义上讲,作为国际法新发展的国际气候变化法正在形成并发挥着巨大作用。①See Daniel Bodansky et al.,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aw 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围绕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讨论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展开。一方面,国外学界的系统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代表性著作有《牛津国际气候变化法手册》和《国际气候变化法》。②2016—2017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俄亥俄州立大学Cinnamon P.Carlarne 教授等编的《牛津国际气候变化法手册》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Daniel Bodansky 教授等著的《国际气候变化法》。《牛津国际气候变化法手册》是第一本系统阐述国际气候变化法的著作,提供了国际气候变化法所有方面前所未有的权威论述和未来发展的指引。《国际气候变化法》概述了规制全球气候变化的法律和渊源,依次探讨了国际气候变化法的概念、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基于条约的立法、联合国气候机制的嬗变、《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机制之外的气候治理、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的互动等内容。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对国际气候变化法的出现及其发展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薄弱。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正积极地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显然,加强国际气候变化法的理论研究,对正在推进全球治理系统变革的中国和国际气候变化法理论极为重要。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规则制定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和“造法”的新阵地,中国应借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之势,以全球气候治理这一全球治理系统变革的关键领域为突破口,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提升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再升级,为迈向更加民主、公平正义的国际法治作出更大贡献。①参见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8页。另一方面,国际气候变化法是国际法的前沿领域,理论化程度整体上不高,但是国际气候变化法独立性的论证表明其学科发展势头强劲,中国应加强国际气候变化法领域的新问题、新实践、新认知的研究、概括和总结,这既是国际法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又能以此引领国际气候变化法理论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