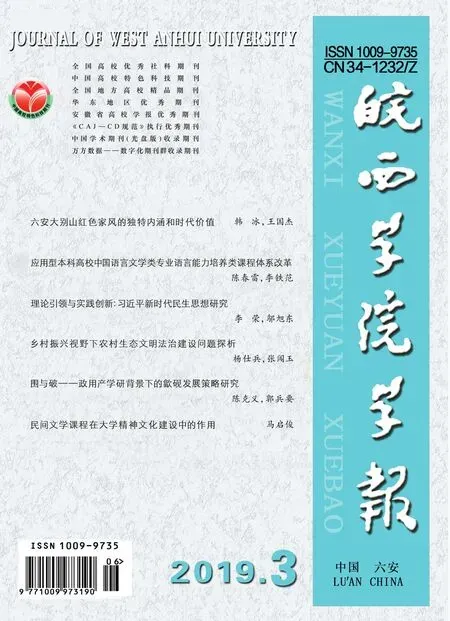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制度探析
高拉杰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重庆 401120)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在我国正式施行。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胎”,国家政策的变动体现了我国对于人权的愈加重视,同时亦意味着将给胎儿利益保护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
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正式施行。其第十六条以在特定情况下,法律拟制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方式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进行了明文规定。诚然,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我国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较之以往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该条文即在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方面对胎儿利益保护予以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民法通则》中立法空白、仅在《继承法》中规定胎儿“特留份”的立法缺憾。但同时,该条文并非完善之规。在愈加多元化、愈加被认可的胎儿利益群中,抚养费赔偿请求权是其中不容忽视的存在,此处却无甚体现。
首先这一规定并未明示胎儿的抚养费赔偿请求权,其次其中虽有“等”字进行兜底,法官对其释义和运用却不甚统一,并不足以应对实务中解决案件争议的需求。有观点认为,该条文明确规定只有涉及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等法律关系时才保护胎儿利益,并不包括抚养费赔偿请求权;我国现行法律亦未规定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应当保护胎儿利益①。亦有观点认为,根据该条款,涉及胎儿利益保护的,应视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从而对胎儿利益予以保护②。《民法总则》出台之后尚且有此争议,更遑论其出台之前的裁判情况了。立法的缺失和不尽完善导致了司法争议,同案不同判现象即是反映。
基于上述缺失和争议的存在,在对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进行探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要否及于胎儿,原因何如;其二,若肯定之,此请求权又该如何及于胎儿。《民法总则》的出台是胎儿利益保护的有利风向标,承继的民法典编撰则是我们进行制度完善不可多得的良机,明确此二问题,方为把握时机、促进制度构建之作为。
二、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要否及于胎儿
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要否及于胎儿呢?请求权的产生基于利益的存在,因而理应先行探讨胎儿的抚养费利益应否予以保护。若为肯定,则可接续探讨在抚养费利益受侵害时胎儿对于损害赔偿的享权资格。要否及于,可待证成。
(一)胎儿抚养费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
所谓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是指在胎儿孕育过程中,对其具有抚养义务的人因侵权行为而致生命或健康利益受到损害,无法在胎儿出生后履行或者完全履行抚养义务,从而影响了胎儿可期待的受抚养利益而引发的对侵权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胎儿抚养费利益的受保护性是这一权利的基础,因此势必需要厘清该利益保护的相关理论缘由。胎儿抚养费利益下属于胎儿利益。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权利保护体系的愈加完整,胎儿利益的保护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并越来越多地运用于实务纠纷的解决。但是基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等的不同,胎儿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1.权利能力说
这一学说借鉴自然人利益保护的理论,以胎儿是否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作为其利益保护的理论基础,以此来认定胎儿的主体地位。根据赋予胎儿的权利能力的程度的差异,可对该学说进行如下几种细分。其一,权利能力否定说。“对于传统民法中已经明确对权利能力的具体规定,除非发生足以让法律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事件,否则不得轻易更改此项制度。对胎儿进行保护的问题尚不属于巨大问题,不能仅为关于胎儿的某些特殊利益而随意更改。”[1](P18)该说严格按照自然人的利益保护标准来审视胎儿的利益保护,认为胎儿没有权利能力。其二,部分权利能力说。“相对于自然人来说,胎儿仅具有部分权利能力”[2]。该说对于胎儿的权利能力持居中态度,不予完全的承认或否认,而是以基本规定加例外情形的方式来进行法律规制,即认可胎儿并非权利能力的主体是该学说的基本规定,但是例外情形下可以对其拟制赋予。而对于例外情形的认定,不同国家的立法尚无统一的标准。其三,相对全面能力说。“全面”即以总括方式先予胎儿以权利能力的赋予来奠基其利益保护,而“相对”则是基于胎儿尚未出生这一与自然人间存在的天然差距所进行的制度调和,即对胎儿全面的权利能力的享有附加一定的条件。根据权利能力的生效时间和有无溯及力的差异,可将这一学说细分为附解除条件说和附停止条件说。附解除条件说即在胎儿孕育阶段便赋予其权利能力,但是若出现一定情形,例如胎儿娩出时为死体,则该权利能力消灭。而附停止条件说则反之。其在胎儿出生之前并不认可胎儿具有权利能力,而等到胎儿活体出生之后溯及以往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其四,绝对的全面权利能力说。这种学说将胎儿的利益保护完全按照自然人的规则进行设计,即认可胎儿从孕育时便具有全面的权利能力,且即使胎儿死亡,亦不能否定或者消减其在死亡之前权利能力的存在。
2.法益说
相比于民事权利的多维度认定标准,法益说则较为简单直接。法益,顾名思义,即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基于其对利益保护的广泛性,该学说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认可,也越来越多地被民事立法所尊崇。实务的需求促使法益说衍发出不同的枝干,较为代表性的是生命法益说和人身权延伸保护说。生命法益说主要依据自然法理论,认为生命的起源要远远早于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和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律,其自然属性不能被任何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剥夺。胎儿与自然人具有同质性,但又有其特殊性。虽然胎儿是自然人的不完全形态,但其是生命成长的必经阶段,值得我们运用规则制度对其进行尽可能的保护以维护这一自然馈赠的礼物的完整形态。若生命法益受到损害,对其进行及时的救济方为顺应自然之道。人身权延伸保护说由我国学者杨立新首创。“法律在依法保护民事主体人身权的同时,对于其在出生前或消灭后所依法享有的人身法益,给予延伸至其出生前和消灭后的民法保护。”[3]他基于人权思想将民事主体的人身权涵括出生前、自然人阶段以及死亡后这一全过程,突破了出生和死亡这一权利能力的关卡,从权利能力的桎梏另辟蹊径,以生命过程的延绵性为突破口,力求对相关主体的权益进行最大化保护。
3.侵权责任说
这一学说的出发角度是侵权法。通过侵害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审视,即是否存在侵害行为、损害后果、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来认定是否应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不应基于民事权利的有无,而应基于侵害行为的发生本身。若侵害行为被施加于胎儿,即使其尚未出生,遑论权利能力的享有,依然可基于权益被侵害而寻求相应救济,亦即当事人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影响法律对侵害行为的规制。
多元化的现状,亦是各学说非完备性和非全面性的体现。权利能力说会导致胎儿利益保护的完全或者部分缺席,或者罔顾胎儿真正的需求而盲目施加多余保护;法益说过于抽象;侵权责任说则可能无法适用于非侵权情形下的利益保护。笔者认为,各国对于胎儿利益保护这一问题,应综合考虑立法传统和社会现实需要,慎重进行法律构造,并进行尽可能的制度完善以弥补相应理论的不足,且在司法实务中灵活运用已有制度设计,从而在更大程度上保护胎儿的各项利益。
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的规定可知,我国对于胎儿利益保护所采用的理论基础是相对全面能力说中的附解除条件说。综上所论,这一学说对胎儿利益保护持赞同之姿。那么,胎儿的抚养费利益自然是应当受到保护的。
(二)胎儿之于抚养费赔偿请求权的享有资格
在认可胎儿的抚养费利益理应受到保护的前提下,胎儿又是否具有抚养费利益被侵害时的赔偿请求权的资格呢?对于这一问题,学界认定标准并不统一。否定说严格遵循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这一规则,认为尚在孕育中的胎儿不具有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肯定说则认为即使对胎儿具有抚养义务的人受到侵权伤害之时胎儿尚未出生,但生命的成长是一种过程,胎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生和长大,对抚养费这一利益具有可期待性,应当予以及时、合理的保护,因而应被赋予抚养费赔偿请求权。笔者赞同肯定说,主要基于以下原因。我国《民法总则》表明了对特定情形下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的认可态度,而所谓“特定情形”,即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情形。抚养费赔偿请求权和其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一,均具有一定的财产属性。其二,均是衍生自亲权和人身权的权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胎儿的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要比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的保护来得更为迫切。因为后二者均是胎儿利益的纯粹增加,而前者则是胎儿本来应该具有的成长资金的一种补偿。如果没有额外的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可能对胎儿影响不大;但若胎儿的抚养基金缺失,则势必影响胎儿出生后的抚养和成长利益。因此,胎儿不仅当然地享有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还应尽快以完备的制度对其予以保护。
三、抚养费赔偿请求权如何及于胎儿
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要否及于胎儿已得肯定之证成,那么该请求权又该如何及于胎儿呢?以下探讨实为必要。
(一)享权情形之探讨
上文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的定义即可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即胎儿在第三人侵害其抚养义务人从而间接侵害了其受抚养权时具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此处不予赘言。但我们需对这一问题辖属下的几个特殊点进行更加详尽的探讨。
1.抚养义务人的范围之探讨
我国婚姻法将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人规定为其父母和满足特定情形的养父母、继父母和(外)祖父母等,但是这些规定并不能盲目适用于胎儿。因为胎儿是其父母爱情的结晶,加之其还未出生,那么至少有母亲作为适格的抚养人,尚不存在未成年人抚养情况下出现的收养、以及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情况,因此我们无须多费口舌进行养父母、继父母甚至(外)祖父母抚养义务的探讨,而应着眼于胎儿的父母亲。
父亲作为胎儿的抚养费赔偿请求权所涉及的被侵害对象,一般是没有争议的。实务中对于胎儿抚养费请求权的争议亦多发于其父受到侵害的情形中。因为父亲必然负有对胎儿的抚养义务,而若其生命或者健康权益受到侵害致使其完全或者部分丧失对胎儿的抚养能力,那么侵权人这一侵害行为即侵害了胎儿的受抚养权。
在对父亲遭受侵害时的抚养费请求权进行认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结合实务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胎儿被孕育的同时存在其父母的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下毋庸置疑胎儿的抚养费利益应该得到保护。另一种情况是胎儿的孕育并未伴随着其父母的婚姻,亦即其是父母单纯性行为而导致的孕育状态。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胎儿抚养费请求权应受到如上同等保护。我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因此,即便是不存在婚姻关系而孕育的胎儿,在其生父遭受侵害会影响其未来抚养利益时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③。
胎儿的母亲是否可以成为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的被侵害主体呢?这一情形并不像父亲被侵权时的关系梳理那么明朗。基于母亲和胎儿的同体性,母亲受到人身侵害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胎儿受到侵害。如此一来,要么胎儿因母亲受到严重侵害而失去生命,此时便不再存在抚养义务;要么母亲和胎儿的健康权益受到损害,但是这种损害的伤害程度并不像父亲这一单独个体的侵害那么容易认定,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等待且和胎儿的出生情况结合。且司法实务中几无基于胎儿孕育期间其母亲生命或者健康权益受损而引发的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的诉求,而常以母亲的生命权、健康权、生育权或者胎儿自身的生命、健康权等作为诉因。因此笔者认为,应将母亲排除于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所涉及的被侵害对象的范围。假使母亲对胎儿的抚养义务也完全不能或者部分不能行使,除了基于上述诉因进行损害赔偿请求外,如果实为必要,还可根据胎儿出生后的情况再行抚养费损害赔偿请求,那时便是自然人利益保护的问题了,无须置于胎儿处徒增复杂度。
2.侵害程度之探讨
对胎儿抚养义务人的侵害达到什么程度需要赋予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呢?我们可以运用反推的方式来对其进行论述。父亲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劳动能力是胎儿受父亲抚养的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如果侵权行为使得父亲的生命或者健康权益受到损害,使其完全或者部分失去劳动能力,此时便具备了抚养费赔偿请求权的适用基础。失去生命的认定无甚争议。至于对胎儿父亲健康权益的侵害的认定,可以按照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来予以确认,按照相应的伤残等级判断其失去劳动能力的程度,从而对抚养费的诉求做出裁决。
(二)行权规则之探讨
对于这一权利的行使,学界主要有两种倾向性争议。其一,并不认可胎儿在孕期的抚养费赔偿请求权④。该观点认为抚养费赔偿请求权应当待胎儿出生后,由婴儿本人享有并行使,只是若其尚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可由其监护人代为行使。其二,认为在涉及胎儿利益保护时,应承认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并对其利益予以保护⑤,即认可孕期胎儿的权利主体地位。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原因如下述。首先,抚养费请求权是因为侵权人侵害胎儿的抚养义务人而衍生出的对胎儿受抚养权的侵害,而对负有抚养义务的人的损伤的确定不依赖于胎儿的生命行进过程即可得以明确。其次,“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权利的保护具有时效性。诉讼时效制度即为证明。虽其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权利,但是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敦促享权者及时行权的态度。因此,当权利受到损害,首要应该及时进行权利救济。再者,之所以在胎儿还未出生之前便对其进行抚养费请求权的救济,还基于我国已有的成熟的抚养费计算机制,亦即胎儿未来所需的抚养费是能精确确定的,那么便无必要再行无谓的等待。只是因为进行权利诉求时胎儿尚在未出生阶段,因此可由其近亲属,通常是母亲以胎儿的名义进行起诉,且常常伴随于被侵害的抚养义务人的其他权利诉求。像前述“附解除条件说”的原理一样,假使胎儿死体娩出,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消灭,再行依据不当得利制度对已偿付的费用进行返还即可。
如上所述,我国已经形成成熟的抚养费计算模式,自然可以按此规则来计算赔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据此,我们只需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人均消费性支出(生活消费支出)再乘以18即可计算出胎儿所需抚养费数额。和未成年人需要用18减去其抚养人受到侵害时其现有年龄来计算抚养费年限不一样的是,胎儿尚未出生,十八年无任何短缺,所以直接乘以18即可。此为胎儿父亲生命权益受损以致死亡时胎儿的抚养费计算方式。如果胎儿父亲健康权益受损,则只需用上述计算结果再乘以对应的伤残度(1级为100%,2级为90%直至10级10%)计算即可。
(三)费用返还之探讨
生命是一线而非一点,自然人尚且受到生命中众多不确定因素的威胁而有遭遇人身损害甚至丧生的可能,遑论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有更多不确定性的胎儿?如果支持在胎儿还未出生时就准许其享有抚养费请求权的制度设计,那么我们也必须根据胎儿的成长和出生情况来设计相应的配套制度解决后续事宜。根据我国《民法总则》第十六条的规定,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如此一来,其通过遗产继承和接受赠与所获利益将全部予以返还;相应地,这一效力亦可推及至胎儿的抚养费请求权。如果胎儿死体娩出,起初设定的抚养人对于该胎儿未来的抚养义务消灭,也就意味着抚养费的给付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是为不当得利,受有利益一方应向损失利益一方返还该利益。因此,如果胎儿娩出时为死体,其因抚养费请求权所获抚养费用即应予以返还。
此外,对于介于死体出生和活体出生并顺利成长的中间状态,即如果胎儿活体出生,但是出生后很快便死亡,此时抚养费是否应予返还呢?如果不应,原因何在?如果返还,还多少为宜?笔者认为,如果胎儿活体出生,则不拘其出生后存活多久,均应统一标准,不予返还抚养费。进行这样的制度设计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如果胎儿活体出生后又死亡,这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如何界定并无统一标准。分钟、小时、天、月、年?生命的价值和质量的量化是一个充满主观性的过程,标准不一必然结果多样。不若寻找一个对胎儿利益保护较为全面和少争议的时间点,那便是胎儿只要活体出生便应享有抚养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不论他出生后能够存活多久,因为胎儿活体出生本身便证明了值得保护性。再者,以固定的标准计算胎儿的抚养费,像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的计算一样,只是通过这样一个请求名义来对侵权者进行民事上的侵权惩治,表明法律对权益受侵害者的维护态度。只要在适当时点受侵权人享有这一权利即可,而不要求其持续性的满足享权资格的要求。因为类于“即使享有死亡赔偿金的对象没有死亡,也并不能保证其一定会顺利存活至死亡赔偿金所赔付的年限”,即使胎儿出生后未顺利存活至抚养费所涵盖的年限也不再返还已偿付的抚养费;反之,即使在胎儿顺利出生后其抚养人对其实际进行养育期间所支出的抚养费远远超过赔付标准,也不需侵权人再行补偿。
四、结语
《民法总则》对胎儿利益保护的立法突破,是起步而非止步。欲有效回应司法实务的紧迫需求,仍需对胎儿的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进行理论的不断探究,从而对民法典中民法分则的编撰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提供更加成熟的理论依据,以弥补《民法总则》对于该项内容规定的缺失这一不足,并指导实务中的司法适用以避免争议,来达致法律实务中可操作、法律适用上可统一和民事主体行为可预期的效果[4]。而在这一过程中,认可胎儿对于抚养费赔偿请求权的享权资格,明晰其享权情形、行权规则和费用返还等后续事由,对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构筑胎儿抚养费赔偿请求权这一制度而言,实为不可或缺之步骤。
注释:
① 参见(2017)桂08民终1443号苏某1、柳志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2018)黔03民终645号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刘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 书。
③ 参见(2017)晋02民终1862号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市分公司与郭立红、任佩佩、任建兴、李桂花、班立媛、田鹏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2018)闽07民终631号叶某1、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光泽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⑤ 参见(2018)黔03民终645号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遵义市中心支公司、刘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兼论平等理念下现代法的权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