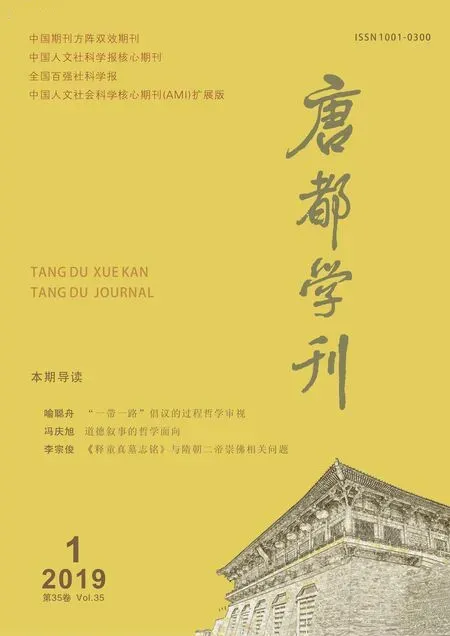唐代的褒城和褒城驿初探
梁中效
(陕西理工大学 秦蜀古道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汉中 723000)
唐代的褒城是褒斜道的咽喉和枢纽,是兴元府发展繁荣的经济文化支撑点,是千里蜀道上长安与成都之间的战略节点。唐代的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驿”。因此,对唐代的褒城和褒城驿探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唐代褒城县城的沿革
汉魏间褒中县在褒河之西、褒谷口的台地上[1]。唐代的褒城县仍然在汉魏褒中县的城址之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褒水又东南历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谓北出褒斜。褒水又南迳褒县故城东,褒中县也。本褒国矣,汉昭帝元凤六年(前75)置。褒水又南流入于汉。”[2]郦氏似乎认为汉魏褒中县即褒国国都。唐代学者对此提出异议。
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初唐魏王李泰主编的《括地志》云:“褒国故城在梁州褒城县东二百步,古褒国也。”[3]证明唐褒城县在褒河西岸,“褒国故城”在褒河东岸,隔河相望,相距二百步。唐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说:
褒城县(自注:东至府三十三里),本汉褒中县,属汉中郡,都尉理之。古褒国也。当斜谷大路,晋义熙末,朱龄石平蜀,梁州刺史理此,仍改褒中县。魏又于此置褒中郡。隋开皇元年,以避庙讳改为褒内县,仁寿元年改为褒城。褒水,源出县西衙岭川。斜水与褒水在县北五里。南口为褒,北口为斜,长四百七十里。褒国,在县东二百步。褒姒之所出也。[4]
由李吉甫叙述的褒城县地理方位判断,隋唐褒城县城仍在褒河西岸的台地之上,是褒斜道入口的门户,县城与古褒国都城并未重叠,但距离很近,“在县东二百步”。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在《通典·州郡典》中也说:“褒城,汉褒中县,有褒水、褒谷。”[5]也证明唐代褒城县在褒谷口。中晚唐诗人顾非熊《行经褒城寄兴元姚从事》云:
往岁客龟城,同时听鹿鸣。君兼莲幕贵,我得桂枝荣。栈阁危初尽,褒川路忽平。心期一壶酒,静话别离情。
由诗中的“栈阁危初尽,褒川路忽平”来判断,唐代褒城县就在褒谷口。胡曾《咏史诗·褒城》:
恃宠娇多得自由,骊山举火戏诸侯。只知一笑倾人国,不觉胡尘满玉楼。[6]
也是立足褒国来写褒姒,而褒国就在褒谷口,胡曾诗歌中的“褒城”显然就在褒谷口的褒河西岸。晚唐诗人韦庄《鸡公帻(去褒城县二十里)》说:
石状虽如帻,山形可类鸡。向风疑欲斗,带雨似闻啼。蔓织青笼合,松长翠羽低。不鸣非有意,为怕客奔齐。[7]314
这里的“鸡公帻”就是七盘古道上形似雄鸡之冠的一块巨石,宋元之后在此石附近设关以检查私茶和行人,故取名“鸡头关”。晚唐诗人冯涓《蜀驮引》也说:
昂藏大步蚕丛国,曲颈微伸高九尺。卓女窥窗莫我知,严仙据案何曾识。自古皆传蜀道难,尔何能过拔蛇山。忽惊登得鸡翁碛,又恐碍著鹿头关。
诗中的“鸡翁碛”即未庄诗中的“鸡公帻”,也就是后世的“鸡头关”。冯涓将汉中褒城的“鸡翁碛”与四川德阳城北三十里的“鹿头关”,视为入川大道上最艰险的两大关隘,一句“忽惊登得鸡翁碛,又恐碍著鹿头关”,让“鸡头关”与褒城名扬天下。壭庄的诗以褒城为立足点来进入褒城的山道,也证明唐代褒城就在七盘岭、即鸡头关下的褒谷口褒河西岸。
中晚唐褒城县在褒谷口,也可从孙樵的《兴元新路记》中得到印证。他自文川道到兴元府,“自灵泉平行十五里,至长柳店,夹道居民。又行十五里,至兴元西。平行三十里,至褒城县,与斜谷旧路合矣。”[9]2615孙樵自东向西穿过兴元府城,然后向北“平行三十里,至褒城县,与斜谷旧路合矣。”[9]2615证明褒城县就在斜谷旧路入口的褒谷口褒河西岸。北宋初年编修的《太平寰宇记》也认为褒城县在褒河西岸,褒城县与古褒国并非一地。“褒城县,本汉褒中县,以其当褒斜大路,故名。汉都尉理此。其褒国城为褒水所坏,盖后汉末、曹魏初移于今理。”“隋初郡与县并改为褒内,三年罢郡,以县属梁州。仁寿元年改为褒城,义宁二年又改褒中。贞观三年又改褒城。”“衙岭山,在县西北九十里,褒水源出此山,至县理东注汉水。”[9]证明东汉末至北宋初年的褒城就在今天褒河西岸的阶地之上,两汉时期因褒河泛溢,冲毁了褒谷口外平原之上古褒国的褒城,即汉代的褒中县城,到汉末三国时期,为避水灾才将县城由平原移到了褒河西岸的台地之上。
从唐宋到明清褒城县的城址未再发生大的变化,但明清地方志曾记载汉唐褒城县在十里外的打钟寺(今汉中市汉台区宗营镇打钟坝村),宋元时期迁到山河堰附近。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良知纂修的《汉中府志》卷1《舆地》:褒城县,“唐贞观复为褒城县,宋元因之徙治山河堰南,本朝仍今名。”卷10《古迹》云:“褒州,具南十里打钟坎。”[10]清代地方志继承了明朝方志的成说。清康煕滕天绶的《汉南郡志》卷3《建置志》:褒城县“汉唐建县于打钟寺,宋徙山河堰。”[11]清道光十一年刊刻的《褒城县志》卷6《城署志》:“县城自汉唐来俱建于打钟坝,宋庆历间移于山河堰北,当褒谷南口,北倚连城山,褒水环其东南。”[12]424由上文可知,清代地方官员与学人,认为汉唐褒城“俱建于打钟坝,宋庆历间移于山河堰北。”完全承袭了明代方志的观点,与史实相悖。汉唐在褒谷口设褒中县和褒城县,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褒斜道的交通咽喉。
其一,唐代褒城县北即七盘古道,称为“七盘岭”或“七盘山”。“在鸡头关下,盘回七转,方至山顶,由此入连云栈。”[13]初唐大诗人沈佺期《夜宿七盘岭》:“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证明褒城就在七盘岭下,不可能在十里外的打钟寺(坝)。
其二,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认为,“褒水源出此山(衙岭山),至县理(褒城)东注汉水。”而打钟寺(坝)在褒河的东岸,且距褒河稍远(约3里),显然宋初县城不在此地。
其三,北宋庆历年间未曾将褒城县由打钟寺迁山河堰附近。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任褒城知县的窦充在庆历四年(1044)《重修大成至圣文宣王庙记》中说:“褒城县隶封汉中,跨据秦陇,控斜谷之岩阻,厥田沃衍,其俗富庶,三堰之美利在。”但学校不兴,“先是旧庙,僻处山坞,荒庭寥落,鞠成榛莽,棼橑倾颓,风雨弗庇,春秋释奠,何陋如之。”于是“择堰之右,得官地一廛,芟秽度址,鸠材僝工,靡逾月而栋宇鼎新,不越时而塑像俨列。”[14]879由此可见,窦充履职之前,褒城县就矗立在褒河西岸,孔庙为主体的学校,“僻处山坞,荒庭寥落”,于是窦充在山河堰傍较为平坦的地方重建学校,而不是迁建县城。
其四,明代张瑞的《褒城县修城记》也说:“褒城今之县治,建自宋庆历以前,历我皇明于兹,五百余年矣。其城池兴废,稽《志》无载,征迹无遗,是兹所未有也。”[14]899明确否定了北宋庆历年间迁城的说法,而且指出褒城“建自宋庆历以前”,此前的城池兴废,已无法稽考。
其五,褒中与褒城县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与褒国有关,而明清方志认为,古褒国“在县东三里骆驼坪”[12]70,也间接否定了唐褒城县在打钟坝。
其六,有学者认为,产生唐褒城县在打钟坝之讹误的原因,可能出自明嘉靖《汉中府志》将唐褒州故址定在了褒城县南十里的打钟坝,清代方志作者误认为褒州即唐代的褒城与汉魏褒中县的故址。[15]
总之,唐代褒城县继承了汉魏褒中县的地脉与文脉,其城址就在在褒河西岸的台地上,元明清三朝褒城县城仍在褒河西岸唐宋褒城的故址之上。明清地方志认为汉唐褒中县、褒城县在褒谷口外十里的打钟坝,到北宋庆历年间才迁徙到褒谷口的褒河西岸,是不切实际的误判。唐代的褒城驿应该与褒城县相互依存,在褒斜大道南端褒谷口的褒河西岸。
二、唐代褒城驿的盛衰
古褒城位于七盘岭之下,是汉渭褒斜道与唐宋褒斜道的门户。褒城驿应该在褒城外的褒河西岸,背山面水,处在水陆交通要冲,管控北上的褒斜道、西去的金牛道与南下进入汉中城或者渡汉江入巴山的米道,交通地位极为重要。中唐以前中原经济文化发达,对巴蜀、汉中的依赖相对较弱,褒城驿相对的接待任务稍轻,游人、商旅多下榻褒城城中或七盘岭之上,因此,现存中唐以前的褒斜道游记诗文,多涉及“七盘岭”与褒城,很少提及褒城驿。
加入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这个中介变量后,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来考察父母来生信念和死亡话题的亲子谈话与儿童来生信念的关系。依次将父母的来生信念(BA量表得分)、死亡话题亲子谈话(PDCA量表得分)纳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采用Sobel检验方法对心理理论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Z=-2.36,p<0.05。当将亲子谈话纳入回归模型时,父母来生信念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表明亲子谈话起到显著、完全的中介作用(具体指标见表7)。
初盛唐文人、商旅经行褒城时,对七盘岭印象深刻,留下了一些诗文华章。初唐大诗人沈佺期《夜宿七盘岭》:
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晓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
这里的“七盘”,即“七盘岭”,证明自北魏以来,为避石门之险已开辟了七盘岭上之路。卢照邻在《早度分水岭》中也有“层冰横九折,积石凌七盘”的诗句。盛唐大诗人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
前日登七盘,旷然见三巴。汉水出嶓冢,梁山控褒斜。栈道笼迅湍,行人贯层崖。岩倾劣通马,石窄难容车。
这是对褒城、七盘岭、褒斜栈道最生动形象的描写。岑参在《礼泉东谿送程皓、元镜微入蜀(得寒字)》诗中有“蜀郡路漫漫,梁州过七盘”的诗句。这些诗章名句,构成了七盘古道与古褒城相依相存的宁静画卷,反映了初盛唐褒城驿所在地的交通面貌,也证明唐代的褒城县城就在七盘岭下的褒河西岸。
“安史之乱”后,以西京长安与东都洛为轴心的中原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加之气候也逐渐由温润向寒旱转变,黄河流域无可挽回的衰落了,长江流域超过黄河流域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区,唐王朝极为依赖近在咫尺的汉中与巴蜀,从唐玄宗开始,关中危机时,皇帝就向西南逃跑,在此背景下,秦蜀古道更加繁忙,作为官驿大道的褒斜道空前繁荣,地处水陆交通要冲的褒城驿声名鹊起,就获得了“天下第一驿”的美名。
“七过褒城驿,回回各为情”的大诗人元稹,亲自体验了褒城驿的繁盛与落寞。元和四年(809)春,元稹以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赋诗三十二章,记沿途所经驿站和山川景观,是中唐较为详尽的蜀道记游诗,这组诗“起骆口驿,尽望喜台”。在骆谷道入口处的骆口驿东壁上,元稹看到李逢吉、崔韶出使云南时的题名,在北壁上有白居易等人的题诗,正是“邮亭壁上数行字,崔李题名王白诗”。证明中唐时期途经傥骆道的诗人、官员是比较多的。元稹在崎岖难行的傥骆道上行走了约6天,其间还在青山驿玩月忆往事。三月十四日左右“行至汉上”,恰逢清明节,“今日清明汉江上,一身骑马县官迎”。[16]143十五日夜宿兴元府汉川驿,做“梁州梦”,有《梁州梦》诗:“亭吏呼人排去马,忽警身在古梁州”。三月十六日,由兴元府向北沿大驿路到褒河东岸(今汉台区河东店),在褒城县令迎接下坐船渡过褒河进入褒城驿。他在《赠黄明府诗》诗序中写道:当年在山西解县,与他对饮的黄县丞,不胜酒力,逃席而去,不成想此人已升为褒城县令,即“黄明府(唐人称县令为明府)。”
元和四年三月,奉使东川,十六日,至褒城东数里,遥望驿亭,前有大池,楼榭甚盛。逡巡,有黄明府见迎,瞻其形容,仿佛似识,问其前衔,则固曩时之逃席黄丞也。说向前事,黄生悯然而寤,因馈酒一樽,舣舟请余同载。余不免其意,与之尽欢。遍问座隅山川,则曰:“褒姒所奔之城在其左,诸葛所征之路在其右。”感今怀古,作《赠黄明府》诗。
少年曾痛饮,黄令困飞觥。席上当时走,马前今日迎。依稀述姓氏,积渐识平生。故友身皆远,他乡眼暂明。便邀连榻坐,兼共樀船行。酒思临风乱,霜稜掃地平。不堪深浅酌,贪怆古今情。逦迤七盘路,坡陀数丈城。花疑褒女笑,栈想武侯征。一种埋幽石,老闲千载名。[16]137
这首诗的“诗序”与诗结合起来,给我们描写了元和四年春三月,褒城县黄县令迎接监察御史元稹,坐船欣赏褒谷美景的快乐场景。由元稹的行程和诗中描写的“七盘路”“数丈城”与“褒女笑”“武侯征”等自然人文景观来看,唐代的褒城县就在七盘路下面的褒河西岸,“褒姒所奔之城在其左”,即褒河东岸古褒国;“诸葛所征之路在其右”,即褒河西岸的褒斜道。褒城驿在县城外东南方向,地势比县城低平,且濒临褒河,因此“有大池”,有“驿亭”,有“千竿竹”“千树梨”,“楼榭甚盛”。中唐时期褒城驿建筑秀美,山水荡漾,翠竹环绕,梨花似雪,桃花灼目。元稹的《褒城驿》诗云:
严秦修此驿,兼涨驿前池。已种千竿竹,又栽千树梨。四年三月半,新笋晚花时。怅望东川去,等闲题作诗。
他说是“军大夫严秦”修的褒城驿。在褒城驿池岸青翠的竹林中,有枝条下垂的“亚枝红”桃花,格外夺人眼目。元禛的《亚枝红》诗自序:
往岁,与乐天曾于郭家亭子竹林中,见亚枝红桃花半在池水。自后数年,不复记得。忽于褒城驿池岸竹间见之,宛如旧物,深所怆然。
其诗云:
平阳池上亚枝红,怅望山邮是事同。还向万竿深竹里,一枝浑卧碧流中。[14]144
值得注意的是,元稹将褒城驿称为“山邮”,证明驿站在褒谷口外的七盘岭山下,而不在汉中盆地中央的汉江之滨。在万竿深竹与碧水之间,亚枝红桃花怒放争春,使得“天下第一驿”名不虚传,也让诗人终身难忘。过了褒城后,到西县(今勉县)白马驿,晚上在南楼忽然听到悠扬的笛声,“今夜听时在何处,月明西县驿南楼”。由西县过百牢关踏上金牛道,经三泉驿、嘉川驿、漫天岭、望喜驿,月底到望喜台,“可怜三月三旬足,怅望江边望喜台。”[16]158元和十年(815),元禛被贬为通州司马,“忽到沣西总回去,一身骑马向通州。”由长安赴通州(今四川达州市),再次经行傥骆道,他在《紫踯躅》诗中说:“去年春别湘水头,今年夏见青山曲(自注:青山,驿名)”“尔踯躅,我向通川尔幽独。可怜今夜宿青山,何年却向青山宿。”[16]630唐代的青山驿在傥骆道上周至与洋县的交界处。他的《山枇杷》诗又云:“往年乘传过青山,正值山花好时节。”“昨来谷口先相问,及到山前已消歇。”[16]631“往年乘传过青山”,指的是元和四年三月于“青山驿玩月”。这两首诗结合起来,证明元稹再次经行傥骆道到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市汉台区),然后由驿路向北到褒河谷的褒城驿,再经金牛道向通州。中晚唐时期,唐朝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日益衰落,在此背景下褒城驿也出现了衰败景象。元稹的《褒城驿二首》:
容州诗句在褒城,几度经过眼暂明。今日重看满衫泪,可怜名字已前生。[16]633
“容州”指的是诗友窦群,曾被贬为开州(今重庆市开州区)刺史与容管经略使,在此期间经行褒城驿,故有题诗。“忆昔万株梨映竹,遇逢黄令醉残春。梨枯竹尽黄令死,今日再来衰病身。”被贬谪的困苦心情,使得他眼中的褒城驿失去了昔日的风貌。到通州后患上了疟疾,几乎死去。其间多次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又几次经过褒城驿。他在《献荥阳公诗五十韵》中说:“稹病疟二年,求医在此,荥阳公不忍归之瘴乡。”[16]665这里的“荥阳公”即“山南西道节度使、兴元尹”郑余庆,他对患了疟疾的元稹颇多照顾。“稹病疟二年”,是指元和十年(815)夏,患上疟疾,赴兴元医治,到元和十二年(817)秋,由兴元返回通州,在汉中寓居二年有余。因此,元稹对汉中极为熟悉,更是七次经停褒城驿。他在《遣行十首》中说:“愁君明月夜,独自入山行。七过褒城驿,回回各为情。”“褒县驿前境,曲江池上情。”“每逢危栈处,须作贯鱼行。”[16]736-737他在《奉和权相公行次临阙驿逢郑仆射相公归朝俄顷分途因以奉赠诗十四韵》中说:“汉上坛仍筑,褒西阵再图。”[16]675讲的是韩信登坛拜将与诸葛亮八阵图的故事。这些美妙的诗句描写了褒城驿和栈道上的经历。元稹不仅两次由长安向巴蜀经过褒城驿,而且五次由巴蜀向兴元、长安经停褒城驿,充分证明了褒城驿在秦蜀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中晚唐的许多诗人都曾经停褒城县或褒城驿,他们的诗文佳作,记录了这一时期褒城驿由兴盛到衰败的历程。
与元禛同时代的羊士谔(762—819),他们二人都与窦群交好。窦群曾被贬容州(今广西容县)任容管经略使,后人称窦群为窦容州。羊士谔在元和初被宰相李吉甫知奖,擢为监察御史,掌制诰。后以与窦群、吕温等诬论宰执,出为资州刺史(今四川资阳)时,在秋天经过褒城驿,其《褒城驿池塘玩月》云:
夜长秋始半,圆景丽银河。北渚清光溢,西山爽气多。鹤飞闻坠露,鱼戏见增波。千里家林望,凉飙换绿萝。
诗人下榻褒城驿,秋夜在驿池边赏月,西山七盘岭上秋风吹来,池中鱼跃的水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诗中的“西山爽气多”,指的是褒河西岸褒城县西北的七盘岭。诗中的“北渚清光溢”,指的是褒城驿北褒河中的沙洲。羊士谔的这首诗再次证明唐代褒城驿就在今褒河西岸古褒城南门外。
晚唐诗人薛能咸通中(860—874)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市)刺史,大概在元稹元和十年(815)经过褒城驿后四十余年之后,薛能经过褒斜道和褒城驿。尽管此时的褒城驿已非昔日的面貌,在驿壁上看到元稹的诗。他的《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云:

元稹诗中驿池碧波荡漾、池岸“万竹与千梨”的褒城驿,到薛能经停时,面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出衰败的景象。他的《题褒城驿池》诗说:
池馆通秦槛向衢,旧闻佳赏此踟蹰。清凉不散亭犹在,事力何销舫已无。钓客坐风临岛屿,牧牛当雨食菰蒲。西川吟吏偏思葺,只恐归寻水亦枯。
驿亭虽在,但景致全无,失去了昔日的繁华。薛能休憩的褒城驿,显然在褒河岸边。两首诗中的“青白鹭鸶”,“钓客坐风临岛屿”,皆是褒河边的景观。如果褒城驿远离褒城与褒河,元稹、薛能等唐代著名诗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最喜欢褒城与褒河之间山水风光迷人的褒城驿。
总之,唐代秦蜀交通发达,国都长安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要冲即褒谷口的褒城县,这里处在褒斜道、金牛道与米仓道、出入兴元府道的交汇处,褒城驿因之而成为“天下第一驿”。元稹等大诗人的佳作,描绘了当年褒城驿的美丽景象及盛衰变化,折射出大唐帝国秦蜀交通的变迁轨迹。
三、唐代褒城驿的影响
唐代褒城驿是当时京师长安南到成都天府之国的中转站和第一大驿,影响深远,不仅唐诗屡有描写,更有文人墨客专文书写,最著名者莫若晚唐文学家孙樵。
他的《书褒城驿壁》:
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乌睹其所谓宏丽者?讯于驿吏,则曰:“忠穆公曾牧梁州,以褒城控二节度治所,龙节虎旗,驰驿奔轺,以去以来,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宁有顾惜心耶?至如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渔钓,则必枯泉混泥尽鱼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几所以污败室庐,糜毁器用。官小者,其下虽气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难禁。由是日益破碎,不与曩类。某曹八九辈,虽以供馈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补数十百人残暴乎?”[8]2694-2695
由孙樵的记载可知,“褒城驿号天下第一”。这个天下第一驿的美名主要是唐德宗避难兴元前后,建中三年(782)十一月,严震(死后谥号忠穆,,故孙樵尊称其为“忠穆公”)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兼任御史大夫。他认为褒城驿是控扼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兴元府(今陕西南郑县)、风翔节度使治所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与剑南道东西两川的交通要冲,“由是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8]3694
褒城驿是国家“直辖市”——兴元府的门户。建中四年(783)“泾元兵变”后,唐德宗逃出长安,避难到奉天(今陕西乾县),受到叛军威胁,准备避地汉中。兴元元年(784)二月,严震派部将迎奉车驾,击败追兵,护送德宗进入骆谷,三月,德宗抵达山南西道的首府梁州,严震亲自率军至清凉川迎接。五月,唐军收复长安,德宗准备返回京师,加授严震为检校尚书左仆射。随后,朝廷又升梁州为兴元府,将“建中”年号改为“兴元”,以示褒崇,“宜改梁州为兴元府,其署置官资望,一切与京兆、河南府同。”[17]同时任命严震为首任兴元尹。兴元府的行政地位比肩西京兆府与东都河南府,一下子升格为国家“直辖市”,其门户“褒城驿”,自然要宏大壮丽。唐德宗返回长安时,就是经褒城驿,由褒斜道回关中。“兴元元年六月戊午,车驾还京,发兴元。是日,大雨。及入斜谷,晴霁,从官将士欢然,以为天助。”[18]兴元府设立之初,朝廷极为重视,成为“宰相翱翔之地”。刘禹锡在《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中描绘兴元府:
天汉之邦,实居右部。按梁州为都督治所,领十有五州,县道带蛮夷,山川扼陇蜀,故二千石有采访防御之名。兵兴多故,其任益重。澄清节钺,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南巡狩,偃翠华而徘徊,箫勺之音洽于巴汉。戡难清宫,六龙言旋,乃下诏复除征徭,升州为府。等威班制,与岐、益同。地既尊大,用人随异。故自兴元至大和,五十年间,以勋庸佩相印者三,以谟明历真相者九,由台席授钺未几复入相者再焉。磊落震耀,冠于天下。[19]
从唐德宗兴元年间,到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五十年间,兴元府至少出了十多位宰相,由于地位尊崇,“褒城驿号天下第一”的美名至少也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晚唐诗人薛能在咸通中(860—874),有《褒城驿有故元相公旧题诗,因仰叹而作》云:
鄂相顷题应好池,题云万竹与千梨。我来已变当初地,前过应无继此诗。
晚唐时期,孙樵与薛能等人看到的褒城驿,已失去了昔日宏丽壮观景象,呈现出“庭除甚芜,堂庑甚残”的衰败景象。
总之,唐代的褒城与褒城驿相互依存,矗立在褒斜道南出口的褒河西岸,背山面水,气象万千,形势险要,交通繁忙,人流如织,是国都长安与成都天府之间的交通要冲,是大唐蜀道经济文化带的支点。唐代褒城雄踞七盘古道入口处,“褒城控二节度治所,龙节虎旗,驰驿奔轺,以去以来,毂交蹄劘。”“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唐代褒城驿在安史之乱后,在严震治理山南时期,随着川陕交通联系的日趋紧密,随着褒斜道官驿大道的繁荣,“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唐代褒城与褒城驿繁盛的局面大约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在唐末逐渐衰败,与大唐帝国的落日残阳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