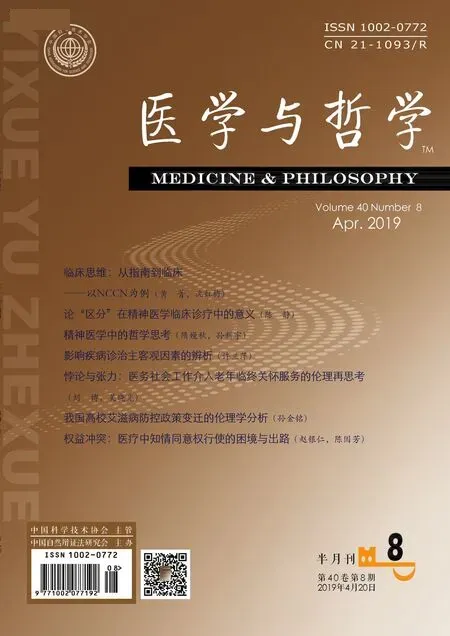不同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疾病隐喻*
李 萍 傅义强
十九大报告将民生问题再次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特别强调:“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1]。爱国卫生运动诞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创造了贫困年代的健康奇迹,带有着那个时代的养分和经验,对新中国政权巩固起到重要作用,新政权把帝国主义话语霸权下“东亚病夫”的不合理隐喻成功转化为动员民众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的话语武器,通过个体、社会以及国家层面的医学人文关怀,最终实现自救并创造出卫生运动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中国卫生模式,这对于新时代提升民众健康素养和健康自觉以及健康中国方针都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1 “疾病的隐喻”彰显多维医学人文关怀
“隐喻”一词,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创造,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2]101。其表达方式和思维过程都带有人的主观意志性,并在意志表达中衍生新义、求得共鸣。“隐喻”本身并无褒贬之分,但在被主体隐喻化过程中会被赋予感情色彩。苏珊·桑塔格最早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运用到“疾病的隐喻”概念,是指人们赋予疾病之上的额外想象、社会意义和价值判断等,对疾病的隐喻亦没有褒贬之分,正如她所指出的,“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样的可憎”[2]184,但是苏珊·桑塔格批判将生活中的一些传染性疾病鬼魅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化成一种道德批判、文化偏见甚至政治压迫的过程[2]3,要想摆脱这些加构在疾病之上的不合理隐喻和偏见,光靠回避不行,而必须对它们进行正视、细究、揭露和批判。
人文关怀是指“通过知识、情感、心理环境氛围体现以人为本、温馨服务和人文精神的关怀活动,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切、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维护、对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3]医学人文关怀是人文关怀在医学实践领域的体现,在通过预防疾病来增进人类健康的进程中,医学人文关怀的探索从简单到复杂、从孤立到系统,是多层次、多元性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医生对患者的耐心治疗、细致问诊,是一种起码的“人文关怀”,而政府的社会医疗保障措施、媒体对医患群体权益的关注,则是一种体现公正公平的较高层次的“人文关怀”[4]。医学与人文关怀的联姻,不仅是脱离现实医患困境的捷径,更是维护人权、促进民生的创举。
疾病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一时段扮演着病人的角色,因此,也都必然经历医疗的过程、感受医学的人文关怀。隐喻和关怀二者之间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疾病犹如一根命运之线穿插其中,将二者联结起来,疾病的隐喻与医学人文关怀包含3个层面的逻辑关系。
第一个层面,从个人角度来说,疾病就是一种普遍发生的身体各部分不相容的状态,在这个层面上,医学人文关怀主要表现在贯彻医学技术和职业道德基础上的治病救人。个人的身体疾病不涉及复杂的隐喻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诊断和治疗。当疾病开始与社会关系相联系起来,就发展到第二个层面,即社会层面的隐喻与关怀。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利益问题,生物的本能就是趋利避害,疾病往往被隐喻为社会有害、传染之物,带给人以恐惧和危害,所以人们远离它、排斥它,在这种情况下,生病成了一件让患者觉得有失人格的事,王一方[5]将其表述为“为他人的存在”,即对疾病的定义看法和病患的感受体验深受患者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群体、文化所影响。这时医学人文关怀的对象范围除了患者本身,还要考虑患者的周边关系,尽可能将患者的精神压力降低到最低,拨开令人难堪的疾病隐喻还原真实的疾病本身,医者医病从医病人上升到医病人的“社会生态场”[6]。第三个层面是国家政治领域的隐喻与关怀,隐喻在与主体的目标结合过程中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演变成现实活动的工具或武器,并带有主体的意志性,动员和说服才是目的。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隐喻被运用到政治哲学里,是为了以强化的效果来呼吁人们作出理性反应”[2]86,不是为了煽动暴力引发群体性狂热,强化的效果依托民众的情感共鸣和积极响应,要使这种强化有力且理性,就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理性把握和引导。这一层面的医学人文关怀的重点始终在于加大国家层面以人为本的生命保障和尊严维护,科学地揭露疾病背后的不合理隐喻,转化为合理隐喻引导人们作出理性的反应,在民族共情的基础上动员自身力量来治病,以个人精神彰显国家风貌。
2 疾病的隐喻与医学人文关怀的历史语境与演绎
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缘起于朝鲜战争中美国对中国发动的细菌战,并随着战争的结束逐渐走向生活化和制度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接轨中衍生出新的隐喻。爱国卫生运动是那个特定年代的“健康中国”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独创的改善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的工作方法,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健康中国”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在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弱化趋势,但应当引起关注,因为爱国卫生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和健康一样,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疾病”,而它本身就在反击这一敌人中周旋于医学、社会和政治等多个领域。
2.1 战时的疾病隐喻与人文关怀
在整个19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2]81,“东亚病夫”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西方世界共同塑造的一个“反角”形象,“病夫”一词最早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的,随着近代西方的入侵,华人的“不洁”赤裸裸地袒露在更多西方国家面前,鸦片战争后“一条长辫一杆烟枪”的中国人形象,在世界普遍殖民主义霸权话语体系下被不断强化,最终隐喻和塑造为世界性的“东亚病夫”,这一带有强烈鄙视意味的称呼又反映出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民众体质羸弱,中国国力整体衰败。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为朝鲜战争中美国细菌战的发动提供了话语前提和国际舆论借口,一方面,美国认为中国以及中国人民本身就是病态的,即使没有细菌战的外部入侵,也会有细菌疾病的内部衍生,很难将中国的日常疫情与美国细菌战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沦为东亚之病夫也被认为是中国人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沉溺于“不安全”的行为中——吸食鸦片、忽视卫生,这是对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惩罚[2]121。故此,新中国陷入了“东亚病夫”道德压迫和细菌战争威胁的双重困境。
美国著名医学社会学家和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指出:“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7]也就是说,医学在宏观上并不局限于医生和病人二者,当疾病被折射到社会甚至国家政治层面时,医学人文关怀的主客体也扩展到健康群体与患病群体的社会各界。细菌战不仅造成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恐慌,而且还让民众在“东亚病夫”的世界话语中承受着道德压迫。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一方面立足医学本身,投身于细菌病毒的真实报道和诊治中,消除了人们的陌生和恐惧;另一方面是对人的生存环境、健康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维护,医学人文关怀在各个层面展开。新中国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使疾病获得维持自身意志的喻义,从“东亚病夫”的不合理隐喻中解脱出来,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似乎特别具有抚慰作用,甚至是解放作用。正如杨念群所说:“在‘反细菌战’中,美国被当成了传播‘疾病’的发源地,‘东亚病夫’受辱的根源不在国内,而是外人强加的一个后果”[8],这种“颠倒的想象”就是中国将疾病不合理隐喻改造为合理隐喻的过程,也是两种隐喻之间的较量对比。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医学人文关怀解构“东亚病夫”的不合理隐喻,因此也就有了“一只苍蝇、一个美国兵;敌人能洒下,我们坚决打干净”[9]的民众认知。
2.2 和平时期的疾病隐喻与人文关怀
随着细菌战的结束,战时的卫生运动日渐式微,爱国卫生运动已不再着力于完成反美细菌战的斗争使命,开始发展为一项独立的群众卫生运动,因此,将军备状态的疾病防疫行为转变为日常公共卫生行动就迫在眉睫,爱国卫生运动就开始以建设新国家、新国民和新国风的普遍愿望走向生活化、制度化的新阶段。和平阶段开始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建设工作,所有“疾病”都被视为阻碍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敌人。
在传统的治病救人的医学过程中,医学人文关怀的主体通常是掌握了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的专业医学人,病人是接受治疗和关怀的被动客体,医生在很多时候就成了病人的唯一救命稻草。这一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实现了客体向主体的转变,开启了医学人文关怀的人民主体的新局面,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为了将爱国卫生运动经常化、普遍深入地开展下去,在卫生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基础上增加了一条,就是“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人民群众由被动的救治客体变为主动的医学主体,通过培训和实践增加群众的健康卫生知识和防病技巧,改善环境、消除疾病隐患,把“除害灭病”寓于“建设社会主义”之中,超越了传统人文关怀单一主体的局限性,扩大了积极效应。例如,在山东最为严重的黑热病,令很多医生为之头疼,但在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的努力下和病患之间的互相鼓励下,于1958年基本被消灭了,并且还进一步解决了抗药性黑热病的治疗难题。以前是医生们发动“bellum contra morbum”(对疾病的战争),现在是全社会发动这场战争[2]106;以前是医生对病人的人文关怀,现在是全社会的互相关怀。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爱国卫生运动”又与“创建文明城市”、“农村改水改厕”、“健康教育工作”、“食品安全”、“控烟工作”等一系列的现代化发展指标密切相连。爱国卫生运动治理环境、预防疾病等工作的根本其实在于全民健康,因此,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就成为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重点,也成为各级爱卫会开展工作的重要内容。它与医学的最终目标其实是一致的,因此,爱国卫生运动集中体现了医学、社会与国家层面的人文关怀,通过服务与关怀,提升整个民族迈入“全民健康的门槛”。
3 新时代疾病隐喻的衍生与医学人文关怀
“疾病”的隐喻在新时代告别了“弱者的武器”[10],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身体衍生的新疾病表征又隐喻着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新时期职业病就是其主要表现之一,目前我国职业人群约占总人口的2/3,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随着经济、技术的飞速变革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新的职业健康问题不断出现,极大地冲击着职业人群的身心健康,如加班、倒班等超时作业、高强度应激状态所致的职业紧张和压力性心身疾病;不当劳动行为和作业姿势等引起的疲劳、过劳及肌肉骨骼疾病等;除此之外经济社会发展中由环境问题引起的尘肺疾病、耳鼻喉口腔等疾病也日益增加。在现代社会转型变革过程中,劳动者承受的就业、住房、婚姻、子女、人际交往等种种巨大压力正慢慢地腐蚀着人的生命活力,身体出现的普遍不和谐的疾病状态,隐喻的其实是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因为病态的身体与病态的社会常互为映衬,共同呈现时代的情绪和社会的创伤[11],人们通过高度透支自己的健康实现的畸形发展,它是不全面也是不健康的发展。
与此同时,医学也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渐渐忽视了人文关怀。许多医院的经营模式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滋生了以药养医、小病大治等乱象,这些都猛烈冲击着“医乃仁术”的人本精神,飞速增长的技术和知识以及大量涌入医学的资本带来了新的利益和权力。医生也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变得神圣化,模糊了医学伦理与职业道德,导致生病成了有钱人的特权,极具权威性的医生甚至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人,这也是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在新时代重塑医学人文关怀?爱国卫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可行的实现路径,即在国家层面加大民生投入的基础上,充分激发社会公共领域的人民主体作用,推动与促进医务工作者的去利益化、复归医学本身对生命的敬畏和责任。
新时代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诉求中,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医学的利益追逐战阻碍了人们对健康的美好期待,“职业病”、“环境污染”以及“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冲突”等交织在一起,并相互渗透。这一时期人们的健康认知也逐渐从没有疾病转向全面健康,也就是国内外比较公认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是指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完美状态”,杜治政[12]认为这一定义将“健康”放入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广阔背景之中,指出健康不仅是医务工作者的目标,而且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因此国家实施的“健康中国”战略,强调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就是正视社会“大众疾病”隐喻的发展问题,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释放更多维的医学人文关怀。通过加大国家民生和社会治理力度,提升公共卫生中人民群体的主体地位,动员全体民众树立新发展理念,培育民众的健康意识和健康自觉。著名经济学家李玲[13]曾表示,爱国卫生运动有其自身特性,即健康作为它的最终产品,在追求健康过程中爱国卫生运动依托的是群众日常的农村和城市基层社区,同时,运动的实施依靠的是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达到了改善环境、强健体魄的效果,还促成了和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风气的形成,这对于实施新时代“健康中国”战略具有一定的意义。要形成全民健康的新概念,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打破因技术至上与利益崇拜所产生的职业冷漠,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下,有赖多维医学人文关怀的润滑、化解与调节[14],一方面需要国家与社会动员全民的共同努力来培植健康新道德,追求健康美好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社会与民众各层面开展综合治理、规范医学行为,强化医学伦理,建立医患双方互信互通,关爱生命。
4 结语
爱国卫生运动虽然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但一直延续至今,是我国所创造的独特的“健康中国”方式,虽然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但它却彰显着多维医学人文关怀,从政治、医学和社会等多个领域来进行探讨各种“疾病的隐喻”,求得群体和个体的共生、共建、共享,一方面个体生命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另一方面个体积极性的发挥也以最大可能来回馈这个公共空间。爱国卫生运动与“健康中国”一直相伴而行,它们有着共同的指向,在新时代下碰撞出灿烂的火花,通过多维层面的医学人文关怀,发挥人民主体的创造性与生命活力,以全民健康带动全面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