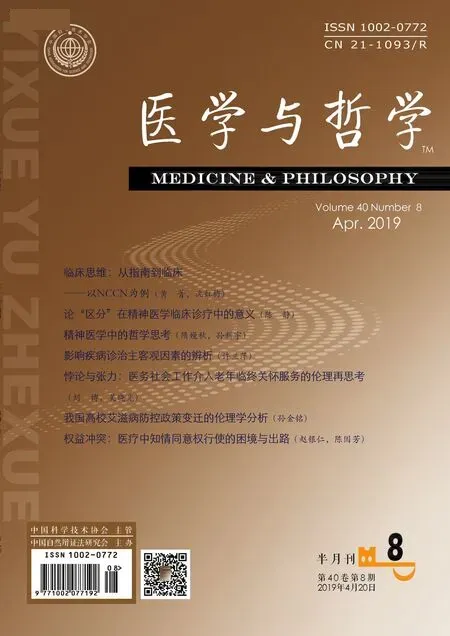AIDS与aids,患者主诉叙事与疾病见证叙事功用伦理的冲突*——评桑塔格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
张红艳 吴光军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乐意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1]5
美国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桑塔格(1933年~2004年)一生饱尝各种致命疾患的滋味(哮喘、乳腺癌、子宫癌、白血病),时不时被迫进入“疾病王国”呆上一阵子,身体和心灵备受摧残与折磨。希腊神话把艺术家的创造力归因于疾病和迷狂,认为艺术家是病人。“只有为艺术而受苦的人,才有可能获得与知识、真理、顿悟相当的艺术……痛苦乃是创造力中一个必不可少,甚至是不可取代的部分。”[2]这一观点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桑塔格的疾患经历及其非凡艺术成就。对桑塔格而言,疾病是一种生产力。《作为隐喻的疾病》《艾滋病及其隐喻》及《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这三部著作均源自于桑塔格对疾病、痛苦和身体的强烈感受,源自于对病患世界所做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精神思索。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986年首发于《纽约时报》,先后被《美国最佳短片小说》(1987年)和《美国最佳短片小说世纪精选》(1999年)收录,成为学界探讨桑塔格疾病意识的经典著作之一。这篇关于艾滋病的小说是在桑塔格得知一个亲密的朋友约翰·蔡金感染艾滋病之后创作的。她在接受记者肯尼·弗里斯采访时谈到,小说在两天内创作而成,灵感和素材是来自自己的患癌经历和一个朋友的患病经历,因为“极端的经历性质上是相似的”[3],她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
1 故事情节解读
小说的中心线索是:“他”患了艾滋病,从怀疑到确诊、治疗,他的病把身边的朋友、恋人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态度、举动关注病情发展,热心地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爱和援助,但最终结局依然令人怅惘。
1.1 AIDS与aids的奇妙联系
AIDS是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征)的首字母缩写,中文音译为艾滋病。 另一单词aid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的第一条释义是:help,帮助,援助;第二条释义是:thing or person that helps 有助之物或人。加了名词复数后缀“s”的aids与AIDS除了大小写及意义的区别外,在拼写和发音上完全一致,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这些朋友以及他们富有人情味的举动可以称之为环绕在AIDS患者身边的温情脉脉的aids,笔者拟借用AIDS与aids这两个同音同形但异意的英文词汇,为阐释桑塔格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提供一个新颖别致的视角。
1.2 AIDS令人恐惧, aids不离不弃
故事中,生病的主角呈缺席状态,姓名未知,声音隐匿。全篇由他的一些朋友的谈话(间接引语)组成。从这些友人的交谈中,读者得以了解到病人的一些基本信息:住在纽约曼哈顿的时尚地区,三十多岁,单身,工作体面,生活富裕。他还是一名时髦的双性恋者,身边有一群与他关系异常密切的男男女女。朋友圈共26人,他们名字从A排到Z。这一明显具有隐喻性质的命名方式也许象征了所有美国大众,面对AIDS,人人都可能受牵连,人人都有风险。
“震惊”是所有突闻自己或身边亲友患重病时的第一反应。因为长久以来,人们宁可相信“生重病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故事的中心人物——“他”,当然也无法相信“这事竟然发生在他身上,竟也发生在他身上”[4]272。他疑似患艾滋病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袭击了这群围绕在他身边的亲密战友们。朋友圈议论纷纷,一部分人不相信他得了“那种病”;一部分人认为不应放弃希望,期待“新疗法”;有人觉得自己没有危险,但也说不准;有人建议他尽快去看医生确诊。艾滋病的特殊传播方式和可怕后果让这群“旁观着他人之痛”的朋友们陷入到无限的恐慌之中。因为,今日的“他”所遭遇的很可能就是将来自己要承担的命运的预演[5]。恐惧在谈话中此起彼伏,笼罩了所有人的生活。但耐人寻味的是,所有人都对AIDS这一词心照不宣地予以规避,而以“这种病”、“这类病人”、“此病”、“这事儿”等来替代,小说自始至终也没有出现AIDS这个字眼,仿佛这个词被诅咒、邪恶可怕。这其实是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在美国首次被确诊并报道以来,大部分美国公众面对AIDS时的真实心理写照。桑塔格对此也直言不讳:“染上艾滋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咎由自取,而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指责,尤其是当艾滋病不仅被认为是性放纵带来的一种疾病,而且是性倒错带来的一种疾病时。”[1]102显然艾滋病成为了一种承受严厉的道德评判而被社会高度道德化的疾病。
令人欣慰的是,惊恐之下,小说中“他”的男女朋友们并未因此而抛弃他、歧视他,反而由此再次凝聚在一起,彼此关系甚至比以前更加亲密,如同筑建了一个新的命运共同体。因为他们不是普通的朋友,他们是相信性滥交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关系早已因这曾时髦的举止而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真诚还是私心,互帮互助、共渡难关是这个共同体的主要旋律。“弗兰克说,他喜欢有朋友在他身边,而且我们也是在互相帮助;因为他的病就像胶水把我们都粘在了一起,扎维尔沉思地说,不论过去有什么嫉妒和抱怨使我们之间变得彼此戒备或暴躁偏执,当这种事发生了你就明白什么事是真正重要的了。”[4]273尽管恐惧仍挥之不去,“他的一些朋友在短暂恐慌后作了积极的心理调整,很快以勇敢、积极的态度正视、接纳并帮助主人公安度由疾病而致的心理创伤”[6]。整篇小说以AIDS为背景描写了大量形形色色的aids人物及其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争相探视,勇敢接触。 “为了在探视时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一个特别愉快的反应,我们彼此竞争,每个人都竭力讨得他的欢心,想成为最被需要的,真正的最亲密最贴心的……我们就是他所拥有的家庭。”[4]278通常AIDS患者是极易被疏远、被孤立的异类,但在这里,“没有任何人躲避他,没有人害怕和他拥抱,或者和他轻轻地在嘴上接吻”[4]276。
其二,热心介绍治疗方案。出院回家休养期间,朋友们热心收集各种偏方奇法,贝西带来了精通长寿保健饮食法的日本专家,维克多推荐了一名视觉治疗专家,斯蒂芬一直跟踪美、英、法等国出版的医学杂志,还和一位巴黎的主治医师有交往。尽管都不奏效,但朋友对他的真诚关爱可见一斑。
其三,医院氛围轻松平和。医院为病人营造了一个没有歧视的生存环境,“大家不怕去看他了……医院现在甚至也不再隔离他们了,他的病房上也没有任何字眼警告来访者有传染的可能”[4]268,主治医生和蔼可亲,对他的病情表示乐观。
其四,封锁坏消息。出院回家后,“传来了两个虽然认识但相当疏远的人的坏消息,一个在休斯敦,一个在巴黎。消息被昆廷截住了,理由是这只能使他抑郁沮丧”[4]280。经常来访、一向健康的麦克斯突然生病后, “绝对不能告诉他麦克斯的事儿”在聊天中被反复强调。朋友们小心呵护着他,不想让他遭受任何额外的打击。
AIDS患者与身边的aids群体命运休戚与共,疾病无情人有情,爱、尊重、同情、陪伴、担当、不离不弃等这些美好的品质在疾病来袭时尤其难能可贵。尽管他们因“性”而彼此结识,但在灾难面前,这群人的举动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放浪形骸地享受所谓的自由后,人们不得不咽下这种不负责任的自由的苦果,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战胜了内心的恐惧,走出了自由的迷局,勇敢地承担起责任,以温情化解疾病带来的各种心理危机,迈向了真正的成熟。”[7]
1.3 aids的温情终究敌不过AIDS的无情
温情脉脉的aids终究阻挡不了伴随AIDS而来的死神的脚步,面对强大的摧毁一切的AIDS, aids终究是脆弱的、无能为力的。AIDS与aids, 相依又相克的关系在小说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主人公生病期间,噩耗由远及近接连传来,其中两个是遥远的模糊的异域他者,一个是亲近的熟悉的身边知己,且病情来势汹汹,令人猝不及防。纽约、休斯敦、巴黎、伦敦,“性之链”传递得越长,AIDS辐射的范围就越广。“他”病了——他们病了——社会病了,谁能保证小型的区域性灾难将不会演变成大型的国际性灾难?
听闻“他”第二次住院,不少人当即哭了,为了他,也为了自己。昆廷让大家安排好时间有序探访,并且表示不能再阻止他母亲坐飞机过来。朋友们开始谈论死亡:他们讨论天主教圣徒塞巴斯蒂安之死,凯蒂说“死亡令人着迷”,希尔达说“我们正在学习死亡”,爱琳说“我可没准备好学习死亡”,经过一间间敞开着门的病房时,坦娅对刘易斯说“有件事我真不忍心去想,就是人死的时候电视机还在播放节目”[4]287。死亡不再像以前一样,是一个忌讳的话题。人们开始正视他的病情发展,也隐隐预感自己的未来。一个冬日的上午,坦娅第一个去看他,“发现他的笔迹在一点点发生变化:近期写的字变得像蜘蛛,很难辨认,有几行字写得跑了行,或者斜到上面去了”[4]287。小说以“他仍然活着,斯蒂芬说”结束。作者对患者前景表示谨慎乐观,但字里行间所传达那种担忧、紧张与无助却使人更加惴惴不安。
“疾病是一个骇人但又迷人的主题,它能对如何看待来自死亡的威胁,给人一些启迪……死亡到来的那一庄严时刻会使人进行自我反省,开始一次自我发现的心灵历程。”[2]主人公“他”住院治疗期间,生平第一次开始写日记,记录下得知自己患病后的心理反应过程,回顾自己的过往,写下“对过去生活,对他那些可以原谅的浅薄的常有的充满悔恨的评价”[4]287。疾病在摧残躯体的同时,也经常给患者带来理智的感悟和精神的启迪,这种苦难孕育的智慧通常具有普世价值和警示意义。
2 患者主诉叙事与疾病见证叙事功用伦理的冲突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一部呈现“艾滋病”患者声音被遮蔽、患者身边朋友多声部交互的疾病见证叙事作品。与科学逻辑求真和生物医学极简索引原则不同的是,从叙事医学和美学张力的角度看,作为叙事的疾病追求疾病故事生成的多叙事进程、疾病意义阐释的多维度丰富性以及疾病带来的生命故事重构[8]。患者叙事和患者主诉故事是医生临床判断、医疗叙事能力检视和施行叙事治疗的基础和依据之一,是医生、患者和患者周围相关者因疾病故事调整对自我、身体和世界认知的重要材料。书中展示了叙事医学故事中的一种冲突类型——患者主诉叙事与疾病见证叙事功用伦理的冲突。从叙事层面看,虽然患者的朋友们不停地给他提供各种情感、认知、心理和行为上的aids,但患者主诉故事却被朋友们的疾病见证叙事彻底压制,疾病事实和意义变得扑朔迷离、模糊不清(朋友们的叙事暗示患者私生活混乱是其致病的根源,但患者认同这一观点吗?患者主诉的疾病临床诊断在小说中是隐匿的,至少是不明确的。主人公始终处于失语状态是否暗示了朋友们不完全了解他的病痛体验,个体痛苦无法与他人言说?朋友们是否只是借助于各种形式的aids来掩饰群体性对AIDS的无知和恐惧?形形色色的adis真的有助于AIDS的治疗吗?)。 疾病见证叙事具有生成故事、补充意义、使“事实”展现出全面性的功用伦理,但《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中的疾病见证叙事却压制患者叙事使得“疾病事实”摇曳不定、缺乏“权威性”。
3 结语
《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极度压制患者的疾病叙事和主诉故事虽然可以带来美学上的张力和阅读快感,但从叙事医学的伦理情怀和目标上看,极度压制患者故事是违反叙事医学的伦理和道德原则的,因为在医(护)者-患者-社会这三个维度的话语角力过程中,患者的疾病故事往往出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呈现虚弱的、被隐藏的、被遮蔽的、被压制的叙事状态,“疾病事实”可能永远不存在或者永远无法接近本真状态。如果把患者朋友的叙事当作循证医学的诊疗转述、后护理叙事或者平行病历,医护人员型读者可以使关于患者的生物医学检验文本和疾病病理意义阐释更加靠近封闭和趋向自足,但从叙事医学的终极人文关怀和疾病意义创造生成的角度看,患者疾病意义表征能力、患者疾病体验的叙事化能力培育或许更应该是医护从业人员、审美批评和读者阐释的关注方向[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