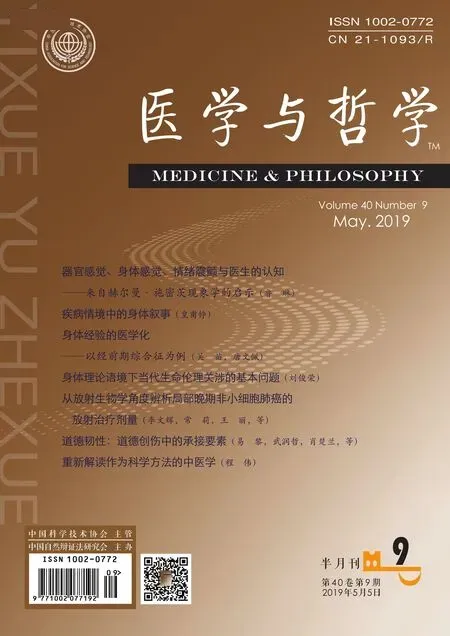重新解读作为科学方法的中医学
程 伟
中医学的临床疗效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其独特的健康观念、医学理念、治疗技术、养生方法所获得的认同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论是在常见病、多发病治疗,还是在诸多疑难病甚至新发疾病的应对方面,中医药学的独特作用不仅得到了直接受益者的青睐,更得到学术界以至更大范围的认同,其国际影响也正从民间到学界再到官方日益扩大。然而,对于作为方法的中医学的独特认知方式的解读还远未深入。对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独特性的医学理念、疾病观念、概念系统与直接具体的临床疗效之间关系的解析,仍在相当程度上停留于、满足于以传统中医自身的言说方式反复陈说而不能深入分析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像青蒿素等具有特定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重大成就与系统性的中医药学的深层关联的探索仍然强调的是实践层面的意义。系统生物学等一系列前沿科学方法的引进、借鉴对于探求中医药学的“作用机理”之类的问题还只是开启了令人有几分乐观的研究进路,在临床成功经验与作用机制之间及其巨大的灰色地带的开垦有待长期执着的不懈努力。
1 中医独特的认知方式潜藏着有待深入解析的奥秘
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把中西医学的差异说成是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差异是一种有一定普遍性的表述。但是,这种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学界似乎并没有一条共同的思想基线。在长期存在并持续至今的关于中医药研究、评价中的种种论争,都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当我们说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两种体系的地位可以对等吗?二者之间的沟通、对话是可能的吗?其实,早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各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各有自己的学术框架,据此都可以对自然、宇宙和人体进行系统的研究。中国的主要方法,当然也不是唯一的方法,是寻求事物之间的共性,寻找同类关系,寻找感应关系[1]。也有人说,中国思想的出发点是“事”。“事”不是实体,而是实体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思想主旨上,西方哲学是关于必然性的思想,而中国哲学是关于可能性的思想[2]。这种特征在中医药学的理论实践中得到了深刻体现。中医药学在实践中已经不容置疑地成功彰显着中医学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也集中体现着中国思想的独特传统价值。
中医学当然有自己的鲜明文化特色,有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这些观念的现实价值,在中医临床实践的世界之中才能真正体现。传统中医诊疗所达至的境界,有时看似简单,却并非仅仅靠一般经验的重复、累积、再现就能透彻说明,中医独特的认知方式潜藏着有待深入解析的奥秘。中医的眼光看到了什么?有限的表观信息何以能传达出科学手段并未关注到的“世界”?事实上,真正对于中医的有深度的理解只能基于对中医药临床成就的深刻认识。因为,基于中医千百年实践的系统化经验的理论说明具有相当的有效性,并且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性。例如,中医临床中既有相对稳定、效不更方的典型证候,更有“但见一证便是”与随证加减。而这里的随证加减并不是简单地对症用药,因为每一个看似单纯的症状实际上都是在一个解释系统中被准确定位的,它基于另外一种症状鉴别诊断系统。中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固然复杂,但其独特认知方式的现实解释功能不容忽视。在这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高度的统一性。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面对同一个风湿病病人或高血压病人,一位西医专家和中医专家关注病人的角度会有相当大的差异,并会导向不同的治疗策略。
在迫不及待地不断追求新技术的取向和刻意捍卫正宗的复古倾向之外,作为方法的中医学有待于在新观念指引下进行深入开掘和重新阐发,这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中医药学超出临床实践意义的重要科学贡献。在当今的医学语境下,聚焦中医临床实践,对中医对疾病的认知方式做更深入的开掘性解读不仅有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还可以为当今医学发展带来更深刻的启示并做出科学性的贡献。
2 超越传统的本质论疾病观与线性还原的因果论
2.1 “刷新”我们的疾病观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把疾病看成对健康的偏离。或者进一步说,疾病是机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受病因损害作用后,因自稳调节紊乱而发生的异常生命活动过程,引发一系列代谢、功能、结构的变化,表现为症状、体征和行为的异常。传统的疾病观,总是试图确定疾病的某种本质,对导致疾病的原因进行无穷追问。具有很大相对性的疾病分类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成了必须遵循的铁律。时下学者比较中西医学时,也每每以所谓“证”状态与“病”本质作对比,其实也是受到这种束缚的表现。关于疾病的分类与本质的本体论的强制性导致了现代医学研究在应对生命科学的复杂性与医学的不确定性的单一向度。走进中医的世界,眼前展现的是迥然有别的医学天地。用完全不同的概念、术语表达的其实是疾病世界的不同维度。但要把这套系统言说直接“翻译”成现代医学术语在当下阶段几乎不可能。而有时超出预期、时常被视为神奇的中医临床疗效,在其自身的境界里其实顺理成章。这样的境界值得我们以谦抑的态度审慎对待,虚心学习。
在此,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沈自尹院士早在二十多年前的见解。他曾说道,过去一直认为感染性炎症是细菌或病毒等外邪所引起,只要消除细菌或病毒,炎症自然会消退。但研究表明,清热解毒药不单纯在于抗菌、抗病毒,而是对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进行精密协调,由此抑制炎症介质的合成和释放,从而改善了炎症与组织损害。因此,需要转变对清热解毒药作用环节的认识,不能仅认为清热解毒药是祛邪以安正,清热解毒药杀菌灭毒之力实际不如其调节细胞因子、炎症介质之功效,其中实含有扶正(扶正不一定是指补法与滋补药,免疫调节就必须通过人体的正气)以祛邪之深意。也就是说,清热解毒中药在严重感染的状态下,不仅能“祛邪”,还能“扶正”。这些研究成果提出了对待外来因素所致疾患还须注意从保护与提高非特异的免疫功能着眼。特异性的杀菌作用固然是好,但还有非特异的免疫功能,那却是人体生来就有而且是最基本的防御杀敌能力[3]。这样,“感染”、“抗感染”的内涵就都有了新变化。对疾病原因的寻求也超越了简单的线性关系的思路。
沈院士[4]还指出,针刺也能提高机体非特异性的抗病能力,同样说明对待感染性疾病不能全赖高度特异性的抗菌药物。这对西医来说将是概念上的转变,这是中医药研究不容低估的贡献。
2.2 所谓“关系本体”有其科学内涵
证是什么?迄今为止,对这一中医学最具典型性的概念的共识度还有很高的相对性甚至表面性,相关认识差异的存在并不只取决于所谓表征指标的客观性问题。一般说来,证作为同时并存的一组症状的组合有其空间维度;其形成的过程及影响因素又有时间维度的考量,证候状态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也有相当的恒动性;其每一构成要素都处于复杂网络的某个节点,时时会出现主次关系的变化。线性因果关系可以无穷无尽地追问,相关联动的结构关系断面剖析也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说,不同于实体本体的所谓“关系本体”就不仅是一个哲学概念,而具有其科学内涵。
关于急腹症的中西医结合研究等也同样曾经开启了抗感染的新境界,但其意义也还没有得到彻底、充分的解读。通里攻下、急下存阴等治法机理的研究,同样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理解。某些证本质的探索,还有其他诸多治法的研究也曾触及到过去几乎不被人知的看似不相干的疾病之间的共同“本质”,其足以带来某种颠覆性观念转变的意义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其实,复杂性研究之不重因果而重相关的取向有其深刻内涵。表面看来比较直观的症状组合所代表的内在关联要求更具系统性的解读方法。
近年来,学界普遍认为系统生物学将可能解读中医药复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系统生物学使西医从整体的方面去认识人体及疾病成为可能,认为系统生物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桥梁[5]。最近,王喜军教授团队的一项关于中药六味地黄丸的研究表明,六味地黄丸通过调控苯丙氨酸、酪氨酸、亮氨酸、硫酸高香草酸、溶血性磷脂酰胆碱等30个血液代谢标记物及12个相关的靶标代谢通路,显著影响大鼠生长发育过程中血液代谢轮廓,并圈定了硫酸高香草酸、苯丙氨酸、甘氨胆酸等8个代谢标记物为六味地黄丸影响大鼠生长发育的核心代谢标记物。证明了六味地黄丸能够显著调控大鼠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血液代谢网络,从而影响大鼠的生长发育[6]。这类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值得持久深入地探究下去,世界可以因你看它的方式而不同。
2.3 寻求“以变而在”的方法论
在另一个方向上,与清热解毒研究可以成为对照的对虚证本质和补益药的研究发现虚证普遍具有细胞免疫功能低下的情况,尽管虚证的表现各不相同。而很多种补益药,无论健脾、补肾、滋阴、温阳,只要用药对证(指补益药针对虚证状态),都可增强细胞免疫,表现为上向调节,这几乎已成为补虚药的共性。这对中、西医两方面都具有意味深长的启迪[7]。异病同治、同病异治,辨病辨证相结合等实际具有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
哲学家赵汀阳有一段重要论述:“中国的连续性从无断裂,其关键之存在论理由是,中国是一个以‘变在’(becoming)为方法论的文明,而不是一个固守其‘存在’(being)本质的文明。空间性的中国之所以能够长存而不被外力所解构,实得益于时间性的中国方法论,即自古以变而在的生长方式,所以万变反而不离其宗。中国存在之本在于其变在之方法论,或可称为作为方法论之中国。”笔者之所以不避文抄公之嫌,大段引用我们并不熟悉的这些表述,实际只是想借用“以变而在”这一颇为精到的概括,虽然不能简单地以此概括中医学的方法特征,但中医学变动不居的“恒动观”确实与之有异曲同工之感。赵汀阳先生还讲到,人们已经知道了各种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甚至比事物本身还重要,于是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样的路径进入由事物(问题)之间的相关性所构成的思想空间才最能够理解这个思想空间。中国顽强之长存能力就在于以变而在的方法论,这意味着,中国精神世界的元规则是作为方法的中国,而不是作为教义的中国[2]。这同样提醒我们要极端重视作为方法的中医学的科学价值。正是中医学的认识方式给我们呈现了不同的认识取向,足以刺激我们尝试寻求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认识、分类方式。中医学整体恒动的疾病观、变与不变动态统一的辨证方法正是近于以变而在的方法论的体现,实际上昭示着一个不同凡响的别样世界。
3 追问的逻辑与逻辑的追问
3.1 中西医之差异是中西文化差异的镜子
中西文化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双方都愿意承认这几乎就是两个世界。二者之间差异的突出表现常被定位在思维方式不同。所幸,对两种文化之间对话的必要性或可能性的共识越来越高。不过,正如有识者指出的,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和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和力度,就好像要按照书架的结构去重组椅子一样会破坏本来的性能。尤其是,中国关心的语言局限性是,特定的语义永远网不住无常的事物,因此永远不能拘泥,只有灵活的心和亲身的体会才能跟上自然的节奏[8]。如前所述,对健康疾病之变动不居的认识方法自有其长处。
3.2 中医的“概念”是更大的思考单元
有必要强调一点,形式逻辑并不发达的中国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的概念思维。中医的“概念”是更大的思考单元。中医的“概念化”方式与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有内在的相关性,中医学显在的理论系统并未实现严格的内部自洽。例如,肾、阳、肾阳、肾阳虚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层级严格的线性关系。但我们可以着力于对传统言说方式表达的相关性经验间的潜在关联的内在逻辑做深入解读,而这终将导致系统化成功经验下潜在规律的逐步发现。概念体系其实很像人际等级体系,一些概念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重要概念被翻译为没有分量的概念,它本来所意味着的思想问题也就好像变得微不足道。不过,面对这样的传统体系我们的逻辑追问只能适可而止。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强求以一种一统天下归于气般的一以贯之的解题方式来研究中医药学,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经验。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充分尊重传统观念与实践经验的传承创新和在以上两者之间不断往复的深度对话与诠释性解析,才是通向未来的光明之路。
3.3 走向创新通用概念
时下许多论者谈论中医问题每每把哲学观念当成具体知识,急于以之说明个别问题,而其实际陈述更多体现为理念却缺乏明晰性与可操作性。捍卫中医的言说者众,隔靴搔痒亦复不少,而维系中医内在生命的临床行动者们每每语焉不详甚至失语。以自视超迈的理念能高视却难以阔步,要走出行动者失语的悖论需要走出浮泛的哲学辩护。我们需要基于中医的认识与实践寻求创造新型的通用概念。
赵汀阳[8]也曾说道,东方的智慧似乎包含着另一种可能解决问题的想象力。中国哲学的独特视野还发现了一些在西方哲学里没有被重视却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一旦能够使某些(数量不用很多)中国概念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体系的一部分,即成为人类在思考任何事情所使用的普遍(universal and general)概念,或者说,使中国语言中的某些关键词成为普遍通用的关键词,那么这将意味着中国思想能够成为通用的思想工具和根据的一部分。从客观的角度看,中国概念进入人类通用概念体系将扩大人类思维的能力。在如何对待中医学的问题上,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期待。而这,正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代表。
3.4 让“科学”向“传统”致敬,让“传统”向“科学”致谢
中药有效性是中医药治疗优势的直接体现,而有效性的科学阐释是连接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科学的关键渠道,中药有效性评价也是发现药效物质基础的前提[9]。用一种新的生物学语言,科学地表达中药的有效性,让现代生命科学领域认识和接受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的科学价值是当代中医药研究的重要使命。中医方证代谢组学(Chinmedomics)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研究中药方剂有效性及其药效物质基础的整合策略,是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方法学意义上的创新。它基于中药复方给药形式的特殊性及方证对应疗效的专属性特点,以代谢组学技术建立方剂有效性评价体系,揭示证候生物学本质;以证候生物标记物发现为切入点,以方剂为研究对象,为中药有效性评价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揭示临床常见中医证候的生物标记物及其相关方剂的有效性,推动了证候的精准诊断及临床治疗经验的挖掘,为提升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的科学价值的认识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解释。这种方法学上的创新开辟了中医药研究的新境界,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同,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
当我们为这样的工具性的创新感到欣喜并充满期待的时候,不应忘记新方法所揭示的复杂世界还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认知方式的多样性问题。曾经有很多人认为,真理只有一个,通向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而忘记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当古老的传统医学启发引导我们走进了一个陌生甚至有几分神奇的世界,我们应当向这种独特的传统表示敬意。而正因为有了借助新工具、新方法的不懈探索与创新,才使得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渐放异彩。日渐自信的传统医学应当以更开放的态度拥抱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