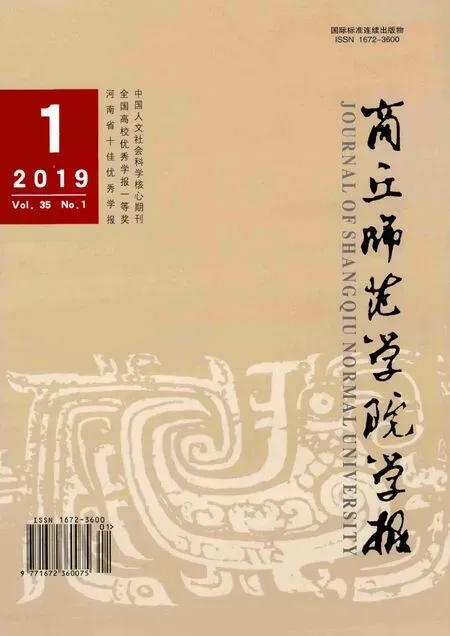魏收散文创作论析
徐 中 原
(云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关于魏收散文,虽有学人对其关注,但多言其史传散文《魏书》,如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曹道衡的《南北朝文学史》、宋冰的《北朝散文研究》[1],极少触及其他,如钱钟书只有数语论及魏氏《为侯景叛移梁朝文》;再者,虽有硕士论文讨论魏收若干散文篇目,但深广度不够,且有的观点值得商榷,如有人认为魏收散文总体风貌以质朴为主,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鉴于此,笔者有必要对魏收散文作进一步讨论。笔者秉持文学本位研究的理念,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和考证法对魏收散文进行整体考察,以期对其散文研究有所补益以及对学人全面认识其散文有所助益。
魏收是北齐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其散文创作主要包括赋作、史传散文以及诏文、册文、封禅、表启、奏议、移文、书信、家训、碑志、祭文等应用文,内容丰富多彩,文风华美。其才气和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赋作、碑志和史传散文中。其赋作散佚不存(只存两句佚文),但通过钩沉史料,仍可窥其概貌:其内容涉及狩猎、宫苑、爱情、言志等,极富藻饰之美是其突出的艺术特点。关于其碑志创作,根据庾信所评,富逸华美是其主要艺术特点。今存《枕中篇》《上魏书十志启》《为侯景叛移梁朝文》等应用文是其骈体文代表作。《魏书》是一部史传散文,代表其最高文学成就。其文学价值主要表现为:叙事简洁生动,趣味性强;刻画人物手法多样,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语言晓畅自然,富有文采。
一、今存魏收散文篇目
《北齐书》载,魏收《集》70卷。《隋书·经籍志》载,魏收《后魏书》即《魏书》130卷,《集》68卷。但只有少量篇目流传至今,除《魏书》外,据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载,仅存文15篇;据严可均《全北齐文》载,仅存文14篇,另存目6篇。张氏所录《为齐即位告天文》与《为东魏袭梁文》二篇未见严氏收录,而严氏所辑《为孝静帝元神和等诏》未见张氏收录。《为东魏袭梁文》是不是魏收所作呢?《文苑英华》卷六四五、《通鉴》卷一百六十作杜弼撰,而《艺文类聚》卷五八作魏收撰。张溥认为,此文作者为杜弼,但态度暧昧,曰:“此作(《为东魏袭梁文》)是杜弼所制,据《艺文》称魏收所作,姑存之。”[2]严可均也持暧昧之态度,他说:“岂此檄魏收润色之,曾编入魏集邪?疑误也。”[3]64二者均未对作者归属问题进行考辨。钱钟书的态度十分明朗,他在考辨《魏书·岛夷萧衍传》所载《檄梁文》与《全后魏文》卷五四所载《檄梁文》的基础上,认为此文应为杜弼所作,并指出其明显不足:“(杜弼《檄梁文》)以斥‘侯景竖子’为主;然后侈陈军威……再斥侯景之‘周章向背’;方及‘彼梁主’之过恶,寥寥数语,与其否得失政,阔略空洞;复以侈陈军威终焉。章法碎乱,主客颠倒,斥侯景与耀兵威二意,皆分割两截,断而复续,非盾鼻羽书之合作也。”[4] 1509-1510换言之,此文写作水平拙劣,与魏收才气相差甚远,只能为杜弼所作。综合张氏与严氏所辑,今存魏收散文15篇,另存目6篇。
又据彭盛《魏收集校注》统计,今存魏收作品25篇[5]26-27,其中包括上述张氏与严氏所辑14篇(漏掉《为齐即位告天文》1篇),其余10篇目由彭氏从《文馆词林》辑得;佚文残篇3篇[5]47,彭氏分别从《文镜秘府》与《春秋正义》中辑得,其中包括上述存目中的1篇。
上述三家所辑魏收散文未全,兹补遗《封禅书》1篇,今仅存其目。《北齐书》魏收本传载:“节闵帝立,妙简近侍,诏试收为《封禅书》,收下笔便就,不立稿草,文将千言,所改无几。”[6] 483此条材料又见于《北史》本传。
综上,除《魏书》外,今存魏收散文26篇,残文3篇,另有存目6篇。
二、赋作
魏收完整的赋作今已不存,但钩沉史籍,仍可窥其概貌。魏收常以赋自矝:“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注]校勘记曰:“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御览》卷五八七引《三国典略》作“唯以章表自许,此同耳戏”……疑《御览》是,这里衍“外更”二字。载《北齐书》第498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按,魏收自夸其是善作赋的大才士,而轻视只会作“章表碑志”之文而缺乏作赋才能的温子昇、邢邵,故说他们除“章表碑志”以外,其他作品均如同儿戏一般,无可取之处。文意畅通、合理,因此《北齐书》是,《御览》误,所校亦误。[6]492可读出三点信息:一是魏收长于作赋,以赋体为尚。二是嘲笑邢邵赋作只有一两首,可推知当时其赋作数量一定不少。但很可惜,今只存其《聘游赋》残文“珍是淫器,无射高县”两句,其余文字均佚而不传。三是在魏收看来,温、邢可引以自许的只有“章表碑志”之作,其他创作包括赋作在内均无可称道之处。
据《北齐书》载,其赋作有《南狩赋》《聘游赋》《皇居新殿台赋》《怀离赋》《庭竹赋》等。讲究藻饰之美是其赋作的主要艺术特色,如《南狩赋》“富言淫丽”[6]484、《聘游赋》“辞甚美盛”[6]485、《皇居新殿台赋》“文甚壮丽”[6]489。魏收雅自期许作赋大才士,应指其具有过人的藻饰才华而言的。《南狩赋》作于532年,为讽谏孝武帝狩猎而作,后因此赋受到孝武帝的“褒美”:“孝武尝大发士卒,狩于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时天寒,朝野嗟怨。帝与从官及诸妃主,奇伎异饰,多非礼度。收欲言则惧,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赋以讽焉,时年二十七,虽富言淫丽,而终归雅正。帝手诏报焉,甚见褒美。”[6]484《皇居新殿台赋》属于奉命之作,为贺文宣帝建新殿台竣工而作。当时奉命作此同题赋者,以魏收为最优,“邢卲已下咸不逮焉”[6]490。由此来看,可得出两点结论:一是魏收自称善于作赋,确属事实;二是魏收是北齐最优秀的赋家。《庭竹赋》和《怀离赋》是两篇抒情赋。前者托物言志,感慨为官之不易,表达了其坚守如庭竹般正直高洁品格的为人、为官的态度。《北齐书》评其为官曰:“见当途贵游,每以颜色相悦。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6]495此条材料印证了《庭竹赋》所表达的主旨。史书载,魏收“轻薄徒儿”[6]334“昔在洛京,轻薄尤甚”[6]486,恃才“轻薄”恐怕是其早年的主要性格,但并非一直如此,由《庭竹赋》来看,其为人也有正直沉稳的一面。后者追忆其病重之时所遣散的二夫人,表达思念之情。《北齐书》载:“(魏收)病甚,恐身后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忆,作《怀离赋》以申意。”[6]490《怀离赋》属爱情题材,在北朝极为少见,值得关注。
三、应用文
魏收创作的应用文有诏文、册文、章表、奏启、奏议、移文、书信、家训、碑志、祭文等。其中,今存《枕中篇》《上魏书十志启》《为侯景叛移梁朝文》等是其骈体文代表作。
碑志也是较能驰骋魏收才气的文体。庾信很是称赏其碑志创作,据《酉阳杂俎》载,庾信曰:“近得魏收数卷碑,制作富逸,特是高才也。”[7] 112可见魏收当时的碑志数量不少,富逸华美是其主要艺术特点。
《枕中篇》是一篇家训文。魏收任齐州刺史时(566年)为戒厉子侄而作。内容是作者告诫劝勉其子侄如何立身处世的,有劝有戒,同时也揭露了世道人心的阴暗险恶及其畏祸心理。这些家训思想主要出自《老子》和《论语》,也有他自己的人生感悟,基本是前人关于修身、处事的语录集,这对明代洪应明的《菜根谭》的编纂形式应该有直接的影响。魏氏的这些家训都是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而发的,对今人仍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从艺术上来看,此文语言典丽,行文骈俪,对偶句式多样,对仗严整,是一篇地道的骈体文;文章以说理为主,但又有一定的抒情性,如抒情之句有“追而为之,喟然长叹”“可不畏欤!可不戒欤”“俾诸来者,传之坐右”,抒情与说理紧密结合,达到了情理交融的艺术境界;讲究押韵,音韵和谐,读之朗朗上口。此文不足之处,在于条理不够清晰、合理。
魏收还创作了一些诏文、表启、檄文等军国公文,如《为孝静帝下诏禅位》《上魏书十志启》《为侯景叛移梁朝文》等也都是较出色的骈文,用典平易自然,语言典丽流畅,对仗工稳,行文整饬。《上魏书十志启》《为侯景叛移梁朝文》两篇被彭兆荪选入《南北朝文钞》,“以为学骈文者,制轮之寸辖,运关之尺枢,廪廪乎其操约而旨严也”[8]序,被视为南北朝骈文中的典范之作。《为侯景叛移梁朝文》一文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情感沛然,气势磅礴。文章多用四言句,音节短促,给人强烈的咄咄逼人之感,又兼以少量六、七言骈句进一步加强感情力量,形成强大不可阻挡的气势。正如张溥所评:“侯景寇叛,伯起草檄,气雄万夫。”[9]286钱钟书也给予高评:“首斥梁武轻险昏暴,尔见缕痛切;次痛侯景佥壬反侧,梁武老悖‘蔑信义而纳判逋’;末言吊民伐罪,师动以义,有攻必克。谋篇有脊有伦,文曰‘檄梁’,庶几称题得题。”[4]1509
《祭荆州刺史阴道方文》是一篇祭文,藻饰丰富,文风华美,情感真挚。文中回忆作者与阴君作为同僚的交游过往占了较大的篇幅,往事历历,而人已逝去,使文章蒙上了浓重的哀伤色彩,尤其是“昔犹肢体”至“天地何长”六句,今昔对比,天人对比,句句催人泪下。
《北齐书》评魏收曰“天才艳发”[6]478“以文华显”[6]483。综上对其赋作与应用文的考察,此评甚为恰切。
四、历史散文《魏书》
《魏书》是一部纪传体散文,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兴亡史。由于魏收借修史来酬恩报怨,书成后曾遭百余人投诉,一度被称为“秽史”。后又经魏收奉命修改,始成流传至今的《魏书》。《魏书》十志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是其新创的志目。
《魏书·文苑传序》集中反映了魏收的文学思想:
自昔圣达之作,贤哲之书,莫不统理成章,蕴气标致,其流广变,诸非一贯,文质推移,与时俱化。淳于出齐,有雕龙之目;灵均逐楚,著嘉祸之章。汉之西京,马扬为首称;东都之下,班张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陆机则晋朝之秀,虽同时并列,分途争远。永嘉之后,天下分崩,夷狄交驰,文章殄减。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赵,网罗俊乂。逮高祖驭天,锐情文学,盖以颉颃汉彻,掩踔曹丕,气韵高艳,才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肃宗历位,文雅大盛,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10] 1869
魏收对文学的看法有二:第一,“文质推移,与时俱化”,即指出了文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演进规律。这是对汉《毛诗序》“变风变雅”说以及刘勰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说的继承。第二,概论了战国至北魏的文学简史,其中对北魏文学论述得最详,将其分成三个时期:昭成与太祖时期、高祖时期、肃宗时期。据现有资料可知,魏收是最早研究北魏文学的学者,紧随其后的是唐人李延寿,其在《北史》中继承了魏收的观点。
《魏书》作为一部史传散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代表了魏收散文的最高成就。
首先,《魏书》叙事简洁生动,趣味性强。钱钟书指出:“《魏书》叙事佳处,不减沈约《宋书》;北方‘笔’语,当为大宗。”[4]1509曹道衡指出:“魏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表现在《魏书》的写作中……其叙事技巧多有可取。……(书中所记事迹),尽管很复杂,却写得层次井然,有声有色。”[11] 386两位前贤都得出了《魏书》善于叙事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笔者认为,《魏书》的叙事还具有生动有趣、富有戏曲性特色。如文中叙述高祖“外名南伐,其实迁也”片断:
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曰:“长驱之谋,庙算已定,今大将军进,公等更欲何云?”冲进曰:“……然自离都淫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丧反旆,于义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以水雨为难,然天时颇亦可知。……已至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下欲之。……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言!”策马将出。于是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高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王公等以为何如?……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桢进曰:“……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10]1182-1183
本段故事的发展线索有两条:一条是高祖欲擒故纵,假意强硬南伐,实欲迁都洛阳;一条是众臣真心不愿南伐而屡谏停驾。高祖决心迁都洛阳,但怕众人恋旧,于是就假装执意南伐。为了不漏痕迹地达到迁都的目的,他利用“霖雨不霁”的不利天气条件,并抓住北人畏惮南伐的心理,向众臣展开心理战术。“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军发轸”,即将出发,高祖故意让众臣发表意见。众臣以赤诚之心多次死谏、泣谏,高祖屡次申明大义不动声色地故意坚持,然后在时机成熟之时假装妥协,于是顺理成章地提出定都洛阳的真想法,进而得到群臣的赞同而达到了迁都的目的。这段文字叙事清晰完整,有头有尾,生动有趣,气氛紧张,又不失幽默感,极富戏剧色彩;同时也将高祖的睿智与臣子的忠心刻画得淋漓尽致,情趣盎然。
又如《魏书·李崇传》所载李崇断苟泰失子案:
先是,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与儿各在别处,禁经数旬,然后遣人告之曰:“君儿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闻即号咷,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10]1467-1468
此段文字本为史实,但由于作者善于叙事,在简洁的文字中却将其赋予极强的故事性,读之如读一则断案趣事,李崇的聪明智慧、苟泰的爱子之心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魏书》善于简笔叙事,如上面李崇断案事就是一个显例。再如:“及帝杀尔朱荣也,子升预谋,当时赦诏,子升词也。荣入内,遇子升,把诏书问是何文书,子升颜色不变,曰‘敕’。荣不视之。尔朱兆入洛,子升惧祸逃匿。”[10]1876寥寥几笔,就能把当时紧张气氛及尔朱荣被杀的悲惨结局清晰地展现出来,让人产生如临其境之感。此类例子很多,无须赘举。
第二,《魏书》长于运用多种手法刻画人物,人物形象个性鲜明。通过叙事以刻画人物是魏收常用的写人技巧,如上述对高祖、众臣、李崇、苟泰形象的刻画无不如此。再如帝杀尔朱荣一段:
三年九月,荣启将入朝。朝士虑其有变,庄帝又畏恶之。荣从弟世隆与荣书,劝其不来,荣妻北乡郡长公主亦劝不行,荣并不从。帝既图荣,荣至入见,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为后患,故隐忍未发。荣之入洛,有人告荣,云帝欲图之。荣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岂信之?”于是荣不自疑,每入谒帝,从人不过数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于明光殿东廊,引荣及荣长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禄少卿鲁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荣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乱斫,荣与天穆、菩提同时俱死。[10]1654-1655
尔朱荣有勇无谋、愚蠢简单、固执己见的性格,跃然纸上,十分切合一介武夫的身份。
《魏书》还多通过直接描写动作、表情来刻画人物。如李冲自劾一段:
辞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10]1188
李冲弹劾李彪这个过河拆桥的小人,因言辞过于急切以致自劾,其怒不可遏的形象情态:震怒、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等,鲜活生动,如在目前。
《魏书》也善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如:
文襄尝侍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悦,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狗脚朕!”文襄使季舒殴帝三拳,奋衣而出。明日,文襄使季舒劳帝,帝亦谢焉。赐绢,季舒未敢受,以启文襄,文襄使取一段。帝束百匹以与之,曰:“亦一段耳!”[10]313
文襄和孝静帝的对话不多,但文襄无视孝静帝的狂傲犯上的贼臣形象,以及孝静帝大势已去,不得不苟且忍辱的性格,均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高祖与元禧关于汉化改革的对话,限于篇幅,兹截取片断:
高祖引见朝臣,诏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为令汉晋独擅于上代?”禧曰:“陛下圣明御运,实愿迈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将以何事致之?为欲修身改俗,为欲仍染前事?”禧对曰:“宜应改旧,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为欲止在一身,为欲传之子孙?”禧对曰:“既卜世灵长,愿欲传之来叶。”高祖曰:“若然,必须改作,卿等当各从之,不得违也。”禧对曰:“上命下从,如风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对曰:“实如圣旨,宜应改易。”[10]535-536
这段文字全由君臣二人间的一问一答构成,气氛平等和谐。随着对话的展开,高祖高瞻远瞩、励精图治、果断刚毅、开明民主的王者风范清晰可感。类似例证,不胜枚举。
第三,《魏书》的语言也很有特色,晓畅自然,富有文采。前者主要表现在本纪、列传中,而后者相对集中地表现在传序和赞语中,如上述所举《文苑传序》即可窥其一斑。前文已言,魏收善作辞赋及章表碑志等骈文,行文骈俪,讲究藻饰,文风华美,这自然会影响到《魏书》的语言风格,使其文采斐然。曹道衡指出《魏书》在“史书中文笔亦可称上乘”[12] 504。张宏也指出《魏书》“富有文采,在尚质的北方文学作品中比较突出”[13] 13。曹氏、张氏之言实为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