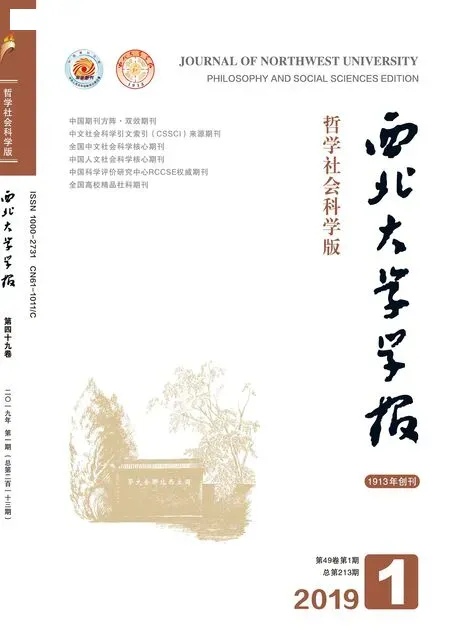走出资本丛林:新时代呼唤人的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
李建森,袁一达,李金笑
(1.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西北大学 哲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马克思对于“物的依赖性社会”的批判在今天依旧是难以超越的,而且仍然具有理论逻辑和现实生活两个方面批判的指导意义。在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视域,主体和客体之间并不存在旧哲学无论是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的那种绝对分明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物质批判和精神批判同样重要;对于社会历史的科学叙述必须扎根于劳动生产这一经济根源,但这绝不意味关于社会历史的哲学概括可以放心于简单而机械的非精神一元决定论。因此,马克思对于“物的依赖性社会”的批判绝不是非道德主义抽象批判,而是超越了非道德主义和道德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历史性反思和现实性超越。“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发展像任何历史进程一样,是一种建立在人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对立统一过程,一种趋于新的道德合理性的过程。它在人的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节点将个体性自由和整体性张力联系了起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类生命道德意识的时代表达。
一、资本丛林和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断裂现象
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历史主义元思考前提追问之一是,我们在哪里?当我们直面当代社会发展问题时,这一追问就是,我们当下置身何处?马克思曾经说过,就其本性而言,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1](P158)从某种历史整体主义思维角度看,人类今天仍然生活在资本应该受到限制而实际并没有得到“应该”(ought)限制的时代。人类今天依然很大程度上身处某种霍布斯“丛林”[2](P138),即 “资本丛林”,资本“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了它们的对立物”。在这里,“丛林规则”是以一种看起来被“克服”了的改良形式——“资本丛林规则”——发挥作用的。就现实过程来看,这种状况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向人们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的。在“前现代”世界市场原本受限于技术和空间掣肘的资本力量和逻辑,从此开始,迅速扩张成为一种全球普遍的历史力量和逻辑,交换价值的生产似乎“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3](P417)。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P404)在这个世界里,生态问题、贫困问题、恐怖问题、宗教文化冲突问题、代理人战争问题、核战争威胁问题以及后意识形态对峙问题等,作为硬币的一面,都和另一面,即发展问题、交往问题、和平问题、平等问题和公正问题等联系在一起,并受制甚至服从于资本力量和逻辑。这就是“资本丛林”及其规则的一般表征。
在“资本丛林”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原本只是在“自然丛林”才被看做是“合理的”普遍非道德现象呢?这是一个内在的人性问题吗?这是一个外在的环境问题吗?类似的设问容易将思考引向前途暗淡的道德形而上学修辞学死胡同,这种抽象性道德哲学思考的历史结论只能是建基于怀疑论基础之上的虚无主义“无言”“莫衷一是”。扬弃了启蒙主义狂傲的黑格尔历史辩证法提供了一个“世界历史”思考方案,但是,“绝对理念”所导致的最后理论结局却只能是一种令人失望的“理性”神秘主义命定论。“‘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4](P25)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过程。在此,人陷入了另外一种丛林即“神定丛林”之中,最终没有获得应有的自由和超越。扬弃了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实践辩证法,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就是,资本主义交往关系中的资本逻辑畸化打断了“类存在”与“个体存在”的现实性历史发展,强化了资本主义世界人的“类存在意识”“类道德意识”与“个体存在意识”“个体道德意识”之间的断裂进程。[5](P96)“类道德意识”衰落和“个体道德意识”僭越,与“资本丛林”及其规则彼此成为对方的根本原因和必然结果。而这一切在随着冷战结束而形成最大“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被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如何在具体历史情境中,树立并遵循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语义下人的“类意识”“类思维”“类生活”[6](P1),才是我们走出“资本丛林”的正确道路。卢卡奇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理解有可取之处[7](P62),在存在论视域,这种“类意识”“类思维”的价值内核就是人的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或人的类总体道德生命精神。它体现和凝结着后资本逻辑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核和生命意志,并因此而成为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正所谓“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P272)。
人的类总体道德生命精神是何以步入一个肇端于资本丛林规则的社会世界呢?在现存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物的依赖性社会”资本逻辑所滋生的那些非道德现象和问题呢?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种可以平衡主体与客体、“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紧张逻辑关系的实践智慧[5](P120),以彻底解决因为在上述关系问题上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而导致的令人沮丧的虚无主义和非道德主义?
二、个人角色裂变在分工发展中的差异性存在自觉及其异化
“感性世界”最令人惊叹的一件神奇事情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持续进行的不断分化及其所带来的几乎无限的复杂性。人和人的社会世界的发展也是如此。马克思受以往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影响和启发,用社会分工来解释社会世界的这种复杂化趋势。马克思赞同亚当·斯密所说:“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3](P238)他说:“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3](P238)受“自由竞争支配”下社会分工的推动[3](P243),人的社会角色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多样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驱动下的社会分工的发展,一方面,使得人的角色越来越单一化,这就是“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服从于“一个以人为机器的生产机构”。另一方面,使得人的角色越来越复杂化,这是因为“生产机构”越来越复杂化,因为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化”[1](P211-212)。当这种社会角色分化与不可逆时间、无限广延空间、自然繁衍血缘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不断裂变着的唯一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差异,因此成为社会世界的一种普遍存在状态。尽管这种“图景”是一种意识形态,可是我们还是不得不说,这就是事实。
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P96),就在于他能够自觉到自己的个性、复杂性,能够意识到个体自己同“类”中的其他个体之间的差异。而且,在现实生活世界中,人还在自觉地不断强化着自身的复杂性差异,发展着自己的越来越特别的个性差异;人还在自觉地强化着对自身复杂性差异的自我意识差异,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发展着对自己个性的自我意识自觉。
与人不同,丛林动物是以本能形式“观照”自己的个性和“类本质”的。“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5](P96),它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争”“和”意识以及“争”“和”关系的契约智慧。它们的个性是不发展的,如果硬要说性状“进化”的话,那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不变的无意识“迫变”本能。“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5](P97)它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类意识”,当然,同样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种意识”,也谈不上自我意识现象及其强化问题。
与丛林动物不同,人懂得以自觉形式“观照”自己的个性和“类本质”。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5](P97)。他们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争”“和”意识以及“争”“和”关系的契约智慧。其个性是发展的,在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的推动下[9](P109),他们意识到了,只有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只有强化自己的角色个性,才能获得最大利益。因此,他们不断地改变自己个性边界的地形地貌,不断地扩张自己个性的地盘。虽然受契约智慧的限制,但是,在交换关系最为发达的资本社会,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人的这种个性扩张达到了异化的顶峰。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人的独立性”达到了空前的异化状态。积极的和消极的个人主义自私性道德思维成为最基本的行为法则[3](P417),“他者”,俨然成为自我的“边界”和“地狱”[10](P7)。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以一种直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国家和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成为这种道德意识的总的集中代表,国家意志、阶级心理和意识形态成为个性,即,“人的独立性”最为直接的自觉形式。诚如马克思所说:“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用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是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3](P164)不仅仅如此,随着“世界历史”“国际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不但有国家意志、阶级心理和意识形态,而且“人的独立性”还创造了国家联盟作为自己的“合理”表达方式,并给自己的个性意志赋予所谓“普遍价值”,一种仅仅反映特殊个性价值的虚假普遍价值。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种“普遍价值”并没有给人类世界带来普遍的价值,并没有实现普遍价值。恰恰相反,它不仅仅摧毁了他人的价值,而且还最终也摧毁了自身的价值。它不仅仅利己,而且还害人,哪怕害人是不利己的。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主义远未像自己所欲求所声称的那样“合理”。在理论逻辑上占据优先“第一性”的个性,没有也不可能在生活实践中拱手相让自己的优势地位。看来,命运似乎没有原先所设想的那样一片光明,在整体上,个性世界依然是一个非道德问题世界。
三、“虚幻共同体”的历史性存在及其生命道德意识独断
共同体虽然是“人的独立性”的产物,可是,它一旦形成,就具有自身的“物质性”,并成为个人的先在前提和规范力量。人是一种在实践基础上的以语言世界为背景的社群性存在。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人总是只有在共同体中,或者只有通过共同体的形式才能存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P135)人是一种“缘在”,现实的人只有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己的真实性存在。在一定生产交往基础之上的家庭、家族、种族、阶级、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国家联盟是现实的人的最基本的存在前提和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家庭、家族、种族、阶级、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国家联盟都是作为个人存在前提的历史性社会共同体。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共同体是具有历史相对性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共同体为个体存在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是个体存在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是,从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共同体所提供的这种基本保证只能够反映特定的历史条件,是人解决自身一定有限历史课题的产物。所以,随着这些历史任务的完成,那些具有特定功能的共同体的历史根据的生命力也就终结了。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选择一种共同体的历史命定论的思维方式,我们同理也坚决反对在共同体问题上的“存在即合理”的庸俗观点。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P3)与此相一致,事实上,共同体无论在“未来”,还是在“现在”,都是历史的,都是相对的。共同体常常在发挥保障作用的同时,成为个体真实自由/理想的“反动”力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合法性共同体、理想性共同体总是以“图景”形式存在的。
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共同体是具有历史发展性的。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区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等三个阶段[9](P108)。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个人、共同体及其关系的特质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在“人的依赖性社会”,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以直接同一的形式存在的。在这里,整体上看,个人还没有从共同体中分离或完全分离出来,共同体支配着个体,风尚习俗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物的依赖性社会”,从本质上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以相互对立的形式存在的。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1](P3)个人作为对抗力量从共同体中分离或完全分离了出来,共同体的神圣性不复存在,个体成为主导的方面。在此,共同体的“共同性”变得“虚伪(冒充)”了,共同体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以特定法律为典型的强制规范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就其可能性而言,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以相互协调的形式存在的。个人与共同体形成一种和谐关系,个人和共同体的异化都得到了克服。人的不现实个性和共同体的“神圣性”、虚伪性都得到彻底克服。那种由自由人组成的真正的“联合体”,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在这里,反映人的类生命道德意识的道德规范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
下面只讨论在“物的依赖性社会”的共同体生命道德意识。按照马克思“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这一社会形态发展的“三阶段论”,当今世界历史正处在由“物的依赖性社会”向“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性过渡的复杂阶段。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都表现出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特殊态势。
相比较而言, 在“物的依赖性社会”, 人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和自由。 理性精神在“上帝之死”(从启蒙运动开始, 尼采只不过使其明朗化了)中获得空前体认, 科学精神在破除封建禁锢后获得迅猛发展, 主体性哲学、 “意识哲学”在对封建社会结构和宗教共同体的破除过程中, 获得了无以复加的荣誉和力量。 可是, 这种主体性哲学意识所包含的虚无主义破坏力也随着那曾经不可一世的旧共同体的坍塌而变得狂妄不羁。 除过它自身, 似乎一切都成为可怀疑对象。 有趣的是, 这种包含在理性主义骨子里面的虚无主义病毒, 被自己的非理性主义反对者承接过来, 并进一步以一种近乎畸形的方式得到发挥, 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似乎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 在这种思想中, 一切整体性的东西, 一切逻各斯的东西都被看做是虚妄不实的, 一切规范和原则都被看做是虚伪的意识形态。 这里只有一个法则, 即, 这里没有法则。 神圣时代被世俗世界取代了, 世俗世界被“后世俗世界”取代了。 这里, “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物化”及其所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 还有非道德主义, 就像一种挥之不去的魔咒肆虐八方, 在此, 资本家和非资本家, 都仅仅只作为资本的器官或“资本的人格化”形式而存在。 一切意识, 都成为“单向度”的了。 “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 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 而使人的生命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P4)
而这一切都是以“对于物的依赖社会”为前提的,以一种其“共同性”需要批判的特别社会共同体意识为前提和背景的。随着交换关系的普遍发展,契约关系得以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交往中得到迅速的扩张。几乎所有的社会共同体都成为一种契约性存在。这种契约精神与神圣精神所不同的是,它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自己无奈的“妥协性”“世俗性”,也就是自己的相对性。契约主义的所谓理性主义精神,是建立在人性恶基本假设抽象基础上的。因此,它们在骨子里就具有将共同体仅仅看做是生活手段的“元工具意识”“元物化意识”。在这一“元工具意识”“元物化意识”基础之上的所有共同体意识,因此现在都具有了“工具意识特性”。有关上帝、伦理、道德、文化、宗教、家庭、民族、国家以及人类的一切共同体意识现在都成为工具性、物化性、庸俗性的了。
继而,共同体意识也就必然成为一种“虚伪的”“虚幻的(冒充的)”的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所谓的共同体意识是十分狭隘的,因为它不过是个人意识的一种巧妙的、精致的、热情的延伸而已。然而,也许“这种热情饱含着诡计多端的刺激性水分”[12](P327)。这种共同体意识,常常要么以新道德“传教士”的身份亢奋地到处煽风点火,要么哭丧着萎靡的面孔四处怨天尤人。总之,在这里,共同体意识是以狭隘的“个性的集体”,或者说,是凭“以集体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异化个体意识”的特质而表现出来的,即,以“集体的个性”形式表现出来。种姓意识、种群意识、种族意识、教派意识、极端宗教意识、国家意识形态等,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是这样。“虚幻的(冒充的)集体”和“虚幻的(冒充的)集体意识”,作为一种“道德精神错乱”[13](P17),成为抽象的“类”的、共同体的普遍的精神存在状态。
所以,那些普遍的社会冲突,甚至那些所谓的“颜色革命”“价值观输出”,无非是异化的个体意识,或者说异化的集体意识所表现出来的反映资本扩张的道德丑陋。从某种意义说,“物的依赖性社会”里的那些“虚假的(冒充的)”共同体交往,就是非“总体性”的“对抗性”生命道德意识蛊惑下的“经济关系对抗”。[1](P3)在这种“对抗性”的伦理情境中,“虚假的(冒充的)”共同体的道德命令于是变成一种单纯性独断,以真像和假象形式出现的非道德现象成为社会伦理普遍。
四、真实共同体生成中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的历史过渡
在当代,交通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技术和仿生技术等的发展,还有全球化的持续深入,给人们重新认识自己、反思个人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在社会现象层面得到前所未有的明晰化。人类世界社会、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交往,使得“类主体”的历史性拓展几近极限。(最少,在“全球”的这一语境下就是如此。或者说,假设人类是唯一的最高级生命形式的话。)
第一,人类今天面对着自身的一个客观的、最大的“类”/“我们”,人的类生命道德主体面临一次空前的趋于真实性的拓展。也许,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最大贡献和最大遗产。在今天,随着冷战的“结束”,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以及作为它的意识形态表现的类主体意识觉醒了,就现实的历史实践经验而言,资本逻辑俨然成为最为普遍的社会力量。与其不恰当地说“历史终结了”[14](P1),“意识形态终结了”[15](P357),还不如说,那个过去曾经根深蒂固的“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的边界趋于消融了。那个“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要死亡了,一个新的具有迄今为止最辽阔领域的需要“大联合”的最大“真正的共同体”就要在崭新的社会生产中萌发了。马克思说:“现代制度……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组织。”[1](P69)这里所讲的“社会组织”应该包括自觉性程度不一的各种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共同体。它们几乎由同一个纽带给联结了起来,这就是它们的劳动受资本逻辑所驱使。虽然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那些凶恶的旧“共同体”的歇斯底里,但是,它不会负隅顽抗到明天。因为,道德保守主义在新近对于人类共同体应付地球变暖、多边协商、文化间性等生命共生伦理共识的否定中,已经收获到了一阵阵响亮的呵斥。这种呵斥,正是一个崭新的共同体道德生命意识/“新我们”呱呱坠地的历史前奏,或者说“前历史开启”。
第二,体现新科技及其开放空间特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创造着这个“崭新的共同体”/“新我们”。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分工中形成的那些独一无二的社会角色及其个性意识,迫使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者不得不努力寻求哪怕是天涯海角的可交换者。交换者彼此成为对方的规定性,成为对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存在。而这一切在当代最新一轮的交通技术、信息技术、通信技术和新材料技术革命性发展之前,还是以简单性的形式、有限性的形式表现的。可是现在的情况似乎一下子发生了实质性的跃升,时间变“短”了,空间也变“小”了。交换关系的拓展是在地球空间中展开的,当这种展开扩展到这个星球的尽头的时候,与之对应的社会空间也达到了自己的极限。经过数千年的扩展,在“物的依赖性社会”,地球似乎嬗变为一个“自然村落”。可是与此同时,一个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绝对的”“我们”共同体出现了。这种“我们性”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性语言的主体间性,而且还是某种显现出更大伦理主体拓展特点的“主客体间性”。现代科学能够让人们更为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统一性关系观点的道德价值,自然作为“我们”的“无机身体”部分[5](P95),同时也获得了某种“全球化”的“我们性”。
第三,“崭新的共同体”/“我们”作为“类存在”必然孕育、蕴含和发展自己的“类意识”“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就现实的存在而言,或者说,实际上,社会世界里的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类意识”本来就是一体的、统一的、同一的。在理论上说,在社会世界,共同体和共同体意识/“类意识”二者是互为前提的。基于“类存在”和“类意识”的同一性总体力量,同时,也基于“一”是“多”的前提这一形而上学法则,“类意识”生命道德思维的最为基本的法则就是,“你的”就是“我的”。在此,共同体“超越了特定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共同体里,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在特定的冲突中让自己置身于共同体的既存社会之外,以便就已经发生变化的行为习惯和新出现的价值观念达成一致”[16](P205)。正如马克思所说:“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5](P121)可是,这一法则离开历史就是抽象的,逻辑只是在历史中才是现实的。正如恩格斯所说:“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1](P14)所以,这一法则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不同的。这种法则分别在“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以自在、自发和自为的特质存在着。在“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不同阶段和情境,“你的”就是“我的”所具有的价值属性也是不同的。这里暂且不讨论主词和宾词“你”和“我”。让我们先分析谓词“就是”。历史所赋予它的意义是,暴力占有思维、契约理性思维和道德共享思维。这大致反映了人的类存在作为道德主体的生命历程。在当代,暴力占有思维随着民族主义、国家利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宗教狭隘主义的德性衰落而声名狼藉。契约理性思维也因为它所导致的普遍的物化现象和虚无主义而臭名昭著。显然,在崭新的共同体来临之际,如何建构一种能够同时克服这两种弊端的道德共享思维及其所指向的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已经成为历史的呼唤。
五、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现实性历史选择
社会历史是进步的,人的类生命道德意识的整体发展趋势是前进的。就整个社会世界的历史状况及其走向而言,人类今天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丛林”,还没有摆脱“抽象的资本逻辑力量”的宰制,但是,在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看来,“真实的”自由和公正天地不在彼岸世界,它就近在咫尺,就在此岸世界;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看来,“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及其决定的个人异化、类主体失落以及类生命道德意识迷失,在今天已经丧失了自己存在的合理根据。体现新科技革命成就和生产力跃升的“地球村”“网世界”等现象,给人的类总体生命道德思维现实化提供了更加充分的前提条件,也让人类看清楚了,一个新的“绝对”共同体,一个具有“绝对”道德约束力的共同体,一个“真正的”新共同体的出现已经具备现实性条件了。在此,孤立存在、封闭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如果没有开放的“类思维”生命道德意识,就将被新历史力量所淘汰。就像邓小平所认为,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17](P370)在当代世界,如果没有人的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我们不可能解决所面对的诸多社会问题,不可能摆脱资本逻辑桎梏,不可能把“资本丛林”变成和谐美丽人间。
理想世界是在发挥真正主体性精神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P136)在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意识变革、道德革命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性途径或根本性办法。但是,社会变革绝不是自发实现的,没有进步性道德主体意识的觉醒,就不会有革命性的现实力量。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就像没有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就不会有资本主义一样。在当代世界,如果没有对于人的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的振臂高呼,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所指引的理论努力和实践推进,没有进步力量的“联合”生命道德意识,现存的社会历史走向,就只能是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背道而驰。
不是全球化,而是“好全球化”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赞成一种有优雅道德意识的全球化,在这里,资本逻辑得以控制,“物的依赖性社会”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行为受到挞伐。生态问题、贫困问题、暴力问题、恐怖问题、宗教文化冲突问题、代理人战争、核战争威胁问题以及后意识形态对峙问题得到重视并着力解决。“虚幻的(冒充的)”共同体及其所表现的极端个体主义、绝对共同体主义、原教旨自由主义、道德虚无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等非道德主义思维方式遭到普遍的抵制。在道德语义上说,这里倡导的最基本法则就是,诚如马克思所说,“你的”就是“我的”,不仅仅是权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责任。在“好全球化”的世界交往中,意识哲学的片面主体性的非法,不在于它所激起的对抗是非法的,而在于发起这些对抗的主体本身是非法的。“好全球化”之所以“好”,就在于它奉行的生命道德精神被代表普遍意志和价值的“真实的共同体”所引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路一带”倡仪构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是一种建立在真正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基础之上的“好全球化”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18]这深刻揭示了一种奉行人的“类总体道德生命意识”的谅解之旅和真正共同体道德实践。这里所倡导的真正的主体性“我”绝不是类似于维特根斯坦的那种具有超验唯我论特质的、以自身的语言界限作为世界界限的“我”[19](P203),也不是圣保罗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20](P210),也不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也不是马哈拉吉说的“那就是你”-“我就是那!”[21](P313)。“我”是下面这样一种境界或趋向于这样一种境界的“善”,是对于这一切抽象自由言说的真理性超越,是对于资本逻辑这种“抽象力量”的现实性超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自由的“我”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5](P121),是真正共同体中最能够体现类总体生命道德意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