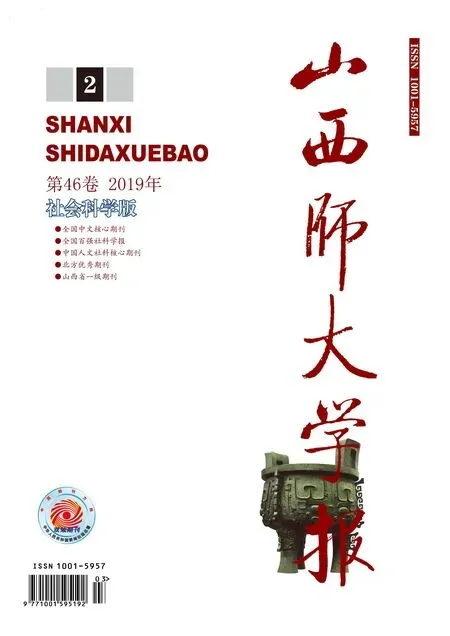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全球化写作”
——以诗人多多和严力的海外研究为参照
谢 丹 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自1827年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理想以来,这一代表人类整体图景的概念始终无法回避对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讨论。在中国文学中“全球视野”和“本土经验”的恩怨纠结相伴相随的是“文学走向世界”的渴望与焦虑。换句话说,究竟是本土元素还是世界普适经验能指引中国文学走进世界文学的殿堂?作家或评论家们往往各执一端,如李锐呼吁作家应“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1]4,而曹文轩在《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以“作坊酿造的地方情调”来比喻文学的“本土特色”,认为以民族性和文化性作为进军世界的手段,不过是“以土特产与人相争的路数”[2]172。他由此反思,“这果真就是文学走向世界的正道吗?”这究竟“是一种自信的选择还是无奈的退避?”[2]173此外,认为文学创作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两端之间寻找平衡支点的折衷论调也大有人在。
在建构诗歌现代性的过程中,关于“中国性”与“世界性”的探讨始终不绝于耳,成为从现代诗一直延续到当代诗的文化主题。当历史的车轮驶进现代的轨道时,中国诗歌自足、封闭的互文体系遭到西方影响而瓦解。新诗在外国诗歌的影响下崭露头角,在性质与形态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对古典诗歌的反叛。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古典诗歌已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国几千年文明的标签。因此,新诗在诞生之初就陷入了尴尬境地。一直以来,对本土色彩的惯性期待使中国现当代诗歌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关于新诗的种种争论也一直延续到当代。本文以多多和严力的诗歌为例,以西方世界对这两位诗人的研究为窗口,探讨中国当代诗歌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写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启示与参照。
一
中国诗歌里“现代性”的建构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在推广白话的过程中,新诗成为一种媒介。然而,许多中国人认为新诗挑战了基本的文化认同,因此它的价值和文学影响在复杂、艰巨的实践中始终遭受质疑。到了七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诗歌同样无法摆脱“先天不足”的命运,屡遭诟病。九十年代初,著名诗人、学者郑敏就指责当代诗歌,尤其是朦胧诗里使用了过多现代西方元素而丧失了中国式的诗意。她将当代诗潮比作一场车赛:“我们来不及认清驾驶人,只能在紧张而喧嚣的喝彩声与啦啦队的欢呼声中向获奖者致以敬礼,当回到自己的卧室时不觉有些茫然。”[3]292学者孙绍振甚至大声疾呼,向当代“艺术败家子发出警告”[3]262,认为“新诗和朦胧诗的全部理论基础都是照搬西方诗歌的”[3]263。
实际上,诗歌的创作从来都不是一个“一尘不染”的空间。20世纪初在西方,英、美、俄等国家的现代主义诗歌都在多重参照里建构自己的“现代性”。如庞德将东方诗的精髓融解于自己的创作中,俄罗斯诗人曼杰斯塔姆把“阿克梅主义”这一诗歌流派定义为“对于世界文化的怀乡之思”。在古代中国,诗歌“互文”体系源远流长。中国古代诗人在写作中往往有意识地与前代诗人及文本建立对话关系。20世纪初,伴随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诗歌的“互文”体系发生了逆转,由原先的向内自省转向了向外凝视。诗歌创作不再从封闭的系统里汲取养料,而是将目光转向世界其他优秀的文化传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欧美文学作品在国内被翻译出版,其中现代主义思潮里的疏离主题在诗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与当时诗坛的精神特质一拍即合。对于中国当代诗人来说,与某些西方诗人相似的经历,使得惺惺相惜的情愫凝铸成了一条创作的精神血脉。
中国现当代诗歌在探索道路上的不懈尝试获得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共鸣。在他们的视野里,当代诗歌并不是“背叛”的代名词,而是演绎着中国诗歌重获新生的实践旅程。“如果用一个词来涵盖中国当代诗歌,它就是革命。”[4]16新诗的变革暗合了庞德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的文学宣言——“make it new” (让一切变得崭新)。不少汉学家将目光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抽离出来,投向新生的现当代诗歌。他们认为:“现当代诗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语言,隐喻着中国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试图重新构建现代社会里的自我认同。”[5]5当代诗歌对传统有意识的疏离,恰恰说明它不唯传统马首是瞻,而是将眼光转向了世界上其他优秀的文学,在传统之外开辟了另一个全新的审美空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奚密教授认为,东西方诗人共同的精神特质在于,他们都是“挥霍痛苦的人”[6]193。当代诗人在穿越历史的黑暗隧道时,遇见了怀着敏感之心的西方诗人,遥相呼应。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世界视野”已经成为沟通东西文学的桥梁,而“全球化写作”恰恰体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开放特质。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人不断以一种时空交错和文化交置的方式,隐匿在当代诗人的写作深处。欧阳江河在论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诗歌时曾特意谈到这一点:“隐匿在我们写作深处的叶芝、里尔克、庞德、曼杰什塔姆和米沃什等诗人也已经汉语化了,本土化了……重要的不是他们在各自的母语写作中原本是什么,而是……在我们的当前写作中变成了什么,以及在我们今后写作中有可能变成什么。”[7]19790年代不少诗歌文本,如孙文波的《散步》、张曙光的《尤利西斯》等在切入自身文化现实的同时,都有意识地并且富有意味地与其他西方文化发生一种相互指涉的互文关系。基于当代诗歌开放性的特质,诗歌的“全球化写作”既指诗人在创作中与其他文化语境下的作家进行对话,形成文本之间的互动[注]诚然,文本互动并不局限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也包括中国文学与其他东方国家(如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家)文学的对话。,又体现在诗人以全球为创作视野与背景,构建自我的诗性世界。总体而言,世界视野是“全球化写作”的核心,诗人以“文本互动”或“全球背景”为创作特点,在诗歌中实现“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自然融汇。
二
既然当代诗歌是一个开放的创作空间,那么其中必然不乏西方影响的痕迹和想象世界的元素。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柯雷、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巴特、康尼狄格州立学院东亚系教授黄亦兵、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郑树森等海外学者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当代诗歌里的西方元素,他们从“影响研究”或 “平行研究”的角度入手,探讨西方诗人对当代诗歌创作的精神渗透或中西诗歌里的情感共鸣。如郑树森集中探讨了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的关系,他以顾城的《一代人》为例,探讨了诗歌的意象,并将朦胧诗的“朦胧”与意象派的“晦涩”进行对比。在西方学者的研究里,诗人多多[注]在当代诗人中,多多颇受海外学者青睐。他的创作生涯开始于1972年。他于1989年离开中国,到英国、美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大学开办讲座和朗诵会。2004年,多多回到了祖国,任教于海南大学。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多多与波德莱尔”“多多与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等都成为学者的研究话题。
在海外学者里,黄亦兵是多多诗歌当之无愧的研究专家,曾出版过关于多多的研究专著。他认为,多多的身上承袭了波德莱尔式的精神气质。他指出,多多曾提到自己在回家的列车上读到了夏尔5皮埃尔5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一行小诗,“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虽然在此后多多的作品中没有出现这句话,但毫无疑问,多多是波德莱尔式的预言诗人。”[8]25多多早期诗歌里紧凑、怪诞、超现实的画面和具有冲击力的视觉效果与波德莱尔的创作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从“平行研究”的角度入手,黄亦兵将多多与另一位法国诗人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身上的“疯狂”特质进行了对比。兰波在巴黎公社运动发生的同年,曾在自己的诗歌里写道:“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时代的预言家”[9]307(“I say one must be a seer, make oneself a seer”)。兰波在自己后来的作品里进一步阐释:“(在一段昏暗的历史里),由于诗人所有的感官都被扰乱了,或备受折磨或宣泄疯狂,因此他们成功地成为了预言家。正因为身处未知,所以他们大胆地探索自身……”[9]307由于黑夜在某种程度上为自由提供了空间,像兰波一样,多多沉浸在自己定义的黑暗里,或疯狂、或执着地在迷途里寻找出口。然而,与兰波不同之处在于,多多演绎的是一种“另类的”疯狂,“守护自己”是他穿越黑暗历史的独特方式。在诗歌忧郁的基调下既隐匿着诗人对抗黑暗时的无奈,同时也暗示了自己不愿向历史屈服的骄傲姿态。
多多与俄罗斯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的创作联系同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多多是第一位发现茨维塔耶娃的诗人,他将这位俄罗斯女诗人引入自己的创作里,从而使诗歌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抒情基调。”[8]31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具有骇俗的独特品质,在俄罗斯近现代诗歌史上乃至世界文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透过茨维塔耶娃的命运和诗歌创作,多多形成了自己看待历史的全新视角。他在1973年第二部诗歌论著的扉页里写到“献给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足以说明无论在精神特质还是在创作形式上,这位杰出的俄罗斯女诗人都深深地影响了多多:
——和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我写青春沦落的诗
(写不贞的诗)
写在窄长的房间中
被诗人奸污
被咖啡馆辞退街头的诗
我那冷漠的
再无怨恨的诗
(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我那没有人读的诗
正如一个故事的历史
我那失去骄傲
失去爱情的
(我那贵族的诗)
她,终会被农民娶
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
——《手艺》[10]17
在茨维塔耶娃曾出版过的诗集里,其中有一部就叫《手艺集》(1923年),但是多多《手艺》的标题除此来源之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出处,就是茨维塔耶娃的组诗《尘世的特征》里的几行:
我知道,
维纳斯是手的作品。
我,一个匠人,
懂得手艺。
西方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多多的《手艺》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最具跨文化特性的诗歌”[8]39。当历史酝酿着一场场永无止境的变革、风波时,个体的世界则呈现出停滞萧瑟、死气沉沉的图景。在对茨维塔耶娃的回应中,多多将自己心目中的诗学幻化成一个女人的命运。正如一位拥有贵族血统的妇女失去了纯真、骄傲与希望,诗人在历史与革命的动荡里艰难地寻找遗失的认同。透过俄罗斯女诗人的形象,多多在自己“地下写作”的旅程中诠释了诗歌呈现心灵的本质。但同中有异。在茨维塔耶娃诗中,所有生活中孤独的苦难、温文尔雅的高傲、敏感而压抑的心灵、不被允许的爱,统统化成优美的辞藻、神秘的韵律。而在多多的诗中,诗人拿着一把人性的尺子去衡量一段过往,希望从历史里寻找属于自我的空间。他以妇女的自怨自艾表达了对历史、对自我的哀伤以及无可奈何的宿命感。因此,如果说茨维塔耶娃通过苦难展现心灵,那么多多则通过透析历史来寻求自我。多多对茨维塔耶娃同病相怜的情愫幻化成一种悲剧式的自我认知,这种认知夹杂着诗人对于历史的感悟,同时透过世界视野收获充溢心灵的元素。确切地说,诗人的“全球化写作”里的一部分“世界”是通过敞开心扉、与西方优秀文学进行对话而呈现出来的,而茨维塔耶娃、俄国历史,甚至是西方文学都为多多等中国诗人搭建了观望世界的平台。同时,多多将“中国”放入了世界的语境里,将个体的认知与世界视阈里的认同缠绕在一起,这种表现手法诠释了美国学者彼得·巴特所定义的“世界视野里的本土怀旧”[11]231—232。
三
诚然,诗歌不是“横向移植”加“纵向继承”的简单配方,也不是一种文化构成上的平衡。虽然在多种关系中,中国当代诗歌和西方近现代诗歌有着直接或亲近的关系,但当代诗人并没有抛弃“中国性”,而是依然在世界视野里执着地寻找自己的文化与身份认同,在更开阔的时空关系里建构自我。将异国元素融入自己的创作里,将想象的触角伸向异域,在未知里表现诗人的主体意识,是多多“全球化写作”中呈现世界情怀的另一种方式。以多多的《万象》为例,这组诗展现了多多在异域里的个体畅游,诗人对自由个体的崇敬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像对太阳答应过的那样
疯狂起来吧,玛格丽:
我将为你洗劫
一千个巴黎最阔气的首饰店
电汇给你十万个
加勒比海岸湿漉漉的吻
只要你烤一客英国点心
炸两片西班牙牛排
再到你爸爸书房里
为我偷一点点土耳其香烟
——《玛格丽和我的旅行》[10]18—21
西方学者认为,诗中所“仰慕”的西方女性玛格丽的名字来源于波德莱尔的诗歌《恶之花》,她象征西方世界里独立自由的个体。彼得·巴特在分析时认为,在这组诗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贯穿于全诗的“声音”,即个体的“呐喊”,它串起了对异域世界的各种遐想,也串起了个体在不同国界之间的“舞蹈”。这一组诗里一系列抽象拼凑的画面散发着异国情调,但多多并不是单纯浪漫地向往西方世界,相反,他在世界视野里反观自身,寻求自我认同,诚恳地展现了自己向往和身处的两个世界;同时,在旅途中展现了自己内心的焦虑。浪漫的异域之旅与苦涩的历史、现实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在一系列异国画面的背后藏匿着诗人心中若隐若现的疏离感,他的域外之旅更像是一段探寻自我的情感征程。
由此,推崇西方精神和强调自我的身份认同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诗人心中,自己倾心向往的异域世界是自由的缩影。然而他并没一味地沉溺在异国的风光里,他苦涩地回味自我在现实中的角色。诗人主动、自觉地与异域建立一种互文关系,在世界视野里完成当代诗歌里“寻找自我”的命题。译者利大英在多多英译诗集的导言里写道:“多多完全是一位现代诗人,因为他的作品里经常可以看到经严格过滤后的世界主义的影响。”[12]2世界视野为当代诗人提供了全新的创作视角,使诗歌的语境日趋开阔,从而在一个更大的格局里建构自我。
如果说,多多将异域作为表现自我的舞台,那么严力的野心则更大,他以“全球”作为自己创作的幕景,在全球语境中探索“全球化写作”的真谛。在中国当代诗人群体中,严力虽然作为“今天”诗群的一名成员,仍然在国内诗坛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比起北岛、顾城、舒婷等耳熟能详的朦胧诗人来说,严力的名字并不那么响亮,但他创作的不少诗歌都已翻译成英语并持续获得西方学者的关注,这与他常年旅居海外的经历相关。同作为海外中国当代诗人,严力与执着于“民族史诗”的杨炼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前者的诗歌中若隐若现。在西方学者看来,严力“游离于传统体制之外”[4]146,他“全身心”地投入“全球城市”的怀抱,构建了一种开放的创作格局。
严力于1985年夏留学美国,1987年在纽约创办“一行”诗歌艺术团体,并出版“一行”诗歌艺术季刊,任主编。在纽约,严力写诗作画的才能很快就得到了认可,同时,他与阿兰·金斯堡(Allen Ginsberg)等美国诗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入了美国诗歌团体。对比国内诗坛的其他诗人,他与海外市场与读者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然而,拥有“朦胧诗人”和“海外诗人”双重身份的严力,尴尬地处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他的诗歌创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当同时代的朦胧诗人在略显严肃的政治历史框架里,以哀痛而朦胧的基调书写个体的觉醒,展现对历史、现实的沉思时,严力的风格则显得轻松、婉转,颇有些游戏的意味,从而渐渐地被搁置在诗坛主流创作的边缘。尽管多年的创作经历使他不断在遭遇失败与寻求个性的旅程上徘徊,但是诙谐的创作风格一直贯穿于他的创作生涯。诗人将“自我”放置于不同国度、不同艺术形式、不同时代里,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启示;如果说历史与个体的命运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诗人创作的源泉和主题,那么对于严力来说,海外的生活经历使他摆脱了地域的局限。他在“全球化”与“全球城市”中追求诗歌意境,在全球梦想里寻求写作的独特表达方式。
“全球城市”这个名词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在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里首次提出的,一直以来它都是西方社会的热门话题。基娅认为,“全球城市”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当前的根本性变化——从经济到文化再到人的主体性,很大程度上都在一些核心重要的国家环境内发生。“全球城市”与另一位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nstein)“世界体系理论”有不少相似之处,都将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由结构性经济联系及各种内在制度制约的、一体化的体系。“全球化”悬浮于中国当代诗歌的表面,往往意味着宏大的历史叙事而非全球叙事,然而严力在创作中却真正融入了“全球城市”的精髓。美国学者魏朴认为,与其他朦胧诗人不同的是,严力在过去几十年的创作里,一直将“全球城市”作为其创作空间的隐喻。诗人运用全球城市里经济、商业、环境、自然等各种元素,从纽约到伦敦,通过不同时期的“时空”变位,展现了诗歌和艺术世界里的现代全球意识,因此在诗坛中独树一帜。正因如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严力遇到了欣赏自己的读者和评论家。
严力的诗歌里时时充斥着城市或商业的“隐喻”,例如在《多面镜旋转体》中,他以广告式的模板展开了自己的创作:
产地:中国 有味多嚼一会儿,
没味就吐掉
生产者:严力
——《多面镜旋转体》[13]3
诗歌里的城市或商业元素没有任何地域标志或历史标签,它们就像一个个随处可见的名牌散落在任意角落。从视角和诗意上来看,“全球化”是严力诗歌里反复拿捏的元素,他没有试图抨击无孔不入的全球化体系,而是“沉浸在全球化的罗网”[4]146里。他将自己放置在瞬息万变的全球浪潮中,同时不断改变自己观察的视角。然而,即使严力的诗歌常常充斥着商业经济的元素,但这些全球化语境里随处可见的标记并没有遮蔽他对自我的探寻。他在2002年创作的《无题》里,无情地调侃了全球城市里必不可少的元素——可口可乐:
我与可口可乐合拍了一张影像
都说他太老太黑太多物质的狂妄
但朋友们都说看不出有甚么夫妻相
虽然百年来他有全球共识的卖相
朋友们还说为了我那下一代的质量
绝不能光从经济上考虑配偶的优良
于是我一次次地把全身心的情感酝酿
直到我在各种条件的衡量中乱了方向
直到我再也没有青春的优势与人较量
直到我内心只剩下一片天寒地冻的凄凉
——《无题》[14]179
严力的诗中充斥着的商业名词不仅是诗歌独特的语言,也是诗人与全球读者进行沟通交流的工具。诗人仿佛站在全球城市的某个角落冷眼旁观,将个体的经历融入世界商品交易的体验里。令海外学者感兴趣的是,严力将可口可乐等商品符号与自我认同进行比照,从而聚拢起巨大的情感张力,“物质的狂妄”使“我”在失望中迷失自己。在全球城市里,商业、消费逻辑取代了情感逻辑,个体的理想被无情的经济实用主义取代。诗人将个体放置在全球城市的宏大语境中,使人性的主题在城市的布景里得到升华。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力实际上延续了朦胧诗时代展现“自我”的传统,保留着与母语语境里相联通的本土脉息,始终“被母语套牢”[14]209,保持了“在场”的亲和力和写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他没有使自己深陷于历史与政治的牵绊,而是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展现自我的寂寞与孤独,使创作洋溢着现代美学意识。在一个非母语的国度,他坚持用母语创作诗歌,企冀通过世界语境来表达自己的困惑、欲望和生命体验。对照他的诗歌《根》:“我希望旅游全世界……全世界的每一天都认识我的旅游鞋/但我的脚从旅游鞋里往外挖掘的/只可能是故乡的拖鞋”,从对根的依恋到世界性视野的呈现,诗人“旅游全世界的壮举”里潜藏着寻找精神之乡的初衷。
作为严力作品的翻译家之一、美国汉学家、黑山学派诗人梅丹5理(Denis Mair)在谈到严力作品时说到,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城市对他来说就像一扇巨大的窗户,他透过窗户眺望自己的诗歌世界。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幕景下,严力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位旅者”[4]161,面对世界,反视本土,以世界之眼看中国,以中国之眼看世界。在中国当代诗人群体中,他较早转换话语,落于日常,合理地运用口语与日常事象组成超现实语境,并经由富有黑色幽默与反讽的修辞策略,在全球化的坐标之下寻找诗歌的价值。在长达几十年的“世界公民”生涯里,严力在全球城市的舞台上、在传统性与全球化的执着守望里,展现自己的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
四
诚然,每个作家的经历不可复制,对于多多和严力两位诗人来说,人生阅历、生活方式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世界视野”对于他们来说可谓水到渠成,信手拈来。分析两位诗人的“全球化写作”,意图并不在于说明世界元素是世界文学殿堂的唯一通行证,或者提倡作家盲目向西方借鉴技巧,而是期望在不少作家、评论家 “仍如大多数外省的贸易公司的经理们如出一辙地相信土特产的力量”[2]172的时候,能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另一种思考。正如博尔赫斯援引18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道:作为阿拉伯世界的经典,《古兰经》里没有一处提到骆驼。博尔赫斯由此联想到:“即使不渲染地方色彩,我们也能是阿根廷人。”[15]85—86真正的民族化写作,并不在于标榜乡土,或是以某种风俗、文化标志物彰显民族特色。与此相似,“全球化写作”不在于刻意呈现广阔的创作视阈,它是世界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自然融汇,是蕴藏在多多、严力等当代诗人诗歌里看似无形、却又分明存在着的精神、格调、思维方式与美学趣味。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学不再是作家本土化的私语表达,而是在文学创作的自觉中把支撑民族自信的自我体悟和世界元素整合为一,在世界文学的传统中寻找适合本民族的文学给养,为当代诗歌乃至文学的发展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