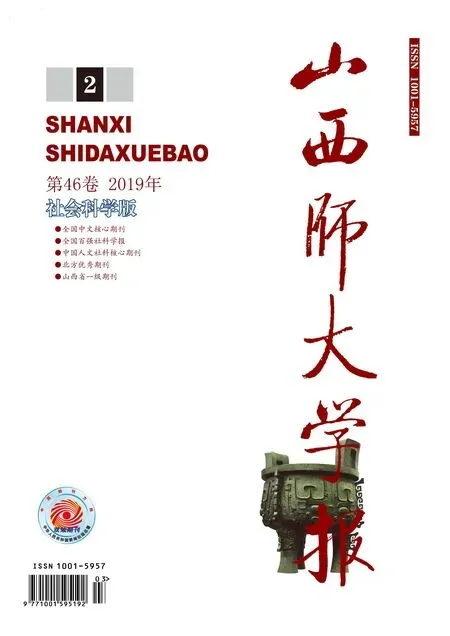论英国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阶级与财富
张 静 波
(中国民航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300)
如果以社会类型观察维多利亚小说,那么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皆为描绘阶级和财富的小说,即维多利亚小说的典型特征为阶级性。奥斯丁的作品实则为描绘维多利亚阶级和财富的经典之作。在《傲慢与偏见》中,有很多讨论婚姻的场景:费茨威廉上校解释为钱结婚的理由——从小过惯贵族生活,有钱才能维持富贵生活;与贫穷姑娘谈恋爱,实在太过危险,不符合身份和常理。奥斯丁也认为上校所言属实,维多利亚时期的阶级社会真相确实如此。由奥斯丁的小说可见,阶级和财富是维多利亚阶层认可的广泛准则,同时也反映在维多利亚时期其他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如萨克雷、狄更斯、乔治·艾略特、夏洛蒂·勃朗特和哈代。
如果仔细研究英国和美国小说,能够看出两国底层草根晋升上层的不同准则。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费恩进入上层的主要条件是个人财富;而在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中,皮普挤入绅士阶层,要在个人教育、行为举止、精美服饰、家具、仆人、朋友和金钱等多方面花费。就算后来成为绅士,也无法抹去个人出身下层的污点。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费恩沿河而行,美国社会展露于阳光之下;皮普生活在伦敦,暗影迷宫,似乎在告知读者,皮普或许难以获得贵族绅士的体验和认可。
一、维多利亚初期的阶级转变
19世纪的英国工业时代,社会阶级最重要的变化为贵族阶级和新兴阶级的对立,这正是英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世界的转型依据。恩格斯认为,工业革命激发了新型阶层即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之前,18世纪英国贵族阶级依存于土地和继承,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底层一贫如洗。[1]17维多利亚初期,英国社会以农村为主,高端和低端人口依赖土地相互联系,这种依赖关系尚未被大规模工业化所击碎。阿萨·布里格斯认为:“工业革命前,除了最古老的资产土地以外,其他持久资产不到英国资产的三分之一;到1860年后,份额已经超过一半。”[2]189
英国是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从1770年开始,英国的棉纺厂、炼铁厂和煤矿逐渐工业化。19世纪初期为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开创了维多利亚“新阶级”社会。纵向经济的突破,挑战了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的横向经济。在维多利亚社会中,由于经济利益冲突,不同利益集团呈现对抗局面,如中产阶级(工业利益集团)与贵族阶层(土地利益集团)的对立,阶级划分更为显著。从19世纪初期的奥斯丁到19世纪末期哈代的维多利亚小说家,其作品中的阶级体验贯穿于19世纪的英国小说中。
对比18世纪小说《汤姆·琼斯》和19世纪的《爱玛》,阶级差异鲜明。汤姆·琼斯的贵族社会,以财富和出身为中心,收入皆与土地有关,小说中的道德冲突皆出自此群体。而在奥斯丁的小说中,通过商业赚钱,与土地利益日渐疏远,他们与传统收入渐行渐远。在《爱玛》中,典型人物是埃尔顿夫人,她的收入来自新型贸易产业,其言谈、衣着和举止,异于当地乡绅。埃尔顿夫人的经济根基和社会出身不同于传统社会:一方面,她需要拥有土地的贵族乡绅认可其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她来自财富优渥的新型阶层,土地乡绅也需要她。19世纪的英国,社会阶层逐渐认可富有的新兴阶级。
在维多利亚社会中,有钱并不意味就是上层阶级。维多利亚时代的第一代富人,虽然家财万贯,也未必能跻身上流社会;绅士贵族们对于金钱至上的观念,感到庸俗和厌恶。狄更斯《艰难时代》中白手起家的纺织厂厂主庞得贝、萨克雷《名利场》中的老奥斯本,为维多利亚时期的首富代表,被视为唯利是图、富而不贵的代表。但是这些富商的子女,继承家业财富,渐被上流社会所认同。无论如何,维多利亚的社会阶级和财富显然密不可分。1835年托克维尔参观新兴工业城市伯明翰后写道:“整个英国社会都是建立在金钱特权之上。”[3]77贵族乡绅不只出身名门,财富是显赫头衔的基石。18世纪首相威廉·皮特认为:年收入超过20,000英镑的富人,如果个人期望,应该授予贵族称号。
事实上,英国19世纪从贵族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转变,过程并不简单。19世纪社会阶层与18世纪类似,贵族为上,直到一战后,这种阶层划分才逐渐解体,之后才出现现代社会的“民主”概念。[4]45社会阶层更迭的复杂性体现在维多利亚的小说中。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将“快乐英格兰”的理想社会视为怀旧神话,认为在贵族社会里,不论高低贵贱和谐相处的场景,不过是滑稽幻觉。然而无法忽视某些社会真理,即小说的主要议题是主人公的出身问题。菲尔丁早就认识到:英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为个人出身和财产继承。
二、维多利亚小说的上层阶级与财富
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阶级和财富议题很是复杂,19世纪英国社会阶级划分也众说纷纭。历史学家一般认为,从19世纪中期到现代社会,分为三个阶级:上层、中层和下层;或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维多利亚小说区分得更细致,即:不必工作之人,拥有部分家产之人(介于工作和不工作之间)以及无家产、依靠体力劳动“勉强糊口”之人。
维多利亚社会中的其他界线,如宗教、政治和社会地位等,使得这种结构更为复杂。上层阶级主要是国教教徒,大部分中产阶级为非国教教徒。[5]67从政治结构而言,分为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者,政治成员由贵族的托利党和中产阶级工业家的辉格党组成,激进分子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另外,英国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对于工人阶级影响较大。乡村劳工比城市工人政治上趋于保守,更多为国教教徒;城市工人对宗教较为冷漠,在政治上更加激进。
据统计,至1803年,上层阶级或无须工作谋生的家庭约为27,000户,占总人口2%;中产阶级63.5万个家庭;下层家庭约有1,347,000户。上层阶级可以分为三类:贵族、有田产的士绅和无须工作的乡绅及绅士。贵族是最大地主,地产过1万英亩,年收入超过10,000英镑,这是英国权力最大的少数群体,大约300到400户。士绅的地产少些,大概为1,000到10,000英亩,年收入约为1,000到10,000英镑,大约有3,000户。这两类上层阶级,拥有英格兰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乡绅或绅士的土地和收入少些,年收入约为700英镑到1,000英镑。[6]106以上数据可以作为衡量英国维多利亚社会和小说中个人阶层与财富的划分依据。
在一战和通货膨胀之前,19世纪的英镑很稳定,1英镑约为5美元。根据菲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记录通货膨胀的统计数据,从19世纪到现在,英镑增值40倍。[7]169这意味19世纪年收入超过10,000英镑的贵族,现在年收入约为200万美元。普通绅士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才能在上层社会立足,不为谋生而外出工作。
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的年收入为100,000英镑,远远高于当地麦里屯的律师和乡绅。达西作为英国最富裕的三四百户贵族,在麦里屯的乡村舞会上露面,轰动程度可想而知。达西高高在上、傲慢疏离,而当地人好奇巴结,读者在了解维多利亚的阶层和财富后,就理解入木三分。
严格而言,达西没有世袭头衔,不属于贵族,但家族历史悠久,坐拥家族财富和资产,维持贵族生活必需的奢侈收入。维多利亚时期有头衔的贵族,地产超过10,000英亩,收入丰厚,生活优渥,伦敦有房产,方便社交。达西迎娶没落乡绅姑娘伊丽莎白,和无地的彬格莱先生做朋友,而彬格莱的父亲做生意发财起家,表明彬格莱先生家世悠久,但不是贵族。
维多利亚小说中描绘的贵族,隐性含义为:豪宅,最少五十个仆人,丰厚的年收入,拥有议会权力和个人选区佃户投票权以及传统的巨大声望。在考察维多利亚小说的财产继承时,需全面考虑。维多利亚的贵族继承遗产和所有权,并不是在乡下继承几栋庄园,更像是继承一家拥有多种股权的大公司,且该公司必须运营稳定,不能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以保证几代人都拥有同样资本。因此在维多利亚小说或英国现实社会中,很多豪门家族日渐衰落,大量房产被用来出租,缘由财产和资本难以运转。
维多利亚贵族绅士之后,是有田产的士绅阶层,头衔称号为骑士或准男爵等。士绅有房产、收入和财产比贵族少很多,仆人只有五六个。士绅之下,是一群有趣且重要的“绅士”。在简·奥斯丁的笔下,绅士可能是士绅的儿子,或是未继承房产,但获得承诺,如《曼斯菲尔德公园》中的埃德蒙德·伯特伦;或父亲无头衔,靠生意发财而挤入贵族行列的后代,如《傲慢与偏见》的彬格莱。《傲慢与偏见》中的士绅们,倒也乐意把女儿嫁给没有地产的有钱人彬格莱,可见财富在维多利亚社会的重要性。
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位绅士每年需要大约20万美元生活费,才能维持身份头衔和日常生活。绅士无须工作,雇佣各种仆人如厨师、女佣、保姆和男仆,维系日常生活。服装专门手工定做,异常昂贵。在《远大前程》中,皮普成为绅士的紧要事件是花费20基尼购置服装。这表明,昂贵服装对于绅士地位的重要性。1基尼大约1磅多,20基尼折合到现今约为4,000多美元。皮普的继父乔看到价格后,几乎晕倒,这笔置装费相当于他一半的年收入。
维多利亚社会中绅士的服装价格昂贵,而仆人的工资少得可怜,人力比马力便宜。伦敦每年至少有10,000名女仆在找工作,年收入从6磅到10磅不等,包食宿。高级女仆每年12磅到20磅,厨师14磅到20磅,男仆15磅到20磅,管家最高大概为50磅。折合为现代美金,最低年收入6磅约为1,200美元,最高50磅大概10,000美元,仆人的收入确实菲薄。[8]105
维多利亚社会科技尚未普及,大部分底层工人在服务行业。1850年到1870年,仆人数量增加了60%,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穷人和富人两个阶层相互交融,中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崛起。狄更斯早期小说中表现的穷人和富人的生活联系是维多利亚生活的真实再现。19世纪的伦敦地图表明,城市中的富人区和穷人区相连,看似极端,实则合理。
细读奥斯丁的小说,可以看出维多利亚初期社会各个阶层地位相互流动、不甚稳定。每部小说中,都会看到房产转手,许多人的社会地位往往从绅士跌至底层,如《理智与情感》的达什伍德一家。在《爱玛》中,家庭女教师泰勒小姐地位攀升,成为有房产的女主人;而另一女士贝茨小姐则跌至寒酸境地。奥斯丁的小说印证了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论断:“阶层不是固定家庭,更像公共汽车或酒店,人员满满但人群不同。”[9]2319世纪早期,社会变革更多地体现于贵族和中产阶级之中。奥斯丁的小说证明,阶级地位看似稳定,实则是幻觉,因为婚姻和阶级在不断缓慢地变化。新晋家庭的适应能力如变色龙,只需一代,后代模仿贵族穿衣打扮、举止行事,成为上层人。在萨克雷《名利场》中,一名商人靠牛油发迹,儿子培养成绅士,女儿成了淑女,虽然上层人依然奚落他。但发财致富的商人们如若想在上层阶级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如此。
贵族和准男爵是英国社会的明星,中产阶级盲目仰慕他们。在狄更斯的《小杜丽》中,米戈尔斯先生不断吹捧贵族,但总是受到上层的羞辱。英国小说里很多资产阶级暴发户,不惜一切代价与有头衔的贵族交往。在《名利场》中,乔治5奥斯本很乐意将钱输给准男爵的儿子,只为让同僚们看到他们的交往。街道、住宅和物品也以阶级来划分。在《小杜丽》中,格罗夫诺广场以“高额房租出租不透风的小屋”,“因为这些房子非常抢手,房屋代理商便做广告,说它是本城区最高贵的地区里的一座体面的住宅,那是上流社会的名流才配住的地方。”[10]152
19世纪小说中英国社会阶级差距最大的是绅士和平民。18世纪的英国社会,绅士出身至关重要,绅士头衔代代相传,意味着财富、土地、教育和举止。19世纪,绅士概念不断扩大,重视财富、教育和举止,其次才是出身。托克维尔认为,从英国到法国到美国,绅士的演变反映了民主的发展历程,而英国人的绅士观使得英国免于流血的暴力革命。[11]539
19世纪社会中,绅士概念的扩展不再局限于传统含义。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本内特认为,自己与达西不相上下:“他是一位绅士,我是一位绅士的女儿;我们刚好门当户对。”[12]283由此可见,在维多利亚时代,绅士演变为平等和民主理想,在公众中获得了力量和尊重。在《远大前程》中,狄更斯描绘一位铁匠的学徒,只身出发到伦敦,最终成为一名绅士。狄更斯对于绅士的理解颇有意思,潜含他低层出身,其小说内容也是他最为熟悉的领域。
绅士作为一种社会阶层,在美国没有对等阶级,美国人很难理解绅士在英国阶层的重要性。莱昂内尔·特里林提出了类比阐释:获得学士学位预示着社会地位和经济前景,没有的人心存自卑。同样,18世纪末期的无名绅士处于上层社会底层,很多人相当寒酸,在美国相当于无名学院学士,而英国的贵族阶层则意味着拥有常春藤名校的声望和资源。[13]211
19世纪英国上层阶级的人员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它接纳了更多的富裕中产阶级,原因在于:19世纪英国的国民收入增加了8倍,通货膨胀较低,而人口增加了400%,更多人有资格加入。到19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商人晋升为贵族,下议院以土地为主的贵族人数下降。1865年,四分之三的席位被地主乡绅占据;到191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七分之一。士绅阶层则被资产阶级通过联姻而渗透。上层阶级人员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维多利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与财富
中产阶级与上流社会的区别,并不是财富收入较低,反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收入较高,主要区别是他们须为生计而工作。[1]23一些杰出的海外商人、官员和法官的收入与贵族相当,因此与贵族通婚。狄更斯的《董贝父子》中的董贝就是这样的商人,其家族生意追溯到18世纪,并因而与贵族阶层通婚联姻而步入上层阶级。
19世纪早期,中产阶级中最富有的是自耕农和佃农,但后来被制造商和商人所取代。中产阶级之下,则是银行家、商人、医生、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记者、作家,以及底层的低薪公务员、铁路人员、剧院人员、疯人院管理员等。英国的社会等级制度将传统职业,如律师、牧师和服务人员等列于首位。这些职业与绅士地位相称,因此绅士后代涌向这些职业;而雄心勃勃的成功的中产阶级,亦把这些职业作为跃入上层阶级的跳板。而贵族阶层对商业心存既定偏见,起初不被绅士认可。在商业中,收入差别巨大,高级商业和金融的财富明显高于工业收入。
到20世纪中叶,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数量从1803年的63.5万户,增加到1867年的154.6万户;中产阶级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60%下降到35%,也就意味着财富逐渐均衡分布。维多利亚小说展示出社会结构中的民主化趋势从极端走向平均。工人阶级开始分化为“体面基层”和“粗陋下层”,上层阶级又细分为地主阶级、职业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以及北方新型实业家和企业家。
中产阶级的特征是什么?首先,维多利亚时期有着严格的宗教道德规范,中产阶级强调努力工作、家庭为主和道德严苛。大多数中产阶级为非国教教徒(如卫理公会派、公理会派和浸信会派),也有较多英国国教教徒。事实上,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伦理道德植根于个人宗教信仰。其次,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受教育程度不同,中产阶级主攻非手工专业知识。再者,中产阶级家庭一般雇佣厨师和女仆,富有的中产阶级也雇佣管家和男仆。在萨克雷和狄更斯的笔下,描绘了那些拼命从中产阶级跃入上层阶级的男士,雇佣招摇的男仆,彰显个人的野心和地位。最后,中产阶级和劳动者的重要区别是中产阶级拥有一定财产,不从事体力劳动。
在维多利亚的小说和传记中,有着诸多中、下层阶级分化、向上流动的例子。詹姆斯·密尔是一位哲学家,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注]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译作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为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古典思想家和哲学家。詹姆斯·密尔的一生是社会阶层提升的实例:母亲是苏格兰的女仆,认识到儿子的聪明才智,获得当地乡绅的财力支持,送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并获得教堂圣职。他可能获得助理牧师或家庭教师一职,但这些职业使他难有闲暇去写作。然而,他娶了一位中产阶级女人,岳母管理一家疯人院,赠送女儿一笔丰厚嫁妆。这使得密尔获得财政自由,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英属印度史》。该书出版后,凭着个人专业学识,密尔于1818年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助理检察官,相当于助理国务卿的职位。密尔的升迁提供了维多利亚早期社会流动的缩影,通过乡绅财力支持,提升个人教育和能力,婚姻经济状况优渥。后来詹姆斯·密尔的儿子意识到19世纪最重要的阶层真相是:脱离既定的出生阶级。
四、维多利亚时期的下层阶级
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从经济财富划分阶级制度时,阶层是复杂的,但毫无疑问的是:维多利亚的中产阶级对底层感到恐惧,在青年时期从底层晋升到中产阶级的人,对出身一直感到羞愧。詹姆斯·密尔从未告诉儿子自己的个人出身;狄更斯也从未告诉妻子,童年曾在工厂工作,他的小说也证明,这是他一生中最令他不安的经历。
维多利亚时期庞大的下层阶级,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由工匠、熟练工人、不断增长的工业劳工、日益减少的农业劳工、家庭佣人、失业穷人、赤贫人口,以及疯子、乞丐、流浪者和罪犯组成。狄更斯的小说以这些群体为中心,其普遍特征为:依赖于资本家,生活、工作环境不安稳和工资较低。
工人阶级的住房狭小,其居住的社区和街道拥挤肮脏、臭气熏天。维多利亚初期的利物浦,五分之一的劳动家庭住在地窖里。在曼彻斯特部分地区内,一间屋子里住着十几人。由于就业机会受市场周期的影响,工厂关闭就意味着全体工人被迫步行迁移到新的城镇。工会成立缓慢,社会保障极低,工资就是最低生存水平,因此典当行在工薪阶层地区生意兴隆。除了少数高级匠人和熟练工人,工人阶层似乎难逃既定贫苦阶层的宿命。
恩格斯认为,工业化表现为四个特点:强化劳动分工、引进现代化机器、使用蒸汽动力和工厂密集化。密集化则表现在工厂系统和大型工厂城镇的扩张。狄更斯在《艰难时代》中,对于工业城镇科克镇描述如下:
镇上有好几条大街,看起来条条都是一个样子,还有许多小巷也是彼此相同,那儿的居民也几乎个个相似,他们同时进,同时出,走在同样的人行道上,发出同样的脚步声音,他们做同样的工作,而且,对于他们,今天跟昨天和明天毫无区别,今年跟去年和明年也是一样。[14]27工人阶级中最重要的划分是熟练或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一般需要七年学徒期,正如《远大前程》中皮普在锻造厂的经历。熟练工一般占劳动力的15%,受过低等教育,年收入50到90磅;非熟练工人年收入则不足50磅,未受多少教育。维多利亚时期还包括童工,是工业革命中的重要劳动力。到1835年,14岁以下的儿童占棉花劳动力的13%。[15]111工人阶级之下,则是靠慈善救济而勉强存活的穷人、流浪汉和靠犯罪为生的底层成员。
在维多利亚时期,无技能工人和失业人口居住于城市的贫民窟里,生活环境最肮脏,下水道污浊,霍乱、肺病、肺结核、斑疹伤寒、佝偻病、慢性胃炎等疾病肆虐。失业人员生活在恐惧中,被典当行和放贷者摆布。如果负债超过20英镑,就可能锒铛入狱。失业者极易坠入犯罪之路,和妇女走投无路时被迫成为妓女的情况类似。在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犯罪阶层存在于下层社会。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地区,另一个底层侧影是罪犯居住地,他们钻墙或房顶挖洞,警察追捕时,方便逃脱。维多利亚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对于城市贫穷和罪犯众多的反应大多是充耳不闻。“雅各岛”是当时伦敦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之一,由于房屋陈旧、下水不通等卫生问题,1832年和1848年霍乱流行。1850年,市议员彼得·劳里爵士宣称,雅各岛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狄更斯曾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通过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波茨纳普先生表明:“我不想知道它,我不去谈它,我不允许它!”[16]185
从1803年到1867年,英国家庭数量从200多万户增加到600多万户。人口剧增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家庭数量从100万户增加到450多万户。狄更斯的小说记录了维多利亚初期的数十年内,流浪汉和穷人数量剧增的现象。人口剧增意味着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到1851年,超过51%的人口居住在以伦敦为首的大城市中。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案通过时,英国大多数城市选民都是工人阶级;直到1893年,这个阶层才逐渐组织完善,成立工党。在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期,社会规模不断扩大,阶级“金字塔”变高变薄,这种变化不见得对下层阶级有利。因为社会顶层财富大幅增加,其余四分之三的家庭,共享不足五分之二的可用资源。优点则是社会逐渐趋向平等,不再等级森严。
然而,维多利亚的小说家并不是经济学家,不以统计学描绘阶级。作家笔下的阶级,体现在人物性格和社会环境,也体现在人物的各种经历,对于爱情、性、金钱、宗教、自我的态度中。人物的社会背景也反映阶级内涵:如住所、教育、家具、服饰等。迈克尔·伍德认为,现实主义彰显在物质世界之中,因此,维多利亚的经典小说必然反映社会的不同阶级。[17]25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描绘了罗莎蒙德·文西的华丽服饰,而狄更斯《小杜丽》中的玛吉则衣衫褴褛,富贵与贫困的对比,本质指向维多利亚社会的阶层问题。
本质而言,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人物,实则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个体代表。在《爱玛》中,奈特利先生被视为特定历史时刻的乡绅代表,社会变化被小说家所记录,读者亦可以比较同一小说家的早期和晚期作品,对比社会阶层的变化轨迹。从奥斯丁的第一部到最后一部小说,贵族阶层变化巨大,例如如何管理财产,处理国家事务,以及到何处度假。通过梳理这些细节脉络,可以看出英国维多利亚社会的结构和阶层演变。例如,比较奥斯丁1802年的《诺桑觉寺》的蒂尼将军和1817年《劝导》中的沃尔特·艾略特爵士,两部小说均描写了以温泉闻名的巴斯,短短数十年中,可见巴斯的社会习俗的变化——贵族举办的公众舞会被小型宴会所取代,意味着贵族迫于民主压力,逐渐从公众视野退于幕后。[18]57在《董贝父子》中,记录了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演变过程——工人阶层从之前的棉花工人转变为钢铁工人。在后期的《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狄更斯笔下的人物职业表明,伦敦的经济焦点从工业生产转移为金融体系,货币才是财富流通的主角。
乔治·艾略特如此评价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因为一切都以阶级和金钱为基础,除了个人内心激情的利己主义,其他皆为悲剧。英国小说的传统形式中,很少描述抽象悲剧,换言之,悲剧体现在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在奥斯丁的小说中,宗教视角实则为阶级角度,小说人物的死亡,并不是生命意义的重述,往往是继承遗产的机会。美国评论家亨利·詹姆斯批判道:某些19世纪的英国小说家过于“庸俗”——只关注和描述急功近利、野心勃勃、胜利在望的主角。[19]109对于维多利亚小说家而言,他们大都会被詹姆斯的此番言论逗乐,甚至当作是一种恭维。换言之,只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们,才有能力描绘英国各个阶层的生活状态和思想精神。而他们之所以被逗乐,是因为詹姆士的粗鄙,他没有机会和经验描绘英国各个阶层的言行举止。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意义,大概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