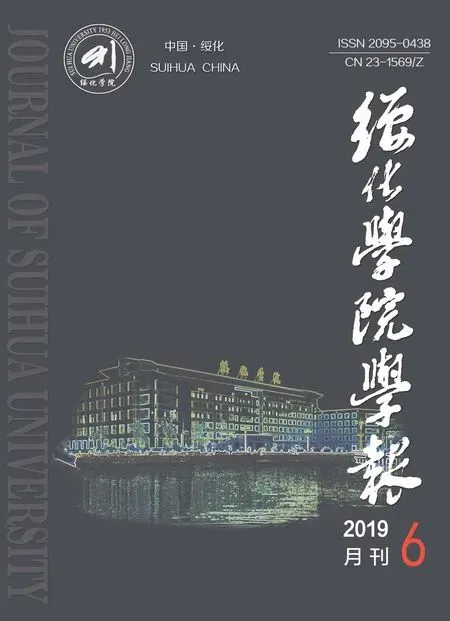主题视阈下的电影改编机制
——《归来》对《陆犯焉识》的改编研究
卫琳琳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81)
《陆犯焉识》是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笔下具有颠覆性意义的转型之作,小说通过讲述知识分子典型陆焉识在历史与政治洪流挤压下遭遇的无尽人生悲苦,寄托着精神独立与自由的人生诉求。据此改编的电影《归来》是张艺谋执导的文艺片,影片截取陆焉识劳改释放、回归家庭后的生活片段,谱写了一曲文革伤痕下饱含温情的爱情悲歌。
一、自由到爱情的主题简化
(一)自由与爱并行的人性关照。严歌苓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主体作“雌性”书写,以温情悲悯的笔调叙述女性在生活夹缝中承受的苦难与人性的崇高。而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则以祖父严恩春的人生遭际为原型,奠基于对家族史的探析与自我解剖,首次以男性为主人公展开叙述,通过孙女学峰的主叙述视角与陆焉识的日记式回忆视角,将自由与爱的人生探寻作为小说的双重主题与人物灵魂所在,对知识分子倾注浓厚的人文关怀,以此深掘丰富深邃的人性。自由是陆焉识一辈知识分子倾其一生追寻的精神家园,小说书名的确立经《浪子》《无期》等以人物特性为出发点的设想到《陆犯焉识》的最终定题,“犯”字的点睛之笔与自由相对,代表着陆焉识一生在不同形式囚笼中的生存境遇,既是劳改时期有形的人身监禁,也是数十年独自对爱情的反思咀嚼中,怀着愧疚的赎罪心理对妻子与家的无形忏悔,同时也借此审判时代与民族记忆中人性的污浊与纯净。其精神自由的缺失蕴藏在传统包办婚姻的操控、学术界勾心斗角的倾轧与西北荒原时期政治人身自由的失语中。
陆焉识的人生经历过三段爱情,在妻子冯婉喻的数十年等待之外,一份是留学期间与意大利女子望达的自由恋爱,是青年时期以接受婉喻的婚姻不幸换来的自由,二是避难期间与重庆女子韩念痕的恋情,是他中年时期从逃避家庭的琐碎生活中获得的自由,两份恋情都以回到婉喻身边结束。而陆焉识对冯婉喻的爱情也超乎他最初对包办婚姻本身的抵触和想象,留学归国后他瞒着恩娘带婉喻看梅兰芳的戏,以出差为由与婉喻度蜜月,两人在恩娘监视下形成看眼色行事的默契。而在西北劳改的20年里,他为婉喻盲写只有彼此能理解的书信,在对人生的咀嚼与反刍中回味家庭生活的幸福,反思、痛恨自己曾经的背叛;陆焉识在千里逃亡的计划中步步经营,只为能看婉喻和孩子一眼,忏悔自己曾经的出轨行径,对婉喻的思念成为他非人境遇中唯一的生存理由;陆焉识也在因逃跑为家人带来政治身份困扰时选择自首,冥思苦想出离婚协议书的解脱方式。自由是陆焉识人生中最为执着的信念,也正是在追逐自由与自我解剖中完成了对爱情的领悟与坚守,在追寻自由途中领悟了爱情,也在寻爱中获得最后的精神自由,两种主题的发展在小说中相辅相成。
(二)《归来》的爱情叙事。电影《归来》简化小说的多义性主题,保留并强化了爱情的单一元素。张艺谋曾在专访中自述道:“《陆犯焉识》的小说有一种寓言感,我很喜欢这里边有各种可能性。我说这个故事,是把历史沉淀到一些生活细节中,然后表象的是一个爱情,是一个厮守。”“其实你看整个故事,删繁就简来看,它无非就是一个归来的故事。你可以不去讲政治,不去讲文化,只讲人和人的故事,其实就是这么简单。”[1]电影以爱情为主线结构影片,对陆焉识的人生经历与政治背景采用空白手法,将“归来”意象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核心故事情节包括两次“归来”,一是陆焉识作为逃犯看望婉瑜的短暂归家,却因女儿丹丹的告密与妻子失之交臂;二是文革结束被释放、恢复政治自由后回家寻找记忆的归来,年迈的陆焉识陪伴失忆的妻子冯婉瑜在漫长岁月里等待爱情归来的故事。同时影片创造性地转换了小说中寻得心灵自由的结局,代之以焉识在风雪中无止境地陪伴婉瑜等待自己归来的留白性结局,衍生出文革的政治暴力对人性造成无法磨灭伤痕的批判性主题,而非传统影片大团圆的创造风格,伤痕背后的文化失语引人深思,是架构在革命历史年代之上的人性、温情、淳朴爱情的回归。影片题目“归来”兼具多层含义,有陆焉识劳改释放归家的行为层面的归来,面对时代与历史物是人非的面貌依然坚守爱情的情感归来,更是导演张艺谋在商业影片领域对前期真诚朴实风格的回归。
二、文学与电影的媒介差异
首先,电影与文学归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文学的传播媒介是抽象的文字符号系统,而电影是由画面与声音组合的视听符号系统。文字符号与视听符号反映对象的途径不同导致读者与观众接受效果的差异,因此作为传播受众的审美感知也不同。电影以表象的手段直接诉诸大众,接受者能感知其更为固定的本原状态,从而带给观众真实直观的视听享受,而文学则是含蓄的审美体验,借助高度抽象概括的文字激发读者记忆存储中的个体经验与思维形象。正如乔治·布鲁斯东在论及小说与电影的根本差异时,指出小说与电影的意图都是让人“看见”,但二者的方式不同,“人们可以是通过肉眼的视觉来看,也可以是通过头脑的想象来看。而视觉形象所造成的视像与思想形象所造成的概念两者间的差异,就反映了小说和电影这两种手段之间最根本的差异。”[2]小说因文字语言与主题蕴藉的丰富性属于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表达,而电影的呈现更为通俗简洁,是从精英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的过程,在表达沉重历史感的同时也能传递温情。
小说在文学接受过程中靠个人阅历、想象力的发挥理解其内涵,而电影则受杂糅因素影响间接作用于观众的审美效果。电影中特定环境的选取在表现人物性格、人物关系、生活工作等方面能够营造相应的视觉氛围,通过连绵的雨雪天气、秋冬季节渲染悲凉肃杀的气氛,为电影叙事营造一种时缓时急的节奏感,文革时期的被迫分离与时代伤痕暗示主人公精神世界的悲惨命运,以此奠定影片的悲情基调。影片的色彩设计以平淡内敛的灰色调为主,打造历史感与年代感,偶尔缀以象征革命的红色,色彩的交错丰富了影片画面的层次。同时,音乐与画面的融合有助于特定情感的孕育,“影片里的音乐不仅仅起艺术上的作用,它还能使画面给人以生动自然的印象;音乐给画面以气氛,并使画面仿佛具有第三度空间感。”[3]如陆焉识作修琴师为婉瑜弹钢琴试图唤醒其记忆的画面,钢琴曲《渔光曲》的音乐选取优雅舒缓,拉长电影缓慢的叙事节奏,它既是年代属性的象征,也在影片中为情节发展提供契机与推动效果。
其次,文学与电影在叙事表达上的差异有历时性与共时性之分。小说与电影改编的实质都是在一定时空内展开故事的线性叙述,但小说作品大多以时间为线索结构全篇,叙事时能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自由穿梭,其想象时空由观众任意建构,而电影则需要明确的时间、空间量度标志,主要以空间形象的逻辑关系作为叙事线索,共时性特点更为鲜明。文学作品中涉及政治历史时空的文字语言不适用于电影的语言表达,长篇小说的故事盘根错节,叙事时间跨度长,电影有限的容量也难以承载,因此,导演对电影的二次创造便结合自身经验打造全新的影像时空环境,调整原著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
《陆犯焉识》全篇长达36.5万字,严歌苓结稿后也称“终于写了一部抗拍的作品”。小说在政治与历史的宏大背景下,通过留美博士、精通四国语言的知识分子陆焉识跌宕起伏的60年人生,表现对自由与爱的精诚追逐。两条并行的时间线索贯穿全文,一条从陆焉识在西北草漠劳改的生活开始,到释放回家后为获得精神自由而复归流放地的结局,另一条从青年时期的包办婚姻到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监禁、劳改为止。两条线索相互交叉出现,叙述极为灵活,让读者自如游走于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段。而电影则偏向于空间表达,《归来》的影片时长111分钟,在有限的叙述时间与地域范围内选择了陆焉识“归来”之后的故事。小说中的陆焉识流连于青壮年时期的繁盛地上海、美国、败落时被禁锢的西北荒漠,以及抗战时期的避难所重庆,而电影则将故事的讲述定位于中国北方阴雨连绵的某城市,甚至将镜头集中于“家”的地点,地域的高度集中更易突出情感主题的表达,同时将人物简化为陆焉识、妻子冯婉瑜与女儿丹丹的三元结构,整体风格都遵循极简主义。情节选取是文学作品改编的关键,影片依据小说意图表达的主题展开主要线索与冲突。小说囊括陆焉识青年时期到老年漫长的60年人生跨度,而张艺谋则以小说的后20页为基础展开想象,改编时忠实地保留了小说的核心人物、强烈的戏剧冲突与情感表达,结合影像造型与声音、画面等元素,在主题表达上不断创新,将电影艺术的观赏性与文学性有机结合,实现文字精神化的描述语言到影像视觉化的成功过渡,与鲁迅《故事新编》中“选取一点因由,渲染成篇”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电影也擅长采用蒙太奇的镜头组接手段,在电影叙事中担负拼接历史与现状的叙述功能,使电影艺术获得异于文学的反映生活的巨大可能性。
三、导演话语的个性化创造
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擅于运用细腻的镜头语言,使电影背景触及整个历史社会,力图将个人经历与感受放大到社会层面,符号化地呈现中国社会的全貌,具有浓郁的本土文化色彩,因此电影作品的主观性、象征性、寓意性较强烈。张艺谋是20 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之一,以独特的电影创作风格挖掘民族文化底蕴、探索时代演变精神。在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上,张艺谋强调文学之于电影艺术的重要意义:“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作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4](P73)
《归来》是2014年张艺谋加盟乐视后的第一部改编作品,电影改编涉及叙事视点与叙事方法的改变。小说的叙事主体由“我”和主人公陆焉识共同承担,在陆焉识的回忆式叙述之前,先由“我”的少年视角引出“我祖父”的故事,叙事视角的重叠产生了双重离间效果。而影片中则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视点,观众无法感受第一人称自叙时近距离直观人生的体验与态度。同时,影片用字幕的方式暗示叙事重心的转移,银幕上的“三年后”、“很多年后”构成影片的线性叙事线索,淡化了小说中40年代的抗战与解放、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与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时间关节,而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命运悲剧反衬时代留下的伤痕,影片用一种委婉含蓄的隐喻实现了对历史的反讽。
对影像风格的极端重视是张艺谋改编创作的主导性因素,他曾表示:“我在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时候,尽量使形象视觉化,假使做不到视觉化的话,那么根本无法去拍摄电影。”[5]电影对小说的重塑包含导演丰富的个性化元素。在电影中,色彩的主要修辞功能是通过突出和强调,即在色彩的对比与变化中展现导演的思想和创作意图。[5](P31)色彩是电影画面的重要表意手段,影像色彩中擅于运用红色是张艺谋电影改编中独特的艺术风格,如,90年代的《红高粱》以红色场景作总基调,象征热情奔放的生命力与自由的人性,烘托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以红灯笼的意象为线索贯穿全片,而《归来》中丹丹对芭蕾舞蹈《红色娘子军》的热爱与一袭鲜艳的红衣独具象征意味,是与父母亲情冲突的起因,也是革命年代的符号化象征。张艺谋运用红色的特殊审美作影片的唯一亮色,用以隐喻革命年代的文化背景,与全片的灰色基调构成强烈反差,讴歌人性,体现中国传统符号的艺术之美。
火车站意象作为特定线索贯穿整部影片,与归来的主题相呼应。剧中的两次“归来”都与火车站紧密相关,第一次是焉识逃亡归来,与婉瑜在天桥上生别的匆忙相见,第二次是刑满归家,重获政治自由的归来,由转行做织厂女工的女儿丹丹接回家。此后,失忆的爱妻冯婉瑜每月初五亲自到火车站等待心中的陆焉识归乡,直至影片结尾的多年后,镜头定格婉瑜在陆焉识的陪伴下保留的接站习惯,电影以等待归家的循环书写,营造一种归来未果的悲戚氛围。而火车站在影片中重复出现六次,不仅是陆焉识数次归来的转折点,也喻示着故事走向与情感蕴藉,承载着巨大的希望与绝望,是婉瑜对焉识情感寄托的载体。
四、市场经济与主流意识形态制约
文学著作改编的影视作品往往上座率不俗,解构经典成为市场经济导向下的潮流,张艺谋选取《陆犯焉识》这类文学作品作为改编题材也是市场需求下的产物。同时,导演在市场化浪潮下对电影改编领域的探索离不开票房收入的衡量,相较于小说而言,电影与大众市场的联系更为密切,观众的反响与上座率直接决定电影的命运。影片的制作生产需要票房价值的经济回馈,涉及较大的资本投入、利润回收与再生产问题,因此电影艺术受制于商业运作规律与艺术创作规律的双重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代表国家强制性的意志,国家电影电视总局即代表国家意识形态,扮演“把关人”的角色。电影作品作为现代大众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个人化表达的空间之外必然要体现统治集团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影片内涵无法脱离阶级意识与时代思潮的制约。如电影对文革敏感历史的规避与隐性表达,影片并未直接表现历史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而通过男女主人公最终未能相认的命运悲剧反衬时代遗留的伤痕。同时影片也暗含对人类道德伦理价值的维护,《归来》中丹丹因芭蕾舞剧的主角争执与父亲陆焉识划清界限、告发父亲的行为存在道德方面的缺失,多年后由丹丹主动认错并帮助陆焉识唤醒母亲的记忆,其中不仅包含自我认知的变化、亲情的推进与升华,更暗含社会和国家意识所号召、认可的主流。
电影与文学的生产机制与生产方式不同,两者在生产接受层面的区别直接影响电影改编效果,改编者在操作过程中既不能一味追随商业目的与大众的媚俗欲望,也要防止轻视大众的精英姿态,把握雅俗之间的创作尺度。在接受美学家眼里,文学作品是不完美的暗示,是对读者的邀请。小说形象的生成是读者在作品文本指引下结合自身经历与审美情趣的再创作过程,是想象力加工下的二次创造,阅读者容易接受的是与认知能力、审美趣味相应的艺术作品。而电影通过演员的演绎直接呈现在荧幕上,是演员对角色性格的理解、导演的审美经验与造型师的艺术手法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的具象化拒斥观众的想象。正如《归来》对原著的处理中弱化其政治背景,用爱情叙事取代对历史的关注,转向于表达亲情、爱情一类大众偏爱的温情主题。
影片《归来》于中国内地公映后即面临褒贬不一的巨大争议,支持者认为影片大量删除原著情节,使电影具备极简主义风格,有限的情节集中在高密度画面中,“归来”的意象得到反复渲染和叠加,同时电影以含蓄的手法揭示了历史的创伤,渲染了浓郁的悲剧意味。而批判者则指出电影抽离了时代背景,以小情小爱消解时代伤痛,观众很难产生共鸣,具有通俗剧的基本元素但戏剧性不强,保留过多背景的空白需观众自行填充,政治话语不足易造成大众的误读与理解的缺失。但从文学作品之于电影创作的意义而言,文学作品是影片改编的源泉,电影改编在忠于原著基础上有所创新,既是作为传播者的艺术追求与个性化创造的表现,也是市场化对电影创作方式的引导。电影改编使文学实现了从纸质传媒到影像化传播的跨越式转换,在扩大文学传播空间的同时丰富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影像化改编是文学作品传播的重要走向。
结语
在文学泛化的语境下,电影改编的实质是影视艺术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与再生产,以视听方式在银幕上重现文学原著的艺术世界。张艺谋对《陆犯焉识》的改编是革命性的,他在服从文学基本特性的原则基础上,张扬自身独特的电影风格与艺术个性。本文以小说与电影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本为基础,文学与电影的传播媒介差异、导演作为传播者的个性化因素、传播受众角度的市场经济与主流意识形态三方面相互作用,探究文学作品改编为电影的机制与策略。通过阐释电影《归来》改编的新视点与研究空间,力图深入发掘文学作品改编的魅力,探索当代电影改编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