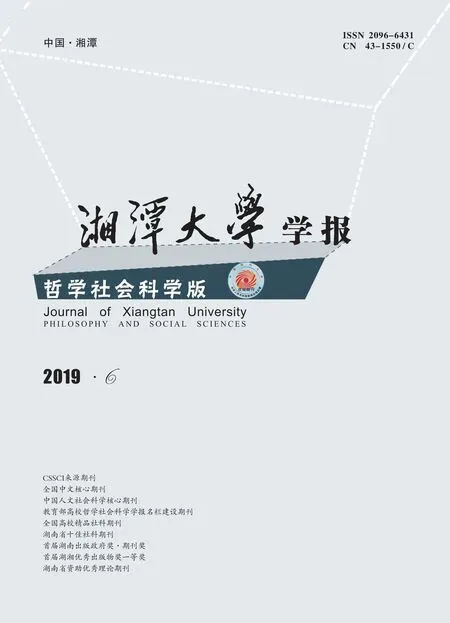镜与灯:本体论视域下王国维与况周颐求“真”词学观比较*
刘晓丽,杨 雨
(中南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长沙 410010)
引言
王国维与况周颐是清末民初非常重要的两位词学家,一位被誉为近代词学的开创者,一位是传统词学的结穴,《人间词话》和《蕙风词话》作为两人词学思想的代表被誉为“晚清词话的双璧”。关于两位词学家的研究蔚为大观,其中,彭玉平、王攸欣对王国维,孙克强对况周颐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而就两者进行比较,尤以杨柏岭的《况周颐、王国维词学思想比较研究》这一篇颇具代表性,他提到两人对“真”这一范畴理解的异同,强调他们对“赤子之心”和“艳词”的认同,况周颐对艳词的肯定是儒教君臣之义的影响,王国维则是在艳词上看到了缕缕生活的意志[1]。王鸳的硕士论文《况、王词学真实论比较研究》从词史观念、创作方法等方面比较两人以“真“为核心的词学思想的相通和相异之处,并探讨导致差异的原因[2]。杨柏岭比较的是况周颐、王国维二人的词学思想,对于求“真”只略作论述,并没有深入展开;而王鸳的论文重在通过文本互读比较两人的差异,原因分析虽涉及词体偏好、知识结构、审美宗尚等等,但是都泛泛而谈,分析不深入细致,且原因分析缺乏一以贯之的核心关键词。笔者在对他们的差异进行梳理分析时发现,在两者不同的学识背景和不同的人生选择背后,词学审美范式、求真路径以及有关情景表现的物我关系的思考上所体现出的差异都可以通过再现与表现这一对范畴来观照,从认识论以及文学本体观的角度来看,再现与表现可以借用艾布拉姆斯有关“镜与灯”的隐喻来表达,再现有如镜子,强调文学客观反映世界;表现有如灯光,认为文学是借由主体内心的烛照来认识和显现世间万物。本文在此借用这一组对比来形象描摹王国维与况周颐在中西文化影响下词学本体观的特质,以再现与表现为视角,审视况周颐与王国维“求真”理念的差异,以深化对况周颐和王国维词学思想的认识。
一、王国维与况周颐共同的词旨——“真”
“真”这个范畴,在西方多指认识之真,导向的是科学,中国人则多用以指性情之真,导向的是伦理。具体来说,儒道两家对“真”的理解也有不同。在儒家来说,它指那种符合善的主观情感,也包括客观真实。道家的“真”则是与“伪”相对,重视伸张人的本性和与自然、天地相合的真性情[3]87—88。本文所涉及的“真”不仅是反映在词学批评标准中的对景真、情真的描述,而且是对文学本质的体认,甚至是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蕙风词话》和《人间词话》中以“真”为核心的词评标准已得到学界广泛的讨论和认可。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曾多次提及“真”字:“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为佳,且易脱稿”[4]14;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强调的“真”与其“境界说”也是一脉相承的,“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5]59两人都继承了中国传统词学的缘情精神,肯定了真实情感在艺术活动中的显著地位。
王国维和况周颐二人对“真”的态度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二人对艳词的态度上,他们认为从求“真”的角度来看,艳词往往会流露出词人的真实情感。王国维本人不少艳词写得精彩动人,一往情深,他认为所谓的艳词(即爱情词)可写,但必须写出真情实感、动人心弦,绝不可轻薄淫狎。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5]245他称“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为“真”,正是因为这种“淫鄙”是人类内在本性之“欲望”的表现,是人性的“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5]316。他还曾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5]147其所谓“神”就是真情实感所体现出的深意。况周颐同样也极度推崇艳词,不仅自己喜作恻艳之词,认为这是词之本色,而且在词学理论研究上对艳词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叶嘉莹曾说:“关于艳,我以为在历代词评家中,当以况周颐对之最有深切的体认,且作过大胆的肯定。”[6]164况周颐《蕙风词话》中多次提到《花间集》,评其中的欧阳炯《浣溪沙》时云:“‘兰麝细香闻喘息。绮罗纤缕见肌肤。此时还恨薄情无?’自有艳词以来,殆莫艳于此矣。半塘僧骛曰:‘奚翅艳而已?直是大且重。”[4]56况周颐肯定王鹏运(半塘)的说法,将《花间集》的恻艳引申为“重拙大”,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艳骨”这一范畴为艳词正名,如:“程颂万《美人长寿庵词》……清而不枯,艳而有骨。”[4]546“何为艳?情从艳出,词中极尽男女之情事;何为骨?真字是词骨,真乃生命之真,凸显人之为人的最真实的生命本体,富有生命哲思,而情艳又有此思想之骨并表现为或秾词丽句或清语丽质的文辞形式,则为艳骨,否则便是艳而无骨。”[7]况周颐认为艳词体现了人之为人最本真最自然的真实情感,这是 “风骨”转而成为“艳骨”的关键所在。
在共同的求“真”观的影响下,二人对李煜都推崇备至。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不必学唐五代词中)中提到“其铮铮佼佼者,如李重光之性灵,韦端已之风度,冯正中之堂庑,岂操斛之士能方其万一?”[4]41言下之意,李煜的性灵不是一般人能学至。在况周颐看来,“性灵”是表达自我的“最高真实”。他诠释“顽”与“拙”字,“若赤子之笑啼然,看似至易,而实至难者也。’”[4]250他对“顽”和“拙”字的解读体现了他对“赤子”般至真至纯之情的激赏。王国维也同样强调“赤子之心”,他评价李煜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所长处。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5]101两人都提到“赤子之心”,也正印证了李贽在“童心说”中所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卷三)
二、王国维与况周颐“求真”观念的同中之异
王国维与况周颐在求“真”思想上有着相同的旨归,这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真实情感表达的一脉相承的传统。然而他们对“真”的理解也因为各自不同的境遇、学识背景和文学本体观而有着不同的表现,下文将从词学审美范式、词学创作方法两个方面来审视二人的求“真”观:
(一)词学审美理想:有境界与重拙大
南北宋之争贯穿清代词学整个发展过程,王国维与况周颐在这一问题上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词史观念和审美标准,这其中也内含着两者对理想审美境界之要素“真”的不同理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就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5]1他认为:“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5]《人间词话未刊稿》255五代、北宋词符合王国维最高的词学审美理想,而南宋词已沦为馈赠礼品,失去真情,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5]191王国维看到当时词坛学姜张者流于浮华,学梦窗者,流于晦涩,针对词坛弊端提出来尊北抑南的主张和审美倾向,通过五代、北宋所呈现出的“境界”传递他的词学观。关于“境界”说的解读众说纷纭,如叶朗认为王国维所阐发的无非是情景交融、真实再现、文学语言形象感等意思,是属于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说”[8]609—624的范围;而佛雏认为王国维之所以标举“境界”,是因为“神韵”等概念主观性太强,不讲再现,强调境界则可以补救其客观性之不足[9]235;王攸欣则从中西哲学辩证的角度解读,认为“中国传统文论谈的都是经验论的,作者主观感受的和读者主观感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构成文学的根本的东西,文学根本的东西就在于客观的对象,他所描述的对象的本质。王国维的探本之说就在这里”[10]177。论点各有千秋,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对真景物、真情感、情景交融、自然浑成的追求。五代、北宋词流畅自然、浑然天成、至真至性,正是王国维心中“境界”之最佳写照,正是“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写景也必豁人耳目,……无矫揉妆束之态”[5] 226,读之“语语都在目前”[5]172。
事实上,况周颐对南北宋之争的态度并不像王国维那样偏执,他在《蕙风词话》说:“词学权舆于开、天盛时,寝盛语晚唐五季,盛于宋,极盛于南宋。”[4]390学界大多凭此句认为况周颐尊南抑北,而其弟子赵尊岳在总结他的词学思想时说:“词学以两宋为旨归,正其始,毋歧其趋可矣。”“举《花间》之闳丽,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与三者有合焉。”[4]651这证明况周颐对唐宋词的评价持开明宏通的态度,认为南北宋各有千秋。但况周颐又说 “唐五代词并不易学。五代词尤不必学”[4]41,在对朱淑真和李清照的评价中说 “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 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沉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4]191。他认为五代和北宋词的佳境和风格是由当时的风云际会所决定的,时代和环境已改变,后人难以学至,不可复制,出于词坛纠弊的初衷,“唐五代词的流丽华艳是不可学的,北宋词的清空疏淡是不易学的,南宋词的沉著寄托不仅是可以学的,而且又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推广的必要性。”[11]所以,况周颐“尚南”,且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4]6。“重拙大”是常州派的理论主旨,“重”是诚挚的思想感情和深刻的思想所体现出的气格;“拙”是真率、真挚,是基于真情的质朴;而“大”是事小而意厚、词小而旨大、身世之感通于性灵的寄托”[12]。归根结底,二人的不同尊尚其实最终是由于王国维与况周颐在求真过程中所标榜的审美理想不一样,一个是纯任自然的“有境界”,真实的情景交融自然会有意境、有格调。一个是“重拙大”,在追求真挚表达、合乎性灵基础上追求词作思想的深厚博大。
(二)求真路径:自然白描与比兴寄托
王国维与况周颐不同的词学审美理想对应着不同的求真路径,而两人对吴文英迥然不同的评价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们的分歧,我们可以从两者对吴文英的批评上窥见他们的不同。
王国维痛诋吴文英词: “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5] 《人间词话附录》381“词忌用替代字。……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5]150“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5]165对于提倡“语语都在目前”、强调“不隔”的王国维来说,吴文英雕琢、代字、用典晦涩成了他倡导自然天成的真境界的反面教材。他说:“美成《青玉案》(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请圆,一一风荷举。’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5]157他认为此词自然白描体现荷花的真实神韵,自得境界。他强调:“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5]228他所推崇的是 “自然” 天巧, 如纳兰容若般“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5]213, 如“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5]《人间词话未刊稿》285。王国维认为吴文英雕琢、浅薄,他对强作寄托之解释深恶痛绝,说“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处,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5]296他认为飞卿、永叔、子瞻触景生情、触物起兴,自然有意境有气格,如果铺排、用典、雕琢,极尽外在人力去寻求宏大的寄托,不真实、不含蓄也就失去了意格和美感。
与之相反的是,况周颐对吴文英推崇备至。“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梦窗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非若琱蹙绣,毫无生气也。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力。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梦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4] 98这里况周颐对吴文英的密丽艺术特色十分推崇,并且强调艺术技巧上的密丽容易学至,但是其情感内涵的深厚博大后人难以企及。他还说 “梦窗与苏辛殊流同源”[4]99,其弟子赵尊岳的解释颇有见地:“重大之语,重大之字,重大之意义,极不易入词。然能加以驱使,转使词味益为醇厚,又不见斧凿痕迹,此固非笔圆气厚者不易工之。”又卷一云:“词知雅入而厚出,则思已过半。雅入,由外而内,藉文藻以写性灵,是谓词章。厚出由内而外,寓性灵于文字,谓之骨干。不雅入,其失在表;不厚出,其纤在骨,尤犯大忌。”苏辛虽豪纵,梦窗虽致密,皆得雅入而厚出,此所谓“实殊流而同源”[4]100。况周颐认为:“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即倚声家言自然从雕琢中出也。”[4]302上文的“驱使”和“不见斧凿痕迹”是对“自然从雕琢中出”的绝好诠释。这些都在说明况周颐对梦窗艺术表现力和词作内涵深度的充分肯定。况周颐将梦窗词作为诠释“重拙大”有寄托的范例,认为梦窗词沉厚有气格。
三、词学本体观:“无我之境”的再现与“尽其在我”的表现
王国维与况周颐所推崇的“真”境界,都强调“情景交融”,这是中国传统意境论的共识,他们求真的词学思想同中有异,异中又有相通之处,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各自的词学本体观中去探寻:
(一)物我关系
求真就是要写真景物、有真感情,创作过程必然要牵涉到审美主体“我”与客观外在“物”的关系。所以,对于“情景关系”的探讨从深处探究,实是“物我关系”。我们要探寻王国维和况周颐二人求真观的差异根源,首先从二人对“物我关系”的认识开始。王国维有著名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论述:“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5]19王国维也提“有我之境“,但是更推崇“无我之境”。王国维推崇的“无我之境”并不是作者不在场,而是把词人的主体性掩于天地之间,让客观事物的“真”和“美”自在显现。学界关于王国维受叔本华影响的论点早已成为共识。叔本华说:“真正的艺术品惟从这样的领悟(按:指审美的领悟)中产生。它们的恒久的价值和常新的(获得)赞赏,正源于这一事实,即它们表现了纯客观的要素。”[13]342所谓“纯客观的要素”指的是审美客体的内在本性、本质力量,实即上述客体的“理念”,主观表达是以纯客观为基础、为原点的。这一段话很好地解释了王国维的境界说的真景物和真感情之间,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王国维认为在词作呈现的境界里,“景”与“情”都是对客观真实的直观反映。“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体现了植物的生机、春意之盎然,从一枝具体的红杏上升到所有的红杏,所有的植物共同的生命力的体现,这是对富有生命力的植物之共同本质的再现。此时的创作主体是保持一种审美静观的姿态,并没有把主观之感情投射到外界之事物上,而是抛弃了功利杂念等个人欲望、意志的牵绊,是审美主体处于一种抛去功利的审美静观、本质直观。
况周颐一直传承中国传统的文学表达方式,以个人心灵为主旨和原点,表现外在景物和情景融合之意境。他直接谈景的论述不多,“宇内无情物,莫如山水。眼前循山一径,行水片帆,乃至目极不到,即是天涯。古今别离人,何一非山水为之间阻。”[4]221他认为山水皆为无情物,是词人主体赋予其情感,山水本无意,是词人自身被山水阻隔,赋离情别绪于山山水水。玄修《蕙风词话诠评》:“处当前之境界,枨触于当前之情景,信手拈来,乃有极妙之词出,此其真乃由外来而内应之。若夫以真为词骨,则又进一层,不假外来情景以兴起,而语意真诚,皆从内出也。”[4]14据玄修的理解,况周颐以“真”为词骨,在审美主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是注重由内而外,由主体观照客体的。他认为词人的主体作用远远大过客观事物的呈现,是主体对客体的观照下产生的美。况周颐强调审美主体的主导作用,实是“有我之境”,这与王国维境界说所提倡的客观再现是有区别的。
(二)主体情感与“真”“善”之关系
我们再来看 “真情”。关于真感情的描述,王国维提到主观之诗人李后主。单从字面意义看,王国维推崇的李后主是主观之诗人,这与他一再强调的“无我之境”是否矛盾呢?佛雏对此做过解释:“‘主观之诗人’并不意味着在挥毫时凭恃其主观,就审美与创作的态度而言,就抒情内容所具有的普遍性而言,‘主观之诗人’ 及其感情倒应该具备充分的客观性。从王氏把据传是后主‘后身’的纳兰容若,称之为‘自然之眼’也可以证明。纯客观之眼也,这样的‘主观之诗人’最能摆脱个人意志、欲望、利害关系等等的羁勒与奴役,而‘自由’的进入审美静观,因而独能客观的‘静观’交织在一起。往往具有‘人类之感情’的性质,虽然是高度‘个性’化了的。”[9]286这与上文叔本华的“纯客观的要素”的论述似乎不谋而合。李后主也是用个性化的真性情的方式再现了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情感之美,人的本质理念之美,即王氏所说“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才会如此打动人。因此,王国维的求“真”思想里,推崇“无我之境”所透露出的审美之真是客体意志和本质的再现,也是创作主体作为人的本质理念的显现,而不单纯是创作主体个人情感的显现。王国维认为创作主体在创作时应首先“入乎其内”,对外在事物倾注其中,但又不能停滞于此,而是应该“遗其关系”,“出乎其外”。要先“入乎其内”,“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优乐”,而后“出乎其外”,“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5]243,也就是超越个人情感。在王国维看来,陶渊明标榜的“悠然现南山”的“无我之境”的背后其实是陶渊明“忧生”底蕴之上的“超然”[13]。王国维所倡导的“无我之境”其实是在“入乎其内”的“有我之境”之基础上,抛却杂念而达到的澄澈如镜的审美直观。当他表达的情感已超越了一己之私,那么也就再现了“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人类全体之普适性的情感本质,从而具有了“善”的意味。
返观况周颐,他在评陈以庄《菩萨蛮》时说:“所谓尽其在我,何也?然而以谓至深之情,亦无不可。”[4]97并在洪文惠《盘洲词》一则中说“委心任运,不失其为我”[4]76,这里引用了《论语》“古之君子,尽其在我”,强调“我”的主体作用。《惠风词话卷一》中 “吾”字出现了36次,可见在真景真情中,主体“我”占据的主导地位。况周颐在讲到借鉴前人名句时说:“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咏玩索之,吾性灵与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4]21他将“性灵”与常州词派的传统“寄托”说结合,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已。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略无变化之陈言耳”。“触发于弗克自已”即心中有不能控制之表达的情感,而不是先外在地定一个宏大的寄托,文以载道。他所强调的寄托是从性灵流露而出,绝非有意寄托、有意比附之作可比,寄托之“善”是不能逾越“性灵”之“真”的基础。与王国维相比,况周颐更强调 “尽其在我”的“有我之境”,强调“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国维对“真”与“善”的追求是以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超越个人的忧生忧世,隐匿个人的一己悲欢,反映人类的普适性情感,以“真”为基础,最终超越“小我”转向“大我”的“善”。况周颐反躬自身,不管是汲取名家名句的精华还是追求“重拙大”之寄托,都以极带个人色彩的性灵、胸襟来涵养和表现,最终,“万不得已”之个人抒写因其真挚而达到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鸣,路径不同,本体观不同,却殊途同归。
(三)本体观:再现与表现
“再现”与“表现”两个概念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学本质论——再现论和表现论。再现论认为文艺是客观现实的再现,这个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模仿说”;表现论认为文艺是作家心灵的表现,着重抒发人的志向和情怀,在艺术上就要求自我表现。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两种本质论也即是表现手法都不是截然分开的。今道友信说:“西方古典艺术理论的模仿再现,近代发展为表现。而东方的古典艺术理论却是写意即表现,关于再现即写生的思想则产生于近代。”[14]224—225钱志熙就认为再现与表现的消长互补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规律。[15]当然,“表现”和“再现”说是西方主客二分思维下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美学强调主客体的“一体圆融”。
王国维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在英译《意志及观念之世界》中强调哲学家与诗人之价值“不存在于实际而存在于理论,不存于主观而存于客观,耑耑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于是彼之价值超乎个人之外,与人类自然之性质异,如彼者,果非自然的欤?宁超自然的也”[5]425。也就是说,境界,一方面是作者通过纯粹直观而体察到的客体的本质理念,另一方面,又是主体在直观到理念时的一种精神状态,与客体的理念合二为一,也是人作为一个客体的部分理念的体现。于王国维而言,真景物是事物理念的再现,而喜怒哀乐之真感情则是主体体会到理念时的心境,此时的心境作为主体的一种本真状态,也是主体本质的一部分,也是对主体内在本质的再现[10]183—187。与王国维不同,况周颐所强调的“真”乃是以表现为主,以表现审美主体的内心情感为主,也即他强调的表现真挚情感的“词心”。《蕙风词话补编》首则说:“性情与襟抱,非外铄我,我固有之,则夫词者,君子为己之学也。按此则为蕙风论词总纲,词话精蕴所在。”[4]355此话一语道破,作词就是为了表现自己,性情不是外界物质赋予作者的,而是作者内在固有的,这是《蕙风词话》论词的核心精髓。他特别注重主体的性情在词的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词的本质特点就是“陶写性情”。在世界、作者和作品的三者关系中,词人居于主导地位。作品是作者“陶写乎性情”的外在表现或存在模式。宇宙(阴阳)对作者有影响,但不是主宰;它只是服务于作者陶写性情之所需,是经过作者之择取(酌剂)后,将其情感投入或交流后的外部世界。因此,词作是词人性情的自然流露,或可称为词人的自我表现。正像王阳明所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王阳明《传习录·下》)这才是况周颐的“词心”,是其求“真”重性灵的原点。
(四)矛盾中的思想探源
王国维的审美直观与况周颐的“万缘俱寂、湛怀息机”都是创作主体在一种类似于道家的虚静状态下实现的,在这个层面上,王国维与况周颐都被后世接受者指向了中国传统的老庄思想,这种澄怀坐忘的境界其实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得道境界,这与西方的审美直观有着相通之处。这也是后世诸多论者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庄子的“自然”思想相联系的原因。事实上在王国维以“境界”为再现的观念中,虽然叔本华的影响很大,但是中西影响又是不能割裂开来的。饶宗颐在《人间词话平议》中指出:“王氏遮康节以论词,人多不知其本。”“邵康节(邵雍)曾论圣人之反观之道,谓‘反观者,不以我观物,而以物观物(《皇极经世》)王氏之说,乃由此出。”[16]321彭志平就曾提出过王国维有着庄子思想的底蕴,又在叔本华自具逻辑体系的哲学美学中获得了深度的共鸣,实际上是由庄子导乎先路,做了铺垫,而又得叔本华之强化,终究衍成一时期思想之主流。[17]从王国维的文学、哲学观来审视他的词学观,王国维不仅受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文论的影响,也认同中国传统,两人的相通之处也正是中西哲学不谋而合之处。正如再现与表现说最终结合的发展轨迹,我们也要既辩证又圆融地看待两者在中西文化影响下的差异。当然,王国维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彭玉平认为王国维对西学从信任到怀疑到遗弃转而还是皈依传统;而况周颐的词学思想也有复杂的发展过程,况周颐早期喜作艳词,他对花间词也评价颇高,受王鹏运等常州词派词人的影响,又想坚守词体清艳的本色,所以他频繁地使用“性灵”一词,用主体真挚的情感来弥合常州派之过于注重身世、家国寄托与艳词之间的矛盾,所以他强调在“性灵”基础上的“寄托”,在艳词中寄入“风骨”“重拙大”正是对这种矛盾心态的平衡与弥合。两人在矛盾中完成了对自己词学世界的探索。
结语
王国维受庄子和叔本华影响,认为词作之境界是对审美客体本质理念的再现以及对主体静观到客体本质的心境的再现,从而突破传统,希冀通过“境界”如镜子般反映和再现客观理念和生活意志。况周颐受中国儒教传统浸淫,强调由内而外的真情流露,认为词就是独抒性灵,是“陶写性情”,是主体性灵对外界的烛照。况周颐就词谈词,以词体推而演之,上升到诗学、美学的高度,他始终坚守传统立场,成为常州词派的集大成者。王国维骨子里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知传统而变革传统,他“用中国的学术规则对西方文学理论进行介绍和转化……他在精神上以意境说为内核,承袭了中国文化‘求无’‘义主文外’的学术规则,但他同时吸收了西方文论中的美学观念和新范畴,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理想的’‘写实的’,创造出了‘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写境’‘造境’等新概念……他创造出中国文论现代化的一种新的话语”[18]。两人词学理论各有建树也各有局限,本文选取了“求真”这个切入点,以再现和表现这一对本体观的范畴来审视,展现了两人求“真”词学观在“镜与灯”中的对比与融合,借助西方文论的视角,以传统文论为依托,深化了对晚清民国两位词学大家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