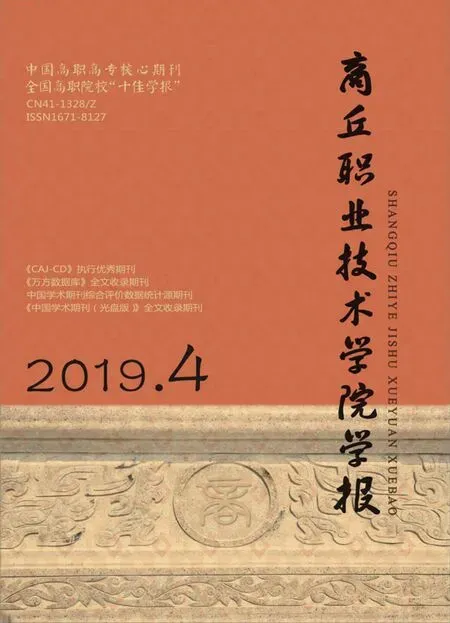唐代监察体制的外部独立性研究
章 燕,郭佳琪
(北方工业大学 文法学院,北京100144)
监察独立是古代监察体制运行及其政治实践中一项重要的原则。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洞悉权力时,因缺乏自我抑制性特征,而导致行政权、司法权等无法自监自查,因此,只能于政权体制内将监察职能独立于其他职能。
监察独立,是指直接行使权力从事监察实践的监察官履职独立,即监察官作为独立的自主个体,在具体案件中仅以事实为依据、以监察法规为准绳,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监察独立包括外部独立、内部独立。外部独立指的是监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在人事等方面独立于皇帝和其他机关,以防止外部的干扰和控制;内部独立指的是必须在监察机关内部构建保持监察官吏独立的规范的制度。基于古代监察独立性原则,对中国古代监察独立制度设置与实践运行进行研究、探索,自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仅以唐代监察外部独立性为研究对象,采用史学基本研究方法,分析其制度设置、实践运行与最终效果,并试图以现代监察理论做出科学评价,以期为我国现代监察体系的完善提供历史借鉴。
一、唐代监察机构体系的外部独立性
历朝历代都在为形成完善的中央监察机构而努力,但直至唐代,才真正形成分工明确、权力集中、机构统一的独立的有机监察机构体系。
第一,台谏分立。唐代中央监察机构体系包括御史体系、言谏体系,二者职能不同、分工明确,各自独立。御史监督百官,谏官规谏皇帝,分工的目的在于强化监察权与谏议权的不同职能,促使监察独立,以最大地化发挥其效能。
第二,机构统一、监察权集中。唐朝改变隋朝御史台掌管中央监察事务、司隶台和谒者台统率地方监察事务的三台分立局面,将全国的监察事务都委任于御史台,使全国监察权力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御史台权力的集中,结束了自汉代时皇帝特设监察、丞相司直行政监察、专职监察导致的监察权力分立的历史,监察权力得以统一集中行使,提升了御史台的地位。
第三,独立于地方行政的监察体系。在唐代之前,不论是监察御史还是刺史,最初都是中央派往地方的巡察官员,但最终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动、机构制度设置的混乱,都演变成为集行政、监察、军事等权力于一身的地方长官。权力的集中导致了地方监察体系脱离中央监察而存在。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察,唐代设计了具有针对性的独立地方监察制度。最有代表性的为“道察”制度。唐代将全国分为若干“道”级别的监察区,每“道”包括数州,使监察区域与行政区域分离,革除了按行政区域设置监察机构的弊端。御史台派出十二名监察御史定期巡视各“道”监察区,每次巡察地点、时间、人选都不固定,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监察职权所带来的外部干扰。另一种地方监察是皇帝派遣巡察使巡察地方,唐中宗诏令言:“左右台内外五品已(以)上官,识治道通明无屈挠者二十人,分为十道巡察使,二周年一替,以廉按州部。”[1]巡察使直属于皇帝并对其负责,而按期轮换的方式使得巡察使不能久居地方培养势力。两种针对地方的独立监察方式都是为了建立中央—地方垂直、独立的监察管理体系,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
需要强调的是,地方监察的独立性一直是监察体系中的重点难题。地方巡察使、采访使虽不能久居某处地方,但这种在地方设置固定监察机构的体系,亦能导致采访使权力扩张,无法分离监察与地方的关系。唐玄宗“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2],指出了巡察使与刺史拥有相同的弊端。因而玄宗改巡察使为采访使,并敕令强调:“自今已(以)后,采访使考察善恶,举其大纲,自馀郡悬所有奏请,并委郡守,不须干及。”[3]试图分离采访使与地方的关系,保障地方监察的独立性。但之后州县二级行政体制向郡州县三级行政体制转变,以及政权变动的原因,采访使更名为节度使,发展为形同“刺史”一样的地方行政长官。
二、唐代监察人事制度的外部独立性
“唐代监察是否独立于其他外部机构与人员”是分析研究监察人事制度重要的内容之一。唐代监察机构的人事制度体现中央政府欲在选任、升迁环节消减来自外界的干涉,以保证监察人事独立的意图。
(一)监察官员的人事选任
首先,监察官员人事选任排除了吏部干预。隋朝开皇年间,吏部掌管任命御史的权力。唐代初年,御史人事任免权发生重大变化。“其将除拜,皆吏部与台长官、宰相议定,然后依选例补奏,其内诏别拜者,不在其限。选授之命,不由铨管。及李义府掌大选,宠任既重,始得补之。自义府之后,无出於吏部者。”[4]由此得知,六品以下御史的任命由吏部、御史台长官、宰相三方审议拟定人选名单后依照选例补发奏报,皇帝查看选任的名单而决定。唐高宗时期彻底废除了吏部对于监察官员的人事任免权。五品以上的监察人员,如从三品的御史大夫为册授,正五品的御史中丞皆皇帝制授,由宰相进拟而皇帝决定;六品以下监察官员具有特殊性,不经历吏部铨选的环节,“凡六品至八品御史,皆进名敕授”[5],监察御史人选由宰相商议拟定,皇帝决定任命。
其次,皇帝注重对监察人事权的控制。唐代对六品以下官吏任免一般是旨授,即由吏部主持铨选。为减少外部机关对御史独立性的干扰,六品以下的御史人事任命不再属于吏部铨选范围,而改变为敕授——由宰相拟定,皇帝最终亲定,最终决定权归于皇帝掌控。而针对出使地方的巡察人员,往往由皇帝亲自指派。除此之外,皇帝还往往通过特殊亲选制度,加强对监察人事权的控制。唐朝初年至德宗时期,皇帝注重监察人员的亲选。皇帝亲自选择,往往是破格擢用,史称辟用。例如,唐太宗亲选张行成为殿中侍御史、武则天擢傅游艺为给事中。
最后,通过皇帝最终决定权与亲选特权、宰相荐选、御史台长官自选等多种方式与程序,来限制宰相、御史台长官对监察官员人事权的干预程度。无论是制授还是敕授,宰相荐选为最主要的监察候选人选任方式。然而制度规定只赋予了其拟定御史候选人名单的权力,皇帝则拥有程序上的最终决定权。除皇帝具有亲选特权外,宪宗至唐末时期,皇帝还逐渐赋予御史台长官自选权,分化和限制丞相对监察人员的选任权。总之,唐朝欲通过监察御史人事权的分解,实现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他机关对监察独立性的干预。
然而权力的分解,并不必然导致权力理想化受限。当皇权式微宰相权力扩张时,宰相荐选制度限制未能发挥实质性作用,反而无限制扩大荐选权,皇帝的最终决定权沦为形式化的程序。开元年间,“姚崇引宋璟为御史中丞,顷之入相”[6];还存在改变修正皇帝意见的情况,文宗时期“教坊有工善为新声者,诏授扬州司马,议者颇言司马品高,郎官刺史迭处,不可以授贱工,帝意右之。宰相谕谏,官勿复言”[7]。这事实上是对皇帝选任权的侵夺。
(二)监察官员的考课、升迁
唐代通过考课制度对监察官员进行政绩考察,依据考课结果决定官位和俸禄的提升。在考课程序中,政绩的考察、政绩的核准、考课的标准、考课的结论如果受其他外部机构的控制,必然影响监察官员的外在独立性。
1.唐代完善、客观的考课程序限制了考核人员的主观性、随意性
唐代监察官员的考核程序与其他官吏相同,分为定考和判考两道程序。定考是指御史大夫归纳统计监察官员政绩,经被考者核定无误后,报送吏部考功司。而判考则是由吏部考功司判考官员审核御史大夫上报的监察人员的政绩,依据考课标准得出结论。考课的结论,监察官员本人可以复核。吏部考核监察官员必须以御史大夫的统计、本人核定的政绩事实为依据,以客观考课标准为准绳得出考核结论。被考核的监察官员还拥有对吏部考核结论有异议时的复核权。可见,唐代已经存在较完善的客观、公平、公正的考核制度,从而限制了吏部滥用对监察官吏的考核权而干扰其独立监察的可能性。
2.皇帝对监察人员的考核具有干预权与决定权
这在制度上表现为监察人员考课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了皇帝对监察人员考核的重视,决定了监察人员官位的升迁和俸禄的提升,尽可能排除外部机关的干预以保证监察的独立性。
第一,唐代监察人员的考核时限被缩短。唐代官员考核由吏部考功司选举出的考核官吏进行,按时间分为岁课与定课,岁课一年一次,定课四年一次。监察官员因职务性质的特殊性,被皇帝视为极为重要的官职——御史大夫是“清望官”,御史台的其他官吏为“清要官”①,考核时间被缩短。监察官员在仕途升迁方面呈现特殊优势,《唐会要》记载:“其台官先定月数,今请侍御史满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满十八月,监察御史依前一十五个月与转。”[8]
第二,在实践中监察官员不论品阶高低,皇帝都可对其频繁使用非普通考核程序的特殊权力。唐史记载了李素立行使监察御史职权时为唐高祖赏识,“自是屡承恩顾”。逢李素立丁忧本应停职守制,高祖以其特殊重要性为由夺情,并亲自考量决定其升迁至侍御史一职[9]。韩愈任监察御史时,因上疏极论宫市,使得德宗大怒并将其贬而降职为阳山令。以上两则案例,充分证明了基于监察御史直接对皇帝弹奏的工作程序,以及其对于维护皇权的特殊重要性,唐代皇帝往往行使特权直接决定监察御史升迁或贬黜的职场命运。值得补充的是,唐代监察御史一职具有广阔仕途。据《新唐·宰相表》记载,唐朝由御史大夫升宰相者二十一人,御史中丞升宰相者十一人[10]。因此,皇帝对监察人员升迁的决定权使监察人员依附于皇帝,排除外部机关对其干预,为了升迁而尽职尽责地履行监察权。
三、唐代监察程序中的外部独立性
唐代监察弹劾程序中,监察人员能否独立于外部机关行使监察权,成为判断监察官员是否具有独立性至关重要的标准。
依据弹奏方式的不同,唐代存在“对仗奏事”和“仗下奏事”两种主要形式。“对仗奏事”指在朝参时不论官品大小,均可离席出班陈奏事状;此处的“仗”为皇帝上朝时的仪仗,所以特指公开奏事。据《唐六典》记载:“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以上,每朔望朝参;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参。”[11]而其中所指的参加常朝的“供奉官”包括了所有监察官员。皇帝上朝时,御史按照服饰规定衣冠入仗,公开宣读弹文,被弹人必须马上离开仗内。与之相对的则为“仗下奏事”,即机密要事朝会后奏报。然而唐统治者一般禁止滥用“仗下奏事”方式。按唐玄宗开元五年时规定,非机密要事,不得“仗下奏事”;唐律规定,非密而妄言有密而密奏者,处两年半有期徒刑。可见,鼓励对仗奏事的形式,明显具有监察独立性的特点——御史不受其他外部机关控制,独立公开直接对皇帝弹奏。
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唐代屡设屡废的限制监察权力的“进状”制度,实际上妨碍了监察御史的外部独立性。唐初,御史弹奏并不需要经过其他任何外部机关即可独立完成,这有效保障了监察的独立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台》:“旧弹奏,皇帝视事日,御史奏之。”然而,同文记录的景龙三年(公元709年)监察御史崔琬弹奏宰相宗楚客受贿一案,使得唐代监察程序出现重大改变。“自景龙三年以来,皆先进状,听进止。许则奏之,不许则止。”御史崔琬弹奏证据确凿,但因宗楚客乃武则天从侄,中宗对弹奏不了了之,并于两周后制定进状制度以限制监察御史程序完全独立,即御史在弹劾前将弹劾状呈送中书门下审批,听候进止。肃宗时期,为纠正李林甫留下的专权弊政,肃宗曾试图废除进状制度,恢复独立弹奏旧制。乾元二年(公元759年)肃宗敕“御史台所欲弹事,不须先进状”[12],恢复了御史单独弹劾的权力。德宗时期,因御史张滂朋党私利而弹奏中丞一事,下诏御史不能专举,恢复进状制度。《册府元龟》卷五二二《宪官部》“私曲”条记载:“无何,御史张滂复以朋党私衅弹中丞元全柔,众议不直,乃诏御史不得专举。”特别是唐后期安史之乱后,宰相专权,控制了御史的弹劾权,御史无法独立行使弹劾权。故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唐御史迁转定限》中评价“案唐世台官,虽职在抨弹,然进退从违,皆出宰相”。
总之,为限制御史滥用职权参与朋党之争或谋图私利,更好地为政权稳定性服务,唐统治者制定了进状制度。由于该制度有利于宰相有效控制“雄要”的监察职权,得到宰相的支持,屡废又屡恢复。御史朋党之争、宰相专权哪一种对皇权危害更大?御史不滥权、宰相辅政之忠心哪一方更值得信任?独立广开言路、限制与控制监察权滥用哪一个价值更重要?“进状”制度存废反复,一方面显示了唐代对监察独立制度与理论还正处于探索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另一方面也揭示了制度背后皇权与相权惊心动魄的龙虎之争。
注释:
①唐代的官吏有清浊之分,其与选举官吏的身份重要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