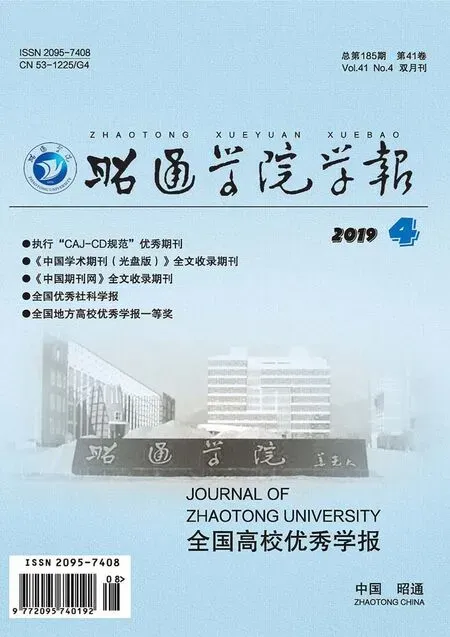现代化语境下生存的博弈与反思
——论周大新小说中民间艺人群像的社会意义
姜汉西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手工艺人一类特殊的群体,尤其是在一个具有厚重乡土气息的地域文化空间里。他们虽没有巨商富贾的财力与魄力,也无法使自己跻身于社交名流之行列,却靠着自己的一技之长多了一份收入来源,而常年的商业行为和走街串巷等活动方式同时也起到了沟通村里村外两个不同空间维度之功用。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多方交际的性质,使得手工艺人们往往成为了一个区域的权威和中心,在民间社会往往以话语主导者的姿态出场。然而随着现代信息传媒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影响下国家和民族的中心任务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乡村在现代化的浪潮下饱受裹挟和冲击,手工艺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也在社会思潮的席卷下中发生了新变。周大新正是注意到了这一群体在时代转型中所表现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从而将焦点锁定在了手工艺人形象的描摹和刻画上,并且以一种民间视角和人文关怀去呈现他们的精神生态和内在的情感诉求。从周大新的一系列创作来看,《家族》、《紫雾》、《铁锅》、《银饰》、《勒》、《屠户》、《步出密林》和《向上的台阶》等短篇小说在内容层面上从不同的艺术形式各自的特点和对社会的适应性角度展开了对手工艺人形象的集中叙述与思考,将人性的探索和对时代的反思推向了一个极致。长篇巨著《第二十幕》则是将家族传下来的织丝技艺和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风云联系在一起,内蕴着极强的历史纵深感与思想容量。手工艺人们的命运和时代浪潮的起伏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底层大众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身上附带有二十世纪那个风起云涌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和经济信息,通过外在的社会环境揭示和内在的个体精神剖析,周大新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那个时代特征以及个人的生存状态的契机,并且在个体与整体的对比观照中,对于思考家族与时代、个人与社会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安身之本到立命之累:技艺的传承困窘境
中国的乡土属性是地理选择和历史积淀的结果,乡土不仅仅昭示的是一种空间和地域,还包含有一种内在的相对稳定的乡村特征,这种特征相较于都市而言最显著的标志就在于不流动性,或者说是封闭性,即如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那样“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具有贬义的概括和形容,“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1]从一定意义上来看,正是由于乡村社会封闭的特点,使得外来文化的影响和融入难上加难,因而在乡村很多古老的传统得以延续和保存,与此同时,乡村原始性的一面也渐渐被暴露出来,而原始性本身又指向着封闭的内因,封闭性成了对原始性最好的佐证,正是在两者的互相作用下,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才有了现实的保障,因而乡村才是传统中国最为真切的本来面貌。但我们所关注的是在这样一个封闭地域和文化空间里,社会结构的稳定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秩序,这些秩序的呈现和表达往往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实物来藉以完成和实现。于是那些手工艺人往往可以依靠着自己的独门绝技在十里八乡范围内夺得一席之地,并且技艺的传承也是在家族内部时代沿袭,由此我们看到从秩序的维系到整个社会结构本身,都有着一套属于自己的稳定结构和承续法则。
《铁锅》中的郝家就是如此,祖上世代都在做锅一直延续到了他这一代身上,可是从哪一辈开始,最初是怎么做起来的?自己都已经说不清楚了。然而就是因为“无论什么朝代不论什么家庭总得要锅做饭”,这种类似于家训的信条推动了造锅工艺在郝家的传续,到了郝祖宛父亲这一代“已经可以日产各种型号的锅一百一十口,麻山铁锅的声明在四方震响,开始有陕西和湖北的商贩牵马拉驴地来买锅”。而他们父子身上也都有着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来自于对荣耀的渴望和对家族昔日辉煌的重铸,正像郝祖宛的父亲所教导他的那样:“好好干,早晚有一天我们要建成一个大锅厂,让方圆百里家家的锅上都打咱麻山郝家的印戳,让咱们这门手艺的老辈们脸上也光彩光彩、荣耀荣耀!”[2]家族的精神和个人的责任,正是在一代代的讲述中得到强化,而更为年轻的家族成员也从中将自己的潜能和智慧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铁锅》中家族代际之间对于这种再创辉煌的追求在《第二十幕》中同样有着相似的表达,尚家织造丝绸已逾千年,分别在北宋开宝二年和明万历十一年两次被中外绸商誉为“霸王绸”,后代人以此为傲的同时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并落实为笔下的文字要求家中的孩童从小就开始背诵,“有生之年,发誓不忘数代先人重振祖业之愿,力争使尚家丝绸重新称霸于中外丝绸织造界,再获‘霸王’美誉”[3]。手工艺的传承在最初只是一个藉以谋生和安身的手段,在慢慢的发展和延续中我们看到这种技艺不但没有给自己的子孙带来幸福,反而对人生构成了一种压迫,迫使着一代代的人去舍弃掉自己的太多的自由和选择甚至是抛弃喜欢的姑娘去完成对家族手艺的守护和传递。
从郝祖宛到尚达志他们一生都在以家族手艺的传承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在遭遇了一次次的挫折后而又一次次鼓起勇气,他们的付出和牺牲是义无反顾的也是毅然决然的,正像安·比尔基埃所言:“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通过爱,家庭将长短程度不等的先辈与后代系列的利害与义务结合在一起”[4]。因此他们为了家族技艺和家族声誉的重振而做出的努力是带有一种义务性质的,而那些和他们发生联系的局外人同样也为了这样一种使命在竭尽所能地伸以援手,甚至不惜以自己为赌注全心全意投入。在郝家的铁锅生产面因资金问题即将破产之际,邻家女孩秋芋和郝祖宛一起捡拾废铁背到城里去卖,在最后资金缺口依然无法填满的时候,秋芋不惜以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金钱。在《第二十幕》中盛云纬和秋芋一样,始终牵挂着尚吉利大机房的兴衰荣辱,在机房生产面临危难之际一次次挺身而出,帮助尚达志化解危机。而这两个女人最后换来的却是男人的背叛,郝祖宛因受不了一家人对自己婚姻的阻挠毅然炸毁了做锅用的炉子,远走他乡。而尚达志虽然一生没有离开南阳城,却也一直没有给予盛云纬一个妻子的名分。在祖业或者说是手艺的传承中太多的人成为了牺牲品,这其中还包括尚达志在购买机器时被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的女儿绫绫,以及累死在生产线上的妻子顺儿和为保护机器而惨遭日本人蹂躏致死的儿媳容容。尚吉利大机房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起起伏伏的轮回,尽管几代人都在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懈努力,但始终无法实现理想中的那种繁荣而后昌盛局面,更不用说去完成家族对“霸王绸”的期许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尚家的丝织业是处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环境的好坏对生产本身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近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是一个常态,而生产的关键在于内心的坚定和时代的安稳,对于家族产业重振的执着与时代的飓风大浪相碰撞,牺牲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技艺本身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掌握者可以从中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满足,从而实现人生价值并收获人生的幸福,但是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郝家的铁锅生产还是尚家的丝织业都在某种程度上挟迫了族人的人生选择,剥夺了他们生命独立意义上的自主性。而有时候那种因荣光和声名所唤起的自豪感和使命感也并不总是那么强烈,反而在垂暮之年会生发出对自己这一辈子所作所为的无限感慨,由此也将我们的思考引向对手艺人自我存在价值的人道主义关怀和个体生命的无限同情。周大新正是从技艺的传承角度,将传承者和传承本身对于人和人性异化提了出来,为了承担起这份家族责任,他们将一切的追求都投注到了这一个点上,将一切为之所做出的牺牲都视为理所应当,对爱情的背叛和对亲情的疏离已经慢慢褪去了他们身上的人之所有的情感和态度。手艺本身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表征,而对于郝家和尚家几代人的命运的观照,也是对传统文化在不断传承中呈现出的负面性的反思,并且这种思考从个人一直延伸到了民族和国家。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揭示出技艺的流通与传递虽然是内向性的,但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个人和家族不能只是将目光紧盯着眼前的那一方小天地,而应该有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情怀。
二、从保守封闭到商业化运作:技艺的价值新变
在家族中得以延续下来的技艺本身是一种带有浓厚历史感的传统文化载体,无论是技艺的生成过程还是表现形式都有着不可磨灭的传统文化烙印。在特定时期内,这种技艺能够满足于手工艺人对物质的满足,是受制于传统生产手段和风俗习惯的结果,然而随着世事的变迁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以机器大生产为代表的现代化浪潮势如破竹般席卷而来,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家族技艺在此浪潮之下必然要受到冲击。尤其是手艺人身上所暴露出的小生产者的诸多弊端和局限就会得到更为直接地凸显,因此对于手艺人的生存困境的思考就必然要涉及到传统技艺本身在当代的现实遭遇和适应性问题,就像李泽厚所发问的那样:“中国传统思想和心理结构往何处去?是保留还是舍弃?什么是未来的路?”[5]。从五四时代对于破旧立新的急切渴望到二十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期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大的破折与转变。当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五四时期那种“打倒孔家店”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和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最为显著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守住了民族的根与魂,这个民族在对未来的展望中才能够有自信,而传统文化正是扮演了根与魂这样的角色,尤其是在当代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里,对外来文化的过度迷恋和热情反而会丧失了自我民族的底色,从而沦为西方文化霸权下的“他者”。由此在二十世纪寻根文化思潮下,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通过对“最后一个”形象的塑造,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无限深情,而郑义的《远村》和《老井》则展示出了晋中之地上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同样表达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怀旧与留恋情绪。民族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是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会发展变化,还可以有革命性变化,但抛弃不得;抛弃得越多,失败越大;若彻底抛弃,必然彻底失败。历史不乏证明”[6]。因而对于以传统手艺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只是从文化的新旧交替角度出发,简单认为旧文化就是糟粕,应该被赶尽历史的垃圾堆,从而得出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必然扼杀这一结论,传统技艺本身同时也应该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这种散布在乡间村落里的传统手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技术的一种形式,“技”代表的是本领和能力,是对手艺本身掌握的一种评定标准。而“术”所强调的则是一种方法和方式,是将“技”输送出去并且能够换来物质满足的手段,因此技和术是一种双向的贯通,两者是属于有机的统一体,内在的一致性决定了不可将其中一个要素予以分离。从家族传承的角度来看,手艺人本身的技能和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进步,尤其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甚嚣尘上的商业化环境中,就更加强调商业化运作的手段及其功用,当技艺成为了一种商品后,商品本身的质量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营销成为了一种关键要素。《家族》里的五爷有一门做“冥宅”的家传手艺,平时以此为副业赚个十块八块烟钱,五爷讲究“积阴德”从不多要钱,但是到了自己的下一代时,看到别人家靠着做生意富裕了起来,两个儿子和女婿都争相要开棺材店,当大儿子最先表露出这个想法时,五爷厉声喝道:“知道棺材是什么吗?冥宅!冥宅都敢拿来做买卖,亏你想得出!”五爷做冥宅有着自己的打算,从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手艺和做生意联系在一起,那种商业化的模式对他来说是“坏阴德”的。然而乡村早已被现代化浪潮所侵袭,儿女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使得他又不忍心去加以拒绝,终于在女儿提出了开葬品店的提议后“五爷的身子微微一震,他未料到女儿也会提这个问题,嘴慢慢张开,又缓缓闭上。许久,才吐了一口痰……”五爷明知道做这种生意是坏阴德的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却最终还是改口道:“你们要是真想干,我也不拦—”[7]。在一条街上三家棺材店先后开业,在互相抢夺客源的竞争中,各自从棺材的质量和花样以及服务上下功夫,大德继承了五爷的手艺,力气又大,一时间客源不断,生意颇为兴隆。小德依靠着自己的绘画本领开启了壁画棺材的新天地,还增加了送货上门的服务,并且兼埋寿衣,主顾也是越来越多。云娇则是通过租花圈、做式样新颖的骨灰盒以及免费放哀乐来扩大影响。
在这种商业化的竞争中,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一种良性发展,无论是服务的系统性还是作为商品的棺材本身的质量都有了保障和提升,但是在这个表象之下,却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危机。三家店的主人本是同父同母的兄妹,那种流淌在各自血液里的对于家族的认同感,也就是亲情本身,然而自从有了各自的店面后,利益至上的市场规则打破了家族所赖以为系的伦理和秩序,对于金钱的追逐一步步窄化着亲情和伦理的存在空间,商业的竞争在最后完全沦为了亲人之间的打击和报复。大德被这种局面弄得束手无策,他也想象妹妹和弟弟那样费尽心机去争取更多的客源,可又怕别人说用此法抢生意不道德,但又想不出别的吸引买主的新招数,只好摘掉招牌宣告倒闭。大德关门的那一天小德因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长出一口气,可大哥的命运很快就又轮上了自己。在大德和小德的店面相继关门之后,云娇成为了两家人共同的敌人,在得知丈夫被引诱出轨后,她也走向了自己的“死亡”。从一个和睦的家庭到最后的离心离德反目成仇,在这一过程中,手艺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人心,是人在市场经济下利益熏心后的一种丑恶面目的显现。
相对于《家族》中所弥漫着的悲剧气氛而言,《步出密林》则有着更加令人深思的现代性意味。在沙湾村,玩猴是当地人引以为豪的本领,祖上哪一辈哪一年开始玩猴,已经无法考证,但是最初的玩猴活动是先有了猴子和当地人和谐相处的基础,后因一场天火将庄稼和树林烧毁殆尽,人和猴子在逃荒的路上形成的一种谋生游戏。但是到了沙高这一辈人,在基本的生计无忧之后却无法获得更高的物质满足,欲望占据了内心后显现出狰狞的面目,于是玩猴成为了他们赖以赚钱和致富的手段,通过猴子他们将自己的欲望一步步扩张。沙高正是将自己的前途与家庭的命运和关猴、玩猴紧紧连在了一起,才会被欲望蒙蔽了双眼,于是猴子成为了他的愿望和理想得以实现的依傍,“一想到将有一群活蹦乱跳的猴子在自家院里,而且随着猴子而来的将是一座下四上三、七间卧转到顶的小楼,他的眼角顿时又闪出不少欢喜”[8]。在成功捕获了猴子后,他从训练到开始表演对猴子都是近乎残忍地剥夺,为了增加看点赚取更多的钱,他让因关猴而致残的振平和猴王老黑进行拳击比赛,而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迫使已经怀孕的猴子爬杆当众摔死……从中可以看到沙高对金钱的渴望已经泯灭了他的人性,而这正是市场经济影响下人的异化的一个表征。相对于沙高而言,他的妻子荀儿无疑是被寄予厚望的灵魂和主心骨,她目睹了自己丈夫的所作所为也意识到了当前的危机,并通过自己的毅然决然的努力去改变着一切,则是对于市场经济下利益至上和金钱崇拜的一种反拨和抵抗。
三、结语
手艺人是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技艺本身往往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内蕴和丰富的民族文化根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中,这种传统技艺在彰显着自己的文化荣光的同时也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不可忽视的缺陷和弊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技艺本身所包含的人文内涵和精神价值掩盖了其消极性的一面,但是这种消极性因子并没有消失,而是选择了蛰伏和潜藏。新时期以来,社会环境经历了一个大的变革,从国家的意识形态到社会上的思潮风气都在被现代化浪潮所裹挟,全面转型的时代主题下,固有的一切秩序和伦理结构都面临重组的可能,不同类型的人群也开始重新分化,社会形势和时代环境迫使着每一个生活于其中的人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们今后的人生。手艺人本就是社会中的底层,他们大多从土地中汲取生活上的满足,在乡村世界中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受制于环境的封闭和文化教育的欠缺使得他们在思想上和视野上都存在着局限性,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他们是无法掌控自我命运的,但是面对大形势他们又无可奈何,只能将最后的一根希望稻草系之于传统手艺之上。然而他们只是懂得如何提升技艺的水平,并决心为此付出毕生的努力,却无法在方法和策略上去通过技艺换取物质上的满足,反而在市场的角逐中走入了无法自拔的迷途,最终被市场所淘汰。传统技艺是一个历史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遗存,文化遗存在当下市场中是略显苍白无力的,但手艺人却是一个存在于当下生活中的真实个体,需要安身立命,这种历史和当下的融合与交织所营造的正是手工艺人的现实悲剧。底层大众是一个缺乏关照的群体,他们默默地生默默地死,在他们不为常人所知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渴望,在那种情感诉求和理想追寻背后正是他们作为人的丰富性的体现,从渴望到欲望再到人性的泯灭和人格的失落,周大新所关注的正是他们身上的精神状态的流变,其中内蕴着作者对生活于社会底层大众的人道主义关怀,而这种关怀也是周大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在沙高和荀儿的对比中,我们会发现周大新是一位带有强烈现世关怀的人道主义作家,“在日益追求高速化的今天,商品经济大行其道,冲击着传统的法则与规范,而同时现代性的弊端也不断暴露出来,于是积极性地反思成为了一种社会思潮。”[9]如何将这种反思进一步深化,并且从当下的角度对现代病作出回答自然也成为了必须要面对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