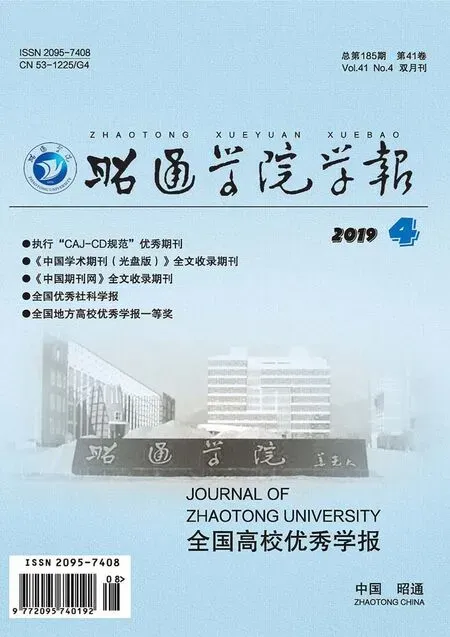论《绅士的太太》中的都市空间建构
(潍坊理工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山东 潍坊 262500)
纵观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其中呈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纯自然的乡村式诗体小说,多见于《边城》《柏子》《龙朱》等湘西题材的写作,写的是故乡景与人融合下的美。而另一种则是融入人文景观的都市题材,多存在于《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讽刺性小说,揭示城市和城市人的丑陋。大城市的繁华刚开始带给沈从文的除了好奇,还有自卑和屈辱,但同时区别于湘西的都市人文也带给了沈从文新的写作方向——都市题材。
列斐伏尔曾提出“三元辩证法”,即空间的知识理应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联系起来。在列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物质属性,但绝不是与人类、人类社会毫不相干的物质存在。一方面,每一社会空间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模式中;另一方面,空间也是一切社会活动、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一切社会力量纠葛一体的场所。在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中,沈从文为我们构筑了带有西式都市色彩的居住空间,以及都市环境塑造下的官宦形象。
一、都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交错混杂
农村人初进城的一刹那感觉是对都市文化的最准确的定位。[1]沈从文也正是怀有这种视角才写下《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中国的现代性应当由乡下人进城谈起,而且都市物质的现代化与人的精神现代化比起来,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在沈从文笔下的都市化文学是一个现代性展示的过程,是一个生命价值与历史方向性进展相纠缠,相矛盾,甚至相对立的过程。
都市题材的创作是沈从文来北京讨生活,耳闻目睹后有感而作。对于一个从湘西小山村走到大都市的人来说,首先感受到的便是强烈的视觉冲击,繁华的商场,喧嚣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品……都是湘西所没有。因此在写作都市题材时,沈从文更愿将自己进入北京城后所见的震撼场景融入到小说中。于是也就出现了都市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大段描绘。况且家居环境,是一个更容易描写和发现都市病态的场所,走进家中,一切私密皆暴露出来。
沈从文都市小说中的私人家居场景常常以某一人或某一对夫妇的家庭环境为主,小说《绅士的太太》中就以两个绅士家庭为描写对象,描绘的场景多集中于客厅和卧室,而场景中常常刻意营造昏黄的色调,在整体氛围上呈现出安静沉闷的气氛。在这场景下,人们都重复一件事情——打牌。这种压抑的格调在沈从文的湘西描绘是不多见的,绿色,蓝色,红色,才是描写故土的基本色调。昏黄是都市小说中才表现出的一种色彩。而在小说中,居家场景的布局多以中式为主,房间内的物品则是在中式中夹杂着西式物品。
例如对绅士的家庭有如下描写:“一栋自置的房子,门外有古槐一株,金红大门……房子是两个院落的大小套房子。客厅里有柔软的沙发,有地毯,有写字台,壁上有名人字画,红木长桌上古董玩器,同时也有打牌用的一切零件东西。太太房中有小小宫灯,有大铜床、高镜台……有用不着的旧式洋伞草帽,以及女人的空花皮鞋。”[2]古槐、金红大门、红木长桌、古玩等皆为传统中式物件,构成整体的空间结构,但在传统的格局中穿插沙发、地毯、洋伞、女人的空花皮鞋等西式物件。传统生活中融入现代都市的印痕,可见西方的都市化物件已经渐渐走入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正经受现代的洗礼,但却没有完全步入都市化,是一种不纯粹的都市文化体现。[3]
除了对绅士家的整体布局摆设进行描绘之外,沈从文还对另一位绅士家大少爷的房间进行建构。在建构之前,沈从文借众人之口对大少爷的总体特点做了介绍,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留过洋,获得哲学硕士,具有较高的学识素养;第二,为了与三嬢偷情,瞒着父母不去就职,赋闲在家。两者的设置自然是为了体现绅士阶层(甚至可以说是知识阶层)的腐化肮脏。但同时又注重小说的整体性,既然赋予大少爷留学归国的身份,便为其构建具有都市化色彩的房间结构。小说中有这样的介绍:
于是两个妇人就进到这大少爷书房了,一个并不十分阔大的卧室,四壁裱得极新,小小的铜床,小小的桌子,四面皆是书架,堆满了洋书,红绿面子,印金字,大小不一…… 床头一个花梨木柜橱里,放了一些女人用的香料,一个高脚维多利亚式话匣子,上面一大册安置唱片的本子本子上面一个橘子,橘子边旁一个烟斗。……
与之前对绅士家的描写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房屋建构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以中式家庭框架为基础,融合各种西洋物件,且这些西方物品都属于附属品,并不是作为生活必需品出现。笔者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北京虽是政治文化中心,但较之上海,都市化发展并不明显。固有的传统文化气息还十分的浓厚,人们可以接受舶来品,但也不愿舍弃原有的文化。第二,文章作于1929年,此时的沈从文刚来北京讨生活,人生阅历加之自身的性格特点使其仍怀有保守的文化思想,更愿意将视角停留在传统文化上。
除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空间,作者在小说还涉及了××酒店、××秘密俱乐部等公共空间,尤其是对××秘密俱乐部的描写,作者写的非常隐晦,但情感却是十分充足,并在这个俱乐部里让情感发生了进一步变化(大少爷与绅士太太暗生情愫)。××秘密俱乐部实则为一个赌博场,'“特别室”“当差的”“起花高脚玻璃杯子”“甜味橘子酒”“皮篋”,有别于早期中国自有赌场的脏乱差,沈从文为我们构建的是具有浓厚现代都市化色彩的新型赌场。但沈从文对此是有所避讳的,小说中的每个人对此都有所回避。“只到过三次,万千莫告给爹爹!”“输了不多。姨娘输了两千七百,把戒指也换了,瞒到爹爹。”因此对公共场所的建构着墨并不多。
二、都市空间建构上精神空间的揭示
我们能从这些西式物品中找到“都市”的痕迹,但沈从文却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对其建构,尚不能明确看到作者对于都市的态度。作者对都市的态度很大一部分通过北京这一大空间下的人物体现。北京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使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金融商贸体系和浓厚的文化氛围,在都市化的大环境下形成了众多知识分子和官绅,这在沈从文湘西系列小说中是没有的。
《绅士的太太》中沈从文以两家绅士生活为视角展开叙述,首先构建了繁华骄奢的物质空间,对此在上文已经进行详尽的叙述。然而作者的用意不仅仅停留在对物质空间的叙述,清末的外敌入侵逼迫北京接受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事物,包括政治和文化,同时也迫使北京由一般性城市向都市发展。被动化和紧迫化导致北京的都市化发展呈现不健全和不均衡的状况。都市化的北京催生了一系列的都市文化符号,身份等级的划分以及不合礼法的行为都成为沈从文构建的都市精神空间,是物质空间下作者真正想揭示的。
作者首先建构的是一个具有等级秩序的上层社会,在绅士家中,绅士及其太太属于上层,在其之下还有“三河县”的娘姨,“车夫,门房,厨子,做针线的,抹窗子扫地的,一共十一个下人。”下人的出现实则是都市化的一个明显表征,快速的经济发展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也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雇佣关系。在此之前的小说中是没有这样的等级分化的,比如在小说《边城》中,码头的船总顺顺算是茶峒“位高权重”的人,却并不高高在上,人人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而在另一位绅士的家中,除了车夫、厨子等干活的下人外,还有三个姨太太,其中还有一个是妓女出身,会做媚笑。在此形成了三个等级,绅士及其正妻,姨太太,下人。沈从文早期对湘西妓女的描写往往充满了怜爱,认为是有真性情的女子,而在《绅士的太太》中却完全抛弃了这种态度,转向了批判。
除了等级身份的出现,沈从文还设置了两件不合礼法的苟且行为。一件是另一位绅士家的大少爷与三嬢之间的乱伦,另一件是绅士太太与大少爷偷情,甚至诞下了私生子。这三人不合礼法的行为构成了小说的主体。现代文明带来的是物质的极大丰富,反过来物质反作用于人类的精神,却带来了精神的异化,知识分子作为最先接触西方文明的群体,也成为最先被异化的人群。尤其是大少爷与绅士太太之间的关系,作者建构了一个强大的精神场,表现绅士太太情感的变化。归纳起来约有三次,第一次是两人坐车去xx废物公馆,“下车时,(大少爷)先走下去,伸手到车中,一只手也有意那么递过来,于是轻轻的一握……感到一个憧憬的展开扩大。”此次行为是大少爷有意为之,绅士太太只是因为偷听而羞愧。接下来在xx(赌场)才是两人真正的“较量”,文中这样写道“当差的拿酒去了,因为一个方便,大少爷走到绅士太太身后去取烟,把手触了她的肩。在那方,明白这是有意,感到可笑,也仍然感到小小动摇……显得拘谨,又显得烦懑了。”绅士太太面对大少爷的暧昧,内心有所动摇,但更多的是逃避。为此三嬢协助大少爷展开进一步的“攻势”。
三嬢走过房中来了,一只手藏在身后,一只手伏在绅士太太肩上,悄悄的说:
“太太,要看我前回所说那个东西没有?”
……
“真是丑事情。”
三嬢不再作声,把藏在身后那只手所拿的一个摺子放到绅士太太面前,翻开第一页。于是第二页,第三页……两人相对低笑,大少爷,轻脚轻手,已经走到背后站定许久了。
……
在沈从文设置的精神场域中三人完成了各自的精神较量,使故事情节发生了新的转变。都市人肮脏不堪的精神世界再次也得到了强化。
三、都市叙事的虚幻性和消费性
《绅士的太太》存在多个版本,1930年发表在《新月》上的是初刊本,随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未收入到其他集子中。直到195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集》收录了这篇小说,沈从文为之做了重大改动,属于校正本。而后1982 年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的《沈从文文集》( 第四卷) 收录此篇。此版本较为驳杂,糅合初版本和校正本,还增添诸多内容。其他重要版本均以 1957 年的校正本为底本,各自做小幅度的增删。2002 年12 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则遵从沈从文遗嘱,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选择了虽不完美但对作家个人及文学史都有重大意义的初版本。[4]
校正本的出现源自特殊年代下的政治压力,对先前小说中的许多模糊化身份做了具体化改正。其实《绅士的太太》开篇便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写一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沈从文写此篇文章绝不是针对某一人,而是塑造一类人,初版本才是沈从文最初的情感表达,因此我们在分析文本时也都是以最初版本为依据。
当然在此笔者还是要对比一下初版本(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沈从文全集》)和校正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沈从文小说选集》)的部分不同,以此来分析沈从文都市叙事中的模糊化处理。试举两例来说明:
在初版本中对于绅士身份的介绍是这样的:一个曾经被人用各样的称呼加在名字上面的主人,国会议员,罗汉,猪仔,金刚,后来又是顾问,参议,于是一事不做,成为有钱的老爷了。而在校正本中对绅士身份的介绍更加具体:国会议员、罗汉、猪仔、金刚,后来又是总统府顾问、参议,于是一事不做,成为有钱的老爷了。[5]将“顾问”改为了“总统府顾问”,而沈从文的同乡熊希龄就曾在北京担任民国总理,在顾问前加上总统府这个前缀,讽刺的对象便直指国民党的某些政客。凌宇由此认为《绅士的太太》是以熊希龄及其议会同僚的家庭生活为模特儿的。[6]此外,对一些社交场所(即公共空间)的描写上也做了较大的改动。初版本中涉及了“××饭店”,“××秘密俱乐部”,而在校正版中都将其明确化,改为了“六国饭店”或“大陆饭店”,“开心秘密俱乐部”。而六国饭店等酒店是国民党政要交际的场所。但笔者认为将校正本与初版本进行比较便会发现,这不过是沈从文与国民党撇清关系的一种手段罢了。由此我们看出,沈从文一开始对故事的主人公以及故事发生的地点都做了模糊化处理,况且小说本来就存在虚构的成分,也就是说在小说创作时作者是尊重都市叙事的虚幻性原则的,而不是改编后的现实批评文。
都市叙事除了虚幻性,更多的是一种消费性。列斐伏尔就曾指出,在城市空间的范畴内来看,消费主义已经占据了主要地位,并且城市空间已经被看作是一种消费的对象。[7]换句话说,凡是都市文学的叙事中,必定会有消费主义。《绅士的太太》中也不例外,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需求暂且不说,单是各绅士家的娱乐消遣便花费不少,打麻将,赌博……整个都市上层都停留在这种金钱消费之下。而且消费不仅存在于上层社会,也存在于下人之间:
得了赏号这些人就按照身分,把钱用到各方面去,厨子照例也欢喜打一点牌,门房能够喝酒,车夫有女人,娘姨们各个还有瘦瘦的挨饿的儿子……
沈从文为我们建构的空间下也充分体现了都市的消费性,整个都市构成了强大的消费场,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