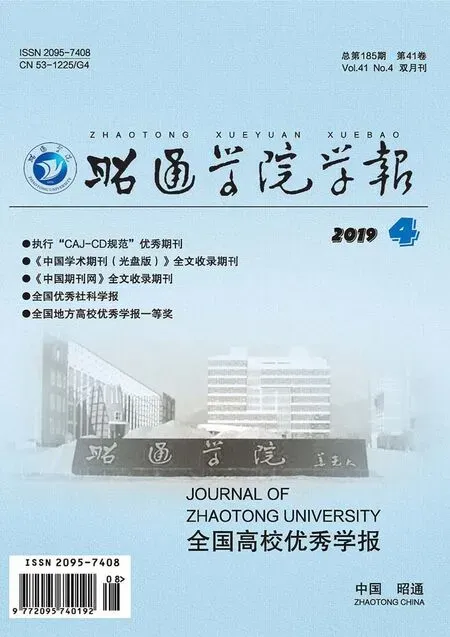论《梧桐雨》和《长生殿》在创作中的异同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备受历代文人的青睐,遍布诗词、小说、戏曲等历代文学作品。清人赵翼评论李杨故事声艳情浓,令人歌哭流涕,可谓“绝妙之词”,一时不胫而走,遍传天下,“文人学士既叹为不可及,妇人女子亦喜闻而乐诵之。”[1]37李杨故事自唐以来不仅成为诗人笔下或批判或歌咏的对象,更成为元明清戏剧舞台上反复敷演的剧目,李杨故事由此在民间得以推广。
中国戏剧成熟于南宋时期,经历了宋戏文、元曲杂剧和南戏、明清传奇等发展阶段。李杨戏贯穿于中国戏剧发展的各个阶段,宋代南戏便有《马践杨妃》存目;元代杂剧家更是创作了大批剧作,但现存可见的仅有白朴的《梧桐雨》,其余均亡佚了;及至明清,出现了许多与之相关的传奇剧,其中被搬上舞台表演次数最多的是清代洪升的《长生殿》。《梧桐雨》和《长生殿》是李杨戏中流传最广、成就最高的两部剧目,它们在戏曲史上分别被誉为“元曲冠冕”[2]16和“千百年来曲中巨擘”[3]406。这两部剧作均取材于李杨戏,经由白朴和洪升的敷演和艺术加工,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作。在创作过程中两剧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洪升曾有览元人《秋雨梧桐》剧之言,由此可知洪升在撰写《长生殿》时曾参看过白朴的《梧桐雨》也未可知。除了体制结构上的差异外,两剧又各具特色。本文旨在分析二人创作中的异同,揭示其中深层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意图。
一、人物身份的异同
《梧桐雨》和《长生殿》选取李杨故事进行敷演,塑造了诸多人物形象。由于白朴和洪升同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两剧对安禄山的书写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其胡人的身份。但二人在对前代素材的运用过程中,《梧桐雨》借鉴了正史和野史的内容,而《长生殿》则遵循“要诸诗人忠厚之旨”[4]自序1的创作原则,有所增删裁剪,因此两剧对杨玉环身份的选择中存在明显差异。
(一)安禄山的身份
白朴和洪升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似。白朴出生于蒙古军大举入侵中原时期,洪升生于顺治二年(1645),正值清军南下。两人历经战乱后,均受外族统治,民族情感受到严重打压,自我身份得不到认同,个人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元、清两代为少数民族政权,在建国初期均施行过严酷的民族政策。元代曾将民众分为四等,汉人属末等,并在用人、科举等诸多方面均有限制。[5]54而清政府虽以怀柔和镇压政策并举,但也进行了严酷的民族压迫,颁布了留发不留头的《剃头令》,并对逃人、圈地等有所牵涉者,一概治罪。外族统治践踏了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文人普遍社会地位低微,职位不振,出现了许多以遗老自称的文人,白朴和洪升都是其中一员。
在仕途之路上,白朴“不屑仕进”。王博文为白朴好友,他称开府史公曾荐白朴入朝,但白朴“再三逊谢,棲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6]206白朴一再谢绝入仕,避退江湖,衡门而居,嘲弄风月,流年光景,这虽然与其父白华变节,历事三朝有关,但根源在于白朴以金朝遗民自居。据孙大雅所言,白朴虽少有大志,但山河巨变,家国俱亡,“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6]207在国破家亡的境遇中白朴顿感身世漂泊,在“绝意仕进”的背后其实流露着白朴强烈的身份归属和民族认同意识。
洪升与白朴不同,他一直心存功名,曾获得国子监的学籍,随着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洪升目睹了清廷的高压政治、社会黑暗。其后,洪升在《长生殿》中道:“竞豪奢,夸土木。”“可知他米薨碧瓦,总是血豪涂。”[7]《疑谶》45面对此种情景,洪升意识到统治者的豪奢侈费,对民众的剥削和压迫,他的民族认同在不断觉醒。并且洪升曾师从陆繁弨、毛先舒等人,他们均是满腹诗书的江湖远客、不愿仕清的遗民文人,这对洪升亦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在《京东杂感》中称:“白头遗老在,指点十三陵。”[8]174在《长生殿》中也有此种论调:“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7]《弹词》174由此可见,洪升对“白头遗老”的强调,是他不断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寻。
因此,在《梧桐雨》和《长生殿》中,不同时代的两位剧作家不约而同地突出安禄山的胡人身份。白朴在《梧桐雨》中直言安禄山为胡人,称其“积祖以来,为营州杂胡……母阿史德,为突厥觋者。”[9]348并将国家的兴衰直接归罪于安禄山这个外族的入侵。而迫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洪升在《长生殿》中对安禄山的描写虽未用到“胡”“虏”一类指称少数民族的词,但文中多处用到“腥羶”“腥臊”等轻辱夷狄的词侧面渲染安禄山的胡人身份,如《骂贼》齣的“恨只恨波腥羶莽将龙座渰”[7]129、《收京》齣的“腥羶满目狼藉”[7]158、《弹词》齣的“叹萧条也么哥,染腥臊也么哥。”[7]175《梧桐雨》和《长生殿》在创作过程中,前者直接,后者间接,都着意突出了安禄山的胡人身份,这是二人在易代之际,异族统治下,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和认同,而对安禄山这个外族入侵者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白朴和洪升民族情怀的集中体现。
(二)杨玉环的身份
白朴在《梧桐雨》中毫不掩饰杨玉环的身份,直言其与唐玄宗和安禄山的秽情秽事。在第一折中点明杨玉环寿王妃的身份以及唐玄宗的荒淫好色,称杨玉环“蒙恩选为寿王妃。”“圣上见妾貌类嫦娥,令高力士传旨度为女道士。”[9]350新旧《唐书》对此均有记载:“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10]3493先不论学界对寿王妃是否为杨玉环的争论,白朴此段记述毫无疑问是对正史的敷演。此外,白朴还揭露了杨妃和安禄山的奸情。“不期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好是烦恼人也。”[9]350句中“破绽”和“烦恼人”等语,均透露出二人确有不耻行径。杨玉环与安禄山暧昧之说肇始于笔记小说《国史补》:“安禄山恩宠寖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而贵妃常在坐……。”[11]18-19此外,姚汝能《禄山事迹》、汪畬《天宝乱杂西幸记》、王仁裕《天宝遗事》等材料中亦有杨玉环和安禄山私通的记录,这也对白朴的《梧桐雨》产生了影响。因此,杨玉环在《梧桐雨》中由寿王妃的身份层层深入,白朴借鉴正史和野史的材料,突出杨玉环、唐玄宗和安禄山之间不正当的情感纠葛。
洪升笔下的贵妃不同于白朴所刻画的淫秽形象。陈鸿称:“世所不闻者,予非开元遗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12]141洪升在撰写《长生殿》时借鉴了陈鸿运用材料的态度,不取无稽之谈,不知者不录。《长生殿》还兼采众家,以唐代《长恨歌》及其《传》为底本,其间多采《天宝遗事》、《杨妃全传》等材料进行渲染补充[7]《自序》《例言》,以表所由,对诸书有选择地进行取材。洪升在自序中称“史载杨妃多污秽事”“凡史家秽语,概削不书”。洪升在创作过程中,如“有涉秽迹者,绝不阑入”,将李杨故事中的污秽之事尽删。在《定情》篇中以唐明皇之口道出:“昨见宫女杨玉环……册为贵妃。”[7]《传情》4洪升一改《梧桐雨》中杨玉环寿王妃的身份,以“宫女”称之,因而李杨结合并未违背纲常伦理,也为唐玄宗纳其为妃正名,这是对杨玉环形象的美化。此外,洪升在《长生殿》中还对杨玉环进行了多角度的评价,一反女色祸国论,在《弹词》中借百姓之口道出:“休只埋怨贵妃娘娘。”洪升将在庙堂倾颓,天下大乱的原因归咎于“误任边将,委政权奸”[7]《弹词》174,在美化杨玉环的同时,也在为其进行辩护。
二、情感基调的异同
白朴和洪升二人备受战乱之苦,一生坎坷,半世漂泊。外族入侵,战火四起,正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正如李杨故事中马嵬兵变,前后的巨大落差形成了“乐极哀来”的情感倾向,正好与二人的人生经历契合。但在创作过程中,白朴和洪升又各有侧重,其情感指向又各具差异。
(一)情感倾向:“乐极哀来”
《梧桐雨》和《长生殿》都有“乐极哀来”的情感倾向,两剧均以马嵬兵变为转折,以七夕密誓,钗钿定情之乐衬马嵬惊变,贵妃殒命之哀,以设宴饮、食荔枝、舞霓裳的纵情之乐衬家国沦落,盛极而衰之哀。这种“乐极哀来”的情感倾向恰与白朴和洪升的个人经历相似。他们早年生活都十分优渥,据曾永义考证,洪升为南宋忠宣公洪浩后裔[13]3,家族显赫,经济富厚;《金史·白华传》中称白朴的父亲白华为金朝贞祐三年(1215)年进士,并受到金朝统治者重用,初任应奉翰林文字,后又担任枢密院经历官等职务,显贵一时。但外族侵入后,二人都饱受动乱之祸、流离之悲。白朴曾感慨道:“念一身九患,天教寂寞,百年孤愤,日就衰残。”(《沁园春》)洪升也道:“须臾故国生荒草,坟第朱门宾客少。”(《王孙行》)在二人的诗歌中都有对家国身世的悲叹,道尽了国破家亡后浓郁的哀愁之感。
白朴“幼经丧乱,仓皇失母”[6]206,其后“流离窜逐,父子相失”[6]207。白朴一直寄居于元好问家中,元好问为其父好友,待之如亲子,“遗山教之成人,始归其家。”经历了国家沦亡、战乱流离,白朴不仅有一腔山川满目的亡国之叹,胸中还压制着满怀郁郁不乐的出世之情,于是他恣意形骸,适意生活,其晚年更是“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6]207壮志消磨,豪情难留,白朴只能与好友谈终日,寄情于山川、沉溺于诗酒,以此度日。
洪升生于清军攻陷杭州时,其母黄氏为躲避清兵,藏身于一位费姓田妇家中,洪升正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出生的。康熙十一年,洪升遭“家难”,与父母分居而住,其后又经家族沦落。洪升感慨道:“国殇与家难,一夜百端忧。”(《一夜》)[8]51在风雨飘摇中,半圮的旧巢还未重建,新祸再次降临,康熙十八年,父亲旧案被翻,虽然最后大赦天下,但家族已然破落。遭遇家国之难,洪升流露出漂泊之感,“故国仍羁客,新年入旧愁。”(《除夕泊舟北郭》)[8]49洪升晚年因《长生殿》之祸,在党争的漩涡中遭排挤而退出政坛,被开除国子监学籍,自此仕途难求,功名无望。
从二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可知,“乐极哀来”不仅是白朴和洪升对李杨爱情和国家兴亡的慨叹,更寄寓了他们对个人经历的唏嘘。早年富贵与晚景凄凉,满腔壮志与黑暗现实,都被二人熔铸在乐的虚幻与哀的本质中。
(二)情感指向:“个人命运”与“人间真情”
《梧桐雨》和《长生殿》在结局上存在着差异。两剧均以“乐聚”“悲离”的情节结构展开李杨的爱情故事。《梧桐雨》以悲离作结,雨滴梧桐,幻梦终醒,在一片哀声中戛然而止,为悲剧的氛围助恨添愁。洪升则对这样的结局“作数日恶。”对此历来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便是洪升为作品中的悲剧场面和悲剧命运所感染,心情悲苦,不能快说[14]83。因此,洪升的《长生殿》在定情、埋玉的情节后,又加悔过团圆。可见《梧桐雨》的悲剧艺术给读者带来的情感效果。洪升在《长生殿》中一改《梧桐雨》的悲剧结局,“嘉其败而能悔”,让李杨结以仙世重圆。《梧桐雨》和《长生殿》一悲离一团圆的结局也造成两剧情感指向的差异。
《梧桐雨》悲剧的结局凸显出个人命运的无可奈何。大权在握的唐明皇在命运地操纵下走向悲剧,贵妃之死,大唐之衰,都是他个人无法改变的。在第三折中,兵至马嵬,六军哗变,陈玄礼诛国忠、杀贵妃,面对“主弱臣强”“军随印转”的情况,唐明皇的言辞也由命令变为乞求,将其色厉内荏,不能自我控制命运的无奈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高力士道与陈玄礼休没高下,岂可教妃子受刑罚!……总便有万千不是,看寡人也合饶过他,一地胡拿。”[9]358唐玄宗的语气由开始的强硬,到后来已然带有商量、妥协的意味。他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救不了贵妃,挽回不了江山,只道:“没乱杀,怎救拔!没奈何,怎留他!”[9]359悲剧的结局更能展现唐明皇贵为天子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操控的无奈,将《梧桐雨》的深层情感指向了个人与命运的矛盾。
《长生殿》以重圆收场将李杨二人的真情展现地淋漓尽致。洪升《长生殿》的创作历经十馀载,三易其稿。他最初“感李白之遇”,以抒己情而作《沉香亭》;后又去李白之事,弃个人情感,加入政治现实,更名《舞霓裳》;最后“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进而创作了《长生殿》。[7]《自序》《例言》从借古人抒己情到对政治现实的揭露,都寄托着洪升的自我悲叹,而《长生殿》问世,则在自我悲叹的基础上着力表现“情”的内涵。“古今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7]《传概》1《长生殿》中“情”之一字的初步显露,体现在李杨二人生离死别的书写上,悲离的内容深化了李杨的真情,死别将李杨的真情升华为至死不渝的至情。“情”的终极展现在于李杨的悔过仙圆。“死而有知,情悔何及。”李杨二人的悔过是建立在“情”基础上,“情悔”是改变分离命运的契机。全剧以重圆作结,人间天上,再续尘缘,将《长生殿》中的“真情”推向极致。
三、结语
《梧桐雨》和《长生殿》在人物身份的书写和情感基调的侧重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异同之处。由于白朴和洪升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相似,两人在创作过程中具有趋同的创作心理,即外族统治下觉醒的民族意识及国家兴亡中产生的强烈情感落差。因此二人在创作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描写安禄山的胡人身份,突出“乐极哀来”的情感倾向,以此抒发自己的民族情怀和对当朝的不满,在对战乱的描写中寄寓身世。但是由于白朴和洪升异趣的创作意图,造成两人对前代素材的处理和情感指向上存在着差异。因此二人根据自己的意图,去粗取精选取材料,从不同身份的杨玉环着眼,塑造了一淫乐一纯美的贵妃形象;同时,二人在创作过程中建构了不同的情节结构,在一悲离一团圆的故事结局中,分别突出了命运的无奈和帝王家罕有的真情。总结可知,《梧桐雨》和《长生殿》在创作过程中形成人物身份和情感基调异同的原因在于趋同的创作心理和异趣的创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