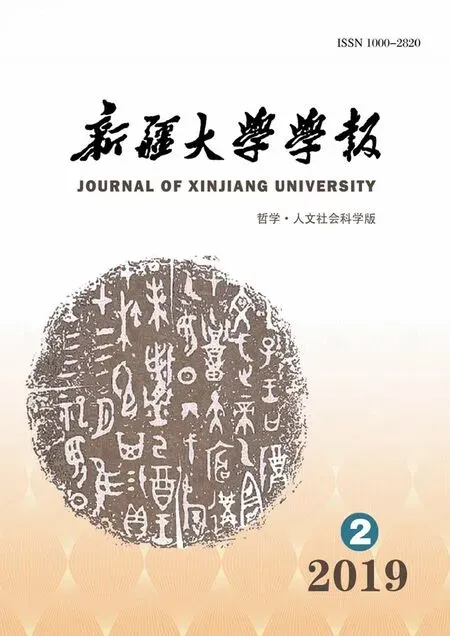黑水城文书所见北宋初年西行求法僧研究*
陈 玮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北宋初年,由于最高统治者身体力行的提倡、官府的支持,在后周显德二年(955)经受重创的佛教复兴,大批中原僧侣踏上漫漫沙碛,西行求法。记有中原僧侣前往天竺取经的黑水城智坚文书,作为反映北宋初年中西交通的重要材料,长期为学者所重视、研究。该文书公布之前,李正宇先生即考证其为敦煌文书,而非黑水城文书,认为智坚途经敦煌城西赛亭庄前往印度,此文书为其离开敦煌前对公验呈文的摘记。[1]3-11该文书公布之后,陈爱峰、杨富学先生指出该件文书反映了当时的中西佛教关系,智坚前往印度必经灵州道。[2]冯金忠先生经过仔细考证后,认为文书中所记朔方为夏州别称,智坚是经夏州前往印度。[3]948-956《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五卷收录有一件署名志坚的北宋初年敦煌文书,将该文书与黑水城智坚文书对比后,可知二者均为智坚在沙州所记,两件文书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笔者在参考李正宇、陈爱峰、杨富学、冯金忠三位先生论述的基础上,拟进一步讨论这一文书,挖掘其中的史料价值,现分述如下。
一、黑水城智坚文书与敦煌志坚文书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收录之俄B63 黑白图版《端拱二年智坚等往西天取菩萨戒记》[4]为俄藏黑水城汉文文书有明确纪年年代最早的一件,其内容多与大英图书馆藏S.3424V《端拱二年(989)僧志坚状》内容相符,S.3424V文书黑白图版收录于《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五卷[5],彩色图版收录在IDP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为便于讨论,现将两份文书按敦煌吐鲁番文书录文格式释录如下:
端拱二年智坚等往西天取菩萨戒记
1.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八日,其汉大师智坚往西天去,马都料
2.赛亭壮宿一夜,其廿日发去。其大师智坚俗姓董,其汉宋国人
3.是也,年可廿四岁。其缘从大师二人。其法达大师,俗姓张
4.其朔方人是也,年可三十七岁。其法诠大师,俗姓阳,年可廿八岁,朔方人是
5.也。端供(拱)二年岁次己丑八月十九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僧智坚记。
端拱二年往西天取菩萨戒兼传授菩萨戒僧志坚状
1.往西天取菩萨戒兼传授菩萨戒僧志坚敬劝
2.受戒弟子每日早起,夜头二时,行道烧香,净水养供,咒香偈云
1.3 统计学分析 用SPSS22.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戒香空香惠香解脱香解脱知见云台遍法界
4.供养十方无量佛供养十方无量法供养十方无量僧遍开
中略
106.斋了后念佛回施
107.端拱二年九月十六日往西天取菩萨戒兼传授菩萨
108.戒僧志坚状
109.难忍能忍是名为忍
110.是人能忍能忍是人
111.非人不忍不忍非人
将两份文书进行比对,不难发现前者所记智坚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前往西天取菩萨戒,后者所记志坚也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前往西天取菩萨戒,智通志,智坚无疑即志坚。两份文书的落款人均为一人,说明两份文书同出于一地。荣新江先生曾指出《俄藏敦煌文献》中混入大量黑水城汉文文书[6],而俄B63文书正好相反,应为混入《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敦煌汉文文书。由于智坚与志坚为同一人,为便于行文,以下迳称为智坚。
从俄B63 文书可知智坚于端拱二年(989)八月十八日启程前往西天取经。根据S.3424V 文书,他于本年九月十六日出现于沙州,为该州一佛教信徒授菩萨戒。这样智坚从启程地到沙州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S.383《西天路竟》云:“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7]从《西天路竟》可知从灵州到沙州需用时三十一日。智坚从启程地到沙州所用时间正好与《西天路竟》所记灵州到沙州时间相符,可见智坚的启程地应在灵州。实为敦煌文书的俄B63号文书记有智坚的两位随行僧人为朔方人,而敦煌文书中的朔方即指灵州。如S.2059《摩顶支天菩萨咒灵验记》云张俅“因游紫塞,于灵□□□□□内见此经,便于白绢上写得其咒,发心顶戴□□□载。……其日冒风步行,出朔方北碾门”[8]。灵□即灵州,与朔方同时出现于文书,可见二者同义。P.2741《于阗使臣奏稿》亦记有“住于灵州朔方的中国使臣宋尚书”[9]。将灵州、朔方并置。冯金忠先生认为俄B63 文书中的朔方为夏州,但无论是敦煌文书中的朔方还是宋史史籍所记朔方,均指灵州。以宋史史籍而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云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以右卫大将军侯赟知灵州。赟既至,按视蕃落,犒以牛酒,戎人悦服,部内甚治。在朔方凡十年”[10]512。又卷四二记参知政事李至向宋太宗上疏云:“今灵州不可坚守,万口同议,非臣独然……我民庶完葺,圣德广被,流沙、葱岭皆为内地,何止朔方一郡哉。”[10]895卷五十记知制诰杨亿向宋真宗上疏云:“今灵州是赫连昌地,后魏置州,盖朔方之故墟,匈奴之旧壤。”[10]1095可见在宋人眼中灵州即朔方。
敦煌文书所记从灵州前往沙州的求法僧人除智坚外,还有后唐定州开元寺僧人归文。S.529文书中,《同光二年(924)五月定州开元寺参学比丘归文状》云归文“昨于五月中旬,以达灵州”[11]9。《定州开元寺僧归文启》云“昨于四月廿三日已达灵州,兼将缘身衣物,买得驼两头准备西登碛路”[11]13。北宋初年,前往天竺取经的僧侣多由灵州路经沙州。范成大《吴船录》卷上云:“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业预遣中……业自阶州出塞西行,由灵武、西凉、甘、肃、瓜、沙等州,入伊吴、高昌、焉耆、于阗、疏勒、大石诸国,度雪岭至布路州国。”[12]《宋会要辑稿·方域》云:“乾德四年,知西凉府折逋葛支上言:“有回鹘二百余人、汉僧六十余人自朔方路来,为部落劫略。僧云欲往天竺取经,并送达甘州讫。”[13]9704
俄B63 文书中的马都料塞亭壮,李正宇先生以为即敦煌城西赛亭庄[1]6-7。从俄B63 文书可知智坚于端拱二年(989)八月十八日启程前往西天取经,八月十九日在马都料塞亭壮过夜,八月二十日离开马都料塞亭开始西行。根据S.3424V 文书,他于近一个月后的九月十六日出现于敦煌。如果马都料塞亭壮为敦煌城西赛亭庄,那么智坚为何在八月二十日离开敦煌后,又于九月十六日再次现身于敦煌?此中原因殊难解释。因此,笔者以为马都料塞亭壮据智坚启程地来看当在灵州附近。冯金忠先生指出“马都料塞亭(壮),‘壮’字右下方有一墨点删去符,‘壮’疑为衍文”[3]949。如此则马都料塞亭壮实为马都料塞亭。
灵州在北宋初“西南至凉州九百里”[14]。智坚从灵州前往沙州必经凉州,其夜宿之马都料塞亭应在灵州西南。塞亭即亭塞,为边防士兵戍守之小据点。关于灵州之亭塞,知制诰杨亿曾向宋真宗谈到灵州“僻介西鄙,邈绝诸华,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10]卷50,1095。彷佛灵州没有亭塞。但实际上他所说的灵州缺乏亭塞是指灵州与其东南方环州之间的道路上缺乏亭塞。《武经总要·前集》云环州“北至洪德砦八十里,砦北即蕃界青冈峡、清远军、积石、浦洛河、耀德镇、清边砦、灵州共七程,沙渍无邮传,冬夏少水”[15]卷18,896。古时亭塞常常充作邮传或驿站。杨亿因参与北宋朝野关于弃守灵州的争论,所以谈到灵州缺乏亭塞,而北宋弃守灵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灵州与环州之间的运输军粮道路往往被李继迁的党项骑兵阻截。
智坚与其同伴两位灵州僧侣能从灵州顺利抵达沙州,主要在于当时灵州至沙州一线道路安谧。在五代时经常劫掠灵州道商旅与使节的党项部落,在宋初与北宋灵州当地官府关系融洽。如知灵州段思恭在任时“悉心绥抚,夷落安静,周访利病,多所条奏,甚得吏民之情”[10]卷10,232。知灵州侯赟在任时“按视蕃落,犒以牛酒,戎人悦服,部内甚治”[10]卷23,512。除太平兴国二年(977)“灵州、通远军诸蕃族剽略官纲”[10]卷18,417外,灵州党项在北宋初年基本上没有在灵州道上剽掠。此时已经叛宋的夏州党项李继迁部仍在夏州一带活动,兵锋未指灵州,直至淳化五年(994)。而凉州吐蕃六谷部与甘州回鹘也与北宋通好。乾德二年(964)凉州“蕃部首领数十人诣阙请帅”[10]卷5,136。乾德四年(965),凉州吐蕃六谷部首领折逋葛支遣人将西行汉僧护送至甘州。据前田正名先生统计,甘州回鹘在智坚西行前的建隆二年、乾德二年、三年、开宝元年、二年、太平兴国五年、太平兴国八年曾向北宋入贡。沙州也于建隆二年、三年、开宝贝元年、太平兴国三年、五年、八年向北宋入贡。[16]宋太祖还以沙州政首曹元忠为“检校太傅、兼中书令、使持节沙州诸军事、行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使、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勾营田押蕃落等使、加食邑五百户、实封二百户,散官、勋如故”。同时以曹元忠之子瓜州团练使曹延敬为“本州防御使、检校司徒、封谯县男,食邑三百户”[13]9835。曹元忠卒后,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980)追赠其为敦煌郡王,以其子曹延禄为“检校太保、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营田押蕃落等使”。以其弟“延晟为检校司徒、瓜州刺史、延瑞为归义军衙内都虞侯,母进封秦国太夫人,妻封陇西郡夫人”[13]9835-9836。可见智坚往西天求取菩萨戒所经之河西诸政权均与北宋联系密切,奉北宋为正朔,向慕华风。这也是智坚前往西天旅途通顺的重要原因。另外智坚在俄B63文书中称自己为汉宋国人,与上博48(28)《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后序“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方汉国鄜州观音院僧智严”[17]类似,说明此时宋人已将沙州视为化外之地。《宋会要辑稿》记有“朝廷以其地本羁縻,而世荷王命,岁修职贡”[13]9836,《武经总要·前集》则云“本朝太平兴国中,义潮孙延禄承袭,累封谯国王,讫今修贡”[5]卷19,959,亦显示宋廷对于沙州之态度较为疏离。
二、两件文书所记之菩萨戒
俄B63 文书与S.3424V 文书均记智坚为前往西天取菩萨戒兼传授菩萨戒之僧人。关于S.3424V 文书所记之菩萨戒,刘铭恕先生认为“唯从戒律文字之首尾两行观之,可以看出志坚的《菩萨戒》,是其本身取之于西天者”[18]48。荣新江先生则指出“志坚是律学沙门,因此在途中把其往西天取经所得之密教系统的菩萨戒法传授给沙州僧众”[19]。但将俄B63 文书与S.3424V 文书比对后,可知志坚(智坚)是从灵州出发抵达沙州,其西行求法之旅才刚刚开始,并没有取回菩萨戒,其在沙州所传授之菩萨戒当为中原旧有之菩萨戒。敦煌文书、宋史史籍及佛教史籍所记北宋前期西行取经僧事状,大都没有明载取经僧所取何经及取回何经。如P.2726取经僧法坚所撰发愿文云:“昨奉圣命,西放遣形,叼习未来梵夹,东化群生。”[20]《宋会要辑稿·蕃夷》云乾德四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书,许之。”[13]9825《佛祖统纪》云开宝四年“沙门建盛自西竺还,诣阙进贝叶梵经”[21]卷44,1022。又云太平兴国三年(978),“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孔雀尾拂”[21]卷44,1028。《宋会要辑稿·蕃夷》云太平兴国七年(982)“益州僧光远至天竺,以其王没徒曩表来上,并献佛顶印大小六、菩提贝多叶各七”[13]9825。《宋会要辑稿·蕃夷》云太平兴国八年(983)“僧法遇自天竺取经回”[13]9826。《佛祖统纪》则记“沙门法遇自西天来,献佛顶舍利、贝叶梵经”[21]卷44.1033。《宋会要辑稿·蕃夷》云“雍熙中,卫州僧辞澣自西域还,与胡僧密怛罗奉北印度王及金刚坐王那烂陀书来”[13]9826。《佛祖统纪》云淳化二年(991)“太原沙门重达自西天还,往反十年,进佛舍利、贝叶梵经”[1]卷44,1039。又云“宝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怀问同沙门得济、永定、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国还,进佛骨舍利、贝叶梵经、贝多子、菩提树叶、无忧树叶、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21]卷46,1071。这些记载均将取经僧所取之经及取回之经概括称为贝叶梵经,只有俄B63 文书与S.3424 文书明确提到智坚往西天所取为菩萨戒经。
菩萨戒是修习菩萨道者所遵持的大乘戒律,遵持此戒可证得无上佛果。《大般涅槃经》卷二八云:“若有受持菩萨戒者,当知是人得阿耨多罗三蔑三菩提,能见佛性、如来、涅槃。”[22]受菩萨戒者可获极道胜、发心胜、福田胜、功德胜、受罪轻微胜、处胎胜、神通胜、果报胜等八种殊胜功德。菩萨戒自南北朝以来流行于内地,迄至北宋初年仍十分兴盛,许多律师都参与为信徒授戒,如《宋高僧传》云释义寂在寿昌寺时,“诸官同命受菩萨戒。”“雍熙初永安县请于光明寺受戒。……四年临海、缙云、永康、东阳诸邑请其施戒。”[23]卷7,163汤用彤先生曾指出后周世宗灭佛“虽世宗未敕禁绝(《宋僧传》十七谓由道丕之力),然僧纪荡然,典籍丧失(宋初天台求经于日本,华严宗求经于高丽),五代之世实六朝以来佛法极衰之候也”[24]。时隔后周世宗灭佛三十五年的北宋端拱二年(989)正月所立《大宋重修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仍谈到后周世宗灭佛,可见其影响深远。智坚于端拱二年(989)八月启程西行取菩萨戒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另外宋初太祖、太宗复兴佛法,鼓励僧人西行求法,史载僧行勤等于雍熙四年前往西域后“自是往取经者颇众”[13]9997。这也是智坚踏上西行道路的一大原因。
敦煌文书中涉及北宋初年西游僧人于所经之处敬做佛事,特别是授戒当地信众的仅见S.6264《天兴十二年(961)南阎浮提大宝于阗国匝摩寺八关戒牒》与俄B63 文书、S.3424 文书。不同的是S.6264文书放映的是后晋时即出游西域的道圆于北宋初年返回内地途经于阗,为当地信徒曹清净授八关斋戒。俄B63文书、S.3424V文书放映的是从灵州出发西行,路经沙州的智坚为当地信徒授菩萨戒。据S.4915《雍熙四年(987)沙州三界寺授智惠花菩萨戒牒》、S.4482《雍熙四年(987)沙州灵图寺授惠圆菩萨戒牒》、S.3798《雍熙四年(987 五月二十六日沙州灵图寺授清净意菩萨戒牒)》,北宋初年为沙州当地佛教信徒授菩萨戒的主要是三界寺与灵图寺。作为外乡人的智坚初到沙州即为当地信徒授戒,可见其所受之推重。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八月,知开封府陈恕曾上言:“僧徒往西天取经者,诸蕃以其来自中国,必加礼奉,臣尝召问,皆罕习经艺而质状庸陋,或使外域反生轻慢。”[10]卷55,1210《宋会要辑稿》亦云:“此辈多学问生疏,受业年浅,状貌庸恶,且自汉入蕃,经由国土不少,见之必生鄙慢。”[13]9997可见按照官府标准许多西行僧人都不合格。但湛如法师曾指出“《梵网经》与《地持经》中规定,为他人作菩萨戒师者,必须持清净、善解律藏、精通三藏”[25]151。因此为沙州本地信徒授菩萨戒的智坚应为精行戒严、佛学渊博的法师。景祐二年(1035)九月,宋仁宗亲作《景祐天竺字源序》赐东京译经院,该序中提到北宋初年以来“取经僧得还者,自辞澣至栖秘,百三十八人”[21]卷46,1071。在这一百三十八人中不知是否有智坚及其随行的两名灵州僧侣。另外不仅沙州的普通信众礼敬从中原而来的西行僧侣,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归义军节度使对这些僧侣也多有礼遇。如至道元年(995)被宋廷遣往天竺取经的道猷,其在灵图寺寄住时曾向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请求开释违律的当地僧人,“足见道猷之非凡并敦煌曹氏族对于中原僧侣之敬重”[18]50。对于东来之印度僧侣,曹氏亦颇为礼遇,如北天竺国法贤自其本国前往中原时,“至燉煌,其王固留不遣数月”[13]9999。
随从智坚西行的两位灵州僧人也值得注意。灵州自唐至五代,高僧大德辈出,在唐有释辩才、释无漏、释增忍,在后唐有释无迹,后晋有释道舟,其中释无漏法体至北宋初年仍不崩坏。灵州寺院众多,唐有法华道场、下院、龙兴寺白草院、广福寺、龙兴寺孔雀王院、城南念定院、永兴寺,其中广福寺至后唐时仍存。灵州地方长官朔方军节度使极为礼遇本地的高僧大德,如自唐末至后唐世袭朔方军节度使的韩氏家族就“对于本府的管内的名僧大德给予相当的关照和尊崇”[26]235。灵州的僧侣对韩氏也非常敬重,敦煌所出朔方节度使韩逊生祠堂碑残卷即云:“今朔方之牧守将吏耆艾淄黄列状,以帅臣韩□善政来上请□□塑像而生事之。”[27]“朔方节度幕府人员亦有礼佛弘法的诸多活动”[26]235,在敦煌文书中多有体现。灵州本地的汉人百姓和蕃部部落也崇信佛教、礼敬高僧。后唐同光三年(925)释无迹寂灭时,“筋骨如生,风神若在,蕃汉之人观礼称叹”[23]卷30,752-753。道周登坛讲经时,灵州本地“道俗峰屯,檀施山积”。“至于番落,无不祇畏。”[23]卷23,597释增忍在贺兰山结庐精修时,“羌胡之族,竞臻供献酥酪”[23]卷26,667。这些高僧中,释辩才“追远之荣,声闻塞外”[23]卷16,388。增忍弟子无辙寂灭后被朔方军节度使韩逊“录遗迹奏闻,太祖敕致谥曰法空,别赐紫方袍,塞垣荣之”[23]卷26,668。灵州百姓还参与营建寺庙,如释道舟“乃率信士造永兴寺”[23]卷23,596。值得注意的是释无迹任灵州广福寺主持时,“塞垣间求戒者必请为力生焉”[23]卷30,752。可见唐末五代时灵州一带菩萨戒十分流行。北宋初年,灵州佛教气氛仍然十分浓厚,《大宋僧史略》卷上云:“今夏台灵武,每年二月八日,僧载(一作戴)夹紵佛像,侍从围绕,幡盖歌乐引导,谓之巡城。以城市行市为限,百姓赖其消灾也。”[28]加之河西诸政权入贡僧侣、西域印度东来僧侣汇聚于此,北宋初年的灵州堪称梵音渺渺的佛教都市。在这种背景下两位灵州僧人随从智坚西行,其立志求法之决心当不难想象。
关于S.3424V 文书的主体内容,湛如法师认为涉及斋会仪轨,指出文书末尾的“斋了后念佛回施”说明“斋会发展到宋代之时,于斋会又增添了念佛回向的方式作为斋会的结束”[25]318。文书行文谈到受菩萨戒弟子须“行道烧香,净水养供”“念本师阿阇梨诸佛菩萨名号,手抱香炉到佛像前请云”。“每日早起,夜头佛前手执香炉,请佛降赴道场,证明忏悔。请佛之时一心专注想念。”智坚指出“儿(尔)欲受斋,须先脱鞋受净水果报,示复如是。”受菩萨戒弟子还须念诵“净水偈云(一)切德水净诸尘,灌掌去垢心无染。”“将香炉度手过,作如来梵如来妙色身”。再祈愿“为今身斋主福受庇护敬礼,常住三宝”。在供养诸佛之后,受菩萨戒弟子须念诵施食偈,设施食与法界众生及鬼子母,“然后斋人自食”。随后还要施食与寺内病人、护迦蓝人、修功德人等五种人。智坚还指出“斋人须用澡豆净水漱口方可成斋”①智坚S.3424V《端拱二年(989)僧志坚状》,http://idp.nlc.gov.cn/,访问日期2012年2月15日。。可见该文书确为智坚在给沙州佛教信徒授菩萨戒后,为信徒受斋所作之仪轨文。仪轨文谈到持斋弟子需敬礼本师释迦牟尼佛、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普贤菩萨、兜率天宫慈氏菩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侯世菩萨摩诃萨。北宋初年沙州本地寺院的授菩萨戒牒一般以阿弥陀佛为壇头和尚,释迦牟尼为羯磨阿阇梨,弥勒尊佛为教授师,十方诸佛为证戒师、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与沙州本地菩萨戒牒相比,S.3424V仪轨文没有谈到礼敬阿弥陀佛、弥勒佛,可见当时在中原流行之菩萨戒与沙州之菩萨戒已有所不同。另外仪轨文要求受菩萨戒弟子大量念诵真言、陀罗尼,如普贤菩萨灭罪真言、如来灭轻罪真言、三身真言、普礼十方诸佛菩萨真言、本师释迦牟尼佛真言、慈氏真言、水真言、发遣鬼神真言。这些真言均有助于受斋人被佛法护持,“持此真言者无有罪不灭兼转女或男身”②智坚S.3424V《端拱二年(989)僧志坚状》,http://idp.nlc.gov.cn/,访问日期2012年2月15日。。这些真言和施食偈以及请佛降临道场都说明智坚所作之设斋仪轨融入了许多密宗元素。
三、结 语
综上所述,北宋端拱二年(989)西行求法僧人智坚路经沙州,在这里留下了一份旅程手记和斋戒仪轨文。20 世纪初,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在敦煌获得智坚的旅程手记。由于一些原因,该手记被俄国早期整理者编入黑水城藏品,在中国出版时又被编入《俄藏黑水城文献》。智坚所作斋戒仪轨文亦于20 世纪初被斯坦因发现,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智坚所撰旅程手记详细记载了他的启程时间、地点、身份和随从人员,将手记与斋戒仪轨文对比,可知智坚从灵州出发,经一月始抵沙州。他初抵沙州即为当地佛教徒礼遇,被邀请授菩萨戒,在授戒之后又为该佛教徒作设斋仪轨文。从仪轨文行文来看,中原之菩萨戒与沙州之菩萨戒略有不同,而且智坚将大量密咒与密宗仪轨融入斋文,使该斋文区别于传统斋文,富于密宗特色。智坚所撰旅程手记和斋戒仪轨文的被发现,印证了北宋初年丝绸之路东段灵州道的畅通与安谧;说明北宋初年中原佛教复兴后,内地僧侣积极参与西行求法,也反映了沙州与中原地区的佛教交流及中原佛教对沙州民众的深刻影响。